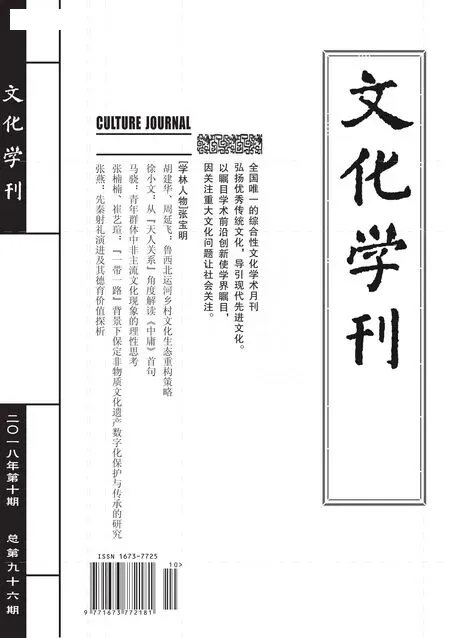从“天人关系”角度解读《中庸》首句
徐小文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一、《中庸》及中国哲学
《中庸》言简义丰,将此前中国哲学史上至此为止出现的思想凝聚在一起并加以超越,以至更深远,达到新高度。《中庸》篇幅虽短,却自有高度。朱熹曾评价说《中庸》“文字相当整齐,字字相对”,可以说,《中庸》是对此前哲学发展的一个总结。
《中庸》首章从“天”出发来讲性命之学,后由“天道”下贯至“人事”,这条路是中国哲学核心问题“天人之学”的一贯之路。子思从存在论角度去谈“天”,赋予其形上意义的哲学根据,如刘咸炘在《<中庸>述义》中道:“道本于天而备于人,子思详言人与天地合一之理,而特命之曰中庸。至中而后人道悉准乎天,至庸而后天道即在于人。”子思将人与天地合一之理称为中庸,此即为天人合一之理。故此,“中庸”概念打通了天人关系,使得天人问题成为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上的许多问题都是该问题的变形,多可还原至此。当然,对于这一部分的详细分析与论证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将以《中庸》首句为例,进行详尽的义理上的阐发。
然而自宋代起直至现代尤其是新儒学家,受现代性思维的影响,着重以“心性之学”来阐释《中庸》文本,甚至有学者包括冯友兰、徐复观等认为《中庸》应分为上下两篇。他们认为由于《中庸》上篇极其深奥精微,下篇非常具体,故上篇是形而上学,下篇是人伦日用,这正是受了现代性思想影响,认为经验的事实和抽象的义理是可分离的两方面的事,亦即形上应与形下分开。这一点在牟宗三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本就可以是宇宙之理,天理是为我们人发明的,这反而颠倒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让天理去符合人这一主体,这无疑是受到了西方主体性哲学如康德哲学的影响。[1]
然而中国哲学本就是一个贯通为一的整体,根本不可分。早在宋朝时,朱熹就提出过“致广大而尽精微”,形上即是形下,形下就是形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日常人伦和天道天理是一致的,中间没有缝隙。且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应是超越时代的,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必须面对并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为何,是改变世界、为所欲为还是超越自己的有限性。故现代性所导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在于人们不愿意去面对并思考这些问题,只愿思考常识性思维下的问题,因此,也就难以理解为何古人将举手投足、洒扫应对也当作圣人之道了。故此,《中庸》确实是一部贯通形上形下的哲学经典,二程亦有言为证,如程伊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此处的“六合”指的正是整个宇宙,由此可见,《中庸》从“天道”开始,散处于万物中而又皆归于“天道”,天人合一,极具辩证性。
故而本文将致力于从“天人关系”角度来解析《中庸》的首句,以此为切口窥探《中庸》的哲学义理,并反思现代性带给中国哲学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从天人之学出发来阐释首句;第二部分对于首句在首章及全书的地位及作用加以论述,以此来窥见《中庸》整体的系统性;第三部分重点阐发《中庸》首句体现出的天人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性,并反思现代性给中国哲学带来的灾难。
当然,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同西方的形而上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形而上学规定有二:一是研究作为存在者存在尤其是关于存在者必然和本质的学说;二是研究最高存在者的学说。由此,西方更多是一种将天人相分离的静态的认识论,而中国并非像西方那样以一个至高的超越者,如上帝来做一个认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初始者,中国形上学中的“天”和“道”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创生秩序,且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中国哲学并不否认事物的规定性和稳定性,但却认为事物的规定性正是在宇宙万物各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中产生的,人为干扰秩序的结果最终会损害我们人自身,这正是中西的不同之处。如《周易》中讲“六位时成”,“时成”两字就说明宇宙万有的发生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动态的,因此,作为万物之始的“始”并非物理时间上的“始”,而是形上意义的“始”,这也就意味着“生”,亦即完成,既是生化,也是转化,是“死”的对立消化方面。这一点可以作为下文解释“性”字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哲学中天道与人事相统一的原因了。
二、天命之谓性
《中庸》首章三句的意义在于:明确表达了“天”的逻辑先在性和形而上学的绝对性。首句“天命之谓性”表明了天的绝对性及其对人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天命”之“命”一般都被训为“命令”之“命”或“令”。而“命令”含有上对下之义,且具有绝对性和必然性,意指必须去做,故“命”就是用来强调天的绝对性或决定性之义的,且不可违背,必须执行。
我们先来分析“天”。正如上文所说,这里的“天”含有“命令”的绝对义,故这个“天”并非西方的上帝,不可理解为现代自然意义上的物质之天。刘咸炘说:“盖所谓天地者,非谓此所代之苍然,乃知此大自然之形于神也。”这里“形于神”表明:此“形”为形式而非外在的形状,加入了阴阳消息的“动”,这里的“天”就是宇宙论意义上的天(universe)。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这样解释:“‘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以者用也,即用此阴阳五行之体也。”由此可见,船山认为体和用是必然联系、内在统一的。“天运而不息,只此是体,只此是用。”可见,船山所说的“体”并非固定的静止的实体(substance),而是通过“用”体现出的运行不息,而这个运行不息就表现为用,由此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不二得以明显体现。但二者又有分殊,“有形未有形,有象未有象,统谓之天;则健顺无体而非无体,五行有形而不穷于形也。”[2]这里的阴阳五行是象语言,五行虽以形现之,但不穷于形,故不可仅从知性思维的形上去理解,天是运作不息的,无体就是它自身的无体。杜维明在《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中也认为:“尽管天在儒家传统中不是一个人格的上帝或全能的创世主,但它并非没有超越的旨色。”[3]这里的“超越”是指在人之外,以人为内,故“天”在儒家传统中意味着在我们之上的东西。《国语》中所说的“绝地天通”也正是这个意思,确立了天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超越性。因此,《中庸》首句的“天”正是这种超越性的天,亦即与人相对的天,天的形上意义就是作为创生一切宇宙秩序、人伦纲常的终极根据。
然而,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对“天”的解释却略显含糊:“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4]在朱熹看来,天地只是一种化生万物的功能性概念。但这里的化生万物其实并非神学意义上的创造或者物理学意义上的产生,而是形上意义的生之本然,这个本然本身是“神”,故朱熹所理解的“天”既可指本然之天,也可指实体的天,由此为宋儒讲“天即理”提供了可能。而船山则很明确,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明确说:“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圣贤之教,下以别人与物,而上不欲人之躐等于天。”这里,船山明确区分了天道与人道,人道虽不离天道,但二者仍有分殊,人道不可僭越于天道。故此,“天”具有绝对性与超越性。
“性”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复杂且重要的概念。现代人尤其是心性哲学家通常将“性”理解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本性(human nature),这显然是受现代性思维影响而发生的偏颇。可这里的“性”显然并非如此,由于上面还有“天命”,天所命之谓性,故这里的“性”并非自然意义上的天然本性,亦非局限于人心。天命于人的并不一定是人性,也可以是其他东西。
自古以来言“性”者大体有两个路径:一是从生说性,一是即心言性。“性”的原义是“生”,关于这一点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辩证》中遍取各经文来证明此,许多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因此,中国古代论人和物之性,通常有两义:一是就人和物当前之存在引申其自身既起之存在;二是就人和物自身之存在引申其他事物之存在为性。[5]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很显然,先天的性是相近的,后天的“习”即生活方式造成了人的行为的不同。从性的先天源头上来看,性是同出一源的。在孟子同告子关于“性”的争论中,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这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人的基本欲望是天生的,都反映了这个“生”字。孟子也承认自然天性的“生”,“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这表面上是指五官的生理功能,但“性也,有命焉”表明了这里不是纯粹在讲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从哲学概念上讲的,认为“性”是一个先天规定的东西。孟子其实是要用“性也”来对前面的生理上的器官作一个哲学的系统性的说明,而非简单的生理学的描述,孟子讲性,其实也就是在讲“生”字的本来意思。中国哲学里讲“天性”,或指自然本能,或指天生之潜能。后者在《庄子·马蹄篇》中有所表现,庄子将潜能称为人的常性,人就是他的常性。由此可见,天所命的“性”的确应是从“生”上来讲的,那种即心言性的心性之学会使“性”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天人学的背景消失,转而变成一个人类中心论的概念。
心性之学意义上的“性”只局限于人性,但是,“性”并非专门属人的概念,物也有其性。《周易正义·无妄》中“物皆不敢妄,然后万物乃得各全其性”[6],亦即所有事物都要有其性,且不可违背天,方能得其性,故人有人性,物也有物性。《尚书·洪范》中:“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7]这些都是自然的潜能,如木就叫做曲直,金意味可改变,土即可做庄稼。但这里五行所说的物质都只是在象的意义上说的,并非真正的物质,如金可改变是指所有的事物能自我产生,进行变更。故本性不等于自然之性(nature),而是指事物潜在的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往往与人有关。故“土爰稼穑”意味着根据土的本性潜在地有事物可能归为物之常性,即使是人和事物发生关系后产生的可能性也可看作物之常性。换而言之,土的本性包括其对人而言的可能性,即它和人发生关系后产生的可能性。故此,若如上文所述,同心性学家一样将性仅理解为人性,那静物之性又如何谈起?故朱子在《中庸章句》中清楚地将性注释为:“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和物都各有自己所禀受的天赋之理,而“以为健顺五常之德”,这就是性。船山亦说:“天命之人者为人之性,天命之物者为物之性。今即不可言物无性而非天所命。”故万物各有其性,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且皆为天所命,故性命论不可简单地等同于人性论。
总结而言,《中庸》之前,古人皆从“生”来言性,即心言性是后人从心性论的立场对孟子性论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中庸》对性的言说基本是延续了前人即生言性的传统,并予以发展。《中庸》中有许多宇宙论思想,而宇宙论有许多成物的东西,故即生言性使境界大开,从事物的生长讲起,于是就有了天地的概念,直接与天地打通,由此具有宇宙论与存在论的创生之意,“性”字也就成了一个宇宙论或形而上的概念,这一点在《中庸》后来提出的“诚”这一重要概念中也得以体现。“诚”在古汉语中通假“成”字,有成长、完成之义,子思将“生”和“诚”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从而使性有了成己成物的意识。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论述:“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本,故曰成之者性也。”[8]可见事物不但在生和成上重要,生成后的区别也很重要,使大千世界的区别性和多样性得以呈现的正是“成”。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限于天”表明通过天产生事物而使事物有规定性。事物有一个纯有,于是生和成便出现了,“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在戴震看来,道和性是一回事,这一点子思也如是看待,表现在《中庸》首章第二句“率性之谓道”中。“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这里是倒过来讲的,对于事物的限定最初就有了,由此只需讲“分”。分是把事物区分开,指对事物的限定,然后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过渡到具体的事情上,亦即形上与形下的关系。故“性”本身是规定性的起始和原则,而它又限于天,由此各事物根据天对性的规定性而有其同一性(identity),形成于“一”,从而“各成其性也”。而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分,事物才能成为统一的东西,才能“成其之性”,因此,性是构成事物特殊性的根本。“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性是人和事物都有的,而事物之所以称其所是,根本是从阴阳五行之运行而来,此即是天道。只是戴震要求我们也要注重事物的特殊性,而这特殊性的产生正是来自于性之本,使潜在成为现实。也正是在看到这样的分殊关系后,戴震才说虽然人和物各有其性,但事物本身并无善恶,讲性善性恶只与人有关。从戴震的论述中也可看到,朱子对“性”的注释仍存在偏差,他将“性”释为“理”,虽彰显了“性”本来具有的本质规定义即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但同时也失去了性由天道而来并产生万事万物的生化活动义。故天所命为性,此性既是人性,亦是物性,因此,《中庸》首章首句并非专门针对人而言,而是在言天,是在宇宙论、存在论意义上而言绝对性与超越性。如果像心性论哲学家那样,仅从心而做人性论的论述,那么《中庸》首章三句的后两句也就显得无所谓而失去意义了。
三、《中庸》首句的地位及作用
《中庸》首句的地位及作用其实已暗含在上文的阐释中。从首句在《中庸》首章三句中的地位及内在逻辑来看,首章三句是整个圆融的从天道到人事的纵向的天人关系的逻辑结构,而《中庸》首章在全书中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首章三句中。因此,首句作为在对天的绝对性及其对人无可置疑的权威性的阐明,为下文从天道过渡到人事做了很好的铺垫,也是对此前中国哲学的总结,由此足可见首句的重要性。
由首句到首章三句,可看出中国古人将人成德的过程看得十分困难。但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近代甚至现代,对此过程及困难予以重视的人越来越少,反而将人的主体性提得很高。由此,通过上文对船山释义的分析,可见船山的解释并非主体性的,他的重心在道而非圣人,最后回到天道,以道作为圣人立教的前提,同时也作为圣人立教的目的,这是一个螺旋性的循环。“道”通过圣人传给普通人,很显然这是纵向而非横向的关系。虽然船山在上述这段话中并未明确说圣人效法天道,但是圣人只是在效法的这层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故此,《中庸》首章中前两句都是针对天道而言的,遵行天道,禀受天所命之性;第三句则开始由天道降到人事,谈如何达到天道、寻其本性,此即“教”。由此,这样一个由天及人的纵向的天人关系架构就很圆融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其间的逻辑甚是严密。而此间的逻辑与发展,皆是从这首句“天命之谓性”而衍发,所以首句是《中庸》全书的立根之本,也是中国哲学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
四、《中庸》首句体现的“天人关系”及对现代性偏差的反思
由上述论述可以很明晰地看到,《中庸》首句完全是在“天人关系”的纵向逻辑架构及语境下谈的。本部分将再做进一步剖析。
“天”在中国哲学的概念中有“无限”的涵义。人有生有死,但天是不老的。故“天”在中国哲学中肯定有“无限”的意思,但这个意思始终未被明确说出。由此,从纯粹的抽象哲学上讲,“天人关系”也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由于天道高高在上,故即便是圣人,最终只能做到敬侍天道,而不能就是天,因为还有“教”亦即效法,圣人只能力求做到与天相似,而不能代替天。
其实考察先秦两汉的经典著作不难发现,对于先秦两汉的哲学家而言,人象天法地禀受天命是很自然的事,也是中国形上学的基本原则。《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就是效法天地的明确表现。孔子承袭尧舜文武,他们都是象天法地,前人如此做,孔子自然也就效法天地,然后立教。由此可见,古人皆以效法天地为人间正道。对此,《易经》也有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天地变化”表明圣人效法天地不单是静态的,还包括整个宇宙的大化,亦即那种天地的无限的根本的自由。如果说“天尊地卑”表示的是静态,那么“天地变化”就是给人类的自由留下了一个无限的天地,使得人有可能像天地一样自由。但这个变化是一个宇宙大化,而非个人去“以干天和”的胡作非为,故圣人只能“象之”“则之”,“象”和“则”都表明圣人所有的行为都是以天为依归的。
同样,在《礼记·哀公问》中,哀公问孔子君子为什么要“贵天道”,孔子答道:“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9]“不已”亦即无限,“贵其不已”表明由于君子有限,而天道无限,而任何有限的事物都无法解答存在的意义(significance)在何处这个问题,故君子必须“贵天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无限并非一个量的概念,而是意义的源泉,是给我们人定位的坐标。后面几个“是天道也”其实呈递进关系,从时空到无限到生存的条件最后再到意义的发现。总结而言,君子贵天道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首先,看到日月东西等宇宙自然现象永远如此循环不已。古人对于自然无限运作的原因很好奇,于是天道作为规则性概念出现。其次,“不闭其久”表示天道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最后,没有无限的外在时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故“无为而物成”,这要比从一个具体的事物产生另一个具体的事物更为关键,无限的天道是产生一切事物的条件,绝对的时空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故此“已成而明”,不仅要“成”,还要有意义,亦即要在天道的背景下。由此,对古人而言,天地生人,天道指点人道,这是顺理成章、合乎情理的。孔子在答鲁哀公问教时也是这个道理,“教”到了极致就是“道”,“教”的最终目的是懂得天道,圣人之所以能自行其是,恰恰在于他们能不违天道,能法天,而儒家的天道论意义就在于此。
在整个前现代中国,“人法天”并非一个疑惑和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到了宋明以后,论述的中心地才有所偏离,但要注意的是偏离并不等于完全放弃。但是,在西方现代性思想进入后,人们将“天”自然化为一个自然物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这对人而言是可怕的,故启蒙思想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极大,把握自然规律并利用之彻底征服摆布天、操控天的思想成为时下流行的思想。因此,如果中国人要进一步反思自己的传统,那么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近代以后我们如此大规模地接受西方的这种思想,接受那种常识性思维方式,将天看作物理的客观的自然的对象,而古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必须反思古人要求人效法天,效法的究竟是什么。效法的其实并非是无所不能,而是因为天代表了一种绝对的、没有商量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同时对我们人以及整个自然都既有意义又有规范性,故我们要效法天。所以我们一定要跳脱现代性的逻辑去理解古人的思想。一些新儒家学者用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自然会产生许多问题。
汉代董仲舒也对“人法天”的思想做了很多阐述。“人法天”的思想其实从《尚书》时就有了,董仲舒只是对这个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因为他认为人事的一切制度都是由法天而来的,“礼者,继天地、体阴阳”[10]。《左传》中赵简与子大叔关于礼的对话也体现了这一思想:“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1]这也是从天经地义和法天层面上来讲的。但是把“礼”仅解释为制度和行为规范显然是非常表面的,故董仲舒从哲学层面上来解释“礼”。“法天”并非说看见了征兆后就简单地照着做,“继天地”是要将礼看作是天地中一个有机的成分,天地所谓的整个运作并非指人与天是分开的,而是指礼就是天地运作的一部分。这里就有“天人关系”,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礼”是其中的一部分。“体阴阳”中“阴阳”并非静态的东西,这表明事物包括整个宇宙万有的任何变化运动,归根到底是阴阳在起作用,虽然这种起作用并非一种方式。而正是因为能“体阴阳”,故“礼”是一个活动的而非静态的东西。可见古人的表达方式并非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那样,用概念性的语言(discursive language)来表达,而是用一种象语言使其自身具有独特的特点。但是这个传统特点在晚清就被切断了,故现代人不知如何讲象语言,而是完全从概念性语言上去理解古人象语言的表达方式,可这完全是两套语言的叙述系统。
人如果不能“法天则地”,就不能“王天下”。故“三代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正是在这里,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套自由的理论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然而为什么“不则天”就不能“至王”呢?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讲:“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12]一个“祖”字表明天是所有事物的始基(origin,Grund),故天是一个哲学概念。“无所殊”表明天本身并无区分,包括其在后来发展出的所有千变万化,但在最初的始基那里你是看不出的,事物的最终根据即在此。“建”“经”“和”“成”暗示天并非西方所讲的那样是静态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动态的功能,当然这种动态也并非17至18世纪所讲的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机械的动,它就是“动”,就是一个产生万物的“生”的功能,且这个功能是在告诉你要把万有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可以像西方那样说天是在做先定和谐的工作,但基督教的先定和谐并未突出在一个不断的运行过程中来规定和谐,而是在上帝创世纪时这个世界就已经和谐了,这是静态的。而中国古代讲的天是要“建日月风雨”的,日月风雨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运作才能“和之”。事物为什么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而非机械的外在事物的堆砌?因为天使得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当我们说一个事物有其整体时,我们其实是在说这个事物有其意义,而具体的事物并非一个整体。天形成一个整体(“和”)和一个完成(“成”)表明天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的物质,它还是一个构成差异、构成万有事物的和谐和完成事物等许多复杂功能的宇宙大化,这才是“动”,才是阴阳消息所指。因此,“法天”不是说去效法某个具体物,因为圣人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建日月以和之”,他们只能做到知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以和之,以及推动事物的完成而不要横加干涉,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但是“法天而立道”并不等于简单地按照道理去做事,“法天”是指掌握了这个道理后,自己去立道,因此,具体如何做就是圣人的事情了。故人并非是完全听任天道摆布的傀儡,人还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圣人的作用也就得以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也是承认主体性的,但是这个主体性并非绝对的,因为天是无私的,天最大的德就在于普爱而无私。故圣人效仿天也应去包容一切,热爱一切。这也是一种象思维,以天来隐喻人,使人得到启示,知道应当怎么做,这就是“法天”。这正是我们在现代性影响下,被常识性思维侵蚀所遗忘的。
五、结语
《中庸》首句是在天人关系的语境下来谈的,它揭示了天的绝对性及其对人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同后面两句共同奠定了中国形上学或者说天人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形上学的成败得失基本上可以以这个格局为枢轴来衡量。但它的意义绝不仅局限于历史的过去,即使是对于当代的形而上学乃至一般的哲学思考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涉及的“天”“命”“性”等都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因此,要更好地理解《中庸》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与反思,需要怀有中国哲学史的全局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