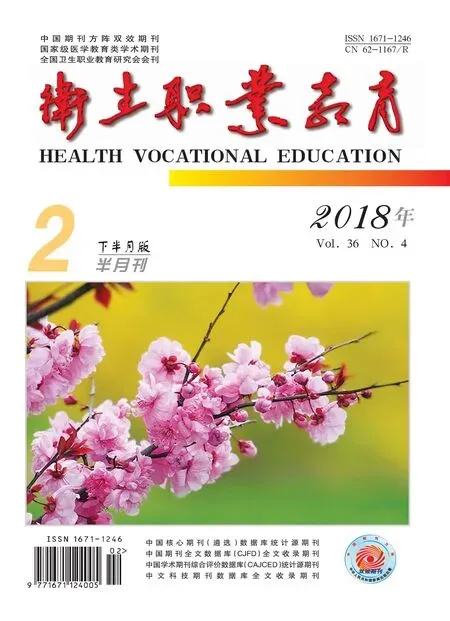传统医德思想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四个维度
汪小莎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在当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医学模式深层转变、医疗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国民对健康生活的关注度、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各界对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素质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多元社会思潮的涤荡冲击,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升级,医学人文关怀缺失,医学物化现象凸显,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呈现出实用性、功利性、现实性等显著特点。如何溯本清源,引导在校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摆在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 传统医德思想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意义
1.1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传统医德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古代医家防病治病的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铺就了医家行医济世的道德轨迹,形成了博爱济世、勤勉慎独、大医精诚、仁爱友善的价值理念,这些思想精华为古代医者研习医术、行医治病、救济众生确立了行为准则,成为照亮医学事业前行的智慧之源和宝贵财富。汲取传统医德的思想精华并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是医学院校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自觉,也是增强医学生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合理途径。
1.2 提升医疗卫生行业人才素质的根本诉求
党的十八大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医德、树良医”就是新时期医学院校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具体体现。2011年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上,把对医学人才的素质要求概括为“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丰富的人文素养、强烈的责任感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素质和专业水平,培养医德高尚、医技精湛的医疗卫生人才是高等医学院校的重大使命。医学生的道德品行、价值观念、职业态度、专业水平等不仅关系到自身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质量,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通过传统医德思想的浸润加强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提升医学生道德素质的根本诉求。
1.3 加快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然趋势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学生是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接班人,肩负着服务人类生命健康的神圣职责,医学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对医务工作者道德素质与期望高于一般社会从业人员。习近平总书记用“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16个字,概括了广大卫生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内涵。医学生肩负防病治病、维系健康的使命,他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重视中医药经典医籍研读及挖掘,不断弘扬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以“仁和精诚”为核心的传统医德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人文情怀、哲学思辨、伦理道德体现了中华文化深邃的哲学思想、深切的人文关怀、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为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精神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涵养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也是加快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应有之义。
2 传统医德思想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四个维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医德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充盈着博爱济世、勤勉慎独、大医精诚、仁爱友善等丰富的思想精髓,体现了“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观。传统医德推崇“仁、和、精、诚”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目标,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诉求,彼此渗透,在内容上有高度的契合性,在本质上有密切的关联性。
2.1 以传统医德思想之“仁爱济世”的责任意识培养医学生爱国为民的人文情怀
传统医德汲取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仁”,把“行仁”作为行医第一准则,“医者仁心”强调医者对生命的关怀与照护,行医应心怀仁慈、博爱施众。医者之“仁”首先要有“仁德”,“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1]。其次要有“仁心”,医者应以仁心为主宰,依据仁心去行医施治。正如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首要便提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再次要有“仁爱”,正如唐代药药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记载,“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强调医家对病患之痛苦应心怀慈悲,诚心救治。由“仁爱”进而“济世”,古代医者把“济世活人”当成至高的人生追求,《回春录序》提到“医者,生人之术也”,《万病回春》提到“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医圣张仲景抒发“进则救世,退则救民”的旷世箴言,北宋范仲淹确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人生志向,彰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定位为“以济世利天下”的壮志豪情。自古以来,中国医家就恪守“生人之术”的职业抱负和“济命扶危”的人生信仰,主张医者以仁爱之心救治病人,并通过治病救人,撒播仁爱之心,惠及大众苍生,从而家庭亲睦、人伦有序、社会安定。清代名医徐大椿指出“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探讨治病之法与治国之术的相通之处。医学“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医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自乡而国,罔不获济”。将医国与医人相提并论,认为治国与治病相通,医国与医人相互吻合,这些均体现了古代医家济世经邦的责任意识和治国理政的政治抱负。
医乃仁人之术,人道主义精神始终是医学的灵魂所在。《中国医师宣言》第一条承诺就是:平等仁爱。强调医者的责任是:坚守医乃仁术的宗旨和济世救人的使命。关爱病人,无论病人民族、性别、贫富、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都要一视同仁。古代医者以人为本,仁慈至善的伦理思想,济世医国、拯救苍生的人格理想对于培养当代医学生爱国为民的人文精神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一是树立医者仁心、推己及人的人本思想;二是确立投身医学、救死扶伤的责任意识;三是激发爱国爱民、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
2.2 以传统医德思想之“勤勉慎独”的习医态度提振医学生敬业精术的职业精神
传统医学文化以中华文化为母体,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形成了人命至重、生命至上、敬畏生命、珍重生命的生命观。我国最早的医书典籍《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一语道出生命之可贵;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记载:“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太平经》里提到,“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也”;吕坤的《呻吟语》提到,“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开篇提到,“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而“人所贵者,盖贵于生”,这些都深刻地阐释了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以生命的一维性和不可逆性,凸显了生命的神圣和尊贵。“医乃仁术”是传统医学文化对医术的高度概括,因此对行医之人而言,仅有“仁德、仁心、仁爱”的医德不足以济世医国,还必须具有济世活人的“医术”。古人云: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明代徐春甫认为,“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清代吴尚先在《理渝外治方要略言》中强调,“医以济世,术贵乎精”。医术的精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学习积累,需要广泛涉猎各类知识,深入探究医学原理,需要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求学态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医学理论广博深奥,医学知识学无止境,正如《备急千金要方》里强调的,欲为良医,不仅要懂医道,还“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老》《庄》,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才能达到“诊必副矣”的效果。此外,行医必须谨慎诊治,多方思考,正如晋代王叔和在《脉经序》中提到“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对于危重病人,医生不可“自虑吉凶”,需要出诊时不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人以病请,即夜数十起弗辞”,风雨无阻、一心赴救。
“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勤奋学习是医学生投身医学、立志从医的永恒主题,也是将来服务人民、报效社会的重要基础。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行医必须德高技精,德艺双馨,才能“以其术仁其民”。在现代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下,继承和发扬古代医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博学,“不舍昼夜,一心赴救”的敬业,“朝勤夕思,手不释卷”的勤勉,“留心研究,究其微赜”的细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谦逊,对提振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有着极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
2.3 以传统医德思想之“求实不欺”的职业操守培养医学生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行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儒家倡导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原则,古人强调“一诺千金”“言而有信”,认为“诚信”乃一个人的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医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医学科学推崇的“严谨为学”,医学价值倡导的“济世救人”[2-3],决定了医学不仅要“精于专业”,更要“诚于品德”,医德与医术并举,两者互为促进、相得益彰[4]。关于医德,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主要论述了“精”和“诚”两个问题。“精”是指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诚”是指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诚实无伪,诚心不欺。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与病患感同身受,心怀“大慈恻隐”的同情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行医之人只有“精”与“诚”兼备,“仁”与“术”结合,方能成为良医。周敦颐《周子全书·通书·诚下》提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认为“诚”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基础,是德行之首,亦是人的各种善行的根源。诚信乃修身之本,为医之诚一是表现在不欺人。《备急千金要方》告诫行医之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活幼新书》有言“为医先要去贪嗔,用药但凭真实心”,医家在诊脉、辨病、用药各个环节必须实事求是,杜绝任何形式的欺骗,做到“寸心不欺”。医生对于患者,应当“利心淡,仁心现”,一心救治,无所欲求。二是表现在不自欺。程钟龄《医学心悟》中指出,“医家误,强识病,病不识时莫强识,谦恭退位让贤能”。医者诊治要关注现实,反对迷信,做到“治病必求于本”“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候,观其志意,与其产病能。拘于鬼神者,不可以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以言至巧”。医者要“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做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明代医家李梃把从学医到行医所有的品德都用“不欺”予以归纳,以示“不欺”的重要性,并强调“欺则良知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日昌”。
“病家求医,寄以生死”,这是患者对医者的高度信任,医者的诚信,表现在为人处事、治学诊疗等方面应心怀至诚,言行诚谨,不诳语妄言、弄虚作假。诚信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点,医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关系到良好医疗环境的形成,关系到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5]。“言必行,行必果”,古代医家对待患者诚实无伪、求实不欺的医德医风,对引导医学生自觉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把诚实守信作为高尚的人生追求将起到重要的表率与激励作用。
2.4 以传统医德思想之“天人合一”的人际理念铸就医学生谦恭友善的处世态度
“礼之用,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人际交往中,中华民族向来提倡以和为贵,强调“与人为善,善莫大焉”的友善精神,推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处世态度,人们普遍将“和谐”视为人际关系状况的最高境界。古代医者在处理自身与患者、同道、社会等方面的关系时的高风亮节体现了良好的医德修养,对指导医学生处理人际关系大有裨益[6]。第一,对医者自身而言,重视修己正身。如明代医生缪希雍在《本草经疏·祝医五则》记载,“凡作医师,宜先虚怀,灵知空洞,本无一物;苟执我见,便与物对;我见坚固,势必轻人”,强调接待病人时要态度随和,谦恭有礼,不可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柔和,无自妄尊”,表明身为医者,不可固执己见,要虚怀若谷,虚心向他人学习借鉴。第二,对待病人,强调普同一等。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强调医生对待患者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大医精诚》记载,“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更是强调了医者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不得厚此薄彼,要平等相待,视病人为亲人。第三,对待同道,提倡尊重谦让。孙思邈认为,“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首戴面,而有自许之心,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明代医者龚廷贤对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医生有过深刻的揭露,“吾道中有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病,惟毁前医之过以骇病者”“同道虽有毫末之差,彼此亦当护庇,慎勿訾毁,斯不失忠厚之心也。戒之,戒之”,强调要防止“炫耀声名,訾毁诸医”。
“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历来倡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原则,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智慧。建立良好的人我关系,有助于诊疗过程中双方的良性互动、密切合作,因此,求同存异、宽和处世、谦恭友善是消融医患关系坚冰的不二法宝。古代医家在处理自身与患者、患者家属、同道关系时秉持谦虚礼让,为医学生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医学教育是医学职业的起点和基础,培养医学生崇德向善的职业素质是高等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7]。“仁和精诚”是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医学领域的集中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传统文化理想在当代社会的集中表达,继承和吸收传统医学文化的道德精髓,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和精神命脉的现实需要,是走出当前医学教育道德困境的有效途径,也是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代要求,对于提升医学生医德水平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王治民.历代医德论述选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2]韩喜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基本着力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1):6-8.
[3]俞嘉怡.树立医德与医术融合统一的医学教育观[J].教师教育研究,2014,26(2):50-55.
[4]顾云湘.儒医文化与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16(1):63-67.
[5]马艳艳.中医传统医德对护理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影响[J].医学与社会,2013,26(6):95-97.
[6]潘新丽.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0.
[7]田雅婷.敬佑生命,尊重医者[N].光明日报,201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