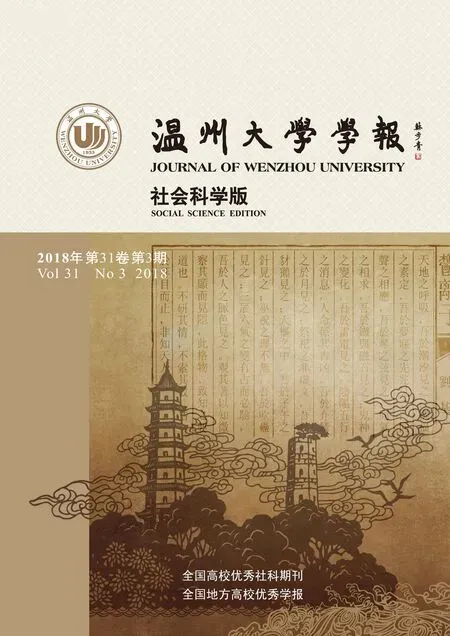疾病、记忆与艺术想象
—— 对读史铁生与普鲁斯特
胡 荣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先后以《作为隐喻的疾病》(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二文,尖锐地揭示出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等病症如何被历史地隐喻化并付诸“隐喻实践”的过程,她的初衷是为了说明:“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5。而她相隔11年的两次努力,正如其所自嘲的,无疑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却无奈的色彩——因为疾病从来不会“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即使清除种种隐喻性的道德评判和政治压迫,疾病的意义也绝不可能止步于身体这个单纯的生理机能体,它深入人们的意识,占领精神领域的要塞,甚至攫取患者的灵魂。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疾病对于人类肉体和心灵所发挥的影响力和改造力,都是难以估量和无法抹杀的,这种作用在天性敏感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试以普鲁斯特和史铁生两位作家为例,管窥疾病与文学创作、特别是创作心理之间的关系。
一、“无眠之夜”与“写作之夜”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一译《追寻逝去的时间》,以下简称《追忆》)的起首,以一个“不眠之夜”开始了长达7卷百万言的追思与回忆。在黑暗的温柔笼罩下,睡意朦胧的“我”在梦境和遐想间沉浮不定,此时,“记忆——不是有关我此刻所在的地方,而是我曾经在过的那些地方,以及我原本说不定会在的地方的记忆——向我而来,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把我拉出这片我无论如何独自挣脱不了的虚无的泥潭。”[2]7-8刹那间,“我”回到了童年时代,化身为那个在贡布雷度假时为等待母亲吻别而不肯入睡的孩子,“往日在贡布雷姑婆家,在巴尔贝克、巴黎、冬西埃尔、威尼斯,还有在别的地方的生活,”“那些地方和我在那儿认识的人,以及他们留给我的之中印象,或者人家对我讲起的有关他们的事情”[2]11,犹如万花筒中的影像般纷至沓来,直至终篇,贡布雷花园里为送客而拉响的铃声再次回响在“我”耳畔,“那么遥远然而又在我的心里”[3]350,那逝去的时光终于经“我”——追寻而重现。无眠之夜仍在继续,但它和“我”残留的生命一样,已接近尽头。
史铁生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开头,也意味深长地设置了一个“写作之夜”。某个秋夜,“我”在一座古园的树林里邂逅了两个天真的孩子(一男一女),随后又永久地“失散”了。在充满象征意趣的布景下,“我”进入了“写作之夜”[4]8-9:
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么?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往事,和故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他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
踽踽独行的人生旅途中,往事和故人,如落叶一般,都在“我”往昔的生命之风吹拂下,翩翩飘入艺术想象的“另一种明亮”;这些往事和故人,从未脱离作者自我的心魂轨迹:“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待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5]169-170小说通篇弥漫着浓厚的追忆与沉思的氛围。这样成熟而萧瑟的人生秋夜,史铁生静坐于轮椅的“写作之夜”,与普鲁斯特辗转于床榻的“无眠之夜”,传达了一种相通的人生境况和写作态度——疾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极其重大,可以从作家对待疾病的态度以及为何选择写作等方面来分析。
普鲁斯特 10岁时哮喘病发作,病情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日益加剧;此外,消化不良、皮肤过敏、畏寒、失眠等毛病也如影随行,让他难得一日闲适。35岁起,备受病痛折磨的他不得不杜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开始了足不出户的自我幽禁的生活,直至51岁病逝。这生命中的最后15年,也正是他呕心沥血、精雕细琢写作《追忆》的时期。哮喘虽不是致命的疾病,但过于敏感的气管极大地限制了普鲁斯特的行动自由,他向往旅行却不能如愿,一生涉足巴黎以外的地方屈指可数,常在家中以研读火车时刻表为乐;对花粉和病毒的防范亦使他失去了许多享受自然的机会,接触人群主要依靠小圈子的社交沙龙。在他生命的晚期,身体状况更为虚弱,终日门窗紧闭,身不离床,对朋友自称生活的常态是“在咖啡因、阿司匹林、哮喘之间苟延残喘,算起来七天中倒有六天是在生死间挣扎”[6]63,这种自诉虽不免夸张,但病痛(包括其异乎寻常的性取向带来的内心压抑)对他的持久折磨也可见一斑。不过,天性并不悲观的普鲁斯特竟然从病痛中悟出了一条生活真谛[6]67:
病痛让我们有机会凝神结想,学到不少东西,它使我们得以细细体察所经之事,若非患病我们对之也许根本不会留心。一到天黑倒头便睡、整夜酣眠如死猪的人,定然不知梦为何物,不惟不会有何了不得的发现,即对睡眠本身也无体察。他对他正在酣睡并不了然。轻微的失眠倒让我们领悟到睡眠之妙,如同于黑暗中投下一道光束。深究记忆现象,其意义并不仅在于求得准确无误的记忆。
由病痛推而广之——痛苦,其实是推动人们创造艺术、品味爱情、获知真理的动力。在《追忆》第二部“在少女们身旁”中,普鲁斯特借画家埃尔斯蒂尔之口,表述了智慧获得的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教诲传授而得,毫不费力;其二则得自亲身经历,充满错误和痛苦。第二种方式提炼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智慧[7]。在第七部即将结束全书之时,他再次重申[3]215-216:
想象、思考,其本身便可以成为绝妙的工具,但它们也可能失去活力。此时,痛苦便来启动它们。而那些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们则在只有这种时期我们才去的画室、我们内心的画室里为我们作出重复过那么多次的表演!这些时期仿佛是一幅图片,画着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痛苦。因为,它们也包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并且就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新的痛苦又冒了出来。就各种意义而言的新痛苦;也许是因为不可逆料的处境迫使我们进入与自我的更深层的接触。……一个人的形体再丑陋,也不可能爱而没有痛苦,也得经受磨难才能得知真理……幸福的岁月即是虚度的年华,我们等待痛苦,以便进行工作。
普鲁斯特创立了他的“痛苦哲学”,即正视痛苦,认识其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和驱动价值,从而超越一般性的肉体和精神的磨难,到达艺术和真理的彼岸。普鲁斯特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一认识,他从痛苦出发而最终消弭痛苦的努力集中体现在《追忆》的写作上。他之所以以写作了却余生,除了天赋的敏感心灵和自幼年起就朦胧怀有的文学梦想外,更重要的是,对他而言,写作“显示为一个寻求对于生活中的困境的可能的答案的过程”;由其个人的社会角色、身体状况和人格隐秘引发的“负罪感、窒息感、恐惧感和孤独感”,只有在写作中、在艺术创造中才能得到释放和解脱①参见:涂卫群.从普鲁斯特出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26。。通过写作,他希望揭示“真正的生活,最终被发现和澄明的生活,因而也是惟一充分经历的生活”,而这种写作,又是通过在回忆中想象和在想象中回忆,最终得以实现。
史铁生的病历有所不同。21岁时,他的人生轨迹被一个偶然宿命般地改变了。仅仅是一次调养不当就导致了双腿瘫痪;随后,急性肾损伤、尿毒症又接连袭来,史铁生自嘲其大半辈子以“生病”为职业。对于他来说,疾病是命运的一个空白启示,愤怒、苦涩、困惑、无奈、冥思,直至坦然承受。他没有殷实的家境和超脱的社会地位,又生活在一个视残疾为报废的时代,疾病给身心带来的苦痛几乎是令人绝望的。经历数次生死边缘的徘徊、追问和思考,史铁生就人生的意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过程说”,人生的过程即是“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的过程[5]21-22: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和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够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地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
在这一生存理念中,“痛苦”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著,它是“好运”的前提,是幸福的先决条件,不曾经历痛苦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这样,史铁生终于穿透了命运赋予的病痛的厚茧,俯瞰生命中不得不承受且必需承受的“痛苦”,和曾存在于另一时空的普鲁斯特一样,得出了化解苦难的药方——“审美的救助”,对他来说便是写作。为何要写作?他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尽一致的解答:“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8]217在这里,写作不妨可看作对“过程”质量的自我提升;将近十年后,他又说:“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5]168写作是一种逸出现实的努力,是一片自由梦想的天地,是受难心灵聊以为生的宿命安排。“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待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5]170以艺术之眼回顾人生、超越现实,这便是病痛和苦难所孕育出来的“写作之夜”。
二、记忆、印象和想象
无论是“无眠之夜”,还是“写作之夜”,两种意象都呈现出生命垂暮之时对于往昔的追怀。此时“记忆”成为一个关键词,那么,记忆是如何转化为艺术想象的呢?
《追忆》中,普鲁斯特采用了叙述与议论相间的意识流笔法,反复摹写时间与记忆的主题。他对记忆的认识,深受同时代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后者在 1896年出版的《材料与记忆》一书中提出,理论上独立存在两种不同的记忆。第一种记忆以“记忆-形象”的形式记录我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时间发生的全部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保留着每件事实、每个姿态的时间和地点。它不考虑实用性,只是出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是一种纯粹状态的记忆,一种真正的记忆,它与意识共同扩展,保留着我们的全部状态,并且将它们逐个排列起来,以便使它们在意识中产生。另一种记忆则仅仅是理智地结构起来的一整套机制,保证了对各种可能需求做出恰当的回应。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或者说,“过去”,就是被这两种极端的记忆形式储存起来了:第一种是个人的“记忆-形象”,它勾勒出全部过去事件的轮廓、色彩和在时间里的位置,完全是自发的;第二种形式是利用它的运动机制,依靠我们的意志,为努力所征服①参见: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65,72,133。。普鲁斯特显然对这种区分、尤其是“纯粹记忆”概念很感兴趣(柏格森的相关言论甚至出现在《追忆》第四部当中②参见: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M].许钧,杨松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0:374-375。)。试想,如果真的存在“纯粹记忆”,它包含了我们对于全部的过去经验的回忆、而且可能被我们的意识所激活的话,那将是多么奇妙呢。它意味着艺术家拥有一个采掘不尽的素材宝藏,而且就深埋于自身记忆的宝库之中!事实上,和对柏氏的其它哲学概念如“绵延”、“直觉”的吸收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种关于记忆的假想,并在创作中不断重申应排斥智力的(即有意识的)记忆,倡导纯粹的(即无意识的)记忆和知觉[9]:
对于智力,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了。我认为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的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到艺术的唯一内容。智力以过去时间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也未必就是那样东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件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这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招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它所隐藏于其中的对象——或称之为感觉,因为对象是通过感觉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很可能不再与之相遇。因此,我们一生中有许多时间可能就此永远不复再现。
他认为,在艺术创造中,才智(理性)无法产生那种“神秘的真实”——而艺术“甘美”的秘诀正在于此[3]206:
至于才智——即使是最卓越的才智——所稀疏采撷的真情实话,在它面前,昭然若揭,它们的意义可能十分重大;但是它们的轮廓不大柔和,它们比较平坦,由于要达到这些真实不用逾越什么深度,由于它们并不是再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们没有深度。有些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心中不再产生那种神秘的真实,从此时起,他们往往就凭着越来越有力的才智进行写作。鉴于这个原因,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比他们年轻时的作品更苍劲有力,然而它们失去了往日的甘美。
那种经过“再创造”的“神秘的真实”,就是在对象刺激下审美知觉引发的一系列“无意识”的记忆,它唤起一种“模糊而深刻的心灵状态”——因此,《追忆》中,“我”可以从玛德莱娜点心浸在椴花茶里的滋味中,“感受到一种美妙的愉悦”,瞬间回到童年的快乐时光;“我”可以在两块高低不平的阶梯上踏步时,猛然回味到曾被大院里的铺路石板绊过脚的熟悉感觉,又联想起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前的类似经历,顿时激动不已;在斯万就要放弃对奥黛特的爱情时,凡德伊乐曲中的一个乐句勾起了他们热恋中的欢乐的全部回忆,使他欲罢不能……“正如空间有几何学,时间也有心理学”[10],现实的时间是单向度的,而心理时间却不然,只需借助无意识的记忆,便可以往返回复,连通往昔与今日,找回逝水年华。艺术想象就存在于对这种无意识的记忆的捕捉当中,存在于这种浸透着生命的血肉体验的回忆和追思、创造和重构之中。
在写作生涯跨越 20年之时,对于任何作家(何况病患作家)都可能面临素材枯竭的困境,史铁生以“印象”为核心,提出了他的化解之术。《务虚笔记》开篇收尾时的一个悖论“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4]10可谓理解整部小说的一个关键。“印象”概念是与“真实”概念相伴而生的[4]10:
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做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琢我的印象。
而且,它们在雕琢我的印象时,顺便雕琢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印象。这些印象的累计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真实”缺席了,在艺术虚构的世界里无所谓“真实”,取而代之的是时隐时现的“印象”,构成并出自“我”的心魂的“印象”。《务虚笔记》中人物面目的有意混淆、叙事线索的蓄意重叠,以及笔法的刻意散漫和偶尔重复,都是为了营造这种记忆与印象交迭闪烁的境界。除了“印象”,“记忆”也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与“印象”的鲜活灵动、自由飘逸相比,它笨拙、僵死、黯然失色:
很多很多记忆都逃出了大脑,但它们变成印象却都住进了我的心灵。而且住进心灵的,并不比逃出大脑的少,因为它们在那儿编织雕铸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4]346。
往日并不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往日的喧嚣与骚动永远都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记忆,只是阶段性的僵死记录,而印象是对所有生命变动不居的理解和感悟。记忆只是大脑被动的存储,印象则是心灵仰望神秘时,对记忆的激活、重组和创造。记忆可以丢失,但印象却可使丢失的生命重新显现[5]36-37。
史铁生将“记忆”与“印象”分别归入大脑和心灵两块领地,前者是智力的,后者则与智力无涉,而与神秘、情感、创造等密切关联。他甚至比喻道:“记忆,所以是一个牢笼。印象是牢笼以外的天空。”[11]作家的“真世界”不在于智力性的记忆,而在于印象“对记忆的激活、重组和创造”,使“丢失的生命重新显现”。这样的认识,与普鲁斯特关于两种记忆的区分何其吻合!此处史铁生所称的“记忆”,即是第二种理智的有意识的记忆,而“印象”,其实就是第一种“纯粹记忆”,无意识的“保留着我们的全部状态”的记忆,能够诱使艺术想象力饱满迸发的力量和园地。史铁生还以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小点心的例子,证明“印象”的巨大效力人人皆可感之[5]37,他还没有意识到,在不同的时空下,他与普鲁斯特对于记忆与想象的理解,经历了不同的曲线,竟然最终趋向一致!这只是个巧合,还是蕴藏着某种必然的因素呢?我相信,是病患纠缠下、敏感心灵长年累月不懈的沉思、追忆与创造,牵引着他们不期而遇,虽然二者的风格不同,与普鲁斯特偏爱于以长篇累牍的形式、重现绵延不绝的往昔相比,史铁生更惯于运用思维之网,打捞某个片断,俘获一些“印象”。
此外,疾病对于两位作家写作的影响,在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方面也呈现出某种奇妙的一致。那就是母亲和(外)祖母的形象。在《追忆》中,“我”对异性的爱情(希尔贝特和阿尔贝蒂娜)始终充满了猜疑、误会和隔阂,相继随时间减弱而逝去。只有外祖母和母亲的关怀永远温暖、甜蜜、安全。尤其是外祖母,她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的作风和性格,不仅在母亲身上得到了继承,还深深感染了“我”,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塑造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外祖母和母亲共同演绎着母亲这一角色,她们之间的职责区分不甚清楚,基本上是重叠的;相比之下,外祖父、父亲、兄弟无足轻重,经常被忽略,造成无所谓存在的错觉。史铁生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最初的人生记忆中到处飘荡着奶奶的声音(《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母子关系是着力最多也是最主要的亲缘关系(《务虚笔记》),奶奶和母亲的形象贯穿我早年的回忆(《记忆与印象》)。奶奶的慈爱和母亲的坚忍庇佑着“我”的成长和成熟,而爷爷、姥爷、父亲不是“人形空白”(《一个人形空白》),就是轻描淡写、一闪而过;妻子呢,留给她的篇幅也相当有限。对于母亲和(外祖母)的终身依恋,是普鲁斯特和史铁生在写作中难以掩饰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形成不能不和他们遭受病患袭击的(青)少年时代相联系。两个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极为相似,母亲和(外)祖母悉心照顾敏感柔弱的儿(孙),无私奉献母性之爱,成为事实上的监护者(她们总是把更多的关怀放在那个最弱的孩子身上);同时,父亲和(外)祖父则与他较为疏离,甚至因为他成年后无法分担家庭责任而产生某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阿尼玛(anima,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意象)原型隐藏在母亲的统治力中,甚至会使儿子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恋[12]。只有当儿子的心理达到一定的成熟独立后才能摆脱这种依恋。但艺术家是个例外:“在创造性艺术家那里,个人原型依恋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并常常地回归到对母亲和姐妹的个人依恋去。‘女神’的替身形象表现了对母亲和女儿的‘伟大女性’的延续联结,它在一个男人的心灵中生活并活动。”①转引自:童庆炳.艺术与人类心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145。而当这名艺术家兼有幼年患病的经历、更为依赖母亲时,这种依恋显然会愈加强烈。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普鲁斯特和史铁生作品中的家庭性格角色分配,似乎也就豁然开朗了。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 //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2]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M].周克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M].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
[4]史铁生.务虚笔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5]史铁生.灵魂的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6]阿兰·德波顿.拥抱似水年华[M].余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上[M].李恒基,桂裕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499.
[8]史铁生.答自己问[M]// 史铁生.答自己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17.
[9]马塞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M].王道乾,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1.
[10]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六卷[M].刘方,陆秉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137.
[11]史铁生.记忆与印象[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63.
[12]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M]// 荣格.荣格文集.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