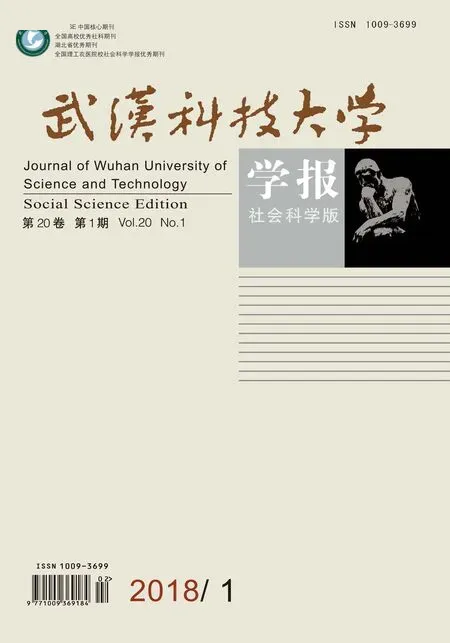“因信称义”与“因义离信”
——马丁·路德与现代伦理
何 怀 宏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2017年是马丁·路德所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年。宗教改革的一个精神主旨是要回归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原始基督教精神,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但其运动的一些结果则广泛深入地影响到了此后五百年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相对于耶元初的世界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各种条件和动机的推动和激荡下,无论如何,五百年之后的当今西方社会,反而是一个更加世俗、离信更远的社会*从16世纪始到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文化变迁,一个精彩的概述可参见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正是从宗教改革开始他的叙述的。。本文主要从伦理的观点来看这种演变,这自然要多方关涉伦理与精神信仰的内容和关系,但这里只是试图分析和比较这前后两端的两种主要观点,一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一是罗尔斯的“因义离信”*这是我个人相对于马丁·路德观点提出的一个说法,自然不可能全面地概括罗尔斯的思想。。它们在近代以来西方精神伦理的系谱上也比较趋于两端,由此或还可展示近代以来的一种思想趋势。
不过,如众所知,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虽然使用类似的词汇,马丁·路德与罗尔斯所说的“义”实际上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宗教的观点,或者说是从一种信仰的内部观察世界,包括观察人生和道德的观点;还有一种则是比较纯粹和独立的道德的观点,即从社会的观点,从各种信仰的外部来看待各种信仰与道德的关系。
具体来说,这里所说的“信”和“义”有不同的涵义:在马丁·路德那里,“信”就是对基督的“信”,“义”也是在上帝面前的“义”,终极意义都是指向得救和永生。但是,当马丁·路德强调“信”与“义”之别乃至对峙的时候,这时的“义”主要是指律法和善功,颇符合一般所说的“义”。如果再细分,这些“戒律”中有一部分是有关宗教的礼仪和禁忌,还有一部分则是有关道德的戒律和义务,而“善功”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高尚的行为,还有一部分则是基本的义务,自然,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都是后者。而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义”是独立的、道德的义,“信”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是指各种信仰,包括信仰一个超越存在的宗教信仰,也包括多神论与自然神论等,以及非宗教的、追求某些价值的信仰,罗尔斯理论中的“义”也主要是指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
所以,即便“因信称义”和“因义离信”两者的思想精神意蕴有许多不同,显然这两种观点又处在一种深刻的相互影响,即挑战和回应,同时也互相渗透和吸收的关系之中。由于使用同样的概念,即便是原本宗教的“信义”也可能被移用或挪用到世俗社会的领域,而各种不同的“信”也和这种一般道德的距离有远有近,或者有不同的认识和权重。“信”和“义”的内容和关系在这前后两端的两个思想家那里是如何引起和阐述的,呈现出一种怎样的交织,带来怎样的复杂性和问题,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在某种限度和范围内平衡、调适,这些就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一
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罗尔斯,他们这方面的思想最初都是从其个人生命的体验挣扎出来的,之后才转入比较系统的论述和论证。五百年前欧洲的精神生活氛围与今天大不一样,尤其那些执着于精神追求而又真诚和敏感的人们,常常被一种深沉的罪恶感笼罩,绝没有现代成功人士的那种志得意满或普通人的心安理得。于是,渴望得救和永生成为头等大事,即便王子贵胄,也常有遁入修院或自愿放弃所有财产而甘愿赤贫者。
马丁·路德在他的幼年常听母亲唱一首童谣:“谁也不爱我和你,皆因你我都有罪。”*参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本写于1937年的罗马的书,我认为是在精神上描述马丁·路德心路历程最好的著作之一。一种“古老的恐惧”可能从他幼年看见阴森森的矿井就开始了,但对世间成功的追求也还是有巨大的分量。马丁·路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但他的父亲也可以说是一个刻苦工作、自我奋斗的典型。新近出版的马丁·路德传记指出传主不仅不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子弟”,而且家境富裕*作者在书中第一章“超越神话”中依据2003年以来对路德家庭故居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动物骨殖、器皿、玩具等资料,认为他的家庭相当富裕;同时也指出,其父母对他也并非严苛到不近人情,虽有体罚,但也是当时常见的,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父子互相关爱。参见Eric Metaxas:Martin Luther:the man who rediscovered God and changed the world viking(Penguin Random House,2017.pp.10-14)。。但这种家境的改善可能正是其父辈从农民到矿工、矿主奋斗的结果。父亲还希望显露出才华的长子路德能够通过学习法律更上层楼。1501年,马丁·路德18岁时就读于埃尔福特大学,后来拿到了学士学位。但颖悟的路德自己遇到了一些震撼性的事件,如1503年复活节他邀约一个朋友去他家小住,早晨却看到朋友被窃贼杀害,躺在血泊中。尤为著名的一次事件是1505年夏天,马丁·路德在旷野遇到雷击,他当时就立下誓愿要当修士,7月进入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在那里,他极其严格地遵守隐修规则:夜工、斋戒和祈祷,忠诚于贞节、服从和守贫的愿望,恐惧着最后的审判。
我们谈到社会上弥漫的一种普遍的罪孽感,而这种罪孽感在马丁·路德那里又格外沉重,因为他比一般人更高、更加执著地追求天堂和永生。在修道院,他乐意承担最卑下的工作,祷告、禁食、鞭打自己,甚至超过修道院最严格院规的要求,这使他看起来形同一副骷髅,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他的斗室也不设暖气,经常彻夜不眠,偶然或在席子上睡一下。但是当他觉得自己稍稍接近圣洁的时候,又常常会为自己人性的欲念感到突然堕入深渊。精英毕竟是精英,马丁·路德放弃了父亲希望他学的法学,但很快就因自己的才华和苦行在宗教界崭露头角。他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还被委任为副主教,管辖11个修道院,但这自然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他的目标是得救和永生。他同时在修道院苦修和在维登堡大学任教讲授圣经。失望的肉体苦修和圣经的长期研修终于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转折。有一天,他在反复研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时,突然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充溢他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刹那间脱落,他领悟到“人得救乃不是靠善行,而仅仅是靠信心”。
对这一转变的准确时间还有不同看法,或许它不是那样突然顿悟的,或者说,这种顿悟也还是长期追求的一个结果,是为了一个精神目标而长期食不得味、寝不能安的一个结果。但无论如何,在马丁·路德34岁写出反对赎罪卷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他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人只能凭信称义的牢固信念。
在马丁·路德的思想中,“因信称义”的确具有根本的分量,这也是后来宗教改革派的一个精神基石*马丁·路德在《桌边谈话·论称义》中谈到:“这个论我们如何得救的信条,是整个基督教教义的要点。神学中的一切争论都必须以此为依归。以前众先知的工作大体都是为阐明这件事,他们对这个题目有时很为困惑。我们若以有恒的信心坚守这个信条,别的信条,如论三位一体等等的信条,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只有藉着基督才能得救,乃是上帝宣布的最清晰明确的信条。”参见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533页)。。我们简要地叙述了马丁·路德这一思想产生的过程,现在可以来察看一下他的阐发和论证方式。在广义的“论证”或者“说服”他人和社会的方式上,马丁·路德主要就是诉诸原原本本的圣经:他讲授圣经、翻译圣经、引证圣经,他希望人们都能看到他所看到的圣经的真正精神,上帝的真正涵义,但这种引证的确又需要细心的选择和阐释。发布《九十五条论纲》之前,他是对少数人讲授,而在这之后,他要对多数人说话,他要使心中领悟到的精神发散开去,新发明的印刷术和用德语翻译的圣经大大地帮助了他。
在传统社会中,引证不仅可以是一种论证方式,而且是一种能够对大众更起作用的说服方式——即它常常比理性的论证更为有效,虽然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经过时。引证最高的权威文本差不多一直是传统的论证方式,尤其是对多数人有效的一种论证方式,这甚至于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在宗教生活中还是能够经常看到。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尤其在改革派那里,对圣经原文的引证更是一种主要的论证方式。但对圣经,不仅会有理解的不同,其中的字句也有不少看上去不一致的地方,这样就还需要选择。即便是“唯独圣经”,在圣经中最为强调那些篇章、那些段落,也还涉及到一个选择性的问题。
马丁·路德一方面认为包括旧约在内的整个圣经都是神圣的。他在旧约序文中谈到:旧约既是新约的基础与证据,就不当受轻视,不要见怪旧约里所常用的简朴语言和故事,不管那些语言和故事是多么简朴,它们都是上帝的权威与智慧所产生出来的判断,正如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所说,这是那使一切聪明通达人都成了呆子,却向婴孩或愚钝人显示出来的圣经,但是,他自然更看重新约。比较两约,他说旧约主要是一部律法书,教导人们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并举出人们遵守或破坏这些律法的一些例证与故事。新约则主要是一部福音书,或说是恩言,教导人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遵行律法的能力。但圣经的整个精神都是从头至尾赞美信仰高于一切善功、律法和功德。
在新约中,马丁·路德认为约翰所写的福音书乃是那唯一的、亲切的、真实的主要福音,远超过其他三福音书之上,同样,圣保罗和圣彼得的书信也远超过马太、马可、路加。圣约翰的福音书和第一书,圣保罗的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以及圣彼得的前书,乃是把基督指示给每一个人的书。尤其是罗马书,在马丁·路德看来,这封书信实在是新约的主要部分与最纯粹的福音,它不仅值得每一个基督徒研读烂熟,而且值得他天天去全心揣摩,以它为日用的灵粮,因为它本身乃是一大光亮——这光亮差不多足够用来照明全部圣经。
马丁·路德觉得自己悟到了的真理要向尽可能多的人呈现,使这真理走向大众,就首先需要翻译,而且是普通人通过方言就能阅读的翻译。马丁·路德先是用德语迅速地翻译了新约,后又投入了对旧约的翻译*翻译有时是比著述更重要的工作。马丁·路德在匿居瓦尔堡时,三个月就将新约译成德文,于1522年出版。因旧约篇幅太大,所以他把它分成摩西的历史和律法书、其他历史书、先知书三部,陆续翻译出版。路德的全部德文圣经在1534年问世。,他在这方面所花的精力和心血不亚于他的著述。在马丁·路德之前的时代,甚至像路德这样的学者修士也不容易觅得全本圣经,看到的多是部分解说和语录,或者说即便找到原文的圣经,也没有本民族语言的圣经,而马丁·路德将其翻译为德文,使圣经能够为所有略通文墨的人都能够阅读——甚至能够通过朗读使不识字的人也能深受其感染。这样,它就将对社会的整个中下层发生影响,尤其对其中的具有宗教性的“会根人”发生影响。
在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广泛传播之后,也遇到了一些来自罗马教会人士对他译文准确性的批评,马丁·路德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翻译的辩驳和辩护的文章:《论翻译:一封公开信》。他认为翻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谁都能从事的工作,需要有一颗敬虔的心。他批评有的罗马教会人士一面抄袭和盗用他的德文译本,一面却攻击他的翻译,并带点讥讽地说“让他们翻译一本适合自己的好了;我祝他一路平安。”[1]533
马丁·路德在拉丁文言之外,用当时的地方口语开始翻译圣经有开拓之功,也是态度严谨和信实的,他谈到他为了一个词的翻译也常常“旬月踟蹰”。但他的确也在自己翻译的圣经中有的地方加入了自己解释的意思。他在译“罗马人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时,译成“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仅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即加上了原文没有的“仅”字,而且坚持不改。他为自己辩护说,这和德语的特点有关,如要翻译得清楚而有力,就得加上这个字。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和纯正的信仰有关,是符合圣经的精神以及早期教父们的解释的。他认为原文本身和圣保罗的意思都需要有这个字。在那一节,保罗论及基督教教义的要点,即我们因信基督称义,而非因遵行任何律法称义,并且他完全废弃一切行为,甚至说,律法虽是上帝的律法和道,但律法的行为并不能帮助我们称义。马丁·路德说:“我并非是惟一或首先说到仅因信称义道理的人。在我以前,有安波罗修,奥古斯丁和许多别人都如此说了。”[1]386他说他着重“仅因信称义”,并没有其他的理由,而只是要冒犯人、降低人,使他们知道,他们并不能因善行称义,而仅因基督的死和复活称义。唯独信仰,而决非任何行为,才能把握福音所传的死和复活。但马丁·路德并不是完全否定善行,或者将善行与恶行等同,他只是否定善行在“称义”或“得救”方面的意义,否定人仅仅靠自己的善行能够称义和得救。他说:“若他们不能因律法的善行称义,就更不能因恶行和无律法称义了!因此,人不能说,因为善行爱莫能助,所以恶行就能为助了;正如人不能说,因为太阳不能帮助一个瞎子看见,所以黑夜就能帮助他看见了。”[1]386
二
在圣经的最高权威之下,马丁·路德并不是不看重理性。1521年在面对高压的沃木斯会议上,他在最后陈辞中恳切地喊道:“我的良心,我的良心是为上帝的话所约束。除非有人能够根据圣经用理智的明晰论据来说服我,我不愿,亦不能取消前言。”[1]7所以,可以说他还是诉诸了某种范围内的理性,我们也可从理性的角度更仔细地考察马丁·路德对“因信称义”的详细阐述。
马丁·路德在《罗马书序言》的开始也表现出一种理性,甚至分析哲学家的态度。他说,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其中用字,知道圣保罗所用“律法”“罪”“恩”“信”“义”“肉体”“灵”等词语的意义何在[1]479。他在《加拉太书注释》中对一般的“义”的概念作了一个分类,认为义有各种各类。有一种义是属政治的,为世上的君王、哲学家和律师所处理;也有一种义是属礼仪的,为人的和教皇的遗传所教导。此外,另有一种义,称为律法或十条诫命的义,这是摩西所教的。但是,还有一种超乎这一切的义,那就是信的义或基督徒的义,这义我们必须从以上所说其他的义中分辨出来,因为其他的义与此义十分相反,这些义可以说都是上帝的恩赐,像我们所享有的其他善事一样。 这最优秀的义,即信的义,也即上帝藉基督在律法之外所归于我们的义,它既不是政治的义,也不是礼仪的义,也不是上帝的律法之义,也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且是与前面的义绝对相反的;那就是说,这义仅是被动的义,来自神的恩典的义,而前面所说的义乃都是自动的义,人主动而为的义。在这种最好的恩典的义中,我们不行什么,也不将什么给上帝,却只接受上帝在我们心里动工。这义我们不是遵行,而是容纳,不是具有,而是接受;父上帝藉耶稣基督白白地将这义赐给了我们[1]501。
马丁·路德认为: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这两个世界里的义其实有天壤之别。律法的义是属地的,涉及地上的事,我们用来行善。但是正如地上除非先从天上得着雨水,成为肥沃之地,否则就不能结实;同样,在我们的功德或善行之外,除非先靠基督徒的义成为义,那么我们靠律法的义即便行许多善事,还是等于没有行什么,虽遵守律法,还是等于没有遵守。但这种义是属天的、被动的;不是我们生来所有,而是从天领受的;是并非由我们赚得的,而是用信心把握的;靠此我们才能驾凌于一切律法和行为之上[1]504。
因此,马丁·路德说,如果我教训人说,人因遵守律法可在上帝面前称义,我就逸出了律法的范围,将自动和被动的两种义混乱了,而且是一个坏的逻辑家,因为我没有按正意分解。相反地,我若以律法和行为摆在旧人面前,而以赦罪的应许和上帝的怜悯摆在新人面前,我就是按正意分解了道。因为我们必须使肉体或旧人与律法和行为连结,使心灵或新人与上帝的应许和怜悯联系。因此当我看见一个人已经受够了伤痛,被律法压制,因罪恐惧,并且渴望安慰,我就应从他眼前撤去律法和自动的义,用福音将被动的义摆在他面前。因为这远超于人的力量和才能之上,甚至也超乎上帝的律法之上。固然世上万事最优秀的是律法,然而它不能平静一个不安的良心,反倒使这良心更加恐惧,直到绝望的地步,因为罪藉着律法就显出真是罪。因此,困恼不安的良心无法对抗绝望和永死,除非它把握着在基督里所应许白赐的恩典,即由这信而来的被动的义或基督徒的义。以上所言的确像是马丁·路德心路历程的夫子自况:他由在恐惧和罪恶感重压下的旧人变成了得到白白的恩典、满心喜悦的新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父让子来到了人间,并死而复活。从此人就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不受律法管辖。因为律法到基督为止,如保罗在以后所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徒的义属于新人,律法的义属于从血肉所生的旧人。
马丁·路德在《罗马书序言》中还进一步论述了信仰与律法的关系以及信仰的统摄力量。他分析道,纵使一个人因怕惩罚爱赏赐,就在表面的行为上遵守律法,可是这并不是出于内心或乐意或对律法的喜爱,而是出于不愿和强迫;如果没有律法,他就会宁愿别样行。可是在他内心深处是恨恶律法的。所以要认清楚,律法的行为和律法的完成乃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律法的行为乃是一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能力遵守律法的行为。但是,在这些行为之下,人心里既然仍旧存有对律法的嫌恶以及在遵守律法时所感觉到的强制,所以这些工作就都是白费而毫无价值的[1]480。这些话与两百多年后康德的观点看来,客观上构成一种对峙,康德在承认人的有限性方面也认为人履行义务是不可能不带有某种内心的强迫乃至于嫌恶的,但是,它认为这种出自纯粹义务心的强行是有价值的。而马丁·路德认为,如果人的心灵是用圣灵浇灌了的,那么他成全律法乃是用愉快和喜爱的心去遵行律法,而且,是不需要律法的强制而甘心过一种虔敬而善良的生活。圣经特别看到人的心,注意到一切罪的根基与源头,即人内心深处的不信。正如唯有信才能使人称义,才能带来圣灵,才能产生对于善良与永恒的工作的愉快;同样,唯有不信才使人犯罪,才使人放纵肉体,才产生对于坏的行为的爱好,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所经历的一样。 因此,基督把不信称作唯一的罪。这样说来,“义”便是这样的一种信,而称为“上帝的义”或“在上帝面前有效的义”;上帝因我们的中保基督的缘故而把它赏赐给人,并把它算为义。奥古斯丁认为义是内在的,但改革领袖们则不然,只是将其算作“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义务和律法。马丁·路德解释保罗在罗马人书第三章所说好像是因信废了律法,但保罗接着又说“断乎不是,我们因信更是坚固律法”,就是说,我们因信成全起律法。马丁·路德也承认,那最好的“义”也是隐藏在奥秘中的义,是世人所不知的,甚至基督徒也往往不完全了解它,且在受试探时很难把握它。
马丁·路德在《论善功》中也细致地论述了信仰与善功的关系*参见Martin Luther: Treatise on good works, regimen books and christian classics( Vision Press,2017)。。他认为善功主要是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摩西十诫,而凭这种信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生活,也都是善功。摩西十诫中前三条诫命是讲上帝与人的关系,即讲信仰,后七条戒律是讲人与人、人与邻舍的关系,这些戒律是以信仰为先导和依凭的。善功的本质其实是信仰,除了上帝所命令的以外没有善功。诸般善功以相信基督为第一,最高,最宝贵。马丁·路德甚至说在信仰里诸般行为一律平等,彼此相似;行为当中所有的区别都消失,不管它们是大,是小,是长,是短,是多,是少。因为行为之所以蒙悦纳,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信仰。除了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之外,无人能称义。没有信仰的行为不能使任何人在上帝面前称义。第一条诫规定我们心里对上帝的态度,第二条诫规定我们口中对上帝的言语,第三条诫规定我们行为上对上帝的态度,都在摩西的第一块和在右的法版书写着。当然,但愿我们也能够遵行第二块法版的七条诫,对邻舍运用信仰,正如在这头三条诫中是专在对上帝的行为上运用信仰一样。他谈到第四条戒律“顺服父母”在后面七条中是最重要的,他也谈到第五条诫“不可杀人”是对愤怒和报复说的。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他还不太能够想象20世纪以意识形态之名的大规模集体杀戮,还有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等等,也都须严格遵守。但是,他再次强调,一切善功都包括在信仰里。一切善功,不拘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美好,若没有信仰,就都是死的。虽然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说,一切信仰,若没有行为,也都是空的。
但我们的确看到了马丁·路德对一种道德底线的坚守,这尤其表现在他反对暴力迫害与杀戮上,他尤其反对对精神和知识的“异端”实行暴力。他自然是反对罗马教会对“异端”的迫害和烧死的,但他也反对改革派对“异端”的暴力——既包括对罗马教会人士、修士和修女的暴力,也包括对更为激进的精神和知识人士的暴力。他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 论基督教的改革》中写道:“我们当以著作去消灭异端,而不可用烧死的办法,因为古代教父即是这样做的。假如用火去消灭异端是一种学术,那么,绞刑吏便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博士了;我们也用不着再研究学术,谁有力量胜过别人,谁就可以把别人烧死了。”[1]146这道理也可以说是从“因信称义”中来的,如他在《论翻译》中也说,“既然我们证明惟独信仰而非任何行为,才能把握基督的死和复活,而且祂的死和复活又是我们的生命和义,那么他们何必如此诬控人为异端分子,如此烧死人呢?”[1]386
马丁·路德如何看待以前论述义务和行为的思想家,包括看待那些德性高尚的非基督徒呢?他在《罗马人书注释和加拉太书注释序言》中谈到,固然有许多人,例如犹太人和异端派,为上帝的缘故,把属世的福分看为粪土,乐意丢弃它们;还有希腊的先贤和哲学家,认为这些人虽然在人面前不夸称他们的义,而以爱好道德和智慧的心来行义,可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禁不住要自满,且自夸是聪明、公义、良善的,至少是在他们的意念中禁不住要如此,而且连这种人也是寥若晨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清楚述说了人由行为而来的义。然而,上帝的判断却与此迥异,因为照着这判断,称义是在行为之前,而善行是从称义产生出来的。基督徒的义也不是如经院学派所想象的,是人本性的固有素质。律法的行为乃是全部律法的行为,无论是司法的、礼仪的、道德的。若道德律的行为不能使人称义,那么属于礼仪律的行为如割礼就更不能使人称义。律法的行为可以行在称义之前或其后。在称义之前,甚至在异教徒中有许多善人如阿里斯底德(Aristides)、 法比乌(Fabius)等,也守了律法,行了善事。在称义之后,彼得、保罗和其他基督徒都遵行律法,然而他们也不能因此称义。不杀人、不犯奸淫等等,无论是按天性,或人的力量,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的恩赐和权能而行出来,都不能使人称义。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人必须首先将我们的义和智慧废掉,并将它们从我们的心里和我们自满的意念里除去。基督愿望我们将心倒空,否认我们自己的义和智慧,好叫我们不因罪而惧怕以致得不着恩典,也不因德行而追求荣耀和虚空的满足[1]494-495。
马丁·路德在大学讲授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对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也相当熟谙,应该说他是知道和能够使用理性的论证方式的。但正如前述,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精神氛围,就是人们对于得救的渴望非常迫切,而又相当绝望,即处在一种最大的渴望却遭受重压的境遇之中。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那时一种相当普遍的对摆脱罪孽、得到永生的强烈渴望,而当时的许多人感到即便是苦苦修行,还是很难看到个人被拯救的曙光。人按照教会与教义的要求履行各种艰苦的磨炼:戒律、善功、苦修,但人性的欲望还是时时冒头,而惩罚的压力又通过种种教义,乃至时刻窥伺在旁的“魔鬼”的诱惑暗影使自身感到几乎万难摆脱。马丁·路德立志也是够高,苦行也是甚严,但还是感到几乎无望摆脱“罪性”,甚至觉得自己处在濒死的边缘,在这样一种时刻,让思想冲破藩篱的路在何方?也许只能通过唯一的和完全的投身信仰才有希望。
所以,马丁·路德终究觉得教义与苦修救不了他,理性和学问更救不了他,而他偶然接触到全本圣经却为他打开了一扇大门,通过对圣经中一些篇章和话语的独特理解,他感到突然窥见了基督的真义,那就是《罗马书》中的“义人因信而得生”。与其无望地在行为中挣扎,不如全身心地投入信仰,委身上帝。他自己也曾购买过赎罪券,但现在他感到那些还在狂热的气氛中购买的人们是走在了一条错误的路上,而他们的错误还是足以造成利用这一错误而获得大量利益的人的腐败,人们以为自己是在敬拜上帝,用金钱补赎罪过,但接受这些的却还是人,是那些自身已经不怎么在乎信仰,但却对俗世的权钱名充满兴趣,在道德的深渊中堕落更甚的人们。所以,他对售卖赎罪券奋力发出了自己的一击,他自己也绝没想到这一击会有如此的分量,不仅造成了罗马教会的大塌陷和基督教会的大分裂,而且在精神上、思想上影响巨大和长远。
三
近代以来的人们离开信仰、放弃宗教有多种途径和程度。有通过怀疑的人文主义的,有诉诸新的社会理想的,有的甚至是纯然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它们有的是完全否定信仰,也否定道义,或者说是“背信弃义”。但我们这里考虑的不是近代以来种种认为信仰与道德皆不可信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而是一种仍然强调甚至极其强调道德,但却与信仰拉开距离的路径,即“因义离信”。
的确,马丁·路德之后,有一些人因为对“因信称义”的强调而更加贴近了信仰。如一百多年后的帕斯卡尔,他深受在天主教中具有新教思想倾向的冉森派的影响,逐步放弃了人文和科学的研究与活动,一次次在精神上更深地皈依上帝,最后进了修道院,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归宿。但这往往是一些小教派和个人的努力,而时代的大潮流却看来是越来越依赖于理性。“因义离信”的倾向可以说是从两百多年后的康德那里就发端了或者说发展了的,而且他将其做成了一个全面的哲学理论体系。他赋予道德以一种高度的独立性,即使道德相当独立于政治,也相当独立于宗教。上帝的位置还保留着,但被推到了远方,作为一种德福一致的前提和保证起作用,而道德的根基和标准则被置于理性之上,从理性的论证演绎而来。康德反对以任何目的和结果,包括以神圣的目的来解释道德,以作为道德的根据,他认为道德就是道德,义务就是义务,它们自有其理性的根据,从而开启了一种不再是以价值、善为中心,而是以义务、正当为中心的现代伦理学中的义务论传统。
后来的许多理性道德理论中甚至就完全没有了上帝的地位。到20世纪初叶,韦伯可以说通过诉诸思想学术的“价值中立”和强调政治行动领域的“责任伦理”而反对“信念伦理”,继续了“因义离信”这一路向。韦伯不是不清楚,甚至不是不向往那种信义紧密结合的精神之火,但是,面对现代社会,他觉得只能强调两者的分离,尤其在政治领域要强调一种责任伦理而非信念伦理。而20世纪下半叶,罗尔斯则将这一思想取向做成了一个比康德更精密、虽然范围也更有限的一个正义理论的体系。罗尔斯比康德更进了一步,甚至所有的价值理论和人生追求,包括康德的全面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也都被纳入了“广泛理论”而必须与核心的道德的“正义”相区隔。
当然,在一个从长期被信仰笼罩,信仰与道德结为一体的精神氛围中发展而来的西方近代社会里,信仰与伦理的关系可以说始终有一种深刻和微妙的紧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紧张更是常常被推到极致,呈现为一种难以摆脱乃至万难忍受的困境。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有对道义的极度强调,有“如果没有道德,上帝如何可能”的追问,他尤其不能忍受对孩子的凌辱和杀害,甚至借书中人物的口谈到,如果这样的罪行也能够发生和容忍,那么就可能没有一个公义的上帝,或者说上帝的存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觉得离开道德的上帝及其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他那里,分量更重的还是信仰,他也同时追问:“如果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或者换一个反面的说法:“如果没有上帝或是上帝死了,是不是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事都会做,什么也都可以做?”他觉得没有上帝的道德或者说离开信仰的道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还借“宗教大法官的传奇”深刻地描述了一种人类中多数与少数的自由困境。
罗尔斯(1921-2002)也经历了一个像马丁·路德一样从自身的生命体验而发生一种思想和精神转向的过程。他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在他读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两年,对宗教发生了一种超越习俗的热情,开始深切地关注神学,他1942年底提交的学士毕业论文即以《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基于共同体概念的一种阐释》为题,他甚至考虑进入神学院学习以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在论文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越快地停止膜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情况就越好。一盎司的《圣经》抵得上一磅(或许一吨)的亚里士多德。”[2]但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他不久就参军到了太平洋战场,直到战争结束重返大学。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在罗尔斯的电脑中,发现了一篇他创建于1997年的遗稿,题为《我的宗教观》,其中记录了他转变的心路历程:
我出生在一个习俗宗教的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个圣公会教徒,我的父亲是一个南卫理公会教徒……我也只是一个习俗宗教的信徒,直到我在普林斯顿的最后两年。我变得深切地关注神学和它的教义……我甚至都打算去神学院,……但是在战争最后的一年左右,所有这些都改变了。……从那时开始,我认为我不再是一个正统教徒……我开始是一个信仰正统圣公会教的教徒,而在1945年6月我却完全放弃了它。……有三件事凸显在我的记忆中:克雷山脊事件、迪肯的死、听到关于大屠杀的消息以及对它的思考。……这些事件——尤其是广为人知的第三件事——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我。……当上帝并不能从希特勒那里救出数百万的犹太人,我怎么能够祈祷和请求上帝来帮助我,或者我的家庭,或者我的国家,或者任何我所关注的值得珍惜的事情?上帝看起来是公正行事。但是大屠杀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被解释,所有我听说过的这样去做的企图都是丑陋的、罪恶的。把历史解释为上帝意志的表达,而上帝的意志必须符合我们所知道的最基本的正义观念。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最基本的正义?因而,我很快就拒绝至高的神圣意志的观念,而基督教教义中表达的正当(right)和正义(justice)的观念却是另一码事。……我开始想它们当中许多都是道德上错误的, ……由此,我认识到对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否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恶,这些自由成了我的道德和政治观点的支点。最终它们也成了我关于民主政体观点的基本的政治要素,通过政教分离的形式体现在各种制度之中。……(而)关注于我们自己的得救以至于其他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参见Johu Rawls: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259-266)。译文采用罗尔斯:《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兼:我的宗教观)》(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罗尔斯所述的战争中发生的三件事除了听闻我们现已熟知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外,一件事是在克雷山脊一个路德教的牧师在布道中说,上帝让我们的子弹打中日本人而保护我们免受他们的子弹,这让他觉得荒唐且愤怒,他认为基督的教义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使用。另一件事是他的战友迪肯因为血型不符而让他去了医院输血,迪肯自己随一位上校去了前线侦察而两人均被炸死。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止一件,罗尔斯幼年时曾经两次患病传染了他的两个弟弟,结果他活过来了而两个弟弟都死了;还有与他同样应征入伍的许多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在战场上死去而他幸免。为什么灾难落在那个人身上而非这个人身上?而那个人其实可能比这个人更不应该对此负责。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对此是怎样预定和安排的?而这其中除了自然的灾难,更有人为的灾难——有些灾难如大屠杀完全是人类的罪恶引起的,一个完全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对此视若无睹?战后罗尔斯继续探讨了宗教的历史,他的研究使他进一步感到要捍卫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正义的话,就必须离开排斥异端的宗教来独立地探讨道德与正义。但即便从他的这篇晚年遗稿来看,虽然他强调和推崇人的理性,但也并没有断然地否定信仰和上帝,他还是被像让·博丹那样的一种从宗教信念中引申出来的宽容的思想所吸引。
罗尔斯后来一直致力于对社会正义理论的探讨,尤其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试图将宗教乃至一切有关人生价值追求的广泛理论与社会正义理论分离开来,他认为现代民主社会已经形成了各种多元的信仰、哲学和价值理论的格局,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得到全体公民或几乎所有公民的认肯。这些合理然而却并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之多元性,正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正常结果。而他的问题意识在于:这些持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追求的人们如何和平稳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罗尔斯回顾了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他认为三次历史性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性质,而首要的发展正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它使中世纪的宗教统一分崩离析,并导致了宗教多元论,而这又依次孕育出其他各种各样的多元论。宗教权威和基督教时代的信仰不再是支配性的。宗教改革使中世纪基督教这样的权威主义的、救赎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宗教产生分裂,新的宗教与从中分裂出来的罗马教会有所不同,又有所相同:路德和加尔文也还是与罗马教会一样是不容异说的。
因此,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其实正是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其间伴随着16~17世纪围绕着宗教宽容所展开的漫长争论。所有公民,他们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又因各种合理的宗教信仰和哲学学说而深刻分化,那么,他们所组成的社会如何能够达到长久的稳定和公正?罗尔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的正义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至善的问题。近代道德哲学家一直试图解决这一多元共存的正义问题。他们希望确立一个独立于教会之外的、适应于日常有理性和良心之个人的道德知识基础。道德究竟是本源于上帝理智中的一种价值秩序,还是以某种方式源于人性本身——理性、情感或者两者的统一?休谟和康德均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认可后者,但他们还是属于一般的广泛的自由主义,而罗尔斯试图提出一种范围有限的政治自由主义,即认为可以发现一种所有合理的广泛价值理论和宗教信仰都可以相容或支持的“重叠共识”——也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正义原则。这些基本的正义原则是独立于各种广泛理论和信仰的,并不是从它们引申而来的,并不以任何一种信仰为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是与信仰脱离的,当然,这并不影响正义能够与各种不同的合理信仰兼容和得到它们的支持。
总之,在罗尔斯看来,政治自由主义恰恰是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因为宗教改革导致了教会的多元化,乃至个人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这自然是违背其创始者路德与加尔文的意愿的。面对接踵而至的宗教战争,大概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筋疲力尽,打不动了,最后达成一个临时的停战协议;再就是寻求一种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的理论,以作为新的、独立的正义理论。后者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罗尔斯并不像有些学者那样批评乃至激烈地否定宗教,他还是将合理的宗教信仰看作一种可以与正义理论相容乃至给予支持的价值体系或广泛理论,但试图成为“重叠共识”的一个方案的他的正义理论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不仅基督教,也包括其他所有的宗教和广泛的价值理论,他有意地摒除了他的正义理论中生命信仰和生活价值的内容。罗尔斯并不致力于否定和批判一般的宗教信仰,甚至我们可以说,一种与其早年信仰不无关系的怜悯,可能还是深深地渗透到他的强调最关怀最弱势者的道德哲学之中。“离信”只是在罗尔斯社会的正义理论中呈现,这并不妨碍他的个人生命仍然可以持有一种信仰,持有信仰者也同样可以对道德或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一种独立的、理性的建构与探讨。
在罗尔斯之后,虽然说信与义分离是一种大趋势,尤其在学术界更是主流。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互相接近的愿望和努力,比如在信仰这边,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一次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提出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承认不同的宗教和伦理传统对于何为善恶正邪提出的彼此不同的根据,但宣言的签署者们认为,这些分歧不应当阻碍人们公开宣布一些人类已经共同拥有并共同肯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类对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义务的共识,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其人”“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以及几乎可以在所有宗教和伦理传统中发现的这四条古老诫命:“不要杀人,不要偷窃,不要撒谎,不要奸淫”。他们认为这些基本义务是可以独立于任何特定精神信仰而构成所有信仰的共识的——恰正是因为它们不特属于某一既定信仰,才能作为各种信仰的共识。
而在道德学术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一种寻求信仰的努力。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德沃金的最后遗作是一部名称为《没有上帝的宗教》的书,他在书中对理性和自由主义学说的不足进行反思,他坚称,无论科学、逻辑还是价值,最终还是需要信仰支撑。他认为假如那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以及激进派的学者都能够从一开始就重视宗教,也许我们今天的社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精神上严重匮乏。当然,他所说的宗教信仰,并不只是有神论。他认为宗教并不等于神,宗教比神要深奥。他初步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人文主义“宗教”的设想*参见於兴中:《自由主义者的宗教问题——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之介评》(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步入中老年后,也开始认识到自己以及理性的局限性,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宗教问题,如著名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曾经对宗教有过不屑一顾的批判,但在年事渐高的时候又对宗教发生了兴趣;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左派思想家昂格尔最近也出版了新著《未来的宗教》。
四
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包含了一些评论,但笔者现在尝试对“因信称义”和“因义离信”这两种观点作一些总括性的分析和批评。
从信仰与道义的关系来看,在传统社会中,信仰与义务、价值与规范,基本上都是结合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传统中国的儒家希圣希贤与德行义务,还是古希腊城邦的多神论与追求卓越行为,犹太教的信仰与戒律,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的信与义,都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有些结合得非常紧密,并都是将前者放在更高或更优先的位置。马丁·路德所反对的罗马教会,也同样是将信仰放在至上的地位。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最高”和“唯独”,“最高”意味着下面还有次高的内容,而“唯独”则是囊括了所有的部分。罗马教会自然也是将信仰、信心视为最高和至上,但它不排斥其他的部分,还强调礼仪、戒律、善功和补赎。但在长期的过程中,下面的部分有可能会侵蚀、遮掩甚至替代最高的部分,而这也就是改革宗要抗议的,它们要恢复最高,要强调信仰本身,所以采取了一种“唯独”的观点。人仅凭信即可称义,即可得救和永生。律法和善功并不是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不要律法,而是说,遵守律法乃至爱邻人将是信靠上帝的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一种副产品。
这里可以分析出三种观点:一是“人仅凭信仰就可称义”,与之对立的则是“人仅凭自己的善行就能称义”,这种观点是非宗教信仰的道德观点,但这中间还有一种观点,即人首先或主要是要凭自己的信称义,但是,也要通过自己的善行、功德来称义。这种观点大概就是天主教的观点,它是一种仍然守住信仰的中道,但在长期实践中却可能产生流弊——忘记了以信为至上的本义。
在一个宗教兴起的时候,无论基督教信仰精神的古代兴起还是近代的复兴,大概都必须诉诸一种能够极大地调动人的信仰的力量,但如果它要在社会上取胜,或者需要巩固这胜利,那么就一定要整饬纪律,乃至产生某种具有差序的制度,产生出一套严密甚至繁复的礼仪和戒律。少数信仰精英可能会渐渐不满意于这些制度礼仪,但它们却可能对多数有效。包括新教自身,在加尔文那里马上就开始着手建立秩序和纪律,而也许正是这种制度秩序,止住了马丁·路德启动的“滚石”(茨维格语),使新教教会壮大起来,其教义传播开去。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蕴含的信仰的良知自由,打破教会对圣经的垄断解释,“平信徒皆为祭司”的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思想,不仅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当时就引发了一些激进的运动。其中一个极端运动如明斯特城的共有共享财产的实践,很快就造成了混乱和流血,以致昙花一现;而加尔文的日内瓦城却成为新教运动和精神的模范而影响深远。这样的两座城预示着非常不同的两种方向。
但新教虽然后来也在组织上巩固了,却再也不能获得罗马教会的那种相当普世的统一,这也许就是它的自由平等和个别化的教义思想特点所确定了的。即便都是推崇信仰和圣经,也还是会有许多不同的强调和理解,这就造成了种种疏离以致分裂。新教和罗马教会分离了,它自身也分离成许多教派和教会。欧洲精神一体的昔日再也不能复见。但由于新教还是比罗马教会更重原始的信仰精神,所以,它虽然缺乏旧的宗教制度的那种建树,却还是能一次次激发起热烈宣讲和传播福音的运动,并以这种运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世俗社会。
可以说宗教改革派还是抓住或重新恢复了一些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信仰的原始和持久的精神。另外,它也看清了人为加在信仰上的一些外部附属物就只是附属物,从而再次肯认了人就是人,而上帝就是上帝。这可能是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即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马丁·路德为什么如此强调“信”,这自然一方面是抗议罗马教会的腐败现象,还有更为根本和重要的一面,也可以说是防止人的僭越。路德本人也是坚守信仰和行为的范围和限度的,实际也是坚守比较原始的基督教的界限,即主张信徒不应该过度地介入社会政治、介入此世,而应该是以属灵的国为限,主要是因信仰得生命和自由,而在世俗的国,则还是要服从,不追求社会的完美和人间的天堂。“因信称义”强调人凭自身无论如何达不到完全的道德的义,人在道德上无法功德圆满,更达不到那种高尚完美的善。人不能完全信任自己,更不能放任自己,这就削弱了自由和个人本位思想可能造成的危害。于是人不能不诉诸超越存在的力量,希望着他的恩典。藉此肯认,人才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设定一个牢固的界限而不致僭越,从而阻止无数的恶事——因为有许多的罪行正是以“人间完美的理想”之名犯下的。
一种精神信仰能够极大地调动起一个人的力量,也往往能够使一个群体都达到某一种精神水平或进入某一种精神氛围,从而使道德水平也自然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至少不会始终紧盯着物质利益。如果说人们达不到完全的“义”,是否又能够达到完全的“信”?而且,如果人们的主要追求改变了呢,即“信”的内容改变了呢?当得救的热望淡化乃至消失,这时会发生什么?“唯独信心”,但如果没有善功、道义、礼仪与戒律的夹持,这个“唯独”却慢慢淡化、转型或者突然丢失了呢?信仰的确是可以突然得到或顿悟的,但是不是也可能突然丧失?既然可以完全自由地凭个人的良知来进入和判断真理,那么,一个原本的信徒会不会凭他的内心来达到这样的结论呢?某种宗教信仰,甚至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真理其实都是虚幻的?另外还有从来就不信的众多人呢,对他们怎么办?如果按照绝对的预定论和完全的恩典论,认为得救与人的行为、与尘世的努力全然无涉,而活着的人、肉体的人又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和普遍的“信”,那么,是希望还是绝望?另外,还有其他宗教信仰也大概会有类似的“因信称义”以及无超越存在的信仰者会不会对“因信称义”望文生义,将此一原则挪用到世俗的生活领域,乃至滥用为可以用信念来证明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手段呢?当然,新教思想家可以说人与上帝的连接并不是在圣洁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在完善的上帝与不完善的人的基础上,甚至就是在人的罪性的基础上。是上帝接近人,而非人能够接近上帝,人只需信靠上帝。但是,何以一种信靠,尤其是相信一种与人的努力无涉的预定论能够使人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包括在世俗社会中抗恶行善的巨大力量,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仔细探究。从道德的本质根据或者说本体论来看,“因信称义”如果将“义”理解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因而可以“得救”,那么,“因信”而“称义”即便在理性逻辑上也是成立的,并不矛盾。但如果将这“义”理解为道德的“义”,则在理性逻辑上是通不过的,或者说只能依赖一种信仰的飞跃。道德是有一种独立性的,有它自身的根据和内容,这种根据和内容不是来自政治权力,也不是来自一种精神信仰。
另外还有道德的功夫论的问题,即人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义人?这涉及到心灵与行为、信心与习惯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一棵好树才能结出好果子,从一个好人,一颗善良的心那里,才能保证源源不断地产生好的行为。但是,如何训练成为一个好人,如何养成一颗好的心灵,恐怕也还是要努力从行为习惯上着手或者不偏废。正如新约《雅各书》第二节反复说明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马丁·路德认为这篇虽然包含一些杰出的段落,但其也重视行为和律法,与保罗和整个圣经的精神有违,他个人并不认为它是真经,不具有使徒书的权威。参见Martin Luther: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anchor books(Random house,1962, pp.35-36)。类似的,中国心学一派的儒家如王阳明也是极其强调道德良知的精神力量,但是到了晚明,其后学的一些流弊产生了,一些人只是空谈心性而行为放诞,以致明清之际的一些大儒反过来强调行为习惯和规范约束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在事上磨炼,那怕是“强恕而行”。
时光过去了五百年,人类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美洲,后又有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马丁·路德似乎不很清楚或者说不关心和重视这些事情,但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却至为巨大。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民族国家也迅速定型和发展,我们除了处身于一个文明历史和文化取向相当不同,但却紧密联系的全球世界之中,也处身于自己所属的政治社会,亦即处身于一个主要是以地域而非以宗教信仰和种族来划分的国家的架构内,政教分离或信仰自由也多载入这些国家的宪法。试图将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社会中的人们的信念、信仰统合为一种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而从全世界来看,那就更不可能。这种多元化已经不仅是现状,还被人们视为正常甚至正当。那么,罗尔斯的问题就始终存在,即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人们如何和平共处乃至守望相助?
当然,以上的评论和疑问是仅仅从一种单纯的道德观点,从一种政治社会、一种全球化的人类的观点所作的批评,如果从一种信仰的内部的观点看,当有另外的看法或结论。我们也要考虑到马丁·路德的话主要是对信徒或准信徒说的,是主要在教内处理“信”与“义”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肯定还是可以乃至必须独立地提出一种能够包括所有人的道德,以处理各种各样活着的、不同信仰和价值追求的人们的关系。而从康德到罗尔斯的努力,看来就是尝试探讨这样一种道德的可能性,这些人无法靠加入对方的信仰或确认一种统一的信仰来解决人与人、国与国相处的问题,他们或许只能主要依靠理性的对话来沟通和达到某些基本的有关行为规则的共识。
这方面的探讨的确也遇到许多问题。罗尔斯是一生做一事——即毕生探讨社会正义理论的一个典范。他并不否认合情合理的信仰与正义可以相容和给予支持,他只是认为应该将信仰从正义的内容和根据中分离出去。但罗尔斯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澄清和解决正义的重叠共识如何与价值信仰连接的问题。即便同意有许多价值信仰与这种重叠共识是可以调整得相容,但是它们与重叠共识的关系肯定不是等距离的,反过来说,即政治的正义对这些价值信仰可以做到基本上中立,但并不可能完全中立。这有理性的原因,有一些价值信仰可能内在地蕴含着更多的对正义共识的相容因素和支持力量,还有一些价值信仰则可能只有较少的相容因素和支持力量。另外还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原因,如果使某些,甚至最好是某一种扎根本土的价值信仰与正义共识建立比其他价值信仰更为紧密的关系,它也能够给予这种正义以最强大的力量支持,而且给许多遵循正义者个人解决安身立命和终极关切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有时是致命的弱点是:它缺乏足够的力量,它有时甚至不能够保护自己。它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无论对多数还是少数,人毕竟是完整的人,除了义务感和正义感,还有种种深度的价值追求和更高的信仰渴望,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和生命意义的追寻,这些才是最富有吸引力的,最能提供行动力量的。人们还常常看到,将信仰与规范——有时甚至是误导的信仰与错误的规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教义,却往往比单纯理性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整合力。且不说理性也不易消弭分歧,乃至“唯独理性”也会犯错,而即便是充分恰当的理性,也还是力量不够。我们会遇到单纯理性的瓶颈甚至陷阱,以致有时我们不得不问:分离信仰与道德、价值与规范是否真的可能?这样做会不会切断我们的传统,分裂我们的人格?而且,即便最后达成某些共识,它们是否过于稀薄,缺乏厚重的支持和强大的吸引力?
也许出路还是在于某种平衡和适度。而要如此,就可能首先需要这两个观点各自有意识地限定自己的范围,如果“因信称义”仅仅是就一种精神信仰的内在而言;如果”因义离信”只是就一种应用于调节所有人关系的道德理论而言,它们看上去的歧异也许就并非是内在固有的,至少不易酿成暴烈的流血冲突。以上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的对照主要是为鲜明起见,而人类实践在这五百年的时光中对各种尖锐的观点已多有磨合与调适,生活的力量和灵活性都要超过理论。而在理论方面,注重超越信仰的思想观点与注重人间道义的思想观点也还是可以进一步互相接近并加强沟通,除了自己所持的观点,也考虑到另外的观点。也许我们是能够做到不同的观点有某种视野的融合的,进而在“信”与“义”的各自内容和相互关系上,达到某些比现有认识更为深刻的认识,比现有共识更为有力的共识。
[1] 马丁·路德.路德选集[M].徐庆誉,汤清,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2] John Rawls.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