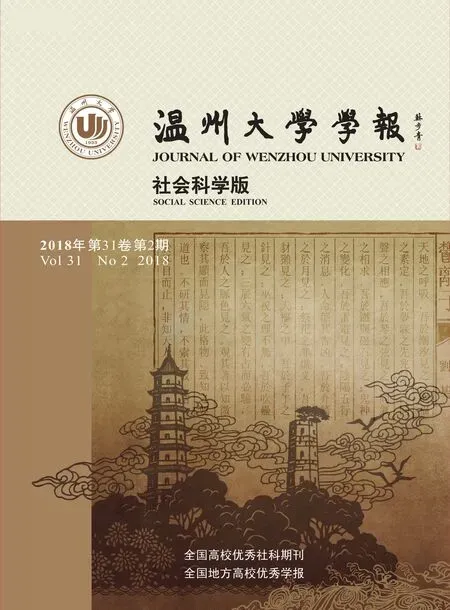张振夔的社会政治理念及其经世实践
孙邦金,齐雅芬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张振夔(1798 - 1866),字庆安,号磬菴,永嘉场下垟街(今龙湾区永兴街道祠南村)人,自号介翁。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精研经史,又通军事、水利、律历、文艺、医药,是个通才。他认为,“害心者一时误两三人,而流弊遂历数十年而成俗”[1],故深感教育之重要,终生以学官为己任,道光丙戍(1826)大挑一等,任常山县训导。后来,曾三次担任镇海县学教谕,前后共五年之久。任职镇海期间,适逢鸦片战争爆发,积极参与抗英准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镇海战事一败涂地后,辞官回乡,时年方48岁。此后十年,一直居家馆课生徒。59岁起,主讲温州东山书院,67岁主讲台州宗文书院。1866年,69岁主讲乐清梅溪书院时,卒于任上。磬菴善古文辞,有《介轩诗钞》十卷(共1 128首古今体诗)、《介轩文钞》八卷和《介轩外集》二卷,都为《介轩文集》二十卷。孙衣言为撰《永嘉张先生墓志铭》,有题跋,并有多处评语。今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引文皆出于此版本)。张振夔与端木国瑚、鲍作雨、刘灿和黄式三等人交游论学,并曾与鲍作雨一起主纂有道光《乐清县志》。当时鲍作雨随许松年在福建作幕宾,修志之事多赖磬菴先生成之。
目前学界有关张振夔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笔者目见惟一的专著只有张氏后人张鸣华教授编著的《清代永嘉之学——纪念张振夔先生诞辰210周年》①参见:张鸣华. 清代永嘉之学:纪念张振夔先生诞辰210周年[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该书其实是几篇文章与行述的结集,显得杂乱无章、不够系统,未能全面展现出张振夔的学思言行及其在晚清温州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有鉴于此,笔者拟主要从政治、学术与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来勾勒张振夔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经世实践,以窥全豹并求教于方家。
一、“以道得民”的仁政理念
儒家士大夫即便是没有牧民之职,兼世济民的理想大多也会萦怀不去。张振夔身为教谕,在其《儒以道得民论》自道“儒虽有老,起居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表现出对民众苦乐感同身受的社会关怀和忧患意识。《介轩诗钞》中感怀民间疾苦的悯农诗曰,“开畦引远流,求获正谋始。未获安有租,催科已在里。”(《听蛙》)《煮海谣》中有云,“朝开煎,暮停煎,煎不以时四士鞭。……劳劳那许谋朝夕,男呻女吟,分作沟中瘠!”[2]477对以煮盐为生的盐户的辛劳与贫苦,抱以深切的同情。与之鲜明对应的是官吏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压榨和人身束缚,对此张氏不免义愤填膺。
张振夔所撰《儒以道得民论》,其实是对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儒家道义论的再次重申。孟子政治哲学的要义在于,要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政治认同尤其是道德认同,为此必须占据社会公平正义之“王道”这个至高点。这个政治道义,既有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也有政治合理性的问题。换言之,它首先表现为政治肌体的一种道德情感,即与民同乐、同甘和共苦的道德感通能力,其次才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行政技术的执行等层面的问题。正所谓“人饥而我不恤,将我饥其谁恤之?”(《上某观察书》)当一个当权者“内饱而不复恤人之饥”(《上俞松石观察书》)时,当一个作为社会有肌体的政权丧失了感同身受的能力之时,对于百姓疾苦冷漠无情的时候,那么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会成为摆设,离它覆亡的命运也就不会太远了。无情的帝王将相兴亡嬗变的历史,屡屡从反面证明了“以道得民”的至简道理。在《读唐史杂咏》组诗中,对于隋末唐初食人魔王朱粲的覆亡,磬菴有诗云:“可叹造物太不仁,为尔生此刍狗民。斩之洛水上,掷以瓦砾恨未伸。”①张振夔. 读唐史杂咏[M]// 张振夔. 介轩诗钞:卷六 //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18。《介轩诗钞》卷六一共七十二首诗,全部为作者的《读唐史杂咏》组诗。此卷组诗是张振夔读隋唐史过程中以诗咏史的记录,一首诗评价唐史中的一个人物,夹叙夹议,或褒或贬,颇有特色。当时朱粲挟兵自重一方,所过之处视民命如犬彘,以吃人肉为乐,狂妄一时,然而天道好还,其最终还是罪有应得,落得个死于非命、万民唾弃的下场。张振夔在弊病缠身的晚清中国,重申儒家这个至简的政治道义原则,显然已经深切体味到清王朝已日渐陷入对民间疾苦麻木不仁的道德困境。张氏在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革新弊政、改善民生之前,从根本上反思当权者离心离德所造成的政治道德危机,殷鉴不远,绝非虚谈。
二、“抱负经济,事事求诸实践”的永嘉经世理念
有清一代学术,在乾嘉鼎盛期曾一度呈现出义理、考据与辞章之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以考据之学最盛。到了嘉道时期,整个思想教育界仍旧沿着朴学化或考据化道路不断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从考据到经世的转型,汉学与宋学之争再次高涨。张振夔准确地把握到了当时学术之脉动,在权衡各方之间的歧异与得失后,最终提出了自己“勿区汉与宋”“笃于伦常”的学术立场。他批评考据学通常为了学术而学术,“即有号为精核,亦矜矜然博览万卷,曷尝力行乎一二?”而词章之学则凌空蹈虚,“一试之于有用之地,辄格格不入”,两者的缺点皆在于不敷实用。真正的“治经之道,宜取古人之言有裨世用者……使大可效于朝廷,小亦可济一乡一邑”,恢复儒门经世致用、康世济民的终极面目才是当务之急。
对于乾嘉学界闹得不可开交的汉宋之争,张振夔的主张是“勿区汉与宋,博约在持志”[3]。如果说汉儒之学的主要特点是“博”,是平面铺开,那么宋儒之学就是“约”,可谓上下直贯。汉宋之争,是一种学术上的博约之争。张振夔不无见地认为,“博文约礼是圣学大关键,彻内彻外,毫无余蕴。汉儒以博文为学而不知约礼,故放诞而有遗行。宋儒以约礼为学而不复博文,故迂阔而不近人情。”[4]汉学与宋学各有弊端,关键是如何通过由博入约实现博与约两者的相对统一。
张振夔为了统摄汉学与宋学、博与约,避免双方各执一端聚讼不已的局面,提出了“笃于伦常”之学的对治策略。在他看来,“士之学为词章者不若精于考据,而精于考据者又不若笃于伦常”,“笃于伦常”的实用学问才是儒学之核心要义。因此,他一直主张“欲弟子学文,莫若先从事于伦常”[5],希望跳出乾嘉学术汉学与宋学两相对垒的旧格局,融汉、宋于一炉,以恢复儒学的致用性格。张振夔在本体论上肯认了宋儒性命之学的重要性:“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死无所丧。窃以为能尽性则生有所得,死无所丧;不能尽性,则生无所得,死真丧焉。”[4]587这里隐含了对清代汉学只谈训诂、讳言性命的批评。与此同时,在知识论上他又不同意“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4]588的知识论,批评了宋儒囿于“天理”——先验德性之知而忽视了后天经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清代汉学在知识扩展与积累方面的贡献。在工夫论层面上,张振夔特别强调渐进,尤其是反对阳明后学的顿悟之说。他主张“静坐即以书之义理,实验诸心身日用之间,务使知之,必可行之,至用力久,而体察入微。”在静坐入定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思与行,“务使知之,必可行之”,知与行的能力就会愈加协调统一,从而摆脱知行分离、销行入知等弊病。张振夔后来总结道,“君子论学勿问其为汉为宋,要必合仁与义,本诸身而能征诸庶民者,谓之儒。”[6]他所讲的儒学——“笃于伦常”、“知行统一”之学,显然不同于宋儒的穷理尽性之学尤其是主张顿悟的心学,也不同于清儒学不而思的学问,而是指一种“必合仁与义”(有体)、“本诸身而能征诸庶民”(有用)、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兼顾的经世实学。
从上述可见,张振夔并没有轻视天命心性之学的重要性,不过他一生对实用技艺之学显然更有兴趣,也更有成就。正是基于“勿区汉与宋”“笃于伦常”的思想主张,他又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抱负经济,事事求诸实践”的教育理念。他在《通艺课约序》中指出,“世固有滞于艺而不知道者,要未有舍艺而可博其义理之趣也。……夫一艺诚不足尚,不犹愈于一艺之无成者乎?”[7]在他看来,一味地轻视技艺之学为末学、小技,缺乏技艺之学的训练,造成有学而无术、有体而无用,恰恰是传统儒学的一大病症。而技艺之学作为必不可少的自存和致用手段,堪为性道之学发用于一己和民众的桥梁,理应予以重视。张振夔一生从事教育,对于科举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看得很清楚:“今之所谓学者,六经、四子书申其呫哔而已。今之所谓教者,八股、试贴习于摩揣而已。其好为高论者,则又贬斥游、夏,相尚坐忘。”[4]585通过科举教育来造就和选拔人才,是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科举应试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自不待言。但是,应试教育不能凌驾于整个教育之上,教育的真正目的并非科举本身,而应该是“明理以达用”[8]的成人之学。
在道、技合一观念指引下,张振夔在镇海教谕五年任上,曾尝试在程朱性道之学之外加入经过变通的“六艺”训练,结果遭到强大的阻力而少人问津。除了既有的“士希贤圣,艺皆末也”传统观念的障碍,也有科举的现实压力使然。归田之后,他把在镇海教谕任上未能施展的教育理念贯彻到后来的教育实践中。在他执掌东山书院期间,师生之间“相与诹经稽史,考校东嘉儒派之得失,以裕后生经济之用而自补东隅之失”[9],开始自觉地结合永嘉经制之学的传统探讨社会现实问题,有意养成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风。他自己说,“吾瓯有先生其人,当道学晦塞之时,独能唱为此编,为周、程、张、朱嚆矢。而今瓯之儒者,罕能闻知而兴起焉。此则予所为低徊慨叹,而不能自已者矣”[10],明确表达了希望接续和发扬永嘉经制实用之学的立场。他的学生庆生在《介轩文集书后》中评价其师曰:“盖士生于穷乡僻壤,罕能自拔于流俗间。有风雅超轶者,亦止能为当世文章耳。而先生则抱负经济,事事求诸实践,不欲以文字自名,而论议所及视古立言者无多让焉,岂不难哉!”[11]学生说老师“抱负经济,事事求诸实践”,是中肯的评价。
三、“治隆宜正己”的经世实践
张振夔官镇海教谕时,适逢鸦片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加当地的抗英斗争,先向裕谦等人上书《战守策》,被指派“监发军仓”兼管镇海军事后勤事务。后来,林则徐督军镇海时,献上战艇图,可惜由于林氏不到月余即被发配新疆而不了了之。其间,张振夔有不少思考值得总结和反思。
首先,张振夔对于引发此次战争的鸦片,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官民在如何处理日益深重的鸦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严禁与驰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双方聚讼不已,进而导致官方犹豫不决、举措失当。张振夔在这场争论中,是个坚定的禁烟派。他说,“鸦片之误人,毒矣哉。国以之贫,家以之破,躯肉以之脱,骨髓以之竭,子孙以之绝。幸而不绝,祖泽犹厚也,其孔子嗣而食之,盖三世希不绝矣”[12],极言鸦片害国破家的严重危害。在《读黄鸿胪请禁鸦片疏感赋》中云,“当朝论侃侃,破格铁铮铮,屈贾应同传,苏黄旧著名”,将敢于逆鳞上书的黄爵滋与屈原、贾谊等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并列,高度评价了黄爵滋上书谏言这一举动,肯定了禁烟的必要性和抗英的正当性。
其次,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不期而至,张振夔较敏锐地觉察到中外攻守易势的现实情势。他有诗云,“从今别有关心处,海上兵氛待扫除”[13],表明如何应对海上侵略将会将成为政府日后最为棘手的战略问题。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他以诗明志:“治隆宜正己,悔吉得先庚。树腐招虫啮,篱修笑犬狞。未能胜草薙,聊且逐蝇营。”[2]537-538张振夔意识到在中外强弱情势已然翻转的情况下,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丢掉以谈判求和平的幻想,及时改革自强做好防备,方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至于如何训练水兵进行海战,改变以往单一的陆地防御策略,他也有过具体建议,兹不细表。
张振夔与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虽然感觉到中外力量对比的失衡,但对于西方船坚炮利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之先进程度尚无足够认知。从他对于西方科技稍带轻蔑的看法中即可见一斑:“今之嗜鸦片者及甘为夷人走私者,皆云夷人巧夺天工,非中华所能及。不知奇技淫巧,三代圣王有厉禁,中华人直不为耳,非不能也。”[14]这种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且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落后是国人“不为耳,非不能也”的观点,不能不说是犯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通病。
张氏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也颇不以为然。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谈到基督教的时候,认为其不过是外向用力而非反求诸己的盲目迷信之典型。他说:“子曰:‘性相近也。’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今舍次与又次之功,而专求上知于天,……毋怪泰西之教日以礼拜天主为事,而不知返求诸身也。”[4]16张氏很自然地把基督教的天主与儒家的神秘之天相提并论,并把礼拜天主与中国普通百姓“专求上知于天”——为了追求福报而烧香拜佛的功利性宗教行为相提并论。在他的判教系统中,基督教的礼拜行为就连“次与又次之功”也算不上,基本上将其归类于最低级的盲目迷信和崇拜偶像这一类,鄙视意味十分明显。而 30多年之后,温州人孙诒让在目睹西方基督教在晚清中国“燎原莫遏”式的发展之时,则非常明显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进而不无忧虑地指出,“窃谓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稣基督之诬诞,《新约》《旧约》之鄙浅……,窃恐议瓜骊山,重睹于秦坑。”[15]这里将基督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冲击,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提并论,可见孙诒让如临大敌般的文化危机感。而张振夔当时还囿于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的中西文化观,对于西方文化的隔膜与轻视,明显缺乏世界历史的眼光和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敏感性。当然,在基督教还未广泛流布晚清中国之际,张振夔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对基督教的看法,对此后人是不能过分苛求的。
再次,张振夔从镇海归田之后,仍旧不忘济世的抱负,除了海防、团练等军事实务之处,张振夔对于永嘉地方盐务、教育和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等方面亦有不少论述。孙衣言在《永嘉张先墓志铭》中记载道,“尝为郡守令议团练、议水利、议书院、教士、育婴、义仓、皆平实切利害。”不仅如此,张振夔“晚年以诸艺无所试,惟医可济人,卒致力焉”(《行述》),还有悬壶济世的行医本事。这里仅略微分析他对当时人多地少、流民日多的看法。在嘉道之际,由于人稠地少的人地关系紧张造成的基层民众生计日蹙、流民日多的问题已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焦虑,这被后世称之为嘉道“治平之虑”。对此,张振夔曾不免天真地认为“吾不患田之不足,与田之日耗,而特患游民之太盛。”(《鸦片漏银后议议》)在他看来,当时的问题不在于农业人口过多难以供给养活,而是从事工、商业等“末业”的游民和流民不断增多导致农业人口不断流失,动摇了农业这一国本,对于尚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无疑是致命的威胁,可事实上,当时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在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面前无力抵抗而不断破产,以及由此引发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才是根本的原因。农业时代的中国既无法抵挡也不能理解工业时代的西方,双方的相遇是个悲剧性的开始。近代农业不断向工商业转移人口乃是大势,此时还想通过维系一种“糊口农业”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农业人口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只能说张振夔还局限于农本观念,其“不患田之不足,与田之日耗”的看法已是十分保守的传统定见。
四、结 语
总体上看,张振夔对于晚清温州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研经史、旁及百家,力主“勿区汉与宋”、“笃于伦常”的学术立场,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之际显得殊为难得。在一生矢志的教育领域,他重提“抱负经济,事事求诸实践”的永嘉之学,以坐言起行的永嘉经世精神提撕风教、造育人才。在晚清中国沉陷内忧外患之时,他再次重申“以道得民”、“治隆宜正己”的儒家政治道义论,当是正本清源之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衣言在《〈介轩文集〉序》(1870年)中肯定了他在晚清温州永嘉之学的复振过程中有筚路蓝缕之功。在清代中晚期温州思想文化借助永嘉经制之学的传统由沉潜而复振的转变过程中,张振夔是一个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
[1]张振夔. 论书院育婴堂轻重[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3.
[2]张振夔. 介轩诗钞[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张振夔. 西湖诂经精舍[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68.
[4]张振夔. 杂说[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85.
[5]张振夔. 宗谱小序·艺文谱[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78.
[6]张振夔. 儒以道得民论[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4.
[7]张振夔. 通艺课约序[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05.
[8]张振夔. 上某观察书[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88.
[9]张振夔. 上俞松石观察书[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33-634.
[10]张振夔. 读儒志编题后[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68.
[11]庆生. 介轩文集书后[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15.
[12]张振夔. 介轩文钞[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1.
[13]张振夔. 姚研青学长招饮志谢兼示同饮诸君[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52.
[14]张振夔. 赘言[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2.
[15]孙诒让. 答温处道宗湘文[M]// 张宪文,辑校. 孙诒让遗文辑存.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