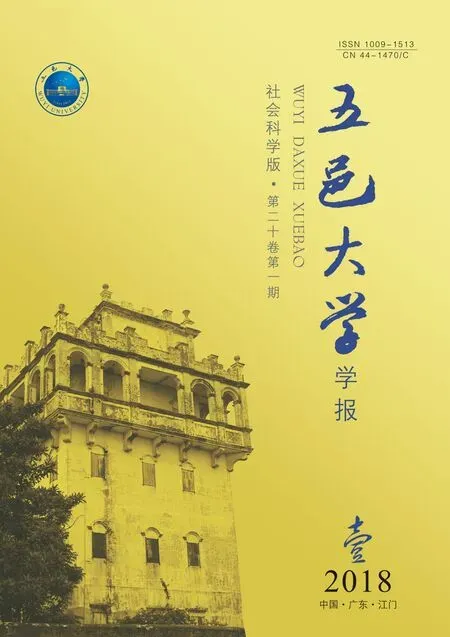从陈垣书信看陈垣的学术人生
庞光华,吴 珺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陈垣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如果说陈垣的学术著作是其学术成果的最终体现,那么陈垣的书信便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实现这些成果的。陈垣青年时代学习西方近代医学,当他弃政从事文史研究时,便用医学方法治史。他在元史、宗教史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成果颇丰。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他的书信中有一定反映。这些书信不仅反映了陈垣的学术人生,更勾勒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侧面。学术界对陈垣书信是重视的,例如陈智超《从 〈陈垣来往书信集〉谈书信的价值与利用》①,李欣荣《从陈垣书信看南学北学》②,曹旅宁《读〈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③等,都对陈垣书信的价值有较深的认识。本文依据陈垣书信来窥测陈垣先生的学术人生,陈垣书信主要依据资料是陈智超编《陈垣全集》④第二十三卷。陈智超先生是陈垣嫡孙,收集编撰陈垣的书信等资料最为详实。
一、陈垣书信关于宗教史的研究
1908年,陈垣与苏墨斋访书东瀛,在富士川游博士家见到多纪元胤所撰《医籍考》的稿本。陈垣认为,多纪元胤是日本医学界的钱大昕,其治学方法如乾嘉诸老,考据精详,条理缜密。医学方法启发了陈垣后来的治史之路,这从他1932年致陈约⑤的信中可得到印证。陈垣在信中说:“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1]593-594。
1913—1916年,为陈垣从医学研究向史学研究的过渡期,据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2],陈垣在此期间没有发表文章。此后20年,陈垣在元史、宗教史和考据学等方面取得相当的成就。
陈垣的史学研究,尤着力于元史与宗教史等方面。1917年,陈垣发表了首部史学论著《元也里可温考》。1923和1927年,他分别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上、下篇。日本学者桑原骘藏⑥称陈垣为以科学方法整理材料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称此书“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3],并指出“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3]。
重视元史中关于宗教史、民族史、地方史的材料,解决了过去元史中没有解决的基督教史的问题。他从研究史学之初便对宗教史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是前人研究没做到的,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垣在治史时,善于从地方志中挖掘材料。他在1917年写给慕元甫的信中说:“唯《宋元镇江志汇刻》,此书日本尚有传本,当仍在国内求之。赵孟頫、潘昂霄毁教两碑,已在至顺《镇江志》第十卷发现。……至顺《镇江志》,诚考也里可温之宝藏,无论如何难觅,不可不备一部也,……”[1]10可见,至顺《镇江志》与“也里可温”⑦的关系十分密切,陈垣“由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发现了方志材料中有关‘也里可温’较为详细的记载”[4]28,此外,“由元至顺《镇江志》、明万历《镇江志》、明万历《杭州志》、康熙《镇江志》、康熙《凤阳府志》、康熙《钱塘志》、道光《广东通志》、民国十年刻本《湖北通志》等,进一步考证出也里可温教人十和也里可温十余寺”[4]29。
1924年,陈垣去信胡适,告诉他检阅《黄氏日抄》全文,知当时摩尼确已混入道教。后来又得其友告知,嘉定《赤城志》(《台州丛书》本)卷卅七有知州李谦戒事魔诗十首,便知闽浙沿海一带,如明、台、温、福、泉等州,皆盛行摩尼。接着,陈垣谈及摩尼对中国的影响,“不独南宋时闽学受其影响,即北宋时道学家所提倡导之太极、两极、阴阳、善恶、天理人欲等对待名词,殆无不有多少摩尼兴味也。”[1]351945年,陈垣在给朱启钤的信中指出:“《贵州通志》卅二云语嵩化后,钱邦芑为作塔铭,方于宣序其语录行世。《滇黔佛教考》据此以为于宣卒在语嵩后,大误。”[1]326他接着解释道:“今观语录于宣序,乃永历八年撰,其刊行当在语嵩生前。”[1]326这些都是书信中呈现的陈垣治史与地方志历史材料相结合的例证。
在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陈垣在抗战时期所著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宋明清时代的动乱历史进行考察。它们与《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一起,成为这一时期体现陈垣爱国情怀与不屈之民族气节的代表作。陈垣在1946年给杨树达的信中指出了这三部著作的写作实质:“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1]328这也正如他于同年给方豪的信中说的那样,陈垣说《清初僧诤记》“前数篇因派系纠纷,殊眩人目,然此烟幕弹也,精神全在中后篇。”[1]96所谓精神,便是借清初东南法门的政治纷争控诉日伪汉奸欺压国民。与此书相互映衬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则是因为当时“日寇猖狂,平津沦陷”[1]424而“藉以泄其愤耳”。[1]424《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以佛教语录考史,极大地扩展了史料的范围,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陈其泰评价此书:“从这部著作开始,陈垣先生在论著中大量正面发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义的议论,实现了由严密考证向更高层次——自觉体现时代精神的飞跃,这就为陈垣先生的学术注入新的生命”[5]。
二、陈垣书信关于《元朝秘史》的研究
《元朝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陈垣在《元朝秘史》的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⑧。1933年,陈垣写信给黄子献,因为明译《元秘史》过于简略,所以请他将日译《元秘史》译回汉文,并提供自己将蒙文翻译为汉文的版本给黄子献参照。他指出翻译的关键在于“一名、一句不遗”[1]180,这样才能便于与《元秘史》的蒙文对照。针对明译《元秘史》过于简略的原因,他在信中解释道:“明译志在语言,故人名地名多略,如八卷二五页之九十五功臣,名字尽行略去,是也。今译志在事迹,故拟照蒙文一名、一句不遗……”。[1]180翻译应该“不嫌复沓”[1]181,以句为单位,在逐行逐句翻译出的基础上,用汉文文法勾勒联缀,使得“文气自厚”[1]181,从而“见蒙古文体本来面目”。[1]181此外,陈垣在《元秘史》的译音用字上下了一番功夫,采用音义兼备的译法。杨志玖指出:“……谐音与会意兼备的译法,在《华夷译语》中还是个别现象,在《元秘史》中则普遍应用了。这种音义兼备的译法,是汉字的特点和优点,可能由《元秘史》开其端而由陈先生首先揭示其奥秘。前人读《秘史》,或习而不察,或不以为异,或熟视无睹,只有等到陈先生,才以敏锐的眼光,精细的心思,辛勤的劳作,发现并总结其中的规律”[6]。
陈垣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于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雕板印行,在此之前,陈垣在给姚从吾的信中说:“我近为《元秘史》译音用字作一文,尚未敢付印,谨将目录抄呈,改日或为抄一份呈政也。”[1]264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文中,他还考证了俄京所藏《元秘史》的来历,并去信告知时任《东方杂志》主任钱经宇,谓“俄主教拍雷狄斯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在中国所得之本。今承先生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吾人至深感谢。”[1]109-110陈垣曾用顾千里原校本校对叶氏刻本得讹误数百条,并打算用钱经宇赠给北平图书馆的鲍本再校对一次。以上二例,足见陈垣治学严谨。
三、陈垣书信关于《元典章》的研究
陈垣在校勘学上有很大的成就。他“就故宫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和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7]于1931年,他写成《沈刻之元典章校补》⑨、《元典章校补释例》,总结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后一著作后易名为《校勘学释例》⑩。他曾多次去信胡适乞求对方指正,如“《元典章校例》已遵示改正数点,仍不甚惬意,奈何!兹将序目录呈,乞正。”“《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1]53《校勘学释例》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各种问题。李山对“校勘四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稳固的方法体系使校勘学在面对纷纭复杂的校勘问题时,具有强大的应变力。科学不仅在于它的不断更新,也在于它的相对稳定。校勘四法所赋予校勘学的正是这种稳定功能”[8]。
四、陈垣书信关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
陈垣是全面研究调查《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是四库学专家。在《陈垣全集》第二十三卷与《四库全书》研究有关的书信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陈垣写给与廖世功、樊守执、余嘉锡的信,研究了《四库全书》本的《大唐西域记》。
陈垣细心考证了廖世功所藏《大唐西域记》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底本,《四库提要》称为“吴氏刊本”的指的是吴氏西爽堂刊本。并指出馆臣的疏略。他说:“卷十一第七页‘式修供养’以后一段廿九行凡五百十六字,为宋、元藏本所无,盖据明藏本增入者也。《四库提要》(地理类四)未检校宋、元、明藏本,仅以理想推定自‘今之锡兰山’句起,至‘无量功德’句止三百七十字为明人附记之语,此馆臣之疏略也。”[1]33陈垣进而指出,日本缩印本《大藏经》用宋、元、明、高丽四本互勘的校勘方法是审慎的,这种审慎的方法便是他所提倡的“他校法”。“他校法”重视用多种版本进行对校,不迷信宋元旧版,还强调利用版本以外的各种异文资料。一般学者对日本所刊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多有批评,实际上《大正新修大藏经》也有很多优点,所以才被学术界广泛利用。
五、陈垣书信关于《十三经注疏正字》作者的考辨
在给樊守执的信中,讨论了《四库全书》疑案一则。此桩疑案的焦点在于,《十三经注疏正字》的作者是浦镗还是沈廷芳。甘良勇《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笺证》一文初步探索了这个问题,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则作了深入考察。据李慧玲所考察的清代文献,主流的看法认为作者是沈廷芳,如《四库提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文苑传》二《沈廷芳传》,《清史稿·艺文志》经总义类,等等。还有一批文献是根据《四库提要》所持观点衍生的,如清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十四《仁和沈先生》,清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五《沈廷芳》,清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二十七《沈廷芳》,清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之《沈廷芳》,清李元度纂《清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诸襄七先生事迹略》附沈廷芳,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七十七《沈廷芳》等,它们与《四库提要》所持观点一致,均认为《十三经注疏正字》的作者是沈廷芳。
在近代文献中,也有认为其作者是浦镗的,但这样的文献较少。如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八《献县学案·浦先生镗》载:“浦镗,字金堂,号声之,一号秋稼,嘉善人,廪贡生。……先生独究心注疏,每遇古籍善本,辄广为购借,于文字之异同,参互考订,前后历十二年,成《十三经注疏正字》八一卷,兼综条贯,抉微纠谬,不在陆德明下。仁沈椒园为御使时,尝录存其副。后携书北上,及丧归,则原稿已失。至嘉庆中,阮文达元撰《十三经校勘记》,犹屡引其书焉”[9]。
陈垣在1926年给樊守执的信中明确了他的观点。经过他的考证,《十三经注疏正字》的作者是浦镗无疑。根据陈垣信中所述,其中强有力的证据是,沈廷芳在作《浦声之传》时明确表示《十三经注疏正字》一书为浦镗所撰。陈垣这一证据应以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为主要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八曰:“案廷芳为浦镗作传云‘《正字》书存余所,故人苦心,余当谋诸剞劂,芳得附名足矣。’而镗弟铣作《秋稼吟稿序》云‘《正字》书沈椒园先生许为付梓,今已入《四库全书》,而非兄之名也。’据此,则是书为浦镗撰,非出沈廷芳”[10]。
陈垣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将此书作者误为沈廷芳,是因为书稿在沈廷芳家,四库馆也没有加以考察,采进时便误以为此书作者便是沈廷芳。这样看来,清代文献学著作如《四库提要》认为此书作者为沈廷芳的记载是四库馆臣失考之过,而后来根据《四库提要》观点的清代诸多文献便是在此基础上一错再错,由此导致了认为沈廷芳作《十三经注疏正字》的观点成为清代文献的主流。
陈垣在信中列出他的三点看法,兹录于下:
一、《四库》编纂之例,除官撰诸书外,生存人不录。故《四库》书以生存人得录者仅一毕沅撰之《关中胜迹图志》,可参考《简明目录》地理类《关中胜迹图志》条。沈廷芳纵能躬与《四库》事,何能私自为此。二、沈廷芳是否曾躬与《四库》事至易考。《四库》书成后,凡曾参预其事者,无论生卒,均得列名《四库总目》卷首。今《四库总目》卷首所列职名三百五十余人,并无廷芳名,廷芳何能为此。三、据汪中撰《沈廷芳行状》,廷芳卒于乾隆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始下命编纂《四库全书》,时廷芳已前卒矣。[1]73-74
这三点证据足以证明此书不是沈廷芳所作。
六、 陈垣书信关于《通鉴胡注表微》中爱国主义的阐述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陈垣对“史源学实习”一课进行改革,在课堂上讲全祖望的《鮚埼亭集》,以“正人心,端士习”[1]92,并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在民族危难关头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在1950年给席启駉的信中,曾回忆道:“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1]337陈垣从1944年开始写《通鉴胡注表微》,为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所感动,他此时的心境与那时的胡三省是相仿的。在此书中,陈垣“对身之生平颇有所叙述”[1]482,这是前人著述中没有注意到的。
《通鉴胡注表微》的开篇便是《本朝篇》,可见其以祖国为中心的主体意识高扬,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卷首说:“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11]胡三省在国家沦亡以后,依旧怀有故国之思,认为祖国不能忘却,称宋为“我朝”“我宋”“吾国”“本朝”等,而不是“亡宋”。这正如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所说:“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以后,故《四库提要》称之为元人。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11]陈垣之爱国,一如胡三省之爱国。可以说,陈垣是用做学问来抗日的,他说:“所有《辑覆》、《佛考》、《道考》、《诤记》、《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1]337
陈垣于1945年1月完成《本朝》和《出处》两篇,他写信给陈乐素,感慨成书之艰难。信中说:“成书殊不易,材料虽已找出一千一百余条,未必条条皆有按语。如果按语太少,又等于编辑史料而已,不能动众。如果每篇皆有十余廿条按语,则甚不易。”[1]848-849再加上当时战火纷乱,人心惶惶,陈垣的治学环境极其恶劣,《通鉴胡注表微》的写作便难上加难。吴怀祺认为此书“反映了近代史学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出陈援庵先生的学识,民族爱国的情操”[12]。
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重视在史学研究中的实证性。他在与陈乐素的信中说:“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1]849接着,他指出须寻找与胡三省生活时代相近的历史事实的缘故,即“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1]849陈垣先生强调史学研究不能离事而言理。事实上,陈垣先生绝大多数著作都充满了实证主义的精神。
七、陈垣书信关于自己治学精神演变的阐述
中国近代史学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陈垣在书信中不止一次谈到史学风气转变这个问题。1943年,陈垣去信方豪,说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此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1]921950年,陈垣写信给席启駉,谈了同样的问题:“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1]337此外,陈垣在1954年的一封信中指出:“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惜衰老时觉不及耳。”[1]392因此,他决定“今后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1]392关于这一点,在他给胡适的公开信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1]63后来进一步明确了上述治学方法:“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1]63-64
由此可以看出,陈垣史学思想的转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31年之前,推崇钱大昕“精密之考证”;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抗战爆发前,提倡顾炎武的经世之学;三是抗战爆发后,研究全祖望正人心、端士习的治学精神;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毛泽东选集》,用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研究史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综上,陈垣书信集所反映出来的学术人生是丰富多彩的,有好些地方是其学术著作中所没有体现的,这对于我们研究陈垣先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注释:
① 载《书城》,2010年第7期。
② 载《读书》,2013年第3期。
③ 载《读书》,2011年第3期。
④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陈约(1909-1999),陈垣第三子,书法家。
⑥ 桑原骘藏,日本大正昭和时代的著名东洋史学家,留学法国,京东大学教授。
⑦ “也里可温”是元代对天主教的译音,陈垣著有《元也里可温考》一书,收入《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至顺”是元朝文宗皇帝图帖睦尔的年号,在1330年5月-1333年10月。
⑧ 陈垣撰写有《元秘史音译类纂》、《元秘史校记》、《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三书。收入《陈垣全集》第十一、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⑨ 收入《陈垣全集》第十册,名为《元典章校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⑩ 收入《陈垣全集》第七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