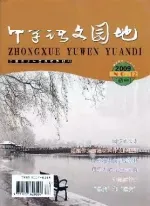挖蚓人
桑义汉

酒后闲谈,爷爷总是给我讲述他年轻时挖蚯蚓的故事。
那时爷爷刚成家,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爬下床,干刨上几口大白饭,骑上那辆锈得不像样的自行车就跟着村里的挖蚓大队出发了。所谓的挖蚓大队是挖蚓人自发组成的,因为都在一个村,路上也好有个照应。那时我们村大概有四五百人,每天披着朦胧的星光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行至大路时又常常会遇见别村人,场面也颇为壮观。不过人虽然多,却并不嘈杂,无需多少言语,仿佛是一种默契,因为大家心里想着的都是今天的收成。
他们挖蚯蚓不是为了卖钱,而是用来喂鳝鱼。那时候,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个不大不小的鳝鱼池,卖鳝鱼可谓是农民们除种田外唯一的收入了。鳝鱼喜吃蚯蚓,用蚯蚓喂出来的鳝鱼肉质肥厚,更能卖出好价钱。因此,每到鳝鱼生长的旺季,即小暑、大伏那阵,每户都会专门派出一个人出去挖蚯蚓。
这一出去可不得了,近的话去二三十里外的荡区,远的话得去八九十里外的涟水县。通常凌晨两三点出发,骑到目的地天刚蒙蒙亮,他们可没空歇歇,提起铁锹就开始挖,接近中午才收工,完了又匆匆往家赶。
这挖蚓人可不顾你当地人的感受。荒野里没有蚯蚓可挖时,就跑到人家田里乱挖一气,甚至连田埂都给人家挖烂了,因此他们深为当地人痛恨。有一次,爷爷摸黑骑自行车到了涟水,挖完蚯蚓回头,却发现自行车被人扔下了大河沟,没办法,只得徒步走回了几十里外的家,到家时,已近半夜。
提到涟水,爷爷总是眉飞色舞地说:“涟水那个地方穷呐,他们那边包的饺子都没有菜馅的,全是豆角包的。”在一旁的我便诘问道:“他们那么穷,你还去挖人家田?”爷爷呷了一口酒,叹道:“孩子,那个时候也是没办法啊。”我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的确,在那个年代,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没有人会管你是不是更穷,大家都只管填饱自己的肚子。
挖蚓人有时候并不能如愿以偿,满载而归自然更是少有。不过有时也会有意外的收获,邻居家的大妈有一次去挖蚯蚓时挖到了一尊银灿灿的菩萨像,喜得她宝贝似的一直珍藏着,逢年过节就拿出来拜,连嫁闺女时都特地让女儿拜了才出门。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乡下养鳝鱼的自然也少了,挖蚓人也近乎绝迹。挖蚓似乎永远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众多像我爷爷一样的挖蚓人远去的记忆。那个年代虽然很苦,却也有着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无法体验到的生活滋味,以至于爷爷每每回忆起那个年代,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爷爷至今仍把挖蚯蚓的工具安放在家里,留作念想。
挖蚯蚓是一件苦活,却也是我们家庭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它就像美酒,得慢慢呷,细细品。爷爷每次讲述挖蚓人的故事,都会慨叹:“那时候,谁又想象得到,我们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知足了……”
[点 评]本文以一种过来人“惯看秋月春风”的闲话笔调,讲述了挖蚓人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个生活真谛——也许,只有在苦日子里活出滋味的人,才能真正品出好日子的滋味。文章选材独特,情感质朴,无意说道而道自见,颇有汪曾祺小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