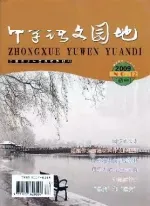外婆的温度
杜若冰/文 吴应海/评

小时候,我最喜欢土豆了,外婆也最爱土豆,分别是,我喜欢吃,外婆喜欢种。
外婆将土豆当个宝,土地还未收获时,她就时不时来看看,拂起这片叶,翻翻那边土。如果土是透明的,外婆恐怕就天天趴在那看了吧。每每这时,我就站在外婆身后,痴痴地笑她。风吹过,土豆的叶随着夕阳的旋律轻轻摇摆。
好不容易等到可以收土豆时,外婆便经常带着我去挖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挖累了,外婆就站在田埂上,她身上的衣服被风吹得鼓鼓的,像是要起飞一样。每当这时,我都觉得外婆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我蹲下身,拿着一个小木棒,细细地抠着土豆边缘的土,待看到那浅黄色的薄皮了,我便开心地扔掉木棍,抓住土豆白色的茎,猛地向上一拔。清脆的断裂声响起,我跌坐在田塍上,手中还死死握着一片大大的叶子。
外婆见了,也蹲下身来,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指绕着土豆周围的土一转,勾起食指一抠,一颗硕大的土豆便被大地挤了出来。外婆拿起土豆,轻轻一抖,土块便落了下来。外婆又挖了几颗,然后将土豆递给我,领着我回家去。
风有点凉,但手中的土豆却散发着暖意。我低着头想,土豆长在土地里,被大地呵护着,土豆是温暖的,那大地的温度会是多少呢?
到了家,土豆被外婆切成了均匀的细丝,经过油与火的双重作用,变成了餐桌上的一道菜。我趴在桌子上,晃着够不到地的腿,深吸一口土豆丝散发出来的香气。外婆只吃了一点点,便将一整盘土豆丝推到我面前,宠溺地看着我将土豆丝消灭干净。
饭后,外婆在小溪边洗衣服。我就趴在草坪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找着话题。“外婆,土豆为什么叫土豆呢?”我好奇地问。
“土豆啊,就是土疙瘩,土里生出来的豆子,”外婆洗衣服的手顿了一下,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加了一句,“咱们这儿,土豆还叫地蛋,地里的宝贝蛋。土豆啊,就是大地的孩子。”我点了点头,觉得大地母亲真有福气,孩子那么多,又那么讨人喜欢。
外婆用辛勤种植出的土豆将我喂养成一个结结实实的人,我看着自己微微发黄的皮肤,觉得自己就像是大地的外孙女,大地就是我的外婆。外婆曾对我说过,长在地里面的都是好东西,因为它们聆听着大地的脉搏,所以它们懂得大地的快乐与痛苦。
现在我搬到了城里,菜场就在楼底下,外婆却坚持给我送土豆。她说,外面的土豆都是人给催产出来的,不好吃。我摸了摸外婆刚刚送来的土豆,依旧透着几分暖意。我闭上双眼,感受着从土豆表皮传出来的温度。我用了七年的时间,量出了大地的温度,那正好是人体的温度,也是外婆的温度。
(选自 《做人与处世》2017年17期)
[解 读]本文采用了借物抒情的写作方法,先以“土豆”为线索,记叙了“看土豆”“拔土豆”“吃土豆”“议土豆”“送土豆”等情节,突出了外婆的勤劳以及对 “我”的疼爱。在此基础上,作者有感而发,以“我用了七年的时间,量出了大地的温度,那正好是人体的温度,也是外婆的温度”委婉表达了对外婆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而在作者笔下,外婆不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还是一个说话富有诗意甚至含有哲理味的人,比如“咱们这儿,土豆还叫地蛋,地里的宝贝蛋。土豆啊,就是大地的孩子”一句,充满童趣;再如“长在地里面的都是好东西,因为它们聆听着大地的脉搏,所以它们懂得大地的快乐与痛苦”,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