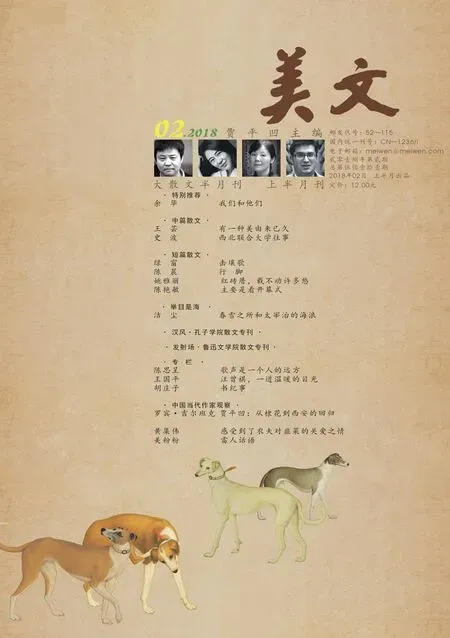红砖厝,载不动许多愁
◎ 姚雅丽
草色烟光,芳菲漫道,春正好。我们回老家祭扫祖坟。锄草、添土、焚香、上供品,重复着往年的程序,悲辛亦无新意。只是在祖母坟前,我们停留的时间似乎比往年更长一些。从厦门回来的堂哥说:“给祖母多供些糕点,多烧些纸钱吧。”于是又有许多纸钱纷纷扬扬,停歇于祖母坟头。恍惚中,祖母清瘦的身影若隐若现,孤寒的目光穿透迷离的阳光,抚摸着她挚爱的子孙。随后我们移步至二叔坟前,这时,年逾古稀的老父又折回去,在祖母坟前默默地站了许久,我不知道,父亲和他的母亲说些什么。父亲步履蹒跚地踩着荆棘,满头白发在苍松翠柏中分外扎眼,我忽地鼻子一阵发酸。我知道,有些距离永远无法抵达。那是河流深处,永远无法触及的悲伤。我们蹚过一条条溪涧,以为可以改变行程,岂知,一切从出发前,就已经规定了结局。
上完坟,回到家里,一家子坐在古厝大厅吃茶话仙。堂哥突然问我爸:“叔,我爷爷从柬埔寨寄来的那张照片还在吗?”父亲起身带堂哥进屋去,我也尾随进去,拿出手机,翻拍了那张老照片。照片上的爷爷神情倨傲,逼人的英气一览无遗。他在柬埔寨娶的番婆面容清丽,俩人这样一站,愣是一对才子佳人。七个孩子北斗七星般一溜排开,俱是身材颀长,浓眉大眼。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父辈的影子,我的影子,家族的影子。照片上这一家子,和我们天各一方,却无时无刻不互相撕扯着。当年爷爷策马于“割香”队伍的头阵,警兵追杀而来,爷爷眉目如炬,扬鞭呼啸而过,如惊鸿掠过长空,消失于尘嚣滚滚中。

姚雅丽 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丰泽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丰泽文学》副主编、《丰泽文化丛书》副主编。出版《雨夜的浪漫》《一个人的荒凉》《香水与爱情》三部散文集。
厦门港。离别的码头人头攒动,生离死别匆匆上演。我的爷爷卓然立于远洋客轮的甲板上,送行的亲友对着海上茫茫烟波,叮咛再三:“等这边风声过了就回来……回来啊……”可年轻气盛的爷爷毅然决然,头也不回。亲人的嘱咐被咆哮的浪涛冲走了。
那一年,是一九四七年。我的祖父二十六岁,祖母二十五岁,我父亲四岁,二叔不到两岁,姑妈尚在襁褓中。细水长流的故事刚拉开序幕,却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
家族的命运,在爷爷跃马扬鞭那一刻,已赫然划出一个悲怆的破音。
南洋,是避难所,也是新生地。远涉重洋的爷爷并没有陷入穷途末路,而是很快地搭起新的人生框架。娶了番婆,养了儿女,他没有对国内的妻儿隐瞒一切。爷爷的内心是坦然的,以他闽南男人的思维来看,这似乎不是他的错,甚至是一种得意或炫耀。“侨批”一封封寄来,刻着我父亲名字的金戒指如今传到我侄儿媳妇的手上。锈迹斑斑的钢笔有浓郁的情绪,似乎是远方亲人模糊影像的物化呈现。漂洋过海而来的全家福,幸福的笑容不加掩饰。奶奶看着照片上自己的丈夫,这个男人是她生命的全部,却又遥不可及。时光深不见底,淹没了悲欢。奶奶看着照片,似乎很平静地对他的长子,我的父亲说:“这是你三弟、四弟、五弟……这是你牡丹妹妹……”接受命运投的毒,伤到骨髓也不给自己任何出路。
我父亲、二叔、姑妈,在父爱缺损中长大。成长的过程太仓促了,似乎跳过了童年。我相信,他们的心灵里肯定有一个难以填补的空洞。一种难以言喻的伤,在家族上空,阴霾般笼罩。
爷爷不管不顾,抛家去国,千里孤蓬,一别成永诀。他的几个兄弟原是浮浪子弟,赌博游冶,不事稼穑,我家由拥有良田百亩,稻米满仓的乡村大户人家迅速败落下来,爷爷的大哥无奈携眷迁居厦门海沧,其他兄弟也流离失所。不过几年工夫,姚家四分五裂,只留下我的奶奶带着儿女,守着红砖厝,守着深巷大宅里深不见底的凄苦。多少夜阑更漏,多少春尽花残,我的奶奶把秋水望穿,天涯望断,她是如何把这一切碾碎,和着苦涩吞咽?
四时听雨,午夜入梦,梦里花好月圆,醒来伊人憔悴损。红砖厝,是地网天罗,把奶奶一生的幸福一网打尽。
七十年的时光莫名消失,而萦绕我心头的那团迷雾却不曾消散:是什么让我的爷爷如此决绝?莫非这次逃脱于他而言,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难道从小养尊处优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难道红砖白石的大宅不是他想要的?难道我的奶奶,坝田(奶奶娘家)一枝花不是他称心如意的伴侣?难道长期的禁锢在他的心里孕育出叛逆的火苗?
我的目光掠过一座座或深或浅,或虚或实的红砖厝,停留于我家的老宅上。老宅安静地立于尘嚣中,有一份遗世独立的凛然。它曾经呼风唤雨的主人,如今也成了旧时代的遗物。从古大厝的每个旮旯渗出来的陈腐气息,幽灵般地出没于新世纪的楼宇花树间。
我曾无数次斜倚老宅的红砖墙,拍下惊艳的美照。老宅房前龙眼,屋后荔枝,四季葱茏。翘脊上布满苍苔,一丛不知名的绿色植物贸然立于瓦楞上,倔强地宣泄着生之昂扬。时至今日,我的父母依然安居于此,好像生了根一样,挪不动。或者像老宅一样,老了,走不动了。它曾经簇新锃亮过,那是我爷爷奶奶的时代。我爷爷身上集结了闽南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海盗精神、江湖义气等多重性格特质。而我的奶奶,自打被我爷爷用大红花轿抬进红砖厝,就已经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她笃定的人生信念。
父亲的家里尚保存着奶奶办丧事时的照片。黑白照片一片惨白,悲伤无处安放。祖厝厅堂上,奶奶的遗像透出阵阵寒气,心气极高的人更有浓烈似酒的焚烧。奶奶原是冰山上的雪莲,在深不可测的孤独中淬炼自己。苦和痛被冰封,无声地注入茎脉、叶片、蕊尖。她的痛全部用来成全自己,也用来摧毁自己。这种可怕的杀伤力,外在的呈现却是那么强悍!奶奶凭一己之力,左冲右突,终成家族的精神领袖,乡村的风云人物,连男人都望其项背。那些威严庞大的事物,实则不堪一击。所有的压力、委屈、伤害,全都压抑于体内,在血管里、细胞里发酵、蔓延,终致五内俱伤。奶奶就这样,在五十岁那年,撒手人寰。奶奶走得太匆忙,等不到许多故事的发生。她一开始就抛弃了自己,替那个离她而去的男人活着。所以拼尽了一切,隐忍了一切,把一切伤都指向自己。她像男人一样耕田犁地,砍柴伐薪,像男人一样操持世事,应对内外。在煎熬和透支中,过早地油尽灯枯了。我不知道,奶奶有没有后悔自己一生绝望的守望?在闭上眼睛那一刻,她是否有解脱人生苦难的轻松?我曾经这样设想过:奶奶不管不顾,丢下爷爷的古大厝和一群儿女一走了之,会是怎样的结局?
但没有如果!奶奶的三寸金莲能走向哪里?红砖厝处处有出口,却处处封锁。
夕阳刻意模糊人世悲欢,可我的悲戚却难以消融。我的脑海中摇曳着家族的另一位悲剧女性———我的姑奶奶。
如果说奶奶是守着一群子女,守着南洋时断时续的“侨批”把日子过下去,那么,我的姑奶奶,她要守的是什么呢?丈夫下南洋,音信全无,也无留下一男半女,只遗一座红砖厝!姑奶奶家的红砖厝我没有去过,却莫名其妙地在脑海里格外清晰。门前流水,屋后青山,一对璧人,一出童话般的爱情故事拉开帷幕。可鸳鸯被尚暖,石榴尚未结籽,还没来得及把缠绵的情话对伊讲,距离已成了天上人间。姑奶奶守了一辈子的活寡,却没有守得云开见日出,而是把自己封锁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从踏入夫家大门那一天起,就走进一个命定的归宿。那个少年郎已日渐模糊,却给她挖了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时光已抛弃了她,从碧玉年华到耄耋之年,漫长的等待荒凉寂寞。
红砖厝如残阳泣血,相思树的花蕊是熬黄的泪滴。姑奶奶老迈的身影如前尘往事。听父母说,姑奶奶年轻时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发染秋霜时依然腰身挺直,眉眼如画,只是目光如寒星,仿佛来自遥远的雪国。姑奶奶领养的一双儿女,给她带来了儿孙绕膝,却没能带她走进现世的花红柳绿。她的曾孙媳妇,眉眼间的戾气同曾祖母如出一辙。虽没有祖辈当年的山水迢迢,青鸟难抵,虽近在咫尺,爱人的心却隔着万水千山。姑奶奶看着曾孙媳妇哭花的脸,脸上浮起的竟是不易觉察的幸灾乐祸。“闽南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姑奶奶对曾孙媳妇的劝告,摒弃了任何感情色彩,似乎忘了自己曾经寒夜孤灯,泪湿鸳鸯枕。
龙眼树细碎的花蕊是伊人碎了一地的梦。越过浓荫蔽日的老榕树,往事的影子依稀。望向山水迢迢,却发现,岁月已老,我还在这里等候,可对岸已无人。
苦到极处莫言苦。姑奶奶安然接受无法逃脱的命运,终得以高寿终。
时光在红砖厝的翘脊上凝固,欲做飞翔状,却被金丝银缕缚。曲径回廊,玉人阑珊。古大厝的爱情故事如墙上的雕花,风欺雨袭,年久日深,苍茫的世事一而再地覆盖它。以至于回首时,已衰腐残损。恰如午间小憩,红砖厝陡然入梦来。它跋涉万水千山而来,许多情节依附在上面,岁月一笔一画,写到结局,已湖山寂寞,无语哽咽。
世界被同化,同时被摧毁。新鲜的事物覆盖着旧时光的痕迹,也把红砖厝挤到了拥趸的角落。我总是在一片陌生里不知所向。阳光不再自由,高楼切割时空破碎。我在如血残照里,像一个孤独的旅者,踟蹰街头。我在寻找什么呢?是寻找家族女性的命运魔咒,还是闽南女性的命运谜底?
直至行到闽南乡间,或泉州老城区,我迷惘的目光不期然地与红砖厝相遇时,猛地有一种魂兮归来的怆然和欣然,我的悲欢无以言述。
“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起。”“皇宫起”的传说,使闽南红砖厝蒙上几许贵族色彩。相传开闽王王审知体恤爱妃(泉州惠安人)思乡之苦,一句“寡人赐你府上建皇宫式房屋”,使得泉南大地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纷纷仿效王府造起了宫殿般的华屋。其实闽王说的“你府上”是单指王妃娘家,传旨的太监误以为是整个泉州府。于是,本属皇家宫阙、帝王宗祠的红色建材,在闽南登堂入室,“皇宫起”民居红云般怒放晋江两岸。
美人如玉,红砖厝似幻。阴差阳错在闽南落地生根的红砖厝,竟与爱情有关。闽南女人也宿命般,被囚禁于红砖厝,生生世世来偿还这一场王者与妃子的盛大爱情之债。当然,君王的金口玉言,只是一句谶语,更难以逃脱的是命运的魔咒,它一环一环,纵横交错,直至打成死结。
《泉州府志》曾载:“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沿江而居……”寥寥数语,浓缩了无数风云。那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原动荡,衣冠仕族踉跄南下,行至闽南,望见一条江,遂择地而栖,沿江而居,成了闽南人的先祖。把这条江,称为晋江,把母亲河的意象安放在它身上;把那座桥,叫洛阳桥,用它来丈量山河的距离。纵然远徙,仍把家园扛在肩上,把血脉融于生命,把整个人生记忆搬过来。
一场迁徙,一场浩劫,一次心灵大震荡。铁蹄声声,家山如梦,故园渺茫。一场千里远迁,把一切击碎!家园破碎的殇从此刻入命运里,在每一个紧要时刻,都会阴魂般地跳出来,掐住命运的咽喉,让你不得逃脱。因为害怕再失去,所以费尽心力,垒建固若金汤的家园;因为害怕再失去,所以先迎你进入城池,再想方设法让你缴械投降。
闽南男人就这样,携着先祖的印记,落地生根,也把潜藏的欲望,融于家园的每一根楹柱间,每一方镌刻里。他们垒造起了一座座“小宫殿”———红砖厝。红砖厝成了闽南地区的建筑符号。砖石上的雕花意韵含蓄,是无数梦想的叠加。闽南人的精神气质,不,闽南男人的精神气质出没于红砖厝的每一个细节里。男人掌控了财政大权、宗法秩序,也就掌控了整个局面。他们关起门来,成了红砖厝里的帝王。妻儿,是他膝下的臣民,是他颐指气使的对象,连爱情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
红砖厝撑起的是闽南男人的筋骨,流淌的是闽南女人的血泪。这血泪,从沉重的典籍,从咿呀的唱词里流出来。不信你随我翻开泉州穆斯林金吉家族的《金氏族谱》——
《金氏族谱》中记载着一段《清源丽史》。元统年间,安溪富翁凌氏携爱女凌无金避乱于泉州城北朝天街。凌无金于元宵佳节赏灯时,邂逅城中望族伊府公子伊楚玉,才子佳人私定终身。可凌翁却把无金许配给富商黄家,伊楚玉也被迫娶了朝廷重臣乔家千金乔珍珍。无金抗婚,投河,继而出家为尼。珍珍委曲求全,含泪劝夫迎娶无金。楚玉如愿,双娇随侍左右。后元兵叛乱,楚玉投笔从戎,战死沙场,二女俱殉夫而亡。凌无金和乔珍珍这两位金尊玉贵的富家小姐,本可以纤手弄玉,飞花点翠。可她们却放弃尊严,放弃幸福,甚至放弃生命。就像雕花依附于红砖,闽南女子也完全放弃了自己,依附于红砖厝里的男人。一切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而发生于泉州洛江梧宅的经典悲剧《陈三五娘》也是一出殉葬式的闽南爱情故事。曾经为爱午夜私奔的陈三五娘,在家族恩仇前,相携往红砖厝里的古井纵身一跳。于是,最有可能成为闽南爱情圣地的陈府红砖厝,终成了埋葬爱情的坟墓。大难来时,爱情轻如飞絮。这就是陈三,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闽南男人的血液。他的爱情,也是闽南式的。宁肯取义成仁,也不成全爱情!渗入骨子里的意识像一把利刃,刺向自己。
时光辗转,山河呜咽。红砖厝处处有出口,却又没有出口。动荡,漂泊。千里迁徙的不安全感植入闽南男人的血液里,这种不安演变成强大的力量,鞭策着他们不停地打拼,无止境地追逐财富,从而使控制的欲望不断发酵,最终成了他们的性格因子,成了飘荡在红砖厝上空的集体意识。闽南女人的整体形象被稀释,成了男人强大影像下的模糊陪衬。
宫殿式的红砖厝,沉重的大门“咿呀”一声关闭,男主人就成了说一不二的独裁者。女人从进入城堡那天起,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权利。一家之主的居室紧挨着大厅,俗称“大房”,大房占据了整座大厝的最佳视点,把控全局,总揽一切,在布局时已不动声色地把唯我独尊的霸权思想泄露,大男子主义成了闽南男人的标签!
房屋的格局就是命运的符咒。先建造起屋宅,随之形成了一套秩序,融进一种无声的语言,沉默的力量,甚至是命运的锁链,从历史深处,一节节蔓延而来。我的心不堪重负,视线仓促地从史籍中逃脱,投注于南安官桥的蔡资深(蔡浅)古大厝群。
号称“闽南小故宫”的蔡氏红砖厝一片锦绣恢宏,是闽南“皇宫起”大厝的典范。十三座汉式古大厝,大小房间四百多间,占地一百多亩,历时五十二年建成。主人蔡浅耗一生心血,筑起一座城池。把闽南建筑的精华荟萃于此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附丽于其上,而不可捉摸的命运之神也在精雕细琢中出没。
蔡氏古大厝的红颜殇,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泉郡名士、教育家、状元吴鲁。我游荡其间,吴鲁瘦劲清俊的身影翩然而至,他深邃的目光穿透红砖厝的翘脊飞檐……
故事刚开始依然美好:才子佳人,门当户对。吴鲁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吴明珠许配与世交知己、南安巨贾蔡资深的侄儿蔡世添。为了迎娶状元府千金,蔡家特地在大厝群里建了一座精巧的小姐楼。可天妒红颜,佳人命薄,花轿还没出发,娇贵的千金小姐就染疾香消玉殒了。为不负婚约,也圆明珠小姐遗愿,状元公吴鲁遂让同宗侄女吴宝珠续缘嫁入蔡府。可叹天不作合,新婚的大红“喜”字尚未褪色,蔡家公子就撒手人寰。留下新妇独守空闱。吴宝珠立志守贞,从此未下绣楼一步。一座绣楼,连同楼上的女子,陷于红砖厝的丛林里。主人耗五十年心力建一片江山,只期子孙万代,家业永固,自然无暇顾及绣楼上压抑的低泣。楼上的女子在,与状元家的姻亲关系就在,至于她如何熬过死亡一般的寂寞,已无足重轻。
结局已摆在那儿,明知是空等待,却还要等下去,等到春尽花残,杜鹃泣血,只等着成为厅堂上的一个灵位,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心如死灰!
某种强大的崩溃如雨落尘埃。我在斜风细雨中走近小姐楼,仍被一种沉重的悲伤压得难以喘息。人亡楼空,徒留门楣上“安贞”二字,任后人扼腕叹息。吴家小姐的三寸金莲,走不出蔡氏大厝群层层叠叠的封锁,更走不出自己心中的樊篱。我踟躇于古大厝深长的巷子里,阳光影影绰绰,依稀可见闺阁女子一生的隐痛和像时光一样绵长的孤独。
雕花琢石,是命运的暗喻,是蚕儿一样的作茧自缚。雕进了心思,却成了逃不出去的迷宫。一格一格的红砖白石,原是精心预设的华丽人生,却成了镜花水月……
是什么力量在吞噬着闽南女人的青春呢?生活使人们把目光放在别处,没有人把目光长久地留停在她们身上。“爱拼敢赢”的闽南男人在携带千年、挥之不去的“失去”阴影里,开疆辟地,欲望升级。这使他们浑然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当成红砖厝里的王。女人也在年复一年的煎熬中,浑忘自己,失去抗争的意识,而把承受一切当成命运的嘱托。
一座红砖厝,就是一个闽南女人的天下,一代一代闽南女子的生活被无声复制下来。脚步被锁住,目光被禁锢。爱情、尊重,对等的情感仿佛是天方夜谭。直至她们压抑半生,鬓染霜,泪痕干,红颜老,再把枷锁套在另一个女人身上。用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指挥新一轮悲剧的上演,也把自身的悲剧演到山穷水尽。这是一个本可以解开的魔咒,可念着咒语的人,同时把自己诅咒。这种可怕的力量,已经融进闽南女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她们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揖手让出掌控命运的桨。
世界日新月异,而红砖厝内,红砖厝外的闽南女子,依然逃不出红砖厝的阴影吗?
我穿过春日午后的阳光,去探访活在现世,却依旧蜷缩在旧时光里的世纪老人。
泉州惠安东岭镇三村,年近九旬的许叶阿婆静静地坐在石墩上。风卷起她的头巾,一绺白发在风中颤抖。老人凝望着门前长长的甬道,似在远眺,又似在等待。她在等待什么呢?
“我们结婚两年后他就去厦门打石场做工了,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 语未尽,声已咽……
时光溯回一九四七年,二十一岁如花似玉的许叶姑娘坐上花轿,被郑生财欢天喜地娶回家。一对小夫妻你侬我侬,忒煞情浓。
婚后不久,郑生财与同村多名闽南汉子离开惠安,往厦门石场谋生。不久,厦门解放。迫于形势,郑生财和一起做工的惠安石匠们去了金门,随后又辗转到了台湾。
这一别,竟是一生!
等待的苦涩,生活的重负,让许叶绝望到试图跳海轻生。面对滚滚而来的海潮,她又爬了起来。如果为了自己的解脱,她情愿逐浪而去。然而她不能死,她得让红砖厝里四时花开,香火不断,她得为红砖厝而活!为了这个信念,许叶抱养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招赘了一个女婿,郑家总算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了。
“在海峡的那边,有你们最亲的人。”老人总是这样对儿孙说。可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能等回海峡对岸的亲人吗?
思念的泪,比海水还苦涩。在漫长的岁月里,临海劳作,再苦再累,许叶都愿意做,为的是某一天,能看到那个她梦牵魂系的身影。但潮有汛,人却无音。一声承诺,耗尽一生等待。世纪老人的一声呜咽,连同红砖厝翘脊上最后一丝光,一起沉入无边的黑暗中。《望春风》那么凄惨的曲调,似在诉尽人间伤心事,那是苦难母亲的绝唱。
惠安阿婆的叹息声是那一辈闽南女子宿命的回音。沉重的大门“咿呀”一声,把伊人的心、伊人的梦也碾碎了。也许,男人当初也曾有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念想,可是,初心就如初潮,很快被纷至沓来的海上花所覆盖。
世界千变万化,唯闽南女子的命运根深蒂固。男人们用红砖厝来寄存自己的野心,也用它来囚禁女人的一生。当年的闽王妃黄小阙,泉州北门的一代双娇,传唱千年的黄五娘,金尊玉贵的状元千金,还有我的祖母,我的姑奶奶们,以及今日,坐在红砖厝中望眼欲穿的许叶阿婆,她们的人生舞台没有观众,是只有一个人的专场演出。每一座红砖厝,都是一座沉默的堡垒。在沉默中坚硬,在沉默中老去,从一开始就已经老去。闽南女子,在苦难面前,那么有韧性,又那么轻易地向尘世妥协。她们只修今生,把泅渡自己的宏愿交给来世。她们越过一座座荒丘,淌过一条条河流,终于抵达相同的归宿。悲伤也罢,欢乐也罢,总有个尽头。当你与人间再无瓜葛时,永恒的乐土将对你张开怀抱。
我走在乡间,或者街市。夕阳西斜,满目光辉,红砖古厝折射出一片耀眼的红。风很轻,我张开羽翼,穿过一些声音。明知留不住,回不去,却踏雪寻梅般寻觅它。我到底在寻找什么?我是在寻找一条河流,一条命运的锁链,甚至,在寻找那遥远的源头。失去了源头,所有的悲欢也变得不可捉摸,命运,也似乎不那么真实了。我告诉自己,我是新时代的人,我呼吸了自由的空气,我是不会像我的祖辈们那么傻,守着徒有其名的一座宅子,一个遥不可及的人,让青春空惆怅。我得携我所爱,越过高山,穿过丛林,快意飞翔!我是得有怎样令人怦然心动的纯粹的美好时光啊!可是,当我一直往前走,却越来越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宿命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仿佛踩在她们的脚印上。
阳光凄迷恍惚,带着某种暗示,某种忧郁和慈悲,它从一开始就看清了结局,却从不说。它知道:守与放,苦与乐,仅一步之遥,越过去,已是来生。
清风拨弄流水,山岳仰望苍穹。我走了千万里路,高山、河流、田野,都在向我说些什么。我站在残阳如血中,蓦然回首,我的身影印在红砖厝里。
红砖厝,载不动许多愁,所以退缩到新时代的一隅。但它的记忆,它的语言,它的思想却无声地浸入崭新的建筑、新鲜的事物及人的灵魂里。那剪不断的哀愁,像血液一样流淌,像永恒的河流在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