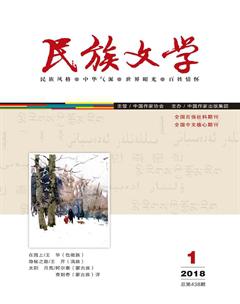入股(小说)
杨兰
缺耳朵趴在猪圈上,头就架在矮墙的上方。猪圈里的架子猪吃饱了,懒懒的,前腿下跪,身体往后一歪,躺下,眼皮挣扎着扑闪两下,睡了,一个挨着一个,呼噜此起彼伏。缺耳朵喜欢听猪睡觉时打出来的噗噗噗的声音。外省妹系着花围腰从屋里出来,一边操着红色长手把的塑料瓢翻搅猪食,一边骂道,这声音都要把屋顶掀翻了,你还真听得下去?缺耳朵笑了笑,往猪食盆那边提猪食去了。
缺耳朵家住在外来村,除了两间翻修过的公房,还有六间牛毛毡棚圈,占地面积在外来村属于大户人家。养猪在外来村没有其他同行,不能成帮派,为了把他家区分开来,村里人叫他家“养猪专业户”,就是独此一家的意思,称呼表明了他家的孤独。同样被称作“专业户”的还有老蔡。老蔡五十岁,媳妇在他还没成“专业户”之前跟人跑了。外来村的两户“专业户”,分别住在村的两头。
正午,老蔡担着豆腐担子往缺耳朵家走来。
缺耳朵家住在村尾,猪圈歪歪倒倒,房顶泛着褪色的白,遠远看去,就像一只干死的形状扭曲的蚯蚓。缺耳朵家喂猪有一段时日了,周围的猪粪也有了相当的规模,气味张狂,一股脑儿往偶尔经过的行人鼻子里拱。
走进小院,见门口七八个塑料桶排成排,在烈日下尽忠职守,老蔡知道缺耳朵拉潲水回来了,他伸着头往桶里看看,桶里的潲水扑哧冒着泡泡,像饿死鬼瞪大眼睛,泡泡变大,破了,剩饭剩菜的油腻味夹杂了些馊臭味,直窜老蔡的眼睛,鼻子跟着惊悚起来。老蔡是缺耳朵家的常客,每次来,他都得对气味适应一番。
外省妹正在主屋左边的矮房里煮猪食,铁锅架在大火上,潲水在锅里晃来晃去,花花绿绿,红红白白。潲水烧开后气味浓烈沉闷,像无数湿热的鼻涕在老蔡身上爬,老蔡的鼻子忍不住收缩,再收缩。一个不小心,左脚踩进了刚从猪圈捞出来的猪粪堆,他提出左脚,甩了甩,继续往里走。
外省妹招呼老蔡进屋坐。老蔡把豆腐桶放在台阶上,朝右边的猪圈走去。缺耳朵正准备喂猪,猪这几天有些拉肚子,源源不断从猪屁股喷出来的粪便使猪圈更加闷热。缺耳朵一边和老蔡打招呼,一边把止泻药倒进刚煮熟的豆渣里。
老蔡往猪圈里看了看问,猪拉肚子好了吗?
缺耳朵搅拌着猪食,说喂了几天药,好多了。
老蔡接着说,会不会中了巴豆?
缺耳朵急说,不会,最近的潲水都是收的。兽医来过了,说可能是暑热导致的。
那就好!老蔡舒了口气说道。这是缺耳朵家的第四批猪仔,也是他家成败的关键。前几批猪喂下来,缺耳朵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欠了些外债。
老蔡不养猪,可他是村里唯一关心缺耳朵家养猪的人。老蔡专门磨豆腐,自磨自卖。缺耳朵家的猪吃他的豆渣。豆渣让两个“专业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惺惺相惜,成了伙伴。
缺耳朵家的猪圈和普通猪圈不同,六个,三个一排分列公房两边,成排的猪圈中间用红砖隔开,有一个半人高。猪槽与猪圈门在同一面墙上,用水泥构建。缺耳朵在猪槽位置往上八十厘米的地方留了一个四十厘米左右的方形口,外面用块石方子向上倾斜着延伸出来,成了运输槽。方形孔上面大概八十厘米的位置有个窗户,人可以伸进木捆子,看着霸道占槽的猪。
缺耳朵挽起袖子,右手伸进猪食里,感觉温度适合后将猪食倒进运输槽,猪仔听到食物落地的声音后拼命往猪槽里钻。猪圈里有十二头小猪,猪槽差不多够猪头伸进去。一些凶悍的猪把前肢伸进猪槽,甚至整个身体都跳到里面,瘦弱的猪便只能在猪群周围焦急乱窜。缺耳朵平时是不管猪仔吃食的,他说猪和人一样,吃食多少有它自己的规则。现在他拿了根小棍子不停地敲打站在猪槽里的猪,他得打破猪的规则,让所有猪仔都能吃上猪食里的止泻药。
缺耳朵不停地倒进猪食,有头猪仔把嘴巴放到方形口上,猪食被堵着下不去,缺耳朵的右手顺着运输槽往下推,一拳打在了猪仔的嘴巴上。猪仔扭了头,接着嘴巴一张又含了过来。缺耳朵眼疾手快,手缩了回来。
缺耳朵喂完猪便带老蔡进屋。缺耳朵的二女儿坐在凳子上,乱蓬的头发,眼睛闭着,嘴巴张开,嘴里还有嚼碎了还没来得及咽下的米饭。饭桌上有白糖腌西红柿,还有绕着菜盘子飞来飞去的苍蝇。
老蔡说,老二放暑假了?
缺耳朵回答道,前些天刚接来,天不亮就跟她妈到早市捡菜叶,这会儿才回家,困了。接着又说,这段时间西红柿便宜得很,个头稍小的都扔路边,她们今天捡了几百斤。
老蔡叹了口气说,土地不好种啊,想想我们不愁旱涝,也算过得好。缺耳朵笑了笑,想起上次回老家,村里人对他客客气气,着实让他有种衣锦还乡的错觉。虽然他们只是住在城市边缘的外来村,还是很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日子。
大女儿从上半间屋出来,看着老蔡笑了笑便往屋外走去。缺耳朵的大女儿九岁,在家算半个劳动力,只是小时候发烧没及时医治,成了聋哑人。
院子里老蔡踩的一串一串的猪粪脚印已经干了。苍蝇从地上窜到刚出锅的潲水上,四肢轻盈走动,嘴巴尝试着伸进猪食里。缺耳朵家的小儿子正蹲在黑橡胶猪食盆边上,拿根小木棍往里戳,苍蝇飞哪儿他戳哪儿。
缺耳朵叫外省妹先进屋做菜,留老蔡吃饭。老蔡说自己要磨豆腐了,他把桶里卖剩下的菜豆腐倒出来给缺耳朵做午饭便匆匆走了。
缺耳朵开始养猪,倒也偶然。
缺耳朵和外省妹在旧州城干苦力。那年爷爷死了,一直跟着爷爷住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不得不跟着进城,跟着进城的还有爷爷生前养的一对猪仔。外省妹看着猪仔问,半间泥巴墙的屋子住五个人都困难,你还想养猪?缺耳朵想了想说,现在老大和老二都来了,儿子又小,你肯定不能出门了,养几头猪,倒也适合。缺耳朵在屋外用石头垒了个小窝,猪仔便安顿下来。后来猪越喂越多,成了外来村人说的“养猪专业户”。
缺耳朵每天站街,等需要苦力活的客人。外省妹背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开始提着个麻布口袋到处割猪草。猪越长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外省妹开始到蔬菜批发市场捡烂菜叶,顺便可以捡些人吃的蔬菜,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捡到城里人丢的剩饭剩菜。吃了剩菜剩饭的猪开始长肉,毛发退化,皮肤红润有了光泽,猪仔终于成了架子猪。长大了的架子猪鸠占鹊巢,挤进缺耳朵家的石棉瓦房,缺耳朵用木架子在屋子上面隔了一层,人睡上面,猪住下面,人猪共住。过了冬天,过了春天,到夏天的时候,从老家带来的两个猪仔成了大肥猪,三千零六十块钱卖给了屠夫,那是缺耳朵家养猪收到的第一笔钱,就是这笔钱坚定了缺耳朵养猪的信心。
卖猪那天,缺耳朵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和外省妹一道把家里打扫干净,请老蔡到家里吃了顿饭,自家的猪没少吃老蔡家的豆渣,老蔡没收一分钱。
有了钱,缺耳朵把二女儿送回老家上学,寄养在同姓大伯家。外省妹说女娃儿得读点书,才不容易上当受骗。
外来村在城市的角落,居民都是外来租客。租客按手艺分片区居住,地广人众的数担货帮。担货帮都是农村人,靠出卖劳力吃饭。缺耳朵本来也属于担货帮,原本和担货帮住一起,他跟担货帮的男男女女一样,每天站在旧州城中心的大街上,等着雇主来找人担活计。大家都挑着簸箕,但凡体力活,他们都干。
一米七二的缺耳朵干体力活本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他偏偏生得瘦削单薄,视觉上哪敌得过高大魁梧的。他开始游走在担货帮的人群边上,等着雇主,然后主动自荐。担货帮遵循的是等待原则,雇主自由挑选。缺耳朵的主动违反了规则,引起了同行的反感。
外來村地处低洼处,缺耳朵家从石缝里冒出来的猪粪像泥石流一样袭击村里唯一的一条水泥路,让本就腥臭的空气变得更臭。周围的租客本来对他“抢生意”早有意见,现在意见更大,只是大家住在一块儿多少得顾些情面。缺耳朵家买进了第二批猪仔的时候,周围的租客终于按捺不住,把他家垒在外面的猪圈偷偷拆了,六头猪仔在村子里乱窜,缺耳朵花了一早上才找回了四头。
见拆圈对缺耳朵的打击还不彻底,人们开始出别的招。
缺耳朵爹娘死得早,跟着爷爷长大,二十三四跟着村里的人去外省打工,一次偶然聚餐上,缺耳朵认识了隔壁纺织厂新招的一名女工,酒饭之间,缺耳朵吹了一次牛,说,中国有“四京”,北京,南京,东京,西京,我家就在西京。
工友们说,北京、南京听说过,东京、西京,好像没听说过。
缺耳朵笑着说他们见识短。
女工刚进城,没文化,安静地捕捉男人们聊天的信息,她只知道首都北京,不过她总结了一下,缺耳朵家也应该是大城市的,于是,跟着缺耳朵回了家。回来后才发现,西京其实就是个穷旮旯村寨。这些,外来村的人都知根知底。这名女工就是外省妹。外省妹比外来村的本地女人俊俏,生养了三个娃儿还新鲜得像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泥鳅一样。外来村里的女人开始挑拨离间,说,要是我,早跑了。外省妹刚来缺耳朵的老家时确实心有不甘,一次行房事时一生气还把缺耳朵的耳垂咬掉,但生了小孩后认命了。她说,三个娃娃了怎么跑?女人们说,带着儿子走,还可以嫁个好人家。外省妹笑了笑说,他的耳垂都被我咬掉了,再走就没有良心了。
女人们是想断了缺耳朵的左膀右臂,如果外省妹跑了,想必缺耳朵也不会再养猪。见苦口婆心没取得成效,女人们便直接说了她们的目的,要他家不再喂猪。
当然,此时缺耳朵有两个选择,但他不想放弃养猪,就搬到了其他小手艺帮派的地盘。小帮派们也受不了缺耳朵家的猪,这些人更损,说外省妹和老蔡有一腿,不然老蔡凭什么给缺耳朵家送豆渣。只有缺耳朵清楚,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老蔡原是黄豆厂的搬运长工,有着外来村人羡慕的铁饭碗,可他在搬运的时候从高高的黄豆堆上摔下来,把下身摔坏了,不仅干不动重活儿,也干不了男女之事。他的女人就是那时走掉的。但缺耳朵还是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搬到了离村子百来米的公房。公房虽然快倒塌,可清静适合居住,也适合养猪。缺耳朵以公房的墙身为墙,在左边搭了个三间猪圈,养猪场开始有了规模。缺耳朵还有自己的盘算,他到医院咨询过,大女儿是后天因素造成的聋哑,做人工耳蜗可以让她重新听见声音,经过反复的发音训练,还能说话,跟正常人一样。只是十几二十万的费用让他不敢想,后来了解到一家大医院有免费耳蜗赠送,但需要两万块钱的杂费。他的短期目标,就是攒下两万元钱,给大女儿做一对人工耳蜗。
缺耳朵的第三批猪是跟老蔡借钱买的,十六头。老蔡家的豆腐生意越做越好,豆渣越来越多。自从听到小手艺帮的闲言碎语后,缺耳朵想,再去挑老蔡家的豆渣,得付钱。老蔡觉得这样也好,免得村里人再说他对外省妹有什么企图。可缺耳朵站街养一家五口,已经很吃力,要是每天都要付豆渣钱,对入不敷出的缺耳朵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老蔡很清楚缺耳朵家的情况,他说我有两个法子,一个是豆渣按两块钱一挑,等猪卖了再一起结清。我算了一下,每天供应六担豆渣,每头猪出栏需要十个月,到时候豆渣钱四千块左右。或者我入后买的十六头猪仔的股,借你的两千块和豆渣钱你都不用给,到时候这十六头猪卖了,我分百分之三十。
老蔡说的两种法子,都能解缺耳朵经济短缺之急。缺耳朵心里清楚,老蔡是存心帮自己。
缺耳朵每天还是站街,外省妹还是捡菜叶,捡剩饭剩菜。猪一天天长大,第二批四头猪中的一头母猪开始不思吃食,整天在猪圈里转悠,嘴巴一直找地方东拱拱,西搓搓,嘴里哼哼。外省妹说这头母猪像是发情了。缺耳朵说外省妹不懂行,猪仔出笼前主人家是必须要骟掉的,这可是农村千年不变的规矩。
事实证明,母猪确实是发情了,缺耳朵很气愤,骂骂咧咧地说,现在的人怎么这么没有公德,不负责任。他不得不回老家请骟猪匠,村里的老骟猪匠已经死了,打听到的外乡的几个骟猪匠早几年也出门打工去了。缺耳朵心急火燎,回家看到后一批小的母猪仔和公猪仔关在一起,除了睡觉时间就是在追逐打闹,更糟心。他必须想办法把猪都给骟了,要不一到发情期,母猪公猪的心思都在别的地方,哪儿还能长肉,白花花的粮食就白喂了。
缺耳朵又到老蔡挑豆渣时,说出了自己的苦闷。老蔡说,城市里什么都有,有给人看病的医生,也有给牲口看病的医生,有给人做结扎手术的医生,也有给牲口做结扎手术的医生。老蔡每天走街串巷,消息广。缺耳朵才知道,城市的骟猪匠叫“兽医”。
城市的骟猪匠把缺耳朵家的所有猪都给骟了。城市的骟猪匠不仅会骟猪,会治病,还会根据猪的不同生长阶段开些药,帮助猪长得更好更快。缺耳朵开始感觉,在城里做什么都得有点知识才行。缺耳朵没有大志向,他只希望娃娃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从小读书学知识,以后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一点,他和外省妹的想法高度一致。
二十头猪,胃口越来越大,缺耳朵和外省妹开始换班找猪食。天不亮,外省妹就到批发市场捡菜叶,缺耳朵还是出门站街。午饭后,缺耳朵到老蔡家担豆渣,外省妹冲洗猪圈。晚上,缺耳朵看家带娃,外省妹出门捞潲水。
潲水只有城市有。城里人富裕,剩饭剩菜没法处理,便拿个塑料袋装着,扔进垃圾桶。外省妹每天晚上都到小区垃圾堆里去捡,她一袋一袋地摸,接着撕开塑料袋,把饭菜倒进准备好的塑料桶里。饭菜放桌子上好看,可外省妹捡到的饭菜全搅和在一起,大多还是变质馊掉的,开始她看着忍不住想吐,慢慢地便习惯了,还如获珍宝。潲水最集中的地方,要数好吃街。好吃街的剩饭剩菜不是被包着丢掉,而是倒进放在店铺外面的潲水桶里,因为是放着的而不是丢掉的,外省妹不能去捡。她想去要,可始终没好意思开口。看着大桶大桶的潲水,外省妹晚上就开始去偷。外省妹偷了三个月,有一次,为了偷成色好、饭菜富足的潲水,她钻进一家专门经营家常小炒的店捞潲水,被别人当成一般贼偷打了一顿。从那以后,晚上捞潲水的换成了缺耳朵。
缺耳朵每晚十一点钟出门,走到好吃街的时候饭店都已经关门。他从街头开始,挨个打捞。一只大漏勺伸进潲水桶,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一阵鼓捣,潲水桶里便只剩残汤凄凉地荡漾。运气好的时候,一只潲水桶里的剩饭剩菜就可以装满缺耳朵的一只黑桶。缺耳朵一个晚上要在好吃街和外来村来回三四次。
十六头猪仔成了架子猪,先前的四头已经快出栏。缺耳朵说这四头猪卖了钱可以先攒起来,等后面的十六头卖了,除去老蔡的百分之三十,自家可以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外省妹觉得马上可以扬眉吐气。那天晚上,缺耳朵和外省妹都做了同样的梦,梦到大女儿戴着人工耳蜗,朝着自己说话,和其他娃娃一起玩耍。
缺耳朵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好日子,他带两个女儿去逛一次好吃街。好吃街是城里人最喜欢的地方,天南地北,各种各样好吃的都有。街上灯火通明,两个女儿分别扯着缺耳朵左右两边的衣服,走得很慢,所有的事物对她们来说都很新奇。他们来到平日生意最好,小孩子最多的一家店铺,坐下,缺耳朵神情从容,像是这里的老常客,女儿倒是局促不安。这家店卖的是地方小吃,两女儿要的都是水晶凉粉,透明的软的凉粉里面有花生、芝麻,还有红色和绿色的软糖,看起来都是甜甜的。
缺耳朵带女儿去好吃街还有一个目的。待女儿们幸福入睡,他担着塑料桶又往好吃街走去。在好吃街,他唯一没有在他们吃水晶凉粉的区域捞到过潲水。他已经看好了,那个区域的潲水统一放在一个死角里,死角的外面有一扇木门。缺耳朵就像餐馆里的服务员那样,轻车熟路地去了死角,满载而归。
吃潲水的猪,比喂猪草和苞谷的猪长得快,而且成本很低,这个经验是很多养猪人经过实践总结出来了。缺耳朵捞潲水的时候遇上了越来越多的同行,城里人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潲水帮”。潲水帮斗智斗勇,各自都有一套抢潲水的本事。
缺耳朵家的猪在缺耳朵去死角偷潲水一个星期后全死了。都说是缺耳朵偷得厉害,潲水帮的其他人报复他。缺耳朵一家人的精神陷入瘫痪。缺耳朵把二十头猪排在小院子里,一双双闭着的眼睛,让缺耳朵越来越无力。他坐在台阶上,两眼空空,心也空空。
外省妹一边哭一边骂,发泄着她的不知所措。缺耳朵说,安静一会儿,你别再让我心烦了。
外省妹哪儿还受得了缺耳朵的气,大声说,都怪你个倒霉鬼,都捞潲水,只有你捞有药的!
缺耳朵突然来了气,说我就倒霉,想不倒霉就赶紧滚。当初把外省妹带到西京老家,就做好了她随时要跑的准备。
外省妹没想到缺耳朵会这么说,她停止哭泣,尖声说,你以为我不敢走?说完跑进了屋。外省妹提着收拾好的东西往院子里冲,大女儿突然跑出来抱着她。这一抱,外省妹的心像被猫抓了一样,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骂,你不是能骗嘛,以前把我骗回来,现在为什么不骗骗我,哄哄我呢。说完把东西砸在院坝边。
缺耳朵突然清醒了,他一直在努力,为的就是家,如果外省妹走了,一个家也就完了。他站起来,说,死猪,又不是死人。
老蔡担着豆腐担子又往缺耳朵家来了。缺耳朵和老蔡重新坐到台阶上。老蔡说,没信心了?
缺耳朵垂头丧气,不搭话。
老蔡说,要想在城里站稳脚跟,从来都不容易!
老蔡曾经比缺耳朵还绝望,女人跟别人跑的时候,他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一个月瘦了三十多斤。因为干不了重活,他给别人洗过碗,洗过厕所,最后才开始磨豆腐。
从哪里倒下从哪里爬起来,老蔡拍了拍膝盖接着说,十六头架子猪,我有百分之三十的股,现在猪折了,我也得担百分之三十的损失。我算了一下,我拿出六千块,你可以用这些钱再买些猪来养。
老蔡又一次帮了缺耳朵,当初并没有说明老蔡是入股。但如果有了六千块,一切便有了转机,他可以养更多的猪,到时候再还老蔡的人情债。
老蔡说,你可以多买一些,喂得多,弥补损失的时间就短。缺耳朵在公房的右边又修了三个圈,养起了四十头猪。
缺耳朵白天有时也站街,晚上给猪找生活。不过吸取了贪便宜的教训,他现在不去捞潲水了,花了几百块钱买了辆二手人力三轮车,去附近饭馆收买潲水。更多的时候,缺耳朵的猪还是吃老蔡的豆渣。
四十头猪仔快长成了架子猪的时候,缺耳朵不站街找苦力活干了,专心养猪。这是老蔡和他商量后决定的,老蔡对缺耳朵说,你不应该三心二意,应该专心致志做一个“养猪专业户”。
午饭后,吃饱喝足的猪已经熟睡,缺耳朵交代外省妹担水冲洗猪圈,自己拿了根扁担,顺手拿起门后的两个长耳朵纤维袋,带着大女儿往老蔡家去了。这也是老蔡和缺耳朵商量好的,老蔡又入了缺耳朵家的股,不过这次他入的不是猪的股份。他出资医治缺耳朵大女儿和她生活的全部费用。
缺耳朵说,大闺女又聋又哑,是个负担。
老蔡说,等她耳朵好了,会说话了,我就教她做豆腐,我可不想远近闻名的“蔡豆腐”失传。这也是我要的回报。
老蔡还说,人工耳蜗我已经订好了,如果你不同意,就算我送她的礼物好了。
老蔡家住在外来村的村头,黑色的瓦房后面有两间短短的豆腐房,豆腐房是后来盖的,地理位置比瓦房高,远远看去,黄黑色的茅草屋顶像鹧头鸪的冠子。
缺耳朵和大女儿从村尾走向村头,太阳浇了他们一身汗。老蔡刚滤完一缸黄豆汁水,豆渣被挤压成一团,躺在白色滤帕里荡秋千。
老蔡说点豆腐是有规矩的,旁人一說话,豆腐就会“醒”,醒了的豆腐是不会结成块儿的,各自飘荡在铁锅里,没有卖相。老蔡又说,不过现在点豆腐是点给我女儿看,就没有那么多规矩了。
老蔡系着白色围腰站在煮豆腐的大铁锅旁,右手拿着个半圆形木勺,左手端着口不锈钢的钢钵。木勺从钢钵里舀酸菜水,他猫着腰,轻轻顺着铁锅一圈倒进去。
缺耳朵很快把盛放在木桶里的豆渣倒进长耳朵纤维袋,然后在豆腐房的木架上拿着钢盆,卸下滤帕的一只角,左手扶住滤帕底,往上用力,豆渣滚进钢盆,接着将豆渣倒进纤维袋。
缺耳朵装好豆渣的时候,老蔡把铁锅里的豆腐舀到了大木盆里,拿着竹子编的筲箕在豆腐上压了压。压好的豆腐,有一部分属于缺耳朵的大女儿,老蔡说,有了女儿,我得管她的生活。老蔡拿来的豆腐都能够缺耳朵家吃上一天。
缺耳朵家的猪长成架子猪的时候,外来村传来了拆迁的消息。几天后,效率很高的挖机开始从村尾作业,缺耳朵一家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外省妹一边哭一边抱怨。缺耳朵对外省妹说,没事,猪在,希望就在。说着打开猪圈门,赶着猪从外来村走了出来。
老蔡看着缺耳朵一家要走,说我和你家一起搬吧。
缺耳朵说你住村头,还没被占,况且豆腐生意又好,就安心地住着吧。
老蔡说,我留下来了,谁照顾我的女儿。说完也开始收拾东西。
外省妹和女儿在前面追着赶着在路上乱跑的架子猪,缺耳朵踩着三轮车拖着家私跟在后面。儿子坐在车上,对着爸妈大声地喊,加油!加油!大女儿回头,跟着弟弟也喊了声,加油!那是大女儿第一次说话。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