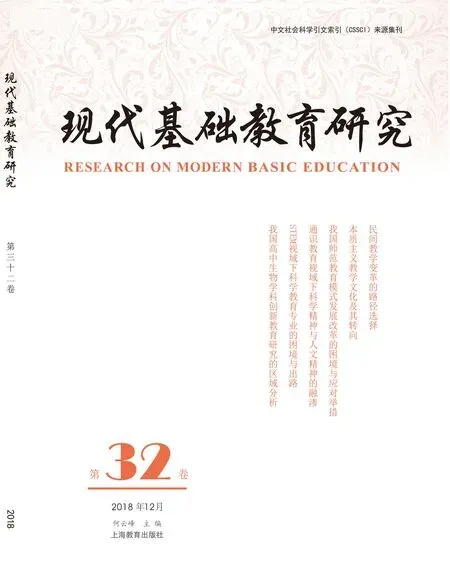荀子教育思想的本质、目标与方法
邵龙宝
(上海杉达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209)
一、荀子教育思想的本质是“礼治”实质的彰显
荀子认为学习“礼”是一个人终身的事情,“礼”是制度、仪式、规范,又可以内化为德性和智慧。德性和智慧的学习是一生的事情,不可以半途而废,学习是为了成为贤人君子。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前者是从性善的角度,后者是从性恶的角度,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过程和目标是一致的,都认为通过修养可以成圣成禹。孟子的“存心养性”是要把善端培养、发掘出来,荀子则强调“化性起伪”。“化”是指人在实践中一方面适应环境,一方面改造环境,在环境与人实践的互动中使自己的性情、人格发生变化。这里的“教化”不仅仅是“教诲”,而是突出了人的能动作用,而这种能动性若离开了实践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在实践中一方面要遵循礼法制度等的规范约束,另一方面要养成自我修养即自律的习惯和品行,这就是内外环境的互动、自律与他律的统一。“礼”还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和风貌,每一个体的精神风貌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荀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他的“礼治”思想。“‘礼治’以社会秩序为目标,用礼义来规范民众的行为,在治国理政中提升民众的道德觉悟和人格境界,用强制性的规范来惩罚违法行为,在教化民众和惩治违法的过程中实现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1]“礼治”的缘起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荀子礼治思想的实质是“礼”的制定、运行、遵守和裁定都要符合“道”,这个“道”就是遵循仁义和礼义来进行教化。荀子一方面强调礼乐教育对个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个体在实践中与环境的互动,对自身言行举止的反省、自我修炼、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修心、修身的软约束可以提升人格,另一方面强调个体要受到“礼”的强制性、制度性和规范性的硬性约束和管制,二者相得益彰,才能使社会有秩序,使个体得以成圣、成人。
荀子的“礼治”的实质就是“礼”与“法”的有机统一。荀子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为了彰显其“礼治”的实质。荀子曾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篇》)在荀子看来,学习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经》结束;就其目标来说,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学习要真诚,要长期积累,不可以有片刻懈怠。荀子认为儒家的思想道德理念都是通过“礼”来转化为现实的。“道、仁、义、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道、仁、义”是荀子“礼治”思想的内核,“礼”的外在的制度性的硬性规范和约束是“礼治”的法制之面相。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成其为“礼治”,这就是荀子教育思想的本质。我们从荀子的“礼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到,其间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礼法并重、德法兼治、软约束与硬约束的有机统一是荀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礼法并举”思想。管仲早就看到了刑法的局限性,认为礼仪教化恰好弥补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著名的“礼义廉耻”乃是“国之四维”的观点。在管仲的“礼法并举”中,虽然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国家治理中的四条命脉,突出了礼乐教化的重要性,但更多地表现了法制的特色。而荀子的治国理念从表面上看是“以礼辅,以法治”,以至于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而实际上,荀子是强调礼治中的仁义的支柱作用。他认为“礼、义、廉、耻”比法更重要,它们才是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礼”又是能够把治国理念落实到民生日用之中的枢纽或桥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礼”,“礼”关乎每个人的德性、行为和人格操守。“礼义廉耻”历来是贤人君子追求的美德。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人格,不是法律制度,他强调法律制度是为道德人格的提升服务的。唯有尊崇礼法,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修养之士,才能成为谦谦君子和贤达之人。他的教育思想既注重仁义,又强调礼法,是仁义和礼法二者的高度统一。
二、荀子教育思想的目标是培养贤人君子
荀子教育思想的目标是培养贤人君子。荀子最为赞赏和推崇的是大儒,认为他们具有“全”和“萃”的学习境界和人格风范。他们不仅知识广博,且能触类旁通,以已知推无知,用悟道去解析和应对新问题、新事物,这在《荀子·劝学篇》中有精彩的论证和描述。在荀子看来,“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所以君子要博览群书以求融会贯通;学思并重,注重理解,只读诗书还不够,还要善于向良师益友学习,并且理论要联系实际,克服自己身上的陋习来养护身心。养护即修身,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这种修养的境界要达到:“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荀子·劝学篇》从头至尾都在论述如何通过学习成为贤人君子,成为“全”和“萃”的大儒,而他所论述的学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作为真正的君子,学习是为了充实和完善自身,使学问能真正入耳、入脑、入心,把有价值的思想、理念切实落实在日常行为之中,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要垂范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满足浮躁和虚荣心。荀子教育思想的目标是成为贤人君子,而贤人君子的最重要的标准是遵照礼义立身处世。一定要与行为合乎礼义之道的人交往;与恭敬有礼的人谈论道的境界;与言辞和顺的人谈道的价值;与态度诚恳的人论及道的精深意蕴。
三、荀子教育思想的方法是“亲近良师”“虚壹而静”
荀子认为学习应该亲近良师。亲近良师的好处是,不仅在学问上可以受到全面的熏陶,还可以在道德人格上得到切近的影响。学习古典文献如《礼经》《乐经》虽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书》尽管古朴但不贴近现实;《春秋》讲微言大义,隐微但不够周详。而亲近、仿效良师不仅能获得通达的事理、全面的知识学问,还能受到人格节操的感染和提升。荀子所说的良师实际上就是“人师”。“人师不仅注重知识论、认识论,更重视价值论和伦理学,看重将二者有机地统一,尤重将认识论转化为价值论、伦理学,在教育实践中致力于‘化理论为知识,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人格,重视学问之‘道’。与‘器’相关的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与‘道’相关的是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人师对待学问和三尺讲坛的敬业程度应以‘学、会、工、巧、精、通、生、化、圣、神’的十个逐级而上的境界为理想目标。”[2]现在这样的“人师”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温荀子教育思想的意义之所在。
荀子论教育方法特别强调学习要有恒,“虚壹而静”,不可浮躁。学习不专注,学问就做不深、做不大。《荀子》开篇第一句就郑重地写道:“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不能停止。荀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在学习时用心不一是做不成事情的,他用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骐骥、驽马,雕刻、蚯蚓和蟹等世间的万物进行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尤其强调“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篇》)。指出没有潜心钻研的精神,就不会有洞察一切的聪明;没有默默无闻的工作,就不会有显赫卓著的功绩。在这里,他不仅论述了学习态度、专注的学习精神如何造就一个人的精神风貌,还阐发了志向对一个人成为贤人君子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荀子的教育思想的本质是礼治的实质和彰显,其教育思想的目标是培养贤人君子,而教育方法和路径是亲近良师,强调学习要有恒,“虚壹而静”,不可浮躁。荀子的教育思想铸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貌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仁义”是“礼法”的内核,“礼”是秩序与和谐,其内在动力是“乐”;“法”是强制的规矩和刑罚,是一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的工具和手段。一个人不懂得礼仪、礼节和礼貌,行为举止不能文雅、得体、有礼,尤其是没有廉耻感的人,是无法成为君子的。礼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对君子讲仁义,对小人用礼法,君子和小人有时候会互相转化,所以,仁义和礼法必须并用,并用的内在理路是“循道而行”。荀子论“礼”强调义务多,强调权利少,一味要求臣民服从,这是历史的局限。在今天,荀子的礼治教育思想要为构建法权人格服务。这种人格既重责任又重权利,应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