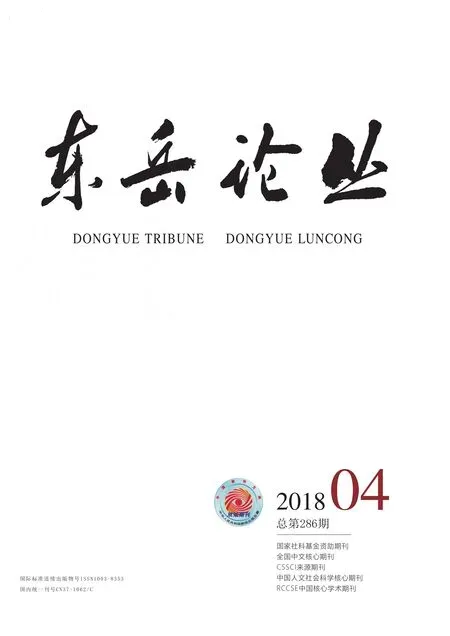金兆燕《旗亭记》与乾隆时期扬州文学的职业化
邹 琳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一、《旗亭记》的创作与金兆燕入幕
金兆燕,字钟越,号棕亭、芜城外史、兰皋生,安徽全椒人。善诗文,工度曲,谱有《旗亭记》传奇。金兆燕一生经历入幕、中举、做官、致仕后再入幕等几大阶段,他自言“得于山水花月之地,嬉娱暮年*金兆燕:《亡室孺人传》,《棕亭古文钞》(卷四),《淸代诗文集汇编》(第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人生大半时间可谓都在扬州各大幕中辗转度过。他前半生以戏曲《旗亭记》而名动曲坛,并因此得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之幕。但其后发生了署名风波,离幕后他与程廷祚的序文中也流露出愤懑的情绪,这说明在《旗亭记》的创作改编过程中金兆燕实有怨言,《旗亭记》也因其复杂性受到后人的关注。
但是,《旗亭记》的创作是在金入卢幕之前,倘若二人果真早已对于《旗亭记》存有分歧,为何金兆燕仍旧选择卢见曾处就幕?以《旗亭记》为线索,将金兆燕游幕、就幕、离幕的人生经历作一次重新的探问,则会发现,金兆燕的言与行,出身与选择、愿望与经历之中,存在着数个微妙的反差与相悖,这相悖背后,则是当时文坛风气与生态的影响。
金兆燕创作《旗亭记》的时间为1757-1758年之间,完稿同年冬天入幕。《旗亭记》受卢见曾赞赏,亲自为之改编序评,并于1759年由雅雨堂刊刻出版,为《雅雨堂两种曲》之一,再行安排敷演。后人多普遍认为,《旗亭记》就是金兆燕入卢幕的敲门之砖。
然而,《旗亭记》出版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旗亭记》的作者一直被默认为卢见曾,金兆燕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对这一署名权的旁落应当是有意见的,然而他并未就此发声。要探究这个问题,就需重新探询金兆燕与卢幕的关系以及金兆燕入幕的经过。
金兆燕选择卢幕是经过长期的审慎考虑的。在正面接触卢见曾之前,他已经从各方渠道,了解了卢见曾四年以上。金兆燕对卢幕的了解和间接接触可以追溯到1750年,其时他与李葂相交游,李葂是卢幕资历最老的幕友之一,金兆燕之家又有世代游幕的传统,不可能不对卢幕进行了解。除了李葂,卢见曾的学生王昶,幕友吴敬梓、厉鹗等人,也与金兆燕早有交游关系。但在1750-1754年之间,金兆燕曾两次上京科考,四处蓬转,投诗干谒,却尚不曾投于卢门。金兆燕与卢见曾的初次见面是在1754年,金为自己当时居于卢幕的长辈吴敬梓收殓送终。之后又经过了一年,金兆燕才做出选择,主动写干谒诗投卢。1755年起,金兆燕屡屡投诗给卢见曾,其诗多见于《棕亭诗抄》中,持续时间将近三年。一系列的诗歌赋作,大都以金兆燕主动投献,展示自己“求幕”的诚意,而卢见曾处于关系中较为冷淡的一方。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757年2月,卢见曾红桥修褉时,第一次主动邀请金兆燕参加,并在见面时提及了《旗亭记》的本事,这是《旗亭记》开始创作的契机。1758年起,金兆燕居卢见曾盐运使署,创作《旗亭记》直至完成。这直接促成了金兆燕入幕之事的敲定,入幕时在1758年冬。
金兆燕向卢见曾的求幕行为,因其漫长,可见其目标明确。而每一次,几乎都以他主动的释放善意,迎合卢见曾为转机。就此来看,《旗亭记》是他又一次牺牲自我的曲意逢迎,他对于《旗亭记》之后会迎来的命运,并不是完全没有心理预期的。而探究其入幕经历,从打听,到干谒,到参与红桥修禊,再到入署、入幕,是具有递进性的。如果站在卢见曾幕府的视角上,这些递进式的难关,实际上起到是“逐级选拔”的效果,也就是一次“招募流程”,《旗亭记》则相当于幕主卢见曾为预备役幕友出的一道选拔考题。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清康熙二十九年十月生于山东德州,乾隆三十三年卒于苏州狱中,一生历经康雍乾三朝。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成就,便是转运扬州,担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出身书香门第,雅好诗文,为山左耆老王士祯、田雯的学生,曾于王士祯、赵执信处学习诗文,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与文学追求。在《雅雨堂诗集》中,他曾撰文试图调和王、赵二家诗歌主张之间的矛盾,认为“先生谈龙录,大旨持异于渔洋,而未尝不同归者”,并提出了王、赵诗文存在相互学习的现象,这与马瑜理先生在《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马瑜理:《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东岳论丛》,2017年第4期。中的观点是相符合的。卢在王赵诗派相争的历史环境下,提出这一诗学观点,可知其诗歌眼光与文学素养。卢见曾致力于文学事业,由时人及后人一致认可为当时的“文坛盟主”。而他的文学事业之中,又以其举办的文学活动,特别是红桥修禊最为著名。“极一时文酒之盛”*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38页。,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其时和修褉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李斗:《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上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页。;由他建立的幕府,在历史评价上,是清初至清中期最大的一任幕府。
红桥修禊,主要是指卢见曾在乾隆二十年与乾隆二十二年举行的大规模修禊活动,它是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在众多文学活动中,红桥修禊中参与的文人类型是最丰富的,它包括当时著名幕友及文人、普通幕友、其他幕内的文人、无归属的无名文人、甚至包括有文化的盐商。需要说明的是,明清商人往往有向士人融合的主动倾向,“商人在帝制框架内……士绅阶层的并存交融”,体现于“依附、巩固现行社会体制的角色转变方面”*常文相:《从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但这往往受到传统文化阶级的阻碍。在清朝早期,商人身份的文化爱好者不被允许参加红桥修禊等正规文化活动,但在卢见曾举办的红桥修禊中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可见卢见曾所举办的修禊活动有意扩张了参与者的数量,既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特征,也符合卢见曾借机招募幕友的意图。金兆燕便是其中一位无名的参与者。果真如此,那么在这个时代,看似彰显着文人自由与文学传统的文酒之会的兴盛,其实意味着职业性对于文学活动的浸透与影响。这兴盛于江湖的文学活动的性质,正在悄然发生着不为人知的改变。
在理解了参与红桥修禊对于金兆燕求幕的意义之后,笔者将眼光重新转回金兆燕身上。当时金因上京赶考,不能与会,同年夏天,金特意取道扬州,向卢见曾和修禊诗,并主动与卢见曾会面。

1758年秋天之前,金兆燕入盐运使署(并非入幕),成为盐运使署的“座中之人”。他应当已经享受着一定的幕友待遇,由卢见曾供给衣食来源,这种待遇远胜当时其他幕府中人。在这一期间,卢见曾也一同参与了创作《旗亭记》。金卢二人应当彼此都心知肚明,创作《旗亭记》就是金的“工作”。在卢金二人这一连串围绕“就幕”而进行的试探与职业条件洽谈之中,《旗亭记》从头到尾地创作完成了,金也在入署三月之后实现了入幕之愿。《旗亭记》是幕友用来交换职位的商品,处处体现着幕主的要求,并不是一件自由的文学创作作品,因而金兆燕甘愿牺牲署名。更何况,《旗亭记》的创作过程也有卢见曾的参与。这或许也是《旗亭记》的署名被归于卢见曾时,金兆燕不曾反对的原因之一。
《旗亭记》作者权的模糊性,是这一时代里特殊的文人幕府所带来的特殊现象,《旗亭记》的创作过程中,凝聚着金兆燕为进入卢幕而付出的心血,记录了卢幕招收幕友的实际流程,也表现出了大型幕府在乾隆时期对文人的吸引力。《旗亭记》的出现,说明幕府从体量、人选、数量上的扩大,也说明了幕府从更接近于个人中心的文社向一个大型的综合职业场所开始转变。
二、《旗亭记》的改编与幕府文学的特质
《旗亭记》署名的模糊化,没有给金兆燕带来明显的不快,但金兆燕的不满情绪发作了在《旗亭记》的改编问题上。
在《程绵庄先生莲花岛传奇序》中,金兆燕对他曾共客卢幕的朋友程廷祚,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兆燕少无学殖。日抱简牍为诸侯客,以期其口。戊寅冬,与先生同客两淮都转之幕。先生居上客右,操椠著书;而兆燕不自知耻,为新声,作诨剧,依阿俳谐,以适主人意。主人意所不可,虽缪宫商,秤拍度以顺之不恤。甚则主人奋笔涂抹,自为创语,亦委曲迁就。盖是时老亲在堂,瓶无储粟,非是则无以为生。故洪溜含垢,强为人欢……”*金兆燕:《程绵庄先生〈莲花岛传奇〉序》,《棕亭古文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这一段话,历来被学者认为是反映了康乾时期落魄文人寄人篱下的无奈心情。固然如此,然而,为什么金兆燕对于抹去自己署名权之事相对沉默,但却对于改编问题表现出激烈的不满呢?如果同样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现代社会,态度或许刚好相反。这意味着金兆燕的反应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与身份的典型性。
事实上,作为一个幕僚,金兆燕对于署名权问题的沉默是符合传统的。吴广训《清代幕友人际关系及其从业心态探究》*吴广训:《清代幕友人际关系及其从业心态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0年。中提及,直到清代,幕友的工作主要还是以刀笔、刑名、尺牍等实际的政治琐事为主,幕僚制度主要依附于政治制度而存在。幕僚会被要求书写“工作文件”,例如代笔案牍文书,他们个人的文学创作,则不受幕主重视,也不会遭到干涉。
但是幕主要求幕僚进行一项文学戏曲创作,这件事在当时来说还是较为稀见的。它的发生,与当时幕府性质的变化有关。从清初以来,学人游幕现象变得更加频繁,也有一种特殊幕府形态正在兴起,即学者文化型幕府的逐渐增多。这一点,在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曾经提及。以幕主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群体(还包括非幕主的官僚、盐商等)则出现了一种潮流,以学术赞助的方式支持学人们。而卢见曾的幕府就是这种特殊幕府的典型,卢见曾幕府内,有记载者近百人,主要是学人、文士类型的幕友,而非实际处理政务的“师爷”,其幕友担任的最“实政”的工作也不过是校勘经书,创作诗文等等,虽不在朝野,但它的功能类似于一个文化创作组织。这一种特殊形态的幕府,集中了一时一地的学者与墨客,增强了文化交流,这更有利于当时文学与学术的进步。
对于习惯于“代笔捉刀”的幕友金兆燕来说,在幕主的授意下进行的创作,得不到署名,是一件符合常理的事。但为什么金兆燕对于卢见曾的改编表示不满?当代学者研究《旗亭记》时,通常认为金兆燕的创作目的是自伤身世,寄托情感*“剧本眉批云:‘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此《旗亭记》之所为作也’……可见金兆燕创作《旗亭记》本意并不在抒写男女之恋情,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当时金兆燕五应会试,均铩羽而归……借写才子佳人之遇合,抒发怀才不遇之意,以解心中郁结之苦……”相晓燕,《〈旗亭记〉作者考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笔者十分认同。但是金兆燕在一部“代笔”的幕僚作品里寄托自我情感,或许并不那么合适。他对此的怨言一直忍到去幕之后才爆发,就是他明白自己行为的“不合适”。但他选择在为程廷祚《莲花岛传奇》写的序文里进行公开表达,又说明他认为自己的怨愤是理所应当的。这种态度上的复杂性,是源于《旗亭记》性质上的矛盾。
假如将传统中幕友在幕府中书写的文学进行分类,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类作品。一类是职业文章,也就是为幕主“代笔”的一切文章,包括书信、尺牍、案卷、诗文、编辑、评点等等,均为应用性文章,但也具有幕友个人在文学创作中流露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一类是私人文章。这一类是幕友自己尽逞才情,随心而作,或为干谒,或为自高,或为同行认同、交结关系,这些都属于自由创作。一般而言,自由创作更倾向于小说、戏曲、诗赋这些艺术性更强的文体,比如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过程中,虽然也有一段时间居于卢幕之内,但《儒林外史》无疑只是一部私人作品。
《旗亭记》在类型上更接近于私人文章,它源发于作者的私人情感,充满创作的激情。但是,它的创作过程又深受卢见曾的推动影响*“分韵之余,论及唐《集异记》旗亭画壁一事……经年,复游于扬,出所为《旗亭记》全本于箧中。余爱其词之清隽,而病其头绪之繁,按以宫商,亦有未尽协者。乃款之于西园,与共商略。又引梨园老教师,为点排场,稍变异其机轴,裨兼宜于俗雅。间出醉笔,挥洒胸臆,虽素不谙工尺,而意到笔随,自然合拍,亦有不自解其故者……”《旗亭记》卷首,卢见曾,《旗亭记序》,清乾隆六十年雅雨堂刻本,复旦大学古籍部。,而最后,卢见曾甚至改变了《旗亭记》的主旨。在《旗亭记》的评点文字中,卢见曾俨然以作者自居。如该传奇第十出《叹月》【雁鱼锦】曲眉批云:“此步《长生殿·尸解》京韵,作者偶戏为之,曲成漏下三鼓,为进巨觞。” 卢见曾或许认为,自己是《旗亭记》真正的作者,而金兆燕不过是一个代笔之人。因此,《旗亭记》同时具有职业文章与自由创作的双重属性,它既可被视作“代笔”作品的种类的扩大,也可以反映幕友的自由创作受到了幕主的干涉。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再对金兆燕《旗亭记》改编的怨言进行审视。金兆燕对改编的怨言,具体表现为“为新声,作诨剧,依阿俳谐,以适主人意。主人意所不可,虽缪宫商,秤拍度以顺之不恤。甚则主人奋笔涂抹,自为创语,亦委曲迁就”。这些包括对自由创作过程的干涉与对创作内容的篡改两方面。具体来说,他反对的是审美的俗化、技巧规则的错误、新加入的内容以及主旨的调整。这并未有害作品的根本,但金兆燕十分愤激,他的反对,充满了对自我风格的捍卫,说明他内心深处把自己视为真正的作者,他不在意署名权,却认为作品的主权属于自己。他为作品任人曲解而感到愤怒,却并未认识到,自己入幕的真正代价不是一个戏曲作品的署名权,而是自己对作品的话语权与解释权。
幕主与幕友对一件作品的不同看法,说明幕府中产生的文学作品的归属问题变得模糊了,它代表着一个转变期,也是幕主介入幕友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标志和开端。内涵的矛盾和外延的模糊,在事物的转变发展期是必然的过程。也正因为《旗亭记》性质上的矛盾,使得金兆燕将卢见曾的改编视作对自己作品主权的侵犯。
设此为真,那么在此情况下在幕府诞生出的文学作品,应当被视为新的种类。一方面,这类作品不再纯粹是自由创作,随着幕主对幕友创作介入程度的加深,变成一种非自主的“职业创作”。另一方面,这类作品既出于幕友的个人创作,又不完全体现幕友的自由意志,它属于幕友、幕主和幕府环境进行的“群体共同创作”,或许可以被称为“幕府文学”。群体性是幕府文学与自由文学之间最重要的差异。
在了解幕府文学与自由文学的差异之后,我们再来看《旗亭记》改编中金兆燕与卢见曾的具体分歧,则会发现新的答案。后世研究者认为,金卢两人的版本都具有不错的文学水平,这意味着两人的分歧可能更多的是立场上的矛盾。卢见曾对《旗亭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由政治主导的教化主旨。这在当时的文坛,尤其是以宫阙、皇亲、地方官员为中心的文坛,属于主流倾向。但将时间前推几十年,顺治康熙年间的扬州文坛,真正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遗民风格。这说明,文化权力的中心从江湖转向了庙堂,也就是《清诗史》中所提到的,“爱新觉罗氏皇族在整个统治时期从未轻忽松动过对文化的包括对诗文化的制控力,在前期尤为突出……在康雍乾三朝间即已建构成庞大的朝阙庙堂诗歌集群网络”*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而幕府文学的出现,无疑是与这种文学控制政策持续的时间相合。
如果果然存在关联,幕府文学是如何实现文化控制的?这涉及到第三个问题:改编本《旗亭记》的盛行与扬州文人的职业化。
三、改编本《旗亭记》的盛行与扬州文人的职业化
《旗亭记》的改编、出版与排演,都受到了政治的影响。《旗亭记》最过人之处,就在于其人物饱满,结构精巧,曲词流丽*李胜利:《金兆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其论文中第四章第二节对《旗亭记》的艺术水准进行了详细的鉴赏分析。。其中,结构和曲词,都是卢见曾所着重修改的部分,尤其在结构关目方面,卢见曾在初次读到《旗亭记》时,便将“头绪之繁”作为修改对象,最终的剧本便是以几个关键性的人物串联繁复的关目,将剧情删繁就简。改编时,他又“引梨园老教师,为点排场,稍变异其机轴”。在改编之后的排演环节,卢见曾更是为《旗亭记》的推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两淮盐运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戈阳腔……”《旗亭记》在出版排演上的成功,与幕主卢见曾是分不开的,而卢见曾之所以能提供这么大的帮助,是由于他两淮盐运使的身份。两淮盐官例蓄花雅两部,《旗亭记》可借此排演。卢见曾又以此为机,广邀当时的文人名家进行赏鉴、点评。仅仅留下诗文记录的人,就有沈德潜、袁枚、王昶、沈大成、赵翼等。
值得注意的是,似金兆燕一样的文人剧作家,在当时并不稀见,然而,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却已经整体衰落,其原因之一,便是文人创作不再适合舞台表演。若《旗亭记》不是在卢见曾幕中所作,它很可能与其他众多文人剧作一样止于案头。就这一点看来,幕府对自由文学的影响并非压抑,而是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
卢见曾创作与出版《旗亭记》的目的,是想令“逸于正史而收之说部”的故事发扬光大,并改变当时流行戏曲“导淫述怪”的现状。这是卢站在一个宗经征圣的儒生的立场上,想要教化百姓、补齐正史、修正风俗、建立典范的个人抱负,并确实从文字到主旨都改变了《旗亭记》。如《骂奸》一节,金版为“履洁怀清者,千秋姓字香”,而卢版改作“传檄清君侧,前锋到洛阳”;《春游》【天仙子】中,卢将“盖世文章空锦绣”改作“磊落壮怀空自负”,将《渡江》【长拍】中“叹兴亡”改作“谈兴亡”……总而言之,将书生意气的自负与牢骚,改成了忠君报国的志向与从容,主角人格趋向于沉稳冷静,原本中情绪激荡的感染力也有所减弱。
金兆燕原本的《旗亭记》,私人情绪较强,富有文人剧作的文学特征;卢见曾的改编,令作品主旨变得冲淡平和,冠冕正统,使得作品更适合排演,传播上也更易盛行。《旗亭记》的盛行,说明这种合作在效果上是积极的。

商业行为与市场性,是职业化的标志。但对于《旗亭记》乃至卢幕中其他的文学行为而言,这一特质确有体现,然而仍属模糊不清。首先,《旗亭记》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谋生,创作过程中受幕主的影响,并且在刊刻及搬演后,也进入了大众市场,这些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这又不是完全的商业行为。卢见曾并非抱着经济目的来进行刊刻与排演;金兆燕获得的报酬不是直接由市场销售带来的稿酬,而是卢见曾的一份幕友资助;而《旗亭记》创作时受到的影响,也不是市场要求,而是卢见曾的要求。卢见曾作为一个不以商业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文学性幕主,似乎不应当成为市场的代言人,但他在与幕友创作的关系中,又确实承担着市场的角色。正是其中“幕府”这一环节的存在,拉远了幕府文学与市场之间的距离,而幕府反过来代替了真实的市场,并具有职业场所和市场环境的双重性。这不止体现在《旗亭记》中,也体现在当时的其他幕府以及卢幕的其他幕友身上。
首先,以“谋生”目的来看,幕府具有经济上的优势。在清代前中期,科举取士的减少,文化政策的紧缩,对前朝遗民的封杀,都令文人失去了他们传统意义里最正统的晋升途径。因此在文人游士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幕府普遍地对文人具有吸引力。正如袁枚曾说:“中丞之门,不见有士,偶过公门,士喁喁然以万数。岂……皆不如公耶?……静言思之,未尝不叹士之穷而财之能聚人为可悲也。”*(清)袁枚:《与卢转运书》,《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出口的减少,进入者的增加,相互叠加,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彷徨失幕、无所归依的文人群体。扬州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趸蹇在扬州者甚多。
以文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来看,幕府中的文人呈现出商业合作关系的多样性,其特征就是幕府分工细化的出现。例如卢幕中,幕友分工就包括编校刊刻、校正经学著作、评点诗文、编辑诗抄、诗文酬唱、写作书法榜联、戏曲创作等许多方面。幕客们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形成一套包括创作、编辑、刊刻、出版、传播的系统,令幕府显示出了制度化的特征。
以谋生为目的进行创作与文人间的多样性合作关系这两个特点,与职业化文学的特征相合。它或许还不足以断言幕府文学是文学走向职业化过程中的产物,但已可以说幕府文学,包括幕府的组织结构、文人生态、创作过程,都开始具有文学职业化的特征。金兆燕及其作品《旗亭记》也不例外。成熟的职业化通常包括对技能、行为、制度与从业者素养四个方面进行的特化,这在金兆燕身上都有所反映:金兆燕拥有专为卢幕的创作“歌咏序跋”的技能,“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延入署中,一切歌咏序跋,多出其手”*陆萼庭:《金兆燕年表》,《清代戏曲家丛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旗亭记》的创作与改编具有职业行为上的特殊性;卢幕文人分工已出现了职业制度的雏形;而关于第四点,金兆燕对《旗亭记》的微妙态度,则是职业从业者素养形成中的表现。
对金兆燕来说,《旗亭记》出版和传播上的成功,无法弥补他自己的作品被篡改的伤痛,这种屈辱的感受,直至他离开卢见曾幕府三年之后,才被他正面写出来。但这种态度也是特别的,金兆燕除了传统的尺牍幕僚,还负责了所有大戏词曲的创作,《扬州画舫录》有记,“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这类作品想必也受到了卢见曾要求的限制,但金兆燕并未流露过不满。对卢幕的生活,金兆燕是十分满意与愉快的。“幸舍栖迟春复秋,逢人便道此间乐。官梅亭畔百花妍,戏谱新词付锦筵。”“搜罗轶事存风雅,商略新词付管弦”,他回忆起创作戏曲的经历,也充满温馨的诗意。
金兆燕对于《旗亭记》的态度,有三处微妙的反差。一是对《旗亭记》署名被夺感到不满却隐忍不发,并且这种不满只局限于《旗亭记》相关,并未蔓延至对卢幕与卢见曾的评价;二是对《旗亭记》被幕主改编表现得极为愤激,但同时又不在意其他作品为迎合卢见曾做出的修改;三是他对《旗亭记》的内容十分在意,对《旗亭记》的成功与盛行,却保持着一种与己无关的漠然态度。这三点,一方面与《旗亭记》在金兆燕心中的特殊性有关,一方面与金兆燕对自己的位置认识有关。他似乎认为,旗亭记的创作应当只和自己有关,但旗亭记的创作结束之后,出版、传播都与他没有关系。这比较符合传统文人对待私人创作的态度。对自己花费心血感情的创作,他怀着一种爱惜羽毛的心情,不容侵犯。但如果是纯粹出于幕主要求进行的创作(入幕后所作大戏词曲),则毫不在意。同时,自己作为被卢见曾资助供养的代笔幕僚,是理所应当以幕主的要求为第一位的,金兆燕对工作环境、要求和待遇都十分满意,他在《旗亭记》上的逆反态度,或许更近似于对卢见曾侵犯了自己的私人创作空间的愤怒。
金兆燕的矛盾态度表明了从业者素养在此时还未成熟。在这一前提下,金兆燕对于《旗亭记》态度的矛盾,其实是自由创作和职业文学的矛盾的体现。职业创作需要符合幕主的要求,而自由创作是自主、自发的,表达的是金兆燕个人的创作需要。两种文学性质的背后,蕴含着政治压力和文化权力的转向。这也表现为当时诗社力量的松散与幕府力量的集中。幕府作为地方文坛的中心,以包容但不干涉的方式与周边的文学组织进行互动,同样能体现出政治影响下的文学对当地自由文学的试探。
金兆燕本人的一生,也展现出职业文人与自由文人的双重性。他在长年游幕中,不自知地为幕府而改变,两种观念的矛盾在他一生的行为选择中时常暗中角力,令他总是感到复杂的感受和无从索解的苦闷。他对卢幕的满足是作为一个幕僚的满足,他对作品被改编的愤怒是出自一个自由文人的愤怒;他一生之中,八次科举,以功名为己任,这是他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骨子里的追求和理想;但是,他辞官之后,却愿意留在扬州,继续作为幕友客于盐商幕中,这则是他作为一个幕僚的惯性,也是对幕僚生活的选择。他后期客于江春幕中,起先十分惬意,后来却又生出不满,则是因为江春固然供养他衣食,却不像尊重一个自由文人一样尊重他,还把他与其他幕僚等同视之;虽然如此不满,他也无法果断离开江春之幕。甚至金兆燕在扬州做官时,还过了一把做幕主的瘾头,与亲友一同居于官署,吟风弄月,诗酒风流。后世学者总将金兆燕视为一个“半生踪迹只依人”的幕僚,固然不错,但或许对金兆燕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幕府生活成为了金兆燕需求的一部分,但他对纯粹的幕僚地位并不满足,这说明职业化对自由文人的驯化还不完全,金兆燕的从业者素养还未完全建立。不彻底的幕僚心理和无法放弃的文人追求之间的矛盾,不会只在金兆燕一人身上发生,在扬州文学职业化的过程中,还未彻底转变的职业文人,时时会感到矛盾带来的无形压力。
由幕府而肇兴的“职业化”趋势,对当时的幕府文学乃至扬州文学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职业化的作品,首先产生在两个过程中。一是在文人向幕府汇聚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以应幕、就幕、诗会为中心的文学作品。譬如《旗亭记》这样的作品,便是因为文人就幕才诞生的;二是就幕之后,文人根据幕主的意志与需要,再进行目的性较强的文学或学术的创作,金兆燕入幕之后所作的歌咏文章便属此列。这两类因幕府而生的文学作品,由于其数量多,传播力度广,也同样影响了乾隆时代的文坛。例如金兆燕所居的卢见曾幕府,其中产生的学术与文学作品,在内容、传播、风格、偏好上都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与当时朝廷政策紧密相关,这或许是由于卢见曾拥有两淮盐运使的政治身份的原因。卢见曾及其幕府对文坛的影响,被时人评价为“重整骚坛”,这也侧面说明了政治性通过幕府向文坛的浸染。
如此看来,幕府文学一致性的强弱,其实代表着政治意志对幕内文人控制力度的强弱。而职业化,则是清初的政治在通过地方官加强对文化权力的控制的过程中,对地方文学产生的影响。在整体的历史阶段里,幕府的文化掌控力是不断增强的。这与清代前中期文化权力的中心从江湖而至庙堂的转移现象,是吻合的,也反过来可以解释,乾隆时期扬州文人的立场为什么会朝廷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