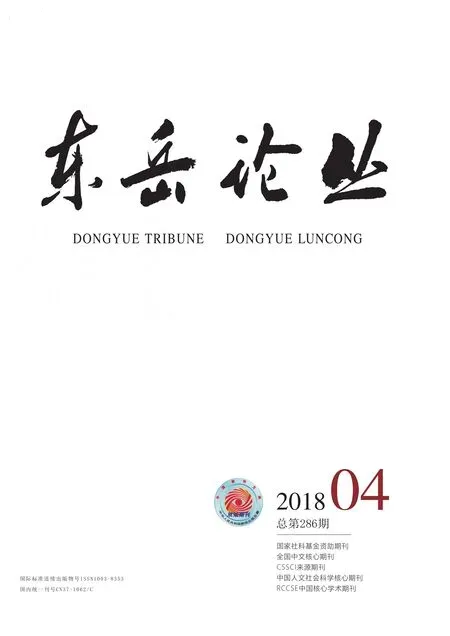论孟子“浩然之气”与“大丈夫”人格养成
梁宗华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浩然之气”是孟子对孔子儒学创新发展的一大功绩,对“浩然之气”的探讨,历来是学界关于孟子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前人气论传统的基础上,孟子基于以心善言性善的理论思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浩然之气”及“夜气”“平旦之气”等观念,既讨论了“浩然之气”的内涵特质,又点明了涵养“浩然之气”的路径,促进了气思想的道德化,具有独特的人格养成意义。孟子所论“浩然之气”是人之修养过程中所追求的生命境界,是理想人格理应具有的精神状态;而作为孟子理想人格的“大丈夫”,与“浩然之气”存在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言,“浩然之气”的最终目标就是“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养成。孟子“大丈夫”人格在价值取向、处世态度和人生持守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内涵,表现了强烈的“以德抗位”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象显然是以充盈德性色彩的“浩然之气”为底蕴的。
一
中国关于“气”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孟子之前,古人已提出了“天地之气”“血气”等观念,试图以“气”观念来解释宇宙人生中的诸多问题。古人论气的典型,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周幽王二年,都城镐京附近发生地震,周太史伯阳父揭示其起因在“气”:“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这是以“天地之气”来解释自然现象。在伯阳父看来,天地之间存在阴阳两种气,阴阳二气之间有一定的秩序;灾异如地震等现象的出现,是人为破坏、扰乱阴阳二气秩序的结果。明确肯定天地之间存在有自然秩序的“气”,并认为这种自然之气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一定的关联,这成为先秦比较普遍的认识,史籍中屡见记载。《左传·昭公元年》载,秦国医官和提出“六气”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国语·周语下》则记录了周灵王太子晋论气之聚散与民生日用之联系:“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
天地自然之气之外,春秋时还出现了“血气”的观念,用以解释生命体的活动。先秦文献记载中,“血气”一词首见于《国语》*参见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国语·鲁语上》载鲁大夫展禽之言:“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国语·周语中》记晋大夫随会聘于周所论:“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由此可以看出,血气关系着人之寿命,而能否调治“血气”则构成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左传·昭公十年》晏婴论“让”为德之主,而与“让”之懿德相对的“争心”则由“血气”引发:“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血气”为生命内在具有的自然能量,一任“血气”的本能,便会产生“争心”等恶端,因此要“思义”,发挥人具有的道德理性来克制“血气”。可见,春秋时人多认为作为生命之气的“血气”虽不可缺,但也具有负面意义,对于“血气”强调一种对治的态度。
孔子讨论到“血气”问题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孔子认为人生在少年、壮年、老年三个阶段,人体内的“血气”各有所不同呈现;根据不同阶段血气的不同特点,应该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显然,“血气”指人内在具有的生命活动状态。如春秋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一样,孔子对“血气”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主张对治“血气”。如果从孔子对“血气”的论述来理解其“性相近,习相远”思想,则夫子所谓“性相近”其实是指人在各个阶段“血气”的变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如人生少年时“血气”未定型,老年时“血气”则衰弱,在这个意义上,“性相近”才有了切实的内涵。实际上,在孔子之后的郭店楚简的相关文献中,便不乏以“血气”来解释人性的例子。“血气”观念之外,《论语》中关于“气”的用例中还有“辞气”“食气”等,这反映了“气”的概念被儒家所普遍重视。
孔子之后,子思也有关于“血气”的讨论,《中庸》有言:“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有“血气者”能够“尊亲”,而“尊亲”主要指向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情感,这就意味着“血气”与人的情感情绪存在关系。郭店楚简*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将这一点阐释得更清楚,《语丛一》云:“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血气”活动的生命体,自然会有喜怒等情感。《唐虞之道》又谓:“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则表达了时人应对“血气”的另一种态度,即强调“顺”。相较于春秋时期孔子等人对治“血气”的取向,《唐虞之道》主张顺“血气之情”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唐虞之道》将“血气之情”与“性命之正”并谈,涉及到了“血气”与人性的关系。《性自命出》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这里的“喜怒哀悲之气”其实就是《唐虞之道》所谓的“血气之情”;“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就是把生命体具有“血气之情”视作人性,这是一种自然人性论。故而《性自命出》又有“好恶,性也”“情生于性”等观点。
综括起来看,在“天地之气”“天有六气”等观念中,“气”的含义基本属于物质意义上的,主要指自然界所具有的基本物质元素;春秋时人及儒家学者关于“血气”的用例表明,“血气”主要指生命体含有的物质能量。此外,“气”还有精神意义上的用法,如《左传·庄公十年》有语,“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孙子·军争》篇谓,“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其部分内容表现出的“血气”与人性存在联系的思维模式,似是间接影响了孟子对心性与气关系的思考。
二
孟子继续了传统气思想的讨论,但孟子谈论气,与传统气论及此前儒家气论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孔子从人生修养角度讨论了“血气”,《中庸》里述及“血气”为“尊亲”的根本,郭店儒家简则探讨了“血气”与性情的关系。孟子没有沿用“血气”一词继续探讨,《孟子》全书没有一处提到“血气”,他另辟蹊径,提出了配义与道、充溢德性光辉的“浩然之气”。
通观《孟子》,“气”字集中出现在《公孙丑上》和《告子上》两篇。《公孙丑上》篇推出了“浩然之气”等核心观念,深入讨论了心与气、气与志的关系问题。《告子上》篇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夜气”“平旦之气”等说法。综合这些资料不难发现,孟子对“气”观念的运用,有物质性的方面且有神秘色彩,但基本属于气的精神意义层面。下面我们先就《告子上》篇涉及“气”的部分来展开讨论。《告子上》载: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此章可以分作两部分来讨论。第一部分孟子借山之性来喻人之性,山有生长草木之性,人具有仁义之善性。牛山之草木等生物凋零,乃是外在因素如人类过度砍伐作用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牛山没有生长草木的特性。同理,人类丧失其善良之心,亦有其外在原因,不能推翻人性本善的事实。不同于以“乍见孺子将入井”明“恻隐之心”的事例论证,此处孟子论证其人性善采用了比喻的说理方式。在说明人皆有仁义之良心后,孟子就讨论到了“平旦之气”“夜气”等。由人之良心转到“夜气”,这说明,孟子对于气的讨论,与其性善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夜气”“平旦之气”是孟子在人皆有仁义之“良心”理论基础上的逻辑延展。
在肯定人性善之后,孟子接着言“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东汉赵岐注曰:“其日夜之思欲息长仁义,平旦之志气,其好恶,凡人皆有与贤人相近之心。”*②沈文倬点校,焦循撰:《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6页,第776-777页。孟子言性善,人心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并强调扩充此四端以成圣成贤,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有四心、四端之善性,具体呈现为“平旦之气”“夜气”的形式。可见,“平旦之气”在孟子乃是人之善性“良心”感发而具有的精神状态,故赵岐解“气”为“志气”,后焦循亦采此说。反之,人若不知培养、呵护本心之善端,不断残贼、戕害本心善性,“梏之反复”,则“夜气”这种由性善发露而呈现的精神状态就会丧失,那就距离禽兽不远了。“平旦之气”和“夜气”虽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皆是根源于心性的精神之气、道德之气。

在《公孙丑上》篇里,孟子从“不动心”处谈起,直接讨论到了心与气的关系。公孙丑请教孟子关于“不动心”与告子的异同,“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孟子就此展开了具体剖析:“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提出疑问:“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孟子回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由师徒间的讨论可见,“不动心”应是当时学者追求个体修养的境界,故有告子之“不动心”与孟子之“不动心”的区别问题。孟子首先援引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观点,并表示认可。对“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一语,赵岐与朱熹在解释方面有着一致性。赵岐注曰:“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4页。朱熹解道:“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急于本而缓其末”*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页,第232页。。朱子此处的“本”指人的本心。可见,孟子此处将“心”与“气”并提,“心”指善心,仁义之本心,而“气”乃人体由内而显于外的精神状态。孟子主张内在之善心乃是精神“气”的基础,性善乃是精神“气”的内在支撑。换言之,若要探究人所具有的精神气、道德气,需要深刻体认作为大本大原的善性良心。因而孟子认可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论断。

总之,孟子论气,在承继“气”观念强调精神意义的基础上,以其善性良心为理论基础,在心与气、志与气的关系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集中突显了“气”观念的德性色彩。这是孟子“气”论与传统“天地之气”“血气”等观念不同的地方。因孟子从人之本心上言气,所以他不重视作为自然生命体内在本能的“血气”观念,而是着重讨论了带有道德意味及神秘色彩的“夜气”“平旦之气”等,强调了心志对于气的统帅作用。至“浩然之气”理念提出,则进一步彰显了孟子“气”观念的德性色彩。
三
“浩然之气”一词见于《孟子·公孙丑上》篇,是孟子“气”论思想的独特表达。孟子论“浩然之气”是难以描述的:“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在这段不到百字的话语中,孟子既讨论了“浩然之气”的特质,又指明了涵养“浩然之气”的路径,可谓意义丰富。


学界往往把孟子“浩然之气”与《管子》中的“气”论联系起来,甚至直指孟子受稷下道家的影响。*如陈鼓应先生认为,孟子的气论极有可能受稷下道家的影响。见《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5页。诚然,齐国稷下道家十分重视“气”思想的探讨,提出了著名的“精气”说。《管子·内业》篇有言“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又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孟子“浩然之气”与《管子》“精气”说确有相似处,但我们更要看到二者的区别。《管子》 “精气”说基本上仍延续了气作为物质力量的意涵;而孟子浩然之气则是“集义所生”,又需“配义与道”等修养工夫来涵养,具有鲜明的德性色彩。可见,孟子浩然之气与《管子》气论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容忽视。我们既要认识到孟子曾长期游齐久居稷下学宫,可能受到稷下道家的影响,同时也需要有所辨别,作为孟子思想独特创造的“浩然之气”,因其具有的充溢的德性色彩,显然与稷下道家“精气”说区别开来。
四
善养“浩然之气”的最终目标可藉由“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养成来呈现,“大丈夫”理想人格是由“浩然之气”作支撑的。作为孟子理想人格的“大丈夫”,以“居仁由义”为价值取向,以“知时通变”为处世态度,面对穷通不同境遇能够坚持人生操守,表现出强烈的“以德抗位”的精神。“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养成,一方面需要坚定的内心志向,另方面借助于外在艰难困苦的磨练,而这一切恰与 “浩然之气”的存养相契合。
从《公孙丑上》篇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浩然之气”的具体语境来看,“养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擅长的。在孟子的世界中,“浩然之气”绝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一种理论学说,更是实践修养过程中所追求的生命境界,是孟子理想人格理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北宋程子讲“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又讲“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页,第270页。。因此,我们探究孟子“浩然之气”,在具体诠释其特质与涵养方法(所谓“以语言解”)之外,还应当充分关注孟子思想中与“浩然之气”相呼应的理想人格问题。在孟子思想中,最能呈现“浩然之气”的无疑当属其“大丈夫”理想人格。

孟子“大丈夫”人格亦有入世安百姓的层面,“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强调了“大丈夫”在入世过程中知时通变的态度。孟子倡导得志时要济世救民,引导天下百姓共同向善;失意时则需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亦即《尽心上》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承继了前儒“穷达以时”的思想,注重穷与达、得志与不得志的分别,并将这种分别贯彻到其“大丈夫”人格的建构中,反映了其理想人格具有知时通变的处世态度。然知时通变不等于与世俯仰,流于俗庸,而是在权变中亦持守道义,绝不苟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点明了“大丈夫”面对不同境遇的人生操守。此处孟子接连用了三个“不能”,强调无论是身处富贵,还是落魄贫贱,都要有所持守,不变节操。这正是“浩然之气”“集义所生”的存养。概言之,作为理想人格的“大丈夫”,无疑在生存论、价值论等方面都彰显着孟子阐扬的浩然正气,是“配义与道”的典型展开。
孟子“大丈夫”人格还表现出强烈的“以德抗位”的精神。“以德抗位”精神是思孟学派的典型特征,而在孟子实际是他所推崇的 “大丈夫”理想人格所应具备的主体品质及精神涵养*梁宗华:《从孟子看思孟学派的“以德抗位”精神》,《东岳论丛》,2009年第12期。。孟子以“大丈夫”应为君王之师友,具有高尚的德行,不为强权政治所左右。孟子倡言“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强调人性上的平等,君王不能因权势而轻视有德行者,故而“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公孙丑下》)。基于此,他力倡对等的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孟子的抗争精神至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君王有他的财富、爵位,而“大丈夫”能够持守仁义等道德价值,足以与任何权势富贵抗衡。“以德抗位”的精神还体现在孟子“天爵”“人爵”之辨中。《告子上》载:“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人爵”是指世俗的公卿大夫等爵位,而“天爵”则是儒家仁义忠信等道德品质与价值追求。通过“天爵”与现实世界“人爵”(也就是官爵)的鲜明对比,“以德抗位”的主体品质得到进一步彰显。因“大丈夫”须具有“以德抗位”的精神与品质,故孟子认为在当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根本不能算是“大丈夫”,以至讽刺纵横家所行的乃是“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以德抗位”精神的根底从“气”上说,正是人人皆具的“夜气”“平旦之气”、可存养的“浩然之气”,此“气”一旦馁之,“天爵”就失却了支撑点,“以德抗位”也就无从谈起。
在孟子看来,内心志向的笃定,外在艰难困苦的磨练,是铸就“大丈夫”人格的必要途径。“大丈夫”人格的养成,需要有成就人格的内在动机。孟子认为,笃志于仁义,时时处处居仁由义,乃是成就大事、成为“大丈夫”的关键。显然,这个“志”是充溢着“气”的,如前所述,“志”乃是心中产生的意向,可以支配、调动充满身体的气。《尽心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具有高尚的志行,按照仁义的要求来行事,是成就伟大人格的必要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外在艰难困苦的考验。孟子认为,外在艰苦的考验是成就伟大人格的因缘之一。“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追溯历史,许多著名的人物大都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磨练。舜在成为天子前,曾从事过田野耕作;傅说被武丁提拔为相前,从事过夯土筑墙的工作;管仲成为齐国之相前,担任过官狱长的职务。因此孟子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警世之训,为人在逆境中进行道德修养提供精神力量。人所经历的种种挑战,身心所受到的种种磨练,皆是培养伟大人格所不可或缺的,故孟子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大丈夫”人格由此以成,“浩然之气”藉此以见。
综括观之,孟子理想人格“大丈夫”,正是在内心修养和外在考验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无论穷达能保持志意充满、不动心,唯一的路径就是养“浩然之气”,持之以恒地“集义”,始终坚持“配义与道”,以避免“行不慊于心”的气馁情形。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必然养成“大丈夫”理想人格。
——论阳明学派对告子思想的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