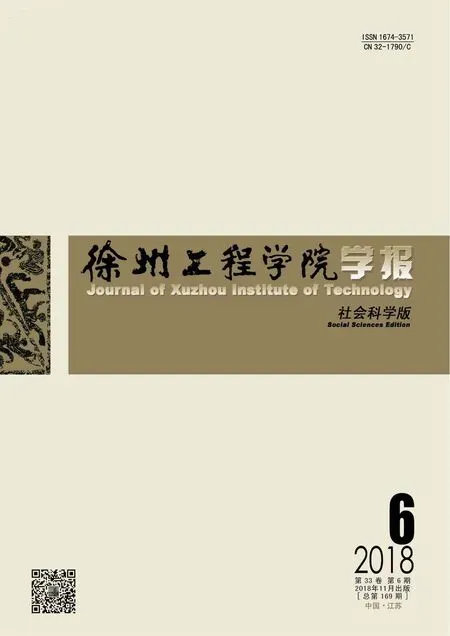回归与超越:身体美学之于生命美学的意义
范 藻
(四川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3)
引言:生命美学不能没有“身体”
“上帝死了!”随着尼采一百年前振聋发聩的一声,当芸芸众生饱尝20世纪的天灾人祸造成的食不果腹和衣不蔽体,还有21世纪以来国泰民安带来的丰衣足食和健康美丽,长期被精神桎梏的身体和让灵魂纠结的肉体,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而大放光彩:
婀娜多姿与魁梧奇伟的美体、花容月貌与清新俊逸的美颜,加上五彩缤纷的美视、婉转悦耳的美听、绫罗绸缎的美服、山珍海味的美食,穿行在大街和小巷,散布在都市和村落,弥漫在空间和脑海,又依托文字、图画与雕塑,更借助银屏、荧屏与视频,还使用T台、舞台与秀场,加上互联网的神通广大和多媒体的出神入化,一时间蔚为大观,让人目不暇接又耳不暇听而美不胜收。
面对如此的美奂美伦,美学理论要么用“日常生活审美化”予以评说,要么从“审美文化现象学”给予解读,而上个世纪80年代悄然登上中国当代美学殿堂,而今已成美学界主流学派的生命美学仍然熟视无睹,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尽管在日常审美活动中身体从未“缺席”过,甚至僭越了生命。虽然,当代中国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潘知常教授也曾多次表述过对美学尤其是生命美学的精深理解:“真正的美学应该是也必然是生命的宣言、生命的自白,应该是也必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1]“美学必须以人类的生命活动作为自身的生命活动的广阔视界。换言之,美学倘若不在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地基上重新构建自身,它就永远是无根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它就休想有所作为。”[2]但是,在潘知常教授的生命美学的园苑里很少正面触碰过身体,更未实质性接触过身体美学。
笔者眼中的生命美学,不论是守望精神家园,还是建构美学大厦,都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和现实前提,那就是要让作为感性意义上和个体身份中的“身体”莅临。的确,守望精神家园固然神圣,而如何呵护现实人生则不可或缺;建构美学大厦肯定重要,而如何夯实人学基础岂能漠视;仰望星空诚然无比高尚,而如何脚踏实地则不可小觑。生命活动有着无限广阔的“疆域”,而如何立足审美活动的“大地”呢?由于生命美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之间关系的意义阐释”[3]。因此,在“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它理所当然地是要包括身体的存在并现身的,也就是说不论是“审美活动”,还是人类的其他“生命活动”,身体都是不能缺席而必须参与的。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生命美学更多的时候是在“仰望星空”,更经常的是在“追问意义”,更看重的是“自由”的乐园,更向往的是“超越”的境界。看来,为肇始于王国维百年余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为光大潘知常近40年的中国当代生命美学,补上“身体”的存在,引入“身体”的意识,不但正当其时,而且刻不容缓。
身体的自然意义和物理功能,毋庸讳言。那么,从美学的视角看,身体的功能体现于:它既是审美的感受器官,比如视角和听觉;又是审美的活动中介,例如形貌和衣饰;还是审美的意义载体,诸如头脑和心灵。这是一个经历审美活动的实践,再经审美意识的升华,而完成的由身体感受到心灵感悟,最后身心一体的连续性的运动形态。由于身体既是审美的对象,也是审美的主体,还是审美的目的。因此,回归身体又超越身体,是身体美学的起点与终点,而这个终点刚好接上生命美学的起点。由此可见,就本文的主旨而言,鉴于回归与超越是身体美学的内在机制和本质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美学才具有了对话生命美学的物质基础和融入生命美学的精神空间,更是能启迪生命美学的哲学意义。
说到身体美学,不得不提到当今世界著名的美学家,也是身体美学的首倡者美国的理查德·舒斯特曼教授,1999年夏,他在美国《美学和艺术批评》(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杂志上发表论文《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Somaesthetics:A Disciplinary Proposal),提出从学科角度重构“身体美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问题,这标志着“身体美学”的正式诞生,随后他的《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等著作在新世纪初相继进入中国,很快成了新的学术热点。吊诡的是,这个与生命美学有着最亲缘而必然的话题,竟然被生命美学的研究者长期漠视。那么,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究竟是什么呢?他在2014年出版的《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的“中译本重印序”开篇说到:
身体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它致力于对活生生的身体进行批判性研究和改良性培养——身体在此被视为感性欣赏(感觉)与创造性自我风格化的场所。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科,身体美学不但力图丰富我们的身体知识,而且力图丰富我们富有生命力的身体体验和能力。……身体美学关注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各种知识形式、社会实践、文化传统与价值以及各种身体学科——所有这些领域共同塑造(或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理解和培养。[4]
至于如何精确理解舒斯特曼的“身体”概念,如何正确认识他提出的身体美学的三个基本维度,即分析身体美学(analytic somaesthetics)、实用主义身体美学(pragmatic somaesthetics)和实践的身体美学(practical somaesthetics),以及他的身体美学的得失和是非,都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建构的身体美学在身体意识的唤醒、身体能力的强调和身体价值的开发诸方面,究竟能够给生命美学带来哪些全新的思维和深刻的启迪,进而弥补生命美学的学问欠缺、完善生命美学的学理构架、丰富生命美学的学科内容和承担生命美学的学术使命。
一言以蔽之:围绕生命的回归和超越的感性实践和理性认识,生命美学应该踏上而且也能够行进在“身心合一”的漫漫长路!
一、回归健康,超越生存——增强生命活力
以围绕人的生命意义探寻的生命美学之“生命”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要理解这个小标题中的“回归健康”和“生命活力”的关键词,首先就得明白舒斯特曼对“身体”一词在身体美学中的含义。2008年舒斯特曼“在山东大学访问时曾对自己使用somaesthetics而不是body esthetics做过如下解释:‘为什么把身体美学叫做somaesthetics而不是body esthetics呢,因为soma相对于body来说,他还没有被身心区分所污染。soma指敏感的活的身体,而body则通常指物质的肉体,也就是说,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重点关注身体的主观性和感知,关注身心统一的整个人,这在体现审美经验时至关重要。’上述舒斯特曼对自己使用somaesthetics一词的解释,无疑切中了身体美学的要害,即身体不仅可以在形式上表现为美、崇高、优雅等美学特性,而且它还可以作为一个通过身体的感觉来体验审美愉快的主体。”[5]毋庸置疑,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在增强生命的活力中成为“体验审美愉快的主体”,才能超越身体美学在生存层面上的局限,而进入生命美学在价值领域里的自由,并感受人伦世界的爱意。由此可见,生命美学再也不能置感性鲜活的身体而不顾了,在它理论大厦的建造中首先应该培育健康的身体——生命美学的第一块基石。
与实用主义哲学、唯意志主义思潮息息相关的生命美学之所以诞生于近代,因为这是一个经历了文艺复兴洗礼、启蒙运动冲击和工业文明辉煌的“人的觉醒”的时代,19世纪后期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述“美是生活”时,就对“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而大加赞赏。针对个体的身体美学,还是人类生命美学,其重要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就是要让这个唯一而真实的身体“活着”——健康地“活着”,如此简单而明了的事实和道理,却是在中西方文化史上为了在所谓的“人猿揖别”中显示人类的高尚和优雅,几乎都一致性地放逐身体。肇始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努力为现实的生命构筑了一个虚幻的理念世界,及至基督教文化的兴盛,更是蔑视人的感性存在和世俗生活;而旷世奇才的尼采在他病痛身体写照的《悲剧的诞生》里推崇生命沉醉的“酒神精神”,又在他崇高精神象征的《强力意志》中倡导生命活力的“意志力量”,“要以肉体为准绳……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6]但是尼采的这一切并非在真正的强调强健的生命,而是在“借船出海”,其真实动机是孕育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超人”,尘世的“肉身”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中国文化尽管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也有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但这里的“健”和“身”都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精神的“浩然之气”和社会的“人伦之义”,其根本仍然是反身体的,老子就说过“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编写的有关修心养性《小窗幽记》里也多次说到“宁无忧于心,不有乐于身”,“心性本不束,肉身是桎梏”。在这样一种反身体的病态文化的熏陶下,鲁智深、李逵和张飞等都是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人物,而梁山伯、潘安和张生一类的白衣秀士、文弱书生和奶油小生备受吹捧,只能说明身体美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阙如。
立足于实用主义哲学的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在他的三个基本维度中有两个就是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实用和实践含义的,而身体要有“实用”和能“实践”,毫无疑问必须是健康的身体。有关身体的美学首先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对此舒斯特曼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求“这不是动嘴而是动手,即以冥想的、严格训练的和近于苛求的肉体实践指向对身体的自我改善(无论是外观的、经验的还是执行的范畴)”[7]。为此,他介绍并提倡了三种健康身体训练法:亚历山大技法(Alexander Technique)、生物能疗法(Reichian bioenergetics)和费尔登克拉斯方法(Feldenkrais Method),来说明具有实践意义的身体美学为身体的审美改善,而进行的科学而有效的训练。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技法的训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它近似于印度的瑜伽和佛教的禅坐,是通过意念的作用来有意识地调节、控制身体,实现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而是身心的和谐。遗憾的是,我们的生命美学坐而论道有余而躬而行之不足,精神魅力有余而身体实力不足,指手画脚有余而身体力行不足。试想,如果我们的生命美学能够高度重视“形而下”的身体,加上理论传统的“形而上”研究的优势和积淀,进而实现既依托身体美学的健康实践,又超越仅仅是为了活着的生存式健康,在身心和谐的愉悦中增强生命的活力,这才是我们所期待而名副其实的“生命美学”。
二、回归个体,超越生理——发现生命张力
要做到身心俱在的健康、达到身心交融的体验效能,其前提不是作为“类”的生命存在,而是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即必须是真实的“这一个”;因此生命美学除了回归健康,能够落实生命之美的关键还在于回归生命的个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个体”呢?尽管笛卡尔说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千古名言,但他的个体是精神层面的个体而不是身体意义上的个体,倒是稍晚于他的法国17世纪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帕斯卡尔对个体的阐释更符合生命美学的精神:“每个人对于他自己就是一切,因为自己一死,一切对自己都死去了。由此而来的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对于所有的人就是一切。”[8]不论是身体美学还是生命美学之所以诞生在西方,是与它的文化对人、尤其是对个体的人的重视分不开的。古希腊城邦制的解体将个人从国家的统辖状态中剥离开了,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相对于上帝而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以后一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都是源自于个体意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直接将身体存在和生命意义归结于“性本能”。以上说明,个体固然重要,回归亦不可少,关键是如何超越这个回归身体后的有着自然属性的生理,从而在回归个体与超越生理之间发现生命的张力。
在身体和个体关系的论述上,叔本华可谓一语中的:“身体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个体,亦即是唯一的意志现象和主体唯一的直接客体。”[9]不论是身体美学还是生命美学,在回归个体的问题上,如果说叔本华阐释的是“是什么”,那么海德格尔阐述的就是“为什么”。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的《尼采》讲座中强调了身体的情感本体论维度:“作为自我感受的情感恰恰就是我们身体性存在的方式。……身体在其身体状态中充溢着我们自身……感情并不是某种仅仅在我们‘内心’发生的东西,而毋宁说,感情是我们此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凭借这种方式而且依照这种方式,我们总是已经脱离我们自己,进入这样那样地与我们相关涉或者不与我们相关涉的存在者整体之中了。”所以,“情调(stimmung)恰恰就是我们在我们本身之外存在的基本方式。而我们本质上始终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10]。在身体的“个体”意义上,叔本华的回归虽然强调了“身体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个体”,但是它是“意志现象”的客体,因此并没有真正回归身体。而海德格尔则不同了,他的“身体”不是碳水化合的物质,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不是能吃会喝的生物,而是有情有义的生灵。海德格尔“个体”论的身体美学,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价值。首先,突出了“我”的在者意义。在他的哲学话语里,“我”就是“在”,“在”就是“我”,因为“我”而使得“在”恬然澄明。其次,揭示了“个体”的生存境况。由于存在的永恒性,肉体凡胎的“我”尽管是世界的存在,而这个存在也是世界强加给“我”的,那么存在即选择,“我”能选择的就是当下的活得精彩。最后,引入了“情感”的本体维度。如果没有这个维度,那么回归也许就只有生物学的意义了,而他从本体论上阐述了我们身体的“基本存在方式”,于是超越了“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生命。
回归身体意义上真实的生命个体,并不意味着沉湎于感性的愉悦和肉体的欢乐,而是要超越生物意义上的有机体的器官机能和生命动能,让身体美学为生命美学输入物质的实力、感性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这是一个如何让身体美学走向生命美学的艰难历程。借用著名学者刘小枫对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分析来论述这个颇为沉重的话题吧:“在现代启蒙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个体肉身要么血肉模糊,要么随意含糊。与萨宾娜一起反抗媚俗,托马斯发现自己跌进了另一种让个人的身体没有差异的在世境况,仍然没有摆脱与自己肉身相关的实质问题:如何让自己的肉身幸福,从各种意底牢结中夺回肉身的权利后,什么是幸福依然还是一个问题。”[11]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对幸福的追问不是爱与不爱的世俗伦理,而是肉身的轻盈与心灵的沉重所带来的生命意义的思考,他越是拥有身体的欢乐,越是感到灵魂的苦恼,主人公陷入了灵与肉的“悖反”。其实“托马斯”是现代人的隐喻,我们确实回归到了身体意义上的个体,我们所获得的尘世幸福依然属于生理的幸福,如何超越身体的生理性而进入生命的生灵性,出家修行也罢,周游世界也罢,投入事业也罢,痴迷学问也罢,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一样,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然而,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物与我、灵与肉、性与情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发现了生命美的张力。
三、回归体验,超越生活——感受生命魅力
仅有健康的属于个体自由的身体,如果长期足不出户,终日无所事事,那么,生命仅具有生物学意义地活着。研究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更看重的是他那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理念。在创立身体美学时他首先阐释了“身体意识”的来源和含义,他在其《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于2009年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写的序中说道:“所谓的‘身体意识’不仅是心灵对作为对象的身体意识,而且也包括‘身体化的身体意识’:活生生的身体直接与世界接触,在世界之内体验它。通过这种意识,身体能够将它自身同时体验为主体和客体。”[12]舒斯特曼的“身体意识”不是纯粹的意念和意志,而是“身体化”了的“身体意识”,这里的“身体化”指的是经过在长期的身体体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感性与感兴、亲自与亲在的身体体验成效和认知模式,这是一种“我体验我存在”的鲜活感和生动感的生命存在感受。并且这种“身体化”将产生“同时体验为主体和客体”的神奇效果,即主客一体、物我交融,起初达到的是张孝祥描写的意境:“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最后实现的是苏东坡的境界:“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张孝祥是中秋之夜过洞庭湖的“表里俱澄澈”个别性情景体验,苏东坡是历经坎坷曲折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总体性人生体验,很显然他们都在体验中超越了体验,由具体的生活际遇进入到了生命境域。
对身体的体验予以深刻阐释的当数20世纪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大师梅洛-庞蒂,他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了身体在空间中的关系。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多次使用“体验”、“知觉体验”和“身体体验”,他认为“体验”是“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与它们一起,而不是在它们旁边”[13],这种体验既不是柏格森强调的瞬间直觉,也不是谷鲁斯所谓的内在模仿,更不是立普斯阐释的自我移情,当然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身体力行、真实接触和现场感受,更不可能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而是通过长时间和反复性地尝试和体验,全身心地投入,进而在感知途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等身体的内在方面和环境、他人,乃至与自己的身体建立起一个“身体—实践图式”。这有点像竞技运动和舞蹈艺术在经过长期而科学的训练后,让运动员和舞蹈者形成的“肌肉记忆”和“身体感觉”。他用这个图式为我们解答了“艺术创作之谜”,当一个艺术家在日积月累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在自己熟悉的艺术技法和创作对象之间找到最恰当的表现方式,就像马克思论说的“有音乐感的耳朵”。梅洛-庞蒂还将个体的主体性体验,延展成了体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体验,“是我的身体在感知他人的身体,在他人的身体中看到自己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种对待世界的熟悉方式;从此以后,由于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所有他人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是一个系统”[13]。身体的感知和体验,不仅设身处地,而且以己度物,最后相交相知、共振共鸣,形成了一个群体体验的场效应,犹如巴赫金所谓的“狂欢节气氛”,将个体的体验传导为群体的体验,反过来又加深、加强和加重个体的体验,从而再一次超越了有限生活的时间经历和空间场域,强烈地感受到因为身体在场和身体接触而产生的快感与震颤。
梅洛-庞蒂以知觉为抓手、以体验为核心建立的身体美学,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体验有四点超越日常生活意义的重要价值。一是,它是一种以肉身实在体验为依托的内在体验,然而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他所谓的“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是水乳交融式的主客一体的体验。二是,它是一种以身心合一体验为目的的生命体验,尽管是肉身的在场和亲临,但不局限于肉身,而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的五官感觉,融合了体验者的认知、情感、意志和思维,是内外一致的生命体验。三是,它是一种以建构身体—实践图式为特征的艺术创作体验,体验人和创作者合二为一,认知模式和创作对象圆融无碍,这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物我交融的艺术体验。四是,它是一种以体验主体发动的主体间性的复合式体验,体验场域和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类似通常说的把快乐分享给他人,使自己获得了双倍的快乐,这是由我及他的群体体验。身体美学高度注重体验又超越体验而达到的一种生活态度、艺术修为和人际和谐,给生命美学以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吸取身体美学对身体体验的重视和方法,突破一般意义上的肤浅而零碎、偶然而片段、独自而封闭的体验,在身爽体畅的体验中达到心旷神怡,享受生命的活力进而感受生命的魅力,让以爱为鹄的、以乐为兴趣、以情为核心的生命美学,在身体的亲临和参与中既望“云气”又接“地气”。
结语:生命美学如何拥有“身体”
没有“身体”的生命美学因缺少人间烟火而“高处不胜寒”。“将生命从具体的身体—物体中抽离出来,视之为弥漫于宇宙间的力量,是不少生命美学家的致命错误。这样既使生命成为一种悬空的精神,又把具体的身体—物体降低为供生命流转的工具,所守护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人们的某种意念。”[14]其实这不是生命美学的过错。隶属于哲学范畴的美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放逐了身体的存在,在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对话中就认定“永恒的美”,“不是视听产生的快感”,他在美的相对性思辨中连青春少女都开除了,因为“比起神,最美的年青的小姐不也就显得丑吗?”[15]柏拉图也说“灵魂脱离肉体,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16]。这成了西方美学长期以来以奉理性精神为圭臬、以求上帝意志为法宝的始作俑者,直至1750年鲍姆嘉通才又把美拉回到了“感性”的世界,其著名论断“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为身体美学的出场预设了空间。
然而,魂不附体之“身”与貌合神离之“心”的身心分离太久了,要实现安身立命之“身”与形神兼备之“心”的身心合一,难矣!因为“身”所具有的物质形态和动物属性与“心”所具有的精神形态和社会属性,在本质意义上形同水火,就连博学的浮士德也陷入了这无尽的纠结烦恼:“它们总想互相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居地。”以回归身体和超越生命为旨趣的生命美学,对此困境是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还是绝地反击,从而浴火重生?答案毋庸置疑,生命美学应该而且也能够建立起身心合一的哲学路径和美学策略的。
首先,他者与自我的融合。人的身体对于人而言,既是他者的对象化客体,又是自我的亲在性主体,身体在这里具有了“主—客一体”的二重性品质和“他—我一身”的双面性特征。如何化解这个“二律背反”的纠结,还是要从他者与自我对立面统一于“自身”的矛盾解决入手,与其说是要完成一次思维视界的融合,不如说是要达到一种现实场景的整合;在审美实践中不但要真正做到“我的身体我做主”,而且要真诚实现“我的生命听我的”,这样的话,就为身心合一的生命美学从学理上证明了存在的必然性。
其次,感觉与思维的契合。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前提是我能够感觉到“我在思”,这是靠身体的在场而感觉到的,也许是在看或听的同时在“思”,这时视听的感觉有助于思维的运动,即是闭目沉思或夜半思考,大脑依然会呈现与思维内容有关的景象。这种感觉与思维契合的原理说明,身体的亲在感觉与生命的能动思维是能够同时发生在某一个个体身上的,这就为身体在适时介入生命的审美活动过程中,做到了感觉与思维的同时性俱在和共处性存在,从而为身心合一的生命美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再次,呈现与隐逸的会合。一方面,作为具有社会学价值的美学,在其本质意义上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或者要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实践,因此,在每一次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就得有人的身体或行动的呈现;另一方面,作为思辨性质的哲学范畴的美学,其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是隐含在活动或作品之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何让这种“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呢?借助肢体、表情、手势等“身体语言”,使隐逸得以显现。生命美学引入了身体美学的入驻,就会借助身体的呈现来传递隐逸的思想情感。
最后,快感与美感的结合。传统的美学要么将二者分离开来,要么将二者视为先后次序或高低关系,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18]由于身体美学对人的生理反应和性征器官进行的审美研判后而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再加上生命美学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原始欲望进行了合法性的认同,那么余下的问题是生命美学如何堂而皇之又名正言顺,并更加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身体产生的快感,来丰富和充实生命的美感。
如前所述,我们在对身体美学回归与超越的往返来回中,既感到了生命美学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发现了完善生命美学的大好机遇,那就是在从“身体”走向“生命”的过程中,回归健康,超越生存,进而增强生命活力;回归个体,超越生理,进而发现生命张力;回归体验,超越生活,进而感受生命魅力,从而实现身心合一生命美学的最佳效果和最高境界。从身体到个体再到体验,回归是手段,超越是指向,生命的澄明才是身体美学、生命美学的真正目的,只有身体美学的介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命美学。就此而言,王晓华教授的“生命美学是以身体为审美主体的美学”[14],真是深得我心!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身体之欲与生命之爱时,说的那样:“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的器官,……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8]毋庸置疑,这种属于“人”的自我享受,是由身体感受到心灵感悟,再由心灵美感到身体快感的并在回环往复过程中而形成的水乳交融般的“身心一体”。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烛照下,在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引入中,生命美学的完整要义终于昭然若揭了,那就是身体存在意识、个体本位主义和社会审美价值的三位一体。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一种身体感性实沉的“立地”与生命意义追寻的“顶天”——顶天立地的生命美学即将呼之欲出。
借用奥地利著名诗人特拉克尔的名言:“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那么,我们要说的是:身体,伊甸园的呵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