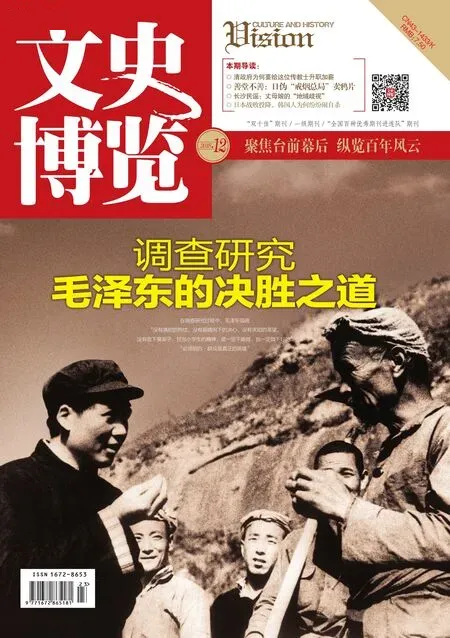善堂不善:日伪“戒烟总局”卖鸦片
利用鸦片侵略中国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在华特务机关就驱使日本、朝鲜浪人,以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贩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并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利用关东、热河一带出产的烟土,公开推行其毒化政策。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财政日益困难,为贯彻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和军方决定在中国大规模地贩卖鸦片,希图以贩卖鸦片的巨额收入来维持汉奸政权,支付一部分战争经费。
1938年,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军事顾问原田熊吉的指使下,“维新政府”设立了所谓的“戒烟总局”,并在各主要城市设立了分局,公然准许开设烟馆,以便大量倾销鸦片。为了避人耳目,逃避贩卖鸦片的恶名,原田熊吉又指使在“戒烟总局”下开设了日伪最大的鸦片公司——宏济善堂,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负责。
里见甫是日本著名浪人,记者出身,有“满洲市场鸦片王”之称。因其久在伪满洲国依附关东军,与原田熊吉和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总务课长楠本实隆成为莫逆之交,原田极力怂恿其出面主持宏济善堂。
盛文颐,字幼盦,江苏常州人,排行老三,上海人称盛老三,是清末著名官僚买办盛宣怀之侄。此人在清末民初曾任知州、道台、盐务局总办,津浦、京汉铁路局局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他不顾民族大义,竟投靠里见甫,被日本委为宏济善堂主持人之一。
宏济善堂中央行设在上海虹口,在盛文颐的拉拢下,上海郑芳熙等人参与投资,经营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从伊朗等国购运而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伊朗等国鸦片来源断绝,故从东北、内蒙古等地采运,交宏济善堂出售。里见甫、盛文颐还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设立地方行负责承销宏济善堂的鸦片,这样苏、浙、皖三省鸦片贩卖遂为宏济善堂独家经营。
日本的毒化政策使沦陷区烟馆林立、乌烟瘴气。以南京为例,日军占领不到一年,鸦片泛滥成灾,至1938年11月止,吸烟者不下5万人。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专营鸦片的土膏行30余家。
“维新政府”所设立的“戒烟总局”名义上是宏济善堂的监督机关,实际上除每月照收少数捐税外,概不过问。宏济善堂运销鸦片的数量及经营情况从来不呈报“戒烟总局”,所以其收入也无从稽考。它的业务直接由日本兴亚院(抗战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楠木实隆为该院调查官)负责监督,每年运销鸦片的数量也由兴亚院核定。
据汪伪实业部调查:宏济善堂1940年约销鸦片500万 两,1941年 450万 两,1942年 350两,1943年 350万两。至于该堂历年盈余除中央行抽取极少数外,全由里见甫、盛文颐及秘书主任兼会计调查科长日本人大西直接解往东京,在华日本机关也不知其详。据“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供称,日方每月从中拨政费20万元,其余的则成为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
汪伪汉奸对宏济善堂的巨额收入早就垂涎三尺,但知道它的后台是日本人,不敢公开惹它。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就曾指使他们的党羽门徒到上海各处的土膏行、售吸所“登门拜客”,以种种借口迫使各行各所向他们交纳“月规”。

宏济善堂戒烟部,名义上帮助戒烟,实际上是鸦片贩卖组织
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后,陈璧君、林柏生要宏济善堂每月“补贴”4000万元,盛文颐不同意。后减至1000万元,陈公博亲自找盛谈,盛文颐自恃有日本人撑腰,仍不买账。
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毒化政策早已义愤填膺。1943年12月,南京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17日,伪中央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揭露日伪贩毒罪行,捣毁了宏济善堂南京分行。次日,南京大、中学生3000多人从朱雀路到夫子庙,打烟馆、砸烟具、轰烟客。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乘机捞取政治资本,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此时,日本国内反对派也借此大肆攻击首相东条英机,并在国会揭露日本军方利用海军舰艇把宏济善堂的鸦片大量运往广东、海南岛等地销售,朝野大哗。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日本大本营海军报道部部长谷获少将公开发表声明:“在华皇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宏济善堂系中国人盛文颐主持,与皇军并无关系”。
这样一来,日本与宏济善堂的微妙关系反而更加引人注目。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手下的实权派、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辻政信对里见甫主持宏济善堂也持反对态度。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军方遂告诫其侨民及士兵“不得再干预烟土问题”,里见甫被迫停止贩卖鸦片的活动。盛文颐见主子态度骤变,不得不于1944年春将宏济善堂解散。
抗战胜利后,盛文颐的家产被清算。他在上海拥有十几处豪宅,家中所有的痰盂都是纯金打造而成,其他用具,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鸟笼子,也都是黄金做的。查抄的逆产,仅目录便长达128页。其本人因罪行严重,逮捕后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