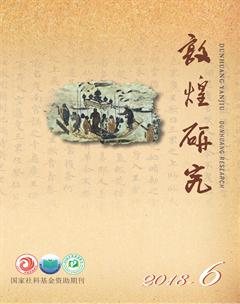四川广安冲相寺定光佛龛像研究
符永利 王守梅
内容摘要:四川广安市肖溪镇的冲相寺石窟是一处重要的隋唐石窟寺,其中开凿最早的定光佛造像,题材特殊,造型独特,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样式类型分析,可看出此尊定光佛像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属于简化类型,所饰的太阳纹头光在冲相寺石窟中有一定的典型性。这种颇具特色的头光可能是由古印度犍陀罗起源,经西域、河西从天水、汉中传入巴中,再经巴中沿渠江传至冲相寺。定光佛造像的着衣方式也独具特色,而其手印更蕴涵特殊含义,应表现的是本生授记和三童子缘。该龛造像反映的是早期定光佛信仰,属于正统信仰,与五代之后流行的晚期闽西定光佛信仰不同。隋代之所以在此开凿这尊定光佛像,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求得授记、祈愿成佛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冲相寺石窟;定光佛;类型;年代;造型;头光;服饰;信仰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6-0038-11
冲相寺石窟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肖溪镇冲相村八组,地处渠江上游北岸台地上,距广安城区60多公里,地理坐标为N30°42′20.41″,E106°54′48.21″(图1)。据我们2012年调查资料显示,冲相寺尚存摩崖龛窟58个、造像261尊(不计浮雕)、题刻77幅以及大小不等的崖墓14座。主要分布在大雄宝殿之后的定光岩及其东西两侧以及狮子山的崖壁上,东西绵延约200余米,自西向东通编58号。作为定光佛道场的冲相寺,最著名的当属定光佛龛,此龛编号为K26,位于定光岩中段正面上方偏左侧,在此面岩壁的最高处,位置显著,造像独特,研究价值颇高,也是冲相寺石窟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龛造像。
关注此龛造像的学者并不多,相关研究论文仅见四篇,如刘敏先生的《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及石刻调查纪要》[1]、《广安冲相寺锭光佛石刻造像考略——兼论锭光佛造像的有关问题》[2],另有翁士洋的《广安冲相寺与定光古佛信仰》[3]、杨洋的《四川广安冲相寺石窟研究》[4]。刘敏先生的调查开展较早,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对造像特征作了初步归纳,同时提出一些可供探讨的问题,颇具启示意义,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文中存在尺寸数据有误、细节描述偏差较大等问题。翁士洋先生主要讨论定光佛信仰,认为冲相寺定光佛造像反映的是正统信仰,而非五代宋初兴起的定光佛民间信仰。杨洋的硕士论文在第四章将冲相寺定光佛造像与其他地区的同类造像作了比较,揭示出表现在时代、服饰与手印诸方面的特殊性,也对其重要价值有了进一步认识。总体看来,冲相寺定光佛造像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调查方面的基础数据有待实地复核,予以重新纠正确定;第二,造像特征需要深入而全面地歸纳提炼,涉及到头光、肉髻、面相、体型、姿态、身体比例、着衣方式、手印等方面;第三,需将其置于更宏大的中外定光佛造像体系之中,相互比较,于分类定型中认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相关的传播源流等问题;第四,特殊手印的含义不明,有待解读。本文仅就部分问题试作论述,请专家指正。
一 基本概况
冲相寺定光佛龛(编号K26),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制,龛宽170、高242、深75厘米。龛内正壁雕一尊立佛,像高220厘米;头后雕有圆形头光,内饰放射状锯齿纹,圆光外为彩绘的尖桃形,并有彩绘的身光一直延伸至龛沿;磨光高肉髻,面相较方,弯眉睁眼,鼻口略残,神情庄重,额头稍窄,下巴浑圆,长耳厚大,颈饰三道;窄肩,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胸下衣纹呈U字形,衣角下部饰有万字纹;双手向身体两侧半伸,左手掌心朝上,右手掌心朝下;腰下着长裙,赤双足各踩一朵仰莲圆踏。踏下为长方形低台(图2、图3)。
二 年代问题
定光佛造像的年代一般被认为是隋代,直接依据是龛外左侧壁上的一则楷书题记,内容如下:
永……(熙)……/王知球写同……父(与)子向……/先发心……主……冲相寺/定光(佛)并给贡木□未庆讫会……/铭意(题言)□清者……(会)……先……/……财帛公□□庆(开)/皇□年十一月十八日设(斋)题谨记/永(为)福□□记/”。
由于风化严重,仅能释读部分字句。由题记可见,定光佛龛像当开凿于隋代开皇年间(581—600)。
又据立于唐开元六年(718)的《大唐渠州始安县冲相寺七佛龛铭碑》载:
佛法尊于皇唐。修龛者,使持节、渠州诸军事主长史丁正已也。……按部始安,遂届于药寺。其寺,隋开皇八年流江郡守袁君等所立。皇朝奏修祠额,寺有石迹,削成建造此龛。[5]
这里显示,冲相寺本名药寺,建于隋开皇八年(588),唐改名冲相寺。《广安州志》卷39又云:“唐初赐额曰‘冲相,自宋齐至唐均隶始安县,宋元均列渠江县。”此处又表明冲相寺在宋齐之时已经建立。而民国《重修冲相寺记》中又载有“(冲相寺)创于晋,称灵山,梁(大)同为药寺”等。笔者赞同翁士洋先生的见解,即“冲相寺确切的建造年代,据传为晋代,有待考,但至少可以确定在隋开皇八年前已经建立”,“隋开皇八年流江郡守袁君等所立的并非是寺院,而是石刻佛像。”[3]冲相寺石窟的始凿年代当在隋开皇八年。
再从现存龛窟的分布区域及造像特征来看,分布在定光岩中段正面岩壁的龛窟是时代最早的,而定光佛龛又处此壁顶部中间,俯临全境,位置尊崇,按顺序也应是此区最先开凿的。故可将开凿于隋开皇年间的定光佛龛,明确置于具体的开皇八年(588)。
此后定光佛龛应当经过后世多次装修,但基本原貌未变。现可明确的有两次,主要集中在明清,一次是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一次是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明代万历题记见于定光佛龛左侧,竖排两行,楷书,内容为:“万历三拾三年□……/始□装功德……”。可见这是一次装修功德活动。清代道光装彩之事见于《装修冲相寺佛像石记》,此则题记位于定光佛龛下方,涉及的相关内容为:“……是岁十月二十七日,吾族好事者装彩定光古佛,父老云集,恭读圣谕,以宣扬天子之雅化……郡庠苏穆如谨记。大清道光戊申冬月朔四日,镌石工许世兴刻。”苏穆如曾在冲相寺设馆两年,对此事比较熟悉,而且装彩定光佛像的也是苏氏之族人。
三 样式类型
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论,可以确定为定光佛的造像多为立像,也有跏趺坐式,有单体圆雕造像、背屏式造像,亦有造像碑,石窟造像中除了圆雕之外,还有浮雕、壁画等形式,质地不一,形式多样。此处仅按组合关系作为标准,将之分为五型。
(一)A型:七佛组合
七佛中的定光佛,即迦叶佛[6]。释迦之前的六佛是指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其中前三佛属于过去庄严劫佛,而后三佛以及释迦佛则属于现在贤劫佛,弥勒佛属于未来星宿劫佛。故在一般的七佛造像中,定光佛造像是存在的,只是无有特殊标识,除非题名之外,无法具体分辨到底是哪一尊。
一般呈并排形式,按坐、立姿态的不同,可分为两式:
1. A型Ⅰ式:跏趺坐式
实例如云冈第10窟后室南壁拱门与明窗间的方形帷幕龛内,七佛均结跏趺坐,中央佛举右手,两侧三佛均施禅定印。
2. A型Ⅱ式:立式
实例如云冈第13窟南壁中层,在窟门与明窗间的三个屋形龛内雕七尊立佛,佛像均为波浪发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
(二)B型:三佛组合
三佛组合造像中,一般会有“儒童布发”{1}的情节作为其标识。按是否处于三佛的核心主尊位置,可以分为两式:
1. B型Ⅰ式:处于三佛中的左侧或右侧
实例有阿富汗肖托拉克石雕三佛造像,年代在公元4~5世纪。三佛均呈立像,中间为现在世释迦牟尼佛,比较高大,左右代表过去世的定光佛与代表未来世的弥勒佛略低。定光佛位于右侧,缺头部,右足前跪一童子,以发布地,表现的正是“儒童布发”故事[7]。
2. B型Ⅱ式:处于三佛的中间主尊位置,着重凸显了定光佛的地位
实例有云冈第18窟,年代在云冈第一期(453~465),正壁主尊为立佛,高15.5米,东西两壁各有一尊立佛,高9.1米,小森阳子先生根据主尊右下方的小像可能是儒童,将其判定为定光佛[8]。
(三)C型:与弟子、菩萨组合
定光佛为龛内主尊,立式造型,左右或胁侍二菩萨,或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与其他诸佛造像的组合形式相似。可以分为两式:
1. C型Ⅰ式:一佛二菩萨组合
实例见于龙门古阳洞北壁西部比丘尼法行造像,为帐形龛,龛内雕像已不存。据大村西崖著《中国美术史·雕塑篇》附第474图看,龛内主尊为立佛,发愿文云:“永平三年(510)四月四日,比丘尼法行□用微心,敬造定光石像一区并二菩萨,愿永离烦惚,无有苦患。愿七世父母,□缘眷属,现在师徒,亦同此福。亦令一切众生,咸同斯庆。”由发愿文可知,造像为定光佛胁侍二菩萨。
2. C型Ⅱ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
实例亦见于龙门古阳洞北壁,位于此壁下部,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是菩萨装的立佛,有发愿文曰:“延昌三年(514)□月十二日,清信女刘四女为亡□造定光像一区。”这尊定光佛特殊之处在于身着菩萨装。
(四)D型:本生或因缘故事组合
主要表现授记及三童子献施。按照表现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三式:
1. D型Ⅰ式:授记本生
跟定光佛相关的授记本生,其实就是孺童本生故事,按照情节表现的复杂程度可以分为两个亚式:
(1)D型Ⅰa亚式:单个场景的单幅表现形式。
一般选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情节来反映故事主题。儒童本生常见的情节主要为儒童散花或者布发,此式主要表现其中的一个场景,属于一图一景式。
仅表现儒童散花情节的图像实例,多见于克孜尔石窟,如第100号窟右甬道外壁、第69窟主室右壁右侧及第163窟的定光佛壁画等[9]。
仅表现儒童布发情节的造像实例,可见于云冈石窟,仅作一立佛,儒童长发披地,佛像蹈足而过,主要在第19-1、11-16、5-10、5-11、13-16、15、34、35、38、39等窟[10]。
(2)D型Ⅰb亚式:一图多景或连续画面形式。
在定光佛立像周围,将儒童买花、散花、布发、腾空的授记故事多场景式或连续性地予以表现,这种具有故事情节的、合并多个片段的画面构图,被称之为合并叙述[9]。此式造像,在犍陀罗地区主要采用浮雕形式,时代多在公元2~3世纪,画面中孺童从买花、散花、布发到受记腾空,出现了四次,定光佛则以高大的形象占据画面中心位置,如拉合尔博物馆所藏出土于西克利的犍陀罗浮雕、现藏大英博物馆的浮雕儒童本生像。亦有简化形式,如省略买花或腾空的儒童形象,亦有略去卖花人的,如中亚迪尔发现的犍陀罗立佛(日本私人收藏),头光上浮雕七宝莲花,足侧有童子作五体投地状,主要表现散花与布发掩泥两个场景,其中散花则用头光中的莲花表示,并未出现儒童形象。
另一处典型的实例在云冈石窟,出现了大量表现儒童本生故事的造像,亦多为浮雕形式,主要在云冈中期和晚期,尤以晚期最盛,據统计约有17幅[11],其中构图最详的是第10窟前室东壁的儒童布发画面(图4)。
2. D型Ⅱ式:三童子献施因缘
此式造像常表现为立佛,左手或右手持钵低垂,下有三童子相攀肩而蹬,其中一童子双手捧物欲投入佛钵中,称作“定光佛并三童子”题材{1}。
此式实例多见于云冈石窟,云冈早期如第18窟南壁既已出现,至云冈晚期数量骤增,如第19-1、5-11、5-38、5-39、25、29、33、34、35、38、39等窟均有此类造像[10]106。另外,河北邯郸峰峰矿区鼓山响堂山石窟水浴寺西窟也发现有北齐时期的此式造像[12]。
3. D型Ⅲ式:授记、三童子同时组合表现
将儒童本生与三童子献施两种题材放在一起表现。例如河南浚县浮丘山北齐四面造像石的北面中龛(图5),在立佛和三童子的外侧,还雕有一尊手持莲花的男像和两尊女像。手持莲花者即为儒童,其旁女像为卖花给儒童的王家女瞿夷及侍女。据经典所载,这个王家女瞿夷也同时得到了授记。这是以献花表现授记本生的故事,也有采用布发情节的,如河清三年(564)梁罢村碑,立佛右下作童子献施,左下则为布发掩泥,共用一尊定光佛立像,表现两个故事情节,且呈左右对称布局。
(五)E型:单尊形式
定光佛为立式,独尊,大体可分为两式:
1.E型Ⅰ式:并不出现儒童的人物形象,仅以莲花等物来象征或者暗示故事情节,并成为辨别定光佛身份的特殊标识。莲花在此表示儒童散花。
实例1:单体圆雕立像,出土于犍陀罗的西克利,现由欧洲收藏家收藏。此像为圆形头光,波浪纹发髻,身着通肩装佛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抓衣角,赤足立于方台座上,与当地出土的其他诸佛造型无异。所异者在于,头光中浮雕六茎莲花,底座正面饰三朵莲花。
实例2:单体圆雕立像,出土于犍陀罗的塔波拉,现收藏于东京Matsuoka艺术博物馆。此像圆形头光内浮雕两茎莲花。
2.E型Ⅱ式:单尊立像形式,并无其他暗示或象征物,仅靠造像题记方可判定身份。
冲相寺定光佛造像即属于此式(图6),龛内除了定光佛立像,并无儒童、童子之类人物,亦不见莲花之类象征物。但造像本身已存在能揭示其定光佛属性之潜在标识,这就是双手所施的特殊手印。这种手印虽然在常见的定光佛像甚至其他佛像都很难见到,但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正代表了定光佛的本身标识。手印问题下文将予专论,此处不赘。
综合上述分类定型可以看出,代表过去佛的定光佛像,起初一般出现在七佛、三佛组合中,地位并不突出,也存在与其他诸佛一般无异的造型和组合,根本不含有自身的任何特色。随着佛教的发展及传播地域的变化,定光佛逐渐在造像中得到重视,授记本生尤其得到强调,造像中热衷于刻画此类故事情节,着重表达“求得授记”的成佛思想。这一现象在北朝比较盛行,晚期尤甚。广安冲相寺定光佛像所开凿的年代(开皇八年)虽已进入隋代,但南北仍旧没有进入真正统一,事实上还属于北朝晚期,定光佛造像的出现便是受此风所染的结果。不过,冲相寺的定光佛像与北方相比,其实已是这类造像的简化形式,其源可追溯至犍陀罗地区的作法,只是简化得更加彻底,连外在的象征物诸如儒童、莲花等统统省略掉,只专注于定光佛本尊,且以之作为一龛主尊,甚至将其安排在当时定光岩整个造像区的最高位置,不可不谓对定光佛的尊崇已经远超前代。而在造型设计上却设置了独特的手印,不借助外物只靠造像本体来突出定光佛的特质,这是此前所未见的。
四 太阳纹头光
背光是佛教造像背后的光圈式装饰图案,一般处于佛教诸尊像的头部或身后,包括头光和身光,这是佛“三十二相”中“眉间白毫”和“长光一丈相”的表现,属于佛本体的一部分[13]。背光表现的是佛的神圣伟大,象征光明和智慧,代表着佛的炽盛,表示的是普照一切无所障碍的超常的光,同时又可以起到装点佛身的效果,能反映出各时代造像样式和造像者的审美观[14]。冲相寺定光佛的身后亦表现有背光,为外桃形内圆形{1}双层头光,圆光中雕刻放射状的锯齿纹一圈,桃形头光上部及身光为彩绘而成。这里要讨论的是圆光中雕刻的一圈锯齿纹,又被称作太阳纹{2}。下面试对这种特殊头光纹饰的形制类型、流布及寓意等,略作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这种装饰纹样在冲相寺石窟中的表现情况。据初步统计,58个龛中发现有锯齿纹头光的有K1、K23、K26、K43、K45、K47、K50共7个龛,单体实例有13个,其中用于主尊佛像的4例、弟子5例、金刚力士4例。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一)A型:尖桃形头光
圆形头光之外表现尖桃形外层头光,主要见于主尊佛像。其中按桃形光中是否有纹饰再分为两式:
1.A型Ⅰ式:尖桃形光比较小,内素面不见纹饰,此式仅1例,即K26定光佛。
2.A型Ⅱ式:桃形外层头光比较大,内镂雕不同的纹饰,或如意卷云纹,或缠枝忍冬纹,前者纹饰如K45主尊,后者纹饰则有K47、K50主尊。
(二)B型:圆形头光
不表现桃形外层头光,仅为圆形头光,主要见于弟子、力士造像。按是否雕有装饰纹带,亦可分为两式:
1.B型Ⅰ式:没有装饰纹带,主要有K1右侧弟子、K43左右二力士、K45左右二力士、K47左侧弟子。
2.B型Ⅱ式:圆形头光外再雕一圈装饰带。主要有K23左右二弟子、K50左侧弟子,凸棱圈间隔的光圈带中浮雕菱形、椭圆形等几何纹,相间排列,菱形中有凸起的小橢圆状物,形似眼目。
由以上分析可见,这种头光纹饰可以用作主尊佛像,也可用作胁侍弟子或护法力士,似乎并无神格方面的限制,但在表现形式表现出佛教世界的等级观念,其中A型与B型之间的区别,就是为了强调这种等级差异。同时A型Ⅰ式与A型Ⅱ式的区别,主要是时代特点表现出来的差异,也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出K26的开凿时代要早于K45、K47和K50。同时,K1、K23、K43、K45、K47、K50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类似性,反映了它们时代相近,尤其是K43与K50在龛窟形制、规模大小、造像题材与组合等所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相似性{1},更印证了这一点。经分析排比,这7龛的年代有隋、盛唐,亦有中唐,盛唐最多,可明确这种头光纹饰在冲相寺石窟的流行时间范围,当在隋至中唐。
至于太阳纹这种头光的源流、寓意问题,限于篇幅,仅作略述。经初步考察,这种头光纹饰首先产生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实例是阿富汗Paitāva出土的舍卫城双神变的佛传浮雕,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15],时代在公元2—3世纪,立佛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垂握衣角,大圆形头光内的边缘饰有一圈锯齿纹,齿纹较小,排列细密,形如连续的小正三角形,这当属于早期形态。此佛肩膀表现升腾的火焰,而在另一件阿富汗绍托拉克出土的相似造型的造像上,身光边缘所饰即为火焰纹,所以Paitāva造像头光中的锯齿纹其实表示的也是火焰,只是为了与佛肩写实的火焰相区别而设计成这样,其用意相同,都是表现光明的。
太阳纹头光在犍陀罗地区出现以后,又受到希腊太阳神造型因素的影响,出于对太阳的崇拜,这种头光纹饰开始发生变化,齿纹更加尖长犀利,变得更加形似太阳光芒{2}。如现藏东京的释迦牟尼佛铜坐像[16],制作于公元3世纪,为跏趺坐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圆形的头光不大,边缘处被制作成放射形的锯齿状一圈,形如佛头后照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在这里,锯齿已经成为头光造型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属装饰,这应属于发展型。此外,犍陀罗作品中还有一件巴雅说法佛石坐像[17],坐姿、手印与上述一件造像相同,圆形头光内的边缘部分浮雕一圈太阳纹,三角形齿纹中有个别造型变得腰部有些圆凸。时代较晚的作品,如印度北方邦班达县出土的佛陀铜立像,属于笈多时代,约在公元400年前后,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头光显得很大,边缘制作成一圈锯齿状,稍异的是光线末端呈现小圆球形[18]。这两件实例可看作变异型。
太阳纹头光随着佛教而东传,先至新疆地区,发现的实例并不多,但这种东西承接的桥梁作用却不容忽视。再往东,这种纹饰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已是公元6世纪初期,按徐玉琼对莫高窟北朝佛像背光装饰纹样演变过程的划分,属于第三阶段(525年之前至545年),表现较多的则在第四阶段(多属北周时期,545—585),并认为这种锯齿式火焰纹应是来源于古印度、西域地区,具体来说应是“对迦毕试佛教造像背光中锯齿纹变异后融合产生的新纹样”[19]。河西其他石窟目前还未见到太阳纹头光。中原北方地区,在石窟造像的盛地如山西云冈、洛阳龙门亦基本未见。长安造像圈中目前也没有发现较多实例。
唯独比较流行的地区在四川,除了广安,如广元、巴中、安岳、夹江等地均有发现,尤以巴中地区最为多见。具体来说,广元地区最著名的两处石窟中,皇泽寺未见,千佛崖仅有1例;巴中地区主要分布在北龛和西龛,南龛1例,北龛7例,西龛9例,水宁寺1例,涉及10个龛,共18例;安岳卧佛院1例,夹江千佛岩2例{1}。这些实例,不出上文对冲相寺石窟太阳纹头光所作的类型分析范围。在施用的尊神身份上,增加了地藏与菩萨;佛中可以判定具体身份的有菩提瑞像、释迦、阿弥陀佛、定光佛等;时代范围大约从隋至晚唐,其中盛唐最多,达到12龛,其次为隋代和初唐,中唐、晚唐则最少。与犍陀罗及西域、河西等地相比较,以巴中及广安冲相寺为代表的四川石窟中的太阳纹头光表现出了极强的地域特色:一是以石窟造像为主要表现形式,采用镂刻技法的占多数;二是放射状的锯齿造型更多地继承了犍陀罗地区的发展型,齿纹更长更尖,外围以闭合的圆形继承中又有创新;三是尖桃形外头光的引入,以及装饰纹带的多样化,不仅可以强调等级观念,而且还可以增添时代气息。
由于成都本地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中不见此种形式的头光,故推断冲相寺太阳纹头光的来源需要考虑北方因素。一般而言,四川石窟以川北的广元和巴中为首传之地,再由北向南波及其他地区。在太阳纹头光方面,冲相寺石窟与巴中石窟表现出比较多的“亲缘”关系,不仅形制相近,而且多伴有天龙八部等像,尤其是在时代上能产生一种早晚关系,在类型上巴中更为全面,似存在近似“母子”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初步推测此种太阳纹头光的传播线路,应是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起源,传至西域地区,再到敦煌等河西走廊,然后经由天水、汉中南下,过米仓道而至巴中,最后沿南江、巴河、渠江传至广安冲相寺。至于安岳、夹江两地的太阳纹头光,可能又是另外一条传播线路。
五 着衣方式
冲相寺定光佛像的着衣方式亦具特色。此前有研究者将之确定为“身着U形罗纹袈裟”[1]或者为“菩萨装”,认为“(定光佛像)服饰为三层,内为僧衹衣,中间为无袖无开缝裙披,外为通肩风披”。[2]杨洋在硕士论文中描述道:“定光佛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周饰U形衣纹,中间三角形衣角(上饰万字纹)垂至膝下,下露百褶长裙,内衣大袖口直悬腕下呈三角形。”[4]16以上所述均有不同程度的偏差,为此将我们观察的结果陈述于下。
依佛本制,缠缚于佛及僧众身上的法衣常有三种,称为三衣,各有不同的名称,为求简单方便,按照陈悦新引《十诵律》的作法,简化僧伽梨为上衣,郁多罗僧为中衣,安陀会为下衣[20],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外衣、中衣和内衣。从领口与袖口(图7、8)进行仔细观察后发现,定光佛上身著有三层佛衣,内为双领下垂式的内衣,比较轻薄贴体,为窄筒袖;中衣和外衣均较厚重,都为一块长方形的棉布,并无衣领和衣袖。中衣横披,中间部位从后颈覆下至胸,左右两侧覆双肩及双臂,两摆从手臂等距离垂下;外衣从右肩披垂至胸,再横向左侧搭垂于左肘部,外衣覆盖了整个右肩和右臂,绕搭左肘又覆盖了左前臂,胸以下垂成三角状衣襟。外衣四个角,一个垂于双膝间,上饰有“万”字纹,另一个角垂于左手下,另外两角垂于体后两侧。腰下系裙,这点是没有疑问的。这种着装方式比较特殊,目前笔者仍未找到与之相同的实例。不过根据内衣与中衣双领下垂、外衣袒左搭肘的特征,可以命名为双领下垂外衣搭肘式。
六 手印含义
冲相寺定光佛像特殊的手印,长期以来学界未作出合理的解读。常见定光佛像的手印一般为无畏印,或抓握衣角,或向下伸手托钵,极少见到这种双手斜伸、一掌朝上、一掌朝下的手印(图9、10)。杨洋曾解释说:“这种一手托天、一手覆地的手印,”显示的是“定光佛佛法的无际无边和天地间唯我独尊的显赫地位,反射出冲相寺地区对定光佛无比的推崇和浓厚的信仰”。这种说法没错,是从佛像表面动作和气势上来认识的,但放在其他佛像身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流于宽泛,而不中的。刘敏先生指出:“这种手印除此佛外尚无前者,亦无后例。其创作构思是否与儒童接受定光佛授记有关,亦待进一步进行考证。”这为我们解读这种特殊手印指明了方向。定光佛之所以为定光佛,就是有着不同于他佛的特质,这种特质正是开凿者们需要着力挖掘和表现的。所以解读其手印,亦当从定光佛本身的特性去入手。
不妨先提出我们的观点:定光佛双臂自然斜伸,手指并伸,右手掌心朝下,表示为释迦前世儒童进行授记,可暂称作授记印;左手掌心朝上,表示接受三童子献施,当是定光佛与三童子缘。
从前文论述可知,定光佛造像中一般最常表现的就是授记本生、三童子献施,以至于儒童、三童子、莲花等可以作为辨别定光佛身份的标识。但冲相寺定光佛龛像中并无这些形象,我们说它是一尊简化的定光佛造型,但并不代表它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这些内容由显性变为了隐性,由直观的表现变成了暗示性的象征。
关于授记,造像体系中似并无明确规定的手印。但是佛教经典中载明,授记之时有摩顶的动作,而摩顶正是佛手下伸,掌心朝下的。《法华经·嘱累品》云:“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嘱汝等:汝等应当一心流布此法,广令增益。。”《地藏菩萨本愿经》云:“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授记。”《楞严经》云:“(普贤菩萨)白佛言:‘若于他方恒沙界处,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深,未得见我。我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于十方摩顶授记。自果未成,亦于十方蒙佛授记。”可见,摩顶是为付嘱大法,或为预示当来作佛之授记的常用动作。摩顶在石窟造像中的直观图像,我们可从云冈罗睺罗因缘、雕鹫怖阿难入定缘中看到,如云冈第9窟前室西壁、第19窟南壁、第38窟东壁所表现的释迦佛摩顶罗睺罗的场景[10]108-110,第38窟南壁则表现有释迦佛摩顶坐禅阿难的场景[10]125-126(图11)。按此,冲相寺定光佛右手可以理解为授记印,那么定光佛所授記的无疑便是释迦前世儒童了。
冲相寺定光佛的左手掌心朝上,呈托物之状,与云冈第12窟前室东壁的定光佛立像(图12)的左手动作类似,唯一不同处是仅仅缺少一只钵。按照定光佛立像左右两个题材的对称布局原则,既然右手授记用以表现儒童本生,那么左手便应表现童子献施,因此佛像左手掌心朝上动作的含义正是托钵接受献施。这两种不同手印在定光佛造像上的结合,是因为植善根与授记均是成佛的基本前提条件,表达的主题无非就是期望将来成佛而已。
总之,这种掌心朝下的手印表示的应当是定光佛为儒童摩顶授记,而手掌心朝上,表示接受三童子敬施,此处表达这两个特定故事的方式不是形象化的雕刻特定人物或器物、莲花等,而是设计采用了两个独特的手印,更多地带有暗示性或象征性。省略掉以往造像中常出现的受记的儒童和佛手中所托的钵,三童子的造型等也一并略去,体现出的是定光佛晚期造像的简化特色,带有浓厚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时代较晚,地域靠南)。
七 定光佛信仰
定光佛属于过去佛,因授记释迦牟尼将来转生为佛而著名。由于现世释迦牟尼已涅槃,而过去佛、未来佛又很遥远,于是在功利性很强的民间信仰中,便将过去、未来佛统统引入到现世中来。一如五代布袋和尚契此被作为弥勒的化身一样,定光佛也出现了转世化身,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闽西的定光和尚。这种后期的定光佛更多地属于民间信仰,是中国化的产物,与圣僧信仰有关。有研究者将早期的定光佛信仰称为正统信仰,即尊崇印度佛教原始之佛菩萨信仰,而把后期的定光佛信仰划属民间信仰,即尊崇中国佛教民间产生之佛菩萨信仰[3]。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研究冲相寺定光佛造像体现出来的定光佛信仰,必须要与后期的民间俗神信仰区别开来。
按理说,定光佛是过去佛,早在久远劫前已经离开娑婆世界,因此信徒更多的是信仰现在佛和未来佛,对待过去佛可能只是像对一般佛菩萨那样表达单纯的恭敬和祈祷,在信仰层面的地位远远不如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但如冲相寺石窟对定光佛的尊崇,却是前所未有的,那他们又是出于何种缘由来信仰定光佛的呢?其实,对定光佛的崇拜源于其授记的本生故事,因为真正让功德主们关注和追逐的主旨应该是定光佛授记成佛的最终结果,而非定光佛本身。云冈第5—11窟中的儒童本生雕刻中,将原来佛经中记载的少年修行者儒童(释迦前世),竟表现成了身着俗装的邑人信众形象[10]19-20。功德主将定光佛所授记的儒童换成了自己的形象,所表达的希冀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迫切求得授记的祈愿。
从文献看,求得授记成佛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十分流行。如北齐文宣帝对著名高僧法上“事之如佛”,“乃下诏为戒师,文宣帝常布发于地,令(法)上践焉”[21]。效法儒童布发,希望求得授记成佛的还有高昌王。高僧释慧乘于大业六年(610)“奉敕为高昌王麹氏讲金光明,吐言清奇,闻者叹咽,麹布发于地,屈乘践焉”[21]939。可见北朝至隋时期,这种求得授记成佛的信仰需求很兴盛。冲相寺定光佛造像当是在这种信仰需求下所产生,更由此将原本是药寺(可能供奉药师佛为主)的冲相寺改为了定光佛的专门性道场。
结 语
定光佛龛是冲相寺石窟开凿年代最早的一龛,应开凿于隋开皇八年。其类型属于定光佛造像的简化样式,不仅省略了为之授记的儒童,而且不见象征性的莲花,在三童子献施的表现中亦将三童子略去,同时也省掉了手中所托的钵。抛开了外在的人物与法器、供具,那么如何表现定光佛的特质?为解决这个问题,工匠设计出了掌心向下呈摩顶状的授记印和接受献施的手心朝上的受施印,体现了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以独特的手印来暗示这两个本生和因缘故事,是冲相寺定光佛像的与众不同之处。同时,定光佛像的太阳纹头光、双领下垂外衣搭肘式着衣方式也是其独特之处。单以太阳纹头光来考察,可知此种图案应是起自古印度犍陀罗地区,东传西域和河西走廊,向南经米仓道至巴中,由巴中再传至广安冲相寺。在太阳纹头光与巴中地区有较多相似性,暗示出冲相寺与巴中地区具有更深的亲缘关系。同时在所有可以确认的定光佛石窟造像中,冲相寺的定光佛像年代偏晚,且分布地域最靠南,这也是其表现出来的特色之一。另外,以定光佛为全区最受崇敬的对象,建成为专门的定光佛道场,这也是少见的。定光佛像所体现的信仰也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的。总之,冲相寺定光佛龛像是研究早期定光佛信仰的绝好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敏.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及石刻调查纪要[J].四川文物,1997(3).
[2]刘敏.广安冲相寺锭光佛石刻造像考略——兼论锭光佛造像的有关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3(4).
[3]翁士洋.广安冲相寺与定光古佛信仰[J].空林佛教,2013(6).
[4]杨洋.四川广安冲相寺石窟研究[D].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2004:32.
[6]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一)[J].敦煌研究,1992(4).
[7]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C].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27-228.
[8][日]小森阳子.昙曜五窟新考——试论第18窟本尊为定光佛[C].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24-338.
[9]耿剑.“定光佛授记”与定光佛——犍陀罗与克孜尔定光佛造像的比较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3(2).
[10]赵昆雨.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104.
[11]赵昆雨.云冈的儒童本生及阿输迦施土信仰模式[J].佛教文化,2004(5).
[12]刘东光.响堂山石窟造像题材[J].文物春秋,1997(2).
[13]封钰,韦妹华.佛教雕塑背光图像的象征意义[J].东南文化,2010(2).
[14]顾虹,卢秀文.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4(4).
[15][韩]李姃恩.北朝装饰纹样——五六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246.
[16]赵玲.印度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67.
[17]李静杰.中国金铜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244.
[18][美]罗伊·C·克雷文,著.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印度艺术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8-79.
[19]徐玉琼.莫高窟北朝佛像背光装饰纹样特征及其演变[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20]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6.
[21]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第八·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傳[M].北京:中华书局,2014: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