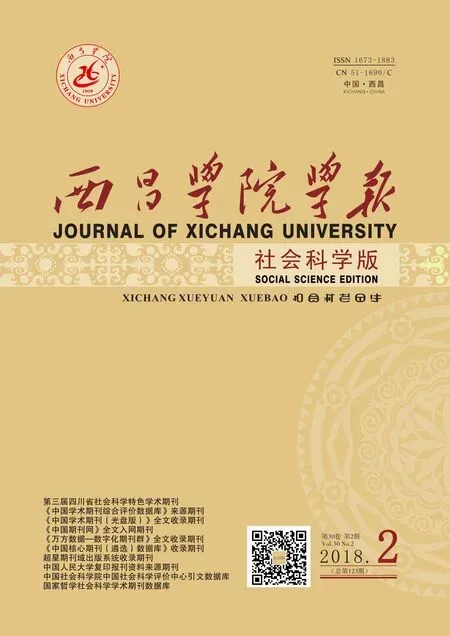安宁河流域早期铜业开发研究
王 瑰
(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云南 曲靖 655011)
童恩正先生曾指出,在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大陆,从东北到西南,有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条传播带上,由纬度高地形低、纬度低地形高而形成的自然条件互偿特征,使得这里的“太阳辐射、气温、降水、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均具有相当的一致性”,[1]这是其能成为横跨数千公里同质文化传播带的基本原因。但是由这种原因导致的文明传播,就性质而言应是一种人类自发迁徙的客观结果。只有在青铜时代,通过铜矿采冶的高度社会组织和整合,人类才能获得自觉迁徙的基本力量,这也是早期国家往往与青铜时代伴生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条“半月形文化带”的东北端辽西,恰是我国北方重要铜金属成矿集中区,考古发现有大量3 000年前左右的铜矿采掘和冶炼遗址[2];其西南端则处于我国川滇铜矿带上,该区域发现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南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其铜器经检测系本地铸造,距今3200~3800年[3];在其中部地带则还有中国西北铜矿资源分布最多的白银铜矿区。而这条文化传播带,还存在“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相同的文化因素更加显著”的特征[1]。这些反映的,便是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形成,与古先民的铜矿资源需求及寻觅间应当存在一种难以绕开的关系。
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东南端即是今川西南地区,该地有三百余公里的安宁河,自东北向西南流过,汇入雅砻江,再入金沙江。安宁河,汉代称孙水,清代称安宁河,中游开始两岸为宽谷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为四川省第二大平原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大农耕区,舒适宜居闻于西南。安宁河流域不仅农业资源丰富,铜矿资源同样丰富,其早期铜业开发,对经过其地的西南丝绸之路古“蜀身毒”道的畅通、对汉代的西南边疆开发,以及对西南丝绸之路南北线的连接都具有重要作用。这对“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形成中的铜资源动力是一个辅证,对探索铜业开发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新的启发。
一、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与西南丝绸之路北线的畅通
司马迁说“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4]3254确实,铜铁资源,天下所在皆有,但储量丰富的地区,却很少见,司马迁在其《货殖列传》中,明言的多铜之地,只有两处,一为“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的巴蜀,[4]3261二为“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的吴地。[4]3267巴蜀皆有铜,而饶在蜀之严道。严道铜山,汉文帝赐予邓通铸钱,以致“‘邓氏钱’布天下”。[4]3192文帝之时,严道铜山有如此之富,必定有前期采掘冶炼的基础。
《华阳国志》载秦灭蜀后,秦人、东方六国移民带着先进生产方式进入蜀地,“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5]148“家有盐铜”而非“家有盐铁”,可见铜而非铁才是秦并蜀后获取的最大宗矿产资源。严道,治今雅安荥经,在成都平原西外,其铜矿开采从先秦至民国不绝,而其附近地区则还发现大量战国秦墓[6]。可见,蜀地的“盐铜之利”并非虚言。一般认为三星堆、金沙遗址时期,就已大量采用严道铜矿。而严道也恰恰处在西南丝绸之路北线之上,是成都平原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冲要之处。
当然,严道属于大渡河流域,不属于安宁河流域。但是,若是严道铜山在当时技术条件难以大规模开采以满足国家和市场需求时,势必要另寻矿苗。实际上到西汉中后期,严道铜山的产量就不足称道了,所以后汉初班固作《汉书·地理志》蜀地腹心未载有产铜之地。而寻觅新铜苗的方向,就是安宁河流域。沿着严道南下,翻越天险小相岭,即进入安宁河流域的源头地区,又开始进入一个铜矿富集区。《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邛都县南山出铜,[7]1600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亦载之。邛都县处安宁河流域腹地,大致为今西昌市,其南山之铜,今也有汉代考古的印证,就是著名的西昌东坪冶铜遗址。能被《汉书》记载的产铜之地,其规模应该说都是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遍查《汉书·地理志》能有此待遇的,不过丹阳、越嶲、益州三郡而已。当然,安宁河流域的铜矿,绝不是汉人进入后才开始采炼的,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最晚战国时期流域西北盐源盆地的汉定筰县地,已能大量铸造反映本地习俗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风格上虽然兼具滇西北、滇中、蒙古、巴蜀等地的风格[8],但从铸造技术来看,“大多为本地铸造”,学界认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筰都夷的遗存。不过,邛都夷腹地的安宁河谷,迄今还很少发现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但是这不能说明邛都夷的发展更落后。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诸夷的叙述来看,司马迁是分为两个圈层来介绍的。居于内部圈层的在金沙江以南是夜郎、滇、靡莫等国,金沙江以北是邛都等国,他们都“椎结、耕田,有邑聚”,是文明程度较高者,外部圈层在金沙江南和西,是巂、昆明等部落,“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4]2991金沙江东、北则是徙、筰都等国,筰之东北则是冄駹等国,“其俗或土著,或移徙”,[4]2991文明程度又次之。筰都夷恰在邛都夷外层,邛都夷以农耕为生。不过,从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来看,筰都夷所在的盐源盆地种类、数量、级别,都要多于和高于邛都夷所在的安宁河流域的青铜器。但是这不能说明,邛都夷的文明程度要低于筰都夷,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邛都夷处地平坦宜耕,汉人进入后,集中居于河谷之中,或将其遗存大量破坏,或大量销镕其旧青铜器皿以为新用之故,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毕竟安宁河谷若没有相对足够发达的铜器文明,是很难与近在咫尺的筰都夷长期对峙的。
东汉,又在毗邻安宁河流域北段偏东的零关道(治今凉山州越西县)发现有较大铜山,即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所载越巂郡零关道铜山[9]。当然,既然是司马彪所载,那么这座铜山至少繁盛到了西晋。
安宁河流域的这两大铜山,向东北与严道铜山相连,这就成了一条通往成都的大道。而实际上,这两座铜山,都还只是安宁河流域上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铜山,沿途其实还有很多产铜之地,如今安宁河流域北部的冕宁县、安宁河流域西南部的盐源县、会理县、米易等县,都有大量铜矿资源分布,清代时期也都大量开采。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现,从成都平原往西,经严道,沿安宁河流域南行,直至金沙江,这条道路全程与铜矿资源的分布相伴随,且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安宁河流域腹地还分布有国家级的大铜矿。而这条道路恰恰是西南丝绸之路北线古“蜀身毒”道(又称“零关道”)在今四川境内的线路。而沿古“蜀身毒”道跨过金沙江进入今云南地区,经大理、保山等地出境的线路,即今所谓西南丝绸之路“永昌道”,其南北仍是铜矿资源的分布地带,剑川海门口遗址就在这一线,《华阳国志·南中志》明载永昌郡地方“出铜、锡”,[5]285清代的滇西铜厂群也在这个地区,可见古“蜀身毒”道的全线都伴随着铜矿资源分布,是一条金色的文明交流通道。
铜矿采冶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须要动员和组织起庞大的人力,这个动员和组织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进入早期国家的基础准备。这是我国青铜时代与早期国家产生同步的历史所正面证明的,也是后世帝王禁矿所侧面证明的,因为矿场对矿工的高度组织实际上也就为他们可能的起事反叛进行了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这样的准备就是准早期国家的状态了。铜矿采冶聚集人口的规模,根据清代的文献,是能有一个具体参照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提督康泰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10]一碗水厂在会理州北部(属安宁河流域),同治《会理州志》载曰:“康熙五十二年开采,历未报税”;[11]云南铜厂方面,光绪时督办云南矿务大臣唐炯奏称“从前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12]可见,一个小铜厂聚集万余人是完全可信的。从先秦至清,中国的铜矿采冶技术并没有明显进步,安宁河早期铜矿采冶聚集的人口至少与此相当。由此,沿线皆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安宁河流域,通过铜矿采冶组织起来的人口,就不难想象了。而这些高度组织的铜矿采冶的人口,实际上就形成了安宁河沿线的相当程度的文明基础。文明的资源是综合性的,丝路两端的商民由此往来,自然就有了稳固的综合保障。直接联系南亚与蜀地的古“蜀—身毒”道早在汉开西南夷之前就已存在,且沿安宁河流域北上,通往成都平原,安宁河流域早期铜业开发自有一份不小的功劳。
二、安宁河流域铜业扩张与西南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
西南丝绸之路的南线,一般依《史记》称为“五尺道”,安宁河流域的早期铜业开发,很可能是将西南丝绸之路“零关道”与“五尺道”在金沙江中游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
《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住狼县。”[5]210住狼,廖本注,住当作堂,狼当作琅,以为即《南中志》之堂琅县。会无,大致即今凉山州会理、会东地,在安宁河流域东南外。因此,这条记载云南学者多认为是由蜀入滇之另一大道,也以此为其开通之下限。窃以为这条道路是确实存在的,其作为官方道路开通至晚应在汉武帝元鼎六年(111BC)。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军定邛、筰事云:“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駹皆震恐,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冄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4]2997从文本的叙述来看,汉军先诛且兰,再诛邛君,随即杀筰侯。且兰,《华阳国志·南中志·且兰县》“汉曰故且兰”,[5]260《汉书·地理志》“故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7]1602沅水,即今湖南沅江,则且兰之国正在今黔东湘西一带,南与南越国相接。《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载:“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4]2996从此段叙述来看,汉军先破且兰,而后兵向南越,南越已破的消息传来,便回师灭头兰,头兰又灭,夜郎王遂降。《索隐》云“头兰即且兰”,[4]2997其所据当为《汉书·西南夷传》。但若此,汉军则两次攻且兰,颇不可解。且《史记》该段叙述,且兰、头兰分得很清,还特别说明头兰是“常隔滇道者”,因此,头兰当如任乃强先生所说,在今滇东北一带,为夜郎藩屏之国,如此也才称得上“还诛”。[5]279-280而汉军还军之后,其进军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头兰,而是邛筰,所以才会说“行诛头兰”,即在进军途中顺道灭了头兰。若此,汉军灭邛、筰的进军线路,应是从今贵州腹地经今黔西北、滇东北,过金沙江而入邛都夷境。邛都夷在内,筰都夷之外,灭邛则筰直接暴露于汉军兵锋之下,所以才“并杀筰侯。”而由滇东北入邛都,汉军所经道路,当是自堂琅县(治今昭通市巧家县)进入金沙江河谷。
对此,从地理形势和文献上可以找到两条理由:其一,汉军灭头兰后,由堂琅县入邛都夷是最可行而便捷的道路。昭鲁盆地北部外沿金沙江一带皆连绵之崇山峻岭,北上交通极度艰难,至今欲从昭通深入到安宁河流域最捷之路也在巧家过金沙江。其二,汉军还需要以兵威将滇东北扫荡一遍。元封二年(109BC)汉廷分犍为南部置属国都尉,统四县,汉阳、南广、朱提、堂琅。这四县是武帝建元六年(135BC)初开南夷设犍为郡时所置,为犍为极西南之县,其中朱提县以今昭鲁盆地为腹心,堂琅县则在今昭通市巧家县、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一带。但是,犍为南夷诸县,并非兵威所定,而是唐蒙重币贿赂夜郎侯,使之纳土为郡县后,“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才开置的。[4]3840唐蒙开道数年,巴蜀民疲惫不堪,南夷又数次反叛,难以实际统治,汉廷为集中财力、兵力征伐匈奴,“遂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4]3840南夷诸部实际上已经不再奉汉廷政令。因此,此时汉军诛头兰,必定要向其已设诸县,炫耀兵威,南夷最西之堂琅县,也当行军耀威。而堂琅恰处渡江捷道之上,可收两便之功。
另外,从考古发现来看,从堂琅渡金沙江,入昭鲁盆地,应是早就存在的另一条沟通金沙江南北的道路所在。川西南安宁河流域与滇东北昭鲁盆地,同处“半月形文明传播带”上,安宁河谷北部冕宁县新石器时代高坡遗址发掘出的瓮形器、碗、钵、器流等器物的某些类型就与昭鲁盆地野石山、盆地边缘马厂遗址的相关器物非常接近,但是在安宁河流域的其他地方却很少发现,惟西昌市西南经久乡大洋堆遗址的中段发现过相似的瓮形器。冕宁—西昌—昭通的连线,勾勒了一条安宁河与昭鲁盆地的文明交流古道。
而从商代晚期断续式地绵延到东汉时期的,在安宁河流域广泛存在的大石墓文化,也有跳出安宁河谷,从会理县城河流域进入金沙江的现象。2005年会理县南阁乡雷家山坡上发现了一片古墓地,其出土物中的“圈足杯、平底单耳罐、叶脉纹纺轮等具有明显的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文化因素,而单耳罐、尊形器、圈足罐、双鋬手罐等则具有金沙江流域石棺葬文化因素”,[13]可见,安宁河流域通过城河进入金沙江。而城河流域恰恰也是会理青铜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带,上游的会理盆地,下游黎溪、河口、普隆、新安一带都有发现[14]。而城河流域青铜文化特征,同时受到滇西、滇池、横断山石棺葬,以及蜀文化的影响。显然这片地区是一个东西南北的交通中心,任乃强先生认为的由此过金沙江,南下昆明的魏晋时期川滇捷径,很可能是古已有之的先民交流、迁徙道路。
不过,还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考古揭示来看,城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所受蜀文化影响要远远高于盐源盆地的青铜文化。除了不少陶器的相似外,其非墓葬出土的成熟青铜器中,就发现有典型的蜀式器物——“烟荷包”状钺,[14]而盐源盆地青铜器身上蜀文化的影子不过是锻造技术的相似,并没有典型蜀式青铜器的出现。盐源盆地在安宁河谷北,城河流域尤其是青铜器出土最多的下游,则在金沙江北岸,因此,很可能两地的蜀文化是从不同的道路传播而来的。无独有偶,滇东北昭鲁盆地以营盘墓地乙区为代表的成熟青铜器遗存(与其西边的黔西北威宁中水青铜时代遗址第一期文化内涵和时代都一致),“主要为巴蜀文化的东西”。[15]两相观照,不得不令人产生蜀文化进入昭鲁盆地后,又西下金沙江,再逆江西上的印象。毕竟当时昭鲁坝子与滇池间最近的大道,即由今昭通市鲁甸区翻越古堂琅山进入曲靖市会泽县的道路还难以逾越,或由五尺道由东而绕,或由此西下金沙江直入滇中滇西反为捷径。
同时,昭通市巧家县1991年发现的小东门石棺葬,也表明金沙江石棺葬文化很可能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已经沿江而下到达这里[16],但再没有东进。这至少能说明,巧家是金沙江沿岸古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巧家对岸的四川会东县与宁南县之间,有一条金沙江支流黑水河,沿河谷北上,恰能到达安宁河流域的腹地——今西昌平原,这条道路在今则是西昌到巧家的大道所在。
城河流域青铜文化富集,有个绕不开的因素,就是城河下游的黎溪盆及金沙江东下北岸一带,都是铜矿富集区。而巧家,其县城金沙江对岸今属凉山州会东县地界,也是铜矿富集地,清代在此有著名的大风岭铜厂。金沙江南岸今会泽、东川、巧家交界一带(皆属汉堂琅县)则是川滇铜矿带上铜矿最富集之地,2013年东川区铜都街道营盘村玉碑地也发现了炼铜聚落遗址,考古学家推断其时代为战国以前。这个遗址的典型陶器为底部有叶脉纹的带耳陶器,所展现的特征,并不同于滇池地区,考古工作者认为可能是小江流域的独特文化[17]。但带耳陶器(源自西北文化的典型器物),及其底部叶脉纹的特征,在安宁河流域的考古文化中却也很常见,如在西昌棲木沟遗址、会理县东咀遗址、德昌县汪家坪遗址等都是常见器物。而传统认为这些器物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一般是在汉代中期以后。可见此处铜矿的开采可能稍晚一点,且应当来自北岸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的扩张。从《汉书》《后汉书》都记载邛都南山出铜,又都未提及堂琅产铜,且邛都之铜又得到了迄今西南发现的最大的东坪汉代冶铜遗址的印证来看,这个论断是颇能成立的。
此外,我们若是再次注意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越到青铜时代,文化共性越多,而金沙江中游的石棺墓本身是沿金沙江传播,且东端又在巧家,恰是金沙江两岸铜矿资源最密集分布的地区,而巧家以下要在永善方有铜矿,但至今永善至巧家尚须经昭鲁盆地出横江乃可到达,巧家以下直至永善黄草坪,江水多滩亦难行舟,清代云贵总督张允试图开通此段金沙江航道也以失败告终,因此,石棺葬人群沿金沙江支流城河扩展到会理盆地,或沿金沙江下至巧家,其动力很可能是寻找铜矿资源,反之到达会理盆地的安宁河谷先民也可以同样的道路进入金沙江两岸。而一旦到达巧家,昭鲁盆地与安宁河流域的道路就算连接起来了,西昌—巧家—昭通连接为线,西南丝绸之路北线的“零关道”和南线的“五尺道”也便实现了连接,金沙江的阻隔进一步被泯灭,西南边疆的文化一体性趋于更高层次。汉军灭头兰后,由此道北上安宁河流域,亦有了文明基础。
三、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与汉代对西南边疆的开发
安宁河流域的铜业开发,是“零关道”畅通,西南丝绸之路南北线实现连接的重要动力和保障,这本身是西南边疆早期开发的基础性工程。但在此之外,对于第一次将西南边疆纳入华夏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汉代而言,安宁河流域的铜业开发还为汉代开发西南边疆提供了直接的金融保障,从而为将西南地区初步融入华夏文明系统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汉开西南夷,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在初开阶段,汉廷主要靠货贿建立与西南诸夷的关系,货贿物品之中,铜钱是赠送的大宗物资之一,也是汉廷开道和用兵经费的主要来源。如唐蒙治南夷道“费以巨万计”,司马相如定西夷,“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4]3046、3047“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7]1158班固总结说是“散币于邛僰以辑之”。[7]1158为铸造钱币,保证经费,汉廷则大量采铜铸钱,“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7]1163两汉史书中类似记载甚多,可以说汉开西南夷,铜矿资源的大举开采也是其基础性保障工程之一。至于后汉,以安宁河流域为腹心的越嶲郡,往往成为西南夷开拓的基地。光武帝建武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嶲”,[18]2853建武二十七年,西南徼外大国哀牢决意归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18]2849明帝时遂以哀牢国地设为永昌郡,汉廷不仅开地数千里,“蜀—身毒”道也最终打通;益州刺史朱辅在明帝时期经营西南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18]2855从户口来看为汉代西南最大边功,“白狼、槃木、唐菆”都是生活在越嶲郡以西以北的族群,安宁河流域正是招抚他们的基地。东汉招抚西南诸夷,最常用的手段还是赂以财物,这是白狼王所献《远夷乐德歌诗》中“多赐缯布”所明言的。[18]2856西昌市南东坪村发现的炼铜铸币遗址,面积巨大、铜渣堆积厚,是国内罕见、西南地区目前可见最大的炼铜铸币遗址[19],发现的王莽时期的货泉铜母范和东汉五铢钱铜母范也具官方身份[20],安宁河流域实是当时西南夷地区“金融中心”,而这个身份则来源于安宁河流域当时国家级的铜矿资源。西南丝绸之路沿线都有五铢钱发现,也是对这个地位的印证。
同时,从西昌东坪遗址的文化遗物来看,“东坪遗址居住的是内地来的移民”。[20]这暗示出安宁河流域的铜矿开发,是王莽以后才趋于高峰的。凉山州博物馆的孙策、唐亮两先生通过对安宁河流域考古文化的纵向综合研究,就发现“东汉以后,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突然消失”,推测原因是“汉朝政权对此地有了强有力的控制,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部分邛人放弃了氏族社会的习俗与汉人融为一体”的结果[21]。这个推测应是成立的,不过这个转变的另一前提性基础应当是汉人的大量进入,只有汉人大量进入,汉廷的地方政权才有足够的控制力量,安宁河流域仅西昌境内的汉代砖室墓就达数百座[22],而砖室墓在四川地区最早的起源是王莽时期[23]。王莽时期在金融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郡国重新获得了铸币权,光武中兴复行五铢后,虽未有明诏记载放权郡国铸钱,但和帝初即位,即于章和二年(88年)四月以先帝遗意“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18]167至少此后就算铸币权仍在中央,铜矿采冶的权力却回到民间,那么安宁河流域丰富的铜矿资源就足以吸引大量商人、铜工不断进入了。这项政策是与安宁河流域东汉时期汉文化因素急剧增强同步的,当然也就凸显了安宁河流域铜矿资源之于洛阳汉廷在西南边疆建立中国古代史上可能最大的西南边功间的重要关系。
[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J]//霍巍.川大史学考古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279-309.
[2]李延详.辽西地区早期冶铜技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
[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J].考古,2009(7).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54.
[5](晋)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李中.严道古地[J].文史杂志,1988(6).
[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刘弘.老龙头墓葬和盐源青铜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6(6).
[9](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3512.
[10](清)杜汝崑.四川建昌镇杜汝崑咨略[M]//(清)何东铭.咸丰邛嶲野录(《中国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7.
[11](清)杨昶等.同治会理州志.卷九.赋役志.铜政.[M]//中国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2.
[1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的矿业[G].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
[1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会理县雷家山墓地M1发掘报告[R].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64.
[14]唐翔.会理青铜文化综述[J].四川文物,1999(4).
[15]李霞,万杨.云南昭通地区先秦至两汉时期墓葬综述[EB/OL].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http://www.crntt.com/crn-webapp/cbs.
[16]昭通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巧家县小东门墓地清理简报[J].四川文物,2009(6).
[17]蒋志龙.金沙江支流东川玉碑地遗址[J].大众考古,2014(6).
[1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姜先杰.西昌东坪遗址冶铜铸币原因初探[J].四川文物,1999(4).
[20]林向等.四川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的发掘[J].文物,1994(5).
[21]孙策,唐亮.邛都夷活动范围的新认识[J]//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2]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J].考古,2007(5).
[23]罗二虎.四川汉代砖室墓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