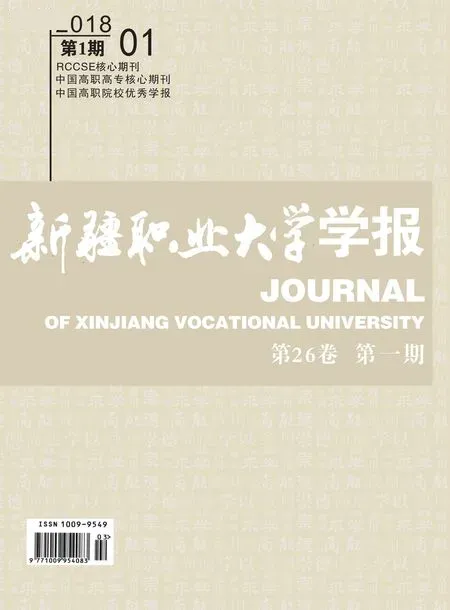《容斋随笔》考据谬误三则
黄立志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04)
一、洪迈及其《容斋随笔》的历史地位
《容斋随笔》之所以被后人称颂,一则是洪迈出身官宦世家,自己又曾经官至端明殿学士,后唐天成元年(926)始置,以翰林学士担任,掌进读书奏。宋沿置,由久任学士大臣担任。大概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参事之类的官员,他有条件阅读各种典籍。他曾经写道:“在所存两千卷书中,写有题跋的有五百零二卷。”[3]。二则洪迈很智慧,见解独到,譬如《陈涉不可轻》一文从崭新的角度总结了陈胜的失败,他认为“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所以败也”[4]。卸磨杀驴,一定是要先卸磨后杀驴,不能未卸磨就杀驴。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就是如此。古代很多有作为的皇帝也是寡恩忘旧,譬如汉景帝之废周亚夫,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他们成为一代明君的节奏。这部书大有补《资治通鉴》不足的作用,文革时期还少有地出版了。
《容斋随笔》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献的考订。洪迈的笔记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摘记加点评。他的很多史料都是对比而言的,十分契合。譬如关于李白之死,民间甚至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是他饮酒过度在当涂采石溺亡。他查了李阳冰所作的《草堂集序》和李华的《太白墓志》,认为民间的传言不足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关于鄱阳学宫的考订颇见功底[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由穆公校点的《容斋随笔》,内容很多,没有翻译,只有正文。仔细阅读了洪迈的这本著作,很难找到他的推理或证据的错误。因此,这部著作就有很高的学术研究的价值。笔者认为《容斋随笔》不应该归于笔记小说范畴,应当属于学术著作,因为小说个人创作的成分很大,联想的文字很多。事实上,《容斋》更多是根据已有的文献进行阐发和修订。
笔者认为《容斋随笔》以后还会被重视,是因为作者的治学十分严谨,采用了量的研究,使用大数据。这在南宋那个毛笔时代十分可贵和难得。譬如“侍郎右选注拟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人”,都精确到了个位数,对于研究南宋经济和吏治而言,是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由此可见,书名虽然是《容斋随笔》,但是作者并未“随笔”。
二、《孙膑减灶》的推理谬误
关于《容斋随笔》“考据”的考据,的确很难去考据。一方面历史比较久远了,他当时读的书有些都已经失传了,无法考证;另一方面,作者比较严谨,可以说是字字推敲,很难推翻作者的论点。毋庸讳言,考据是《容斋随笔》的一大特色。有许多同类文章,读来颇有新意。然而,笔者读了洪迈的一些考据文章以后,认为他是为考据而考据,似有偏狭之嫌。
《孙膑减灶》(《容斋随笔》卷十三)是关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胜庞涓之事,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认为“皆深不可信”[6]。笔者认为洪迈的说法有主观臆断之嫌。首先,洪迈是一种推理,并无实际证据。其次,他的推理也有一定的问题。他认为孙膑是救急之师,没有功夫去数灶。庞涓派100人去数10万个灶,不过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假如要派200人数灶也不过一个小时,何况庞涓的部队也需要休息和吃饭,并不耽误行程。5万灶和2万灶更容易数了,何来“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再次,他认为孙膑无法精确地计算庞涓晚上到达马陵。这个应该不算难事,派侦察兵观察庞涓部队的行进速度和位置,这是可以计算到的。另外《史记》中交代“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洪迈却忽略这个地理现状,说“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笔者觉得洪迈这种说法似乎有悖常理。这么狭窄的地形,能坐车中吗?不能骑马吗?古代的战车毕竟是少数,多数士兵需要步行或者骑马。况且马陵地形狭窄,视野有限,士兵看到了树上的字不会报告吗?所以,这个考据上,洪迈的论证十分牵强,不足信。
三、《卜子夏》的纪年错讹
关于“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7]的考据,洪迈认为司马迁是错误的,认为“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容斋续笔》卷二)笔者仔细揣摩洪迈的这段文字,一是他怀疑年代是否有误;二是怀疑是否有这个史实。究竟是哪里错误,洪迈并未指出来。在“史记世次”(《容斋随笔》卷一)一文中他说“《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可以看出,是对《史记》的纪年产生了怀疑。应当说洪迈根据纪年的推理进行怀疑是有道理的。应该说他主要怀疑的是年代问题,而不是史实问题。
这句话出自《史记·孔子弟子列传》,原文是“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现在有人考证魏文侯正确的即位时间是前446年(元年在前445年),1935年,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三十八“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考”考证洪迈的推理是错误的[8],因为推理的依据纪年存在错误。笔者认为钱穆的说法可信。至于钱穆纠正《史记》的纪年错讹,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严格地说,洪迈指出了司马迁《史记》的纪年错误,这是正确的,然而并未说明正确的纪年时间。关于具体的纪年时间后代的钱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在《史记》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西极化人》的构思来源考辨
《容斋四笔》(卷一)记载了有关《列子》中周穆公“西极化人”[9]一段文字,“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最后洪迈认为唐朝人所写的《南柯太守》《黄粱梦》之类的故事创作构思是从先秦时期的《列子》套用来的。笔者看了周穆公的事情,其中谈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应该是西方所说的催眠术。会这种催眠术的人“化人”将他催眠了,然后再唤醒他。在《内经》中也有提及,古代的“祝由术”就是这个事情。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有一种说法是先秦时期。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有人会这种巫术。《黄粱梦》是唐人沈既济所作的《枕中记》而来,这个小说中,有个道人吕翁给卢生一个瓷枕头。从这个情节来看,应该是吕翁催眠了卢生。因此,唐朝人所著的那几本有关梦幻的书,未必从《列子》这个范本中套用来的,很可能是作者听到或者看到了催眠术这种情况,众所周知,唐朝是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然后就写了《青衣》之类的小说。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不宜仅仅从文学史的角度去分析,应当考虑到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还需要考虑到医疗技术和心理学技术的作用。可见,洪迈的结论未免偏见。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版本没有收录这则笔记。可能是他们认为这则笔记有点怪力乱神的意思,也可能是编者考虑到这则笔记的不可靠性。只有何林和良石编译的这个版本有这则内容。
《容斋随笔》耗费了37年的心血,1 220则,50万多字,可谓精工细作呕心沥血。任何一部好的作品都需要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作品经不起时间的拷问。写本子,撰著作,敲文章,都需要精心构思,反复琢磨,长期积累。这样的文字,才能够流传于世,才能有高被引频次。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