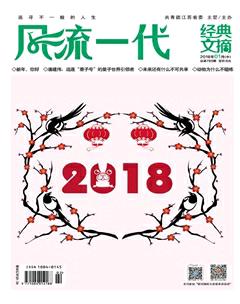父亲与破烂
王樽
①
童年时我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差不多到九岁,才拥有了生平第一顶棉帽。我们叫皮帽,其实是布面内有人造栽绒的那种,是父亲从别人丢弃的废品中捡的。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捡来,我见到时,父亲正坐在屋子中间,像个严谨而巧手的工匠,举着洗刷过的旧皮帽在煤火炉前烘烤。
那帽子整个轮廓还保持得周正,大概新时是草绿色的,但已褪成暗黄,一只栽绒的护耳有根老鼠尾巴似的小绳,另一根已经断掉了。几十年过去了,帽子的模样依然清晰记得,因为那是我的第一件“奢侈品”。这顶在父亲手里吱吱冒着热气的旧皮帽,让我在彻骨的寒冬里感受到微弱而美好的溫暖。那天凌晨时分,我从梦中醒来时,见到父亲仍对着火炉在烘烤那顶旧帽子,屋里没开灯,炉火的红光映着他鼓鼓的眼睛和高耸的鹰钩鼻……此刻,想到他当时的样子,就想到教堂里虔诚默祷的神父,专注认真又凝重。到清晨来临,那顶帽子仍未烘干,父亲吸着鼻子,说:“还有点湿,但可以戴了……”我已记不清那顶旧帽子陪伴我度过了多少寒冷的日子,也许数月,也许数年。能记得的是,从我们小时,父亲就与破烂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我们的生活与破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不止一次,父亲给我们讲述他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经历:半夜上班路上,每每途经酱菜厂的废弃堆,因极度饥饿,有天他钻到破损的腐乳缸内翻找,结果没找到一块囫囵的腐乳,就舔食已经风干在缸壁上的残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吃腐乳,如果我们吃也要站到门外。腐乳是他记忆中伤心的痛。但他喜欢讲述这段经历,其中多少带有炫耀的色彩。人是很卑贱的,痛苦和贫穷甚至屈辱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炫耀。因为经历过极度的饥饿与贫穷,父亲成了一个痴迷成瘾的破烂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都会捡回一堆废旧铁钉、螺丝之类,久而久之,他的一个大木箱子里就盛满了这些劳什子,谁家缺个螺丝、螺冒、自行车铃铛盖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从他的“百宝箱”里找到。他的破烂王的名声,左邻右舍尽人皆知。这还不算,当母亲身体好些时候,他竟给母亲找了个工作———到废品站里分拣收购来的废品。
最令我们难堪的是,他不甘寂寞,喜欢把其作为一种美德,逢人便说自己捡破烂的体会,不管别人是否有兴趣,追在别人身后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破烂“传奇”。
当我少年懂事时,便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觉得脸面丢尽。
②
母亲退休之后,妹妹接班顶替成了回收公司的员工,虽然是当会计,但终是跟破烂有关。我一直怂恿妹妹离开,我想那不只是工作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命运的象征。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人如果天天与破烂打交道,最终自己也会变成一堆破烂。后来,妹妹终于离开了回收公司,去了一家大商场当会计了。
但父亲的破烂情结却牢不可破,且一生都在步步退却中接近———从“文革”期间的市委战备办公室,到石油公司,再到一家郊外的加油站,他喜欢留恋在废旧物品里,从中谋求新的用途。退休后,更是如鱼得水地干起了“破烂专业”。
别人扔掉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破烂,都可能被他捡回家。在他看来,天下没有真正无用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1995年夏天,父亲去邮局取汇款,被两个骗子合伙演“双簧”骗走了两万元。贫穷节俭了一生的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很长一段时间茶饭不思,甚至幻视幻听,神经兮兮。这时,他捡破烂的劲头更是空前得无以复加,往往在夜深人静时,他还周旋在小区周边的垃圾箱,仿佛可以从垃圾箱里捡回自己被骗走的两万元钱。于是,在他的小屋里,到处都是破皮鞋、烂家具,甚至连可能是死人家丢出来的被子、席子都要照单全收地卷到自己屋里。2000年早春,我去北方老家探望,见他的屋里随处可见捡回的破烂,包括一些塑料包装盒、旧衣服和鞋子,屋子里气味浑浊,无法站脚。我打开窗户,站在床前跟他说话,心中满是心酸与悲凉。
当晚,整理我原来的藏书,见一套精装本的《鲁迅书信选》因潮湿发黑彻底霉烂了,我将其丢进了小区的垃圾箱。第二天早晨,我见那套霉烂的书出现在他的枕边,我很生气地责备他:都扔进了垃圾箱,怎么又捡回来了?他目光怯怯望着我说:“这还可以看啊!”我说:“你一辈子都没看过鲁迅,发霉了才看?”他木讷地说:“没准我明天就看。”
说完,他用衣服袖口去抹那封面的霉斑。喃喃地叹息道:“我和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快死了也没发财啊!”
我说:“谁也不能靠捡破烂发财。”
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忽然轻声地喃喃自语,“谁都不知道,捡破烂多么有意思啊!”
我想追问他捡破烂究竟有什么“意思”?见他眼角有浑浊的泪水,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③
我终于没有质问父亲:捡破烂到底有什么意思?是见他浑浊泪眼里暴露的可怜无助,不忍和悲哀让我欲言又止。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回答,依照他的性格,即使能讲出道道,他也会三缄其口。到了晚年,他已经变成一个只沉浸在自我臆想中的沉默老人。
尤其是当母亲去世后,父亲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连电话也不接,一方面是因为耳聋,一方面也是他再懒得与人沟通。我想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在指责他的生活方式,都在以自己的观念劝他想开点———又不缺钱花,干吗还要去捡破烂?!我和我的哥哥姐妹都以他的破烂情结为耻,但谁也没有去想他乐此不疲的原因。在捡破烂中,他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所能体会到的“有意思”,也许确实是别人所体会不到的。
关于父亲与破烂,我不想再说什么。他穷在其中,苦在其中,想必也乐在其中,既然觉得有意思,那就是他的一种选择,一种活法。也许主动,也许无奈,更多的可能是艰难困苦的日益逼迫。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局外人。
我不想再去干涉和试图改变他,他已近七十岁,所有的道理都不缺。有天晚上,我在整理旧书时,又清理出几本或过时或霉朽想丢弃的书,我拿到他的房间,说想扔掉,问他要不要?
他十分诧异地望着我,像意外接到礼物的孩子,连连说,要,要哇!黑暗中两只眼睛炯炯有光。
④
2005年2月12日,我从深圳的邮局出来,手里拿着刚刚取到的拙作《与电影一起私奔》的第二次印刷的样书。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得知:父亲因脑溢血在一家民办的养老院里辞世,享年73岁。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据说,父亲在养老院时吃住都极糟糕,还常常遭服务人员训斥。
父亲去世后,他收藏的所有破烂,连同他生前的各种生活用品都被迅速处理掉了。
处理和遗弃破烂,是每个人最后被画上的句号。
很多年来,我都一直在努力,就是坚决抵制父亲曾经的生活。
但我不无悲哀地看到,不经意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重蹈父辈的道路。虽然耻于承认,但在父亲与破烂的纠缠里,对自己有着“剪不断”的彻骨影响。潜移默化中,破烂的意识渗透进自己的血脉。比如,当我要丢弃家中无用的东西时,总会反复考虑其可能具有的利用价值,为此常常欲弃不能;我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电子邮箱是汉语拼音全拼的“垃圾教授”,当初起名只是出于一种自嘲,而“垃圾”的概念却与“破烂”不谋而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沉浸于用废旧画报的图片进行新的拼贴制作,有位女作家还在报刊撰文,以欣赏的笔调介绍我“创作”的那些“从垃圾上盛开的艺术奇葩”。
我想,冥冥之中,这些都有一种深层次的父子衔接。
正如每个人都无法改变和逃避遗传的因子,前辈的精神流淌在自己的血脉里。尽管我们竭力抗拒和抵制,仍难以撇清,并眼睁睁地看着———那幽暗的细流在网状的蓝色经络里无限渗透。它们恣肆地左奔右突,编织出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幸与不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