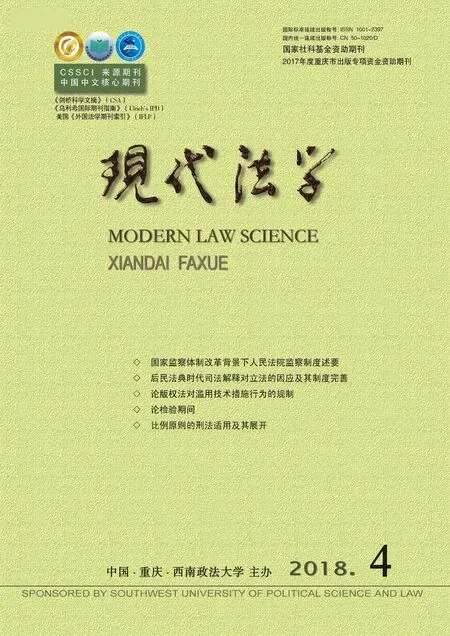涉外侵权法律选择中的“侵权行为地”界定
——从侵权一般冲突规则的解释切入
林 强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正式施行,至今已逾7年。该法第44条(即学理上所称的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核心连结点“侵权行为地”的含义一直悬而未决,亟待澄清。
在限地侵权中,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在同一法域,追问“侵权行为地”并无实益。在隔地侵权(Distanzdelikt)中,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分离,且分别位于不同的法域,如果该案件不适用《法律适用法》或其他特别立法中的侵权特别冲突规则,又不受该法第44条特殊连结点的指定,这时必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判定“侵权行为地”具体所指则为首要任务。在《法律适用法》实施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87条曾对“侵权行为地”作出过复义化的解释,即“侵权行为地”既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又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这两个连结点所指定的法域的法律不相同时,人民法院可以择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7条规定:“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但是,《民通意见》对“侵权行为地”的这一解释,显然不宜直接套用在《法律适用法》的相同概念上。因为从规范效力来看,《法律适用法》第51条已明确终止了《民法通则》第146条的效力,依附于该条的《民通意见》第187条也理应无效。另外,《民通意见》虽然肯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了两种含义,但是并没有指明两个法域的法律不一致时,应如何进行法律选择。将问题留给法官自由裁量最终还是回避了对整个问题的解答,在未对司法实践做详尽探究的情况下,无法由此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条关于“侵权行为地”界定的习惯规则。
当前,学界就这一问题存在两类迥异的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应当对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做单义化的解释,但是持该观点的学者内部又有分歧,有的学者从2007年7月11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非合同之债准据法的864/2007号(欧共体)规则》(下文简称《罗马II规则》)的立场进行反思,认为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更符合我国国情[1];有的学者则借鉴日本立法经验,认为将“侵权行为地”认定成“侵权结果发生地”更为妥当,仅在加害人按照常理无法预见侵权结果发生地之时,方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2]。第二类观点认为,对“侵权行为地”应当做复义化的解释,但是不同于《民通意见》,持该论点的学者认为,美国俄勒冈州2009年《涉外侵权和其他非合同请求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较为可取,在加害人明知或应知侵权结果发生地时,应当由受害人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或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中于己有利的法律[3]。相应地,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在立法中对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概念亦存在单义与复义两种解释模式*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典型立法如奥地利1978年6月25日《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律》第48条第2款,有类似立法的国家还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典型立法如2002年3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219条第1款第2句,有类似立法的国家还有荷兰、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等;有些国家避免对“侵权行为地”作出界定,而用“引起责任的事实”作为连结因素,即“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可以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地”,典型立法如2005年修订的《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20条第1款,有类似立法的国家还有古巴、约旦等。(参见: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规则和原理的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404;邹国勇. 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109;Symeon C. Symeonides. 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9.)。
各种学术观点似乎皆有一定的理据,尤其是粗浅地从比较法的视角进行观察,单义解释模式与复义解释模式皆有一定数量的立法例,这似乎表明无论选择何种解释模式,司法处置都大体上能够得到妥当的结果,否则立法或者司法早就对相应的界定模式予以变更。但是本文认为,确定“侵权行为地”的含义本质上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不能脱离法律规则体系而孤立地论证某一观点的合理性。前述学术观点至多只具有部分妥当性,立法的分殊恰恰从一个侧面表明“侵权行为地”含义的选择需要立足于特定立法的整体。为此,本文接下来两个部分将立足于有代表性的特定法域的冲突法体系,详考两种模式在各自体系中的运作机理。最后,回归我国现行立法,运用获取到的比较法经验,探寻可能的法律解释路径或未来的修法方向。
二、单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的实践
早期成文国际私法大都未直接规定侵权冲突规则,作为侵权冲突法主要渊源的学说和判例对“侵权行为地”一度坚持单义化的解释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迎来了国际私法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的高潮,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立法单义化地界定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常见的界定模式有三种:一是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典型立法如《罗马II规则》第4条第1款;二是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典型立法如1978年奥地利《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48条第2款[4]125;三是附条件单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典型立法如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律》(以下简称《瑞士国际私法》)第133条第2款,立法者原则上将隔地侵权中的“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当加害人应当能够预见到侵权结果发生地时,则界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4]169。但是晚近以来,这些单义化界定背后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明显有别于其之前的实践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早期单义化界定的实践及其所遇批判
早期国际私法虽然均对“侵权行为地”做单义化的解释,但是内部对于“侵权行为地”究竟具体指的是“侵权行为实施地”还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已有明显的分歧。在跨境活动尚不频繁的情况下,很难说两种见解均充分考虑到了隔地侵权的特殊性,这种差异更多是因为各自奉行的学说不同。欧陆学者受到“法则区别说”的影响甚大,基于“场所支配行为”的理念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19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侵权行为地”应当是被告本人或其代理人实施行为地,该观点很快便被该时期欧陆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及司法者接受[5]536。20世纪初,美国法院判例支持了“侵权行为地法”在涉外侵权案件中的适用*早期美国法院在侵权冲突案件中决定究竟是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还是法院地法时摇摆不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43年在Smith v. Condry案中运用了“相似理论”(doctrine of similarity),即法院能否援用侵权行为地法规则,取决于该规则与法院地的相应规则是否具有相似性,因此,实际上是法院地法在侵权冲突案件中居于支配地位。后来,下级法院判例逐渐松动该立场,在Slater v. Mexican Nat. R. Co.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根据“义务理论”(obligation theory)适用了侵权行为地法,后续判例逐渐抛弃“相似理论”,转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约瑟夫·比尔(Joseph Beale)在主持编纂《第一次冲突法重述》之时,采纳“既得权”学说对当时的判例予以规则化,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使行为人承担责任所必需的最后一个事实发生地”*详见《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第377条,该表述后来被称为“最后事件规则”(the last event rule)。,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侵权结果发生地。
早期学说与判例对“侵权行为地”做单义化的解释,不仅受到前述特定学说的影响,还受到了法律形式主义思潮的影响,典型如“最后事件规则”,它可以精确地界定“侵权行为地”,实现法律选择结果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及一致性,迎合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旨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及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单义化解释“侵权行为地”的正当性基础逐渐受到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利了人员交往与商贸往来,隔地侵权大量产生,如国际产品责任案件、跨国诽谤责任案件等,这些案件为进一步检验诸种单义化解释的合理性提供了契机。例如,跨国诽谤案件中的被告在报纸上发表了诽谤原告的言论,但是该报纸在欧洲各个国家都有销售,且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侵权行为实施地究竟是报纸的编辑地还是发售地?应把整个案件笼统识别为一个诽谤行为还是每发售一份报纸就单独成立一个诽谤行为?对此认识不同,适用“最后事件规则”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只笼统地存在一个诽谤行为,需要确定第一份报纸的销售地在何处,确定过程不仅艰难,而且产生的结果也极具随机性;如果认为每次发售都单独构成一个侵权,也无法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与唯一[5]637-638。单义化的解释方案在应对隔地侵权案件之时,仅仅是做概念演绎,所得结论也并无多少合理性。
第二,早期单义化解释的思想根基逐渐受到动摇。如前所述,社会发展一旦诱发规范背景的改变,概念的运用就陷入了瓶颈,自然也难以回应社会的需求。欧陆的自由法运动以及美国现实主义运动都对法律形式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尤其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将矛头直指冲突法中的“既得权”学说,酿造了随后的“冲突法革命”。“冲突法革命”颠覆了诸多传统国际私法的理念*关于冲突法革命的理念与传统国际私法理念之间的差异分析,可进一步参见:Kegel G. Paternal Home. Dream Home: Traditional Conflict of Laws and the American Reformer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79, 27(4): 615.,与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相结合,其明显地敌视冲突规则,更关注法律规则的内容、所涉政策利益以及法律选择的最终后果。在这些价值的引导下,美国司法实践甚至抛弃了机械性的侵权冲突规则,用“方法”解决侵权法律冲突问题*对此可进一步参见:Symeon C. Symeonides. The American Choice-of-Law Revolu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37-43.。
(二)晚近单义化界定的回归及其运作
与美国不同,欧陆国家并没有放弃冲突规则。相反,“冲突法革命”给学者提供了反思和改进既有冲突规则的契机。在“冲突法革命”中,传统国际私法的“法域选择”方法受到激烈批评,卡弗斯斥责其是“蒙眼”选法,丝毫没有顾及法律选择实体后果公正与否[6]。故晚近冲突法学者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是如何在坚持冲突规则的同时,以法律可控而非纯粹主观的方式给法律选择的结果注入合理性。有学者认为,冲突法对“实质正义”的考量倒不在于法律选择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实体法中的正义标准,而是要求冲突规则在指定法域的过程中考虑国际背景下各方的实际地位及他们对法律选择结果的合理期待[7]94。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制定冲突规则时,更为精细地考量所涉主体及案件类型的特殊性。
系统性地从法技术层面对侵权冲突规则的改进提出构想的是莫里斯(Morris)。既往研究多着眼于侵权法律选择的灵活性来解读其“侵权适当准据法”(the proper law of a tort)思想,他则提出了一套规则建构的理念。他认为,当代侵权实体法规制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同一条冲突规则适用于纷繁多样的侵权案件无法得到社会可欲的后果,应当将合同冲突法中的“适当准据法”方法运用于侵权冲突法中,以给法律选择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可能的规则建构路径是:“应该要有一条(涵盖范围)足够广且足够灵活的冲突规则,可以考虑到(侵权冲突的)例外情形和更一般的情形,或者我们应该建构一条全新的规则去应对例外情形。”[8]申言之,侵权冲突一般规则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足够多的侵权冲突类型,必要时还需要针对特殊的侵权冲突类型或问题规定特别冲突规则。当代冲突法中的侵权冲突规则往往不止一条,且连结点更为多样。就规则的设置而言,立法除了设置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之外,还针对特殊的侵权类型规定了特别冲突规则,甚至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还引入了例外条款*在其他国家,例外条款(exception clause, Ausnahmeklausel)还有不同称谓,如“避开条款”(escape clause, Ausweichklausel)、“纠正性条款”(Berichtigungskausel)等。我国学界习惯性地称其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如无特别说明,最密切联系原则与例外条款在本文语境下意义相同。。
当代部分国家或区域仍坚持对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做单义化的界定,这并非是立法惯性使然,应当从前述思想基础和立法技术角度来认识其合理性。以下围绕欧盟的《罗马II规则》,进一步阐述当代立法者如何运用前述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保证对“侵权行为地”做单义化界定的同时,仍能避免早期实践所遇之非难,最终确保法律选择的妥当性。
《罗马II规则》第4条为侵权一般冲突规则,该条第1款规定:“侵权所产生之非合同之债的准据法应当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而非导致损害发生的事件所在地法,也不是该事件所产生的间接后果地法。”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直接损害结果地”。《罗马II规则》的序言为当前的立法规定做了说明:立法者认为长期以来各国对于隔地侵权中“侵权行为地”的认定并不一致,统一的解释可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参见:Rome II, Recital 15, Recital 16.。如果复义性地界定“侵权行为地”,灵活性有余但难以实现前述两个价值取向,故不足采。两种单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的方案都可以实现前述价值,但立法者认为适用侵权直接损害发生地法更优,原因在于其更能实现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反映出民事责任的当代发展及严格责任体系的发展*参见:Rome II, Recital 16.。为何能实现这些目标并非不证自明,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大多数案件中将“侵权行为地”认定为“直接损害发生地”最有利于双方获取法律信息,实现获取法律信息成本的公平分配:加害人可以预见到他的行为可能在另一国产生损害,相应地可以获取相关国家的法律信息并进行风险评估,从而将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受害人在其人身及财产所在地*《罗马II规则》序言对“直接损害发生地”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其具体是指人身受到伤害地或者财产受损地。(参见:Rome II, Recital17.)进行投保并规避风险,也在情理之中[9]475。如果以“侵权行为实施地”来界定“侵权行为地”,对于受害人是不利的,因为他无从预知“侵权行为实施地”会在何处,在各国侵权实体法远未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依照本国法律所投的保险也可能因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法的适用而导致目的落空。更为致命的是,接受侵权行为实施地的立法例,将会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欧盟内部的侵权案件和涉及第三国的侵权案件予以区分,从而增加交易成本及冲突规则设计的复杂性[9]477。
但单义性地解释“侵权行为地”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会遇到一些难题:第一,存在一因多果的情形,即一个侵权行为在多国境内产生了损害,突出的例子如不正当竞争案件,加害人在一国之内所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了特定受害人在多个国家境内均遭受侵害。严格依照侵权一般冲突规则,须适用多个国家的法律,不仅可能产生潜在的判决冲突,还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这些案件类型还包括其他关于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的经济侵权以及跨国人格侵权等。第二,从前述立法原因的剖析中可以看出,立法者选择“直接损害发生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存在若干假设,包括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预见利益的平衡以及加害人对于结果的可预测性。一旦这些假设在具体个案中不能成立,适用直接损害发生地法便缺乏正当性。例如,加害人确实无法预见损害的发生、受害人明显为弱者,甚至极端情形下加害人是弱者等。由于侵权类型及个案的复杂化,机械地适用直接损害发生地法难免会产生问题,故需要引入缓解机制。
《罗马II规则》虽采纳单义模式,但在规则体系中设置了两大缓解机制化解了可能的困境:其一,《罗马II规则》第6-9条分别针对不正当竞争或妨碍竞争侵权、环境侵权、知识产权侵权以及劳工行动引起的侵权等规定了侵权特别冲突规则,部分规则对直接损害分散在各国可能带来的问题做了修正,如第6条第3款b项*该条款规定:“如果被告住所地是法院地,且法院地也是受到直接且实质影响的市场所在地,则原告可以选择适用被告住所地法。”。部分规则是对直接损害发生地的偏离,例如,第9条劳工行动引起的侵权责任适用的是行为实施地法、第7条环境责任则采纳原告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或侵权结果发生地法的模式。其二,在其他情况下,如果适用直接损害发生地法并不妥当,且存在最密切联系的场所,可由第4条第3款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予以纠正。
瑞士是典型的附条件界定“侵权行为地”的国家*依照《瑞士国际私法》第133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当加害人与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不在一个国家时,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如果加害人应当预见侵权结果发生地,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瑞士国际私法》同样有相当数量的侵权特别冲突规则。该法第110条第2款及第135-139条均是特别冲突规则,对“侵权行为地”的界定同样有别于侵权一般冲突规则。另外,该法总则第15条第1款还设置了充当矫正功能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自然也可以纠正分则中侵权冲突规则的法律指定。将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国家并不多,前文也提到因为受害人无从预见侵权行为实施地,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最终将导致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故从这点来看,此种立法模式欠缺一定的正当性。
(三)小结
当代立法采取单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的做法并不是对早期侵权冲突法实践的简单重复或肯定。立法者在界定隔地侵权中的“侵权行为地”时,做了一定的利益和政策考量。如果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侵权行为地”的界定不能满足一些特殊侵权类型的利益和政策需求,宜在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之外制定侵权特别冲突规则*参见:Rome II, Recital 19.。必要时,对立法所不能预见到的极端情形还需要运用例外条款来纠正“侵权行为地”的界定。
三、复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的实践
晚近以来,许多国家都有意对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古巴、约旦、拉脱维亚、索马里、西班牙、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都在侵权冲突规则中采取了此种立法措辞。这一连结点采取模糊化的表述,例如,以“产生侵权责任的事实”作为连结点,既可指代“侵权行为实施地”,又可指代“侵权结果发生地”[10]59。虽然此种做法有利于灵活地应对隔地侵权,但是如果不能寻找到裁判标准,法官难免会陷入恣意擅断的境地。对此,有学者主张受害人可以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中对自己更有利的法,但是选择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必须以受害人可以预见到侵权结果发生地为前提[2]。这种观点部分体现了“有利于受害人”(favor laesi)原则[7]119,但从各国立法的具体表现来看,这并非是最有利于受害人的做法,尚有法官依职权适用对受害人有利的法以及不论加害人是否可以预见到侵权结果发生地均赋予受害人选择权的做法。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评判,哪种立法例更优?所有隔地侵权都适合依据“有利于受害人”原则来选择准据法么?如果不合理,在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贯彻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国家又是如何通过立法技术来避免不当的法律选择后果呢?
(一)全面“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实践
西梅恩尼迪斯(Symeonides)教授对“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隔地侵权中的运用状况作出过详尽的分析。大致而言,“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实践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实践是在所有隔地侵权案件中均根据“有利于受害人”原则来确定准据法;第二类实践是仅在部分隔地侵权案件中运用“有利于受害人”原则[10]59-67。在立法中,第一类实践的直接表现就是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规定在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如何来贯彻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又有多种不同的立法安排。下文以德国的实践为线索,来评价这些立法技术的具体得失:
在1999年《民法典施行法》增订侵权冲突规则之前,德国侵权冲突法的主要渊源存在于判例法中。“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确立许久,学理化的表述为“并立学说”(Ubiquitätslehre或Ubiquitätstheorie)[11]89-94,即侵权行为的任何一个构成要件所在地均可以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为“侵权行为地”,法官需要依职权适用这些法域的法律体系中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法官最后多选择适用法院地法*这也是莱弗拉尔选法五点考虑中选择适用优法所面临的批判,对此可参见:Willis L.M.Reese. American Trend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ademic and Judicial Manipulation of Choice of Law Rules in Tort Cases [J]. Vanderbilt Law Review, 1980, 33(3): 725.。在德国起诉的多数案件中,“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至少有一个发生在德国境内,法官在比较过程中认为法院地法更优,是一种普遍性的司法态度[12]524-526。依职权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还可以产生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当“侵权行为发生地”与“侵权损害结果地”分布于多个法域时,法院需要一一查明并对比这些国家的法律。查明和比较两个或更多法域的法律体系,对法官来说无疑是重负*参见:Bundestagsdrucksache 14/343(1999), S.11.。如果不能查明部分国家的法律,无法比较出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因此,转而适用次优的法律,是否可以算是法律适用错误?如果通过比较,一国法律中的部分规定有利于受害人,部分规定又不利于受害人,应该如何适用法律?这些均是依职权适用可能会遇到的难题。学界通说与少数实务意见则认为,应当直接赋予受害人选择权,只有在受害人没有选择的时候,法官方可依职权确定并适用对受害人有利的法[11]228-230。但是正如前述,只要法官仍需要依职权查明并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必然存在着前述困境。
1999年修订后的《民法典施行法》第40条第1款第2句直接赋予受害人选择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的权利,如果受害人没有行使选择权,则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此种选择权在性质上被认为是冲突法中的形成权,受害人需要在一审言词辩论的先期首次期日(《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5条)结束前或者在书面准备程序(《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结束前提出。一经提出,在嗣后的程序中对受害人也有约束力[12] 527。此规定背后有若干理据:第一,受害人可以自行比较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从而运用单方法律选择权选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法律;第二,在程序上对法律选择的时间进行限制,有利于诉讼经济,并有效地保障诉讼当事人双方的攻防平等*参见:Bundestagsdrucksache 14/343(1999), S.11.;第三,受害人未选择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之时,直接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避免了前述依职权查明更有利的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修法之后仍难免非难,德国严格贯彻了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但是也走向了最不利于加害人的一端。然而,受害人并非都是侵权关系中的弱者,实体法中没有明显的国际趋势表明必须在所有侵权类型中都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考量,也没有理由认为国际侵权中的受害者就应当比纯粹国内侵权中的受害者享受更优越的保护[12]525。对此,一些立法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受害人如要选择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应以加害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侵权结果发生地为限*2009年通过的《俄勒冈州侵权和其他非合同请求法律适用法》即是如此。(参见:Or. Rev. Stat. 15.440(3)(c).),似乎由此可以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也维护加害人对法律选择结果的可预见性。但是,在操作时如何判断“预见到了”或者“应当预见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倘若加害人最后被认定无法预见“侵权结果发生地”,仍需要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也就是说,以加害人可以预见侵权结果发生地为条件,限制受害人的选择权,实质上是单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的一种缓解机制。如前一部分所述,如果没有侵权特别冲突规则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缓解机制,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另外,这种选法方法背后的立法逻辑还存在重大缺陷:授权受害人选择适用更有利的法本身就预示了该侵权类型中的受害人应当予以优越保护,但在加害人无法预见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情形下,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有利法的权利,还要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如此一来,法律选择结果体现为优先保护加害人对法律适用的可预见利益。但是从常理来看,加害人能否对结果加以预见,可能实际上并不会影响整个侵权类型的定性以及是否给予受害人优越保护的预判。
对全面依据有利于受害人原则选择准据法的另一个批判在于,从思想基础来说,“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固然体现了实质正义的需求,但是实质正义的衡量标准并不仅限于此。举例来说,在跨国人格侵权中,允许诉请人选择有利于支持其诉请的法律,可能会极大地限制被诉人享有的言论自由。还有一些公共性侵权可能涉及一国的规制性利益,同样也不能以有利于受害人的方式规避法律的适用,所以,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适用于一切隔地侵权案件并不妥当。
1999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在修改之时,立法者未针对特殊侵权类型制定特别冲突规则,依靠其第40条第3款以及有限情况下的反致之适用,并不能完全矫正“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可能带来的不当结果[13],司法实践主要倚重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1条规定的例外条款。该条款在判断有无实质更密切联系之时,特别提及是否有既存的“法律关系”或者“事实关系”不无道理,旨在提醒法官应当注意到特别侵权类型[14],适时地避免适用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0条可能产生的不当结果。但是这种立法方案的弊端也极其明显:过于倚重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1条例外条款将对司法造成极大的负担。所以,如果侵权冲突法的规则体系中仅有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与例外条款,司法操作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二)部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实践
通过前述德国实践的考察,可以知悉全面地引入“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并不合适。但是吊诡的是,有研究表明,美国高达86%的隔地侵权案件适用了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15],对此需要辩证地看待:首先,大量产品责任案件并未统计在内,产品责任案件中支持受害人的比例仅有52%[16]。其次,由于存在一个联邦体制的框架,《联邦宪法》规定的特权与豁免条款、平等保护条款均对州际冲突案件的结果施加了一定影响,在部分案件中扩大性地保护外州受害人是宪法的要求*柯里关于宪法对冲突法有何影响有过深入讨论,克格尔对柯里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整理,可参见:格哈德·克格尔. 冲突法的危机[M]. 萧凯,邹国勇,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79-91.。再次,州际贸易条款等宪法性条款授予联邦部分的立法权限,联邦的统一立法消解了大量可能的重大规制性利益与政治性利益的冲突。例如,在证券、反垄断等领域均有联邦性立法*在美国,竞争法领域的联邦法有《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证券法领域的联邦立法有《证券交易法》《全国证券市场促进法》《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反不公平贸易方面的联邦立法有《拉纳姆法》等。关于美国商法经济法方面的进一步立法介绍,可参见:彼得·海.美国法概论[M].3版.许庆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31-283.,这些领域便几乎不存在州际侵权冲突的案件,现存的州际侵权冲突得以较为纯粹地私法化(相比较于经济法中的侵权责任而言)。从私法视角出发,加之有宪法条款的保障,倡导“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结果上便无太多可指责之处。但是,这些条件在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都具备,尤其是在国际法律冲突背景之下,各国在环境、金融监管等领域的规制性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就不容易达成法律适用方面的妥协。当前,美国正着手编纂《第三次冲突法重述》,侵权冲突规则部分试图将美国既有实践总结成一般规则,即在侵权冲突案件中区分“行为规制”(conduct-regulating)和“损失分配”(loss-distribution)争点,当“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分别位于不同州时,赋予受害人适用任一州法律的权利,被选择州的法律适用于所有争点。此种有利于受害人的立法例有其特殊的实践背景,其他国家不宜随意借鉴。
许多国家的立法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适用限定在若干特殊侵权类型中[10]62-64,但就已有立法来看,实践差异较大。有的国家将受害人选法的情形单一地限定在产品责任侵权中*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均只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适用限定在产品责任侵权中。,少数国家将其限定在人格权侵权或核侵权中*波兰、捷克仅在人格权侵权的涉外案件中适用“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奥地利只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运用在核损害侵权中。,也有国家或地区将该原则适用在多个领域,除了前述侵权类型之外,还包括环境侵权、不正当竞争侵权等*阿尔巴尼亚、比利时等国在多种特殊隔地侵权中均运用了“有利于受害人”原则。。
(三)小结
通过前述德国实践的考察,可以知悉贯彻“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最佳立法技术是直接赋予受害人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法的权利,其他立法方案均不可取。另外,从立法理念来说,在隔地侵权中,全面依照“有利于受害人”原则指导法律选择并不合适,究竟哪些特殊侵权类型可以适用“有利于受害人”原则指导法律选择,目前并未形成共识,理论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四、我国法中“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困境及其克服
(一) 我国现行立法的缺陷
前文已经揭示了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侵权行为地”的解释与侵权冲突规则体系之间的关联。侵权所涉案件类型的多样性表明,无论是采用单义模式还是复义模式的“有利于受害人”原则选法,均需要有法定侵权特别冲突规则的补充以及例外条款的纠正,才能避免产生不当的结果。我国现行立法又是否具备前述两个规范条件呢?
当前,我国侵权冲突规则分布于《法律适用法》和其他部门立法中:《法律适用法》第44条为侵权一般冲突规则,该法第45条、第46条、第50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7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9条构成了侵权特别冲突规则。从规则体系来说,我国侵权冲突法存在如下缺陷:
1.侵权特别冲突规则设置不足
以《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为例,该示范法规定了公路交通事故、海事侵权、航空侵权、产品责任、不正当竞争、环境污染、核侵权、诽谤侵权、民事欺诈等9类特殊侵权*参见:《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18-126条。。《罗马II规则》也设置了大量的侵权特别冲突规则,包括产品责任、不正当竞争或妨碍竞争、环境侵权、知识产权侵权、劳工行动侵权等5类特殊侵权*参见:Rome II, Art. 5-9.。尽管制定者在拟定具体冲突规则的过程中所做的考量不同,特别侵权冲突规则的设置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都对环境侵权、不正当竞争或妨碍竞争等实质性侵权作出了特别规定[10]98-99,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并无对应条文。首先应明确的是,这些社会法中的侵权规则(又称实质侵权法)虽旨在维护特定社会利益,但是多数未必能够上升到重大公共利益的维度,故不得一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认定为强制性规定,从而依据《法律适用法》第4条直接适用我国法*关于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理论,可参见:肖永平,龙威荻.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J].中国社会科学, 2012(10):109.。我国现行立法没有针对其中一些特殊侵权类型制定侵权特别冲突规则,应属立法失误。
2.例外条款缺失
《法律适用法》在总则第2条第2款设置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仅仅是在《法律适用法》对特定问题未作出规定之时起到补漏的作用,无法作为一般性例外条款矫正其他冲突规则适用的不当结果。《法律适用法》第6章也没有规定一条像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1条一样的针对债权领域法律选择的特别例外条款。
《法律适用法》第44条承担了几乎所有隔地侵权的准据法指定工作,在此种情形下,强行借鉴单义化或者复义化“有利于受害人”的界定方式对一般性侵权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作出解释并不可行。行文至此,似乎顺理成章的思路是通过司法解释或者重新立法引入例外条款,并补充一些必要的特别侵权冲突规则,从根本上克服现行立法的缺陷。但是本文认为,过度依赖司法解释或者频繁修法并不是依法治国的常态,如果可以通过法解释方法实现规则的妥当运转,应尽量避免依赖立法来解决问题。即使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修法引入例外条款以补充法定侵权冲突类型并纠正现有立法的不足,仍有一些问题未探讨清楚:究竟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侵权行为地”的选择应采用单义模式还是复义模式?应该补充哪些特别侵权冲突规则?侵权特别冲突规则在连结点的选择尤其是“侵权行为地”的解释上有何特殊之处?后面这些问题,在运用解释论解释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之时亦有可能遇到,故解释论和立法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因此,不妨先从解释论角度切入,寻找可能的法解释路径,克服现有的立法缺陷。
(二) 解释论的障碍: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侵权行为地”
从德国的经验来看,仅有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与例外条款,实际上也能基本实现侵权冲突法体系的有效运转。例外条款在侵权冲突法中主要矫正一般冲突规则对“侵权行为地”所做的常态化界定可能产生的不当结果。那么,解释论上可否援引《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2款,以立法未对“侵权行为地”作出明确规定为由,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个案中确定“侵权行为地”?
“肯定说”的理由包括:无论是单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抑或复义化界定“侵权行为地”并赋予受害人选择适用有利的法之权利,均有可能在个案中受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检视。先由立法界定“侵权行为地”,再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检验法域选择是否妥当的做法,与一开始就不界定“侵权行为地”,一概交由最密切联系原则判定“侵权行为地”的做法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本质差别,都要求法官对个案作出具体判断。但“肯定说”面临着若干质疑:最密切联系原则很大程度上是一条“虚无规则”,对“侵权行为地”的内涵所指不加界定,借助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侵权行为地”是否会极大地减损侵权冲突规则适用的可预见性?法官最终是否会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对第一点疑虑的回应可以是:事实上隔地侵权数量较之限地侵权要少,当前《法律适用法》已针对最为常见的产品责任案件、人格权侵权规定了特别侵权冲突规则,需要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认定“侵权行为地”的情形仅限于立法未规定的隔地侵权类型。总体而言,对冲突规则适用的可预见性并无太大的冲击。另外,最密切联系原则旨在为个案寻找法律关系的重心地,故适用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恰恰最符合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更不会减损冲突规则适用的可预见性。对第二点疑虑的回应则是:没有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属于当前立法的失误。从世界范围来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纳入侵权冲突规则体系中已是一种立法趋势*在2000-2012年间,共有26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含有侵权冲突规则的立法文件,其中有15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文件均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司法实践中滥用该原则倒不一定是法官有意为之,更有可能是当前学术研究不够,未能给司法实践提供有效指引。另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就像是在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本座”。一旦司法实践成熟,寻得类型化建构的基础,便有可能规则化。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适时公布指导性案例来指导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这也是一条避免司法权滥用的重要途径。
本文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虽然可以合理化部分隔地侵权类型的法律选择结果,但仍有其局限性。从学理上说,最密切联系的认定需要基于案件的全部情事,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应从空间地理层面上进行衡量*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6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上是选法方法,所考量的因素不仅限于地域联系,还包括诸如法院地及所涉各州政策利益、判决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当事人的正当期望和减轻法律适用的司法负担等。不同于此,大陆法系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仍主要是做空间上联系密切与否的判断。(参见:陈卫佐.当代国际私法上的一般性例外原则[J].法学研究, 2015(5):205.)。所以,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上还是传统国际私法的“法域选择”方法,只不过其是以原则的方式存在,在吸纳法律本座思想合理内核的同时,又给僵硬的冲突规则注入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合理性。但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不可能对案件背后所涉利益进行衡量,更不许掺杂实体后果的考量。正因此,仍需回应美国冲突法“革命家”提出的批判:单纯做“法域选择”不考虑法律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否得当?在特殊的隔地侵权类型中,“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渗透进了利益分析和政策考量,这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无法做到的。该论断在《罗马II规则》对“侵权行为地”的界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最有利于加害人对法律选择结果进行预判,相对而言,受害人无从预知侵权行为实施地在哪里,对于受害人而言是不利的。当侵权关系中的加害人处于弱势地位,或加害人的特定权利特别值得保护时,可以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罗马II规则》第9条就是典型的立法例,立法者意欲通过此种方式保护工人及工会组织的权益,避免其因为采取行为地受保护的罢工等劳工行动对境外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第二,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并由受害人选择适用任一地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方面,保护受害人,尽可能地给予其救济;另一方面,受害人往往会选择行为标准设定得高、较易于判定争议行为系侵权行为的法律体系,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给加害人施加了更高的注意义务。在受害人是弱者或者加害人侵犯的法益特别值得保护之时,此种法律选择方法具有正当性。《罗马II规则》第7条即是此种政策考量下的立法典型:一方面,该条款原则上肯定了该法第4条第1款规定,适用直接损害发生地法;另一方面,又允许受害人选择适用导致损害的事件发生地法,实际上就是侵权行为实施地法。该条款充分保护了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并有助于在欧盟境内实现较高的环境标准*参见:Rome II, Recital 25.。
第三,隔地侵权中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即单独或者共谋实施的一个行为在多个地方发生损害,不正当竞争或者妨碍竞争侵权案件中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由前述规则来看,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判断的结果可能需要分别适用受影响市场地的法律体系*这种思考方式及其处置后果被称为“马赛克考量”(Mosaikbetrachtung)或“马赛克原则”(the Mosaic Principle)。,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法律适用的复杂化,甚至是结果之间的冲突。为了应对不正当竞争或者妨碍竞争侵权中可能出现的此种困境,特别是出于节约司法成本和诉讼经济的考量,《罗马II规则》在第6条(b)款中规定,当法院地是被告人住所地、法院地是直接且实质受影响的市场地之一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法院地法*此时,如果另有多个被告同时被诉,不论其住所地是否也是实质且受影响的市场,只能允许适用法院地法。(参见:Rome II, Art. 6(b).)。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内化于“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只能部分缓解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部分特殊侵权类型中“侵权行为地”的认定需要做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这绝非司法机关应该贸然去尝试的,更为妥当的做法是交由立法者来解决。另外,还需考虑到的是,《法律适用法》第44条中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与当事人事后选择的法在特殊的隔地侵权中接纳程度较低*例如,《罗马II规则》在不正当竞争与限制竞争、环境侵权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的冲突规则设置上,均排除了共同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也限制了当事人事后合意选择准据法。,且其自身在限地侵权的特殊情形中亦需要被限缩适用*涉外侵权涉及多方当事人,仅其中部分当事人具有共同经常居所地,宜限缩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的适用。当事人事后合意选择准据法不得损害第三方的权利,典型立法如《罗马II规则》第14条第2款、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42条,我国立法无此规定。。鉴于此,在现行立法框架中,企图利用解释论实现侵权冲突规制的圆满,不可避免地会给司法者带来极大的负担,也使得第44条侵权一般冲突规则的适用变得复杂且无确定性。
(三) 立法论的核心议题:“侵权行为地”的常态化界定
通过立法弥补现行立法的缺陷,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引入例外条款、界定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增订若干侵权特别冲突规则。例外条款对于国际私法法典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侵权冲突法领域需要该条款,其他冲突法领域同样如此。当前《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2款仅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补充性原则,并未充分发挥其功用,未来立法宜进一步将其提升为一般例外条款。后两个议题密不可分,核心问题是各种隔地侵权对“侵权行为地”的认定究竟有多大的共性或者差异。如有共性,宜采取共性的界定方式,如各有特殊的利益和政策考量,需要决定哪种情况下“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方式更符合一般的利益与政策考量。对于有特殊考量的侵权类型,立法者宜制定侵权特别冲突规则。
目前,常见的隔地侵权案件有产品责任、核损害、环境污染、人格侵权以及在市场活动中发生的其他侵权案件。人格权侵权有其特殊性,在部分国家,如何协调加害人的言论自由权与受害人的人格权是宪法层面的问题,而一旦发生隔地人格权侵权,又往往引发分散的损害结果。因此,明显的共识是设立一条特别侵权冲突规则,在此不详述。从归责事由的角度来划分,剩下的前三类侵权在侵权实体法中均属严格责任侵权。有别于过错责任侵权,其侧重点在于损害填补,而非行为非难与规制。因此,冲突法晚近立法迎合了实体法中的此种理念,在这些严格责任的涉外案件中更侧重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不过在冲突规则的具体设置上运用了类似于实体法中的“动态系统论”原理*“动态系统论”由奥地利学者Wilburg在其著作《损害法的诸要素》(Die Elemente des Schadensrechts)中提出,后成为民法中重要的方法论。,对受害人的保护强度取决于致损活动的危险程度与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产品责任因生产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不大,且除了发生大规模产品责任事件外,其损害一般限于个体,通行的法律选择方案是阶段性选法的方法。核损害与环境侵权因致损行为具有较大危险性,且跨境损害后果往往波及面广,已有的立法通常直接赋予受害人法律选择权*奥地利就有专门立法特别保护受害人。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38条关于排放物致损侵权也包括了核污染侵权。(参见: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ct § 231(1).)。
市场活动中发生的侵权案件难以完全予以罗列,较为成熟的类型有证券侵权、不正当竞争或妨碍竞争侵权。不正当竞争或妨碍竞争侵权以及证券侵权对共同属人法、当事人意欲适用的法接受度低,故不适合适用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竞争关系、投资关系受到影响市场地的法律更为妥当*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36条第1款及第137条第1款的规定即体现了此种理念,与此类似的还有《罗马II规则》第6条关于不正当竞争和妨碍竞争侵权的冲突规则。瑞士学者在学理上将此称作“市场影响原则”(Marktauswirkungsprinzip)。,尤其是案件以集团诉讼的面目出现时,更应该如此。
剩下的其他市场活动中的隔地侵权案件笼统地对应于侵权实体法中的过错责任案件,难以进一步类型化。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原则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地位失衡,应当排除受害人选择适用于己有利的法律。以案涉双方对法律适用是否具有可预见性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点,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更优,且能实现侵权实体法填补损害与保障自由这两个价值追求。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该界定方式避免了将“侵权结果地”扩大解释成“侵权间接结果发生地”,从而使加害人无从预见可能适用的法律为何,也避免了将“侵权行为地”界定成“侵权行为实施地”,从而导致受害人根本无法预知适用的法律为何并采取投保等方式规避可能的风险。从实体法的认知来看,“过错责任”中的加害人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即是“过失”,故意和过失要件中均预设了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自然也不难预见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往往就是受害人自身抑或其财产所在地,故确保了加害人与受害人对于适用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法均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其次,有批评者指出,过错责任样态下的侵权责任不仅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更在于保障行为人的行动自由[17]608,适用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法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这一重要的价值目标。例如,行为人依照行为实施地的行为与安全规则行事,可能因适用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法,被该地的行为与安全规则判定为违法而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行为人的行动自由几无保障可言。有些国家立法为此将加害人对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是否具有可预见性作为适用该地法律的重要前提*瑞士与日本的立法即是如此,但是二者在立法技术上有一定的差异: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33条第2款规定,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但是加害人应当预见到侵权结果发生地时,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日本《关于法律适用的通则法》第17条规定,原则上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但是如果加害人通常不能预见到该侵权结果发生地,则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对此批评有如下几点回应:第一,与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的侵权制度从令状发展而来,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侵权,故擅长个别化地思考侵权责任问题,总体上并无体系可言,存在着大量诸如“一杯酒责任规则”(dram-shop laws)和“慈善免责”(charity immunity)等针对特定事项的侵权实体规则。有些规则侧重于行为规则,有些规则侧重于损害填补。也正是因此,在具体涉外侵权案件中,法官能够对案件所涉具体规则的冲突进行分析(又称作“争点”分析),判定究竟是属于“行为规制”(conduct-regulation)的实体规则冲突还是“损失分配”(loss-distribution)的实体规则冲突,并分别确定准据法。当前美国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将此种划分方法纳入《第三次冲突法重述》中,但该经验难以被移植到大陆法系国家,不仅是由于前述实体法结构的差异,尚有其他原因。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侵权实体法在制定时多采抽象条文的立法模式[17]621-628,其中并不囊括具体的行为与安全规则。行为与安全规则在性质上属于公法性质的管制规范,其大量产生于自由主义受到修正、福利国家兴起之后,具体包括了交通规则、污染物排放规则、劳动场所安全规则等。违反行为与安全规则直接导致的是公法责任,并不必然产生私法责任。在民法的视角中,对遵守或者违反这些公法性质的行为与安全规则作出何种评价,需要借助“转介性条款”来完成*“转介性条款”的运用需要在公私法互动的背景下来理解,对此可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9-352.,更进一步地需要法官在“不法性”或(以及)“过错”等侵权构成要件下进行判断*关于规制规范与侵权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J].中国法学,2009(2):57.,即遵守或违反行为与安全规则的行为是否符合特定要件,从而判定行为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通常认为,并非所有的管制规范均在民法评价中具有意义,仅仅是违反保护性的管制规范方可能产生私法责任。申言之,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不等于一定要适用该地的行为与安全规则,在侵权责任认定的语境下,法官不是适用或不适用行为与安全规则,而是对遵守或者违反行为与安全规则的事实在既定的侵权构成要件中予以评价。此种待评价的事实应同时包括遵守或违反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的行为与安全规则的事实,这即是“datum theory”理论[18]的体现。第二,如前所述,通常情况下加害人能够预见到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相应地,也能预见到该地的行为与安全规则。在此情况下,适用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法以及根据违反相关行为与安全规则的事实来判定承担侵权责任,无太大可苛责之处。第三,即使极端情形下加害人无法预见到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法,保障行动自由的目的不能一步就位地在法律选择阶段完成,仍可在准据法的适用阶段由法官来完成。法官在对侵权实体法中的“过错”或(以及)“不法性”要件进行认定时,不仅是简单地认定有无违反对侵权责任认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与安全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判断加害人是否对这些规则具有预见性,甚至当侵权行为实施地的相关行为标准与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的相关行为标准发生冲突时,加害人是否具有免责事由。从前述分析来看,《罗马II规则》第17条规定应当将侵权行为实施地的行为与安全规则“当作事实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考虑,这是有道理的且应当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综上可见,隔地侵权中“侵权行为地”的界定实际上并无一致性可言。但是,从各种隔地侵权类型与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其他连结点的兼容性来看,过错责任样态下的侵权责任类型要远比其他类型对当事人的意思、共同属人连结点与附属连结点的接纳程度高。过错责任仍属当代侵权责任的核心归责原则,数量也最多,将最一般且最主要的侵权情形规定于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符合一般认知。以过错责任样态下的隔地侵权为模型,宜将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认定为“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
假若将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界定为“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立法者还应当针对核侵权、环境侵权、证券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或妨碍竞争侵权等几类侵权类型另行设置侵权特别冲突规则。在设置中尤其要考虑“侵权行为地”应当如何界定才能满足特定利益和政策考量,还需要进一步论证附属连结点、共同属人连结点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这些连结点是否可以接纳。由于篇幅及能力有限,无法进一步就此展开论述。
五、结论
《法律适用法》的制定与施行标志着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的初步完备,立法完成之后,学界的研究重点应当转入该法的解释与适用上。与其他部门法一样,《法律适用法》的解释也需要注重体系思维的运用,还需要特别注重运用比较法的方法。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同样如此。
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侵权行为地”的不同界定方式背后具有不同的利益和政策考量。侵权一般冲突规则只能针对较为常见且主要的隔地侵权类型对“侵权行为地”做一个常态化的界定。其他侵权类型对“侵权行为地”的界定如有不同的利益和政策考量,需要由立法另行设置侵权特别冲突规则抑或通过例外条款授权法官在个案中矫正“侵权行为地”的常态化界定。因此,理想状态下的侵权冲突法体系应当由侵权一般冲突规则、特别侵权冲突规则与例外条款构成,三者相互配合形成一个严密的规则体系。《法律适用法》缺失了一些重要的侵权特别冲突规则,也未设置例外条款,故体系上存在重大缺陷。我国侵权冲突法体系的这一缺陷,决定了对“侵权行为地”的解释不宜盲目借鉴单义化的解释模式,也不宜借鉴复义化的界定并以“有利于受害人”原则指导选法的解释模式。
此种立法缺陷还直接影响到了法律解释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企图通过法解释的方法,利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导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与实践障碍,收效极其有限。如前所述,保护受害人抑或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促进司法经济等利益或政策考量无法在最密切联系的判断中予以体现,应诉诸立法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应当引入一条一般例外条款;第二,侵权一般冲突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宜界定为“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第三,补充一些必要的侵权特别冲突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