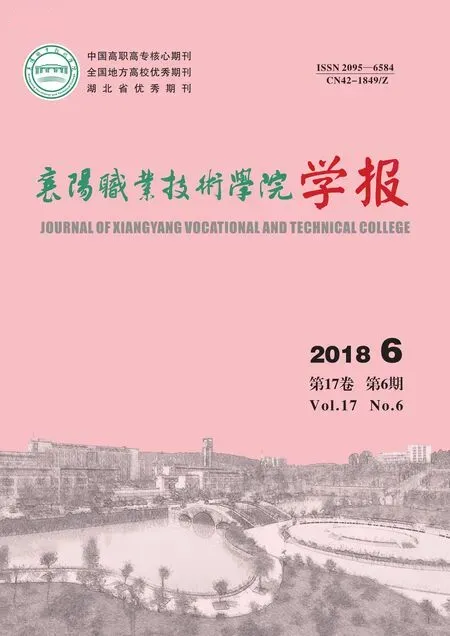从人物角色探析《极花》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郑冬玲
(郑州大学 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极花》自2016年发表之后就引起了评论界的热议,不少学者从最后的乡村的角度探讨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乡村的生存出路;一些学者则从作家贾平凹水墨画的写作角度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少数学者从性别叙事的角度分析当代被拐妇女的生存困境。笔者则以小说的人物角色设置为切入点解析在男性霸权话语中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其中也包含了被拐妇女的生存困境探析。
作为传统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物是行动的执行者,情节的承担者。同时,小说中人物角色的设置也体现出创作者的写作水平、创作意图,甚至隐藏着创作者的情感表达。《极花》是作家贾平凹根据自己一位老乡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小说中人物角色的设置体现出贾平凹对乡村未来的忧虑、对拐卖妇女行为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在传统社会道德体系笼罩下,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生存的压迫和扭曲。
一、女性中心角色:胡蝶
胡蝶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小说的主人公。贾平凹选择了让胡蝶在唠叨中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被拐卖前后的经历讲述出来。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胡蝶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传统社会道德对女性的压迫。胡蝶原本是一位从乡村随母亲来到城市的底层女孩,迫于生活压力,她初中便辍学在家。原打算出去打工为母亲减轻一些负担,不幸被人贩子拐卖到一个偏远落后的圪梁村。由于贫穷落后,村子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光棍,当地人便与人贩子做起了拐卖妇女的生意,从而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在当地人心中,妇女并不是完完整整的人,只是一种可以繁殖的雌性动物。他们认为妇女是可以买卖的动物,是男性的附属品。胡蝶自从被黑亮买到自家窑里,便失去了自由。为了防止胡蝶逃走,黑亮残忍地使用铁链像拴狗一样拴住胡蝶的脖子,把她禁闭在暗无天日的窑洞中。
然而对于胡蝶来说,她在黑亮家遇到的最惨无人道的男性霸权压迫还是两次群体性的男性侮辱。第一次是在胡蝶试图逃跑不幸被抓时,村里的一群男人五马分尸似地将其拖进窑洞,并且对其踢来踢去。在反抗中,胡蝶像皮球一样被人打得左冲右撞,胸罩也被拽去了,上身完全裸光,只能蜷着身子蹴在地上。紧接着,胳膊上,后背上,肚腹上开始被抓,乳房也被抓着,奶头被拉,被拧,被掐,裤子也撕开了,屁股被抠。[1]难以想象一群男人对一个柔弱的女子进行这般的侮辱和迫害,如此的侮辱和伤害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伤,而且还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恐怖点。在这样的男性霸权统治下,女性没有自己的生存话语,更没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这些男性像野兽一样扑向胡蝶,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丝对女性应有的尊重。还有一次就是黑亮在众人的怂恿和帮助下强暴了胡蝶,这又是一次充满血腥的迫害和侮辱。他们把胡蝶的腿压住,胳膊压死,然后再把头固定。接着他们就开始撕她的衣服,撕开了,再撕胸罩,奶子呼啦滚出来。[1]这样粗暴野蛮的侮辱性行为,即使发生在一个男性身上,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然而,一切都是发生在一个买来的外乡女子身上,胡蝶只是任凭那些男人们宰割的羔羊。试想在胡蝶受到一群男性的迫害和侮辱时,村子里应该也会有其他女人,即使不是参与者,也会是旁观者,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位女性村民主动站出来解救一下胡蝶呢?刨根问底还是因为在这样的乡村社会里,男性霸权的话语完全遮蔽了女性存在的声音。
小说中的男性霸权的话语世界对胡蝶的迫害不仅表现在肉体上侮辱和压制,而且体现在当胡蝶梦见自己被母亲和警察解救带回城市的出租屋时的所见所闻。持续的媒体关注、舆论压力、道德压力使胡蝶面对自己被拐卖的事实难以启齿,使她找不到工作。母亲只得托人给她找个婆家,准备把她嫁到离家较远的河南。在男权意识的领地里,女性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赢得女性贞操的同时即拥有对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2]被拐卖的经历使胡蝶失去了童贞,社会中强大的男性霸权话语并没有给她留下合适的生存空间。即使回到母亲身边,她似乎依旧找不到重新生活的勇气。
二、其他女性人物:麻婶子、訾米
小说中的麻婶子、訾米等都是胡蝶在被拐卖的地方认识到的朋友,她们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有着相似的坎坷命运。她们虽然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然而从她们的遭遇中也能感受到男性霸权话语世界对她们的统治和压迫。这些女性角色的设置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村子的落后和愚昧。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在一些偏远的落后乡村中,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思想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每个人心中,男性霸权的话语体系编织在每一个角落。
麻婶子十四岁随着母亲到一盐商家中做衣服时,就被那个盐商糟蹋了,后来就给那盐商做了小老婆。更不幸的是盐商的大老婆对她比较凶,什么事如果没做好,就让她跪搓板,盐商也不保护她,于是她生下一个孩子后就跑了。后来在山西遇到一个当兵的,比她大二十岁,对她还不错。麻婶子也为当兵的生了一个孩子,部队打仗,当兵的走了,麻婶子带着孩子逃荒,途中孩子得伤寒死了。等到嫁给半语子,生了个怪胎,半语子就一直虐待她。麻婶子会翦纸招魂,并且可以赚到一些生活费,依旧得不到半语子的半点同情心,对待麻婶子,半语子多是使用拳打脚踢。当发生走山时,麻婶子昏迷不醒,半语子竟然不是安心守护,或者找医生治疗,而是心意火燎地去给麻婶子挖墓。麻婶子脸上爬满了苍蝇和虫子,半语子也没有驱赶。半语子作为麻婶子的丈夫,从来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半语子是麻婶子的压迫者和统治者。纵观麻婶子的三次婚姻,第一次的盐商只是把她作为一个玩物,没有名分,也没有爱护;第二次是当兵的,对她稍微好点;第三次的半语子对她没有基本的尊重,对麻婶子打骂是家常便饭。麻婶子的一生都是生活在男性霸权话语的世界中,她好像对此已经麻木了,并没有反抗,有的只是顺从。
訾米是风尘女子,曾经做过妓女,不过心地不坏。后来也是被卖到黑亮所在的村庄给立春做媳妇。后来立春、腊八兄弟分家引起了争端,他们把訾米作为一项财产,也列入分家的清单中,原因就是当初买訾米的三万块钱是他们兄弟俩共同出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子,訾米却被当作了一种物品。面对被当成物的情景,訾米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当别人问她的意见时,她告诉众人自己并没有意见,后来訾米就像物品一样分给了腊八。面对胡蝶的关心,她告诉胡蝶自己只是个人样子。其实在那样的乡村中有一些人并不是人,不是外人给他们强加的,而是他们自己承认的。[1]小说中訾米在面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世界时,她发现了女性的反抗处于一个无物之阵中,她们的反抗是绝望的,命运几乎不会发生实质意义上的改变。于是她逐渐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甘愿作为男性使用的物品。
三、男性权威角色:老老爷
《极花》中的男性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男性权威占主导的文化世界。老老爷作为圪梁村的最高权威,对圪梁村人行使着精神和道德上的领导权。根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讲述: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 “统治”和智识、道德的领导权。[3]老老爷作为村里辈份最高的人,他肚里知识多,脾性也好。平时村里的人都会找他选日子,看天气,观星象,写吉字,编彩花绳,问建议等,他逐渐获得全村人的尊重和信仰,成为神一样的存在。正是在以老老爷为首的文化权威存在,男性霸权的话语在圪梁村异常活跃。胡蝶作为一个被拐卖到圪梁村的女性,起初一心要逃离这个地方,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她甚至坚持每天在墙上刻下一道线条,用来计算时间。然而在她屡次决定逃走时,老老爷都会以监视的方式或规劝的意味使她放弃自己的逃离念头,还经常用一种神秘的玄象启示胡蝶她就是圪梁村的人。例如他告诉胡蝶在圪梁村的夜空中可以找到属于胡蝶的星星,从而让胡蝶在内心深处接受自己被拐卖的事实,确证自己就是圪梁村的人。然而当胡蝶向他打听圪梁村的地理位置时,他却绝口不提,他不希望黑家买来的媳妇跑了,在某种意义上,老老爷也是圪梁村拐卖妇女的一个帮凶。
老老爷总是像上帝或者天神一样规劝指引,使胡蝶甘愿在圪梁村生活下去。后来,胡蝶怀孕了,老老爷又说:“这孩子或许是你的药。”[1]他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宿命的理论使胡蝶逐渐放弃了自己回家的愿望。这种男性的文化权威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每一个反抗者的血液中和呼吸的空气中。胡蝶最后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完全接受在圪梁村做黑家的媳妇。怀孕生子并不能成为胡蝶忘记回家寻找母亲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都是主体自身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胡蝶最后甘愿做黑家的媳妇,主动融入黑家,认黑亮爹是爹。这种无声无息的变化都是以老老爷为首的圪梁村男性文化霸权对胡蝶的思想意识的渗透和统治的结果。人在绝望的时候容易问苍天和鬼神寻找未来的启示,胡蝶只是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子,她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拯救自己,老老爷的神启式的规劝充当了苍天鬼神的功能。最终胡蝶不知不觉地臣服于老老爷的男性文化霸权话语下,放弃了自我,慢慢变成麻婶子,变成訾米姐。
四、结束语
贾平凹通过一位被拐卖女性——胡蝶的坎坷经历描绘出中国最后的乡村的生存图景。在这最后的乡村中生活的是数不清娶不到媳妇的单身汉,是一个又一个被拐卖到异乡的妇女,是知法犯法的村长和长者。而空气中弥漫着的男性霸权话语给这些贫穷落后的村庄又涂抹了一层厚厚的野蛮和残暴的色彩。以弱者的底色来渲染霸权,无视女性受辱,无视法律尊严,无视社会谴责,有站在男性立场上说话的嫌疑,但也能揭示出男性霸权是环境使然,时代使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