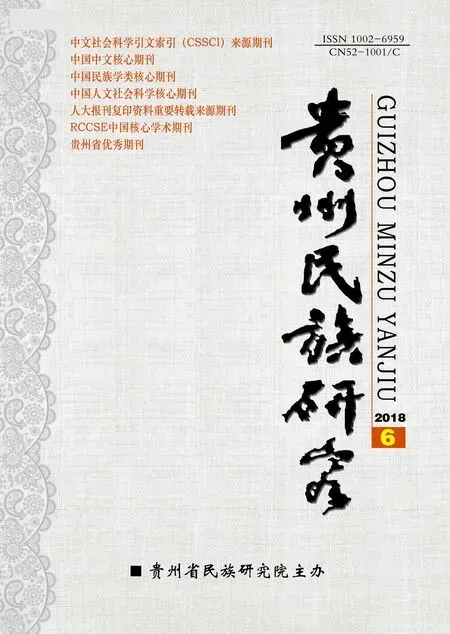全球化视域下民族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突破路径研究
高祥荣 张晨曦
(1.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2.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少数民族电影是一种因电影主体独特性而孑立于世界电影艺术之林的准电影类型,在少数民族电影的准类型下,又包含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电影和(类)少数民族作者电影等电影分支。我国少数民族电影曾有过辉煌的“十七年”,涌现了《刘三姐》 《阿诗玛》 《五朵金花》 《阿娜尔罕》等大批佳作。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电影产业的生存空间受到外部强势文化的挤压,在电影市场中逐渐流于边缘化。继2015年上映的佳作《狼图腾》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并夺获金鸡、百花最佳故事片奖后,2017年,一部《冈仁波齐》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火热又自然的记录片风格电影作品,不仅获得了总票房逾亿的佳绩,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商业电影史上一个令人惊喜的里程碑,而且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国内影评网站豆瓣上取得7.7分的同时,走出国门,在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获得了100%的新鲜度。这使不少电影创作者和电影文化产业从业者看到了少数民族电影在桥接商业化和艺术化上的独特优势,并重拾改变少数民族电影边缘化窘境的决心和信心。
一、少数民族电影主体的独特性
学界普遍认为,狭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是指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或血缘身份的电影作者,根植少数民族题材、通过少数民族历史与生活的情境和现实从而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电影。但笔者在反思以往少数民族电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这样的现象:如果严格按照作者身份等界定,即“一个根本,两个保障”原则(文化原则为根本,保障少数民族电影根植少数民族题材,少数民族电影作者是文化身份上的少数民族)来界定少数民族电影,那么在我国电影界几乎无这样的研究样本可言。
此外,还有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是,以电影作者的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来界别电影类型的分类方法,带有太过浓厚的作者论色彩,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否得宜,还有待商榷。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以根植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反映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少数民族视角拍摄的电影作品都纳入到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中来,而不必囿于作者的文化身份和血缘身份。既然对所面对的市场和受众并未进行界别,那么对电影作者的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进行限制,无疑是人为地割裂了相对于电影客体的少数民族电影主体上的整体性。在对少数民族电影研究时进行对概念严谨的把握和阐释是好的,但这种阐释应当置于当下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视域内来理解。全球化对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阐释做出了怎样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又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影响了学界的研究思路,是我们必须厘清的问题。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成为了学界研究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主流的框架。就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这一细分领域的研究来说,也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而要求我们在当前语境下理解并直面全球化对中国民族电影产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思考并采取与当前现实相匹配的抗御措施。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好莱坞影视文化作为外部强势文化以风驰电掣之势入主我国的文化商业市场,挤占了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赖以生存的空间,使其逐渐步入边缘化境地。与此同时,我国一些有志于复兴民族电影的电影创作者开始积极探索抗御这种强势文化的有效途径。不少研究少数民族电影的学者和电影工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要在增强少数民族电影竞争力,推动少数民族电影“走出去”的同时,在已有的电影市场的基础上培育少数民族电影的受众群体。换言之,少数民族电影学者和业者并非自愿在艺术电影的领域内自娱自乐,也不是对商业电影市场没有兴趣,同时从未放弃过对海外电影市场的追求,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期望与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达成和解,以求得少数民族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就要创作出让全世界电影观众都能够理解的电影佳作,不能对观影者的素质有所限制,同时这要求电影创作的主体不一定是囿于单纯具有民族血缘或民族背景的,而是能从少数民族视角出发,同时兼顾到广域上的电影审美、电影质量的专业电影创作者。
应该意识到的是,即使是作者具有少数民族血缘身份或文化身份所创作的少数民族电影,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作者个人的认识框架,艺术创作从来没有也不能避讳其先天的自我气质,一部分以“汉族视角”拍摄的少数民族电影可能的确流露出某种先天的审美偏见,但这种创作进程中的畸变也未必不是异质文化在交流和靠近中相互碰撞的表现,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这种畸变的存在,同时力图桥接无差别的受众和更具包容性的电影创作主体,以民族视点代替民族身份,锻造更多根植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品电影。
二、全球化视域下的少数民族电影文化产业生存现状
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引进大片、商业大片不断挤压着少数民族电影这类小众类型影片的生存空间。市场的残酷和冷遇导致了少数民族电影在生产环节上的恶性循环,优质少数民族电影的产出难度陡升。由于不良的市场预期,寻求投资对于少数民族电影来说特别困难,低成本投入又会极大程度制约少数民族电影在创作和制作上对规模和规格的追求,一些已经在市场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却常常因为成本不足而被迫放弃,在宣发上又给电影上映和票房带来不良影响。在商业运营上,释放创作者所有的设想困难重重,“边缘化”似乎成为少数民族电影难逃的宿命。
在这种状况下,依然有不少创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当做文化创作的富矿,借此为发力点,参与到全球文化市场竞争中,因为电影工作者都清楚地明白:有记录才有记忆。只有将本民族话语纳入到电影文化与电影工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证本民族电影文化的生存空间,才能将民族印记刻印在光影之间,才能掌握书写本民族历史的话语权,这种表达的渴望和焦虑同时化作压力与动力,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产业工作者对发展与突破的渴望。
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包罗万象,容纳了包括民族建筑、服饰、音乐、舞蹈等在内的许多令观影者耳目一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观赏性极强。同时,作为异质文化,这些充满独特风情的元素在被凝聚到大银幕上之后,其天然的奇观化和陌生化效果被凸显出来,对于国内观影者来说,文化上的亲近和地理上的亲切会使这些呈现在银幕上的旖旎景象内化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部分补充、代偿和认同;对于海外观影者来说,这些风情各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则更具独特的吸引力,是代表“东方”的文化符号。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并非没有“走出去”的能力,过早地断言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之路将越走越窄也太过武断。一些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佳作就证明了特殊、小众的题材只要摄制精良,未必不能和商业化良好结合。
以往不少少数民族电影不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异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而是在根本上缺乏审美性、观赏性和娱乐性,只是盲目地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填塞到电影之中,缺乏对于独特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群体价值和审美取向的探索,致使电影的审美价值不高,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也流于表面化。没有思想和价值上的思考、表达和交流,缺失了少数民族电影对主体的观照和对外部的视野。因此,在全球化视域下,将少数民族的故事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讲述,就成为了使少数民族电影传播得更为广远的关键。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这部影片将对文明殖民与族群身份认同的探讨置于历史与战争的母题之中,将少数民族故事置于大时代背景中,这样有利于观影者以外部视野来理解少数民族文化,达成对异质文化在价值层次上的共鸣和理解。
三、全球化视域下少数民族电影文化产业的突破路径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随着电影市场逐渐成熟,我们逐渐培育出了一批眼光卓越、审美成熟、能够与异质文化和解、具有多元文化包容力的观众。著名导演谢飞在评价《冈仁波齐》时,就发自内心地对这部影片和这部影片的观众感到欣喜:“这样一部没有任何明星的记录风格的文艺片,六天突破一千六百万票房,说明我们的市场和观众开始多元化了”。基于目前市场愈加成熟的现状,政策应该及时跟进,为国产电影尤其是少数民族电影的腾飞提供支持。
(一)对少数民族电影文化产业进行政策倾斜和支持
首先,国家需建立政策层面上的支持或调控,在审查、上映、融资及税收层面进行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制作方和发行方则需要把握现阶段已有的优惠政策,如充分利用国产电影保护月,推动更多制作精良的少数民族电影进入影院。在影院的建设上,要通过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协同支持建立特色民族影院线,在联系档期商业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上映,在满足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形成特色的少数民族电影放映线,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建设释放平台,让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实现其审美价值。由各级政府支持建设的试点影院应秉持灵活的排片原则,在实现商业盈利的前提下,释放出更多的场次以实现其保护少数民族电影的社会效益,同时根据所在试点和聚居地的民族需求,灵活地调节电影上映的深度与广度,如描述藏族生活的电影,在藏族聚居地的影院就可以适当延长上映档期。这样的少数民族影院要形成相对一致的选片原则和购票规则,以期逐步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观影习惯,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二)按照市场的思路进行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
同时,要注意接驳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市场的思路进行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制作、宣发、营销。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市场经济的思路,优化资源配置,树立科学的创作和生产理念,尽快“断奶”,实现少数民族电影的市场化生存。
这首先需要电影质量过硬,影片是电影工业的最终产品,影片的质量除了会影响档期票房的高低多寡,还会衍生出一系列媒介产品所具有的边缘效应。比如对电影作者的个人名誉进行加持或减损,对电影周边及对电影拍摄地的旅游服务业产生一定影响。在全球化视域下,电影不仅具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艺术消费价值,还具有争夺意识形态高地,抗御外部价值侵蚀的作用,因此具有优秀传播力的电影佳作的产生备受期待。《狼图腾》和《冈仁波齐》已经证明了少数民族视点的电影可以产生精品,只要深入到少数民族最为异质的文化中心,就能使其奇观化和陌生化的民族风格、中国风格衍生出巨大的光晕效应,取得艺术与商业上的双丰收。其次,电影的营销和宣传、发行也均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操作,通过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积极利用政策倾斜和优惠,找到宣传和发行的爆发点,进行多层次、多梯队的配置,推动投入成本效果最大化。
(三)培育全球化视野下少数民族电影传播的主客体
关于少数民族电影细分市场的完善,还要注意继续培育少数民族电影传播的主客体,通过培植有能力、有意愿以本民族视角叙写本民族故事的电影创作者和鉴赏力强、包容性强的电影受众,继续推动少数民族电影传播的完整化。
当前需要培育和挖掘有能力、有意愿表达自我,叙写民族故事,传播民族文化的民族身份、民族视点的优秀导演。在全球化浪潮中,电影成为资本角逐的战场,少数民族电影多是小成本、小制作,有与大制作一决高下的拍摄水准,却常常缺乏与资本角逐的能力,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和电影协会要积极搭建平台,给予有意愿的电影创作者表达的机会,鼓励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携作品参与我国各地的电影节,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要帮助和支持他们参与国外电影节的评比,适宜上映的要推动影片上映。对于已经比较成熟的电影受众,在满足他们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的同时,要有引导性地推动他们接触优秀的异质文艺作品,培植他们的观影习惯,培育一代更具包容力、鉴赏力更佳的电影观众。
(四)对少数民族电影文化产业的特征进行深刻把握
少数民族电影业者要对电影文化产业的特征进行深刻把握。电影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中的重工业,具有工业与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作为最终产品的电影,既是工业产品,也是文化产品。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收获商业效益。少数民族电影生发于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中,依托于异质文化,具有浓郁而独特的风情,又能承载史诗叙事,通过电影文化产业的加工与精练,能够聚合历史、政治、商业的文化张力,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化生产潜力。面对尚未被窥得冰山一角的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富矿,要戮力挖掘这些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并通过顶层设计与科学的资源配置的协同,创作出趣味高尚、制作精良的少数民族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