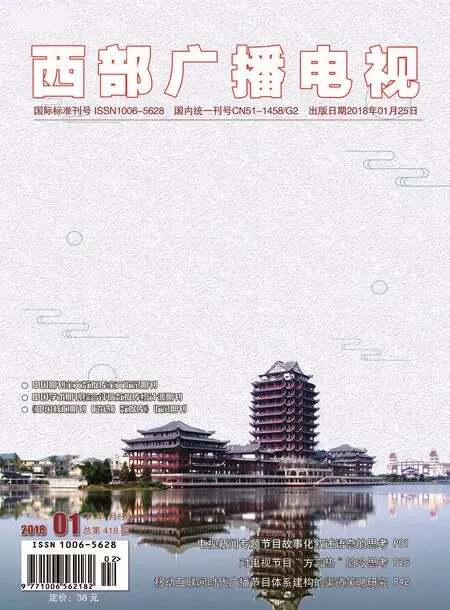漫画式字幕迎合大众审美范式的意义
——以第五季《爸爸去哪儿》为例
王甦民
1 漫画式字幕的形成
《爸爸去哪儿》中,五位明星父亲带着自己的子女要一同度过两天一夜的旅行。究其形式,《爸爸去哪儿》是一款典型的户外游戏类真人秀,以“真人”为表现线索,以游戏设置为条件,通过“人物”和“任务”两大模块的随即碰撞,生产大量的笑点。
漫画式字幕以夸张的文字注释配以漫画符号为主要形式。这些被漫画语言包装过的符号,具有带动人物的心理活动、发掘潜在的动机、使演员的情直观化等一些作用。漫画式的包装手法,制造了更为轻松有趣的娱乐氛围,淡化利害关系,柔和冲突,为节目中的竞争、对抗乃至暴力环节增加一层诙谐的感官色彩。
在受众的视野里,“看见它发生”的真实感是真人秀栏目兴趣的主要来源。在“真实感”诉求方面,真人秀是在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而纪录片则可以说是“虚构”的“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尤其到了后期剪辑部分,涉及更多纯粹的主观部分,那“虚构”的意态更加明显。《爸爸去哪儿》的字幕设计提供了很好的“虚构”形式,通过对字幕的漫画式编辑,编导可以肆意放大、扭曲、变化记录影像内角色的情绪与性格,创造艺术张力。例如,人物愤怒的说话就用红色熊熊燃烧的粗体字表现;泄气地说话,就用蓝色的冰块状的歪歪斜斜的字体。
2 网络语境下的字幕设计
罗贝尔·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中说到:“不用激动人心的画面去打动人,而要用画面关系去打动人,这些关系将使画面变得既生动又感人。”而在真人秀栏目中,画面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电影语言表述得那样完整,反而更依赖文字、旁白、特效等手法来连接。《爸爸去哪儿》漫画式字幕的运用是该节目传情达意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们天生具有引导性和隐喻性,引导观众从此画面联想到彼画面,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切换身份,不自觉地完成了与节目画面“不言而喻”的共鸣体验。
漫画式的字幕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一种无厘头式的幽默,即是个性的解构式思维。通过自由的想象与多元文化的拓展,以碎片化的文字信息对社会文化图景进行另类观照。而这种纯粹的碎片化或者解构思维,与当下网络语境的形成息息相关。
《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漫画字幕的制作者即是语意符号的开发者,他们理解网络语言的构造和形成规律,通过主观的创造,完成了真人秀中的字幕设计,而这些字幕内容因其符合网络传播的规律,又再一次回到网络媒介中,被更为广泛地传播,形成了一条网络语言演化的生产链条。
3 当下大众审美范式的探求
3.1 娱乐中的无意识
尼尔·波滋曼在著作《娱乐至死》中认为:“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韩国版本的《爸爸我们去哪儿》中使用了大量的音效,其中包含了模拟现场观众的“笑声”,作为环境“笑声”出现的方式源于美国的肥皂剧,电视观众会被这种笑声引导而发笑。中国版本的《爸爸去哪儿》经过几年的探索,经过本土化改造和去俗化处理,让中韩两版迥然不同。例如,在后期处理中基本取消了环境模拟笑声,而放大了节目中参与者的真实声音,并极大程度地利用字幕特效产生联动效果,同样达到了引导观众趣味的作用。
当然,在节目制作中一贯使用的无意识化处理同样被应用。在《爸爸去哪儿》中,总会设置让小朋友组队去当地老乡家“找食材”的环节,幼儿的童真和农民的纯朴相碰撞,使得“找食材”充满了普世意义的理解和关爱。再比如,在画面中出现的表现乡村美景的空镜头时,编导有意加入了诸如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溪流、平静的夜晚等字幕,渲染这种无意识概念。受众观看这些画面和文字会形成内心向往的趋向性,更容易代入真人秀营造的氛围中。
3.2 语言符号的多义性
《爸爸去哪儿》的漫画式风格有诸多优势和好处,但是语言符号表意上的随机性过于强烈,对于意识上的作用有种种不确定性。因为,大多数的字幕是用于阐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尤其是描述孩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用字幕限定孩子的内心世界或者刻意升华,就可能形成一种误导,即在特定的相似环节上,年轻的家长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孩子的想法和电视节目中的虚拟语境一致,这种误读可能会导致新一代的年轻家长与孩子沟通产生更多的障碍。
蔡元培说艺术要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诚然,通过电视播出的《爸爸去哪儿》实在存在这种“寓教于乐”的可能性,当感性能量作为一种传播内容时,传播者却人为地限定了传播符号的能指,接受者的选择性解读也就相对被弱化。这其中存在的必然逻辑关系导致了传播者必须在符合一般逻辑的情况下进行相对合理化的创作,即在规格情理内的创作才是可行的,才是长久的。
3.3 娱乐场域和大众认同
窄播时代的来临,不再是受众盲目地切换手中的遥控器,相反是受众有选择地通过网络、机顶盒来定时、定位收看自己想接受的节目。与此同时,精英文化正在向大众草根文化场域转型,即纯粹的娱乐化。漫画式字幕利用这些诙谐幽默,有别于传统风格的表意形态,贴近互联网语言的形成规律,符合大众的审美认同。
“去影视化”的影像观赏模式与“草根文化”调侃式的游戏文化空间相融合,漫画式的风格填补了真人秀栏目在表意上的客观需求。其虚构的合理性、指引性及限制性都恰到好处。因此,大众娱乐审美的视觉观念在游戏化的语言形态上得到了确立。
然而,真人秀栏目的火热也同样催生出了诸如《中国新歌声》《中国梦之声》《我是歌手》等一批过于同质化的节目,哪怕是在节目结构上有所创新,但是其节目内涵也难有新意。大众娱乐文化场域,一方面是由于大众自我引导自我救赎的产物,另一方面娱乐本身也在有意识地创造语境,大众认同的不同程度会低于当前的语境空间,从而在意识上引导大众娱乐兴味。
4 结语
可以推断,在未来的广播电视产业中,越来越多的满足大众审美趣味的表意形态会被不断地填充在屏幕之上,手法也会更为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人应该以更加多元的艺术理念、开阔的文化视野、审慎的批评态度对待这些解构性的游戏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和思考方面不至于落俗、媚俗,在评判电视节目优劣时不至于跟风、盲目。希望有更多的适宜当下大众审美范畴的优秀电视作品可以被接受,使观众在欣赏中得到喜悦欢欣的同时,接受节目传递的正能量。
[1]刘宇清.叙事元素在韩国真人秀栏目中的运用[J].文史博览,2012(10).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刘洁.纪录片的虚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言爽.浅析韩国明星综艺节目在中国网络的传播[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5]孙文杰.浅谈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的影响[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