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枝雀静
草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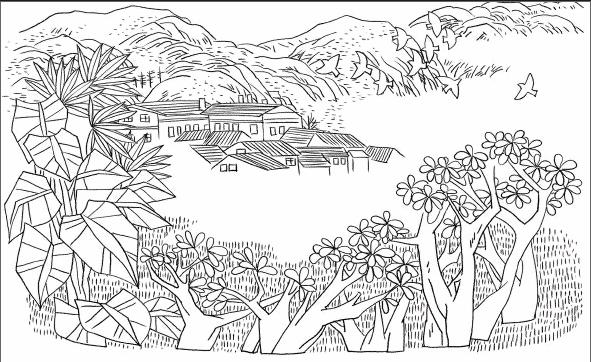
冰枝一点也不喜欢爬山,认为那是愚蠢而体力过剩的人所做的事。可这天早晨与以往不同。老板娘一直在谈论山,说旅店后面的山所通向的山顶平原,人迹罕至,野花遍地。
我没有去过那里。可总有一天,我是要去的!老板娘以尖利的嗓音向所有客人宣布她的爬山愿望。这是七月里的一天,城里酷暑难耐,他们是来此地避暑,而不是来爬山的。他们不会对爬山感兴趣,更不会在乎这个瘦高个女人到底说了什么,她姿色平平,穿着上也无动人之处——除了冰枝。
冰枝对这个往花坛上种植塑料郁金香的女人本没什么好感,可她描述爬山愿望时的神情打动了她。
怎么才能爬到那上面去?冰枝跟着那个女人来到厨房间,压低了嗓门问她。女人笑了,以为她是开玩笑。她不相信冰枝会去爬山。就算真的爬到山上去,不多久就会下来的。
你爬不上去的。
天气太热了。
就算上去了,也下不来。
别费劲了。
女人一脸嘲讽地望着冰枝,似乎很难容忍别人抢在她之前上山,特别是这个女人看上去并不比她强壮,甚至还有点弱不禁风。
怎么才能爬到那上面去?当冰枝再次向那女人发出询问,女人才感到冰枝可能是来真的。
只有一条路,一直往上走,就到了。
女人垂头丧气地望着她,希望冰枝能够改变主意,不要去爬什么山。根本就没有什么山顶平原,那全是道听途说的。
要是爬不了,就赶紧下来啊——女人望着冰枝的身影急速地往山林的方向移去,慌忙喊了一声。这天余下的时间里,这个瘦高个女人再也做不了别的事,除了不停地往山上张望。
冰枝已经在山上了。她为自己这么快就能进入山林的腹地,感到难以言说的激动。山上的世界确实与山下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除了眼前的树与灌木丛,她什么都看不到。身上的汗自上山后一直没有停过,那些黏糊糊、湿漉漉的液体,虫子一样在体表蠕动着,又痒又难受。
她小心翼翼地爬上这一座,又从另一座下来。她不断回到峡谷,溪水也留在谷底等她。她知道爬到山顶并不容易,可没有想到会这样不停地上上下下,给人希望的同时,又让希望破灭。
刚才,在旅店看到郁金香的那一刻,冰枝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个人的身影。她很不愿意自己想到她。这或许是她不想留在旅店的原因。那些塑料做的永不凋谢的郁金香仿佛有一种魔力。
冰枝在镇上有个房子,那屋子后面砌有一个长方形花圃,种着郁金香、月季、芍药、绣球花,还有那些被风吹来的杂花杂草,一年中有三个季节都在发疯似的长。那个叫雀的女人好像也是被一陣风刮来。母亲死后不久,继父就把她领进门,说是在汽车站门口捡的。
哦,一个捡来的女人。
现在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冰枝想起这个叫雀的女人是她继父的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说话。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其实是很难弄的,你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雀和继父之间谈不上有多好,但从不吵架。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怎么能指望她学会吵架呢。
后来,继父死了。车祸。从惨祸发生到断气,不过几分钟。她还没想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个四分五裂的身体就被投进焚尸炉里,化作一股浓浊的黑烟消散掉了。冰枝觉得悲伤,不是为了继父死亡的事实,而是他的死状——身首异处,浑身是血,被人发现在路边的灌木丛中。继父活着时没享过一天福,死亡却让他一劳永逸地获得解脱。冰枝始终无法忘记的是他的死状。
继父死的那年夏天,满院子都是那个女人种的绣球花,浮艳硕大的白花,蓬乱地盛开一地,给人脏兮兮的感觉。
自从女人住进这个房子后,就不停地种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
继父死后很久,连留下的气味都消失殆尽了,女人还住在那个房子里,还在种花,更加勤快地培育新品种。
冰枝喜欢那个房子,推门出去就是河。哪怕是一条已经遭到污染的河。
冰枝想,那房子是我的。它是我的。
后来,她果然将它弄到手,可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此刻,冰枝在一块山石上站定。那来自胸腔内的跳动,扑通扑通——像一面蒙着人皮的鼓,不断发出某种单调的指令。
旅店已经隐在山的那边,看不见了。但如果往回走,不出二十分钟,她就能回到出发的地方。那么,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她就可以躺在床上安逸地度过。什么也不用想。只是那些郁金香,她怎么也无法将它们从脑海中抹去。它们是假的,即使真的郁金香也给人虚假的感觉,鲜艳蓬勃,所向披靡,可全是假的。生命就像一件巨大的无处不在的赝品,充满着嘲讽。
那个叫雀的女人在屋子里绣花,继父死后,她干脆以此为生。冰枝去那里找她,告诉她自己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她和她的母亲都在这里住过。女人听了冰枝的话,点点头。冰枝不知道女人有没有听明白她的意思。女人不说话,一个不说话的女人真是可怕。
冰枝很想把她赶走,像小时候赶一群鸭或一头牛那样,把她赶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有时候,冰枝的脑海里也会有涌上与此相反的念头。如果那女人变成一个正常人,和她说说笑笑,她就能说服自己让她留下。
当赶走的念头起来时,冰枝再也无法说服自己。
你在老家还有老公的是吧?
有没有孩子?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在等你回去是不是?
有一天,冰枝挑衅地说。
冰枝差点说,你现在可以走了。赶快去找他们吧。我的继父死了,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你了。冰枝在等机会,最好是她主动离开。那就不用担什么干系了。她已经想好怎么改造那个房子了,只等那个女人一走,她就动工。
冰枝是撑着伞上山的。她的装扮好像是去逛公园,而不是爬山。从灌木丛中钻进钻出的时候,她也撑着伞。树枝与伞面摩擦发出的声响给她带来某种庇护感,她对山以及一切可能威胁到她的事物,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
她在山上走了太久,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虚脱,死在这山上。太阳并不直接照在身上,她的身体及四周并没有一点阳光及其碎片的影子,可炎热却像屉笼里的蒸汽,让她身体里的汗液不断地往外冒。endprint
群峰在身后发出齐整而无声的轰鸣,推着她向前。
除了走下去,走到那山顶之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当老板娘开始说山的时候,冰枝并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她的声音和别的声音混在一起,给人一种尖利、不那么舒服的感觉,就像她的身体给人的感觉。一种硬邦邦的形象。一件看不出质地的白色紧身低胸上衣,下身是红色一步裙,细高跟凉鞋。冰枝担心那鞋子在走动时忽然折断,豆芽菜似的身体也跟着遭殃。
有些人光是听声音,就能作出判断。可那个不发出自己声音的女人永远不在此列。
有一年继父的祭日,冰枝做了几样小菜,带去那个房子里。那是黄昏,房间里暗着灯,女人坐在窗前微弱的天光里绣花。女人抬头望了她一眼。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既不像她母亲,也不像她认识的任何人。
女人和这个镇上别的女人都不一样。唯一的解释是,她不属于此地。所有的行为都在表明她不过是暂住于此,随时可能离开。可她让这个房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女人身上某种东西的折射。
冰枝看不见女人的内心,可她看得见房子里发生的一切。她重新喜欢上了这个房子。她不断地回去,好像只是为了看看它,她放心不下它。同时她想象着有一天,当自己搬进去后会怎么样。
继父生前并没有和女人登记。这就是说,女人的一切并不受法律保护,冰枝随时可以赶她走。只要她下定决心。
事实上,不止一个人建议她这么做。
谁知道女人将来会不会把什么儿子女儿的都接来。毕竟人家有事实婚姻嘛,要是拆迁了,问题更多。
冰枝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
不断有路标出现在山石上,粗壮的树身上也有各种标志。“三哥的营地”这几个字不断出现,那后面所跟着的箭头,指向草丛、岩石,或洞穴。三哥是谁?三哥的营地是个什么地方?
冰枝被炎热弄得晕乎乎的头脑,仍残留着那个女人的身影。有一刻,她陷入疯狂的幻想之中。那场谈话,她酝酿了很久。数次搁浅,又重整旗鼓。各种细节都考虑到了,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她要把这个事情搞定,不能再往下拖了。
女人的脸从往事的显影液中浮现出来。一个与她毫无关系的女人,一张呈隔绝状态的脸。那张脸甚至没有明显的皱纹。也没有表情。她吃饭,走路,绣花,做所有的一切,却毫无表情。
有一刻,冰枝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陶土面具。一边是完整秀美的脸,有眼睛、鼻子与优美的唇;另半边的鼻子与眼睛成两个不规则排列的洞,嘴唇则开裂成一个狭长似深渊般的窟窿。秀美与惊恐万状共同呈现于同一张脸上。
冰枝不敢再想下去。
那个叫雀的女人好像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她知道她在想什么。当冰枝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事情的时候,她只是说,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冰枝没有问一点时间是多少时间。她什么也没有问。女人的神情把她震住了。
这个不喜欢说话的女人,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她在等待她。等着她说出那些话。她知道她会说的,那是迟早的事。
那一刻,冰枝忽然感到后悔。她想把那只伸出去的手,缩回来。她宁愿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
她终于在一棵树下,停步。短暂的休整似乎打开了她体内对炎热和疲累的耐受空间。一个新的耐受系统已经生成。一股热烘气和泥土深层腐殖土的气味在她低头时,冷不防窜进鼻孔里。
新鲜的艾草的气味混合着软绵绵的热烘气,包围及推搡着行走中的她。草叶摩擦着她的小腿肚、脚踝,痒酥酥的,这是在野地里经常行走的人所熟悉的感觉,让人产生警觉,却知道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危险。
艾草的氣味消失不久之后,冰枝看到了野果。那些星星一样闪烁的覆盆子出现在道路右侧,她几乎是狂喜似的冲过去,抓过来塞进嘴里一阵乱嚼,汁液在口腔内流淌,甜美而芳香四溢。有些甚至来不及咀嚼,就被囫囵吞下了。它们个头太小,根本用不着咀嚼。它们还不够她塞牙缝呢。她不停地采撷那些果子,往自己的嘴里送,她感到饿,很饿很饿,不仅是肚子,脑子里那种晕乎乎的感觉更加强烈了。她明白自己是饿着了,临近中午才出门,什么食物也没带。
那些野果使得她的肚子成了一个无底洞,怎么也无法填满,不仅无法填满,其实是更加空了。野果唤醒了身体的饥饿感,而她根本无法满足它——此刻她的进食行为更像是一种哄骗。
她很快就把枝上的果子摘光了。除了那些青涩的,有明显虫咬痕迹的,不能吃的,其余都被她席卷一空了。吃光了。她舔了舔嘴唇,仍然觉得不满足。根本没有一点刚刚吃过东西的感觉。
饥饿——这是她出发之前没有想到的。她好久没有这么饿过了。她双眼模糊,热望着道路两旁的灌木,充满希望地向它们走去。没有风,所有看不见的果实在盛夏里成熟,是炎热催熟了它们,无风的密闭状态促使它们由红变紫,干燥,皱缩,汁液丧尽。她闻着那种气息,浓郁黏稠的甜腥气,在深厚密闭的林子里静静地发酵。
但她没有感到更饿。她的身体对饥饿有了耐受力。当双脚机械地前行时,那张被炎热所包裹的脸似乎因为认命,而变得更为冷静了。
那个女人叫冰枝给她一点时间。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冰枝很快就明白她在说什么。她病了,或许很快就要死了。冰枝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她不去医院,也不吃药。看上去,似乎并没有遭受太大痛苦。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女人的伎俩。这种不太说话的女人,你永远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每隔一段时间,冰枝便去那里看她一下。她们之间根本无话可说。三个月过去,那个女人才开始消瘦下去。衣食住行有些费劲了。冰枝无能为力,又不能像女儿伺候母亲那样去帮她。她做不到,也不可能。每次,她去那个房子,留下一点食物就走。她去得越来越勤,但只限于提供食物。她不能让自己表现出过分的关怀,这显然与她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不符。
那是一种煎熬。这个陌生女人的存在于她是一种煎熬,好像要死去的那个人不是她,而是自己。
太热了。汹涌的热流从四面八方拥来,将她包围。慢慢地,她把饥饿忘了,疲累和热重新主宰了一切。她气喘吁吁,体力上感到难以为继,却没有停止脚下步伐。她要走下去,如果走不动,那就爬,爬也要爬到坡顶上。endprint
当那阵气味出现的时候,她看到蝴蝶从树丛里飞出。它们不是从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飞出,而是从树的体内飞出。所有树在瞬间敞开了自己,放出了蝴蝶,那些和树身的颜色一样的蝴蝶。
蝴蝶带来了气味,她从未闻过这样的气味,浓郁黏稠,充满幻觉,好像来自树木。这片林子里所有的树都散发出自己的气味,或许是同一种气味,或许并不是,现在这些气味汇聚在一起,几乎铺天盖地。她贪婪地闻嗅着,张望着,一点也搞不清楚那些树、蝴蝶和气味是怎么回事。她在寻找花。可那些树太高了,枝叶密集地伸展着,交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的来路与去处。
没有看见花。
那年冬天到来的时候,院子里的花几乎都枯谢了。冰枝开始和一个在人民医院上班的男孩约会。有一天黄昏,她路过那个房子。她让男孩等在外面,自己进去了。女人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对她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外面很冷,房间里却很暖和,有一种被精心保存下来的暖。冰枝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房子,给她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女人忽然说,外面很冷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病弱者的虚无缥缈感。冰枝点点头,想起男孩还在外面等他。那个阳光俊朗的男孩儿,有一双白皙修长的手,外科医生的手。她喜欢那双手,那么干净,好像永远也不会沾染人世的污浊。或许,他会成为她的人生伴侣。她要让那个男孩儿成为她的人生伴侣。这是她站在女人床边忽然想到的。
女人快要死了,而她将拥有一个美好的伴侣。这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它不停地用一件东西去置换另一件,上天要用一个伴侣来置换掉这个女人的生命,因为这个女人的生命是一种无用的、即将被淘汰掉的东西,一种用尽则废,不值得怜惜的东西。
当初,女人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那时候,冰枝还没有想到死亡。死亡不是用来想象的,它是一种最平淡、最理智的事实。每个人都知道它,但认识它的机会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
冰枝在树下行走。几乎看不见路面,它们被过去时间所降下的树叶覆盖住了。她在那上面走着,整个人轻飘飘的,一种体力耗尽的虚脱感,不断有蝴蝶成群结队地从那树丛里飞出,扇动着周遭的空气,像是平地里刮起一阵风。她并不能完全看清楚那些飞翔的精灵,好像它们不曾拥有清晰的飞行路线,而是在一闪一灭中快速藏匿了身影。
一段陡峭而窄的上坡路。黄泥地,裸露的树的根系,像人类的骨头,已经被雨水洗得泛白。她抓着一根灌木的枝,借助其力量,挣扎着上行。每爬过一段坡地,她便感到自己离那个地方不远了。或许下一个山顶就是所有山峰的顶部,此行的目的地。
当痛得最厉害的时候,那个叫雀的女人用一种奇怪的方言哭喊着,表情抽搐,连声音都变了。无疑,女人在向她求救。她买来止痛片。那些针剂或药丸在进入女人的身体后,暂时起到缓解作用,可当药效一过,更大的疼痛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折磨她。
冰枝能做的只有观望,就像隔着玻璃幕墙看外面的世界。最后,她连观望都厌倦了。她不想再管她。她厌倦透了,甚至感到后悔。为什么答应她的要求。她老想象那种痛,好像它们已经长到自己身上。总有一天,它们会从她的体内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当疼得最厉害的时候,冰枝以为女人很快就会死去。一个人不可能无止境地痛下去。她会死的。肯定会的。
她盼望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其实,女人需要的不是止痛片,而是结束生命。不怀一点希望,没有任何留恋地,让一切终止,永远结束。
可也有不痛的时候。来自死神的短暂的怜悯似乎让她看到了希望,一种没有任何用处的希望。那些希望在绝望的夹缝中生长,最终被吞灭。
冰枝臉上通红,浑身赤热,像一条吐着红舌头的狗,不住地喘息着。炽焰在她体内燃烧,蒸发掉了最后一丝水分。没有风。连空气都在积聚燃点,以期完成最后的自燃。
直觉告诉她,快到了。那个对方就在不远处,随时可能出现。她腿脚颤抖,身体蜷曲,几乎躺倒在地。周遭只有树,无数的树木,倾斜的树身好似要向她压来,将她埋葬在这热浪滚滚的地方。下一秒钟,她就会消失,化为乌有。
而世间一切如故。
在那种煎熬几乎抵达峰巅的时候,她的耳边似乎传来一个声音,模糊的翅膀的拍打声,遥远而富有节奏。她聆听着。那一刻,她的视力与听力都变得无比迟钝。可她似乎看见和听见了一切。
冰枝感到自己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离天空和云彩非常近的世界。视野所及是白花花的阳光和一片野花漫漶的平原,望不到尽头。可并不感到热。她已经丧失了所有对炎热的感觉。她一生所有的力气都在这次爬山中耗尽了。
太阳像一个无知觉的圆球悬在高处,无时无刻、沉默不语地看着她。她瘫坐在地上,伞被丢在几步之遥的地方,已经散架了。
渐渐地,那声音化为清脆的风声来到头顶上空,持续轰响着,最后弃她而去,将她丢在这白花花、空无一人的山顶平原上。
干燥的尘土气混合着草木的甜腥气扑面而来。冰枝挣扎了几下,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着那条平坦的道路尽头走去。
冬天最冷的时候,女人停止了进食。她已经吃不下,也不想吃。她干瘦的身体成日缩在被窝底下,早已丧失人形。那些疼痛在把她弄得形销骨立后,便弃她而去,去找别人了。她的眼神变得寒冷,安宁,无所畏惧。有时候,她甚至会莫名地微笑一下,对着某个对方愣怔上许久,好似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毫无例外——那神情简直让人恐怖。冰枝不能问她此刻在想什么,人之将死,到底是何种心情,感到害怕吗?
她第一次知道这个女人来自高原。那里夏天不会很热,冬天也不会很冷。晚上八点钟还有阳光照耀。那里的人普遍都皮肤黝黑,眼神明亮。密林里的大叶茶自由生长没有污染。老虎躲在山坳里。小孩长大后都要出门远游。
关于那个地方更多的事情,女人已经没有力气说出。
她躺在床上,四肢展开,努力保持着最后一点人的样子。好像她所承受的一切,只是为了体验一个人最终所要体验到的东西。她马上就要熬过去了。一切都会过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即将抵达的胜利之境,让她面带微笑,一种不明所以的笑,好似回到童年高耸的山岗上。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