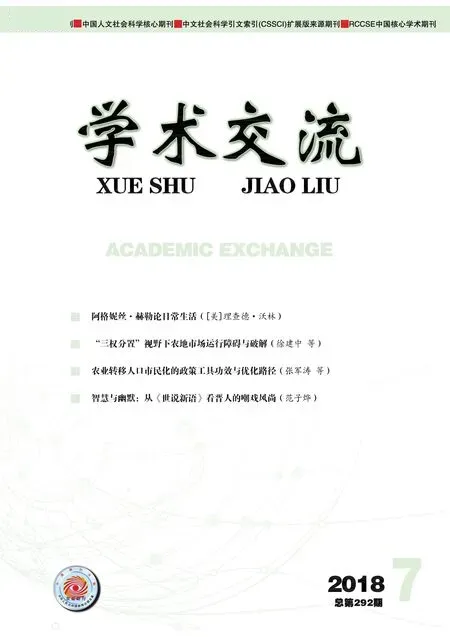从笪重光《画筌》到汤贻汾《画筌析览》
孙 超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清初画家笪重光(1621—1692)*笪重光生年,本文采闵靖阳《辟笪重光生年之谬》说,见《书法赏评》2016年第3期,14页。,著有《画筌》,骈体文六千余字,无章节,阐述作画的构思与技法。“画筌”出《庄子》“得鱼而忘筌”之典。笪重光认为《画筌》只是实现独立创作的途径,学成后应当有所超越。这既是自谦,也是文人画自由精神的体现。《画筌》得到同时代王翚(1632—1717)、恽南田(1633—1690)等大画家的赞许,并有评语穿插其间,可见当时的广泛影响。嘉道间画家汤贻汾(1778—1853),与笪重光结缘于丹徒,以精神为契合,对《画筌》产生兴趣,析为两卷十则,每则后复独抒己见,成《画筌析览》一书。在继承《画筌》思辨精神的同时,又强调秉持夙慧与独立创作,在画学上有所突破。兹参以相关史料,阐释从《画筌》到《画筌析览》的精神传承与理论嬗变,进而探究汤贻汾的画学思想。
一、汤贻汾与笪重光的精神契合
汤贻汾作为恽南田之后常州最著名的画家,生平及绘画创作,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清史稿》云:“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以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惟汤贻汾、戴熙二人。”[1]评价是非常高的。《画筌析览》是汤贻汾结合自身创作实践,对古今绘画理论的总结和提炼,在清代画史上亦有一席之地。汤贻汾选择笪重光《画筌》作为立论之基,是因为二人地域、身份、心灵皆有共通之处,是一种精神契合的产物。
(一)结缘丹徒
笪重光是丹徒人,汤贻汾曾在丹徒为官。嘉庆五年(1800)四月,世袭云骑尉汤贻汾任京江营守备(正五品),驻江苏镇江府城丹徒县圌山寨,翌年春卸任。官丹徒一载,汤贻汾遍访精法楼等名胜,与当地文人王文治、冯锡宸、顾堃等往来密切,多有唱和,广泛参与了当地的文化生活。笪重光是丹徒著名画家,汤贻汾得见其真迹,大为称许,对其绘画理论产生了深入探索的兴趣,当在情理之中。汤贻汾《画筌析览自序》说:
先生丹徒人,名重光,字在辛,自号江上外史。顺治壬辰(1652)进士,官佥都御史。予向居其乡,多见真迹,皆神与古会,非深入画禅,能道此中三昧耶?嘉庆甲子(1804)上巳,雨生汤贻汾识。
阐述了与笪重光产生地域因缘,并选择《画筌》作为立论基础的心路历程。笪重光为丹徒人,罢官后又归隐于此,故当地多有画作流传。汤贻汾宦游丹徒,有缘得见真迹并悟其真意,是以《画筌》立论的直接原因。
(二)官员画家
汤贻汾与笪重光,有着画家与官员的双重身份认同。《画筌》介绍的技法,无一不是笪重光在创作实践中总结而来的,《画筌析览》更是汤贻汾绘画经验的升华,笪重光与汤贻汾达成理论共识的首要基础,便是画家身份的契合。秦祖永《桐阴论画》列笪重光为“逸品”,赞赏其对笔法与墨法的精妙把握:
笪江上侍御重光,风流儒雅,跌宕多姿。笔墨二字,阐微入妙。闲写山水,高情逸趣横溢豪端,良由鉴赏精也。肥不俗,湿不溷,视世之有笔无墨,有墨无笔者,相去奚啻霄壤。
笪重光山水有逸趣,笔墨和谐,远超时俗。然而秦祖永指出,笪重光画作精妙,也源于高超的鉴赏能力。笪重光精于画学,下笔之时便有成竹在胸,而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也完善了笪重光的绘画理论,这便是画家身份与画学思想的相互作用。汤贻汾选择笪重光,画家是二人之间第一重身份认同。
画论多为擅画者阐发,单纯的画家身份,不足以让汤贻汾在历代画论中,选择《画筌》作为立论之基。共通的社会角色,即官员身份,是二人的又一身份契合点。汤贻汾袭爵后,由京口守备,仕至浙江乐清副将(从二品)。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一云:
世称武臣能诗者,曹景宗也;武臣能画者,李思训也。余友汤雨生参帅兼之,故曾宾谷侍郎有《汤生歌》赠参帅,云:“班超佣书投笔起,丈夫当效傅介子。汤生年少一书生,今作百夫之长耳。相从将军泛楼船,暮归蛮府飞华笺。八分书似刁斗铭,千首诗过交河篇。日南半壁天海空,山川形势全在胸。兴来挥写着绢素,咫尺万里乘长风。武夫中有汤生否,学士文人犹落后。可惜汤生好身手,但与吾侪争不朽。偏裨何日树功勋,金印悬来大如斗。”读此诗,可以想见其风度。赠此诗,参帅犹作骑尉时也。
广东布政使曾燠的《汤生歌》,作于汤贻汾守备广东时,汤贻汾儒将形象,跃然纸上。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破南京城,已退隐的汤贻汾组织乡勇抵抗,事败殉节,悲壮慷慨。笪重光以科举入仕,其英武之气,报国之情,未尝稍减。汤贻汾为武将,其英武表现为海天在胸,运筹帷幄;笪重光为文臣,英武之气则体现为直言敢谏,不畏权贵。笪重光巡按江西,因弹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正一品),弃官归里。英武之气,根源于深沉的报国之情。“位卑未敢忘忧国”,退隐之身而不忘报国之念,是笪重光与汤贻汾共同的人生选择。同为精于创作,有所建树的画家,皆是英武果敢,忠心报国的官员,身份认同,拉近了汤贻汾与笪重光的距离,为从《画筌》到《画筌析览》铺平了道路。
(三)慕道抱朴
笪重光与汤贻汾皆服膺道家学说,心灵上颇多契合,是汤贻汾选择《画筌》立论的决定性因素。笪重光与汤贻汾皆为官员,却不失赤子之心。褚人获曾记载笪重光的一则轶事:
顺治壬辰,句容笪在辛重光联捷礼闱,以丁艰归里,过吴门,寓同年姚茵稚馠先生家。一日闲步至吴子缨命馆,推测子平。在辛貌质朴,又麻衣麻冠,绝无贵介容,子缨为之布算,亦甚忽略,并不誉及科甲功名。一字推毕,在辛取子缨所持素扇,书高达夫“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句。后题“笪重光书”,以子缨牌板书“命友天下士”,故书此诗以讥之也。子缨见之,惶愧无地,而在辛毫无怒容,一笑而别。抵暮,其牌板已为人取去牌,有为之介绍者,馈银十二两,始得返璧。[2]
笪重光顺治九年(1652)进士,丁忧里居,不以贵介姿态示人。偶遇轻慢而不失风度,题句讥讽后,一笑而别。麻衣麻冠,本无骄人之意;题句笑别,方见平常之心。笪重光得功名,却不为之束缚羁绊,潇洒从容。汤贻汾官山西灵丘都司时,亦有黄巾衲访之佳话。其内敛平和,可谓共通。
汤贻汾曾扮作道士,笪重光也有学道的经历。据《长春道教源流》载:“朱太倥字冲阳,昆山人,读书好古,得詹真人法。句容笪重光、青浦诸嗣郢与之游,直以师事之。问飞升、黄白之事,即叱曰外道也。”[3]朱太倥叱飞升、黄白之事为“外道”,其所重者,应在内丹,即自身的内在修为。这种超越表象的精神体验,对笪重光《画筌》超越技法的画学观,或有启发。笪重光生平好道,罢官归隐后,成为道士。杨钟羲《雪桥诗话》载:
(笪重光)弃官去,不知所终。“郁冈扫叶道人”,其别号也。啸亭主人谓,有金氏子随舅氏某之官甘肃,遇道士于汉龙山,年九十余,作江南语,状貌伟然,颇善书法。自云曾为谏职,以劾权相去官,自称“绣发山人”,不言姓字里居,金氏子屡叩之,不告也。及归,告诸士大夫,皆云其状彷佛侍御,然终无左证。
笪重光别号“郁冈扫叶道人”,汤贻汾亦别号“错道人”“琴隐道人”。汤贻汾天性潇洒,袭爵后又杂学旁收,较少受传统思想束缚。为官后,汤贻汾广交方外,《逍遥巾》一剧中更是道服出场,足见其慕道之心。道家崇自然,尚超越。生活中,笪重光与汤贻汾皆能超越社会身份而自得其乐。绘画理论上,从《画筌》到《画筌析览》,皆主张超越技法,回归本心,二者可谓共通。
二、汤贻汾对笪重光的承继
在与先贤笪重光精神契合的基础上,汤贻汾以《画筌》立论,嘉庆九年(1804)撰成《画筌析览》。此时,汤贻汾已官三江营守备,绘画亦近于成熟,保持了《画筌》重画品、尚思辨、崇自然之理论特色。汤贻汾将《画筌》条分缕析,具象与抽象互化,使原作的立论更加清晰,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一)创作成熟时的理论结晶
汤贻汾《画筌析览》作于嘉庆八、九年间,时官三江营守备,乃其绘画创作臻于成熟时期。因其绘画成熟,故能于理论上承继前贤。诗集中首次记载作画与赠画,即绘画成熟的标志。汤贻汾《春日过霍家桥,喜其幽境,偶写一图》诗,即作于此时:
等闲吹月爱琼箫,知是扬州第几桥。港曲有舟通大海,寺门无日不春潮。朱幡过处花俱笑,碧草生时马便骄。绘出水乡幽绝景,一番客路最魂销。(《琴隐园诗集》卷三)
汤贻汾官署驻地,在扬州城东南三十里,霍家桥在扬州城东,为往来必经之处。汤贻汾行至霍家桥,为盎然春意所动,即兴作画。触春色而成图,见汤贻汾灵感充盈,信手拈来;作画于旅途之中,知挥毫泼墨,已为生活常态。诗集编订于晚年,此诗为记绘事之始,见汤贻汾此时对自己的绘画水平已颇自信。值得注意的是,汤贻汾《琴隐园诗集》中首次记载赠画,亦在此时,卷三《仙朗峰焘学博家于朗山之阳,声溪之上,有亭曰“宾山亭”,索图并题》诗:
山不在高仙则名,谁呼为主谁为宾?十年衫色如出青,一朝涅入红黄尘。仙乎仙乎好归去,朗山不住声溪住。君不见,溪上花如霞,山头云似絮。纵使随风逐水行,不曾离却江南路。君将改官大令。
仙焘为安徽宁国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嘉庆七年(1802)官江苏泰兴县学训导,汤贻汾曾任泰兴都司,想二人应由此结缘。仙焘索画,可见汤贻汾此时已有画名。此诗入集,可视为汤贻汾对自身绘画成熟的再次确认。作《画筌析览》之时,汤贻汾的绘画创作已近于成熟,此作是其画学思想的凝结。
(二)儒道互补的思辨承继
文人托物言志,故作画多有寄寓;道家清净逍遥,则论画通脱超越。笪重光与汤贻汾皆为文人,又深受道家思想熏陶,从《画筌》到《画筌析览》,传承了重画品、尚思辨、崇自然的理论特征。
如何定位绘画,是构建画论体系的根本,笪重光与汤贻汾皆视绘画为表情达意的途径,有着近乎传统诗文的地位,是严肃的创作,需要认真对待。《画筌》起首,笪重光开宗明义指出,画家的修养决定着画作的水平:
绘事之传尚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为画诀,散在艺林,六法六长,颇闻要略。然人非其人,画难为画,师心踵习,迄无得焉。聊摅所见,辑以成篇。
笪重光考察历代绘画名家,发现他们多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保持独立的人格,堪称高士。绘画的传习,若只重视技法,忽略画家自身修养,精神上得不到提升,画品亦不能精进。笪重光作《画筌》,意在纠正视绘画为一般技能的偏颇,重新唤起对画家修养、精神活动的重视。论皴法,笪重光称“劈斧近于作家,文人出之而峭;鬼脸易生习气,名手为之而遒”。斧劈皴棱角分明,鬼脸皴玲珑剔透,此两种皴法,因其传统而易生俗态。“文人”“名手”为之,能于刚劲中见灵秀,通透中生力度,足见笪重光强调主观,珍视创作,对画家要求极高。汤贻汾《画筌析览》论时景,亦可见对画家修养的重视:
时景既识其常,当知其变。盖一物之有无莫定,由四方之气候不齐。如塞北多霜,岭南无雪,是景以地论,不以时分。画虽小道,亦欲兼达夫地气天时,而后可以为之也。
汤贻汾以绘画为“小道”,显然是对时俗绘画理念的概括,他的意旨恰恰相反。作为画家,既要把握传统的绘画题材,又要悉心体察万籁的细微之变,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是对绘画作为艺术的重视。
笪重光与汤贻汾皆重画品,视绘画为精神活动的外化,故而从《画筌》到《画筌析览》,呈现出尚思辨的理论特色。如论画树,笪重光说:“一本之穿插掩映,还如一林;一林之倚让乘承,宛同一本。”画好一棵树,要善于布置枝叶,如同描绘一片森林;描绘一片森林,又要注意和谐浑融,使之如同一棵树。笪重光对景物自身及景物之间关系的思考,贯穿了《画筌》全篇。一棵树,要“密叶偶间枯槎,顿添生致”;树石之间,则“石本顽,树活则灵”。更广阔的山水间,是“山脉之通,按其水径;水道之达,理其山形”。视野延展到画作整体,便成了虚实有无的考量:
林间阴影,无处营心;山外清光,何从着笔?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景物自身的圆满,景物之间的沟通,画面整体的构建,虚实有无的布置,皆是笪重光《画筌》的思辨内容。经过重重思辨,笪重光凝结出自己的创作原则,即“目中有山,始可作树;意中有水,方许作山”。在《画筌析览》中,汤贻汾将这一思辨归纳为“相顾而自顾”,并扩展到更为深广的领域。水作为一类景物,因形态不同而面貌各异,“水性至柔,是瀑必劲;水性至动,是潭必定。江海无风亦波,溪涧有纹亦静”。汤贻汾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思辨,从景物间的相互映衬进一步推衍到天人交感:
春夏秋冬,早暮昼夜,时之不同者也;风雨雪月,烟雾云霞,景之不同者也。景则由时而现,时则因景可知。
汤贻浚跋《画筌析览》称,自《芥子园画谱》问世以来,“举一不反者,下笔辄如刻板”,其兄《画筌析览》于此有所矫正,可谓中肯。《画筌》《画筌析览》绝少探讨具体画法,而着重阐发主次虚实的辨证关系。在展现作者思辨过程的同时,也启发了读者的创作灵感,以期摆脱千人一面的窠臼。
道法自然,笪重光与汤贻汾皆服膺道家文化。崇尚自然,是《画筌》与《画筌析览》的又一理论特色。笪重光《画筌》说:“从来笔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写照。善师者师化工,不善师者抚缣素。”《画筌》是绘画教材,更是作者师法自然的笔记。在布景上,要遵循自然界规律,“众水汇而成潭,两崖逼而为瀑”。同是画树,既要因地制宜,“坡间之树扶疏,石上之枝偃蹇”,又要相时而动,“春条擢秀,夏木垂阴,霜枝叶零,寒柯枝锁”。笪重光绘画遵循的自然,也包括人文景物,“岛屿孤清,屋舍岂宜丛杂?”描绘萧条意境,断不可多置屋舍,而营造田园风光,则“村聚密其井烟”。总之,《画筌》追求最大程度地还原自然真实,“景不嫌奇,必求境实”。若刻意追求某种特定效果,而丧失真实,在笪重光看来,是得不偿失的:
丹青竞胜,反失山水之真容;笔墨贪奇,多造林邱之恶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览无余;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观不厌。
师法自然,作寻常之景;苦心孤诣,成不厌之观。尊重自然规律的艺术创作,是笪重光提倡的,汤贻汾《画筌析览》于此亦有传承:
人知欲学《兰亭》,则竟学《兰亭》,不屑临松雪所临之《兰亭》。造化生物,《兰亭》也;古画虽佳,松雪之《兰亭》也。何独于画而甘自舍真就假耶?
这段话,汤贻汾意在强调不必盲从古人。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与赵孟頫所临《兰亭序》,皆为珍品,但若要得右军真传,大可不必取道松雪。汤贻汾的比喻,既肯定了前人的成就,也明确了师法自然,匠心独运,才是实现独立创作的根本途径。
(三)文本形态的整合优化
汤贻汾征引《画筌》并附以己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笪重光原作文本形态的整合优化。《画筌》六千余字,正文不分段,信笔挥洒自如,不拘一时一事,对读者的创作经验与领悟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汤贻汾摘《画筌》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五章,介绍特定景物的画法,由主到次,分别为山、水、树石、点缀、时景;下卷分析具体技法与创作心态,五章分别为钩皴染点、用笔用墨、设色、杂论、总论。《画筌》原文后,汤贻汾附以评点,成《画筌析览》,谢兰生跋云:
《画筌》一篇综括大要,随笔所之,自成片段。善悟者,领取意致,莫不心解,而初学时或茫如也。雨生都尉条析之,复以己见诠补焉。其原书如正幅帷裳,雨生去襞积加杀缝,俾适于用。其诠补则针工绵密,益熨贴耳。
帷裳乃古代祭服,用整幅布料制成,不加裁剪,难以穿着。谢兰生以帷裳比《画筌》,言其立论精妙,却错综复杂,难以领会。汤贻汾析释《画筌》,则是恰到好处的剪裁缝补。二者神气贯通,浑然一体,正如熨帖绵密的针脚,不着痕迹。精当的比喻,突显了汤贻汾对《画筌》的梳理整合之功。
抽象事物的具象化,即形象的比喻,是汤贻汾使《画筌》更加明晰易懂的主要途径。《画筌析览》卷下第六章,专论钩皴染点,汤贻汾云:“钩皴染点之于画,犹点画撇捺之于字也。点画撇捺合之为字,分之固各有其法,惟画亦然。”汤贻汾将抽象的钩、皴、染、点等绘画笔法,比喻成写字的点、画、撇、捺,即便未能深通画理之人,读到此处,也可明了具体笔法与整体画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汤贻汾又阐述了具体笔法不专用于描绘某一特定景物,就像笔画不专用于写某一个字一样,“诸法不徒用之于石,用于树一也。树大腹必加皴,身必施点,或钩或染,偏废不能”。诸法自由组合,灵活运用,方为要诀妙处。汤贻汾用简明形象的语言,阐述了通达实用的技法观。《画筌析览》卷下第九章杂论,汤贻汾以人体设喻,亦十分恰切。“画以树石为筋骨,以径路为血脉,以烟云为裳衣,以人物为眉目。筋骨不可不强,血脉不可不通,裳衣不可不楚,眉目不可不朗。” 四个简短的比喻,道破了一幅优秀作品对具体景物的要求,也明确了景物与整体的关系。此章引笪重光《画筌》五百余字,无外此理,真可谓化繁为简,言简意赅。
具体描述的抽象化,即精准的概括,是汤贻汾解析《画筌》的另一重要手法。《画筌析览》卷上第五章论时景,引《画筌》原文一百余字,皆在描绘具体景致:
云里帝城,山龙蟠而虎踞;雨中春树,屋鳞次而鸿冥。爱落景之开红,值山岚之送晩。柔云断而还续,宿雾敛而犹舒。散秋色于平林,收夏云于深岫。危峰障日,乱壑奔江;空水际天,断山衔月。雪残春岸,烟带遥岑;日落川长,云平野阔。雨景霾痕宜忌,风林狂态堪嗔。雪意清寒,休为染重;云光幻作,少用钩盘。晓雾昏烟,景色何容交错;秋阴春霭,气候难以相干。
笪重光在《画筌》中,描述了各种具体景物在特定季节的绘画要领,强调了画家对季节、时序的把握,但字句骈俪而繁杂,读者往往沉浸于丰富的物象之中,难究其竟。且文笔优美,作为文学作品欣赏,亦无不可。汤贻汾析释《画筌》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不失文学性的语言,将笪重光所要阐释的理论,更为简洁明确地展现出来:“故下笔贵于立景,论画先欲知时。”
张如芝跋《画筌析览》,称《画筌》“数千百言,句句俱是好画”,可作画谱看。但“若泥其句语,而遗其景象,失前人意矣”。《画筌》语言的丰富优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其理论内涵的把握。汤贻汾精准地加以概括,真“度《画筌》之金针”,“后来之宝筏”也。
三、汤贻汾于笪重光画论的延展
汤贻汾为武将,亦是文人,守备扬州时撰《画筌析览》,融进了广陵的精英文化圈。文人情怀潇洒自适,故《画筌析览》在承继《画筌》理论特色的基础上,重视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技法上讲求突破成规,独立自信。
(一)秉持潇洒自适的文人情怀
文人情怀是汤贻汾延展笪重光画论的心理基础。汤贻汾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承继了父、祖的传统文人生活方式,故终生不脱文人底色。晚年所作《七十感旧》组诗,第十六首自注,忆及早岁读书经历:
戊申冬,读书天井巷汪氏。业师钱鸥泉先生,年七十馀,居滆湖之滨,工书善弈。明年,受业于姑之夫汪岘山先生,去巷稍西,予下榻楼下,即姑居室后。读书处池馆清幽,有危柯奇石,翠筱紫藤,始学为文。至秋,又受业于庄容台先生,主仁里巷寿南堂,庄氏盖容台先生之族,而予姑适庄达甫先生,亦共宅居,予依姑餐寝,至次年岁终而止。辛亥、壬子,延师蔡质夫先生于家,始应试。癸丑年十六,届当引见,遂辍读。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冬,十一岁的汤贻汾始习制举文,五年间先后师从四人,辗转三处,两度就外傅,孤儿寡母,支撑不易。汤贻汾得袭云骑尉,十二岁已食半俸,本无生计之虞,母亲杨氏仍督其勤习帖括。后应童子试不第,至十六岁晋京引见后,始放弃举业。这种文人底色,在撰写《画筌析览》时,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展现。汤贻汾守备三江营时,驻地风景宜人,流连其中,身心愉悦,可称“吏隐”,官舍更是用心营构的诗意空间:
三江官舍有楼七楹,江环三面,隔岸桃花数十里。季莲溪征君、张老姜布衣、洪稚存太史先后过访,留诗见贻。予尝筑高亭于梨杏梢头,初登见月,即以“江月”名亭。
环水对花,已是妙境自有;筑亭得月,更见文心偶成。三江营官舍,与其说是汤贻汾的办公场所,不如说是任意挥洒性情的个人空间。故友新知,同僚士庶,前辈后生,均曾在三江官舍优游唱和,尽兴而返。除了三江官舍,毗邻的扬州府城,亦是同侪唱酬之地。汤贻汾“居江上五年,往来扬州者屡”,诗集中与扬州文友的互动俯拾即是,琼花观、安定书院等扬州名胜,频见笔端。《七十感旧》列扬州师友十六人,身份囊括官员方外、土著留寓,足见交游之广,契合之深。汤贻汾守备扬州,以疏忽失职罢去,亦从侧面见其平日的潇洒自适。[4]
(二)推崇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
汤贻汾秉持文人情怀,加之生性潇洒,《画筌析览》也推崇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画筌》重画品,强调画家文化修养、独立人格的重要性,未述及创作心态。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是汤贻汾对自身艺术实践的体悟,对画家作为创作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可以看作是对《画筌》内容的丰富和补充,升华、完善了笪重光的绘画理论。汤贻汾认为,精通绘画艺术的关键,首在“夙慧”:
先生曰:“人非其人,画难为画。”骚人高士,斯其人矣,然犹必具有夙慧,而后可以言画。唐人诗曰:“宿世应词客,前身是画师。”言其慧不自今耳。故画之为道,如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不能盖终不能也。
汤贻汾推崇的“夙慧”是先验的,不是后天培养的领悟能力。拥有夙慧,“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象千林;对盆里一拳,亦即度知五岳”,下笔如有神助。缺乏夙慧,则导致“团搦”,即煞费苦心以求尽善尽美,“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经营极矣”,即便大功告成,难免生气全无,“非画之上乘也”。撰《画筌析览》时,汤贻汾绘画臻于成熟,认为理想的创作状态,应是“意所至即气所发,笔所触即机所乘”。这种状态下,画家为“夙慧”所引导,心态灵动自然。
对灵动自然创作心态的推崇,渗透在汤贻汾论具体景物的描绘中。《画筌析览》第一章论画山,汤贻汾以前人“三远”之说立论,即画山“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致冲融”。古人同时给出了“三远”的实现途径,即补绘其他景物,以资衬托:“远欲其高,当以泉高之远;欲其深,当以云深之远;欲其平,当以烟平之”。汤贻汾认为,即便“三远”有成法可参,而“远”仍不可得,失败的根源,在于创作心态,即“病在笔墨太痴”。汤贻汾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调节心态,“砭之只一字,曰‘松’”。松,即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言为心声,画为心像,心平气和,笔底方呈幽远之境。宁静致远,即是如此。
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生发于“夙慧”,在艺术选择上,体现为保持独特的风格,不委曲求全。《画筌析览》第三章论树石画法,汤贻汾借此总结了前人成功的创作经验:
工于叶者多图春夏,能于枝者尽作秋冬。切勿讳短而强长,就生而舍熟。故子久多春,而云林多秋,松年多冬,而南宫多夏。兼长固为能品,不如专习之。尤能专习,果已化工,庶可兼长而俱化。
擅画叶者多作春夏之景,能写枝者多成秋冬之图。看似是艺术探索的懒惰,实则是对自身所长的清醒认识,也是历史上黄公望、倪瓒诸大家的选择。在汤贻汾看来,博采众长固然可喜,但若无法达到化境,难免沦为平庸,堕入俗流。保持自身独特的风格,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反而有可能接近融会贯通的最高境界。汤贻汾主张画家选择自身擅长的创作,是对内在自然的顺应,发展了《画筌》崇尚自然的理念。
(三)突显独立自信的艺术追求
汤贻汾珍视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尊重画家个性风格,理论上独立自信,呈现出对传统画学的全面超越。笪重光《画筌》崇尚自然,主张师法造化,不为成规所缚,“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笪重光列举了历代画史的成功案例:
叔达变为子久,海岳化为房山。黄鹤师右丞,而自具苍深;梅花祖巨然,而独称浑厚。
黄公望、高克恭的绘画风格,分别脱胎于董源与米芾。王蒙、王冕各自师法王维和巨然和尚,而别具新意。笪重光心中的“不拘法”是“变门庭”,即在既有艺术经验基础上,实现个人的突破。汤贻汾《画筌析览》主张“神而明之,自可离法而立”,彻底摆脱“门庭”束缚,是更进一步的崇尚自然。
历代大画家,皆具鲜明的艺术风格。超越某一画家,意味着对特定审美范式的突破。汤贻汾主张离法而立,认为执著古人,是对绘画艺术本质的背离:
画象也,象其物也。今人每画,必曰“仿某、法某”,故一搦管,即以一古人入其胸,未尝以造化所生之物入其胸。以造化生物入其胸,则象物;以古人入其胸,则仅能象其象。
绘画是对自然景物的艺术再现,故画家构思,应是观察提炼世间万物的千姿百态,而不是一头扎进故纸堆,选择一位古人,匍匐其脚下。心中充盈万籁,笔下风光无限;眼里尽是古人,纸上灵气全无。胸中不可有古人,是汤贻汾坚决的态度。论及具体画法,汤氏对定法的突破,同样彻底。钩法、染法已是丰富,皴法、点法更为繁杂,在汤氏眼中,种种技法“皆不外乎阴阳二字”。画家把握好“阴阳”,即明暗对比,则“无可无不可”,进入自由挥洒之境。“必曰某家皴、某家点,是终不过成其为皴与点而已矣”,皴法即皴法,点法即点法,在汤氏看来,画法没有必要和某位名家绑定在一起,掌握明暗要领,即可挥洒自如。
汤贻汾摆脱名家成法的坚决态度,也体现在对特定景物的处理上。论画山,前人定法是:“初下正面一笔为鼻准,结顶嶂盖一笔为颅骨,中间起伏转折处为脉络”。此种画法生动形象,可操作性强。汤贻汾并不拘泥于此,“初下一笔,亦不必拘定何处,可从正面而积累至上,亦可从嶂盖而层折至下,总以有脉为当”。“有脉”是画山的基本要求,它来自细审自然景物,而非精研前人定法。前人画树,讲究“四歧”,出枝要兼顾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以求立体自然。这一理论,即便用今天的眼光看,仍较为合理。汤贻汾在《画筌析览》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四歧之说不可执”。因为“有上而难得一歧,有在根而已发千岐者,枝法不一,叶式多门”。相比自然界树木的参差百态,“四歧”之说显得僵硬,汤贻汾突破此说,正是以造化为依凭。最为大胆的,是汤贻汾指出“不皴亦得为石”。皴法用以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的脉络纹理,是画石的必备技法。汤贻汾敢于脱离皴法画石的原因,在于石头虽千差万别,描绘“不外阴阳之理”。明暗处理,再次成为绘画的关键,是否使用皴法,已然并不重要。“皴而尚未觉其为石者难药,不皴而识其为石者可师也”。汤贻汾论画石,实现了对传统皴法的彻底超越。
突破传统绘画观念,也是汤贻汾独立自信的表现。传统观念,“山水树石而外,凡物皆点缀也”。《画筌析览》上卷前四章,亦按山、水、树石、点缀排列,足见此说已成定论。而汤贻汾自有创见:
然一图有一图之名,一幅有一幅之主。使名在人,则人外非主。主在屋,则屋外皆余。故有时以山水树石为余,而以点缀为主者,此点缀之不可不讲也。
画面之中孰为宾主,当由内容决定,而非传统观念。汤贻汾认为,这是把握点缀的关键,其重要性远在宾随主动、主显宾隐等内容之上。
笪重光以“画筌”名篇,含有读者超越作者的期待。汤贻汾因与之精神契合作《画筌析览》一书,在继承《画筌》儒道互补理论特色的基础上,强调灵动自然的创作心态,并加大突破传统束缚的力度,主张离法而自立。作为常州画派继恽南田后最优秀的画家,汤贻汾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成就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从《画筌》到《画筌析览》,不仅是理论探索,更展现了汤贻汾潇洒自适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