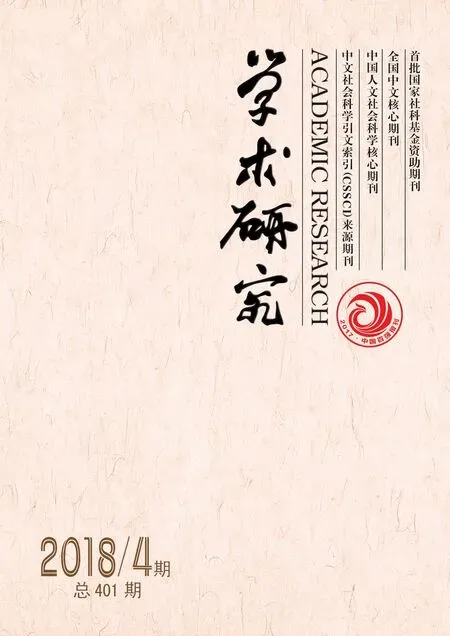源头创新与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取向*
罗文豪 章 凯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人民正以巨大的热情和努力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助力其中并实现更好的发展值得研究者深思。近些年来,包括管理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国际发文的数量迅速增长。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还很小,多数仍处于追赶与模仿状态。这一现状突出地反映出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能力还很不足,难以支撑起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崛起。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与此相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特别提出要“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实施原创性基础理论重大专项研究,大力推进学科建设和学科创新,并以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发展的支撑。同时,学科基础研究的创新也是国家层面上推动自主创新战略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针对学科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夯实学科基础、引领学科发展、参与国际对话的关键战略选择,这其中既蕴含着重大机遇,也对各学科提出了严峻挑战。
对于管理学科而言,如何把握住当前的历史性机遇并实现学科发展是事关学科使命实现的一个关键议题。正如企业组织需要界定自身的使命并努力践行一样,一门学科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同样需要承担起自身的使命,学科使命集中体现了这一学科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一门学科的学科使命通常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是追求真理,至少是尽最大可能地去逼近真理。一门学科力图创造并且组织起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从而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aTsui A. S.,“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9,no.3, 2013, pp.375-394.另一方面,一门学科的使命还体现在改善人类境况上。bWalsh J. P.,“2010 Presidential Address - Embracing the Sacred in Our Secular Scholarly World”,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6, no.1, 2011, pp.215-234.科学创造知识并非是为了简单地堆积知识,而是试图通过更加深入透彻地认识研究对象,更好地预测未来变化并合理改变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类的不断发展。
管理学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样承担着上述两方面的学科使命。一方面,管理学科致力于针对人类社会与组织中的管理现象贡献知识。例如,当我们观察到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业绩有所差异时,管理学者试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为数众多的领导研究者致力于探索领导力,同样是力求对深入理解领导现象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管理学科“改造世界”的社会性使命同样不可忽视。Ghoshal(2005)cGhoshal S.,“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vol.4, no.1, 2005, pp.75-91.以及Ferraro等(2005)dFerraro F., Pfeffer J., Sutton R. I.,“Economics Language and Assumptions: How Theories Can Become Self-fulfill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0, no.1, 2005, pp.8-24.都曾经指出,管理学中的理论和研究结论往往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也就是说,当管理科学研究揭示出某一管理“规律”之后,这一“规律”往往会影响管理者的思维,从而运用在管理实践中。好的管理理论可以发展实践,坏的管理理论也能误导实践。例如,并不全面的“经济人”假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过度的重视和应用。因此,发展好的管理研究与管理理论更加重要。
近些年来,组织管理学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突出地体现在研究论文的大量发表和研究队伍的迅速壮大上。然而,若我们以上述管理学科的双重使命来审视当前的管理学科,便会发现这样的繁荣背后事实上潜伏着诸多困境。从知识创造来看,新的概念、变量关系模型和理论框架层出不穷,但不同的概念或理论之间却依旧缺乏清晰的内在联系,也未能形成逻辑一致、意义明晰的知识体系,近三四十年的研究都未能催生出好的、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的管理理论。eSuddaby R., Hardy C., Huy Q. N.,“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Where are the New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6, no.2, 2011, pp.236-246.即便是那些发表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的理论性文章,也往往缺乏进一步的衍生和发展能力。fHalbesleben J., Wheeler A., Buckley M.,“The Influence of Great Theoretical Works on Subsequent Empirical Work”,Management Decision, vol.42, 2004, pp.1210-1225.从管理学科的社会性使命来看,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问题已经招致学科内外的诸多质疑和反思,g徐淑英:《求真之道,求美之路:徐淑英研究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hGeorge G.,“Rethinking Management Scholarship”,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1, no.1, 2014, pp.1-6.i章凯、罗文豪:《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信念与取向》,《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越拉越大。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管理学科所应当承担的“智库支持”角色也没能有效发挥。j顾海良:《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的使命——基于“社会责任”的观察与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4期。一言以蔽之,从国际范围来看,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学术成果的增加与繁荣似乎并没有带来整个管理学科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管理学科看似快速壮大,实则已经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瓶颈期,kCorley K. G., Gioia D. A.,“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6, no.1, 2011, pp.12-32.管理学科的双重使命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实现。
相对而言,管理学科依旧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迂回曲折或是一定阶段内的停滞不前都是可能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学科的源头是否健康对于学科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也都有过长时间的“黑暗摸索时期”,但这些学科在明确研究对象并对其构建了合理的基础理论模型之后均获得了快速健康的发展。相反,如果一门学科没有合适源头或者在源头上就是错误的,那么其后续的发展要么就是在黑暗中彷徨摇摆,要么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不关注和修正学科源头问题,而只是在具体的研究分支上进行增增补补,往往难以真正实现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管理学科出现长达数十年的瓶颈状态,并陷入到理论创新乏力的境遇中,或许并不仅仅是学科发展中一时一地的偏差所致,而更加需要学者们反思管理学科的源头问题。我们遗憾地看到,在管理学科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学者们都难以找到基础性的学科理论来指导学科的未来发展。a张钢、岑杰、吕洁:《“理论管理学”是否可能》,《管理学报》2013年第12期。面对这样的现状,源头创新之于管理学科健康发展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也更加紧迫地需要管理学者们予以正视。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立足于学科使命实现这一角度,审视当前管理学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并力求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剖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如何推进学科源头创新”这一核心问题,为未来的管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发展取向和策略思考。
一、管理学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当前,在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内,一方面,研究成果数量激增、研究规范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学者规模快速扩大,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发展背后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深切担忧。综合有关学者的分析,并结合我们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多年研究积累,本文将当前管理学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管理研究与实践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开始意识到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或鸿沟。bHambrick D. C.,“2003 Presidential Address - 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9, no.1, 2004, pp.11-16.cRousseau D. M.,“Is There Such A Thing as‘Evidence-based Man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1, no.2, 2006, pp.256-269.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学者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管理者的需要,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学者自身的职业发展;dTsui A. S.,“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9,no.3, 2013, pp.375-394.二是学术研究并非以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困惑为导向,而是更多地从文献出发,缺乏与实践界的对话。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术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往往与管理实践者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相去甚远;eRynes S. L., Bartunek J. M., Daft R. L.,“Across the Great Divid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ransfer across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4, no.2, 2001, pp.340-355.fDeadrick D. L., Gibson P.A.,“An Examination of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 in HR: Comparing Topics of Interest to HR Academics and HR Professionals”,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vol.17, no.1, 2007, pp.131-139.学者们越来越将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往往只能引起少数同行的注意与兴趣;gTsui A. S.,“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9,no.3, 2013, pp.375-394.hHambrick D. C.,“2003 Presidential address - 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9, no.1, 2004, pp.11-16.管理者极少会试图从学术共同体中寻求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从学术成果中汲取有助于提升管理效果的科学发现。iRynes S. L., Bartunek J. M., Daft R. L.,“Across the Great Divid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ransfer across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4, no.2, 2001, pp.340-355.事实上,以当前的管理学科发展而言,即便没有管理学者和他们的专业工作,管理实践可能也不太会受到相应的影响。jTsui A. S.,“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9,no.3, 2013, pp.375-394.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管理研究中一些坏的理论,由于理论的自我实现倾向还对管理实践的发展起到了破坏性作用。aGhoshal S.,“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vol.4, no.1, 2005, pp.75-91.bFerraro F., Pfeffer J., Sutton R. I.,“Economics Language and Assumptions: How Theories can Become Self-fulfill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0, no.1, 2005, pp.8-24.
第二,管理概念与小型理论过度繁衍却又支离破碎。在组织管理学科中,理论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学术共同体的一致认可,几乎所有的顶级管理学期刊都十分强调论文所做出的理论创新,cEdwards J. R.,“Reconsidering Theoretical Progress in 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ment Research”,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13, no.4, 2010, pp.615-619.dHambrick D.,“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0, no.6, 2007, pp.1346-1352.这一现状激励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不断地开发新的理论概念与模型。然而,由于并没有一个一致清晰的标准来衡量理论贡献是否存在及贡献大小,使得当前管理研究中理论发展的水平良莠不齐。eFerris G. R., Hochwarter W. A., Buckley M. R.,“Theory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How will 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vol.2, no.1, 2012, pp.94-106.fWhetten D. A.,“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4, no.4, 1989,pp.490-495.与此同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组织管理理论在提出之后便几乎没有消失或者被淘汰过,而总是能够找到一片栖身之所。gDavis G. F.,“Do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Progress?”,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13, no.4, 2010, pp.690-709.hDavis G. F., Marquis C.,“Prospects for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nstitutional Fields and Mechanisms”,Organization Science, vol.16, 2005, pp.332-343.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当前管理学科的各类理论不断堆积,甚至已经出现过度繁衍的现象。iDavis G. F.,“Do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Progress?”,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13, no.4, 2010, pp.690-709.jTsang E. W. K.,“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t a Crossroads: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5, no.1, 2009, pp.131-143.学者们为了继续做出理论贡献并在学术共同体中求得发展,就只能在一个个细小而聚焦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地勤奋“开垦”。例如将已有的一个或数个概念重新组合或者持续不断地开发新的概念,其结果是既加剧了管理学科中概念与小型理论的过度堆积,也使得整个管理学科支离破碎的状况愈演愈烈。kColquitt J. A., Zapata-Phelan C. P.,“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0, no.6, 2007, pp.1281-1303.lSpell C.,“Management fashions: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and Are They Old Wine in New Bottle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vol.10, 2001, pp.358-373.以领导研究为例,文献回顾发现,近年来领导学者们提出并发展的领导构念越来越多,mAvolio B. J., Walumbwa F. O., Weber T. J.,“Leadership: Current Theories,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60, no.1, 2009, pp.421-449.nVan Knippenberg D., Sitkin S. B.,“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Charismatic-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Research: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7, no.1, 2013, pp.1-60.如道德型领导、愿景型领导、共享式领导、服务型领导、本真型领导、分布式领导等,看似理论概念很丰富、研究成果众多,但实则对理解领导现象和过程、发展领导理论、指导领导实践助益十分有限。
第三,数十年研究并没有孕育出好的理论。在当前的管理学界,存在着一种戏剧化甚至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都在强调理论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oFerris G. R., Hochwarter W. A., Buckley M. R.,“Theory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How will 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vol.2, no.1, 2012, pp.94-106.但管理学科自从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之后,pSmith K. G., Hitt M. A.,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便陷入长时间的理论停滞。在数据获得、分析技术和研究工具进步迅猛的今天,研究的数量激增,但理论体系却未能实现相应的发展,学者们所依赖的理论基本上仍然是30多年前开发的理论。aSuddaby R., Hardy C., Huy Q. N.,“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Where are the New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6, no.2, 2011, pp.236-246.bDavis G. F.,“Do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Progress?”,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13, no.4, 2010, pp.690-709.Colquitt和Zapata-PhelancColquitt J. A., Zapata-Phelan C. P.,“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0, no.6, 2007, pp.1281-1303.对1963—2007年发表在《美国管理学会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文章进行梳理,总结出作者们最常引用的12个微观理论和8个宏观理论,而这20个理论中多达19个理论发表在1963—1984年之间,唯一的例外是Barney在1991年发表的资源基础观。dBarney J.,“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17, no.1, 1991, pp.99-120.针对这一令人难言乐观的现状,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美国管理学会评论》(AMR)曾经在2008年期望通过专刊形式来鼓励学者们发展一些新的组织管理理论,然而在这一专刊最终面世时,专刊的编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极少有投稿真正提供了新的理论”。eSuddaby R., Hardy C., Huy Q. N.,“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Where are the New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6, no.2, 2011, pp.236-246.相反,最终刊出的论文只是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当前理论发展不力的集体反思、批判性观察和可能的建议。管理学科理论发展进入瓶颈阶段、理论创新步履维艰的现实境地由此可见一斑。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当前主流管理研究的学科形象便跃然纸上。那么,这样的学科形象到底对管理学科的发展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学科使命的高度来深刻反思管理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创造知识和造福社会这二项学科使命来审视当前的管理学科形象,不难发现无论是整个管理学科,还是相当多数的管理学者,在践行学科发展使命上都差强人意,甚至忽视或错误理解了应当承担的使命。支离破碎而又缺乏创新的管理理论使得管理学科在创造新知上贡献有限,而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又阻碍了管理学科有效地实现“促进管理发展”的使命。因此,当前管理学科呈现出的学科形象显然不利于管理学科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管理学科发展困境形成的深层次成因
面对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对于富有学术使命感的管理学者来说,我们不会也不该对当前现状感到满意,而应当客观地审视当下,理性地剖析成因,进而勇敢地推动变革。那么,造成上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结合前文对于学科使命的分析,我们认为以下三方面的误解造成了当前不利于管理学科使命实现的学科形象。
第一,对于科学本身存在理解偏差,错误地将科学等同于科学方法。Maslow(1954)f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 p.188.在分析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曾经指出“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陷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今天看来,马斯洛在60多年前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分析与批评放在今天的管理学领域依旧具有一针见血的效用。所谓以方法中心来理解科学,首先指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其仪器、技术、程序、设备和方法,而并非它所指向的疑问、问题、功能或目的。在当前的管理学科中,判定研究质量的标准往往聚焦在这项研究在方法运用上的严谨性高低。其次,方法中心的科学家们还会不由自主地根据自己掌握的方法或技术来决定研究内容,而不关心所研究的问题或内容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是否具有足够的意义。在管理学科中,很多研究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模型中增加了一些变量或者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丝毫不关心这一模型对学科发展的意义以及与当前管理实践的关联,这都是从方法出发而非从问题出发的典型体现。综合来看,相对于问题中心来说,方法中心的研究者将科学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将科学方法和科学混为一谈。在管理领域中,如果研究者们更多地仅仅执着于高深的方法,通常只会产生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平庸结果,a亨利·明茨伯格:《开发关于理论开发的理论》,引自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编:《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徐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4-299页。从而最终无益于管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正因为意识到方法中心的危害,Sandberg和Tsoukas(2011)才建议研究者们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要更多地考虑管理实践蕴藏的理论价值,bSandberg J., Tsoukas H.,“Grasping the Logic of Practice: Theorizing through Practical Rational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6, no.2, 2011, pp.338-360.这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与管理研究本应该践行的使命相一致。
第二,对于理论的本质理解不当,未能正确把握理论和理论贡献的应有内涵。在组织管理领域,Kerlinger(1986)cKerlinger F. N.,“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Science”,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6.对于理论的界定比较受认可,他认为理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构念、定义和命题,通过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揭示现象,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现象。然而,根据章凯和罗文豪(2015)d章凯、罗文豪:《科学理论的使命与本质特征及其对管理理论发展的启示》,《管理学报》2015年第7期。的分析,我们意识到上述理解事实上是对于理论内涵的误解。首先,从理论的表达形式来看,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在主要的理论表达形式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物理学中的理论常常以概念界定和变量关系的形式出现,而化学和生物学中的很多理论则并非以变量关系形式存在。管理学科借助于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建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物理学中的理论表达形式。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在研究物理对象时较为有效,但用来认识组织和人却不一定合适。其次,从理论的本质属性来看,Kerlinger及其他相关的定义都属于描述性定义,而对于理论的本质属性则无任何规定或描述。相反,科学哲学家Hempel(1966)eHempel C. G.,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rentice Hall, 1966.对于理论的界定更加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论的本质属性。在Hempel看来,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到特有的理论定律或原理所支配,从而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因此,当前管理学科将理论理解为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集体误读,这促使管理学研究热衷于搭建和验证小型的变量关系模型,似乎提出和检验了一种新颖的变量关系模型就做出了理论贡献。对于理论和理论贡献的误解一方面使得有关变量关系模型的研究大量增加,加剧了管理学科理论过度繁衍和支离破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得管理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变量模型所描述的“故事”现象上,对研究对象缺乏深刻的认识,学术研究也日渐脱离管理实践而存在。
第三,学术群体的社会使命感缺失,社会责任意识比较淡薄。在当前的学术考核体系和职业晋升制度作用下,存在一种现象,即相当多的学者们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关注多于对知识创造和科学使命的关注。fZhao S., Jiang C.,“Learning by Doing: Emerging Paths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5, no.1, 2009, pp.107-119.gGlick W. H., Miller C. C., Cardinal L. B.,“Making a Life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28, no.7, 2007, pp.817-835.在选择研究对象和问题时,很多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这一对象和问题能否产生一篇或者多篇论文,而不是研究对于知识创造和管理实践有多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如果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再是贡献知识与改善实践,而是为了发表论文和服务于学者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学术生涯就不再是对于真理或原理的探索追寻。当前环境下学者社会使命感的缺失产生的结果必然是管理研究既无法推动知识创造,又与管理实践发展相去甚远,h徐淑英:《求真之道,求美之路:徐淑英研究历程》。这无疑是导致当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的重要原因。
三、管理学科研究呼唤源头创新
根据上文分析,目前主导的管理研究范式在理解科学、理解理论和践行学科使命上都犯下了根源性的错误,并且正是这些错误的不断积累造成了当前管理学科发展的瓶颈状态。在此背景下,现有的主流研究范式已经很难再为管理学科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生命力,学科发展道路的转换势在必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真正推动管理学科的发展,更好地践行学科使命,仅仅在学科现有成果之上进行修补扩展难以根本改变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着力从源头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回归管理研究的初心和学科使命,以期为管理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合适的逻辑与方法论基础。
通过考察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科的发展历史,章凯(2014)a章凯:《目标动力学:动机与人格的自组织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指出一个学科的良好发展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选择正确的研究对象,并对其建立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型;二是拥有与该理论原型相适应的科学方法论;三是选择和创造同理论原型及科学方法论相匹配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这三个基本条件中,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论原型规定了相应的科学方法论,并进而规定了适合的研究方法,因而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学科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于对学科对象理论原型的研究。理论原型作为典型的元理论问题,有助于揭示一系列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原则,从而帮助研究者们认清研究对象的本质,并有利于以逻辑一致的方式整合本学科已有的研究观点和成果,bTsoukas, H.,“What is Management? An Outline of a Metatheory”,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5, 1994, pp.289-301.因而具有“理论的理论”之特征,可以驱动进一步的具体理论开发。c章凯、罗文豪、袁颖洁:《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形态与创新途径》,《管理学报》2012年第10期。在管理学科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无外乎组织和人两个方面。针对这二类研究对象,管理研究中虽然先后出现过不同的组织观(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等)d斯科特 W. R.、戴维斯 G. F.:《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文化人等),但这些不同的认识往往都带有“盲人摸象”般的片面色彩,整体上仍然未能够针对组织和人建构起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型。仍以领导力的研究为例,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领导风格,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是对于“领导力从何而来”这一基本问题仍然缺乏有效的回应,eHernandez M., Eberly M. B., Avolio B. J., Johnson M. D.,“The Loci and Mechanisms of Leadership: Explor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Leadership Theory”,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22, no.6, 2011, pp.1165-1185.更是未能建立起有关领导力的理论原型。正因如此,推进管理研究的源头创新,首要地便是要围绕研究对象发展出合乎实际的理论原型,这是学科发展的基础。
源头创新的另一层蕴涵在于对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注,以问题为中心驱动管理研究的开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加速转型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当代企业的管理实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迭代创新、互联网经济、无边界组织、平台战略等这些新颖的组织管理实践正在不断发展,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管理模式的基本假设,也自然地对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f章凯、仝嫦哲:《目标融合视角下分享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新思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年第8期。在这一背景下,管理学者唯有从学科的基本使命出发,深入地观察实践现象并进行理论提炼与发展,才可能在推动及引领管理变革的进程中发挥管理学科应有的作用,缩小当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过程自然需要学者们真正地以问题为中心,通过深入挖掘当前企业中的管理创新来为理论创新与发展提供现实素材。近些年来国内外案例研究的逐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体现出问题中心的研究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管理研究与实践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助于源头创新的历史机遇。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科学哲学的转向。在主流管理科学中,经验主义主导下的实证研究范式占据支配地位。近些年来,诠释主义、批判主义、建构实证主义等的引入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有实证研究范式的“坚固统治”有所松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是使得人们对于组织的思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同科学哲学观点的兴起与存在,将有助于管理学者在源头创新的过程中根据理论原型选择合适的方法论取向,而不是一味地试图以经验主义解决所有问题。第二,系统科学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正从一个封闭的、可逆的、机械决定论的简单世界转向一个开放性、不可逆性、整体性、能够趋向有序的复杂性世界。自组织理论就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杰出代表,并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系统、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研究中,a约翰·霍兰著:《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它强调系统的整体性、非线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为研究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管理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特征与系统科学的观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部分管理实践者也开始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如华为提出的“灰度管理”和海尔正在实践的自组织管理等。b章凯、李朋波、罗文豪、张庆红、曹仰锋:《组织——员工目标融合的策略:基于海尔自主经营体管理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4期。c周云杰:《互联网时代创业者资源(ER)平台构建——海尔推进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的创新探索》,《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年第10期。对于管理研究而言,系统科学的发展将有助于管理学者们针对组织管理系统建构起更加合乎实际的理论认识。第三,中国古代哲学智慧重放光辉。近些年来,中国管理研究学者也开始重视从古代哲学中汲取营养,尝试将古代哲学思想变成一种“后现代的智慧”,这将有助于管理研究的创新式发展。d黄光国:《“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管理学研究中的后现代智慧》,《管理学报》2013年第7期。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前任主席陈明哲教授指出,他提出和发展的动态竞争概念,就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eChen M. J.,“Presidential Address—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 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9, no.2, 2014, pp.119-137.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的整体性、动态性、辩证性等思想,对于理解复杂的组织管理实践也会带来独到的启迪。f谢佩洪:《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的本土管理研究探析》,《管理学报》2016年第8期。第四,管理实践的进步发展也为源头创新提供了机会。如前所述,当今企业的管理实践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中。尤其是,管理实践中对于人的需求和目标日益重视,标志着管理向人性的不断回归。这些管理实践的不断出现,有助于管理学者们反思和重构对于人和组织的本质认识,从而为管理学科的源头创新提供事实基础。
综上分析,推动管理学科的源头创新并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是既十分紧迫必要、又颇有可能实现。事实上,源头创新的背后意味着管理学科一次深层次的科学范式革命,并蕴含着跃上发展新阶段的机会。这一系列机会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都是公平的。对于本处在后起地位的中国管理学者来说,一味地跟从西方范式,或者是盲目地开发本土概念与理论都很难改变中国管理学界的从属地位。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历史性机遇,在学科范式转换的大势中努力推进源头创新,中国管理学研究就很有可能借此实现“换道超车”,为管理学科发展作出伟大的贡献。
四、源头创新的策略思考
那么,管理学者该如何推动学科发展的源头创新呢?笔者在此提出如下六点策略思考,作为源头创新和未来管理学科研究的可能取向,供学界同仁参考指正。
第一,建构理论原型。如前所述,一个学科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对研究对象建构起正确的理论原型。只有建构起学科的理论原型,才能根本性地促进学科的发展,否则研究成果也只是知识的堆积,而无法形成学科的主干。一个学科针对研究对象建立起有效的理论原型,就会驱动学者开展相应的问题研究。心理学从行为主义到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学者们从刺激—反应模型转向基于人脑的信息加工模型来理解人的行为。一般而言,人和组织是组织管理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然而,当前管理学科对于人和组织的本质认识既不深入,又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分歧,这使得组织管理学科陷入到盲人摸象的困境之中,无法完整地理解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组织管理学科亟需重塑并建立起一套正确的关于人和组织的理论原型,并运用这一理论原型指导后续的管理研究。
第二,聚焦现实问题。促进管理实践的进步是管理学科的基本使命之一,同时管理实践的发展与变化也常常蕴含着管理学科发展的机会。近些年来,组织管理研究的严谨性日渐强化,而切题性和实践关联性却相对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管理学科的基本使命。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如果管理学科不能在管理实践的发展中发挥助推作用,那这一学科的合法地位早晚将会松动。有鉴于此,在未来的管理研究中,管理学者们需要更多地聚焦于现实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变革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问题和重大问题。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内部的组织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旧有的基于信息不对称不平等发展出的层级结构,正在被颠覆和打破,个体的力量和价值不断崛起,而组织能否发挥好平台功能则日益重要。a陈春花:《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弥合》,《管理学报》2017年第10期。在这一系列的组织管理实践变革中,事实上蕴含着大量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当前我国管理学界倡导的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正是这一取向的直接体现。
第三,洞察管理事实。相对于管理理论而言,管理实践总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常常有十分具体的情境条件加以约束。因此,在基于管理现象探索与挖掘管理理论时,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被表象所迷惑,提高对于真实管理现象的洞察力。否则,我们建构出的理论可能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层面上,或者被表象所迷惑。举例来说,在当前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创新和探索中,很多都是特定的文化、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长远来看可能包含了一些相对较为落后的管理思想,并不符合管理进步的未来趋势与方向。如果管理学者们针对这些管理实践开发理论,试图为当前的实践“背书”或寻求合法性解释,那自然也不利于学科使命的实现。要做到洞察管理事实,一方面学者们要更全面地掌握不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运用系统思维深入思考现象背后的机制与运行趋势,挖掘现象的本质。
第四,转变科学哲学。从前文的回顾可以看出,目前的管理学科在学科哲学上有着明显不足。这种不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科学方法等同于科学,从而在研究中更多地是“方法中心”而非“问题中心”;二是现有的管理科学研究在思维特征上以线性思维、决定论、还原论为主要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非线性相互作用和系统复杂性的考虑严重不足,而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组织和人——恰恰是复杂的非线性开放系统;三是现有的管理学研究多以静态视角看待研究对象,对于动态变化的过程考虑不足。面对上述科学哲学上的不足,近年来其他一些哲学思想开始逐渐渗透到管理学科,例如,源自诠释主义、建构主义的新研究范式已经开始吸引学者们的注意,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展的管理研究。b胡国栋、原理:《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德性领导理论的本土建构及运行机制》,《管理学报》2017年第8期。不同类型科学哲学的进入,扩展了管理研究的路径选择,丰富了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思想的进入,也可能造成科学信念的动摇和丧失,从而不利于管理学科的长远发展。事实上,管理研究应该选择和拥抱哪一种科学哲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讲应取决于研究对象以及针对研究对象构建的理论原型。在哲学体系的选择上如果盲目地求新求异,名义上迎合了学科反思的诉求,其实可能更加有害于管理学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尤为强调系统内外的复杂性、非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与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较好的契合性,未来有潜力为管理学科发展提供更合适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第五,创新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方法不应该成为学者开展学术活动的起点或是中心,而应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即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方法为中心。因此,在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中,学者们一方面要对不同的研究方法保持开放性,根据理论原型和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大样本的统计调查、实验方法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案例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等,都是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它们都有各自的适用空间,不能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另一方面,对于长期以定量研究为尊的管理研究来说,我们需要深刻地反思,统计分析方法本身的严谨性无法替代理论或者理论解释的严谨性。如果管理学科迷恋于统计模型与方法,而忽视发展基础理论来揭示管理过程中的实体与机制,就会使得这些统计模型变成断章取义的变量组合,很难产生实际意义。
第六,兼容文化差异。对中国管理学者来说,在源头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应对文化差异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相信,理论发展有着不同的阶段,而其最高境界是理论普适化,即可以兼容不同文化情境的特征,并超越不同文化、而捕捉到人类和组织的共同本性。a章凯、张庆红、罗文豪:《选择中国管理研究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以组织行为学研究为例》,《管理学报》2014年第10期。一个能很好地理解、解释、预测和改变研究对象的理论通常具有很高的一般性,可以兼容不同文化情境因素的影响,这也是科学追求简洁性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理论对于现象之后与之下有关实体与过程的深层次规律的陈述应当是文化兼容的;而在理论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包括推导模型、衍生假设和实践应用时,研究者与实践者才需要具体考虑情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从这一点来看,在本土管理研究中,重视开发情境性理论就否定发展一般性理论或否定一般性理论的存在,这是极其荒谬的。因此,中国管理学者一方面要扎根本土,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出新的理论,并进行普适性检验,在检验中不断修正完善;另一方面,在管理学基础理论还很不成熟之时,应该做到胸怀大志,努力发展学科基础原理,超越民族文化,在洞悉人性和组织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构建学科基础理论模型,在更为普适的意义上为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实际上,基础理论发展了会大大促进本土管理理论的发展。
五、结语
在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寻找并发现具备生长潜力的学科源头是十分重要的。管理学科已经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事实上却仍然没有找到好的学科源头,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的成熟与进步。本文对目前组织管理学科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并从错误理解科学、错误理解理论、学者的学科使命感缺失这三个方面系统地剖析了导致上述困境出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强调回归管理研究的应有使命,通过源头创新直面当前的学科困境,并藉此推动管理学科的新发展。通过对学科发展历程和当前态势的研判,我们认为源头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并且也蕴藏着中国管理学界“换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
显然,源头创新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本文提出的六类策略取向虽有助于推动管理学研究的源头创新,但更多需要的是管理学者持之以恒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章凯(2014)b章凯:《目标动力学:动机与人格的自组织原理》。在复杂性科学的自组织理论启迪下,建构了一个关于个体心理世界的自组织动力学模型,揭示动机与人格的自组织原理,并通过一系列研究开拓新的理论发展空间,在管理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力,也在管理教育中得到了相当多管理实践者的认同与应用。这一理论体系自然还有许多未完善之处,但反思这一理论的建立过程,从人性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出发进行思考和自组织理论视角的引入,恰恰是从源头进行理论创新的现实案例。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分享有关源头创新的内涵和实现策略,期盼更多富有学科使命感的管理学者参与到源头创新的研究进程中来,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心态,共同推动管理学科的范式转换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