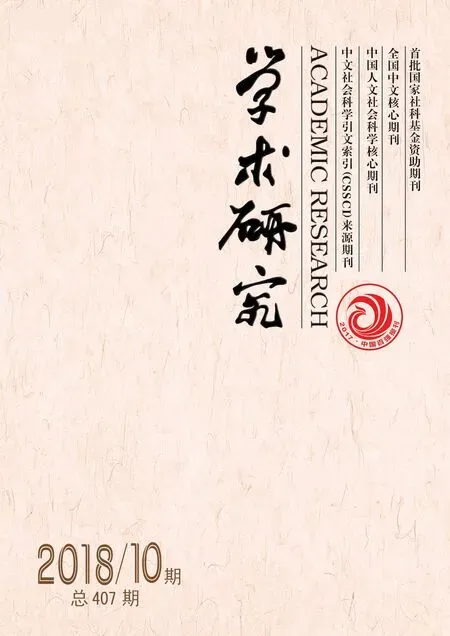侠情与侠意:以悲为美与以侠为累
——王度庐武侠小说再认识
庄国瑞 卢敦基
王度庐(1909—1977)是民国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北京人,满族,原名葆祥(后改为“翔”),字霄羽,“度庐”为其笔名。1938年至1949年期间创作武侠、言情小说34部,其中武侠小说18部,a王度庐:《宝剑金钗》附录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代表作为“鹤—铁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由于1949年后价值判断标准的转换,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武侠小说持歧视之态。王度庐的重新被“发现”,归功于叶洪生、张赣生两位研究者,b1982年6月28日至7月7日,台北《民生报》连续刊出叶洪生《 “悲剧侠情”之祖——王度庐》;1985年3月12日,天津《今晚报》刊出张赣生《闲话武侠小说》。他们都认为王度庐是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几位武侠小说作家之一,是“悲剧侠情小说”的创建者。进入90年代,关于王度庐的研究论文逐渐多起来,特别是2000年由《卧虎藏龙》改编、李安执导的同名电影在多国上映,2001年该片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原著作者同时被强力推回公众视野,获得不少研究者的关注。c比较有代表性的能够对王度庐创作作出整体评价的论文有:李忠昌《简论著名满族作家王度庐》(1990年)、李忠昌《论王度庐的文学史地位及贡献》(1990年)、刘大先《写在武侠边上——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2005年)、徐斯年《生命力的飞跃和突进——评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2006年)、关纪新《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2010年)、张泉《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2010年)。前四篇文章均以其武侠小说为研究重点,涉及侠情小说特点、文学史地位等,后两篇则从民族文学、重写文学史等视角谈到王度庐作为满族作家所体现的京旗文化以及沦陷区文学创作等。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人物形象、情感表现、小说视角等具体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武侠热”持续,有不少学子选择王度庐作为研究对象,如王艳《“英雄”的现代言说——王度庐“鹤—铁五部曲”研究》(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张瑾《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研究》(2008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刘明芳《仗剑江湖,只影天涯——论王度庐〈鹤—铁五部曲〉》(2010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等,也说明王度庐研究的影响在逐渐扩大。研究专著方面,张赣生、叶洪生、徐斯年等人的著作具有代表性。a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1991年)、叶洪生《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1994年)、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1994年)、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1995)、徐斯年《王度庐评传》(2005年)、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2008年)、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10年)。韩云波、宋文婕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王度庐研究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总结,梳理了关于王氏作品研究发端、深化、繁荣的过程,并提出目前关于王度庐的研究视角还不够丰富、基本没有不同意见之间的争鸣、没有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的突破性成果出现、王度庐文学的整体系统框架研究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建构等有价值的问题。b韩云波、宋文婕:《生命力的突进:王度庐研究三十年》,《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由王度庐武侠小说研究的现状来看,随着研究的深入,能够拓展的角度和思考的问题还有不少,不过“侠情”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另外王度庐在表现“侠意”方面也有鲜明特点,在深层基调上与早于或晚于他的武侠作家均不同。
一、侠情:以悲为美,未尽曲折
王度庐可谓是第一次将“情”作为武侠小说主体的小说家。在他之前,具有“侠情”倾向的作品,远者有唐代豪侠小说,其在发端,不过略有意绪,也无作家将之作为表现的核心,近则如叶小凤《古戍寒笳记》、李定夷《霣玉怨》、顾明道《荒江女侠》等,其中以顾氏作品影响最大,连载及单行本皆影响广泛,并且改编成电影、京剧,轰动一时。这部小说人物的选择与设置颇借鉴了唐传奇,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对《虬髯客传》《聂隐娘》的喜爱,语言虽时流于粗糙,但关键在于男女主角同闯江湖的潇洒与几番离合终成眷属的情缘,“把武侠、恋爱、探险等成分捏在一起,就给读者一种新鲜感”。c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相较于以前的武侠小说,王度庐写“侠情”的成功,概言之,在于以下三点。
(一)情意相通,绾结心灵之侣。王度庐的“侠情”不是故事的点缀,女侠不只是男侠的“助手”,或者虽然结合却只有“婚姻”不写“爱情”,他们是真正的“情侣”。当然这两点在顾明道那里也有体现,不过顾作中方玉琴、岳剑秋的离合似乎还没有摆脱传统章回小说及评书作品中巧遇、巧合等套路,而且琴、剑二人因为师父之命定下婚约,给人感觉结合是早晚的事情,作者的写作走向和读者的期待完全相同,削弱了人物“自我表现”的能力,失去了神秘性与吸引力。从情感性质来看,顾作中的情侣可谓是“世俗伴侣”,因为琴、剑二人的联系尚属外在层面,小说反复渲染男女主角才貌双全、胆气超人,但除此之外没有写出他们在精神上的呼应,只写方玉琴内心觉得自己和岳剑秋行事相合、又有师门长辈撮合,所以应该在一起。读者感受不到琴、剑之间“生死以之”的牵挂与缠绵,如果作品最终结局是方、曾结合,也并不难于接受,这说明顾作对情感的表现还是粗线勾勒、流于表面。相比之下,王度庐的男女主角便显出异彩,他们不仅是世俗伴侣,同时是“心灵伴侣”,对方均不可替代,相互也很明白对方内心的处境。李慕白对俞秀莲怀有深情,但坚守道义而牺牲双方的恋情,有很多人不理解,江南鹤就说他误读了几卷书,至有儒生之迂腐,但俞秀莲却知他此种心情,虽然不免哀怨,却并没有强迫李慕白作出任何违背其原则的承诺,俞对于李的体谅,让读者不仅惋惜二人之情,更深深怜惜女主人公的命运。玉娇龙与罗小虎其实没有结识的可能,更不可能成为情侣,但小说设置了荒凉大漠匪徒打劫的奇险环境,让男女主人公在隔离世俗的状态下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罗、玉二人不是不明白婚恋的不可能,但同时都被对方自由不羁的气质所吸引,他们的相知是一种青春的冲撞,又有原始生命力的吸引与冲动,这样的爱恋甚至很难用言语明确解释。李、俞二人之情有“柏拉图”式的深刻,罗、玉二人之恋则有“酒神精神”式的热烈,均在生命、灵魂的层次上发生了联系,所以说他们是“心灵伴侣”,这也正是王度庐写“侠情”超越他人之处。
(二)遗恨两端,悲剧力量动人。王度庐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意识,他说过,“美与缺陷原是一个东西”,“向来‘大团圆’的玩意儿总没有‘缺陷美’令人留恋,而且人生本来是一杯苦酒,哪里来的那么些‘完美’的事情?”a王度庐:《宝剑金钗》徐斯年总序,第3页。他的武侠作品尤其是“鹤—铁五部曲”基本贯彻了这样的思想,论者将之概括为“性格—心理悲剧”、“致力于表现悲怆哀凉之美”。b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7页。江小鹤、鲍阿鸾终于互释恩怨、共期携手,孰料阿鸾因伤而逝,遂成永恨;李慕白、俞秀莲本天造地设、两情相悦,但虽同游江湖,却难结鸳侣;玉娇龙、罗小虎相爱情浓,却终因家世悬殊而乖离。几对主人公的爱情无一不具有深深的遗憾。韩铁芳、春雪瓶固然终成眷属,但是经历了长辈去世、身世之谜得解、江湖争斗,他们相约隐居边陲,内心显然对世俗繁华宁愿保持距离,有一种经历大悲喜之后的沧桑与冷静旁观。作者在创作上主动追求悲剧效果,与其自身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王度庐出身于底层旗人家庭,幼经困苦,长而奔波,个性本就内敛,身体又为劳碌生活所损,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有切肤之痛。而且王氏喜欢《饮水词》,纳兰式婉约低回、哀感顽艳的意趣深得其心,细看他武侠小说几对主人公充满遗憾的爱情,不难感受到这种美学风格的影响。
(三)理念求新,突显现代意识。王度庐小说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引起人们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小说中情感呈现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现代性”。王度庐无疑是“审美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首先,写侠情重视个体,具有“去标签化”的特点。以前的作者往往是把某个人“放入”侠的概念或侠的群体中去写,让他们成为侠、具有侠的特质,王度庐则是“剥离”,把具体的“侠客”从群体中择出,然后写出独属于他(她)的特征,这是一种“‘反英雄’倾向,即把主人公作为‘人’来描写”,c韩云波:《审美与启蒙的悖论:从王国维的道路看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历程》,《江汉论坛》2017年第3期。这样无论写“侠”还是“侠情”都比较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取得了突破。在王度庐之前的武侠小说中侠客自然也有情,但“情”一般不会成为人生困境,尤其是“大侠”们或一时柔肠百转也终会当机立断。李慕白在小说中的定位是“江湖大侠”,但他一点都“不像”,《宝剑金钗》第22回里有个细节写德啸峰、铁小贝勒等人“饮酒谈笑,就以李慕白为谈资,倒是畅快”,李为情所困在他们看来非常有趣,德啸峰等人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大众对于“侠”的看法——李慕白的行为背叛了他的“身份”。玉娇龙也是一种背叛——背离她所属的阶层,贵族小姐基本是柔弱的代名词,玉娇龙不是;贵族小姐婚恋须门当户对,玉娇龙不仅不是,而且选择了与自己身份最为对立的强盗。这对于《儿女英雄传》的情感模式是一种颠覆。何玉凤也是将门之后,也属贵族阶层,闯荡江湖时也颇多纵恣豪气,但小说最终让她与安骥成婚,回归了所属阶层,这是文康的局限之处。玉娇龙虽未能与罗小虎终身厮守,但她大胆地追求了爱情,也明白自己最终不可能回到贵族家庭。其次,在重视个体的基础上突出人物个性。关注个性化情感,重视内心的独特感受与完善,这一点也契合现代人标榜“自我”的特征,所以他的经典作品在今天仍有广泛受众。李慕白这个形象就很“自我”,很多时候都觉得周围人并不理解他。比如史健、德啸峰、铁小贝勒就他与俞秀莲之事都曾劝他要体念别人、要考虑二人之间的感情、如果难成眷属也要处理得果断一些,但李慕白就是难以绕过很“自我”的性情——既无法按照朋友们的建议做,又无法割舍对俞秀莲的牵挂,竭力在真实情感与不违背道义之间寻找平衡,活得浪漫又沉重,李、俞之间情感给人印象深刻也得益于此。所以说他的小说突破了传统的“情节中心”的叙述结构方式,发展到了“性格中心”层次。d徐斯年、刘祥安:《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现代”走向——民国时期武侠小说概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相比之下《荒江女侠》中的感情就不具有强烈的个性,基本在“佳偶天成,巧结良缘”的框架下,琴、剑之情只比别人多几分勇决潇洒而已,并无更多独特品格。再次,“心理活动”成为表现侠情的主要方式。心理活动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向来是只言片语,但在王氏小说中是重要表现手法。李慕白的优柔多情基本不由情节体现,而由心理活动体现:《宝剑金钗》第4回求亲失意返回家中终日颓废,第6回与俞秀莲并辔而行时偷眼观瞧与内心凄然,第7回于旅途中再次想起俞而决定斩断情思,第18回在庙中一会儿想要去向俞家求亲、一会儿又清醒告诉自己实在做不得。在武侠小说中这样写情在王度庐之前是没有的。
但是王度庐呈现的“侠情”也有明显的缺陷。
(一)“以悲为美”的格调单一且不适于武侠。“鹤—铁五部曲”的主角中只有韩铁芳、春雪瓶携手成双,结尾似乎也恩怨俱了,但雪瓶不忍铁芳看见那已补缀回原处的一角红罗,还是带出了玉、罗二人惨逝的悲凉气氛与深藏两个年轻人心底的忧伤,可以说“鹤—铁五部曲”均以悲剧收束,在整体创作格调上显得过于单一、缺少变化。另外,以“悲剧”写“言情小说”毫无问题,而且惯于将梦打碎让人清醒,所以在言情小说中表现主人公的幻灭、揭露虚伪面纱下的社会实质都更能让人印象深刻,王度庐言情佳作《古城新月》《落絮飘香》《虞美人》《朱门绮梦》《琼楼春情》等均如此。但武侠小说却有不同的“气质”,“侠”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自从出现就不是以“幻灭”为目的,无论“侠以武犯禁”,还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等诸多关于“侠”的表述,都表明它是一个突破束缚、具有力量感、给人希望与勇气的概念。它是人们的精神依托,是一个“梦境”——希望,“侠”与“秩序”是对立的,是人们于社会秩序之外追求的一种机会,顺遂社会秩序、道德秩序就难以显现“侠”的特质。比如金庸笔下的情侣,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胡斐、苗若兰,令狐冲、任盈盈,这些人物出场时或性格、或身世、或门派等差异极大,看上去都没有走到一起的可能,令读者激动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有“打破”规则的能力。这是武侠小说能够带给读者激情、想象、升华的地方,而不是像言情小说一样津津乐道于现实情感纠葛,去哀叹主角们的不幸。所以王度庐武侠小说“以悲为美”固然独特,但是“侠”因为顺遂、屈从于各种世俗障碍而最终形成“悲剧”,既终结了读者的想象,也终结了“侠”的超越性,所以完全的悲剧笔调不适合于武侠小说创作。
(二)“初见即是终结”,小说情节与人物性格发展受限。首先,主人公爱情不能发展受制于单一力量,限制了情节能够拓展的维度。比如李慕白、俞秀莲之间的障碍,可归结于一个核心问题——道义,受朋友鼓动前去比武求亲的李慕白得知俞秀莲已与人定亲后,心里虽放不下,但无论如何不肯再主动追求,李慕白一切的忧愁苦恼只为维护“道义”的正当性,没有考虑过“感情”的正当性,小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封死了感情发展的路径。所以无论后来孟思昭苦心托付,还是众多朋友相劝,都不能改变李慕白的想法或者说作者已经确定的情感逻辑。罗小虎与玉娇龙也主要纠结于一个问题——门第之差,当玉娇龙于第一次分别之际提出要罗小虎以官方途径致贵时,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确定——永无结合的可能。涉及爱情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在于人物感情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多种可能性,如此才有可能因为感情的变化而引出曲折的情节,王度庐的小说把侠情作为重点表现对象是其突破,但是未能让侠情发展实属失策。其次,由于人物感情不能发展,重要人物的性格几乎没有发展。李慕白、俞秀莲是王度庐塑造最成功的形象,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两人就像一个家族里的“好孩子”一样,从一开始处理事情就偏于成熟沉稳,到结尾也很沉稳,这就是他们的病症所在。小说中表现李、俞情感发展最激烈的地方不过是:宣化孟府俞秀莲夜访李慕白,言及自己孤苦无依,李则安慰俞自己会尽力帮她寻找未婚夫,但二人相互之间依恋不舍之情也溢于言表;李慕白处理完孟思昭之事,回京后没敢见俞秀莲,最终不辞而别,俞雪夜追李,两人因误会动手随后赌气离开,心中均很难过;李慕白下狱俞秀莲往救,李十分感动终于说了几句实话:“俞姑娘,你现在身世如此凄凉,完全是因我所致,我一日不死,也一日不能心安。”这几处已经算是李、俞交往中感情表现最直接的地方了,除此之外,多数情感表现均为点滴的内心活动。本来爱情关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具张力的情感体验,热烈激动、夺人心魄应该是正常状态,李、俞的交往却显得缺少变化、呆板,因为情感发展的程度已经被作者限定,所以人物性格多侧面深入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基本停留在了出场时的状态。
二、侠意:侠其为累,义岂能弘
武侠小说之所以吸引人,基本上在于笼罩整部作品的“侠意”,也就是“侠”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涵、意蕴。一部武侠小说里会有几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其中不顾自身安危、竭力维护社会与人性公义的“侠意”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点,纵然爱情、武术、江湖极尽变幻之能事,也不会是成功的武侠小说。王度庐的小说受到大家喜爱,除了“侠情”之外,自然也得益于作品中各路侠客身上所表现出的“侠意”,但是王氏小说的“侠意”却与多数武侠小说作家有区别,其核心寄托不在武侠,主人公们的遭遇也与一般大侠不同,比如“鹤—铁五部曲”中除了韩铁芳、春雪瓶之外,其他人似乎都无一例外受到学武行侠的“拖累”。
(一)虽写武侠,但轻视武侠。读过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即王氏不擅长表现武功,“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a叶洪生:《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275页。首先,作者不谙武道,只能凭借书本知识以及自己的理解来写,所以流于表面化、简单化。书里涉及打斗的场面通常都采用勾勒描述的语句完成,而不涉及武学招式表现,如“玉娇龙追上了李慕白,宝剑是如长虹倒挂,从上砍下;然而剑才落下,眼前的李慕白又忽然不见了”,“她的剑法精练,使得别人只能看得见闪闪的寒光,如白鸽子在眼前乱飞似的,但又都眼花手乱,无法招架”,如此之类,所在皆是。其次,作者没有在这方面刻意用力做深入研究。“鹤—铁五部曲”是前后相关的作品,但这五部小说里的“江湖”没有完整的门派体系,只有一些或镖师与自己徒弟、或地主豪客、或强盗形成的派别势力。武林高手有,但对“武功绝技”的表现乏善可陈,江南鹤、李慕白剑法很好,但没有写出剑法的精妙;点穴法、袖箭被渲染为高超的武功;“武功秘笈”也只不过是静玄的“人身穴道图”与哑侠的“九华拳剑全书”,可以看出作者连秘笈的名字其实也没有特别考虑过,只是情节需要顺手一写而已。所以主人公们无论学艺的经历、学到的武艺,看上去都没有特别令人震撼、叹为观止之处。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度庐其实是营造了一个“武侠世界”来写“情”,“武侠”不是他表现的重点。“武”弱、“侠”弱而“情”强,让人不能不得出作者轻视武侠的结论。
(二)武功越高,却越是困顿。王度庐笔下的侠客,不仅不能凭借自身的武艺能力改变命运,在与世俗的纠葛之中,“武术”与“行侠”还屡屡为自己招致困厄,而且武功越高,遭遇的困境愈加严重。玉娇龙最为典型,在新疆长大的玉娇龙,从小任性骄纵,七八岁便会骑马射箭,还常随父亲打猎,随后几年玉府所聘家庭教师不仅教会了她诗词书画,还暗中传授了武功,玉娇龙成长为一个外表秀美乖巧,内里则有智谋擅武功、孤傲不群的奇女子。这样的人物注定不会追求寻常官宦小姐的生活,她理想的恋人也绝不是地位高贵即可,必定要在精神气质上能与她呼应,所以小说表现了大漠绝域充满奇情的“龙虎之恋”。但随后在与世俗的交锋中,当玉娇龙想要凭借武功实现自己的自由时,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一并袭来,她越挣扎束缚越紧,形如“困龙”,最终被迫以计脱身,行走江湖。如此似乎自由了,但她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事实上不可能融入江湖侠客群体,人虽在江湖,心则牵挂侯门,并非眷恋富贵,而是担心影响家族,所以后来虽然成了武功绝顶、人人畏惧的“春龙大王”,却是内心凄凉的一条“孤龙”,从玉娇龙来说,她“伤己”远过“伤人”。对于其他主人公们作者行文过程中似乎也在暗示“不学武行侠”会更好。在“鹤—铁五部曲”中唯有江小鹤是一出场就必须学武的,因为背负家仇,但是江之学武行侠并没有能改变自己飘然一身、伤心孤独的局面。从内在理路来讲,是王度庐并不觉得“学武行侠”可以突破人生困境,家庭、社会、道义的责任与障碍是“侠”也难以逾越的。
(三)萦于私义,而公义难酬。武术与仗义之举帮助侠客们实现了行走江湖的愿望,但王度庐小说中的侠客“不具备(实际上是作者根本不认为他们能够具备)一剑定乾坤的能量,无法成为拯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包打天下的‘救世主’”。b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3页。所以他笔下的侠客都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多数时候都纠缠于“私义”:《鹤惊昆仑》围绕江小鹤复仇展开,鲍振飞因仇恨妻子有外遇,而痛恨一切男女私情,由此纠集门徒杀死了有外遇的徒弟——小鹤之父江志升,引发小鹤学艺、复仇等一系列行动。李慕白、俞秀莲两人涉及的情节在《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三部中均有,前两部分量更多。李慕白是王氏笔下“大侠”的代表,但察其所行之“侠”,主要还是“私义”的范畴:“千里送嫁”,一则对俞秀莲有爱慕之情、二则俞老镖头与自己师父有交情;营救孟思昭是因为孟之受伤完全因自己而起;另外与何剑娥、魏凤翔、冯隆、冯茂、张玉瑾、黄骥北、静玄师徒、玉娇龙等人的争斗,或为帮助朋友、或为江湖意气、或为报仇雪恨、或为武功秘笈等,“为国为民”的公义基本没有。娇龙、罗小虎二人,玉娇龙在没有离家之前的所作所为,解决自己婚姻矛盾、维护家族利益均属“私义”,其他帮助碧眼狐狸伤及蔡九、盗取青冥剑等则属不辨是非、任性妄为。
这就需要问:为什么王度庐不把自己小说里的侠客塑造成顶天立地、领袖群伦式的人物?首先,是特定时代“英雄没落”局面的压力。“鹤—铁五部曲”创作于1938—1944年期间,其实稍早的时候1935年老舍在《断魂枪》里已经深刻揭示了“武侠群体”的没落,外来侵略势力用枪炮无情地击醒了古老东方民族的春秋大梦,时代变迁让江湖镖师、侠客们的生活价值与人生追求失去了意义,过去的辉煌只能封存在记忆里,他们不得不面对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自信自保都不可能,遑论张扬与炫耀?纵有“侠客”出现,也无法改变社会局面。其次,是写作者价值感的失落。从王度庐自身的经历来看,少年时自学成才颇有奇气,但纵横漂泊总不如意,最后以笔墨谋生,虽写武侠但处境困顿,竟不能以之谋生,有时甚至不得不做贩夫走卒的事情。这样的状态之下,写作者内心纵然有“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却是绝难生出“乐观豪迈”的激情去塑造一个个生龙活虎、建树伟业的形象。时代与生活的挤压,影响着创作者落笔时的选择。再次,是外在政治环境的制约。处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又居住在敌占区,以文字谋生的人有说不出的苦衷。王度庐在青岛,连载小说的《青岛新民报》是日伪政权机关报,想来热切谈论历史、积极抒写家国民族的豪迈情怀是不可能的。
所以王度庐虽写武侠,但“以侠为累”。通常来说对“侠”的“价值崇高感”衍化拓展方向无疑是正向的、积极的、更增其雄伟气势的,但因王度庐“以侠为累”的内在思维模式,导致他的拓展是逆向的、消极的、弱化了侠的能力与抱负,“消解”或者说“瓦解”了侠客价值的崇高感。王度庐本身采用的又是一种接近生活真实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这造成了他笔下侠义人物相对“平淡朴实”,缺少“超尘出世”的雄强与飘逸。总体上看近代以来从“南向北赵”到“北派五大家”,确实处在“武侠意识形态”逐步发展提升与成长的过程中,都还在探索与表达各自意见,还没有出现集大成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处在发展道路上积极创作的作家们在观念形态上不完备之处。
三、结语:重新讨论王度庐侠情小说的意义
王度庐作品得到大众喜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他的确开拓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侠情小说”不是集大成的经典,但可以说是发展道路上的经典。他的作品有自己的艺术价值与阐释空间,意识形态、文化权力的变动曾让他的作品遭受灭顶之灾,但是随着时代以及文艺批评价值取向的变化,经几位“发现人”大力揄扬,其小说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与定位。今天再次展开讨论的意义在于不同时期读者的看法——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前文提到过多位学者均认为王度庐在“悲剧侠情小说”样式的创建方面功不可没,张赣生尤其指出:“‘鹤—铁五部作’是王度庐早期的成名作,是他奠基立业之作……成功地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a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关于“完善形态”这一提法,我们以为,与其说是“完善形态”,还不如说是“完结形态”更为妥当,他的小说对后人是一种启示,但是后来没有人模仿他,没有人以悲剧笔调、牵扯于世俗观念来写侠情,显示出他的模式难以为继。王度庐“以侠为累”的观念,更是武侠小说的天敌,不仅限制了小说之内“侠”的发展,也限制了小说之外“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