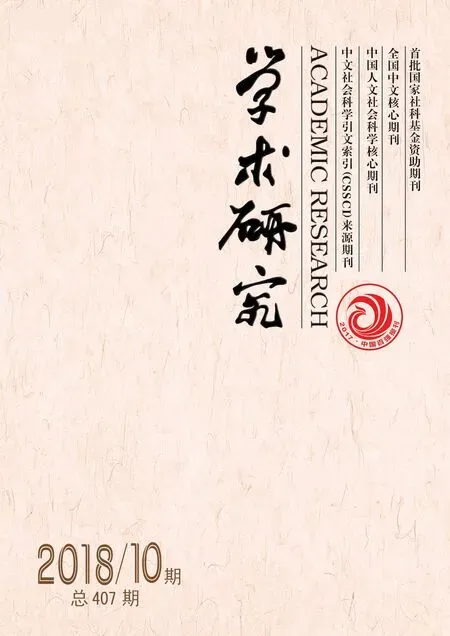历史文化:当代德国史学理论的一个范畴
尉佩云
就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言,相较于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内的纷繁硕果,大陆哲学传统下德国史学理论界未免有些沉寂。即便如此,相伴英美的“语言学转向”,德国史学理论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思考,“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便是一例。沃夫冈·哈特维希(Wolfgang Hardtwig)在对历史文化的概念解释中提到,历史文化概念在德国的历史讨论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并且哈特维希本人给历史文化的定义是“历史知识在一个社会中展现形式的总和”(Hardtwig,1990)。哈特维希总结道:“无论如何,历史文化是从下列认识中得出的结论:一个社团或者社会的过去并非天然给定的,而是文化性地创造出来的,在历史文化描述的模式与复杂性中,它接受了象征性凝练的各种形式,其重要性在于阐明这些形式的目的、实现与功用,并于它们的关系中进行反思。”同时,哈特维希认为,在对过去进行现实意义的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从“社会”向“文化”的范式转移,这种转移所表达的思想是:针对现实性、诠释模式与价值判断的观点并不仅仅被人们理解为史料兴趣的功能,人们应该认识到,它构成了一种承受历史变迁并且具有相关的开启意义构建进程的整体(即德文的“Sinnbildung”)。“语言学转向”使得人们认识到美学在历史知识的构建中具有的重要意义。此外,在传统的历史意识的思想范畴以外,“记忆”在人类历史认知的基础性层面具有了可信度,并在人类的精神层面和行动导向中具有了思想效力。a
从哈特维希以上的解释中可以看出,首先,“历史文化”概念的出现本身是在历史研究接受了历史知识具有的构建性特点和美学维度的存在之后。并且在认知性层面而言,历史文化并非虚妄无物,而是以一种“象征性凝练”的方式对社团或社会的过去进行处理。其次,“历史文化”概念的出现和兴起和20世纪史学研究的总体性变迁是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量史、社会史等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潮流逐渐式微,代之以文化史(或所谓新文化史)研究趋势的兴起。其中代表性的比如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a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1975.、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b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First published in Italian as Il formaggio e ivermi, 1976.等文化史研究作品出现,成为继史学社会科学化之后持续至今的范式。这提醒我们历史文化是一个史学理论范畴内“后发性”的理论思考和构建。
一、“历史文化”的总体思想形态
对于中国的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学家、乃至普通大众而言,“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历史文化”可以理解为“历史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历史与文化”。就一般性层面而言,这些理解都是具有对象性、认知性特点的概念,甚至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个社会中社会精英具有的学识水准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情形是,“历史文化”在中文语境中被视为一种具有认识论特点的知识形态或者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学术界,历史文化是一个更加泛化的概念,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逻辑。c就笔者所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思想概念,在中国现在的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研究和讨论中是缺席的。
而在德国的学术界,“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并且是以替代“社会”这个概念的面貌出现在德国历史学界。约恩.吕森(Jörn Rüsen,1938—)作为当代德国史学理论界的代表性学者,“历史文化”这个概念是由吕森引入理论界的。在吕森的体系中,“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个我们通常理解中的、泛化的知识形态所指(当然,在最基础的层面而言,历史文化肯定是具有认知论和作为知识形态的特点)。他将历史文化放在一个历史哲学的理论范畴中,以历史哲学的思想逻辑来看待这个概念在整个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意义。我们可以将历史文化理解为历史和历史思考在现代社会及人类实践生活中具有的地位和意义伦理。无疑,历史文化一般被理解为经验层面的概念思考,而吕森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将历史文化这种经验性的人类思考范畴诠释为具体的理论范畴,使得历史文化成为现代历史哲学思考的领域和对象。
吕森给历史文化先后下了两个定义,他在20世纪90年代论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定义时写道:
从历史意识到历史文化仅一步之遥。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历史意识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的作用,那么就可以看到,历史意识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触及并影响人类生活几乎所有领域的文化功效(Kulturleistung)。因此,可以将历史文化定义为历史意识在一个社会生活中对(社会生活)实践有效性的表现。作为意识的实践,历史文化中基本涉及的是人类的主观性,是意识的一种活动。d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Schwalbach: Wochenschau Verlag, 2008, S.235-236.
在最近的论述中,他将历史文化定义为:
历史文化是历史意识意义形成功效(Sinnbildungsleistungen)的全部总和。它包括特定的时间过程中人类在面对他们的生活、行动、受难时的文化实践导向。历史文化将人类定位于一个时间变化过程之中,在其中,就是人类行动和受难发生之地,并且,人类本身的行动和受难在历史文化中得以在此确认和完成。历史文化的方向就来自于我们对人类过往经验的诠释,由此我们同时得以理解现在和开启未来视角发展的经验策略。eJörn Rüsen, Historik. 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Köln: Böhlau, 2013, S.221.
从以上吕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前一个定义中,他将历史文化定义为“历史意识在一个社会生活中实践有效性的表现”,在后一个定义中,他认为历史文化是“历史意识的意义形成功效的全部总和”——总的来看,正是由于历史意识在社会实践生活领域的实现和展现,历史文化才得以形成。至于这两个定义在语义学层面的差异,“历史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实践有效性的表现”这个过程就是时间经验的意义形成过程,因而历史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实践有效性的总体性展现就是历史文化。历史意识之于社会生活实践中有效性的展现过程昭示了历史意义的形成,这在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如果历史意识不能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展现其有效性,那么历史意义就是缺失的、无法形成的;历史意义如果已经形成,说明历史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完全能够实现其思想和精神效力。由此,吕森在不同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定义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诠释的角度存在差异——第一个定义更加重视历史文化作为理论逻辑形成的结构性展现;第二个定义更加强调历史文化在人类行动和受难的整体性经验层面的地位和角色。
因而,我们可以将历史文化理解为历史意识在人类生活中的精神实现和思想效力的发挥。而历史意识的精神实现和思想效力的发挥过程却是以历史记忆(Gedächtnis)和历史回忆(Erinnerung)a在英文写作中,吕森将这两个德文概念通常分别作Gedächtnis-memory、Erinnerung-Remembering(或Remembrance)。在德文写作中,吕森倾向用Erinnerung来表示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回忆”。笔者就此问及吕森在他看来这两个德文概念是否具有思想差异性,他并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性。然而在笔者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吕森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还是有些微的差异:他用Gedächtnis来表示更加鲜活的、直接的、短时性的记忆,而用Erinnerung来表示总体性层面上社会性的、长时段的、带有建构性的记忆,这也是在英文中他在一般性层面用Remembrance来表示“历史记忆和回忆”的原因。为媒介或者实现手段。就历史意识的涵盖范畴而言,它更多的是指具有专业化和理性化的人类意识分支,对于人类无意识和前意识的的倾向没有更多的重视。历史意识作为精神范畴,它为专业化和学术化的工作成果及社会实践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历史文化相对专业化的历史实践领域而言是一个更广阔的范畴。相应地,在其精神范畴中,我们不仅要给予历史意识以足够的重视,还要对人类历史无意识和前意识(Un- und vorbewusste)倾向加以关注。因为作为历史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实践有效性的表现,历史文化不仅涵盖了历史意识所给予时间经验的意义形成,还接受了某种无意识和前意识状态影响下的、“现时化”了的过去经验的思想效能。因此,在历史文化这个更大的思想概念中,吕森将其精神动力和促动机制从历史意识的焦点中扩展开来,以“历史记忆”这个概念试图探讨包括无意识和前意识在内的历史意识对人类实践生活的影响和塑造。因为,在“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进入我们的研究领域时,我们必须考量概念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对此,吕森说:“如果我们能够一般性地总结出一个历史记忆的特征的话,那么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有范畴化要求的术语就具有了合理性”。b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S.23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历史文化的功用性分为三个部分来看。首先,从学科范畴上看,历史文化是沟通专业的学术研究与人类的实践生活(Lebenswelt)的理论范畴。吕森的史学理论总体上是一个从人类实践生活需求出发回到人类实践生活并对其具有导向作用的过程,其中,专业的学术研究和人类的实践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c参见尉佩云:《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途径——以约恩·吕森的学科范型论文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建基于他的第一个定义的逻辑基础之上,即历史文化是历史意识在一个社会中实践有效性的表现。正是通过历史意识的实践有效性,将专业范畴内的历史意识和广阔的人类实践生活结合起来。由此,历史文化在其中起到了理论桥梁的作用。
其次,从历史意义的视角看,历史文化是现代社会的意义方案和可能性探索。在传统的历史意义方案(比如起源神话、宗教以及一切元理性的变体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其思想效用之后,我们如何为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当然包括人文学术研究活动)寻找或树立一个合理的意义解释?没有意义的生活是荒谬的、散漫无际的,d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见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等待戈多》这种没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戏剧模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幕意义缺失状态下的生活:无序而且散漫,琐碎而且荒谬。这个若有若无、来又不来、像“漩涡的空心般具有吸引力”的戈多,我们其实可以将其看作现代社会的意义,而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种种荒谬行径正是因为戈多作为意义的缺失而导致的结果。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一个具备可理解性的思想基础之上。意义作为人类受难的出口,将这些洪荒、散漫的历史给予了人文性诠释,由此将痛苦的人类历史经验带入了历史的(人文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吕森的第二个定义中,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意识意义形成功效的总和,其本身就是作为现代社会中人类实践生活的意义方案和可能性探索的领域而存在。
第三,从形成机制上看,历史文化是人类历史意识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实现。我们遵循形式逻辑来分析这个概念的推论。作为论证的第一个层次的“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相互联系”a耶斯曼对历史意识的经典定义,见Karl-Ernst Jeismann, Geschichtsbewusstsein, In: Klaus Bergmann(Hrsg.) Handbuch der Geschichtsdidaktik. Düsseldorf, 1985, S.40.的历史意识,内在地包含着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最为基本的三个历史时间维度的思考。由此类推,作为历史意识实现和具体化的历史文化,天然地也包含着在文化实践层面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三维的探究和思考。因而,在历史文化的形成机制层面,由历史意识所扮演并促动的对时间的感知和诠释,以及历史时间的导向和目的形成了历史文化。而对时间的感知和诠释、时间过程中的导向和时间目的之预设等等都是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等作为人类精神范畴的产物。
那么,在作为不同促动机制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意义构成和思想差异呢?
二、“过去的迷思”:关于历史意义
独立的、单纯的过去对于现在有没有意义?或者说,独立的、单纯的过去本身能否存在?过去,或者历史思考中所谓的“过去”从来不仅限于时间的流逝这样简单。当然,由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时间距离的诱惑,这是给予人类历史思考和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在此,人类的好奇心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我们想知道在永远无法再次回归的“过去”之中生活的人们是否和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描述其鸿篇巨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写作动因时说:“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临近傍晚,我正坐在卡皮托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朱庇特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心中首次浮现出写作这座城市史的想法。”bEdward Gibbon, Memoirs of My Lif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etty Radice, Penguin Classics, 2006. p.161.吉本在其于意大利的“伟大旅程”(Grand Tour of Itatly)中,在罗马废墟上发思古之幽情成为写作这部经典的动因。此处的“发思古之幽情”可以视为跨越时间距离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促发,正是由于这种对“往昔之幽幽,深不可测”的历史意识的诠释和阐发,成为具体探究并撰写罗马衰亡史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纯粹逝去的时间过往本身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横亘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时间裂隙促使我们产生了认识论的兴趣,并为历史想象留下了空间。
过去本身的性质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有不同的阐述。当然,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史学理论的元问题,即过去本身是否真实地存在还是它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话语文本之中?由此一般化地将这两类学者视为实证论者和建构主义者。当我们论及过去的地位和状况时不可避免地要考量其和现在的关系,吕森在论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时说:
在现今的史学理论领域内,在历史意义生成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是建构论的方式。过去的意义被认为是归属于过去,过去本身却对该意义并没有影响。但我认为,过去本身已经以历史发展的结果的方式展现出来。在此过程中,历史思考得以呈现并且也深受其影响。这个“展现”可以称之为传统(This presence can be called tradition)。在历史学家对过去进行构建组织之前,过去已经自我构建为现在作为过去发展结果的方式呈现于世界中。因而,在“过去”被主题化诠释为“历史”之前,“传统”在历史思考中具有持续有效性。cJörn Rüsen,“Tradition: A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ense-Generation and its Logic and Effect in Historical Culture”,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51(Dec. 2012), 45-59.引文出自45页。
在“过去—现在”这个二元时间关系的历史意义问题上,吕森继承的是德国历史哲学传统中的“历史意义的不可预想性”(Unvordenklickeit)的观点,认为过去及过去的意义本身对“现在作为过去的结果”呈现方式的“建构”是具有先在性的。aUnvordenklickeit,一般而言,一方面指的是“过于久远而难以忆起的时间”(J. H. CAMPE: Wb. der Dtsch.Sprache 5 (1811) 236.),另一方面指“超过记忆以外的缘故的开端”(GRIMM, a.O. [1] 2149; vgl. Art. ‹Unvordenklich› und‹Verjährung›, in: W. T. KRUG: Allg. Handwb. der philos. Wiss. (1832–1838) 4, 322. 371;)。“Unvordenklickeit”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出现,是出自于谢林(F. W. J. Schelling)的“论不可预想性之一”(an sich Unvordenklichen u. Ersten)及其“什么是真实的开端”(was wirklich Anfang ist)(F. W. J.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Fragmente [1811/13], hg. M. SCHRÖTER (1979)211.)。谢林对该概念的发展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àνυπόθετoν”,即“真实”、“不造假”(PLATON: Resp. 511 b; vgl. Art. ‹Voraussetzungslosigkeit›.ARISTOTELES: Met. IV, 2, 1005 b.),同时这个概念建立于谢林“形而上学彻底的失败”的观念基础之上。谢林援引康德的说法,在康德看来“这是人类理性的真正的深渊”,因为在人类的思考过程中,每一个条件之前总要附加另外一个条件从而使得这个条件成为可以理解的,但是绝对的不可理解性是无条件的,因为在其前面再也没有一个条件存在了(KANT: KrV B 641; vgl. SCHELLING: Philos. der Offenb. I, 8. Vorles. SW II/3,163ff. KrV B 620f..)。因而,在人类理性深渊之边际,本初的起始是无条件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预设条件。所以,谢林将“不可预想性(Unvordenklickeit)”甚至视为“不可认知(理解)性(Undenkliche)”。以上解释参见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ed.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Gottfried Gabriel. Band 11: U-V.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1, S.339-341。吕森在对过去本身的性质考察中反对建构论者,但他本身并没有走向实证主义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过去并不是具有主体状态的时间维度,而是以现在作为其发展结果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是说,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具体可辨的时空关系的影响状态,而是一个作为意义塑造结果的影响状态。那么,问题就被归纳为,在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过程中,过去是以何种意义方式展现为现在。或者说,在过去到现在的过程中,历史意义的影响和形成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如何在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中演变的?
我们深入到历史意义内部逻辑来看上述问题,吕森对历史意义的定义是:
意义指的是人类世界的时间延展在主观性模式中得到的诠释。任何转变看起来都是有意图的,仿佛他们受到了目的意志的影响。意义概念与意图和目的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目的性则将人类的行动作为一个能进行思维和反思的主体活动凸显出来。b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Sinnbildiung, S.18.
可见,历史意义本身在德国的历史哲学传统中既不是一个实证主义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建构论的概念,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过去的意义对现在的影响是确实的;而人类理性对历史意义的主观性诠释却是带有建构论色彩的。而在吕森这里,历史意义本身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概念——在对历史意义的前提预设进行忽略的基础上,历史意义已经替换为由“过去”到“现在”这个时间过程中的变化、目的意志、未来导向的综合形成。像皮特·莫兹所说的历史意义对于吕森而言“仿佛圣杯中的精神泡沫在源源不断地为他流出”。cPeter Munz, Review of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Vernunf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4, No. 1 (Feb., 1985), pp.92-100.因此,在“现在”作为“过去”历史发展结果的呈现这个问题上,吕森用“Presence”这个概念来表达。“Presence”在表述过去的时间经验在现在人类生活世界的影响彰显的过程中,即在指涉过去的时间范畴的“现时化”影响时,吕森用“传统”这个概念来表达。此处的“Presence”起码有三层含义:首先,过去以现在作为结果的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为“现在性”;其次,这个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过程作为历史过程而言是真实可辨的,就表现为过去在现在的“在场性”;第三,现在作为过去的存在和表现模式,“展现”为“现在”。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过去在现在的“在场性”而言,荷兰史学理论家艾克·鲁尼亚(Eelco Runia)在《在场》(Presence)一文中对此作了陈述。dEelco Runia,“Presence”,History and Theory, Vol.45, No.3(2006), pp.1-29. 该文后来收入他的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鲁尼亚在该文的开篇便说:“历史哲学家长久以来都被‘意义’这个概念引入歧途——起先是不断追随,后来是发誓抛弃……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里,历史哲学家们试图肃清他们的(也是我的)学科内力图确立意义的企图。”e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49.在对意义和在场的关系中,鲁尼亚写到:
我的文章(指《在场》——笔者注)立意在于在追寻越战退伍老兵的回忆时,在拥有一个由他们所爱的人的碳(指骨灰——笔者注)所制成的钻石以纪念他们独特的生命时,在世贸中心纪念日上阅读那些受难者的名字时,在这使人扭曲的重聚中,在这些可比较的现象中,并不是“意义”的缺失而是我更愿意称之为“在场”的缺失……“在场”在我看来,是“伸手可触及”的,它既不存在于文本形式中,也不是建构出来的,“在场”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那些人物、事物、事件、感情。“在场”呼吸着生命的低语和真实使之成为常规和陈词滥调(cliché)——“在场”是完全实现的事物而非被允诺的事物。a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53.
通过鲁尼亚的这段陈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场”其实是鲁尼亚试图用来替代“意义”这个原本作为西方历史哲学中心的概念。“意义”伴随着现代社会的祛魅和元理性的分离(“Vernunft”成为“Verstanden”),伴随着意义和经验的分离,伴随着怀特式的表现主义对意义的冲击,b鲁尼亚在陈述怀特式的表现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对意义及思辨式历史哲学的影响时,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说怀特式的表现主义就像童话中的人许愿时想将自己所触碰的一切都变为金子,结果是他绝望地发现他碰触的食物在他放入口中时也变为金银而无法食用。怀特式的理论失误也成为鲁尼亚提出在场概念的重要原因。见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53.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现代历史思考模式中,意义成为一个问题并不能完全统摄一切现代的历史思考。由此我们就厘清了鲁尼亚的“在场”这个概念的预设目标:“在场”是鲁尼亚试图用来代替“意义”并将其作为历史思考的中心的概念,特别是在处理“过去”与“现在”这个二元时间关系时。
具体来看,不管是吕森的“意义”还是鲁尼亚的“在场”,他们都在处理一个历史哲学的元问题,即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过去的时间经验和现在的意义结构之间、在“发生了什么”和“表现为什么”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人类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过程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总是在“回溯式地”c怀特用“retrospective”,鲁尼亚用“retroactive”来表达。思考我们从过去得到了什么,或者过去对现在有什么影响这类非常基本的历史问题。
在此吕森用传统的历史哲学概念“意义”来表达,因而“意义”成为一种超时空的中介和存在物,像一种时空隧道。过去那些逝去的、流失的、无痕迹的一切时间产物,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讲无根无垠。这些无根无垠而又无比真实的人类过往通过意义作为媒介传递到现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而在鲁尼亚这里,吕森的“意义”变为“在场”。在“意义”受限的地方(比如作为人类恐怖历史经验的大屠杀),“在场”就浮现了出来。鲁尼亚将“在场”没有赋予过多的意义内涵,“在场”就是使你作为个人、使事物“是其所是”的一切东西。相比“意义”,“在场”是触手可及的,是真实的、物质的。因而,在过去到现在的演变中,特别是在处理人类历史的非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在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鲁尼亚就此说,在由过去到现在的过程中,“意义的传递”是以“在场的传递”为前提的。d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83.
在文化实践层面,在由“过去”到“现在”的过程中,吕森的“意义”和鲁尼亚的“在场”都扮演着一个意义扭结的角色。尽管鲁尼亚本人并不认为“在场”会携带更多的“意义”的色彩。然而,作为时间转化和传递的思考媒介,经由这些媒介(即“意义”、“在场”或者其他宗教媒介),那些宏阔而又立体的时间过程作为“过去”需要被“现在”所承接,在这个承接点之上,意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意义的存在,过去的时间之流和现在的人类生活世界无法联系在一起,由此会踱入时间的荒野(也即吕森所谓的“自然时间”)。一旦“在场”打算接手“意义”的思想工作,那么就不可避免需要清算意义带给我们的结果。所以,鲁尼亚说“在场”是以“缺场”来表现自己。笔者认为,毋庸说,“在场”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变体形式——“在场”是以“意义缺场”的形式来思考由“过去”到“现在”这个时间过程中的意义。
三、“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关于历史记忆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中,有一段对话如下:
“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温斯顿顺从地重复到。
“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奥勃良说并慢慢点头表示赞同。“温斯顿,按你的想法,过去是不是真的存在?”
……
奥勃良微笑着,“你并不是形而上学家,温斯顿”,他说。“直到此刻你都没有真正考虑过存在意味着什么。让我更清楚地来说,过去在空间中具体地存在吗?是否有一个地方或者他处作为具体有形而且客观可靠的世界,过去在其中正在发生?”
“不”
“那么过去在何处存在,根本上讲?”“在文献记录中。过去被写下来了。”“在文献记录中。还有呢?”
“在头脑中。在人类的记忆中。”
“在记忆中,非常好。那么我们掌握所有的文献记录,掌握所有的记忆。然后我们就掌握了过去,对吗?”aGeorge Orwell, 1984, Signet Classics, Copyright Sonia Brownell Orwell, 1977. p.248.
借由奥勃良的这个富有深意的提问,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分析。在过去到现在的“转化”b此处笔者用“转化”指的是在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过程中,是一个综合的、漫长的、广泛的过程,既包括时间演变,也包括经验性质的演变,同时也包含着其中人类一切的生活“痕迹”留给现在的产物;同时,这个“转化”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在人类的理性认知中,可能既有迅猛的、冲击性的转变,也有难以察觉的、缓慢而不自知的演变。在总体上,这指的是由“过去”到“现在”的这个时间通道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演变到现在的一切结果。过程中,或者过去本身被“识别”出来并思考对现在的影响时,这是在历史意义领域完成的。而在历史意义领域的内部结构中,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思考却是由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所承担。对于历史记忆而言,其核心概念就是“现时化”(vergegenwärtigen)。扬·阿斯曼在论述历史回忆的“现时化”功能时说到:“凝聚性结构(Konnektiven Struktur)同时也把昨天和今天链接到了一起:它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框架之中,从而产生出希望和回忆。”“然而,一次逾越节晚餐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遵循完全相同的规范进行,从而重复去年的庆典,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现时化另一个更早的事件:出埃及。”c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C.H. Beck, 2007, S.17. 英文版: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版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对历史回忆的现时化这个问题,吕森表达了与阿斯曼类似的观点:“记忆改变了过去的时间状态,使过去不再停滞于过去状态,而恰恰相反,记忆使过去成为了现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启了未来的视角。历史记忆抓住过去的某些事物,并且同时使人们意识到这些事物是过去的逝去,但它们却与现在密切相关,即被现时化了(vergegenwärtigt wird)。”d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S.238-239.
通过上述阿斯曼和吕森的陈述,可以看出,他们对历史记忆的核心内容及功能的认同是一致的,即历史记忆使得那些过去的时间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历史记忆使之在现在的时空关系中产生了现实意义和影响。过去的时间以及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所蕴含的经验性质,随着过去这个时间通道的流转,并没有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虚妄,而是通过历史记忆使其在现在这个时间通道中产生了意义。在过去“转化”为现在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时间的演变,即由纯粹的“那时”变为“这时”;另一方面是凝结于时间中的经验性质的转化;其次是历史意义的转化。在现在表现为过去的由来这个层面上来看,鲁尼亚称之为“在场”,而吕森将这个过去在现在的“在场”称之为“传统”。所以,鲁尼亚的“在场”和吕森所谓的“传统”具有类似的范畴同指性(即前文“This presence can be called tradition”),都指的是过去在现在的时间状态中的留存。阿斯曼在论及“传统”和“记忆”时则说:“群体与个人一样都‘栖居’在自己的过去里,并从中汲取塑造自我形象的成分。奖杯装点体育协会的房间,荣誉证书装点运动员个人的房间,若非要称一个为‘传统’,另一个称为‘记忆’,则并无太大意义。”a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C.H. Beck, 2007, S.47. 中文版第41-42页。可见,阿斯曼和吕森在认为过去在现在通过历史记忆的留存,在时间层面和经验层面而言,他们并没有理论观点的差异。
而在历史意义和历史感层面而言,阿斯曼和吕森的观点分歧却是非常鲜明的。在吕森看来,历史意义不仅是过去到现在的一个时间承接点,而且是现在到未来的一个时间开启点。在历史意义中,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基本的时间维度被先后统一了起来并且找到了相互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过去的事物能够进入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联系中,只有在这种联系中,过去才获得了回忆者所具有的固有的时间性质(Zeitqualität)。b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S.239.
吕森此处所谓的“回忆者所具有的时间性质”其实就是“历史感”或“历史性”。对于一个现代历史研究者而言,作为历史意识功能的“历史感”和“历史性”对相异的时间经验的体悟感知的主要结果,是研究者非常基本而又重要的能力素养,否则可能会导致“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谬误。因而,对于德罗伊森的承继者吕森而言,“历史感”是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此而来的历史意义甚至是作为吕森整个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而存在的,因为在德罗伊森及吕森的逻辑中,历史意识具有的“历史感”和由此形成的“历史意义”使得“过去不再如同以往,过去的特定事件即时间联系依然保持过去的样子,正是通过这种情况的回忆,才会超越它们那种逝去的状态,从而获得现在性和未来性”。cDroysen, Johann Gustav: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ed. Peter Leyh. Bd. 1. Stuttgart - Bad 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 1977, S.69.这就是德罗伊森所谓的“过程”(Vorgang),在这个过程中事件变为了历史(“Aus Geschäften wird Geschichte”)。
阿斯曼则称“历史感”为“神话”(Mythos),并说“我怀疑历史感是否真的存在并认为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更合适一些”。d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68.在历史意义和历史导向问题上,阿斯曼同样表示了拒绝:
回忆是进行符号化(Semiotisierung)的行为。这在今天也是如此,作为与符号化相对应的“意义创建”(Sinnstiftung)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已经失去信用(Misskredit)。人们在这里要清楚的是记忆和历史学没有关系。我们并不期待一名历史教授能够“填满回忆、创造术语、解释过去”,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一直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事实。e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77.
阿斯曼在对来自于上述提到的韦勒名著的《德国社会史》的概念“填满回忆、创造术语、解释过去”所做的脚注中写到:
我认为韦勒主张的历史学应该倡导“导向性知识”(Orientierungswissen),并以此来替代“意义创建”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作为“导向性”概念前提的意义概念实际上和“意义创建”中的意义概念是没有区别的。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科学应该脱离价值判断并作为单纯的认知而存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期待埃及学会提供“导向性知识”。f该脚注于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ünchen : C.H. Beck, 2007. S.77. 第63个脚注的内容。阿斯曼提到的施提默尔(Micheal Stürmer)所引的韦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应该为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2: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1815–1845/491989。
由此可见,阿斯曼并不认同历史学或者历史研究会具有超越性内容。作为历史研究超越性内容的“历史导向”这个吕森非常重视和推崇的概念也被阿斯曼所否定。a关于吕森历史导向问题的评论参见 David Carr,“History as Orientation:Rusen o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Narration”,History and Theory, vol.45, No.2 (May, 2006).韦勒所使用的“意义创建”(Sinnstiftung)概念在吕森的体系里用“意义形成”(Sinnbildung)来表达,也是作为其理论架构的核心概念而存在。不过,在此阿斯曼倒是对“意义”与“导向性知识”的关系以反面论证的形式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述,即历史知识的“导向性”前提的意义和“意义创建”中的意义是并无区别的。这是因为,历史导向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历史统一体的存在,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具有历史连续性。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才能开启未来的时间视角并提供历史导向或者韦勒所谓的“导向性知识”。韦勒的“意义创建”或吕森的“意义形成”中的意义本身就指的是历史连续性的形成。而历史导向和历史意义都需要以历史连续性作为一个前提基础,所以在两者中的“意义”前提没有实质的区别。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阿斯曼和吕森及韦勒之间的这种理论态度的差异?吕森在陈述他以及所属的历史学家群体的思想特征时说道:“我这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共同面对着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面对纳粹时期的统治,我们怎么面对并理解、给出回应,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在德国历史中的定位。如果你读我这一代历史学家的作品,比如蒙森(Wolfgang Mommsen)、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韦勒(Hans-Ulrich Wehler)、科卡(Jürgen Kocka)等,你都会发现置于其中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批判。因为我是这一代历史学家中的一员,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那些在纳粹体制中曾经工作过的人以及他们的动机。”b约恩·吕森、尉佩云:《历史叙事、历史研究与历史伦理——访约恩·吕森》,《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1期。对这一代历史学家而言,将纳粹和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在整个德国历史中进行“历史化”是他们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也是韦勒所领衔的整个“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的学术特点。c吕森在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大本营比勒菲尔德大学供职近10年(1989—1997),并在1990年以后担任跨学科研究所的所长。因而,伴随着比勒菲尔德学派所秉持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批判,历史意义和历史导向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如果要将纳粹和大屠杀这段历史进行“历史化”(“Historizing Nazi-Time”d吕森对“历史化纳粹”在历史哲学层面的讨论,见Jörn Rüsen, History:narration—interpretation—orientation, Berghahn Books(2005).第十章:“Historizing Nazi-Time: Metahistorical Ref l ection on the Debate Between Friedländer and Broszat”。),将其置于历史连续性之中,那么作为历史连续性的思想源泉的历史意义自然成为重要内容。同时,既然作为历史连续性和历史意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维关系自然就是其中之义,未来的视角和时间导向成为其核心内容。所以,在吕森及韦勒的研究中对历史意义和历史导向的坚守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与历史伦理和历史责任相关的层面。
相比吕森和韦勒,阿斯曼在德国的学术界中是作为埃及学家和古典学者。并且,他的主要的任教和生活经历都在德国相对保守的海德堡大学。作为一位实践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意义在历史研究中失去信用”,这是和历史意义在19世纪晚期以来目的论历史哲学和元理性的萎缩相一致的过程。因而,阿斯曼和吕森的理论差异首先是面对的理论预设对象的差异,如果没有面对大屠杀这个在吕森研究中“永恒的主题”,那么历史意义在今日已经“名声不佳”是整体性的学术潮流所在。其次,吕森和阿斯曼的观点差异可以看做历史哲学家和职业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异,或者海登·怀特所谓的历史哲学家的“实用的过去”(practical past)和职业的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之间的差异。eHayden White,“The Practical Past”作者于2008年11月参加雅典“反思和批判之间的历史”(History Between Ref l exivity and Critique)学术会议时的提交论文。怀特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该文后被怀特扩充为书出版:The Practical Pas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30 Nov. 2014)。历史哲学家将理性和秩序带入“实用的过去”之中,而职业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历史的过去”则“不会给出任何有利于当前的教训”,并且“用叙述来表现分离的事实”——由此,反观阿斯曼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期望埃及学会提供‘导向性知识’”则在情理之中。在阿斯曼看来,韦伯的“价值无涉”(Wertfreiheit)的纯粹知识更为可靠。
不过,阿斯曼在上文中提到“回忆和历史学没有关系”则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不管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交往记忆还是文化记忆,一旦我们宣称他们在人类精神领域的普遍有效性的话,我们就不能忽略历史学的根本构成元素——历史学家在一个现代文化社会群体中所拥有的记忆对他的工作的影响。在历史思维和历史认知中,历史学家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对于前意识和非理性的层面而言,历史记忆和回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个体层面而言,甚至个人的记忆对他的学术研究的立场态度、研究取向、价值判断等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为何在德国战后的吕森这一代史学家对纳粹进行反思批判并进行清算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一边宣称历史记忆和回忆在人类精神层面的普遍有效性,一面认为历史学和历史记忆没有关系则未免会陷入论证上的两难境地。
在吕森看来,不论是历史意识还是历史记忆,都是相互交织处于共生的状态中,不可能相互独立而存在。最后,两者呈现为文化记忆的“格式塔”(Gestalt)a心理学上,“格式塔”被解释为“是我们在心不在焉与没有引入反思的现象学状态时的知觉”。吕森此处的“格式塔”指的是在人类文化层面上,人类对自己的活动和过往的一种无意识或“先在”状态的思考和探究,这个思考的结果本身就呈现为“文化记忆”,因而,文化记忆就是人类活动的“格式塔”。安克斯密特在《叙事主义哲学的六条论纲》中称,叙事性解释是一种格式塔,具有提议(proposal)的性质。见F.R.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lol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37.——或者说,文化记忆本身呈现为人类活动的影响和结果的“格式塔”。总体来看。吕森并没有像阿斯曼一样宣称历史和记忆没有关系,他认为历史虽然和记忆不同,但没有历史记忆的话我们就不能历史地思考;而如果没有历史的话,记忆则不能超越个人生命界限以外的可能。因而,历史文化的理论总体上要求历史记忆的阐明,因为历史记忆为历史意识提供了媒介并且将过去转化为现在;我们也不能忽视历史意识在记忆中的角色,因为历史意识将历史记忆带入了生命界限以外的可能,并且使历史记忆牵涉到经验性内容从而使其具有了可靠性。bJörn Rüsen, Historik,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232.只有如此,历史才能在文化上被定义为一门文化学科(Kulturwissenschaft)而存在。
四、结语
在德国,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领域从社会向文化的转变,历史学逐渐承认了其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建构性的一面。其中,历史文化作为整体性研究话语而出现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历史记忆和历史文化这两种学术话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德国的史学界同时兴起并传播开来就不是偶然的了。在以“象征性凝练”的方式处理过去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需要在社会生活领域重新考量历史和历史思考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其彰显形式的特征。而在吕森看来,历史文化作为一种公共历史话语的思考,必须要被纳入到职业历史思考的范畴中并将之理论化,为其在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性研究中寻找到合适的思想位置(“用范畴的眼光看待历史”c“Ein Kategorialer Blick auf Geschichtlichs”,见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S.233.)。本文通过对“历史文化”这个思想范畴的分析,可以窥见当代德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