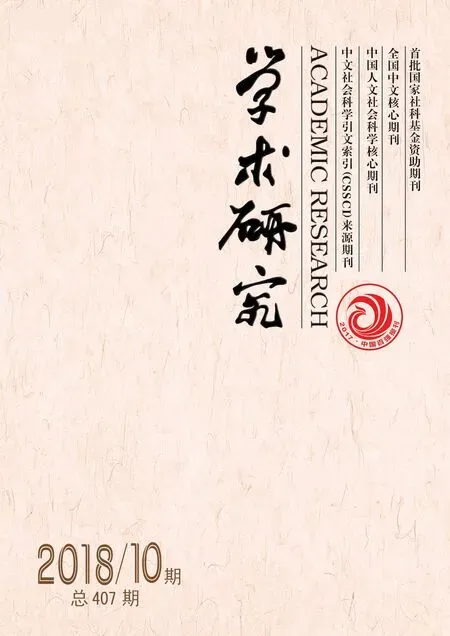历史研究中的因果性与价值
——以马克斯·韦伯与爱德华·迈耶的争论为中心
李子建
一、引言
1928年,20世纪上半叶德国史学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发表了《因果性与价值》一文,从历史中的因果性与价值这两个要素入手,对19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的发展及其当下处境进行了分析。a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in ders.,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Koehler,1959, S.61-89.在梅尼克看来,德国史学在当时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专业分工的细化和对历史细节研究的过分关注,让职业历史学家丧失了对于生命和价值本身的追问,职业史学不再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和导向。其次,日益僵化的专业史学逐渐被部分年轻学者所抛弃。由于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特别是对德意志帝国崩溃的灾难性体验,这些年轻学者表现出了对生活意义的极度渴求,从而转向了对某些永恒和超历史的宏大价值的狂热追求,以至于放弃了对事实的批判和对科学当中因果性的严谨探究。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及其追随者们代表了业余史学的兴起,这些“业余历史学家”区别于传统史家学院式的工作方式,用对待艺术的态度在沙龙和咖啡厅讨论历史。b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S.72-73.对此,梅尼克强调,科学的因果性和对于人类生活中的价值的追求二者必须得到平衡,不可偏废。c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S.66-68.
与此同时,在19世纪末众多且驳杂的德国哲学流派中,以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希望从认识论层面,对各门科学知识的逻辑前提和基础进行讨论和分析:一方面从知识的类型上区分寻求普遍法则的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和探究个别特征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另一方面则为了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有效性,区分科学研究中理论层面和实际生活中的实践层面,为寻求普遍有效的知识确立认识论基础。a对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与历史和历史学关系的研究,参见Thomas Willey, Back to Kant: The Revival of Kantianism in Ger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特别是 Charles Bambach, Heiderger,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赫伯特·施耐德巴赫认为自黑格尔去世后,整个德国哲学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各个学科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情况下,重塑哲学研究的任务、目的与合法性。而西南学派需要放入这种哲学史发展的语境当中加以理解。参见Herbert Schnei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1831-193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在德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关文化科学方法论的讨论中,因果性和价值是两个绕不开的问题。对德国历史学而言,其为了捍卫自身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身份和地位,就必须一方面在对相关材料进行严格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事实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分析和重建历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学科的旧有范式和方法必须面对自1880年代以来,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新思想的挑战,历史学内部有学者希望扩大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运用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联,甚至将个别的因果性上升为某种历史的普遍法则,新旧两种潮流的对立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甚至争吵(Streit)。当历史学像梅尼克所说的那样,不仅在于以科学的标准,提供人类过去发展的知识,而且在实践层面继续充当一种世界观,为人们的当下生活提供意义和导向时,历史学家就必须使某种价值介入历史研究,将自己对历史中某种宏大理念的理解带入因果关系的探究,从而在时间之流中建立某种融贯一致的历史叙述。bFrank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2-137.然而对于寻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而言,以上这种典型的“历史主义”式的表述恰恰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让本来属于实践层面的价值判断介入了属于理论层面的因果性探究,从而导致历史学家主观性的过度发挥和知识的相对性。
本文关注的是发生在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与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 1855—1930)之间,有关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争论,希望揭示因果性与价值这对问题,在当时的有关文化科学方法论之争中的复杂性。文章将提出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迈耶和韦伯关于因果性和价值争论的理论立场和前提分别是什么?他们对于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因果关联的建立、历史学家主体性的作用有着怎样不同的观点?二者在多大程度上同历史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的分歧有关?应当在怎样的时代思想语境中理解这些争论?
二、历史中的个体与史家的主体性——迈耶的史学理论
爱德华·迈耶早年在波恩和莱比锡研修古典语文学、东方学和历史学,1875年以古埃及神“赛特-提丰”(Set-Typhon)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4年后完成教职论文“本都王国史”(Geschichte des Königreichs Pontos)。迈耶曾先后执教于布雷斯劳和哈勒大学,1902年开始在柏林大学执教直到退休。
在当时的德国古代史学界,迈耶不仅是一个具备多种语言能力的杰出史家,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具有世界史眼光及相关学术实践的学者。五卷本《古代历史》(Geschichte des Alterthums,1884—1902)便是迈耶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著作。在这套丛书之中,迈耶以启蒙时代晚期史家海伦斯(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s)的《欧洲国家体系史》为榜样,cBeat Näf, Eduard Meyers Geschichtstheorie. Entwicklung und Zeitgenössichen Reaktions,in: William M. Calder III/Alexander Demandt (Hrsg.), Eduard Meyer, Leben und Leistung eines Universalhistorikers, Leiden: Brill, 1990, S. 285-310, hier S.285.用一种全局性和发展性的眼光梳理了整个古代欧洲和近东的历史进程以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自问世后便广受学界重视。d迈耶的世界史思想及其史学实践并非本文所讨论的对象,相关研究可参考Christoph R. Hatscher, Alte Geschichte und Universalhistorie: Welt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 aus Althistorischer Sicht, Stuttgart: Steiner, 2003, S.53-76. Josef Wiesehöfer, „Alle Geschichte…muß ihrer Betrachtungsweise und Tendenz nach notwendig universalistisch sein“: Eduard Meyer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und die Universalhistorie,in: Wolfgang Hardtwig/Philip Müller (Hrsg.), Die Vergangenheit der Weltgeschichte. Universalhistorisches Denken in Berlin 1800-193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S. 217-240.
迈耶对历史和历史学本质的理论思考开始于1884年出版的《古代历史》第1卷的导言部分。aEduard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ntums, Bd.1: Geschichte des Orients bis zur Begründung des Perserreichs, Stuttgart:Cotta, 1884, S. 1-28. 以下简称《导言》,相关引文的页码将直接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标出。作者首先试图通过区分人类学和历史学各自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一方面为著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阐发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按照迈耶的观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区分在总体上是一般和特殊的区分: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发展的一般基本特征,目的是说明其中的支配性法则,而历史学研究的则是历史当中那些特殊时空条件下的个体,这些个体不受一般性法则的支配。(11)个体是“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个别民族”和“相对于大众的个别人物”:(13)在历史研究中,虽然史家绝不能忽略环境与整体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个体总是趋向于从自身出发理解和把握事物,最终能依靠自身的努力突破静止和僵化的环境与传统。总之,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和那些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社会科学,前者所处理的那些生动的、具有差别的个体不能被后者的抽象法则所通约。此外,历史学还区别于哲学,前者运用日常生活中的直观语言,而后者则运用抽象的构造语言。(15)迈耶在此面对来自邻近学科(Nachbardisziplinen)的竞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b奈夫(Beat Näf)认为迈耶在导论中所预设的学科竞争对手是当时的德国语文学和社会科学。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迈耶对历史学和语文学的区分主要出现在他在1902年于哈勒发表的有关历史学理论的演讲中(下文详),而“语文学”此则根本没有出现。参见Beat Näf, Eduard Meyers Geschichtstheorie,S.291-292.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此前在《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中对此类问题所进行的类似却更为系统的探讨。
迈耶和德罗伊森的历史研究领域都包含了古代历史,两者在国家的优先性、对历史个体性的强调以及对普遍法则的拒斥等问题有着相似的立场。除此之外,迈耶对史家主体性的理解也可与德罗伊森进行比较。在《导言》中,迈耶指出:
历史著述者的任务就是,从传世的历史材料中将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剪辑出来,阐释其发展过程中的关联性,使那些具有决定性的潮流脱颖而出。这就需要一般性的理念和引领性的观点。一切历史写作都必然具有主观性,客观的东西只是一些没有被整理过的事实,是当前的现实生活,而非被提炼出来的有关过去的写照(Abbild)。历史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自身的个体性必须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否则历史写作便最多不过是干瘪的事件排列而已。没有同当下的关系,历史写作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以现在所处状态的前阶段形式出现,只有从某种当下的思想氛围出发,才能形成观点……历史写作就是借助现在的光亮去表现和评判(Beurteilung)过去。(19)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历史研究的具体过程——选择、整理和表现——在迈耶眼中无一不是历史学家从当下出发,运用主观精神参与和加工的结果。这与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大纲》导言部分第5至第6小节的相关主张较为接近。c然而德罗伊森在有关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材料的诠释等问题上有着更完整和详细的论述,参 见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Vorlesungen über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 herausgegeben von Rudolph Hübner, 8. unveränderte Auf l age, München/Wi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77, S.327-328.
《古代历史》第1卷在出版后虽然获得了积极的反响,但鲜有评论者关注导言中的理论部分。零星的批评来自迈耶当时在莱比锡大学的同事、地理学-人类学家拉齐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拉齐尔批评迈耶对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区分过于狭隘。dBeat Näf, Eduard Meyers Geschichtstheorie,S.288. 库尔特·布莱希(Kurt Breysig)则在日后的评论中称赞迈耶的普遍史眼光和对发展史分期的建构,参见 Bernhard vom Brocke, Kurt Breysig,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wischen Historismus und Soziologie, Lübeck und Hamburg: Matthiesen, 1971, S. 303. 值得注意的是,拉齐尔和布莱希都被当时的职业史家们普遍归为需要加以反对的实证主义的代表。在《古代历史》第1卷付梓的前1年,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出版了他的“历史理性批判”计划的第一部分——《精神科学导论》。狄尔泰批判性地借助康德的观点,试图从理性的生命和历史维度出发,aJos de Mul, The Tragedy of Finitude.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pp.1-2.“将历史的探讨与系统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便尽可能实现与精神科学的哲学基础有关的确定性”。bWilhelm Dilthey, Text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Hans-Ulrich Lessing,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S.29.1888—1891年,政治史家迪特里希·谢弗(Dietrich Schäfer,1849—1929)和文化史家艾伯哈特·戈泰(Eberhard Gothein,1853—1923)围绕历史学的主导研究领域到底是政治史还是文化史展开辩论,从而拉开了1890年代有关德国史学理论问题大讨论的序幕。c相关研究可参考Stefan Haas, Historische Kultur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1880-1930,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wischen Synthese und Pluralität, Köln/Weimar/Wien: Bählau, 1994, S.100-112.1889年,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出版《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程》,后历经多次改版,成为了德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又一座高峰。1894年,哲学家文德尔班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上发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试图厘清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各自的认识论基础。而彻底掀起有关历史学根本任务、根本方法和根本研究对象的争论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的著作《德国史》第1卷的出版(1891)。争论的一方是兰普雷希特本人以及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史家,如库尔特·布莱希(Kurt Breysig,1866—1940),另一方则是以贝缕(Georg von Below,1858—1927)为首的主流专业史家(Fachhistoriker),部分社会科学家如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和马克斯·韦伯也卷入其中。
发生在1890年代的“兰普雷希特争论”dFriedrich Jarger/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C. H. Beck, 1992, S.142.的硝烟弥漫于20世纪初的德国史坛。迈耶于1902年发表的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演讲e该文以《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哲学的探究》为题在同年发表(下文中将简称为《理论与方法》),而后收录在Eduard Meyer, Kleine Schriften, Bd.1, Halle (Saale): Max Niemeyer, 1910, S.1-68. 该书在1924年发行了第二版,但内容无明显变化。在Kleine Schriften中,迈耶修订了此文,但所持的基本立场并无重大变化,对于马克斯·韦伯等人批评的回应都被放在了注释当中,本文引述皆来自1924年的版本。以下将仅在正文中的括号内标明页码。正是对此次争论的回应。如果我们将其同《导言》中的相应部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迈耶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发生本质变化。相反,针对以兰普雷希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家”对现有史学范式的挑战,迈耶进一步扩充和加强了自己原先的论证,个别措辞甚至更加锐利。
迈耶首先对当时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进行了回顾,认为以兰普雷希特观点为代表的新潮流不过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其核心是对历史当中个别人物和事件进行同质化和类型化的处理,归纳并最终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法则和规律。(6-9)迈耶对此的否定斩钉截铁:“历史学绝非系统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以一种表现的方式叙述那些曾经属于真实世界的事件经过。”(1)因此,史家的研究绝不能脱离那些从事实而来的历史多样性。(1)“对于材料的内在理解、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以及答案的寻找都源于史家的内在能力”。(2)当兰普雷希特主张历史研究应当运用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对那些集体的、物质的力量进行研究,并从个别上升到普遍的主张,迈耶反驳道,这种自然科学式的取向扼杀了历史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个体的自由意志(freie Wille)和历史发展当中的偶然(Zufall)。
在否定兰普雷希特的基础上,迈耶重申了历史学的本质和基本任务:
所有的历史都是对事件经过(Vorgang)的表现(Darstellung),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在时间中变化的表述。它的对象在被人们认识之前总是已经发生过的,不再存在的,只有这个对象所造成的持续影响(Nachwirkung),其所造成的变化的结果得以继续存在。(42)
在引文中,迈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按照迈耶的观点,历史学家所直接面对的对象只是历史当中的人物与事件留存于后世的痕迹及其影响,而历史学家对于无穷无尽的对象的选择,则完全基于其本身对这些痕迹和影响的感受和判断。在《导论》中被迈耶称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在这里则被表述为“历史的就意味着在现在或者曾经是有影响的(wirksam)”,而“这种影响的内容我们首先是从我们所处的当下所直接感受到的”,(43)“对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些影响是借助什么而产生的?那些被我们理解为某种影响之缘由的东西,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44)a如果我们对比其他德国史家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就会发现迈耶的理解并非孤例。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中对该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已经在其外在形态和现实中不存在了——因为其外在的存在形式已经逝去——其只作为记忆和观念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中,只有在这里历史才是活生生的,只有在这里历史才在向前的发展中产生作用(Wirkung)和协同作用(Mitwirkung)”。而在伯伦汉的《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程》中,该问题则有着更为丰富的表述:“我们的学科所把握的是那些在公众生活中曾经产生影响或者仍然产生影响的所有个体”,然而“具有历史‘意义’(Bedeutung)的对象,不仅是那些在历史过程当中产生影响的东西,而且也是那些能作为获取知识的工具的东西”。即历史学家的兴趣不仅指某种现实当中的影响,也包括纯粹的知识兴趣,伯伦汉在注释中提到,此观点得自韦伯对迈耶的批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参见Johann Gustar Droysen, Historik, S.06; Ernst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it Nachweis der wichtigen Quellen und Hilfsmittel zum Studium der Geschichte, Bd.1 (originally publisched in Leipzig, 1908),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0, S. 6-7.迈耶进一步主张,在众多具有影响的事件中选择研究对象的依据是处于当下的历史学家自己的兴趣。这就是说,对于历史学家从哪个角度做出研究,取决于其对于历史事件所产生影响的哪个侧面感受最为强烈,并以此为动力展开工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44)
迈耶的这个论点其实紧承他在《导言》对史家之主体性的看法,而这个论点在这里还产生了两个推论。首先,既然人必然生活在某个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共同体中,那么某个历史事件所涉及的共同体的范围越大,史家对其投入的兴趣也就越多。(45-46)因而,“历史研究首先只对文化民族感兴趣,而那些原始民族则没有意义,因为其未对历史产生实际影响”,(57)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其次,史家不仅在选择历史对象上所凭借的兴趣是当下和主观的,而且史家在实际历史研究中对细节的探究程度也同其自身所设定的研究目标有关。此外,诸如人物的行为动机,前事对于后事的影响等问题有时无法完全从材料中直接获得,就必须依靠历史学家个人的经验和推断,而不能凭借某种普遍的心理学或者机械的因果动力学的规律。(53-54)总之,历史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进展,除了新材料的发掘外,所凭借的正是处在当下的历史学家自身能够提出不同的、新的问题。
正是对于历史认知主体当中个别的、主观的要素的强调,让迈耶同当时的大部分主流历史学家一样,对普遍理论和概念的运用心存疑虑。他们相信,相比于史家所具有的历史知识和研究经验,其运用何种理论无关紧要。(42)历史学在迈耶眼中是一门经验科学,研究者凭借的是对于材料和对象的直观,而非普遍、抽象的概念。因此历史学并不关心一般国家、法律、社会的系统概念,而只在意这些概念所指涉的具体的时空中的个别对象。(58)普遍性对于迈耶而言——正像其在《导言》中所坚持的——仅仅是历史知识的前提而非目的,这些前提只有实质性地进入个体,影响个体时才有注意的必要性,历史学并不寻求建立这些普遍的法则。(54-55)在这里,迈耶和其他主流史家一样站在了实证方法的对立面上。
在当时有关理论和方法的浓厚兴趣氛围下,该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热烈讨论。部分评论者积极评价了迈耶对于“现代理论”的反击和批判,而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人类学家费尔康(Alfred Vierkandt,1867—1953)则批评迈耶过于强调个体主义,以至于落入到了某种非理性主义的窠臼。而拉齐尔则再次驳斥了迈耶将文化贫瘠民族排除出史学研究范畴的主张。伯伦汉则在他的《教程》的第5和第6版中认为,迈耶狭隘的历史概念使得历史学成为了艺术而非科学。bBeat Näf, Eduard Meyers Geschichtstheorie, S.294.在这些回应当中,最为系统性的批评来自马克斯·韦伯发表于1906年的《文化科学逻辑领域的批判研究:I.与爱德华·迈耶商榷》(以下简称《商榷》)。cMax Weber, Kritische Studien auf dem Gebiet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Logik. I.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duard Meyer,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68, S. 215-266. 引文页码直接在正文中的括号内标出。有关韦伯对迈耶批评的研究,参见Jürgen Deininger, Eduard Meyer und Max Weber,in William M. Calder III/Alexander Demandt (Hrsg.), Eduard Meyer, S.132-158; Ho-Keun Choi, Max Weber und der Historismus. Max Webers Verhältn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zu den zeitgenössischen deutschen Historikern, Waltrop: Hartmut Spenner, 2000, S.172-241.
三、价值关联、价值判断与因果性:马克斯·韦伯的批评
在“兰普雷希特争论”中,韦伯同迈耶共同站在了“围剿”兰普雷希特的一方。韦伯认为,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是一部充满了思辨色彩的作品,“将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领域毁在了数十年的概念建构上。”a其实韦伯和兰普雷希特都希望将社会科学方法和概念引入历史学,并将历史的研究视野扩大到社会、经济和文化史领域。然而前者不能忍受后者在概念和逻辑方面的混淆和滥用,甚至斥责后者为“那种恶劣的骗子和江湖术士”。b转引自 Friedrich Jarger/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S.143.在韦伯看来,传统职业史家在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反思方面也有可以商榷之处,而迈耶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收录《商榷》一文的《科学学说论集》中,韦伯的批判对象不仅包括迈耶这样的历史学家,还包括国民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c张旺山:《韦伯的“文化实在”观念:一个“方法论”的分析》,《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第9卷第2期,1997年5月,第1-38页,此处出自第6-7页。本文对于韦伯理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张旺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梳理和分析。韦伯在这一时期对文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反思性的批判,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随着文化科学的发展,种种“新观点”的产生使得文化科学家们所依赖和习惯的那些概念和逻辑形式重新面临挑战,(217-218)而“兰普雷希特辩论”毫无疑问就是韦伯言下之所指。
在进入韦伯对迈耶的具体批评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明确韦伯自身的理论出发点。韦伯对方法论问题所开出的根本药方,首先是对于文化科学研究中“事实”之确立和“价值”之判断、经验性的因果探究和实践层面上的评价立场的区分。为此,韦伯于1904年撰写了著名的《论有关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知识的“客观性”问题》一文,认为在文化科学的研究中应当坚持“价值中立”(Wertfreiheit)。d在整部《科学学说论集》中,有关事实和价值区分或者价值中立的论点至少出现过40次。韦伯再三强调,这是一种“绝对的逻辑区分”,“二者是完全异质的问题”,其根本就是科学的“公设”,凡从事科学研究者必须认同此项前提。韦伯的这种根本性的立场可以联系到他认定现代科学乃是世界“去魅化”后的一项理智的事业,因而便不再探讨诸如“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意义”等实践当中伦理的、应然的问题。参见张旺山:《韦伯的“文化实在”观念:一个“方法论”的分析》,第8-11页。韦伯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一样,反对狄尔泰以研究对象的不同区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主张,坚持认为一切经验科学的对象,都是本质相同的经验实在。eMax Weber, 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Roschers,, historische Methode“, 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3-41, hier, S.7: Anm. 1, S.12: Anm. 1.在韦伯看来,真正区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两种科学范畴的,是研究者所要面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Kulturbedeutung),而这种文化意义,并非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作为拥有某种价值观念(Wertideen)的“文化人”(Kulturmenschen)f在韦伯看来,“文化人”本身是一种先验预设:“我们是文化人,天生就有能力也有意愿,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立场,并赋予它某种意义,不管这个意义是什么,它都会使我们由它出发,在生活中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某种现象做出判断,将这些现象当作是(积极或消极)具有意义的(bedeutsam)而对之采取某种立场。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146-214, hier S.180-181.的研究者本身所赋予的。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不同于表现其个人好恶的价值观点(Wertpunkt),而是同在某一时期稳定存在的普遍文化价值相关联,这种关联被称为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文化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自然科学就在于其关心的是个别对象的文化意义,而不是普遍一般的规律和法则。同李凯尔特一样,韦伯认为,价值关联不等于价值判断(Werturteil)或评价(Wertung),后者源于个人主观的价值观点,属于实践和伦理层面,而前者则是普遍的,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属于理论层面。此外,“价值中立”的原则还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赞成或者反对生活世界中的某些价值,也不是为了代替实践中的行动者做出决断,即不是为了教导他人应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科学研究必须遵从严格的因果分析原则,只能通过调查和推断来说明某个人、某个共同体在某种形势和前提下可以凭借哪些手段,去做哪些事情,其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其行动的边界在哪里。a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S.151.
其次,针对“在何种意义上,在有关文化生活的科学中存在客观有效的真理”b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 S.147.这个问题,韦伯的答案既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职业史家,也不同于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前者相信,在历史实在中存在某些推动历史发展的理念(Ideen),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之所以能够实现,便在于人能够通过理解、直观等行为把握这些理念,或者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与这些理念同一;cFriedrich Jarger/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Eine Einführung, S.159.而后者则试图建立某种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价值体系,使客观真理在历史之外得到实现。韦伯的方案是在概念和实在之间创造一种被称作“理想型”(Idealtypen)的概念系统,它是一种“思想的图画”和“乌托邦”,其取材于现实但在现实找不到相对应的原型。“理想型”作为一种思想工具,能帮助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思想中安排和整理复杂无序的经验实在对象。d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 S.207.这个概念系统本身是一种历史变化的产物,而历史学等文化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和进步,就在于其能通过扩大和变换科学的视野,构造新的认知概念。e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 S.207-208.因此,“国家”对于韦伯来说既不是在实际历史当中存在的某个理念和精神,也不是超历史存在的某个普遍的范畴,而是某个从历史当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概念,凭借这个概念,历史学家才能更好地探究每一个存在于具体时空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
清楚了韦伯理论的立足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韦伯在《商榷》一文中对迈耶观点的批判了。首先韦伯认为迈耶的问题绝非个例,而是反映了自兰克以来,职业史家群体对自身学科理论与方法认识能力的不足。迈耶对理论问题的反思对韦伯而言“并非医生开具的诊断书,而是病人自己的病情自述”。(215)
韦伯对迈耶的批评概括起来,主要针对的就是史家如何处理研究中“价值”和“因果性”这两个问题。首先,韦伯从普遍的价值关联角度出发,批评迈耶过于强调历史研究对象同史家自身的关系。韦伯认为,当迈耶主张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问题的提出都只是历史学家个人的事情时,研究便过多地沾染上了历史学家个人的色彩,仿佛处在当下的历史学家能够按照历史当中的经验实在对自身影响的大小,通过因果关联的回溯,决定其所要研究的对象。这种做法在韦伯眼里必然导致史家从自身的个别价值观点出发去选择研究对象,而非立足于普遍的价值关联,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判断。(254-255)韦伯反问道,按照迈耶的原则,《古代历史》一书的内容就将大幅度缩水,因为作者和读者只关心那些对其自身以及所处当下造成影响的对象就够了。f当迈耶认为,史家能够将过去的某个时刻看作“现在”,从而将对这个时刻的“现在”也具有影响的对象当作历史对象时,韦伯继续反问道,这些时刻的选择标准是从历史学家自身出发还是存在某种普遍标准。显然在韦伯看来,迈耶会认为这个标准也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事情,因而便再次陷入到了任意和主观之中。参见Max Weber,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duard Meyer, S.255-256.总之,韦伯认为,迈耶将对现在的“影响”作为历史对象选择的标准,太过狭隘,其中暗含了某种不应该出现在科学中的评价行为。
以此为突破口,韦伯接着指出,迈耶在逻辑上混淆了两对本来应该清楚区分的概念,即“原初的历史对象 /二手的历史事实”(primäres historisches Objekt/sekundäre historische Tatsache)和“实在的理由 /知识的理由”(Realgrund/Erkenntnisgrund)。所谓“原初的历史对象”指的是某个历史对象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而“二手的历史事实”则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价值,而是在因果解释中被当作引起本质上具有价值的那些对象(即原初的历史对象)的原因。(261)g韦伯的这种区分概念实际上也来自李凯尔特,而韦伯自己则将前一种范畴称作“历史的个体”,后一种范畴称作历史的(实在)原因,(257-258)参见Ho-Keun Choi, Max Weber und der Historismus, S.215: Anm. 178.而有关“实在理由”和“知识理由”的区分,则涉及到迈耶在《理论与方法》中对李凯尔特的一项批评。李凯尔特在《自然科学概念建构的界限》一书中提到,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拒绝法兰克福议会的德意志皇帝皇冠事件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历史事件,而给他做礼服的裁缝是谁这个问题则没人关心。迈耶则坚持认为,在政治史领域固然没人会把裁缝作为研究对象,然而这个裁缝及所做礼服的样式却可能成为有关裁缝或者时尚历史的一个课题。aEduard Meyer, Kleine Schriften, Bd.1,S.44-45.韦伯认为迈耶在这里的这种表述混淆了史家对于历史实际作用的兴趣,即 “拒绝皇冠事件”,和作为获得知识工具的事实的兴趣,即国王的礼服问题。(238)前者属于历史兴趣的“实在理由”,后者则属于“知识理由”。根据韦伯的区分,历史学家对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皇冠的兴趣在于,该事件对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而国王礼服的材料和款式问题则只是史家认识时人衣着和时尚演变的一种途径。在前者当中,历史学家寻求的是个别的因果关联,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个“归因问题”(Zurechnungsfrage),而后者的目的在于建立某个普遍的类概念(Gattungsbegriff)。b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S.178. Ders.,“Zur Auseinandersetzung”,S.238.这种混淆也使得迈耶只将历史研究的兴趣限制在了那些对实际历史产生影响的“文化民族”当中,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研究那些“文化贫瘠民族”历史对于丰富相关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韦伯来说,史学不仅探究个别的具体对象,而且也寻求普遍的知识概念。
对于坚持因果解释不包含价值判断的韦伯来说,更危险的是迈耶认为,史家应当评价历史人物所做决定的正确性,并对这些人物的人格做出评判。这意味着迈耶将伦理规范和因果性考察、评价和解释混为一谈。(222)正如上文所论述的,迈耶的这种主张在根本上源于他和其他持有历史主义观念的史家们都坚持认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历史个体“虽然依赖于外在条件,然而在每一个意志决定中都是自由的,因此我们总是掌握着自己的意志,并由此对其他人负责,因而不屈从于无尽的因果之链”。cEduard Meyer, Kleine Schriften, Bd.1,S.21.在韦伯眼中,这种主张无异于让奇迹和非理性进入了历史方法之中,必将伤害历史学作为经验科学的有效性。(226)
正如前文所述,韦伯只是将迈耶当作职业史家群体当中的一个代表,其要批评的是自兰克以来德国主流史家所普遍持有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历史学的工作与其他科学工作有着质的不同,历史学在这些史家眼里只是一门“材料收集的”(materialsammelnd)和纯粹“描述性的”(beschreibend)学科,历史学排斥理论和概念。(216-217)韦伯认为,这种历史学例外论的片面之见,在于历史学家过度强调了非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夸大了史学诠释与一般性因果解释之间的距离,从而在对个别事件的理解上由于缺少坚实的“归因链条”(Skelett der kausalen Zurechnung)而堕入了非科学的历史小说(historischer Roman)的范畴。dMax Weber, Kritische Studien auf dem Gebiet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Logik: II. objektive Möglichkeit und adäquate Verursachung in der historischen Kausalbetrachtung,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266-290,hier, 278-279.
当《理论与方法》一文收入1910年出版的《论文杂集》(Kleine Schriften)中时,迈耶在页脚新增了若干注释,以回应韦伯在《商榷》中的指责。在总体上,迈耶依然坚持了他之前的观点,他对韦伯的回应则常常不能切中要害。例如针对韦伯有关“拒绝皇冠问题”的批评,迈耶解释道,我们不能排除那个裁缝因为为国王做礼服的关系,而成为了制衣行业著名人物的可能性,由此这个裁缝对历史产生了实际影响。eMax Weber, Kritische Studien auf dem Gebiet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Logik, S.44, Anm.2.迈耶并未回应他是否赞同韦伯所提出的“实际理由”和“知识理由”的区分,即承认历史研究的对象还包括那些具有知识理论意义的历史对象,而只是在加强和补充自己的原先论点。
四、普遍与个别:新康德主义与历史主义
事实上,发生在韦伯和迈耶之间的争论并非孤例,类似的争论还发生在了文德尔班与狄尔泰以及之后的李凯尔特和梅尼克之间。
在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于1883年发表后,文德尔班撰写了文章《批判的还是发生的方法》,fWilhelm Windelband, Kritische oder Genetische Methode?,in: ders., Präludien: Aufsätze und Reden zur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Tübingen: J.C.B. Mohr, 1907, S.318-355.对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做出了回应。文德尔班认为,对历史理性的批判需要一个基于“批判的方法”的高于历史经验层面的普遍标准,aWilhelm Windelband, Kritische oder Genetische Methode?,S.339-340.“人们不应当只看到历史,还应该看到理性”。bWilhelm Windelband, Kritische oder Genetische Methode?,S.339.文德尔班指责狄尔泰将理性历史化的做法必然导致过度的主观性和相对主义。cWilhelm Windelband, Kritische oder Genetische Methode?,S.351.
与文德尔班一样,狄尔泰同样意识到,应当对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dWilhelm Dilthey, Text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S.29-34.然而,狄尔泰选择了一条更加偏向历史主义的道路。e有关狄尔泰同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历史主义的关系,参见Hans-Ulrich Lessing, Dilthey als Historiker. Das „Leben Schleiermachers“als Paradigma,in: Notker Hammerstein (Hrsg.),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m 1900, Stuttgart: Steiner Verlag, 1988, S.113-130. Jos de Mul, The Tragedy of Finitude, pp.13-20.被新康德主义视为批判根本出发点的康德的先天概念,在狄尔泰看来恰恰是有问题的。1894年,狄尔泰写作《描述与分析的心理学观念》,针对文德尔班的批评,从先天之物的历史性角度进行了反驳。在狄尔泰看来,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对事实与有效性、存在与规范的区分根本不切实际,认识论的有效性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其总是预设了通过经验性方式所获得的特定心理概念。fWilhelm Dilthey, Ideen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Leipzig und Berlin: Verlag von B. G. Teubner, 1924, S.148-149.因此,狄尔泰断然不能接受文德尔班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中,从纯粹的认识论对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抛开主体的历史性存在及其同对象的活生生的关系,而希望作纯形式的区分对狄尔泰而言无异于搭建空中楼阁。
虽然文德尔班和狄尔泰之间的争论不像韦伯和迈耶那样,涉及具体的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因果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哲学层面为一般精神科学/历史学奠基,然而这场争论同样涉及到了在历史知识产生的过程中,主体性的介入问题。于此相比,发生在梅尼克和李凯尔特之间的争论则更多地沾染了“一战”后“历史主义危机”(Krisis des Historismus)g“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危机”是两个复杂且多义的术语。当其同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发生关联时,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新教神学家、历史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所定义。在出版于1922年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一书中,特勒尔奇将历史主义定义为“我们关于人类及其文化和价值的所有思想的彻底历史化”,是一种现代的思想世界和世界观的特殊形式。对于特勒尔奇来说,历史主义的危机意味着历史主义本身陷入了危机之中,其同西方文明在一战中的惨痛经历有关。而正如荷兰学者赫尔曼·保罗(Hermann Paul)所分析的,对于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而言(如宗教领域),历史主义本身的逻辑导致了诸如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危机。参见Ernst Treol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Erstes Buch: Das logische Problem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922), Teilband 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8. S.1-11. Hermann Paul,“Who suffered from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A Dutch Example”,History and Theory 49, May 2010, pp.169-193.的色彩。这一点可以从前述的梅尼克有关当下历史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清晰地看出。h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教育阶层对于灾难和崩溃的经验使得专业史家对于文化阐释的地位急剧降低,后者在战前所持有的那种乐观和高亢此时已经完全破产,职业历史学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不仅因为专业性过强缺乏可读性,而且由于无法提供生活中的导向而成了滞销的过时货。正如梅尼克所分析的那样,公众对生活导向的热望,使得诸如格奥尔格等追求历史写作中审美取向而非知识获取,意义建构而非意义阐释的业余史家获得了更加热烈的反响。参见Lutz Raphael, Die neue Geschichte- Umbrüche und Neue Wege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 (1880-1940),in:Wolfgang Küttler / Jörn Rüssen / Ernst Schulin (Hrsg.),Geschichtsdiskurs Bd.4, Frankfurt a. M.: Fischer, 1997, S.51-89, hier S.72-74.面对李凯尔特关于区分普遍的价值关联和个别的价值判断的主张,iHenrich Rickert, 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6, S. 88-89.梅尼克仍然坚持认为:
没有价值判断,价值相关事实的选择就是不可能的。李凯尔特所认为的那些价值,只有在与诸如宗教、国家、法律等普遍范畴有关时才是存在的。然而历史学家从材料中做出选择时不仅仅是根据这些普遍的范畴,而且也有赖于他从具体内容中得出的活生生的兴趣。历史学家多多少少将材料理解为有价值的,即历史学家对其做出价值判断。j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 S.68-69.在梅尼克看来,价值判断绝非历史学家工作的多余副产品,相反,缺少价值判断的历史作品只不过是缺少历史性反思的材料的单纯堆砌,历史学家必须参与对材料的价值判断,而其中的主体性要素恰恰是历史学方法的重要和特殊组成部分,历史学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aCharles R. Bambach, Heider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p.111.主体性对于梅尼克而言意味着“一种能力,其能够进入某种通过艺术的直觉,将过去加以复活的东西的灵魂中去,而这个过程必须被灌注以生命的血液”。b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 S.82.在生命主义和诠释学的传统中,梅尼克信奉维科(Giambattista Vico)有关人与历史关系的名言:人创造了历史,因而能够认识它。由此,梅尼克认为,主体性的参与虽然可能导致价值相对性的产生,然而这却并不必然意味着历史主义将堕入“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偶然性与任意性”的泥潭,c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 S.82.相反,避免相对主义所带来的价值虚无后果的唯一方式恰恰在于从健康、积极的角度发扬主体性,坚持那种“终极的坚强和富有创造性力量的信仰”。dCharles R. Bambach, Heider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p.112.梅尼克毫不掩饰其同李凯尔特的对立:历史研究不仅是一种科学工作,而且还是一种伦理生活,因而不仅需要科学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在精神层面上对于价值的追求。e不过梅尼克同样批评了迈耶只注重历史对象对于现实的影响,而忽视了那些历史中超越因果性影响并能够被我们感受到的永恒价值。然而梅尼克的批评却并不能妨碍他与迈耶在历史研究中主体性的介入、价值判断、个体性等根本理论立场上的接近。参见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 S.65-66: Anm. 2.要注意的是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解决当前历史学以及整个生活世界中的问题的可能性途径。f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S.73.
五、结语
我们首先可以从学科之争的角度来看待上文所涉及的这些争论。早在1860年代,德罗伊森就曾撰写《将历史提升为一门科学》(1863)一文,批评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的主张。gJohann Gustav Droysen, Erhebung der Geschichte zum Rang einer Wissenschaft,in: ders., Historik, S.386-405.18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的发展以及学者之间的代际更替,德国史学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学科内部对于史学革新的呼声渐高,分别发生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戈泰-谢弗之争”和“兰普雷希特争论”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特别是在后者中,兰普雷希特被主流职业史家视作自然科学方法滥觞下,史学内部实证主义思想的代表而大加讨伐,反映的是对学科认同的加强和对史学自身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地位的维护。其次,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当这些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同历史学发生重合时,谁的方法和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代表人类对于世界的真理性认知,便成为了引发学科之争的主要动力。
马克斯·韦伯对文化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的基础与新康德主义密切相关,其目的并不局限在为社会学和国民经济学而辩,而是指向整个文化科学界。当韦伯批评以迈耶为代表的职业史家,认为将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历史事件当中的偶然要素,同人类行为中的理性考量、一般性的外在历史条件截然对立起来,从而夸大了史学方法的独特性时,这些批评同样也涉及罗雪尔(Wilhelm Roscher, 1817—1894)、克尼斯(Karl Knies, 1821—1898)和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等国民经济学家。hMax Weber, 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1-145.而当韦伯认为社会学 “应当说明性地(deutend)理解社会行为,并以此对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进行因果性的解释”i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5. Auf l age,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72, S. 1.时,他同样也以类似的规定向历史学提出要求:历史学应当对历史事件的存在与过程进行因果性理解和解释。aHo-Keun Choi, Max Weber und der Historismus, S.234.
梅尼克对李凯尔特的反驳则更清晰地呈现出了历史学家对自身实际工作的具体体认与哲学家的不同。在面对李凯尔特有关史家自身的价值判断介入了历史学的实际研究,从而导致了历史知识的主观性的批评时,梅尼克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理论和逻辑层面,而是从自己数十年史学研究的实际经验出发,认为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史家的价值判断无法避免,即便史家可以尽力控制自己自身价值的带入,然而读者还是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些价值判断的存在。b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 und Werte, S.69.梅尼克实际上是在批评李凯尔特只是一个没有史学研究实际经验的理论家,其批评只是一种外行之见。
发生在李凯尔特和梅尼克之间的争论还应当放在20世纪以后,特别是一战后的“历史主义危机”的语境下加以理解,然而这种语境对双方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李凯尔特不能接受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而这在梅尼克看来,则是奠基于历史主义原则之上历史学的内在要求。在李凯尔特眼中,历史主义同相对主义别无二致,甚至会导致虚无主义。相较于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对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哲学有着更大的威胁性,因而必须予以坚决抵制。cHeinrich Rickert,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5. Auf l age,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29, S.8-9.因此,历史主义的危机对李凯尔特来说就是一种“由历史主义引起的危机”(a crisis caused by historicism)。韦伯有关价值中立的主张及其对德国历史学的种种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由相对主义导致的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而在梅尼克那里,历史主义的危机则是一战后历史主义本身所遭受的危机(a crisis for historicism),其自身再也无法同时身兼“科学的方法论”(因果性)和“生活的指导原则”(价值)这两种功能了。d这意味着“一战”所带来的灾难和创伤,使得人们开始对那种认为在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中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内核或者关联性的乐观主义产生了怀疑,而这种乐观主义清晰地体现在了洪堡、兰克、德罗伊森等经典历史主义者身上。历史主义丧失了其将过去与现在整合在某种有机而连贯的历史叙述中的能力。而这正是困扰该术语发明者之一特勒尔奇的关键所在。参见 Frank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132-137. Hermann Paul,“Who suffered from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对此,梅尼克并不打算像李凯尔特那样主张放弃历史主义。相反,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梅尼克相信历史主义和德国史学自身有能力在因果性和价值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因而克服危机方案就掌握在历史学家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