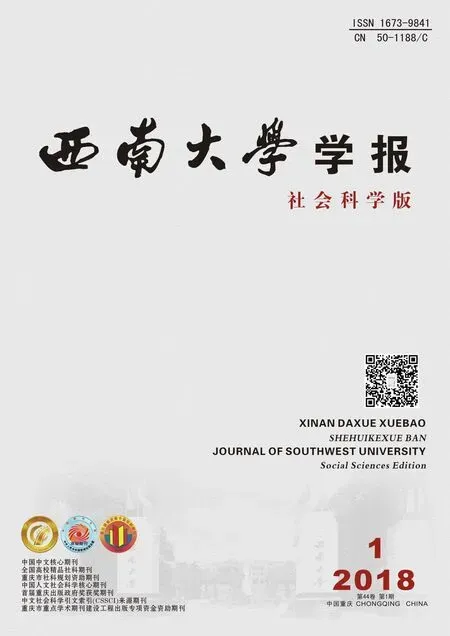试论秦汉刑罚中的司寇刑
张 新 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试论秦汉刑罚中的司寇刑
张 新 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秦和汉初的司寇刑一般是耐为司寇刑的简称,属无期徒刑。获刑者有立户、名田宅等重要权利,但刑徒身份使之处于里中社会生活的边缘位置。司寇的劳役主要有侦捕疑犯、监管刑徒、传递文书和运送物资四类,这与徒隶内部各级刑徒的劳役已经混淆的状况不同。此时司寇的社会地位在逐渐下降,是为汉文帝刑罚改革的重要背景。改革后的司寇刑因性别不同而异名,男性的刑名是耐为司寇,女性的刑名是作如司寇,都是二岁刑。至迟在公元91年二者又重新统称为司寇。此时司寇刑的惩罚措施主要有限制自由、取消户籍等七条,但并非只针对司寇,说明刑期的长短已经成为衡量刑罚轻重的主要标准。秦汉时期的司寇刑经历了从兼具社会身份、劳役属性到只有劳役属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和刑罚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汉;刑罚;司寇;汉文帝刑罚改革
司寇刑是秦汉刑罚体系中的重要一级,史籍和简牍中的相关记载也比较多。在目前所能见到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大多是就《汉书·刑法志》和《汉旧仪》中的相关记载展开讨论,主要涉及司寇的刑期和劳役内容。*如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298、1536页。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7~58页。(日)濱口重国:《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631-639页。(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85页。(日)滋贺秀三:《西汉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6-82页。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5页。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初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日)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3-134页。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公布后,学界开始关注司寇的权利和社会地位问题。*如(日)鷹取祐司:《秦漢時代の刑罰と爵制的身份序列》,载《立命館文学》第608号,2008年。吕利:《律简身份法考论:秦汉初期国家秩序中的身份》,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268页。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日)宫宅潔著,杨振红等译:《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32页。这些成果对我们认识司寇刑大有裨益,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秦和汉初司寇刑的劳役和权利等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有限,对汉文帝刑罚改革后的司寇刑研究很少等。因此本文将在利用新公布的岳麓秦简(肆)的基础上对秦和汉初的司寇刑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并尝试研究其在汉文帝刑罚改革后的情况。
一、秦和汉初刑罚中的司寇刑
(一)概况
岳麓秦简有“泰上皇时内史言:西工室司寇、隐官、践更多贫不能自给(粮)”[1]204的记载,泰上皇即秦庄襄王(前249年至前247年在位),这是目前关于司寇的最早记载。秦代的徒刑*关于是用“徒刑”、“劳役刑”、“身份刑”还是“附加刑”来称呼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刑名,学界看法不一。为了论述方便,本文统一使用“徒刑”这一称呼。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和候刑,其中司寇刑轻于隶臣妾刑,重于候刑。张家山汉简载:“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城旦舂罪完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罪鬼薪白粲及府(腐)罪耐为隶臣妾,耐为隶臣妾罪耐为司寇。”[2]26说明汉初司寇刑也比隶臣妾轻,但此时已经没有候刑。秦代到西汉文帝刑罚改革前,所有徒刑都是无期刑,司寇也不例外。
据研究,秦及汉初“法律条文中的‘耐’和‘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刑名,其实是耐刑+徒刑的省略语”[3]。这一观点已经在简牍资料中得到证明,秦《置吏律》载:“其任有辠刑辠以上,任者赀二甲而废;耐辠、赎辠,任者赀一甲;赀辠,任者弗坐。”[1]139-140这里将秦代刑罚(除死刑外)分为三个等级:“刑罪”“耐罪、赎罪”“赀罪”,其中耐罪应包含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和候。结合上引张家山汉简可知,司寇刑的全称是“耐为司寇”。同时,“耐为司寇”也可以直接称为“耐罪”,只是这种称呼不独指耐为司寇,需要根据文意来确定所指。但是简牍中的“司寇”并不都是“耐为司寇”的简称,岳麓秦简:“城旦舂司寇亡而得,黥为城旦舂,不得,命之,其狱未鞫而自出殹(也),治(笞)五十,复为司寇。”[1]55这里的“司寇”是“城旦舂司寇”的省语,而“城旦舂司寇”是城旦舂的一个类型。
耐为司寇刑虽然有多种称呼,但是判处该刑的刑徒径称为“司寇”。由于司寇刑并不像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仅从称呼上就能区分性别,又因为性别差异会产生刑罚差异,所以有学者提出司寇刑“不向女性科罚”的观点[4]27。但秦《傅律》载:“若群司寇、隶臣妾怀子,其夫免若冗以免、已拜免,子乃产,皆如其已免吏(事)之子。”[1]121这里的“司寇”显然是指判司寇刑的女性。张家山汉简中经常将司寇与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并列,说明汉初司寇也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笔者认为秦和汉初的司寇刑是同时科罚男性和女性的,只是没有出现区分男女判司寇刑的专有名称而已。
(二)司寇刑的惩罚措施
一旦判司寇刑就丧失了很多权利。秦简载“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5]63即司寇不得担任官府小吏。岳麓秦简中还有这样的规定:
这里的“卅年”是指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群耐子”包括司寇子,他们大约在秦始皇三十年五月后就不能担任佐等低层小吏,这意味着司寇子的社会地位降低了。而根据简文记载,司寇的刑徒身份不会被子女继承,司寇子的身份是士伍,即无爵平民。*张家山汉简规定“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8页)秦《置吏律》规定:
县除小佐毋(无)秩者,各除其县中,皆择除不更以下到士五(伍)史者为佐,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岁以上备员,其新黔首勿强,年过六十者勿以为佐。[1]137-138
如果符合任佐职条件的人数不足,士伍子(仍是士伍)只要在十八岁以上就可以充任。司寇子的身份虽然是士伍,但是即使年满十八岁也不能担任佐,显然没有获得士伍应有的权利。实际上类似现象一直存在,《周礼》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6]卷66,p2746-2747“不齿”是指刑徒被释放后不能享受与一般平民同等的权利。睡虎地秦简中收录了两条魏国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的律文,其中有一条关于赘婿的记载:“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5]174赘婿的身份低下,其子孙三世之后才能做官,而且要在户籍上标明是赘婿的后代。这条魏律被收入秦律中,说明在当时具有法律效用。可见秦代歧视刑徒、赘婿等身份的人及其子孙的现象,是有历史渊源的。秦被称为“刑徒国家”[7]107、228,刑徒数量庞大,而他们的子孙也因受到歧视而很难改善处境,再加上类似处境的赘婿等群体,数量必定十分巨大。
司寇没有拜爵、以及因拜爵而受政府赏赐财物的权利,也没有继承爵位的权利:
尝有罪耐以上,不得为人爵后。[2]61
不仅如此,司寇还要承担额外的赋税。岳麓秦简载:
当西县工室中的司寇、隐官和践更者因贫困不能自给时,官府要求司寇缴纳禾,但并没有让隐官、践更者等身份的人缴纳。这条规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再次启用后,司寇的负担无疑会被加重。
据张家山汉简记载,有爵者和无爵平民还享受稟鬻米、受王杖、免为睆老的权利[2]57,这些简文均不涉及司寇。但在《二年律令·赐律》中,司寇又有政府赐衣和赐酒食的权利,只是物品的质地、数量不仅与平民有区别,而且还将司寇与其他刑徒并列:
(赐衣)五大夫以上锦表,公乘以下缦表,皆帛里;司寇以下布表、里。[2]48
(赐)毋爵者,饭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酱少半升。司寇、徒隶,饭一斗,肉三斤,酒少半斗,盐廿分升一。[2]49
“司寇以下”是指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四类刑徒。“徒隶”是指“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能被政府所买卖,具有罪犯奴隶的性质。”*曹旅宁:《释“徒隶”兼论秦刑徒的身份及刑期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他主要论述的是里耶秦简中的徒隶,笔者认为此结论也适用于汉初。另外,池田夏树认为“徒隶”还包括官有奴隶。参看(日)池田夏树:《戦国秦漢期における徒隸》,《帝京史学》第20号,2005年。上述简文都将司寇与徒隶并列,说明二者在“赐衣”和“赐酒食”上的待遇相同。
这里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司寇居住在里中(见后文),但是在赐衣、赐酒食时司寇却与不在里中居住的徒隶并列,这似乎暗示对司寇的赏赐不是与里中居民一起进行的。以下两个算数题可资佐证,首先是岳麓秦简《数》中的记载:
夫=(大夫)、不更、走马、上造、公士,共除米一石,今以爵衰分之,各得几可(何)?夫=(大夫)三斗十五分斗五,不更二斗十五分斗十,走马二斗,上造一斗十五分五,公士大半斗。[8]95
“除”是给予的意思。简文是关于五人领取政府给予的米,然后进行分配的内容,这里没有出现司寇。而岳麓秦简《数》中提供的相关资料“基本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9]。其次,《九章算术》中有平民根据身份分配鹿肉的记载[10]105-106,这个例子虽然讲的是分配非政府给予的食物,但是这反而说明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没有出现司寇。而据堀毅考证,《九章算术》是秦代的数学书,记载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11]297。两道算数题都是以爵位作为分配物品的依据,而司寇处在爵制性身份序列“-1级”的位置,低于有爵者和无爵的公卒、士伍、庶人[12]。这些都暗示司寇不能和同住在里中的平民一起接受赏赐。
关于汉代赐衣、赐酒食的程序,可以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诏书中略窥一二:
诏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如淳曰:“赘,会也。令勿擅征召赘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师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赐之,勿会聚也。”[13]卷6,p174-175
诏书特别强调“县乡即赐,毋赘聚”,并把它作为一项皇帝怜悯百姓的措施。说明在通常情况下,百姓要聚在官府领取赏赐。这时又按照爵位高低、年龄大小来确立领受赏赐的先后顺序,而这个顺序就是他们在“里的社会生活的身份序列”。*实际上爵位比年龄更具优越性,只有爵位相同时才会参考年龄。(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3-424页。司寇既然不参与,在里中就成了边缘人物。
司寇为什么不能与同里平民一起领受赏赐呢?这应该与司寇的刑徒身份有关。司寇刑的全称为“耐为司寇”刑,“耐”是剔除鬓须的意思。*《汉书·高帝纪》应劭注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古耐字从彡,发肤之意也。”(第64页)《说文解字》:“耏,罪不至髡也。”段注:“不剃其发,仅去须鬓是曰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454页)可见,“耐”的早期含义就是剃掉须鬓。可算作广义上的肉刑[14]153。肉刑的本意是通过用刑使受刑人具有“不齿于社会的不洁不祥的性质”[15]11,以达到将其驱逐出社会的目的。据此可以推断,在汉代重要的社祭、赐酺(政府许可的民间聚众饮酒)等里中居民共同参与的事情中,可能都不会出现司寇的身影。*汉初常有像“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汉书·文帝纪》)的记载,说明民爵赐予时,常将赐爵、赐牛酒和赐酺组合起来使用,而这里的“民”“女子”指的是编户良民。同时,赐酺所食用的酒食就来源于赐牛酒,说明赐酺与前两者关系密切。参看(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154、393、409页。司寇虽为编户民,但并非良民,因此不能参加上述活动。
(三)司寇刑徒的权利
秦和汉初的司寇有名田宅的权利,但是获得的田宅数量最少。张家山汉简载“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2]52、“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2]52。有学者认为汉初的主体秩序是“通过皇帝与民之间的田宅给付为媒介确立,里内的秩序也以对应爵级的田宅数形成贫富差别。”[16]这进一步说明司寇在里中的地位很低。司寇也有免老的权利:“公卒以下六十六,皆免为老。”[2]57据前引简文,“公卒以下”包括司寇、隐官。
司寇还有立户、在里中居住和迁户的权利:
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2]52
以上三条材料充分说明,秦和汉初的里中不仅有司寇户,而且政府对司寇立户的态度也是“许之”。既然允许司寇立户、名田宅,自然就可以在里中居住。这些权利使得司寇的身份中不仅有作为刑徒的劳役属性,更具有一种作为社会身份的属性。
关于司寇迁移户口,里耶秦简中有“阳里户人司寇寄、妻曰备,以户(迁)庐江,丗五【年】(前212年)”[18]的记载。阳里属于迁陵县,简文记载了原住迁陵县阳里、身份为司寇的寄和他的妻子备,在秦始皇卅五年(前212年)迁徙到庐江的情况。简牍中有关于迁户的法律:
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5]127
张家山汉简中也有类似记载[2]54。如此看来,司寇迁移户口是有法律保障的。而且从司寇在里中居住和迁户的记载来看,司寇并没有被关押在官府或劳役场所,拥有较大的人身自由。《二年律令·亡律》载:“司寇、隐官坐亡罪隶臣以上,输作所官。”[2]30司寇只有在被监管的隶臣及其以上的刑徒逃跑后,才会被“输往作所之官”[19]154做劳役,这也说明司寇在平时享有较大的人身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司寇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迁徙,秦律:“当完为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司寇、隶臣妾、奴婢阑亡者舍人室、人舍、官舍,主舍者不智(知)其亡,赀二甲。”[1]59同时,《二年律令》170号简中也有类似记载,但中间少了“司寇”二字,这似乎意味着司寇的人身自由有所变化。
有学者根据上引里耶简8-1027认为“下妻之‘下’似指较低的社会身份”,由此认为司寇的“配偶身份较低”[20],这一结论有待商榷。首先,上文所引“阳里户人司寇寄、妻曰备”中提到司寇的配偶还有“妻”,即正妻。张家山汉简有“其毋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2]59这里将“嫡子”与“下妻子”相对,暗示正妻和下妻在婚姻中是嫡与庶的关系。即下妻之“下”表示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其社会身份没有必然联系。另外,我们还可以以奴的婚娶状况作为参考,张家山汉简载“民为奴妻而有子,子畀奴主”[2]34。奴尚且可以娶平民为妻,司寇当也可以。*鹰取祐司认为:秦简、汉简中的庶人为被赦罪者或刑徒、奴婢之被解放者,而且奴婢作为主人的财产并不处于官府的支配及管理之下,所以在爵制性身份序列中是没有位置的。参看氏著:《秦漢時代の刑罰と爵制的身份序列》,《立命館文学》第608号,2008年。这说明司寇的身份不比奴婢低。因此,司寇配偶的社会地位不一定低,甚至可能高于司寇。
(四)司寇刑的劳役
里耶秦简记载:
【尉】课志:卒死亡课,司寇田课,卒田课。·凡三课。8-482[17]165
有学者指出司寇劳作的田属于公田[21]。若考虑以下两点,笔者认为这种公田实际上是屯田。首先,简文中有“卒田课”即关于士卒田作的内容,这种情况一般属于军队屯田。其次,迁陵县的户口非常少,里耶秦简8-2004中有迁陵县在秦始皇廿八至三十三年的六年间,户口数从未超过200户。而根据“迁陵吏志”记载,迁陵县的吏员编制有103个[22],再加上驻军等,人数应该不少。仅靠一百来户平民供养他们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用刑徒劳作和屯田都是政府自给自足的必要措施。但是屯田活动并不涉及全国,因此这不可能是司寇的主要劳役。
法律中明确规定的主要劳役有传递文书,秦《徭律》载:“毋令典、老行书;令居赀责(债)、司寇、隶臣妾行书。”[1]119另一个重要的劳役是运输物资,里耶秦简?-5载:
廿七年(前220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小弗省小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23]192
委输传送,重车负日行六十里,空车八十里,徒行百里。其有□□□□而□傅于计,令徒善攻间车。食牛,牛(胔),将牛者不得券(徭)。尽兴隶臣妾、司寇、居赀赎责(债),县官□之□传输之,其急事,不可留殹(也),乃为兴(徭)。[1]150-151
《徭律》的另一条律文载:“传送委输,先悉县官车牛及徒给之,其急不可留,乃兴(徭)如律;不先悉县官车牛徒,而兴黔首及其车牛以发(徭),力足以均而弗均,论之。”[1]117这里的“徒”指的就是上条律文中的“隶臣妾、司寇、居赀赎责(债)”。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24]卷6,p303,可知岳麓简的记载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但里耶秦简-5的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二月,距离“更名民曰‘黔首’”的时间最多一年左右,其中引用的令文产生的时间应当更早。因此,岳麓秦简《徭律》的记载很可能晚于里耶秦简中的令文,司寇输送物资的劳役在秦统一全国后被加重了。
除了以上两种劳役外,司寇还要协助治安人员侦捕疑犯。如秦简中有狱史触率领司寇晦搜查逃犯[25]186、张家山汉简中有狱史举率领司寇裘捉捕疑犯的记载[2]109-110。侦捕疑犯与司寇“伺察寇盗”[26]298的含义相合。但《汉旧仪》认为司寇的职责是“备守”[27]85,就是在边疆监视敌人。因此有学者吸收这两种观点,认为司寇的伺察对象“既含外寇,又有内寇”[28]174。但是城旦的任务是“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24]卷6,p322;候也是“一种被用以伺望敌情的刑徒”[5]63。几种罪犯的任务都是伺察寇虏,应当各有所侧重。从目前所能见到史料来看,没有发现司寇在边疆“备守”的记载,再结合司寇有侦捕疑犯的任务来看,笔者认为秦和汉初的司寇在伺察寇盗方面是以“内寇”为主。
司寇的劳役还有监管刑徒。《新书》载:“若夫束缚之,系絏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29]卷2,p80-81《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汉代没有作为官职名的“司寇”,这里应指刑徒司寇。冨谷至也曾指出“司寇是对受刑囚进行司法管制的刑役”[7]31。总之,监管刑徒与“伺察寇盗”的意思相近,应当也是司寇的主要劳役。
综上可知,关于司寇从事的劳役,律文中大多有明确的规定。秦《司空律》载“司寇勿以为仆、养、守官府及除有为殹(也)”[5]54。即不得任用司寇作赶车的仆、烹炊的养、看守官府或其他的事。注释者认为司寇用以“备守”,故不得充当其他职役,现在看来这一解释不大准确。因为秦律明确规定司寇的职役还有传递文书和运输物资。目前还没有发现秦及汉初的法律中有如此详细规定徒隶劳役的内容,可见政府对司寇从事劳役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这种谨慎的态度应当与司寇兼具社会身份的属性相关。
二、汉文帝刑制改革后的司寇刑
(一)《汉书·刑法志》、《汉旧仪》中的相关记载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改革后的刑制,因《汉书·刑法志》、《汉旧仪》的记载存在差异而给后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学者们纷纷就此提出见解,虽然目前还存在很大分歧,但基本都认为它们反映了当时刑律的变化、《刑法志》的记载存在文字问题。*如沈家本、滨口重国、滋贺秀三、堀毅、高恒、张建国、冨谷至等,详见注释①。《刑法志》:
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13]卷23,p1099
这一记载存在两个突出问题:1.没有关于鬼新白粲刑期的记载。滋贺秀三等认为原文有脱落,张建国认为《刑法志》在流传的过程中将有关记载误入颜师古注中[30]。2.文中的“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容易让人产生以下疑问:根据如淳的注释,“司寇一岁”与上文相连,指隶臣妾在第三年服一年的“司寇”刑,以凑满隶臣妾的三年刑期,那么“作如司寇”就成了司寇刑的正式刑名,这又与目前的认识相矛盾。
滋贺秀三在分析相关问题后,推测原文有脱文,并试着做了增补(【】内的文字):
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免为庶人。鬼薪白粲满二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司寇】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15]80
关于鬼薪白粲部分的增补暂且不论。但司寇刑部分的“【司寇】作如司寇”得到了出土简牍的证明,如下文引用的居延新简二·四四,因此笔者赞同这一增补。
再来看《汉旧仪》:
凡有罪,男髠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完四岁,鬼薪三岁。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到三月。[27]85
整理者将“女为作如司寇”句读为“女为作,如司寇”恐有误,理由如下:
●捕律亡入匈奴外蛮夷守弃亭鄣逢燧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绛而贼杀之皆要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 九八三。[31]256-257
县官直用常徒者请丞相之当输者给有缺补其不得以岁数免及汉诸侯=国人有告劾罪司寇作如司寇以 二·四四。[32]247
贼律:殴亲父母及同产,耐为司寇,作如司寇。Ⅱ0115③:421。*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简文中的“及”字当为“之”字。
以上三条简文充分说明,男子判耐为司寇,女子判作如司寇。作为法律条文,它们的准确性甚至高于《刑法志》和《汉旧仪》中的记载。因此“女为作如司寇”不能句读为“女为作,如司寇”。综上,汉文帝改革后的司寇刑,因性别不同而异名:男子的正式刑名是耐为司寇,女子的正式刑名是作如司寇,刑期均为两年。而且男性的耐为司寇刑可以简称为“司寇”,如简二·四四所示。如果求全责备的话,将滋贺秀三主张的“【司寇】作如司寇”改为“【耐为司寇】作如司寇”应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耐为司寇刑也可以简称“耐罪”,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CWJ1③:201-1记载:
永初三年正月十四日乙巳,临湘令丹、守丞晧、掾商、狱助史护,以劾律爵咸(减)论,雄、俊、循、竟、赵耐为司寇,衣服如法,司空作,计其年。[33]221
雄、俊、循、竟、赵等人被判为耐为司寇,但木牍(J1③∶201-30)的记载稍有不同:
临湘耐罪大男都乡利里张雄,年卌岁。
临湘耐罪大男南乡匠里舒俊,年卅岁。
临湘耐罪大男南乡逢门里朱循,年卅岁。
临湘耐罪大男南乡东门里乐竟,年卅岁。
临湘耐罪大男中乡泉阳里熊赵,年廿六岁。[34]
他们的耐为司寇刑被称为“耐罪”。但并非只有男性的耐为司寇刑可以简称耐罪,《汉书·刑法志》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13]卷23,p1108这里的“耐罪”不仅包括男女司寇刑,还包括城旦舂和鬼薪白粲等徒刑,与秦及汉初的用法相同。
另外,《后汉书》中有一条关于“司寇作”的记载,见东汉明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赦令:“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35]卷2,p98这里的“司寇作”与城旦舂相对应,说明它指的是“司寇作如司寇”。但是“司寇作”仅此一见,在随后明帝、章帝统治的几十年里,赦令诏书通常这样写:
(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减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35]卷3,p158
较早的类似赦令还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诏[35]卷2,p118、永平十八年(75年)诏[35]卷2,p123、章帝建初七年(82年)诏[35]卷3,p143。这四份赦令关于司寇部分都写作“完城旦至司寇”,没有“作”字。清代的王鸣盛认为“司寇”后面之所以没有“作”字,是因为“史家因吏牍之文而失之”[36]324。曹金华注意到明帝永平十五年诏、永平十八年诏、章帝建初七年诏中“皆作‘完城旦至司寇’,无‘舂’、‘作’二字”,进而认为“似二字可省也。”[37]63这一说法恐不大准确,因为政府赦令一般都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不大可能用省称。这从反面说明,晚至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司寇”仍是男性判为司寇刑的称呼,女性司寇刑还是称作“作如司寇”。
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诏:“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35]卷4,p171永元八年(公元96年)也有类似的诏书[35]卷4,p182。这些诏书都用死罪至司寇来指代所有刑等。另外,公元109年由于久旱无雨,邓太后“比三日幸洛阳,录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35]卷10,p424也是用死罪至司寇指代所有刑等。这些都说明“司寇”又成了男女判罚的统一刑名,因性别而异名的局面消失了。
综上可知,晚至公元87年,司寇刑仍然因性别不同而异名。至迟在公元91年,东汉就已经将“司寇”(这里指男性耐为司寇刑的简称)、“作如司寇”重新统称为“司寇”了。这种变化与刑法发展趋势有关,即以劳役名表示刑法轻重逐渐演变为以刑期长短来衡量刑罚的轻重,因此复杂多样的刑名会被简化。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司寇作”中的“作”就是“作如司寇”的简称。首先,《后汉书》中有“输司寇作”,属于“罚作之别”[26]20。这使得“司寇作”容易和“输司寇作”混淆。其次,从上引敦煌汉简九八三号简的图版中可以看到,开头的“●”顶格书写,但是末尾的“作如”后面还有约一两个汉字的空白[31]上册,图版玖零,说明这极有可能是一条完整的简文,“作如”二字应是“作如司寇”的省称。综上,笔者认为“作如司寇”的简称可能是“作如”,并不是“作”。东汉明帝中元二年诏书中的“司寇作”本应写作“司寇作如”,后世不知“作如”的含义,又因《后汉书》中有“输司寇作”一语,故而将“司寇作如”改为“司寇作”。程树德《九朝律考》将司寇刑称为“司寇作”[38]57,《汉旧仪》的整理者将“女为作如司寇”句读为“女为作,如司寇”,可能都是受到这一篡改的影响。
(二)司寇刑的制裁措施
根据《汉旧仪》的记载,司寇刑仅比罚作重,属于比较轻的徒刑。*张建国认为“罚作最重要的特质,是受到处罚的人身份没有变化,不是刑徒。”也就是说他认为汉代最轻的徒刑是司寇,可备一说。参看氏著:《汉代的罚作、复作与弛刑》,《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在当时人眼中,司寇也算不上重刑,如鲁丕两次被判为司寇,但刑尽后即重新做官[35]卷25,p883-884,除了因为才能突出外,司寇属于轻刑也是重要原因。这时也看不到像秦和汉初对司寇、司寇子那种明显的歧视政策。
但是作为一种刑罚,仍然会有一些制裁措施。秦汉时期所有级别的徒刑都需要服劳役,司寇自然不会例外。据宫宅潔的研究,汉代的刑徒都要穿上用质地粗糙的“七稯布”做的赭色囚衣[4]101。另据笔者总结还有五条惩罚措施:(1)夺爵。史籍中有很多判司寇刑而夺爵的记载,如《汉书》载杨丘侯(《史记》作“瓜丘侯”)刘偃在孝景帝四年“坐出国界,(耐)〔削〕为司寇”[13]卷15,p431,沈猷侯刘受在元狩五年“坐为宗正听请,不具宗室,(耐)〔削〕为司寇”[13]卷15,p434。《史记》中关于二者处罚的记载皆写作“国除”[24]卷19,p1184、1195-1196,说明被剥夺了爵位。(2)没有被赐予王杖的权利。甘肃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中有关于赐予平民中老年人王杖的记载[39]36,可知判司寇刑的人是没有被赐予王杖的权利的。这一做法与汉初相同。(3)限制自由。光武帝时期的李章因为度田不实,被判为司寇,“月余免刑归”[35]卷77,p2493。刑制改革前的司寇可以居住在里中,享有很大的人身自由,而此时的司寇免刑后才能归家,说明改革后的司寇不能居住在里中,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4)注销户籍。东汉洛阳刑徒墓砖铭文的格式一般是“郡、县名+刑名+人名”,这里的县名并非是刑徒的籍贯,而是监狱名[40]。这与汉简中记载戍卒“名县爵里”的做法不同,说明一旦判刑后户籍就被注销,转而登记到监狱的籍簿上。注销户籍和不得在里中居住的惩罚,使得司寇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属性消失。(5)戴刑具。《汉书·宣帝纪》李奇注“弛刑”时说:“弛,废也。谓若今徒解钳釱赭衣,置任输作也。”[13]卷8,p260“徒”指的是各级刑徒。《后汉书》也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35]卷1下,p74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刑徒平时要戴钳、釱之类的刑具。居延汉简又有“施刑,故司寇”[41]449,司寇可以为弛刑,也说明平时需要戴刑具。
另外,司寇又可以分为“无任”和“五任”两种,如东汉洛阳刑徒墓砖铭文有“右部无任沛国与秋司寇周捐”,*同书T1M9:1、T2M60:2也是无任司寇铭文砖,但T2M60:2铭文作“右部勉刑济阴甄城司寇任克”,作者解释道“‘勉刑’即‘施(弛)刑’,指不需要带刑具的刑徒,他们大多数是‘无任’刑徒。”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吴荣曾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免刑和弛刑在汉代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用语,免刑是解除刑罚,弛刑是解除刑具。参看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79-281页。“右部五任河东皮氏司寇荆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196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同书还有6块无任司寇墓砖,编号分别为:P3M10:下9、P6M4:3、P9M30:1、P10M29:1、P11M33:1、T2M11:1(与采42铭文相同)。另外,P7M26:1铭文作“右任南阳都阳司寇麯新”“右任”的意思待考。“‘五任’是指刑徒原居住地的里正及邻里不少于五人为其出具担保,保证该刑徒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或再犯罪,该刑徒因而获得在服役期间免戴刑具的待遇;‘无任’则指无人为刑徒提供担保,为防止其逃跑,而必须给他戴上刑具。”[42]根据墓砖铭文可知,不仅仅是司寇可以分为“无任”、“五任”,城旦、鬼薪等也能如此划分。整个墓地共出土823块墓砖,其中仅有6块标明是“五任”*关于墓砖总数的论述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1964年发掘报告》,第48页。关于“五任”的总数由笔者根据书中附表三(第98-122页)统计得出。;“司寇”铭文砖共11块,其中“无任”8块,“五任”仅1块,另有2块没有标明“无任”或“五任”。*笔者根据《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1964年发掘报告》附表三统计“司寇”铭文砖共12块,其中T2M11与采42铭文相同,故只算作1块(即1人)。无论是司寇还是其他刑徒,“无任”的死亡率都远高于“五任”。另外,由于当时不再以劳役的轻重作为衡量刑罚轻重的主要标准,当各级刑徒从事相似的劳役时,司寇的死亡率不至于这么低。关于这一问题,悬泉置汉简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五凤二年,前56年)谨案,置一□置前坐盗臧直百满以上,论司寇输府徙属县泉置”[43]23,某人判为司寇后输作太守府,后转徙郡辖的悬泉置,这似乎说明司寇一般只在本郡内服劳役。
以上虽然总结了七条惩罚措施,但是这些并不是司寇刑独有的,而是所有等级刑徒共有的处罚。这也说明自从汉文帝逐步确立以刑期的长短来衡量刑罚的轻重后,原本附加在刑罚上的其它用以区分刑罚轻重的处罚措施逐渐消失(但并不是说毫无附加惩罚措施)。
三、结 语
秦和汉初刑罚中的司寇刑一般是耐为司寇刑的简称,它源于秦国故律,是一种比隶臣妾轻的无期徒刑。耐为司寇在当时又被称为“耐罪”,但无论是“司寇”还是“耐罪”,都不是耐为司寇独有的称呼。
耐为司寇的刑徒拥有户籍,在里中居住,可以迁移户口和娶平民为妻,享受名田宅、免老、政府赐衣和赐酒食的权利。从司寇的权利和劳役可以看出,他们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也不大可能戴刑具。司寇居住在里中,但是要从事治安和屯田之类的劳役,这说明司寇受到乡官里吏和县尉的双重管辖。司寇子的身份是士伍,不会继承司寇的刑徒身份。但是大约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五月之前,司寇子可以做佐一类的小官,之后便没有这一资格了。这一规定使得司寇户的地位进一步降低,而且很难被改变。司寇的立户、名田宅等权利,使得司寇具有一种作为社会身份的属性。类似于司寇、赘婿的人群数量庞大,对我们重新认识秦和汉初的社会性质很有帮助。*与司寇身份相近的尚有“七科讁”,而赘婿即属于“七科讁”中的一种。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至前101年)伐大宛,“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第2700页)这里虽没有说明“七科讁”的人数,但从“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的记载来看,数量应不少。而此时距离汉文帝刑罚改革已有六十余年,据此推测,秦及汉初“七科讁”一类的人数十分可观。前引孙闻博文也指出“汉文帝刑罚改革之前的秦及汉初,乃是身份低于平民群体数量较多、官私拥有奴婢较为普遍化的历史时期。”这一论述颇具启发性,而且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作为刑徒,司寇不得担任官府小吏,没有拜爵以及接受由此而带来的赏赐的权利,也没有继承爵位的权利。秦二世元年(前208年)有恢复司寇需要承担额外赋税的记载,这显示司寇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加大。司寇也没有稟鬻米、受王杖、免为睆老的权利。司寇虽然有享受政府赐衣和赐酒食的权利,但是物品的质地、数量与平民有区别,而且还将司寇与徒隶并列,这说明给予司寇的赏赐很可能不是与里中的有爵者、无爵平民一起进行的。司寇虽然居住在里中,但属于里中的边缘人物。
司寇刑的主要劳役有侦捕疑犯、监管刑徒、传递文书、运送物资四类。“司寇”之名就来源于前两项劳役。司寇运送物资的劳役在秦统一六国初期还不算太沉重,之后便成了该劳役的首批征发人群,负担加重。从秦和汉初的简牍记载来看,当时对司寇从事的劳役有比较明确的限定,这与徒隶内部各级刑徒的劳役已经混淆,无法衡量刑罚轻重的状况不同。
总之,从上述内容来看,司寇刑具有社会身份和劳役双重属性,而且是终身的。秦和汉初的一些法令使得司寇的地位一直处在变化中,但总的趋势是权利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这些法令显示统治者在尝试为司寇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以往我们在分析汉文帝刑罚改革的原因时,大多从有效利用刑徒劳役、劳役的混淆使其逐渐失去衡量刑罚轻重的功能、肉刑的废除、以及没收制度的废除迫使重新建构刑罚体系[44]等角度进行阐述。但这些观点主要着眼于徒隶,忽略了作为重要刑等的司寇的作用。
根据简牍记载可知,《汉书·刑法志》关于汉文帝刑罚改革中司寇部分的记载存在文字脱误,滋贺秀三的相关推论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后的司寇刑仍属耐罪,但因性别不同而异名:男性的正式刑名是耐为司寇,女性的正式刑名是作如司寇,都是二岁刑。这时的耐为司寇刑可以简称为“司寇”,作如司寇的简称可能是“作如”。《后汉书》中关于东汉明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赦令中的“司寇作”应是“司寇作如”之误。至迟在公元91年,东汉又将“司寇”(这里指男性耐为司寇刑的简称)、“作如司寇”重新统称为“司寇”,司寇刑因性别而异名的局面结束。司寇刑名的变化,意味着刑罚名称的进一步简化,以往我们只注意到“隶臣妾”“城旦舂”刑名的消失,实际上还应加上这一表现。关于司寇刑的惩罚措施有服劳役、夺爵、限制自由、取消受王杖的资格、取消户籍、穿质地粗糙的赭色囚衣和戴刑具等。但是这些措施是针对所有刑徒的,并不是只针对司寇。由此可见,汉文帝刑罚改革后,尤其是《汉旧仪》记载的时代,*《汉旧仪》中缺少隶臣妾刑,据冨谷至考证,隶臣妾在汉武帝元狩年间以后就消失了。参氏著:《秦汉刑罚制度研究》,第84页。作者卫宏死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因此《汉旧仪》记载的时代应是西汉武帝元狩年间至东汉初年。刑期的长短已经成了衡量刑罚轻重的主要标准。但并不是说毫无附加措施,从东汉洛阳刑徒墓中司寇数量很少的现象来看,司寇似乎主要在本郡服劳役。由于取消户籍和限制自由等原因,司寇刑的劳役属性逐渐加强,社会身份的属性逐渐消失。总之,司寇刑的变化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和刑罚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 韩树峰.耐刑、徒刑关系考[J].史学月刊.2007(2):22-27.
[4] 宫宅潔.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M].杨振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6]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冨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M].柴生芳、朱恒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9] 肖灿.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0.
[10] 郭书春.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1] 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M].萧红燕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12] 鷹取祐司.秦漢時代の刑罰と爵制的身份序列[J].立命館文学(第608号),2008.
[1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卷2战国秦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5] 滋贺秀三.中国上古刑罚考——以盟誓为线索[C]//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8法律制度.姚荣涛、徐世虹,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 椎名一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にみテえる爵制—「庶人」への理解を中心として—[J].鴨台史学(第6号),2006.
[17]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8] 何有祖.里耶秦简牍缀合(八则)[EB/OL].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52,2013-5-17.
[19] 彭浩,等.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0] 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J].中国史研究,2015(3):73-96.
[21] 沈刚.《里耶秦简(一)》所见秦代公田及其管理[M]//杨振红、邬文玲.简帛研究(201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2] 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一)[M]//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考古发掘报告[M].长沙:岳麓书社,2007.
[2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5] 朱汉民,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26]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M]//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28] 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M].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29] 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30] 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初探[J].历史研究,1996(6):12-24.
[31]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M].上海:中西书局,2015.
[34]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J].文物,2013(6):4-25.
[35]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7] 曹金华.后汉书稽疑[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8]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9] 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C]//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4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J].考古,1972(4):2-19.
[41]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42] 于振波.“五任”与“无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9-101.
[43]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
[44] 石岡浩.収制度の廃止にみる前漢文帝刑法改革の発端—爵制の混乱から刑罰の破綻へ—[J].歷史学研究(第805号),2005.
10.13718/j.cnki.xdsk.2018.01.019
K234
A
1673-9841(2018)01-0173-11
2017-06-19
张新超,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重庆市社科项目“出土简牍与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乡里社会研究”(2016QNLS51),项目负责人:张新超;西南大学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及社会变迁研究”SWU1709112),项目负责人:邹芙都;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秦汉乡里问题新探”(SWU1509439),项目负责人:张新超。
责任编辑 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