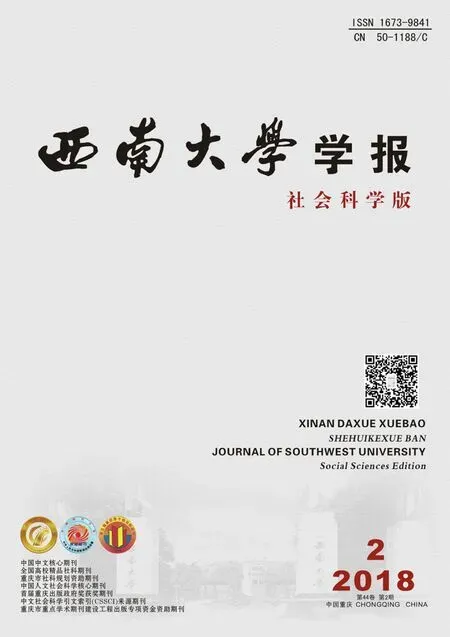论唐传奇虚构叙事的艺术原则与创作成就
黄 大 宏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 400715)
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表达特定文学意图的手段,也是衡量小说成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里的故事应当是虚构的,是小说叙事之本体;故事应当有特定的意义,而且是依据人物的行动——即随着情节的展开——而得以表达的。这是小说理论的常识,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仍然值得特别强调,它是中国“小说”概念与小说作品名实相符的关键,也是判断唐传奇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成熟标志的关键。按照董乃斌的说法,即“长期充当子、史附庸的中国古代小说,由史的政事纪要式叙述转变为小说的生活细节化叙述,迈出了文体独立的第一步。这是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1]。我们认为,这一“转变”的要害在于传奇从志怪破茧而出,把虚构一个完整故事作为叙事任务和目的,从而使故事真正成为表达特定文学意图之载体。简言之,用一个粗陈梗概的事件说明一个道理,和用一个完整复杂的故事承载一个文学意图,二者有重大差别,这是发展转变的结果。这一转变意味着“传奇法”——即小说叙述行为的艺术性在创作事实上的形成,支配这一转变的,则是“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
一、从“幻设为文”到“传奇法”:对唐传奇虚构叙事的历史认识
虚构是唐传奇叙事的历史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认识要晚得多,大体萌芽于元代而形成于明代,至民国初为现代小说研究所接受,主要经历了从“幻设为文”之说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加以概括的过程。追述这个过程,是为了澄清一些相关的误解。
鲁迅曾指出,《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2]179。这是他批判地接受纪昀对《聊斋》“一书而兼二体”特色的眥议,以“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一语对《聊斋》的创作方式、内容特征进行肯定,并首次提出“传奇法”概念。但他没有对何谓“传奇法”作更多的阐释,现有研究也不很明确。陈平原说“翻空出奇的结构,缠绵悱恻的情感,本就是以传奇体(引者按:文中“以”字或是衍文)志怪的基本要求,似乎不必细说”[3],但是,既然认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重要价值,其内涵未必就是“似乎不必细说”!进而,传奇体志怪就只有“翻空出奇的结构,缠绵悱恻的情感”这两个基本要求吗?还是它们实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效果呢?按照鲁迅的意见,叙述花妖狐魅之事的《聊斋》能够超越历代志怪,关键在于与“传奇法”的结合,何为“传奇法”恐怕就不能一笔带过,而是认识唐传奇创作原则的重要问题。这就有必要追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说的来历。
我们认为,虽然唐传奇以叙事取胜,具有史传文的文体特征,却与史传的叙事精神貌合神离。纪昀对《聊斋》艺术的评论以及鲁迅对纪昀观点的批判性接受,都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先要指出,“传奇法”与志怪的结合,决不意味着作家采用传奇的某些手法表现志怪式的内容而已*按鲁迅约在1920年所作《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但后来突破了这种认识,即蒲松龄向唐传奇学习的并不仅仅是文字。见《鲁迅小说史大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因为成熟小说的表现手法都要服从于总的创作原则,从而对事物整体性质的判断不能依赖对个别特征的把握。尽管在“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结合中,志怪提供了事件——或曰题材与内容,并决定事件的性质,但“传奇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在创作方法上具有统摄、包容与集合的性质,还具有与史部叙事写实原则相对立的性质。因为六朝志怪与《聊斋》式的志怪其实是名同实乖的两类作品,至少在作家的创作态度和认知水平上,前者秉承的是纪实原则,后者却有“象外之旨”“言外之意”,须超越纪实而趋于典型化才是“传奇法”的基本精神。由此判断,虽然学者普遍认为纪昀对《聊斋》的眥议具有拘泥于文体规范的保守倾向,却表明纪昀看清了《聊斋》叙事与史传叙事的差距,即《聊斋》貌似志怪,实属传奇,它不是纪实之作,而是虚构的产物。盛彦之《姑妄听之跋》记录纪昀对《聊斋》的评论说:
《聊斋》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之樊嫟,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今嬿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从何而见闻,又所未解也。[4]535
在纪昀看来,“小说”一词本指记录异闻杂事的子史之作,以六朝志怪为代表,乃写实之文,即所谓“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可以“随意装点”,这种“传记类”文字只有当事人才能叙述详尽。《聊斋》故事既非花妖狐魅自述,作者又无从知晓,其“嬿昵之词,媟狎之态”却曲折生动,这显然不合常理。袁枚讥议《聊斋》有“繁衍”之病,大体也有此意。因此,纪昀认为《聊斋》用传记笔法写小说,徒求文笔之胜而有悖于史传的叙事原则,故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鲁迅对此总结说:“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2]183这是合乎纪昀本意的。但鲁迅没有点出纪昀持论的关键,却不能说他不明白,这就是纪昀口中的“传记类”其实不指史部传记文,而指由此衍生的“杂传记”,或曰杂传、杂纪、别传、内传和外传等,虽然隶于史部,形似史体,却是一种小说化的传记文。
杂传记创作兴于汉,盛于魏晋六朝,至《新唐书·艺文志》列为史部十三类之一,仍与正史相区别。《太平广记》则辟“杂传记”一类,专收传奇之作。杂传记之小说意味浓厚,不能以史料视之,前人的态度很清醒。辛文房《唐才子传》说:“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然影响所托,理亦荒唐,故不能一一尽之。”[5]纪昀也说“《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6],意思是《太平广记》既收志怪,又收杂传记,如在《异苑》等书之外,又录《会真记》(即元稹的《莺莺传》,见《太平广记》卷四八八“杂传记类”)之属,是着眼于志怪、传奇内容相近的特点,与类书的性质相合。《四库总目提要》论《飞燕外传》亦云:“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7]这里的“传记之类”,仍然是杂传记的意思。对照胡应麟对志怪和传奇的分类:“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8]282益可知纪昀所谓“传记类”正包含唐传奇在内。
这番清理在于揭明以下认识:首先,纪昀看到了《聊斋》写志怪的艺术方法及其小说史渊源,只是他不认同,即六朝志怪的写法才是正宗,用传记的写法则是左道旁门,这和他的志怪创作原则是一致的。其次,他用来指称《聊斋》叙事文体属性的“传记类”一词,实指史传旁流“杂传记”之属,就在叙事精神上把“杂传记”踢出了史部。这两点很有启发性,虽然我们往往在史部重叙事的认知前提下强调杂传记之属的史体特征,但须牢记,史部叙事原则是实录,杂传记之属却以虚构性而为中国史学传统所不容。因此,记录志怪而有“嬿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之致,岂能出自史体,实在是传奇之风韵!
但是,纪昀的观点却长期被误解,即将这里的“传记”理解为史部记传,以“传奇法”与史传笔法相联系,片面强调传奇的史部叙事血统,从而把对传奇创作方式的讨论引到了偏离要害的方向。在王士禛《聊斋志异题评》评《张诚》为“一本绝妙传奇(引者按:此“传奇”很可能指戏曲)”[4]366之后,蒲立德《聊斋志异跋》即云:“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4]408冯镇峦评论纪氏观点时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而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虽有乖体例可也。”又云:“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4]534事实上,纪昀口中的“传记类”,与“历代志传”“传记体”“史家列传体”等概念可谓形近而神远。影响所及,上述误解却成为研究唐传奇叙事方式的出发点,有学者称:“小说与史乘之不同,主要在虚构。……但是,尽管宗旨不同,传奇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却是直承史传的。”[9]其实,小说最重要的叙事方式就是以想象为基础的虚构,不因作家有无明确意识而改变。故当唐传奇与史乘(包括志人、志怪)秉持不同的叙事宗旨时,虚构的传奇如何能在叙事方式上直承记实的史传文?这是先把传奇归入“杂传记”,再视同于传记体的结果,更是被史部记传派生出杂传记再旁衍为传奇的文体渊源,以及相近的文体特征所影响的结果。其实,传奇以人立篇的准则(正史传记以人立传,杂传记、传奇亦如此)、以“传”“记”为名的命名通例,偏于记事的内容特点等,都是用以构建一个故事框架的要素——所谓传奇在叙事方式上直承史传,意义仅在于汇集了此类拟史特征而已。究其实而言,这是使传奇在实质上等同于史传,还是拉开了距离呢?显然,所谓“《史》《汉》遗法”“班、马之笔”等,只是传奇叙事方式的渊源和文体形式因素,当传奇叙事方式一旦发生重大突破,其性质就根本不同了。陈文新指出:“以史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对‘小说’的虚构便很难采取宽容态度。”[10]把这一论断倒过来,结果必然是说,一旦小说强化了虚构属性,必然在本质上不同于史传,甚至不能列入“史余”的范畴——这也是现代小说学者对古典目录学固守藩篱的批评所在。正如有论者所谈到的,赵彦卫提出传奇有“文备众体”的特点,在唐诗的文化氛围中成长,饱含诗的情韵,“情感和想象的加入,使小说的精神面貌迥异于史传,不止是描写的细腻和文辞的华丽,更重要的是摒弃了史家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而采取爱憎分明的强烈的主观态度,这个感情倾向不仅表现在概述中,而且渗透在场景描写中。史传的文字是冷峻的(也包藏着作者的态度),小说的文字是热烈的”[11]。在传奇中大量插入诗赋,发挥着传情达意、绘景状物、参与情节等多方面的作用(这在史传中只是个别现象),以及叙事角度、叙事时序上的创造等,共同构成了传奇的基本艺术特征。概而言之,鲁迅以“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评《聊斋》,以“传奇”代“传记”,是对纪昀“一书而兼二体”说的批判性继承,超越了对史传形式及表现手法等形似之迹的牵绊,揭示出从唐传奇到《聊斋》的创作成就的奥秘,既正本清源,又得其心——这奥秘就是虚构,就是“幻设为文”。
何谓幻?《说文》云“相诈惑也”,即不真之象。设,构造也,即《易·系辞》“圣人设卦观象”之意。“幻设”连用,即设置假象,故引为虚构之意。无须过多引述古代小说家和评论家对小说虚构的褒贬态度,就以唐传奇出自虚构的认识而言,大抵以元人虞集最早,“盖唐之才人……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事,傅会以为说……非必真有其事,谓之传奇”[12]。所说“想象”二字,在唐传奇创作态度及方法的认识史上,确乎有石破天惊之感。但以“幻设”一词明确表达虚构的意义,则首见于胡应麟,从《少室山房笔丛》的五个用例可见与“幻设”相关之种种内涵:其一,“古人著书,即幻设必有所本”[8]315。此语说虚构应有依据,与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皆有所据,不敢谬言”之意相同,其所本之物,可以指事实,亦可指逻辑。其二,“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8]371。此说唐传奇所述变异之谈尽出于虚构,而《剪灯》系列出于名流之手,记事亦多不实。其三,“唐人小说诗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异记》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铭殊工。盖唐三百年,如此铭者亦罕睹矣,岂薛生能幻设乎?”[8]372由此说可见“幻设”的对象也包括传奇的文辞。其四,“《树萱录》,宋王铚性之撰,盖幻设怪语,以供抵掌取忘忧之义,而郑樵列于种树家,大为可笑”[8]378。此说《树萱录》记事出于虚构,以之为谈资,可怡悦读者,故《通志》不应入史部种艺类,而应列在小说类。其五,“《新》《余》二话本皆幻设,然亦有一二实者。《秋香亭记》乃宗吉自寓,见田叔禾《西湖志余》。《至正妓人行》则昌祺目击事,以拟乐天商妇者也。缘他多虚妄,并二事实历废之”[8]435。此语分明是将幻设与纪实相对而言[8]371。
以上诸“幻设”语皆为“虚构”之意*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六注《招魂》,称其“卒章‘魂兮归来哀江南’乃作文本旨,余皆幻设耳”,意指前数章之辞出于“虚构”,用辞或即受到胡氏的影响。。可知“幻设”的意思就是用虚构方式构造故事和文辞。这里的故事可以是怪异之谈,也可以是人间言动,文辞则有工致、多彩甚至夸饰的特点。在这一意义下,鲁迅在“凡变异之谈……假小说以寄笔端”一段下说:“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2]54并肯定“其言盖几是也”[13],高度认同胡氏关于唐传奇的文学意图和表现手段出于“意识之创造”——亦即虚构的判断。他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54之著名论断,即是受此类观念的影响而提出的。在他看来,六朝志怪偏于纪实,“未必尽幻设语”,唯唐人能幻设为文,借小说之体表达“作意好奇”与“有意”之旨,这是传奇成为“唐代特绝之作”的根本原因。他将“幻设”对象明确指向文采和意想两点,而意想因假托故事而存在,故“传奇法”独异于诸文体者,既在辞章之美,更在叙事之曲折丰满。故云:“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55即传奇与志怪有“传鬼神明因果”之同,而在有无“文采与意想”上分道扬镳,有文采则须“施之藻绘”,有意想则须“扩其波澜”如《枕中记》等。他说:“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所本……间亦有病其俳谐者,则以作者尝为史官,因而绳以史法,失小说之意矣。”[2]58对照《搜神记》所述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之事,《枕中记》叙事丰富曲折,传达士人“歆慕功名”心理之传神,情节描写之“诡幻动人”,得于“施之藻绘”处浅,得于“扩其波澜”处多。出于“幻设”的叙事波澜,使《枕中记》以富于“意想”而称传奇翘楚,非但不以俳谐之风为病,反而正是小说本意。此可谓有驳有立:所立者,传奇创作之方便法门;所驳者,不识小说实质之淆乱批评。
要指出的是,“幻设”之“虚”不同于“虚实”之“虚”。“虚实”之“虚”与“实”相对,意同于“伪”,论此“虚实”就是论“真假”。“幻设”之“虚”乃想象之产物,同于王充《论衡·订鬼》“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14]之意,论此“虚实”则是论艺术典型与生活真实。一般说来,想象生发于作家的创作意图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读者的阅读意图,实现这两个意图的途径是虚构——通过构造典型故事、塑造典型形象,创造超越生活现象的艺术美,从而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认识和揭示生活的本质。只有当艺术超越了它所摹写的原型,所创造的世界才具有独特性和必然性,成为具有更高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典型。就此而言,虚构的本质即艺术的典型化原则。唐传奇的核心成就,正是通过虚构超越了现实,实现了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这就是“传奇法”作为创作方法之于传奇的意义——它是唐传奇作家通过虚构创造的高于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真实,既以此探询生活的意义,也使意义得到呈现——因之使传奇在文体层面得以独立,在作品层面成为小说史的特绝之作。鲁迅以“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论断,既指出了《聊斋》“写什么”的问题,更强调了“怎么写”的问题,从而反哺对唐传奇的研究。
二、“立象以尽意”是潜在影响唐传奇虚构叙事的方法论原则
唐传奇的虚构叙事原则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传统哲学中的“言意之辨”以及为了突破言为语障、理障而产生的“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乃是唐传奇虚构叙事原则的潜在依据。
在《唐之传奇文(上)》中,鲁迅讨论“幻设为文”与唐传奇创作的关系,有一段值得寻味的话:
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2]54-55
鲁迅指出,“幻设为文”的现象渊源甚早,至晋世而兴盛,阮、刘、陶氏诸文皆出于虚构,却以寓言为体,不求文采,影响到王绩与韩、柳古文的创作,却非唐传奇的前世今身。这段话强调唐传奇源自志怪,并在其创作基础上“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形成注重文采与意想的文体特征,应该说是合乎事实和逻辑的。其可寻味处乃在“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一语,是指《大人先生传》诸篇,或为人物立传,或为酒德作颂,或叙世外桃源,内容皆出于虚构,但既非传,亦非记,更不是颂,而是寓言。《庄子·杂篇·寓言》云:“寓言十九,藉外论之。”[15]836郭象说:“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15]837即大人先生、五柳先生等皆为假托言理的形象,重在寓意的表达,故“其言多不辩”。我们认为,这段话里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素有“幻设为文”的传统,只是所“幻设”之“事”的形态不同,文词的“藻绘”程度也有差别;二是“幻设为文”的作法兴盛于晋代,但用来作寓言,至于成为小说创作方法,则以唐传奇最典型,易言之,唐传奇不是寓言。合起来说,鲁迅从小说创作史层面强调了唐传奇在叙事虚构性方面的典型性,以证成其唐代“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同是“幻设”之文,晋世前后的寓言假托形象以寄托道理,唐传奇则以故事承载“文采和意想”,它们都是在“言意之辩”的哲学传统影响下,为了摆脱“言不尽意”的制约,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方式,为实现“象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形成的不同文体形态,它们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因为不同的创作宗旨和创作传统共存。易言之,凡属“幻设”,其必有“象”,只是立“象”的方法不同,使此“象”与彼“象”的特征与形态不同,故其所尽之“意”也就有了区别。
老子认为,“道”是真实存在的,是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并且具有超验性,“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混成一体,即《老子》第十四章所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16]113。因道无形,故无法言说,可名可言者皆非真知大道,故《老子》第一章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6]53。这指出了日常语言在表达终极概念时的局限性,开启了哲学层面上的“言意之辨”,主流观念是《周易·系辞》提出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但人类要认识及把握大道,不可不强为之言,故须别出蹊径,形成以形象把握本质即因言立象、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6]145即通过主体对象的体察,就可以呈现、把握和领悟本体。这就是《周易·系辞上》对言、象、意之关系的解说所揭示的道理:“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17]这里的“象”本是卦象,将天地万物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即可以见天下之事形,把握天下之言动。这种透过“立象以尽意”来冲破言说屏障的思想,经由庄子的深入探讨,以及先秦诸子的发展,成为表达思想的基本原则。《荀子·正名》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18]《韩非子·解老》认为:“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19]这些观念在解决言不尽意又只能以言尽意的悖论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魏晋时期,王弼把《老》《庄》思想结合起来,对言、象、意三者关系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解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20]就是说,在言象关系上,象是体、言为用;在象意关系上,意是体、象为用。哲学家以富于比喻性的语言立象,用富有启示性的象揭示形而上的理,即立象乃手段而非目的,大旨归于明理与认知。至此,以“立象以尽意”的方法突破“言不尽意”的限制的方法论原则终告成立。
到唐代,在书法、山水画创作及其评论领域里,凡创作或议论,大抵都以“取象”为手段,以具体可感的“象”来表达不可思议的言说,即“立象以尽意”的原则在艺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文学自然亦概莫能外,其“象”在诗,即为意象;在小说,就是虚构故事。究其原因,则从表达的功用上说,要精确传达丰富复杂的审美体验,日常语言难以胜任,即《文心雕龙·神思》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21]。“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烦恼困扰着所有的文学家,须借象以言之,此其一。从表达的效果上说,卦象的虚拟性使其内涵具有更多的暗示性和更丰富的象征性,易于激发联想,延伸至象外之象,从而拥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和阐释空间;卦象的不确定性使之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可以使丰富复杂的事物与现象得到共时的、整体性的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的表现。《周易尚氏学》谓:“意之不能尽者,卦能尽之;言之不能尽者,象能显之。”[22]《学易笔谈》谓:“立象以尽意者,正以言难两歧,而象可通变。”[23]《庄子解》谓:“《易》之妙,妙于象。”[24]卦象还具有可视性,使意的表达更形象,如在目前,更易于理解。故朱熹《周易本义》云:“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观奇偶二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则可见矣。”[25]这正是文学形象所追求的表达效果,也是文学形象所能够取得的表达效果,“立象以尽意”的方式无疑为解决语言文字有限性与表意无限性的矛盾提供了途径,此其二。再从表达的根本目的上说,言与象都是人创造的语言符号,观物所取之象可以更好地把握天地之道和圣人之意,典型化的文学形象可以更好地传达文学意图和作品意义,作为一种诗性言说方式的“立象以尽意”原则与文学创作方法完全相通,故谓“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26],此其三。魏晋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强调构造意象,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讲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蕴藉之美,追求“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不可思议之境界,以消除语言文字引起的语障和理障,皆根源于“立象以尽意”的思想和方法。
当然,文学“立象”与哲学“立象”又有不同处,在于“立象”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目的,或曰有象即文学,无象即无文学。钱锺书说:“理颐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舍象也可,……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27]按钱氏之说,文学的“象”与要表达的内容是有机融合的,“象”就是意象,“意”指审美体验和兴趣。在意象之中,“象”是手段,也是目的,“象”蕴含“意”、会融“意”;“意”浸润“象”、化合“象”,从而形成仪态万千含蕴深致的作品。诗歌通过塑造意象以表达情志,是《诗》《骚》以来的传统,经六朝以至唐代,成为中国诗歌的创作法门,岂独文章无之乎?落脚处即在传奇,而旁衍于韩愈等人的杂说之文。如果把钱氏语中的“诗”换作“小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在小说领域,“象”的形态曾经是叙事片断以充当言理之喻体的方式,构成诸子寓言、六朝志怪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成长为具有典型化意义的以人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完整故事,以唐传奇为典型形态。唐传奇既是“有象之言”,且“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即无传奇,“变象易言”是别为一传奇甚且非传奇,传奇通过故事以体现其“意义之迹”,传奇之“象”遂与其内在文学意图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小说从具有叙事意味(或曰小说因素)的文学形态发展到真正叙事文学的一般过程及其特点,转折标志乃在唐传奇。鲁迅指出:“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2]280把这段话放到“立象以尽意”的语境中,就可以对唐传奇的创作实绩、创作方法和历史地位作出这样的理解:中国小说创作发展到唐代,终于学会运用典型化的手法虚构(即取象之法)一个完整的故事(即立象之形态)——这是典型的借小说以寓寄托之法,此系小说创作之法与文法、诗法的互动;或是对现实生活的典型化,以表达于生活和世界,也即对存在本身的发现和理解——即因立象而所尽之意。这种完整的虚构故事依然可以包含志怪因素,即借志怪立象,但叙事形态所达到的水平决不可同日而语。这使传奇超越了假托寓言以议论说理、用实录原则记录事件以谈鬼神明因果的早期阶段,也超越了丛残小语和片断缀合的结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手段,满足了以故事为小说基本面及最高要素的文体要求,由此具有丰富和复杂的意义空间和阐释空间,产生了有类于诗歌意境一般的“言外之意”或“象外之旨”。简而言之,唐传奇作家懂得并掌握了旨在“尽意”的取象之法,使塑造故事成为小说创作的核心,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这是唐传奇在“立象以尽意”的观念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下在小说文体规范上的巨大进步,是唐传奇最具有创造意义的成就,令中国古代小说开启了自我树立的道路,进入“有意作小说”的全新时代。对后人来说,则可以透过那些故事发现及认识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
三、唐传奇是以“立象以尽意”的方式表达文学意图的典范
唐人对于运用“立象以尽意”的原则作传奇有没有明确的意识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唐人作传奇,虽然有“志异”“记异”的动机,以惩恶扬善有益于世为目的,但仍然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学创作,即《任氏传》“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李公佐在《谢小娥传》结尾说“余备详前事,发明隐义,暗于冥会,符于人心”,认为应当借谢小娥复仇的故事,“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沈既济以任氏以死报郑六之情,提醒读者看重女子的痴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李朝威有感于“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的精神品质“宜有承焉”,而凡人竟可以“移信鳞虫”之义举,遂作《柳毅传》。白行简为表彰妇人“操烈之品格”而述汧国之事,因有《李娃传》,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都致力于故事的描述、人物的刻画,而不是摆出腐儒面孔作高头讲章。其实我们看传奇章法,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故事后面带着一个议论的尾巴,如《李娃传》《任氏传》等;一是纯写故事,文随事起,事毕文终,戛然而止处不乏余意未尽余响未绝之风韵,如《枕中记》《霍小玉传》等皆是。就前一情况而言,这个尾巴虽然在形式上与史传有关,在内容上有发明宗旨、说明动机、实施教化的色彩,其实所占文字比例很低;再加上后一种情况,传奇的主体无疑是叙述宛转、文采华艳的故事,较之六朝志怪,这都是完全不同的变化。唐传奇甚至开创了以小说排陷攻击政敌的恶例,动机虽恶劣,但看《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纪》等作品,仍当叹服其想象之丰富,结构之饱满,细节之生动,文采之富艳,影射之精准恶毒。这些都是小说,是以故事及其人物本身的特点达到诬陷的目的;而非弹劾的奏章,以举例为据,点明意义为写作的宗旨。
从创作角度看唐传奇虚构叙事的自觉性,还有两个考察角度,一是考察同题材故事的叙事性发展,一是自创新故事,都可以看到唐人借虚构故事表达文学意图的努力。在前者,鲁迅举出沈既济的《枕中记》出自焦湖庙祝以玉枕使贾客杨林入梦的例子,指出沈作“诡幻动人”的特点及对唐人“歆慕功名”心理的揭示。从我们的视角看,沈既济对杨林故事进行改造,集中在改变人物身份为应试举子和极力铺排入枕后的婚姻、仕宦及家族兴旺景象二点上,使人物身份和故事情节更具因果关联,极大地扩充了杨林故事的情节丰厚程度。更重要的是,《枕中记》故事写出了唐代文人的心理期待,符合唐代生活实际与取士制度,入梦后的奇遇被看成是唐人婚宦生活的理想图景,梦醒前后的焦虑与怅然也高度概括了唐代士子的人生困境。一个奇特的故事化身为反映唐代士子人生状况的当代传奇,这是叙事艺术发展结出的硕果。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离魂记》《补江总白猿传》等大批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28-30]。对旧故事的再创作,扩充了叙事结构,重构了情节链,丰富了故事细节,在社会条件、人物形象和内在精神上完全唐代化了,如果没有叙事意图的自觉性,那么这种效果就无从谈起。
小说不是史料,却可以比史料更准确、更具体、更生动地揭示时代面貌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使人体会到鲜活生命所带来的感动,以及小说艺术的成熟与精到。因此,唐人所作的新故事都可以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中找到存在的语境和生长的依据,这些结构精当、情节曲折、人物丰满、文字曼妙、才情灿烂的故事的典型性和生动性,足以成为认识唐代社会与唐人心理的镜子,从中看到小说家透过人物写出的个性心理和时代精神。
在《飞烟传》之前,没有哪篇小说细致而强烈地写出了不和谐的婚姻带给女性的绝望和反抗。步飞烟对赵象的倾慕之情给予了积极回应,当私情败露时“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的果决,被李生赋诗羞辱时其亡魂的激烈抗争,其不甘命运播弄的追求精神如在目前。小说家还懂得赋予人物不断行动的原动力。李益“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张生乃“真好色”之人,柳毅自许“义夫”,王仙客苦恋无双“死而不夺”,等等,都引出一篇篇绝好的故事!而不是如焦湖庙祝毫无来由地向素昧平生的商人杨林张口就问“欲得好婚否”?小说家们还懂得采用交错发展的故事线索把人物置于感情与名利追求的矛盾之中,埋下情感冲突以至于悲剧的伏笔。李益自进士擢第,因俟试于天官而入京,以书判拔萃登科而入仕,再到与卢氏成婚,这一条情节线索是李益真正的人生轨迹;霍小玉仅仅存在于这些时间的缝隙里,因为李益的人生境况和选择而生喜,生悲,生怨,生恨,纽结成一条挣不脱的绳索,困住自己的人生,却拉扯不住李益必然离去的身与心。小说家还懂得克制叙述权限,只说自己能说的话,从而把叙述权力交给人物。《谢小娥传》就是因此而具有主、次叙述层次的小说。元和八年春,李公佐在建业瓦官寺阁中听到了隐藏着复仇信息的谜语,并了解到谢小娥的父亲、丈夫为强盗所杀的始末,当其时,引荐者是僧齐物,叙述者是谢小娥。元和十三年夏,李公佐在泗滨善义寺与已出家的谢小娥重逢,又从她的口中得知五载艰难复仇的首尾。小说的主叙述层次是李、谢的两度相逢,蒙难和复仇的经过作为次叙述层次,是李公佐对谢小娥所讲故事的转述。这是典型的叙述权力自限的表现,李公佐谨守不在场的事实,把叙述权力交给当事人,保证了叙述的合理性。在小说家就是上帝的时代,这是惊人的自觉意识。唐传奇作家在小说视角创新上的成就不止于此,《东城老父传》从一个曾经的宫廷宠儿命运盛衰的角度,写出一个鼎盛王朝一旦崩溃的必然性。一个黄口小儿以其善于豢养和训练斗鸡而得到玄宗宠幸,从而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和特权。这一事实的荒谬性,是对开、天时期架子还在而内囊尽破的深重隐忧的最好写照,其令人惊心动魄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一个斗鸡小儿在那个辉煌奢华的时代里发迹变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个时代还能或者应当长久吗?其实,《东城老父传》主题的深刻、技法的高超都应在《长恨传》之上,“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它不是对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注脚,恰恰相反,《伶官传序》更象是对它的总结。同样,安史叛军初平、玄肃二圣返正的胜利不能衬托帝王的英明神武,从柳氏被立功蕃将霸占专宠的命运,更能发现战火之中下层社会的苦难,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一小说化的历史记录,可以比肩杜甫的“三吏三别”。爱情总是热烈的,失恋与相思引发的情感尤其深沉动人,更适合作家们展示灿烂的才情,唐传奇在这方面的成功范例指不胜屈。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唐传奇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发现唐代社会的真实生活,一窥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传奇之妙,妙在有象。唐传奇发挥小说构造故事之能事,所立之“象”姿态万千,其意想之丰满、辞章之华美,使对一个故事及其人物的叙述变得亲切可感、曲折动人。故云虚实相间,唯虚为活。透过唐传奇对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心理的诗意再现,作家想要通过小说发现和表达的意义得以充分呈现,小说从此变得无比重要,成为探询和发现世界以及抚慰心灵的重要手段。
[1] 董乃斌.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二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J].文学遗产,1991(1):7-18.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3]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0.
[4]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5]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519.
[6]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下[M].韩希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475.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3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2966.
[8]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9]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53.
[10] 陈文新.“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J].文艺研究,2012(6):54-61.
[11] 杨剑影.唐传奇叙事略论[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0.
[12] 虞集.虞集全集[M].王颋,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371.
[13] 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0.
[14] 王充.论衡[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2.
[1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6]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7] 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39.
[18] 荀子[M].诸子集成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320。
[19] 韩非子[M].诸子集成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115。
[20] 王弼.周易略例[DB/OL].[2017-09-22].东京大学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本:明象.
[21]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5.
[22]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364.
[23] 杭辛斋.学易笔谈[M].长沙:岳麓书社,2010:141.
[24] 吴世尚.庄子解[M].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387.
[25] 朱熹.周易本义[M].苏勇,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49.
[26] 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0.
[27] 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12.
[28] 黄大宏.重写视角下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论[G]//东方丛刊:总第48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4-153.
[29] 黄大宏.重写: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93-98.
[30] 黄大宏.白行简《三梦记》的叙事语境及其题材重写史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