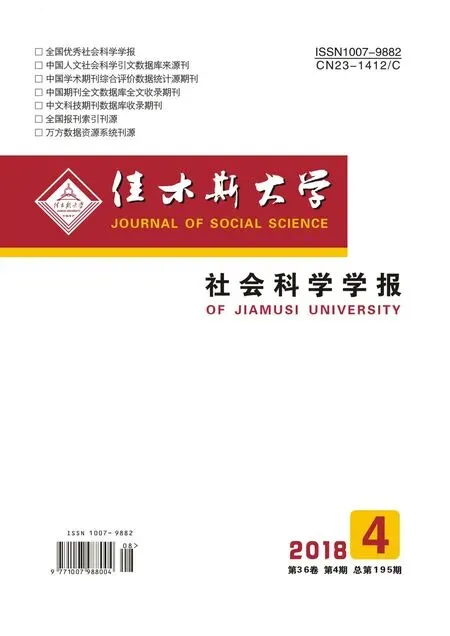涓生手记的叙事策略
——《伤逝》中的子君形象解读*
汪 瑶,乔 琛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伤逝》创作于1925年,是鲁迅唯一一篇以青年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后收入《彷徨》集中。同鲁迅其他小说一样,《伤逝》有着独特的创作背景和深厚的意蕴,但是,笔者以为,小说的解读不应偏离它的题材,就《伤逝》而言,更不应忽视小说爱情的另一方,即女主人公子君的形象。在以往的《伤逝》解读中,子君的形象往往是被置于涓生之次,并且少了点进步意义,比如“个性解放思想不彻底,没有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所以经不住封建势力的四面八方的进功”[1];再如“婚前的子君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具有很强的叛逆精神,她是无愧于具有新思想的时代叛逆者这一称号的……婚后的子君变得那么琐碎、庸碌、虚荣而且怯弱,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与婚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2]这些观点均建立在“涓生的手记”中男主人公涓生的叙事基础上,所以,涓生对子君形象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子君形象的相对被动性,使读者容易忽视一些细节,自然地跟着涓生的思路,误读子君。因而,从叙事学角度,重新解读涓生手记中的子君形象,有助于我们拨开叙事的迷雾,重新审视子君的形象。
一、涓生的叙事:从女神到女人的子君形象
《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全篇都是涓生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是一种内聚焦的叙述方式。读者透过涓生才得以看到整个故事的全貌,通过叙述人知道故事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以及最终结果,这些相对客观的因素。但同时作为叙述者的涓生,却可以对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事件经过进行组合与加工,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在这种叙述关系中,子君作为一个被描述对象,其实就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为一个失语者,这样涓生如何去叙述她,她都无力辩驳,因而文本中的子君形象是涓生塑造出来的,而非真实的子君。
既然是从涓生视角进行叙事,首先得明确涓生的身份,涓生是五四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接受过新式教育并且深深为之感染,他反对家庭专制、旧习惯,一心要冲破旧枷锁,追寻自己的理想。他与子君恋爱之后又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最后还是击垮了他们,最终他们分手一逝一伤。涓生说,自己写手记的目的是为了写下他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了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主题,涓生给了子君如下的形象定位:女神形象、女人形象,最终是难以同行的庸俗女人形象。
作为女神形象的子君,“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胳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3]372是个清秀可爱的女学生样子,就如“新叶”、“紫白的藤花”一样充满清新,而只要听到子君“皮鞋的高底尖触砖路的清响”都会使涓生“骤然生动起来”[3]372。在涓生对子君的初始印象里,子君是如此美好,带着涓生的期待,而在他们进一步接触后,子君面对涓生的侃侃而谈,“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3]372,她不仅善于倾听还能理解支持,涓生有着老师一样的成就感,子君就是他的好学生,他们之间有着共同话题和理想。而当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更使涓生深受震动,“而且说不出的狂喜”[3]374,他知道他苦苦找寻的人就是子君,“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3]374,此刻的子君是如此符合涓生的追求,她是有觉悟的,敢于反抗的,勇敢追求的。他们在一起之后,面对“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连涓生都“有些瑟缩”,[3]376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地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镜。”[3]376为了支持涓生,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3]376;同时还和父亲、叔叔闹开决裂。这样一个个性自由、勇敢无畏、独立解放的子君,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不就是女神吗?涓生对女神光环下的子君充满着崇拜感。他不能在叙述中对女神有一丝一毫的亵渎,因为这个子君是按他最初的理想蓝本而被叙述出来的,否定子君等于否定他最初的理想追求,他要尽可能地去维护这个形象,沉浸在那种依稀可见的女性解放的“曙色”里。
然而,他们走进了平凡的生活,涓生叙述中的子君,由他的崇拜对象而转变成家庭主妇的时候,她在涓生心目中的位置出现了倒置。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充斥在他们之间,在涓生看来子君“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3]377,养起了动物,涓生已经产生不满,她没有顺着他的喜好;接着是子君总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3]378,子君变得不思进取成日里围着家务转;还有为了小油鸡“和那小官太太”暗斗,变得斤斤计较,没有肚量;此刻的子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3]376日夜操劳着生活琐事的子君在涓生眼里是不美的,他对她的好感度逐渐下降,子君不打扮自己,全力倾注在家务上,不务正业没有追求,女神形象在逐渐消亡。而在涓生突然失业后,“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懦了。”不仅如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子君的功业,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3]381她把先前的追求都忘掉了,在涓生看来,子君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庸、俗气、虚荣、琐碎的主妇,和涓生概念里那些庸俗的女人没什么区别。
而此后因为涓生的失业,生活难以维系,不仅杀掉了油鸡还扔了叭儿狗阿随,矛盾进一步激化。子君“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3]383,在涓生看来子君是浅薄的,不理解也不相信他,“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3]384,这之后她“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3]385,涓生觉得苦恼,常常难以呼吸,在涓生看来,渐渐地子君脸上出现了怨色,“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3]386,子君是怯懦的、落后的、庸俗的,不能和他一起战斗了。涓生一直把子君当作被启蒙的对象,如今这个对象失掉了先前的无畏、勇气,令涓生产生与之分离的想法。他神化了最初子君勇敢的追求独立的形象,但是,他认为生活已经消磨了子君先前的追求,使她失掉了个性,没有了理想,“虽战士也难于战斗”[3]386。至此,涓生心中的女神形象彻底消解。
二、涓生的叙述策略:失语、有“过”的子君形象
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关系是特殊的,他们可以是叙述与被叙述的单纯的主客关系,也可以是亲属、朋友、恋人间的熟知关系,随着关系的不同,叙述的关系也会多样化,不同的关系会带来不同的叙述形式,呈现不同的表达效果。[4]小说《伤逝》作为叙述者的涓生和叙述对象的子君,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复杂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是在变化的。
涓生对于自己和子君关系的处理一直是模糊的,从全文看他们同居组建了小家庭,子君算是他的妻子,但是在涓生的叙述中始终没有明确这样的关系。他们更像是师生、朋友、恋人,特别是在老拔贡向涓生提起子君时说的是“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3]391,涓生给予子君的就是这样一个定位。而从涓生视角中的子君形象转变就可发现,涓生对于子君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对子君形象的塑造也是特别矛盾的,她可以是女神,可以是女人,最终只是一个不能一起战斗的同伴。由于涓生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加上他个人的情感观念,他的叙述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他可以在叙述中隐藏一些东西,亦可以在叙述中夸大一些东西。那么在涓生的手记里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
涓生强调的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3]372还有他心心念念的追寻“新的生路”。涓生的理想一直是空虚的,他开始以为找到子君组合成为家庭就是理想状态的实现,然而当现实的生活真正在他眼前展开时,他又表现的不知所措,他不认为是自己的原因,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子君。子君变了,被生活琐事困住,变得普通平庸再也没有先前的勇敢无畏,整天只会做家务,又不读书又不散步,跟不上自己的步伐。埋怨子君的不理解,不思进取。这样的子君怎么能和自己一同实现理想追求呢?
于是涓生想到了分离,他觉得自己一个人也能够“煽动翅子”,子君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何况她如此的浅薄。于是他否定了与子君的爱情,向子君提出了分手。当子君真正的离开,他仅是一点难过,更多的是轻松、舒展,想着还要追求所谓的理想。然而,现实的生活里,他的请托和书信都是没有回应的,生活已经把涓生逼到了墙角。说着要反封建的涓生,最后居然要通过问候一位世交来谋生路,这已是极大的讽刺。涓生理想早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他好像还在反复强调新的生路。然而新的生路一直是虚空的,连涓生自己都弄不清楚,还想着试图成为别人的引导者。
涓生一直是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说为子君,为自己,写下悔恨和悲哀,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对于子君的死他的确有歉疚,但更多的是为当初经历这些事情的自己而后悔和悲哀,结尾处他还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第一步却是要追悔子君和当时的自己,他要把过去一并抹杀,全部遗忘,这是对过去的否定。涓生的抗争彻底失败了,从此以后他要用遗忘和说谎作为前导。整篇手记说是在悼念子君,反而处处是在指责子君的落后与软弱,他在书写子君时,何尝不是在暴露自己,一个虚伪、懦弱、虚荣、自私的涓生躲在了手记之后,只是他藏得极其隐蔽,在子君和新的生路面前,读者甚至会同情他的无助和失败。作为大时代里的人,涓生很难摆脱困境,但是不能否认涓生对子君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涓生的手记更像是在为自己做着辩解,这是一个“无过之过”[5],涓生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要为自己进行辩解,所以涓生就必须时刻调整子君的形象,强调子君在变化,通过不断地否定子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被剥夺话语权的子君,在文中能说的话只有几句,比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3]379而且这些话都要为涓生的叙事服务。而当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消解之后,涓生描述的子君的语句更为简短,甚至是不完整的,总是断断续续的。子君为数不多的几句话里总是跟着省略号,子君似乎要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要么是点头或沉默的状态。涓生塑造了一个沉默,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子君形象,似乎子君的话语一多,就破坏了涓生的叙述目的,他需要控制话语来完善自己的叙事整体,维护自己的立场,引导读者往他希望的方向理解。正是因为涓生处在了一个主导的位置,他对于叙述对象子君的态度和感知的转变,会直接影响着读者的判断,读者唯一依靠的只有叙述者涓生的叙述,因而很容易导致误读。何况作为叙述者的涓生又有意设计了子君这样的形象,借此来逃避对自己过失的追究,以此获得读者的原谅和同情,子君形象就更容易被读者贴上标签成为大众接受的固定形象。
三、涓生叙述的外围:子君形象的另一面
由于叙述者涓生潜在的引导,读者无法更多的获得被叙述者子君的心理活动和感知。涓生根据自我需求对子君进行叙述,他的价值观、自主意识都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何况他和子君还存在着性别的差异,因而作为叙述者的他在对于子君的认知上是有局限的,容易产生人物感知的错位。文本的存在已经决定了无法更全面的还原一个真实的子君,但是由于涓生对子君复杂的情感,即便他非常主观地塑造子君形象,甚至剥夺子君的话语权,但在不经意的表述里也存在着一些真实,我们还是能够从其他方面发现子君形象的另一面。
抛开当时的大背景,单就人性角度出发,子君形象远比涓生有更多的闪光点。子君的可贵在于她的真、她的诚、她的勇。的确,子君无法摆脱限制她的社会背景,她在一个家长专制的家庭成长,接受的新式教育有限,有着传统的家庭观念(涓生何尝没有传统的家庭观念),甚至摆脱不了女性身份限制(涓生埋怨子君做家务时,为何不提出要主动分担,在涓生的理念里是否也潜意识默认,子君就该承担这些,惯有思维里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涓生身上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有着根深蒂固对待女性的态度,他想要的是个田螺姑娘,既能处理家务又能红袖添香。)但是在追求婚姻爱情自由的时候,她表现出的勇敢,大概也让涓生自愧不如吧。
再放回那个时代背景里,单就抗争这一点,子君已经取得了突破。涓生的手记写于1925年,和子君的故事发生在一年之前也就是1924年,1924年的中国社会的状况,孙中山讲演了三民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婚姻恋爱自由的思想是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作为当时的五四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自然也受到了思想的熏陶。所以在面对爱情时,她会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女性的独立意识已经觉醒了,她要强调她的自由,她的事情由她自己做主,她要摆脱家长专制,追求自已的恋爱与婚姻。因而子君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老东西”、“小东西”的偷窥,她是“目不斜视地骄傲”的走过去。与涓生找房子时,面对别人“探索、讥笑、猥琐、轻蔑的眼光,她也是大无畏的,全不关心,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涓生则显得有些“瑟缩”。作为共同追求爱情理想的青年来说,子君远比涓生表现的更为勇敢和纯粹。子君只是为了爱情,所以她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她比涓生更具有行动力,目的也更加明确,只是她没有料想到恋爱会以失败告终。
如果以爱情为切入点再回头阅读涓生关于子君的叙述,便会发现子君一直是陷入爱情的小女儿姿态,特别是面对涓生的时候,她那“微笑点头”、“孩子似的目光”、“脸上的绯红”都是为了涓生一个人,完全沉醉于爱情的甜蜜里。涓生在心里是特别清楚明了的,他看得见她的热烈、纯真、勇敢,只不过这些都是为了爱情。然而涓生所希冀的这些品格绝不能仅仅因为爱情,它们需要发挥更大的意义,于是涓生把这些不断地扩大,直至成为他的理想图景。
实际上,子君并没有顺着他的轨迹前行,子君维系的小家庭反而让涓生觉得被束缚了自由。所以他们之间不断地出现矛盾,涓生一直抱怨着子君难以沟通,但是他又封闭了子君的话语权,所有的罪责都推脱给了子君,他其实并不关注子君的真实想法,总是以自己的立场去揣测子君的想法。但是子君呢,实际上她还在尽可能的挽回爱情,“但是,……涓生,我觉得近来很有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3]386在仅存的只言片语里能感觉出她在试图与涓生交流,打破这种隔膜。可见面对爱情时,子君是为此付出过努力的,不像涓生只是一味的埋怨。子君把她的精力都倾注在爱情和家庭之中,她在很努力的维系着和涓生的关系。
子君在爱情的探索里显得特别笨拙,她想到的方式只是不断“温习”过去,一次次从回忆里找寄托或是投入在家庭生活中。她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着她的追求,甚至最后的离开都不是主动的,是她父亲接回去的,她不曾轻言放弃过,她远比涓生要更为虔诚和执着。(涓生貌似很有追求的样子,然而他的追求一直是空虚的,不如子君的坚定和专一。)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子君存在的缺点,她的言行与女性天生的感性和个性心理是分不开的,同时她还局限于她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涓生手记的叙事策略,也正反映着女性生存存在的困境,不仅制约于当时的观念,而且在文本表达上也被剥夺了话语权,拉开了读者与人物间的距离,无法更深入了解人物的真实想法,造成误解形成一些固有的观念。涓生对于子君的叙述是缺乏女性关怀的,他不曾真正了解过子君的内心,子君实际的形象要比涓生所叙述的形象更具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