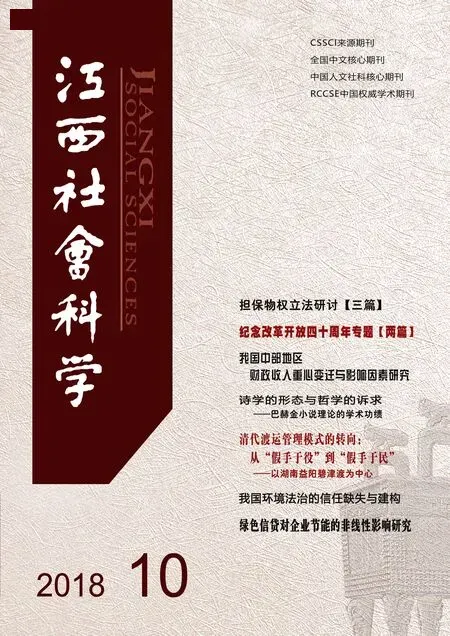卡尔维诺小说的后现代疏离性表征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他以新奇巧妙的小说创作著称于世,被学界冠以后现代小说家的称号。然而我们似乎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卡尔维诺的小说书写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声称其小说的书写手法与模式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手法。然而卡尔维诺的小说创作并非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应用,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疏离。
一、何谓后现代主义小说?
后现代主义概念十分驳杂,有一种众声喧哗之感。根据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伊哈布·哈桑的观点,他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既是历史性又是共时性的建构。他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重新梳理文学史,在历史上重新找到带有后现代主义气质的文学,尽管这种文学在以前的定位中并不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比如他从传统的作家及作品中看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并且重新在现代主义作家中读取这种信息。例如其对劳伦斯·斯特恩的重新发现。正如他所说的:“真实地讲,这种寻找先驱的行为意味着,我们已经在思想中确立了后现代主义模式,一种属于文化和想象的特殊类型,然后着手去‘重新发现’各种作者、各个时期与这一模式之间的类似之处。”[1](P29)
而另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理解是:后现代主义并非简单的是个时间概念,它既可以处在后现代主义阶段也可以不处于后现代主义阶段,它可以超出时代,在精神上提前发生。“后现代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的宣言的重写。”[2](P165)
琳达·哈琴在总结之前学者的观点后,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归结为矛盾现象。他认为矛盾就是后现代主义最鲜明的特征。而这个观点目前也成为一些主要的学者共同的认知。“一个后现代艺术家或作者处在一个哲人的位置上:他所写的文本、所产生的作品原则上不被先行建立的规则所支配,他们不能按照一种确定的意见、凭借将熟悉的范畴用在文本上而受到裁决。不如说那些规则与范畴是艺术作品本身正在寻找的。”[3](P15)
所以在这样的观点下,后现代主义小说应该是:“‘过去的在场’(即对过去的创作规则的批判性享有、既讽刺又对话、既批判又重复)、出自于一个它想颠覆的系统、异类并陈、编史的元虚构(既玩味于自我意识,又想联系世界)、既解构元叙事又成为元叙事的继续、在反对秩序中建立秩序、艺术与生活共谋、艺术门类之间的后现代越界、界限不明而又相互对抗、对多种话语的混合及相互拆台、虚构并且反虚构、超文学的争辩空间(理论与文学话语混杂于一处,面目难分)、合作又挑战、维护又破坏、既不遵守规则又自身在寻找一种规则。”[4](P3-4)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许可以小心地把后现代小说定义为是一种矛盾与悖谬的文学,或者说矛盾与悖谬是后现代小说的精神。
众所周知,卡尔维诺真正登上意大利文坛是1947年以游击战争为题材发表的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之后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祖先三部曲》和《宇宙奇趣》。1967年卡尔维诺移居巴黎后创作了一些别开生面的作品,比如 《看不见的城市》(1972)、《命运交叉的城堡》(1973)、《寒冬夜行人》(1979)。这些作品为卡尔维诺带来世界声誉的同时,也将后现代小说家的标签紧紧地套在了他的头上。此外,还有他后期更为成熟的作品《帕洛马尔》。上文所说的矛盾与悖谬的后现代小说特征是否确实存在于卡尔维诺的创作之中?同时元小说、作者的消失、排列与组合、晶面写作、叙事视角的多角度杂糅、互文等等这些在《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帕洛马尔》等作品中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后现代写作手法是否就是卡尔维诺作为一名后现代小说家的佐证?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二、写作技巧背后的宇宙观
卡尔维诺是运用写作技巧的大师。他在《看不见的城市》《寒冬夜行人》等作品中运用了元小说、作者的消失、排列与组合、晶面写作、叙事视角的多角度杂糅、互文等独特的叙事手法。然而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相似的叙事手法或技巧的背后,是作者独有的深层宇宙观。
(一)“元小说”与“作者的消失”是轻小说美学的体现
轻的核心精神是一种原子的偏斜运动。而正因为这种偏斜,世界才成为了可能,世界成为一种流动的存在,不再铁板一块。它代表着另一种维度与眼界,一种颠覆,一种反思,一种可能性。而卡尔维诺在这种精神下形成的元叙事及作者的消失,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旨意。元叙事代表着一种反思、另一种维度的小说特质,而作者的消失也并非像很多学者认为的完全受罗兰·巴特理论的影响。罗兰·巴特认为:“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其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体,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5](P300)作者不再是文本的中心与神话,他只是文本的“造访者”而非创造者,是“现代的抄写者,在其先辈哀婉的眼光里,由于他埋葬了作者,便不会再相信他的手慢得赶不上他的思想或他的激情,因此,也就不会再相信他在建立一种必然性规则时应该强化这种迟缓和无止境地加工其形式;相反,在他看来,他的手由于摆脱了任何声音和只被一种纯粹的誊写动作(而非表现动作)所引导,因此可以开拓一种无起因的领域——或者至少这种领域只有言语活动这种起因而无别的,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本身也在不停地怀疑任何起因”[5](P305)。卡尔维诺也提出对作者的消解,他曾在《寒冬夜行人》中做过奔腾的文字与打字机之间没有作者存在的美妙假设。但是卡尔维诺的这个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自我问题的深刻探讨,以及原子论影响基础之上的。他试图消除主客之间的隔阂,最终发现,人应该学会隐匿自我,聆听世界的声音。而卡尔维诺从其信奉的原子论中最终解读出让物发声,让自我消失恰恰是世界的解放。世界从自我的重压下得以舒展。所以卡尔维诺在小说创作中也尽量隐匿作者的主体性,让文字自己说话。所以我们会发现卡尔维诺与罗兰·巴特有关作者消失的提法虽然相似,但背后的原因完全不同,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很难认为卡尔维诺是作者之死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验证者。
(二)“多角度杂糅叙事”和“互文”是小说繁复美学的体现
繁复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提到的小说应该具有的特质中的最后一个。繁复隐含了卡尔维诺作为小说家对小说最大程度的肯定。他认为小说最终应该成为一种认识地图式的存在。因为在小说身上有一种罕见的杂糅的气质,它可以将所有门类领域以它独有的方式粘合起来。所以在此基础上卡尔维诺提出对小说可能空间的探讨。小说可以成为作为关系网的小说,从而达成对世界的模拟,对分裂的弥合;小说可以成为认识式的小说,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认知功能;小说可以成为思的小说,让思流淌在小说中。那么如何达成这样恢宏的小说构想,那一定是小说技巧的改变。卡尔维诺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多角度杂糅叙事和互文。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单一的维度,它是多维度展开,维度之间又是相互渗透,具有灵动性,而不是僵死与绝对的。而“繁复”中就包含了对世界多层次多维度的认识,这也是小说独有的智慧与认知方式。而卡尔维诺这样的写作手法同样并不是出于类似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本观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本观认为多角度杂糅叙事是对作者中心主义的一种瓦解,是对神话的瓦解,是对单纯逻辑因果叙事的一种反叛,是对形而上的抵牾。而互文则是在瓦解了文学没有确定所指之后,必然在不断指向别的文本中,意义延展的过程。文学是不及物的,它永远被锁闭在文本之中,符号的所指永远指向自身或别的文本,而别的文本继续这种游戏,一切都只是符号的狂欢,意义在指涉的断裂中消散。而卡尔维诺在运用这两个手法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自己所提出的繁复小说特质的一种呼应。卡尔维诺其实恰恰是把小说看成一种认知的方式。他说:“文学并不了解具体现实,只知道各个层面。是否有这样的一种现实,它的不同层面仅仅是某一个方面,或者仅仅只存在于这些层面上,而这些都不是文学所能决定的。文学勘探出这些层面,这种现实对文学来说更好认识,而也许其他的认知方式还无法了解这些层面。”[6](P52)所以繁复隐含了一种小说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多角度杂糅叙事与互文手法是对繁复特质的实践以及对小说独特认知方式的实践,而这与后现代主义文本观相去甚远。
(三)“排列组合”和“增殖”是小说精确美学的体现
卡尔维诺在其深层宇宙观的支持下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小说模式——晶体小说。晶体小说是卡尔维诺在轻、速度、精确、易见、繁复小说美学基础上提出的比较倾心的小说模式。晶体小说包含两个层面:小说内容与小说技巧。为什么会选择晶体,是因为卡尔维诺一直都有着对秩序的执着追寻。他认为在熵这个宇宙背景下,人必须捍卫秩序,哪怕这秩序只属于一个小范围,或者会转瞬即逝。但是还是要去追寻,不然熵就不再是我们的生存背景了。就像他说:“在整个图案中宇宙变成了一团热云,不可挽回地陷入熵的涡旋之中,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内部,却存在着一些有序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里趋向出现一种形式,似乎能够看出一种图案,一种透视图。文学创作即是这些区域之一,在其内部生命呈现出某种形式,具有一个有生命的机体。”[7](P377)在自然界,卡尔维诺发现了水晶。晶体拥有完美的晶面,有序的结构,完美的模式,充满秩序感。他符合卡尔维诺对秩序追寻的象征物,同时晶面的折光能力,以及能够自我生长,并按照几何图形周期重复性排列组合和无限延展,使得它能够充分包含精确美学的深层意蕴——无限小对无限大的包蕴,小世界对大世界的呼应。那么晶体小说如何在文本中呈现呢?卡尔维诺选择了排列组合与晶面写作。这种手法表面看极具现代意味,将文本意义离散化,对主体消解,对追寻意义的放弃、打乱线性讲述等特质,然而卡尔维诺的这种手法却是来自于晶体模式的启发。排列与组合以及增殖恰恰是精确美学的体现。精确美学中包含着人类试图通过无限小反观无限大的渴望。它不是在排列与组合中将意义离散,以游戏的方式解构文本,而是希冀通过有序去整合无序,通过规则去赋予秩序,从而得到意义,哪怕这个意义在混沌的背景中显得极为脆弱,那也是卡尔维诺所追寻的。同时卡尔维诺试图通过一个个片段的书写(类似于晶面),去创造一个形式上严整的小说。小说的每一个片段都独立成章,如同一个切面,并具有折光能力,相互影射,构成一个井然且恢宏的宇宙。每个晶面如同世界的不同切面,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入世界。晶面写作不是从一维去展开,它搭建的是一个多维的空间体系,在空间中蔓延,不是时间上的延续。晶体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模式,而每个晶面都是高度的浓缩,没有主次之分。这个严整的体系没有沉重之感,因为它是建立在片断书写之上的。每一个晶面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又与别的晶面相互呼应与折射,从而将世界的丰盈和盘托出,并努力划归在秩序的框架里。可见,在这样的写作方式背后更确切地说隐含了作者浓重的古典意识,以及试图对意义追寻的坚守。这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完全区别开来。
三、追寻意义的古典主义态度
小说是这个时代的产儿,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不仅仅是诸多体裁中的一个体裁。这是在早已形成和部分地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间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这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诞生和哺育的唯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8](P507)所以小说必然承接着贫瘠时代的种种呼告,这是它不可推脱的命运。那么小说到底是这个时代的再现,还是时代的救赎?
从时代与小说的关系看,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时代完全一致,它是时代的缩影。时代的混乱、无序完全呈现在它的形式之中。它沉沦在这种破碎、虚妄的形式之中。另一类在黑暗中坚守救赎之路,背负着虚妄,担当着破碎。尽管这样的划分的确也存在偏颇,它太以哲学话语背景去强行划分灵活多变的小说形式。然而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划分中将小说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划分中走出来。卢卡奇从“总体化”出发排斥表现主义而维护现实主义,摒弃先锋艺术。他痛批表现主义的剪接手法,说:“它能够迅速地把事实上完全不同的、零碎的、从联系中撕下的现实碎块令人惊奇地拼接在一起,其细节也可能闪烁着艳丽的光彩,然而从整体来看,却像污水泥潭一样。”[9](P18)他认为所谓的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先锋派最终会走向内容的越来越贫乏,只有注重生活与世界的整体性的现实主义小说才是与这个时代最契合的文学,它是对现代性的救赎。
然而现实主义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小说寻找新的与这个世界契合的方式。以新技巧而引人注目的后现代小说,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绝非只是游戏或沉迷于意义的碎片这么简单。就如同上文所划分的两种小说类型,它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划分。严肃的小说家在小说新形式的探讨中寻找着对这个世界的表达。也许正如本雅明对卡夫卡的推崇,在这个经验贫乏的世界,传统的小说书写加剧了经验的贫乏,而卡夫卡不同于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的小说书写才是这个贫瘠世界的意义所在,它是站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守望。
以卡夫卡为首的新型小说家,在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为世界提供意义,依然坚守着救赎之路,而不是躲藏在碎片背后。那么以这样的路径去分析卡尔维诺的小说依然行之有效。卡尔维诺小说书写的旅程正是寻求意义的旅程。
回顾卡尔维诺一生的创作生涯,从《通往蜘蛛巢的小径》到《帕洛马尔》,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主题一直贯穿始终——一个孤独者在茫茫宇宙对意义的追寻。在这条追寻之路中,卡尔维诺始终都没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始终都是意义的寻找者与看护者。从《通往蜘蛛巢的小径》的波恩开始,卡尔维诺经历着一次次的精神之旅,一次次寻找意义、看护意义的旅程。有人说他是典型的后现代小说家,因为他把小说书写变成一种游戏。卡尔维诺也承认游戏、好玩的确是小说的特质,然而这并不是他小说书写的全部。有一种担当始终浸染在他的小说中,就如同他对待迷宫的态度。他坦言世界如同迷宫:“一方面,当今需要一种面对复杂现实的态度,来抗拒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尽可能详细的一张迷宫的地图。另一方面,面对迷宫的迷惑,在迷宫中失去自我,代表了没有出口的人的真实境遇。”[10](P76)作为个体的我们不是沉溺于迷宫而是向迷宫开战。小说对卡尔维诺来说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拯救。一种引领人们走出迷宫的方式,一种对抗无序、混乱的方式,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诗人活着可以接受绝望感,甚至可以说,绝望感是一种确证,排除盲目、偏狭、迷拜和无意义的牺牲,赖此确立真实的信仰。但诗人不能生活在绝望之中,更不能因为绝望为诗人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地平线而抬高它的意义,正如不能因为痛苦或许是人接近上帝的真理,就把它说成是上帝的真理本身。如果不是在绝望的同时力图消除绝望感,在痛苦的同时祈求抹去痛苦的创痕,生命就没有出路。”[11](P73)既然卡尔维诺不能够沉沦在自己的书写里,那么必然要求在黑暗中肩负起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即便这种追问看似也带有虚妄的气质。诗人开始进行赋予这个世界意义的书写活动。世界即使没有意义,哪怕是诗人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也依然决绝地赋予世界以意义。他要给坚硬的世界以热度,给黑暗的世界以光明。书写不再是欢乐的游戏,而是痛苦的仪式。它一定是从这个世界诞生,但又试图超越这个母体的存在。在信仰的维度下最终也许会遭遇虚无,然而在这持久的遭遇中,信仰也许是从虚无的海洋中打捞意义的唯一途径。
卡尔维诺曾说如果我们不坚持赋形,那么无序便不再仅仅是我们生存的背景了。因为这种信仰,卡尔维诺进行小说书写,在小说的书写中继续探索,并保有信仰。信仰保证了意义的生发。即使最后在《帕洛马尔》中,当卡尔维诺发现为宇宙赋形与寻找模式之路受阻之后,也没有走向虚无主义。卡尔维诺的宇宙是沉默的。语言只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尝试。“语言就像一个孤岛,置身沉默无边的海洋中。从远方看去,它整个就像一块斑点,模糊不清;相对于沉默,语言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窃窃私语’”[12](P62)。而这个语言是人的语言,人用人的语言去追问意义,换来的不过是语言的喧哗,意义在这种喧哗中悄然丧失。然而人们又片刻不能离开语言,而作为小说家的卡尔维诺必须通过语言去完成他的叙述。这仿佛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卡尔维诺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应该沉溺于语言的无所指涉当中,而是开始背弃《寒冬夜行人》所开创的语言方向,使得语言不再过度彰显自己,而是收缩为简单而精准的特质。可以将语言从狂欢中拉入到精确的境地。
卡尔维诺尽管知道解释永远都牵扯着另外的解释,没有一劳永逸的解释,但他并没有因此将意义否定。他用沉默保住事物的意义。用沉默来让万事万物自己说话,他不去追寻所谓的事物背后那唯一的意义,而是学着与万物共处,倾听万物的声音,他不是一个挖掘者、探索者,而是一个倾听者、看护者。因为他深知任何一种形式的挖掘与探索都是意义的丧失过程,而唯有倾听与看护,才能看到事物的意义,即使不存在这种意义,这种沉默也是对事物的尊重。在这种沉默的尊重中,一切都不会变成儿戏,变成碎片的荒原,而是一个充满原子流动而欢快的世界。显然卡尔维诺还是原子论最为忠实的追随者而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四、结 语
事实上被外界所定义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仅仅只占卡尔维诺创作的很小一部分 (而这部分是否一定是在精神上与之契合还很难界定),卡尔维诺很大一部分作品是与后现代小说没有明显关系的,比如卡尔维诺前期小说创作,以及后期的创作。例如他早期的作品《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以及为他带来声誉的《祖先三部曲》的前两部。这些作品完全不能用后现代小说理论来界定。再比如《帕洛马尔》这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可以说是对各种小说技巧的摈弃,一种喧哗之后的平淡。尽管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书写,在他原有的小说理念上改写小说的尝试,然而这篇小说已经完全不是后现代小说能够将之完全定义的了。它对技巧的摈弃,平淡至极的叙述以及浓厚的思想诘问(对意义的追寻)让我们看到是一种小说新的开阔疆界。它跟卡尔维诺的小说理论形成一种完美的呼应。而事实上到底卡尔维诺的小说哪些更具意义,是《命运交叉的城堡》还是《祖先三部曲》,是《寒冬夜行人》还是《帕洛马尔》?卡尔维诺的小说不能独立拿出来评价,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改变我们对小说的已有的理解,他的伟大在于对小说边界的探寻。我们不能够将他的单个作品从他的整个作品脉络中抽出来看,唯有把他们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甚至他们的时间都不能轻易去变动。因为随着时间的流淌,卡尔维诺将小说独特的理解全部附着在他手中的作品上。所以卡尔维诺的每部小说都是作为其小说系统中的一个独特存在而具有意义,其美学价值必须是在其创作的历史延展中呈现的。他的全部小说也都是在这种天然联系的系统中才显示其全部的美学意义。所以仅就一两部小说(并且割裂其与其他小说之间的关联)得出的特征给卡尔维诺一生的创作做定位是很不负责的表现,它们是整体的,而不能够被切割。用后现代小说这个概念截取卡尔维诺创作中的一小段,或者以先入为主的后现代小说理论强行去套卡尔维诺的某些小说创作无疑是对卡尔维诺小说遗产的背叛。
卡尔维诺自己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可以完全界定他,他甚至说自己不知道何谓后现代:“需要说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在意大利文学批评辞典中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假定的前提下谈我的看法。我们意大利人有个概念,先锋派。例如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先锋派是一种运动,它们有自己的纲领、主张,以某种方式跟政治、革命联系。普鲁斯特是对文学形式进行了重大革新的人,但他禁锢于象牙之塔,因而很难说他是先锋派。”[13](P846-847)一直很推崇卡尔维诺创作的小说家巴斯说,在卡尔维诺身上拥有着既现代又传统的特点,同时“理想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应该多少超越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纯文学和政治文学、社团文学和垃圾文学之间的争执”[14](P203)。由此,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被冠以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家可能他身上愈是有着深厚的传统,与逆时代而动的倾向。事实上,被冠以后现代小说之父的博尔赫斯、用小说来思考的米兰·昆德拉、鬼才小说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等被外界认为是后现代小说家的作家身上及其作品中都不乏拥有相似的特质。后现代主义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似乎是对小说语言的凸显。然而这种凸显不只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独有的,它存在于小说萌生之初以及最为古典的和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于是我们会得到一种启示,即小说一直都处在一种传统当中,而这种传统远没有像米兰·昆德拉等人认为的那样,存在那么明显的断裂。而20世纪中后期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同样是在这样一种传统中润泽而生,它既不是对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背叛,也不是对小说最初样态的努力回归,而只是在这一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传统浪潮中继续前行。卡尔维诺的小说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