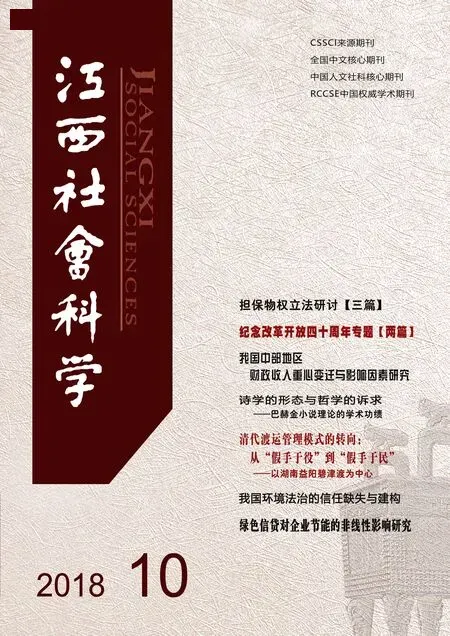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1921—1933)
弗理契(Фриче,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1870—1929)是苏联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艺术社会学家,他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他在十月革命前的主要著作有《西欧文学史纲》(1908)《西欧现代派主潮》(1909)等,20年代后转向艺术社会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普列汉诺夫与科学美学》(1922)、《西欧文学发达概论》(1922)、《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1925)、《艺术社会学》(1926)等。弗理契在美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发展了普列汉诺夫的“科学美学”。他不仅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考察文艺之发生、发展,还尝试建立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一定的艺术典型适应的美学科学系统,不过问题在于,他简化了普列汉诺夫所强调的文艺与经济、阶级的复杂关系,将文艺与经济基础、阶级直接相关联,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忽视了文学生成的内在审美机制以及艺术家的个性。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很长时间将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思想视为文艺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但在1928年至1930年、1932年到1936年间,苏联分两阶段展开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批判,前者是从学理上批判他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后者则将学术讨论扩大为政治斗争。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及其在苏联的命运影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
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给中国现代文论与文学以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弗理契一派的庸俗社会学思想。初步统计,自1921年起弗理契文艺著作在现代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有32篇(本)①,共30种,其中“艺术社会学”相关著作有19种,且《艺术社会学》这本书在当时被广泛传播与讨论;他本人在现代时期的学术地位通常与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并列②。不过,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现代中国的“辉煌”却与他在当代文论研究中的落寞形成对比。以往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维度:其一,对弗理契庸俗社会学思想的批判;③其二,讨论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同中国文学理论的关系;④其三,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⑤其四,从文献资料上对翻译到中国的弗理契著作进行梳理。⑥从现阶段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尽管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就“弗理契艺术社会学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却得出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另外,对弗理契文艺思想及相关阐释性文献整理还很不完备。那么,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命运到底如何?造成其命运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同一理论家在不同时间段对弗理契的态度是否不同?本文将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并尝试以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接受为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曲折路径。
一、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初识与完全接受
1921年,胡愈之翻译的弗理契《鲍尔希维克下的俄罗斯文学》开启了弗理契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不过这篇短文只是对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坛的介绍。耿济之在1924年翻译的《中产阶级胜利时代的法国文学》的《译者附志》中指出:“本篇是俄人佛利柴所著《西欧文学发达概论》(1922年出版)中的一章。佛氏此著系用‘经济史观’的眼光以研西欧文学,欲给读者证明‘社会的经济如何影响文学’。”[1]耿济之第一次将弗理契在研究欧洲文学时使用的新方法介绍到中国,但他没有明确提出“艺术社会学”这一概念。
在弗理契艺术学著作未大量翻译到中国以前,中国学界只是从留日进步青年处知道弗理契在1929年去世,且知道他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如汪馥泉的《俄国艺术学者傅理契之死》、冯乃超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文献》、冯雪峰的《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弗理契著)编者附记中都对此作了说明。不仅如此,冯雪峰还指出弗理契“走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美学’之创始者蒲力汗诺夫所指示了的路,并且将蒲力汗诺夫所奠的基础加以深崛发展;至謪理契底 《艺术社会学》,其间极鲜明地呈现着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底发展和向完成去的痕迹”。[2]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在1930年第1期的国内外文坛消息中介绍了弗理契之死,并将他定位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卫兵,打破了观念论的阵营。[3]
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思想很快被大量翻译到国内,有《艺术社会学的学术会议的报告》《艺术风格之社会学的实际》《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艺术之社会的意义》《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艺术社会学》《工业发达在现代欧洲文学上的反映》《欧洲文学发达史》《艺术作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几乎是当时弗理契在中国的全部译著。译者和阐释者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的选择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论转向现代文论过程中对“艺术社会学”的接受大背景相关,其二,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流行有关。1930年2月第1期的《文艺研究》在介绍陈雪帆译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的广告中说弗理契创立了新学说,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观点检讨古今东西的艺术作品。“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的书后广告中宣传刘呐鸥译《艺术社会学》时表达了相似的观点。[4]1930年,刘呐鸥译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被标上“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1)”的字样。刘呐鸥认为这本书“否定了以前的艺术论,补充了以唯物史观来研究艺术的霍山斯坦因,蒲力汗诺夫等新的艺术论”,“建立了科学的艺术社会学之建设的最初的基石”。[5](P367-368)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著的《艺术社会学》(刘呐鸥译)最终未被列入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据施蛰存回忆,当时左翼理论界认为该书有资产阶级观点。[6](P335)
尽管译者和批评家的思想倾向各异,接受弗理契文艺思想目的不同,但共同认可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中国学者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的最初认识是对日本弗理契评价的完全接受:弗理契是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完善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进入1930年以后,学界才有了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的独立反思。
二、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缺陷反思及其价值的相对肯定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批评界沉溺于对弗理契及其思想的缅怀、赞美与认同中,凌岱发表了《艺术社会学之是非:读弗理契著艺术社会学》一文。这篇文章是目前找到的较早从学理立场出发比较客观思考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凌岱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科学向煽动性、宣传性、实用性发展。弗理契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但不是共产党员,是以学者的姿态同情革命,这样他的艺术社会学缺少煽动性、宣传性,更有真理性。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学经济学之批判》是社会学向经济领域的发展,而弗理契把马克思主义引到艺术领域。弗理契并不是第一个将社会学的原则、方法、观点引用到艺术领域,或是将艺术主题归入社会学范畴的,但他是集大成者,他试图探讨艺术是如何与每个时代的经济形式相适合的,且每个经济形态形成了如何与之对应的典型和形式。[7]更为重要的是凌岱从三方面指出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问题:其一,把艺术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是不行的,这意味着将一切现象加以系统的、组织的、一般化考察,而艺术是不能加以一般化而概括的。不过,艺术可以加以社会学的研究。其二,弗理契讨论怎么样的艺术适合社会发达的每个时代,怎么样的社会产生怎么样的艺术,犯了削足适履的毛病。他将材料装入既定的公式内,选择适合自己说教的材料。其三,弗理契对艺术外表的形象没有涉及,而这恰好是艺术的唯一特色。艺术之外的形象与某个社会的形体和一定的经济组织关系,是不能用经济条件来解答的。
在凌岱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的批判后,是胡秋原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批判。胡秋原在《艺术社会学·译者序言》中肯定了弗理契用社会学-经济学的观点检讨古今艺术,将史的唯物论的新方法与新标准扩大了艺术研究,但他更大的贡献在于对弗理契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批判。当下研究对胡秋原的弗理契批判已经达成共识,这里不再赘述,但相关批评文献除了《艺术社会学·译者序言》之外,还有《佛理采之朴列汗诺夫论》[8]和《艺术作风与社会生活之关系》[9]两篇译文的注释。需要指出的是胡秋原的批判建立在对以藏原惟人为代表的日本普罗文学对弗理契的批判的反思上,而藏原惟人的观点又来自苏联对弗理契的第一次学术批判。⑦可见,这一时期学界不再盲目追随日本的观点,开始有自己的分析。
虽然胡秋原批评弗理契艺术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但他在后来左翼批评弗理契的观点时坚决为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作学术价值上的辩护。胡秋原接受了弗理契的观点,即不能以孟塞维克否认普列汉诺夫在文艺上的遗产,不能过于狭隘粗笨地理解文艺的阶级论,更不能机械地理解文艺之党派性。[10](P13-14)《关于文艺之阶级性》中胡秋原提出要像弗理契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阶级矛盾中理解文学;意识到弗理契提出的文艺上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的价值,但也提出不能将阶级性的反映看成简单的公式,忽略阶级性是种种复杂心理之错综的推动,受社会传统及他国阶级传统影响。[11]显然胡秋原认可弗理契以经济、阶级分析文艺,但受普列汉诺夫影响,提出要警惕弗理契的公式主义,即将文学和阶级直接对应。
胡秋原、凌岱都肯定了弗理契以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对古今中外的艺术考察,且同时指出其艺术社会学思想中存在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错误,凌岱还指出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中对美学要素的忽略。胡秋原并非只在理论上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进行辨析,还以在普列汉诺夫艺术思想审视下的弗理契思想批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无论是凌岱还是胡秋原,都展示出中国学者在理论输入过程中的独立思考,然而,紧迫的革命现实很快剥夺了文学研究中的独立思考。
三、苏联弗理契批判的引入与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批判的政治转向
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重新开始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且这次批判被纳入到对“拉普”的批判和清算中。“拉普”批判过彼列维尔泽夫-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且在文学上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反抗观念论、机械论,[12]但“拉普”是站在“为了普列汉诺夫的正统”的立场上的。苏联的这次批判主要以列宁的党派性观点批评普列汉诺夫的客观主义,并将普列汉诺夫艺术观点上的错误归于他孟什维克的错误政治立场,自然受普列汉诺夫影响的弗理契也被同等对待。由此,先前的学术讨论演化为政治批判。苏联的弗理契批判几乎同时影响了弗理契在中国进入1932年以来的命运。寒琪的《读者顾问:世界革命文学》[13]、鲁迅译的《苏联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现状》(上田进著)、适夷译的《伟大的第十五周年文学》(上田进著)⑧、黄芝威译的《普列汉诺夫批判》(IB著)都介绍了苏联的弗理契政治批判。
实际上,瞿秋白早在1932年1月完成的《论弗理契》一文已经批评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其一,弗理契无意中批评了普列汉诺夫的“五段论”忘掉了阶级性,并作出补充和修正,也认识到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孟什维克”,但在文艺批评时仍然无法脱离普列汉诺夫的客观主义,认为“党派的文艺批评”是主观的。其二,弗理契犯了“逻辑主义”错误,“想在一般真理的简单的逻辑的发展之中去找到对于具体问题的答复”,“没有充分的估计艺术发展的历史的具体性,而只想要找出最一般的发展规律。”[14]瞿秋白不仅从学理上指出弗理契的错误,更从党派的政治立场将弗理契的错误归于其政治上的孟什维克倾向。
瞿秋白的文章发表后,李华卿随即发表《为朴列寒诺夫而辩护——驳宋阳〈论弗理契〉之谬误》,从学理上回应瞿秋白,但他没有注意到瞿秋白弗理契批判的政治意图。这篇文章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李华卿认为,学术研究应当是“虚怀若谷”的,不能因政治问题而诋毁学术贡献。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批判表明中国对科学的艺术论的接受过了不加否定的萌芽与介绍阶段,而有了反思与批判,但瞿秋白的批判缺少独立的立场,只是对西欧和苏联的弗理契批评现状的全盘介绍。李华卿认为,其一,普列汉诺夫并不是仅从生物学和地理学讨论文艺。其二,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忘掉阶级,反而使阶级问题深入上层建筑各个部分;弗理契的补充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列汉诺夫的“五段论”不违背马克思根本原则,且具体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李华卿认为瞿秋白不懂人类是政治的动物,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中包含着阶级斗争。[15]李华卿有意识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辨析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瞿秋白的思想是可贵的,不过,从后来弗理契批判走向可知这篇文章对纠正弗理契的政治批判没起到很大作用。
左翼的弗理契批判具体体现在对胡秋原的批判当中,并且已超越艺术社会学上升到对弗理契整体思想评价。周扬指出胡秋原的口头上的阶级论错在受弗理契的影响,否认苏俄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否认列宁阶段的文学理论。[16]然而仅在半年前,周扬还在翻译《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时肯定了弗理契的马克思主义方法。[17]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周扬从肯定弗理契的艺术观点转向批判弗理契思想的孟什维克主义倾向。
冯雪峰将弗理契视为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且在1929到1931年间翻译4篇弗理契的文章。然而进入1932年,他转变了对弗理契的态度,体现在他对胡秋原的批判中,他认为胡秋原受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的影响,不心服列宁党的文学,不承认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中的孟什维克,不认识虚伪的客观主义的错误。[18]可是,冯雪峰在1946年再版的《现代欧洲的艺术》新加的《译者序记》中肯定了弗理契研究在学术上的价值,并指出其在1932年前后对苏联的弗理契批判一无所知。[19](P332)显然冯雪峰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
瞿秋白在学理上批评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本身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倾向,但受苏联弗理契批判影响,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批评家不仅以列宁主义的立场批判弗理契的孟什维克错误、艺术理论的客观主义,还批判受弗理契客观主义影响的胡秋原。与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的学术探讨相比,左翼更侧重对弗理契进行政治批判,这实际上是左翼政治路线的“列宁主义”转向在文学上的体现,但是左翼将文艺与阶级直接对应,反而犯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中的机械主义错误。
以上考察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1921年到1933年之间的接受。需要补充的是,虽然从1930年之初起左翼从政治立场出发将弗理契批判推向高潮,但学术界并没有就此接受左翼的“定论”,相反,一些批评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重新站到学术立场研究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本文并不将此列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文献相对分散,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影响较小。不过为了保障问题史脉络的清晰,弥补以往研究中对这部分文献的忽视,在此仍要列出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文献有李梨的《读“艺术社会学”后》(《中国新书月报》1933年第3卷第2、3期),向培良的《卢纳卡尔斯基论》(《矛盾月刊》1933年第1期)、《〈艺术社会学〉书评》(《青春周刊》1934年第3卷第4期)、《评茀理契〈艺术社会学〉》(《六艺(上海)》1936年创刊号),西望的《“弗理契批判”的批判》(《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6第25期),冯雪峰的《现代欧洲的艺术·译者序记》(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新艺术丛书社1946年)以及蔡仪的《茀理契的“艺术社会学”方法略论》(《文讯》1948年第9卷第2期)。这些文章或是参照西方文艺思潮,或是基于中国理论现实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重新做出评判。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理论走上更加丰富和自觉的阶段。此外,辛人在1935年又翻译了甘粕、石介的《弗理契主义批判》(《盍旦:文艺、哲学、历史、杂文月刊》1935年第1卷第2期),林焕平在1940年翻译了高冲阳造的《佛里契批判》(《民风》1940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主要是日本学界对弗理契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批判。
四、结 语
根据笔者的统计,1921—1933年间中国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接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初识阶段、学理反思阶段和政治批判阶段。整个20世纪20年代受日本左翼文学界的影响,中国将弗理契视作是世界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并以他的客观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来阐释新文学的发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苏联和日本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立场的进一步传入,批评界对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与激烈的政治批判,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界才较为自觉地思考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价值与不足。胡秋原等肯定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但更从学理上批评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中存在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问题,并警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左倾”趋势、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忽视;左翼除了从学理上批评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错误,更以列宁主义的“党派性”观点批评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客观主义文艺观的继承以及对主观的党派批评的拒绝,并将弗理契的错误归于他政治上的孟什维克主义倾向。不过,在文艺实践中,左翼却犯了与弗理契同样的将文艺与阶级斗争直接对应的错误,走上庸俗社会学的道路。庸俗社会学思想给中国文坛造成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恶劣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政治和学理两个层面得到彻底的清算。在左翼的弗理契政治批判之后,客观主义的弗理契被剔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范畴,左翼的批评理论进入列宁主义阶段。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显示了紧张的现实斗争对细致学术思考的褫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是一个不断选择、反思、批判、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当下的批评中要警惕庸俗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侵害。
注释:
①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21年到1933年间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但为了对弗理契艺术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有整体把握,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以1949年为界限。主要有:福栗许《鲍尔希维克下的俄罗斯文学》(愈之译,《东方杂志》1921年第16号)、佛利柴《中产阶级胜利时代的法国文学》(耿济之译,《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傅利采《绘画底马克思主义的考察》(朱静我译,《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5期)、Maksimow《艺术社会学的学术会议的报告》(冯乃超译,《思想月刊》1928年第3期)、V.茀理契《作为文艺批评家的伏洛夫司基》(画室译,昆仑出版社1929年5月)、傅利采 《社会主义的建设与现代俄国文学》(蒋光慈译,《文艺讲座》1930年第1册)、Friche《艺术家托尔斯泰》(冯乃超译,《文艺讲座》1930年第1册)、傅利采《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许幸之译,《文艺讲座》1930年第1册)、茀理契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洛生译,《新文艺》1930年第2卷第1期)、茀理契《艺术风格之社会学的实际》(洛生译,《新文艺》1930年第2卷第2期)、V.茀理契《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雪峰译,《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1、2期)、V.茀理契《巴黎公社底艺术政策》(雪峰译,《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3期)、V.茀理契 《现代欧洲的艺术》(雪峰译,大江书铺,1930年6月)、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天行译水沫书店,1930年10月)、V.M.Frice《工业发达在现代欧洲文学上的反映——摘译自:“欧洲文学发达史”》(林适文译,《文学生活》1931年第1期)、V.茀理契《毁灭·关于“新人”的故事》(隋洛文译,大江书铺,1931年9月)、佛理采《艺术社会学》(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V.Friche《论朴列汗诺夫之艺术论》(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弗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沈起予译,开明书店,1932年4月)、弗理契《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周起应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1期)、佛理采《精神分析学与艺术》(胡秋原译,《读书杂志》1932年第6期)、佛理采《朴列汗诺夫与艺术之辩证底发展问题》(胡秋原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9期)、弗理契 《二十世纪欧洲文学》(楼建南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2月)、Friche《艺术作风与社会生活之关系》(胡秋原译,《学艺》1933年第12卷第2号)、茀理契《三个美国人》(苏伍译,《春光》,1934年第1卷第1期)、弗里采《柴霍甫评传》(毛秋萍译,开明书店,1934年);佛里契《艺术底将来》(聂绀弩译,《中华月报》1934年第2卷第8期)、傅利弃《艺术家底悲剧》(白涛译,《译文》1935年第2卷第6期)、V.弗利契《人与文学·艺术家的悲剧》(胡风译,桂林南天出版社,1942年10月)、弗理契《艺术社会史概说》(刘汝醴译,《月刊》1946年第1卷第3期)、弗里采《都市的艺术:艺术社会史概说之二》(刘汝醴译,《月刊》1946年第1卷第4期)、弗里采《新的艺术——艺术社会史的概说之三》(刘汝醴译,《月刊》1946年第2卷第1期)。本文中Фриче,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 译为弗理契。对这些文献简单分析可知,其一,Фриче,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的中文译名写法多、不统一。其二,当时批评界对弗理契的关注经历了从他作家作品的研究到他的艺术理论,且重点在艺术社会学思想。其三,翻译者身份构成复杂。其四,发表的刊物及出版社性质也并非都与左翼有关。其五,对弗理契著作的译介在1930年左右达到高峰,主要集中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
②分别根据刘庆福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在中国之回顾》和《卢那察尔斯基文艺论著在中国》的统计,普列汉诺夫在现代中国有13种译文;卢那察尔斯基在现代中国有47种译文。在当下的研究中,多有学者探讨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影响,截至2018年3月,中国知网上“普列汉诺夫”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关文章有17条,“卢那察尔斯基”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关文章有2条,“弗理契”与“现代文学理论”的相关文章有3条。
③对弗里契庸俗社会学思想批判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周平远《20世纪30年代初胡秋原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林伟民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永明《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等。
④讨论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同中国文学理论关系的研究包括:温儒敏《从学科史考察早期几种独立形态的新文学史》(《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吴元迈《一个并非过去年代的故事——弗里契与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中文学术前沿》2012年第1期,杜吉刚、周平远《“左联”时期国际路线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南昌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
⑤涉及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对文学创作积极影响的成果有:刘婉明《前所未有的时代——唯物史观、新感觉派与左联文学批评》(《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王志松《刘呐鸥与“新兴文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等。
⑥对翻译到中国的弗理契著作进行梳理的成果有:赵宪章《二十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明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林精华《苏俄文化之于二十世纪中国何以如此有魅力》(《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7月号)、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汪介之《回望与陈思——苏俄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⑦参看(日)藏原惟人《艺术社会学底方法论——读弗里采底〈艺术社会学〉》(禹玄译《煤坑》1932年第20期)。
⑧参看(日)上田进《苏联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现状》(鲁迅译《文化月报》1932年第1卷第1期)、《伟大的第十五周年文学》(适夷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