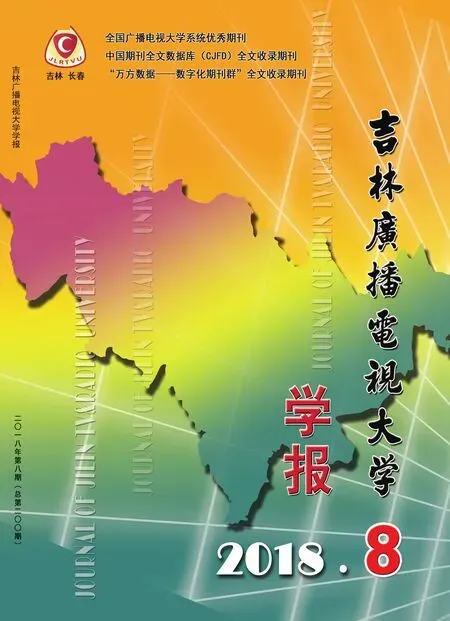报应观对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影响
吕 丽 郭庭宇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就不难发现报应观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中国宗教中一个深植的传统即是相信自然或神的报应。”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②”这样的观念已经从佛经中的言论转变为民俗谚语流传了近千年,其在如今依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儒家思想的直言劝谏不同,报应观从社会成员最为切身的实际利益③出发,以近乎“威逼利诱”的方法,维系着古代中国人的正义感,约束着他们的言行举止。这种在神话故事、宗教传说、公案、侠义小说、各类民间戏剧、文人笔记广泛流传的观念对民间的影响是其他文化因素所不能比拟的。④
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因为毫无疑问,报应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秉承儒家理性主义传统以及现代科学主义观点,以往学者往往忽视其对于民间法律意识的影响,或是以科学理性的立场揭露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实质,但对其本身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并没有深入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郝铁川在《中华法系研究》中用两章讨论传统中国“民众法律意识的鬼神化”问题,将其视为中华法系的一个根本特征。这样的观点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并且意料之中的以反对观点为主。⑤但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意识层面,宗教对传统法律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容忽视也不容否定。尤其是代表民众最朴素最实用宗教理念的报应观更是集中的反应和体现了民众对“罪与罚”⑥的认知,同时也影响着官员司法的价值取向。
一、引语:报应观与古代司法概说
我们在谈到报应的时候,通常会认为其是一种宗教观念,甚至有学者认为自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一直是中国宗教的基本信仰⑦。报应观的来源颇为复杂,其大体是由本土的传统儒家经典传统与道教信仰为基础,随着发展又受到外来佛教思想影响,形成了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报应观。早期儒家典籍中,《尚书·汤诰》记有“天道福善祸淫”之言,《诗经·大雅·抑》中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表述,《周易·辞》则有“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之语。可见在初民社会中,这信奉自然和神灵的报应思想就已经存在了。自汉代佛传入,“轮回”、“因果”的观点又再一次丰富了报应观,随着儒释道三教的渐次合流,宋明以来报应观也成为中国宗教当中最具广泛影响的思想信仰之一。
报应观虽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很少出现在法典中。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从“子不语怪力乱神”⑧开始,统治阶层就更加偏重于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而尽可能远离非理性因素。《论语·雍也》记孔子答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先进》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可见儒学对与报应,鬼神等非理性因素的看法,报应也自然无法作为官方法典的内容。而这种情况在明代发生了改变,《大明会典》有言:
“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怜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摇役,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煌,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答杖决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⑨”
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法典之中已经确立了鬼神报应的正当性,其在国家秩序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从材料中不难看出,报应甚至被上升为与法律相同的高度,弥补法律的不足,时刻劝诫世人要恪守律法。鬼神自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而在鬼神监督下恶行自然会遭到恶报。之所以报应在明代正式进入典章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小说等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报应思想的影响极度加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统治者的态度。
而报应观在传世文献上的表述繁多,形式五花八门,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明清、民国都不曾缺席。其集中突出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后人不断编写整理成集,以供劝人向善之用。这种报应故事的真实性自然无处可考,尤其其中鬼神报应等故事更是无迹可寻。但正如一般宗教的力量来自于人的信仰,报应故事也正因其扎实的群众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更是秉着“神道设教”的理念对报应思想的传播不断的推波助澜⑩,这更加使报应观不断的深入人心。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故事在对官员的劝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前志言之备矣。其中报应之显然而神速者惟居官为最葢。权势在手,喜怒由心。作善则千万人蒙其福,作恶则千万人罹其祸。祸福之及于人者远,故殃祥之报其身者更大。”⑪说的正是报应对官员影响甚至超过了一般的乡民百姓。
报应观在劝诫官员司法上的作用,甚至于矫枉过正,朱熹这样的大儒曾特意告诫司法官员,他认为“分之法家或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入罪以求神速报,夫使无罪者得不直,使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⑫。可见报应观对司法官员的影响之深。当然也能从朱熹的话中看到报应对司法的影响并非是正面的。但我们一谈起古代司法,总是避免不了谈到中国古代的重刑主义,而参考朱熹的话在结合古代的报应观我们或许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近些年大量的学者通过文献从新解读中国古代的传统司法,力图还原出古代司法的真实样态⑬,报应观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
在报应观下,官员的一切司法行为都暴露在鬼神的之下,古语本就有:“公门好修行”之说,又有“作善则千万人蒙其福,作恶则千万人罹其祸。祸福之及于人者远,故殃祥之报其身者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出于对自身的担忧不得不在司法过程中按照“善”的方法进行,虽然官员做出的某些传统主流司法价值所倡导的行为的原因是惧怕恶报或期待善报而不是发自内心,但基于人逐利性的思考,这样的结论往往更具有真实性,并且更具有说服力。如果我们认为官箴等儒家经典中的劝谏与古代司法的真实情况有所差异,那么报应观下的司法实践则由于其普适性使得其更加接近真实。
二、报应观与依法裁断
中国古代由于其独特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模式,既所谓“通达治体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皆到,虽老于吏事者,不能易也。”⑭司法官判决是否是依法的这个问题在学界产生非常广泛的讨论。而这个问题在报应的故事中答案则是很明确的。
首先报应故事中依法处死别人是不会遭受报应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御史某之伏法也,有问官白昼假寐,恍惚见之,惊问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赂鬻章奏,于法当诛,吾何冤?”“然则君将报我乎?曰:我死于法,安得报君?”⑮可见依法裁断是不会遭受报应的。
其次报应参照的标准是法律而非天理或者人情,亦或道德。哪怕真的有罪也要依据法律裁断,偏私或加重都会遭到报应。汪辉祖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归安有民妇与人私,而所私杀其夫者狱具”。县令以非同谋欲出之,而当时张希仲在座说“赵盾不讨贼为弒君,许世子不尝药为弒父,《春秋》有诛意之法,是不可纵也。”后来判处民妇死后,张希仲梦到民妇“一女子披发持剑搏膺而至”说“我无死法,尔何助之急也!”后来张希仲果然被报应死了。⑯可见报应观对与司法官的裁断依法由严格的要求。
最后,报应的故事构成了庞大的“阴司法律”实则为现实法律的摹写,这更使得司法官在裁判时要严格依照法律。唐朝王简易因打死一小怒被追入冥,冥司按问其“非理杀人之事”,最终报之以死。他说阴间以杀人罪为最重“,莫若杀人”⑰。可见人间最重的杀人行为在阴间也是如此。《夷坚甲志》卷三中记载过一则不孝子遭报故事,故事中的熊二不赡养父亲致其乞食,最后遭到雷劈的报应。可见报应观所要保护的法益与古代律文所要保护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妇,素无勃豁状。突狂电穿墉,如火光激射,雷楔贯心而入,洞左胁而出。其夫亦为雷焰播烧,背至民皆焦黑,气息仅属,久之乃苏,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背灯掩泪而己,何雷之误中耳‘未知律重主谋,幽冥一也。’”
材料中不难看出,骂父母的行为是要遭报应的,甚至危及生命,但从犯却可以减轻处罚免除死罪,《大清律例》规定:“凡骂祖父母、父母,及妻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但明清法律在《名例律》中同时规定了“共犯区分首从”“凡共犯罪者,以先造意者为首,依律断拟。随从者,减一等”,可见这与当时的法律规定是一致的。
三、报应观与无冤理念
前文提到的依法裁断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使民无冤则是一种实质正义的追求。一般通说认为,传统中国司法具有实质正义的目标指向,而在这种追求下,民众自然是极不愿见到冤屈的。自古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语。⑱南宋吴雨岩也曾说过“刑部以洗冤为急。民冤尚欲申,何况士大夫之冤”⑲。冤屈往往代表着司法官员做出了错误司法裁断,这种错误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后果,这种后果甚至包括生命。自汉代以来,人君往往因天降灾异,而下诏清理狱讼,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中同样多为记载,可见冤屈与自然报应的关系。瞿同祖先生在阐明报应观时曾谈到“刑狱杀人之中不免有冤枉不平之狱,其冤毒之气可以上达云霄,激起神的愤怒。”⑳
报应观的相关记载中除了劝谏的类似于官箴的一部分,另外很大一部分就是鬼神冤报。这种报应的主体自然是鬼神,这其中的鬼多数为案件中的死者,而神一般为阴间的判决者。在阳世所受的冤屈必然会在阴间被抚平,而制造冤屈的司法官则必然要遭受鬼神的报应,但是本应冤死之人在司法官的明察秋毫之下洗去冤屈,免去一死这种情况下司法官则会获得福报。明成祖在训诫大臣时说“:朕数戒尔等当存矜恤,须体朕意,必循至公,若违朕言,致无罪之人冤抑以死,是汝等杀之,不有阳责,必有阴谴矣。”㉑明宣宗曾对大臣说“:杀不辜者,纵免人责,难逃鬼诛,不可不慎。”㉒潘奎做府吏时,慈心济人。太守严厉,胥吏无敢启口。当时有土豪强暴,诬陷多人。贿赂多名衙役,没有人敢争辩。一日审录退堂,潘奎伏地为诸囚白冤,并数土豪不法事。太守又审讯查实,悉放诸囚,捕豪下狱。后来他的儿子做了尚书。㉓在马惠我的当官功过格中更有“出冤枉死罪一人。算百功。军罪算五十功。徒罪五年者算二十功。三年者算十五功。二年者算十功。一年者算五功减罪者减半算。”㉔功过自然是阴间之功过,事实上司法官查明真相本就是应然之事,在这类的报应故事里,未尝不能感受到对古代司法环境的一丝无奈,只要你能为百姓洗清冤屈就能获得福报,这实际上是报应观在司法正义上的妥协,就是用这样的故事鼓励着司法官对于无冤的追求。
而在司法官遭受死者冤报的这类故事中,死者与司法者的关系大致有两类,其一是司法者错断而冤杀死者,这种情况下死者的死是直接死于司法者之手,司法者必然要遭受报应。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幕客在任职期间,当地有妇人与人有私,她的丈夫被奸夫杀死了,她向衙门自首。但是幕客“恐主人罹失察处分,作访拿详报,拟妇凌迟。”使妇人冤死。最终见一金甲神率该妇人刃刺其腹部。㉕我们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自首减等之法,犯妇应其自首情节本不应死,但幕客因自身原因而让犯妇失去生命,这种行为必然招受报应。值得注意的是,报应观作用于刑官之上时,依照的是“王法”而非传统道德,在道德里是不存在自首减等这样的量刑情节的,而如果报应与法律没有交集,其产生作用也不应依照法律,这实际上是报应观作为一种法律文化深入人心的又一有力证明。另一种情况则是死者死于罪犯之手,而司法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为死者含冤昭雪这样司法者依然会受到报应。北宋祖翱做过大理寺丞,宋史上评价他“处身廉谨,以法律为己任”。但其同僚却梦到冤鬼向其诉枉:“昔日罪不至死,为通判祖寺承枉杀,抱怨数年矣。”其同僚不信,冤鬼说这不是出于祖公的本意,他本有怀疑却放任,最后以死罪定断。则应遭报应,后来果真在过河时船坏水入,惊惧暴亡。㉖冤鬼并非死于祖翱之手,仅仅是于其有关,而司法官的特殊身份使他依然要遭受报应,可见报应观在作用于司法官这个群体时要比其他人更加严苛,这也使司法官更加注意冤狱是否存在,进而促进了官员对于实质正义的追求之心。
四、报应观与慎刑理念
慎刑思想发端于上古三代时期,《尚书》中《舜典》有曰:“惟刑之恤哉”,至于西周时期“明德慎罚”出现,慎刑就已经成为了官方倡导的最普遍的法律思想。“慎刑”之意在中国古代司法领域里博大而精深,邱濬在《大学衍义补·慎刑宪》中认为“慎刑”思想要求司法官在断案时“必明以照之,震以威之”,以此明察秋毫,无罪、罪轻之人使其无冤情,有罪、罪重之人使其无所隐瞒,同时又要当行而行、当止则止,不可为明断是非而恣其威、滥用刑罚,要怀有至诚孚信之心。但正如汉时著名的狱吏路温书曾上书说:“天下之患,莫深于狱。捶挞之下,何求而不得?”㉗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基层司法中,这种慎刑观念贯彻到何种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报应观是如何影响慎刑观念的呢?事实上在古代刑罚与报应存在天然的关联性,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说“:古人认为灭异不是自生的自然现象,而是神灵对于人类行为不悦的反应。政事不修是致灾的原因,而政事中刑狱杀人最为不祥。”㉘这种关联广为人知则是由于史家的大力宣扬。《汉书》载于定国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他说“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子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孙永为御史大夫,嗣封传世云。㉙《后汉书》载虞经“为吏,案发平允,务存宽恤。每冬月,上其状,尝流涕随之。”曾说:“吾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后来他的孙子虞诩官至尚书、仆射,恭为上党太守。㉚这样的故事在史书比比皆是,而乱刑酷法恶报受惩者则更有甚者,同为《汉书》所载王温舒为河内太“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最后被定罪灭族,他自己也自杀了。㉛《旧唐书》中记载武则天时期的监察御史郭霸“尝推芳州刺史李思征,搒捶考禁,不胜而死。”㉜后来,郭霸看见李思征率领几十名骑兵到他家院中,对他说“:你冤枉陷害我,我现在来索取你的性命。”郭霸惊恐万状,拔出刀来自己剖开自己的腹部,不一会儿腹内全是像蛆咬过一样烂掉了。
在大量的史书宣传之下,报应观自然就与刑狱有了紧密的联系,直至后来,报应之说已经成为了劝诫慎刑的主要手段。明成祖在批刑部给事中的复奏死刑时曰“:大辟重法不可率易论决,万一失当,死者含冤无穷。大抵善恶报施,理所必有。”北宋初年礼部尚书晁迥撰文的碑铭《劝慎刑文》中就谈到“大旨惜乎生物之性焉!唯人万物之灵,厥理尤重。因而别撰《劝慎刑文》,明引善恶报应;亦冀流播,警悟当官之吏,疚心于刑,广树无疆福也。”㉝唐朝的崔仁师曾说:“治狱主仁恕。盖仁恕者,天地之心也。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天必福之矣。”㉞这样的观点被儒学理论更容易被司法官员接受,而广积阴德获得厚报的巨大诱惑与滥用刑罚而遭恶报的强烈对比又使官员在断狱之时无时无刻不警惕自身的行为,是否“释贫解冤、教愚扶弱,无乘危索骗、无因贿酷打、无知情故枉、无舞文乱法。”㉟因此报应观开始将慎刑理念在司法实践中推广。汪辉祖在《慎初报》中谈到“向尝闻乡会试场坐号之内,往往鬼物凭焉,余每欲出罪,必反复案情,设令死者于坐号相质,有词以对,始下笔办详,否则不敢草草动笔。二十余年来,可质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㊱”报应观使其二十年在断案之时,谨慎小心,切不敢错漏,看见其影响力之巨大。
五、报应观与息讼理念
众所周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代司法追求的是一种“无讼”的社会状态,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㊲即有诉讼发生,就是教化不行、民风浅薄的表现,作为牧民的职官,必须想方设法杜绝诉讼发生,史书上充满了对于能做到息讼的官吏一般以“循吏”进行评价,《后汉书》中对于黄霸,龚遂等循吏为人称颂的功绩之一就是“狱讼止息数年”、“狱讼衰止”㊳。这样的追求自然使得后世的报应中充满了对于官员息讼的鼓励以及对兴讼官员的惩罚。《居官日省录》中记载了如下几则相关的事例:
刘安民县吏也。持心平正。素为吏民所敬。民有讼不即诣县。必先诣刘陈曲直。决可否。然后行止。一县之讼。为之少息。其后二子皆相继登第。长子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朝议郎。直秘阁。
湖州蒋某。为人阴险。有刀笔才。凡非理之事。一经其饰说。便足夺人之听。平生所害不一人矣。后得一奇疾。发时辄㊴自咬其指。必鲜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伤风而死。
我们可以看出在上述两则故事中,因息讼、唆讼的不同事迹而招致的是泾渭分明的福祸之报。可见报应观对于诉讼的态度。同样在《居官日省录》中还引用了马惠我先生的当官功过格,正所谓“一笔而判生死。一言而召灾祥。一念而分寒暖。行一善。胜寻常人百千万亿善。行一恶。胜寻常人百千万亿恶。”㊵功过格则是对报应最直观的表达,其中对于刑狱之事的报应则表现的更加详细:
惩治讼师扛证。不得刁唆构衅。保人身家。一人算十功。人命立时亲验。假者坐诬。真者随即亲审。或故或误。为首为从。分别定罪。不致游移干连。一命算十功。
耐烦受诉。使两造各尽其情。一事算二功。
不嗔越诉。只平平照常理断。一事算五功。
听审不受嘱托。一事算一功。
重惩诬告。以息刁讼。一事算二功。㊶
功过格将行为所遭受的福报量化,通过上述材料,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报应观对于司法的具体影响,甚至可以量化对比。从功过的数量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息讼对于司法官的重要性。可见报应观对于司法官员的影响以及官员自身的追求。这种追求与儒家思想的倡导是一致,而且其影响力甚至远大于四书五经等经典对于官员的教化,官员为求福报,避免祸报则更加主动按照报应观所要求的的司法方式去进行裁断,这正是上层精英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本意。
六、报应与赦宥理念
赦宥最早是做一种司法原则出现的,《尚书·瞬典》中有“眚灾肆赦”记载,《易经·解卦》中有“雷雨作,君子以赦过宥罪”。《尚书·吕刑》中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根据胡东兴的考证,春秋时赦宥开始有了新的价值追求,是指帝王为获得善报,调和天气而采用的减刑或免罪等措施㊷。我们这里讨论的则是春秋以后的赦宥。
报应观实际上是各种赦宥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古代人认为天降灾害是因为有冤狱的存在《天志》中记载“曰:杀不辜者,天予不祥㊸”。“政事不修是致灾的原因,而政事中邢狱杀人最为不详。”㊹因此想要消除灾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赦宥。这样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人命关天”这个成语的典故:西汉东海有孝妇被冤杀,郡中枯旱三年。后来太守杀牛祭祀孝妇,果真天下大雨㊺。这样的故事在史书中屡见不鲜,甚至于皇帝诏书也频繁提及此事,后汉书记载永和十六年大汉,和帝亲自下诏“疑吏行惨刻,不宜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㊻。宋时“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㊼”,随着时间的发展,后来遇灾既赦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大清律例》中规定:“直省地方偶值雨泽愆期,应请治理刑狱者,除徒流等罪外,其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内情有可原者,该督抚一面酌量分别减免省释一面奏闻。㊽”
当然后来统治者为了寻求福报逐渐过多的赦宥罪犯引起部分儒家学者的不满,熙宁七年送神宗因为大旱想要大赦,但当年已经赦过两次,王安石以一年三赦是政事不修而非消弭灾祸而制止了神宗㊾。后晋的张允在其上书的《演赦论》里提到“窃观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则降德音而宥过,开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讼,一人有罪,一人无罪,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衔冤者何疏,见赦者何亲,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小民遇天灾则喜,皆劝为恶,曰:‘国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灾。’如此,则赦者教民为恶也。且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民也。或曰天降之灾,警诫人主,岂以滥舍有罪而能救其灾乎!㊿”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反驳赦宥有助于消弭灾祸,但影响并不大,后世帝王的赦宥也不见减少。
七、结语:报应观的社会意义
大量报应故事中体现的对于司法公正的追求,而在司法不公时官吏往往会遭到报应,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期盼。可想而知,如果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常态的话,那么自然做到公正的司法官也就没什么值得褒奖的了。
在诸多报应故事中,鬼神起到了法官的作用,而且,司法官员遇到难以侦破和裁决的疑难案件,也会祝祷鬼神。而断案公正,明察秋毫的法官则被神灵化。这种现象突出反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样态,前者反映出民众期待司法公正,希望有神明明察秋毫匡扶正义;后者则反映出在中国古代社会清官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两者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国古代司法是缺乏公正的。而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人世的冤屈不能被救赎,罪恶得不到惩罚,人们自然会把希望寄托于报应。换句话说,报应作为一种寄托,在精神上弥补了司法不公产生的问题。
正是由于司法不公的存在,报应观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多种审判模式,比如“阴司冥判”与“城隍审”。正如龙图公案中有“阳世糊涂,阴间如电”[51]的说法。因为阳间司法公正的缺失,民众只能寄希望于报应。清代朱阳湖于湖广为官,一日遇鬼,鬼生前为山东的强盗,说朱阳湖在做知县时受了他七千两藏银答应为其开脱,但定案时扔拟大辟,而今回来报仇。朱阳湖问恶鬼:“汝作盗应死,敢与法吏仇乎?”,鬼说:“某不敢仇法吏,敢仇脏吏。某以盗故杀人多,受冥司炮烙数十年,而目已成焦炭,每受刑必呼曰‘某当死,有许我不死者在也。县老爷受脏七千两,独不应加罪乎?’”。后果朱阳湖果然缢于床。[52]可见报应观的广为流传,与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期盼息息相关。
而它所体现出来的“正义”和“公道”的观念,形成了与世俗法律鲜明的对照,两者相互借鉴相互警惕,有效的维持了古代民众心中最基本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阴司法律”所表现出的意念,一方面是民众对于世俗法律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应然法律”的祈盼。鬼神作为另类的执法者,负责最终的制裁,冤屈终会昭雪,罪恶终将被惩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就如同笞杖徒流死保障法律可以实现,那么由自然和神灵掌管的报应则是道德可以实现的基石。因此,即使司法腐败,也不会使有信仰的民众失去对“正义”的信心。
但更为有趣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报应观中所追求的“应然法律”很大程度上与世俗法律是一致的,民众往往更多的关注于司法是否公正而很少质疑过法律的合理性。
这实际上表现出了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而这种一致在现今社会实际上很少见。[53]在这种高度一致的模式下,民众信仰报应与信仰法律在外在表现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守法也变成了关乎自身及子孙命运的天然义务。法律制度假托报应观之手无所不及地渗透到民众一切思维领域,作为一种法律文化报应观起到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报应观成为民众最主要的法律意识。民众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接的熟悉、无意识的接受法律规范,虔诚且尊敬这种观念以及其背后的道德理念,这种教化力量对民众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他方式。报应观也因此成为了统治者维持民间稳定的思想基础之一。
注 释:
①杨联升:《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升卷》,8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②见《缨络经·有行无行品》:“又问目连:‘何者是行报耶?’目连白佛言:‘随其缘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③通观《太平广记》33卷《报应》门,所得善报大多数为“福”、“禄”、“寿”以及后世的家族兴盛,而恶报多为不得善终以及家族衰败,从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群众的价值取向。
④刘兴汉认为:“从辑结成集的第一部早期话本《清平山堂话本》,到被称为我国最后一部话本小说集《跌春台》,可以说没有一部作品没有‘因果报应’的劝诫与说教。以至于它径直被称为‘因果报应之书’。”参见刘兴汉:《“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⑤参见陈林林:《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以及“萧伯符、李伟《中国古代民众法律意识是孺家化而非鬼神化——兼与郝铁川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
⑥霍存福老师指出:报应说在说明罪行、过错的时候,一概使用法律术语“罪”的概念。参见霍存福著:《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同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他认为报应观是一种关于罪与罚的叙事。
⑦参见[美]包筠雅著,杜正贞、张林译《: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⑧《论语·述尔》。
⑨[明]李东阳等敕撰《大明会典》。
⑩《大宁县志》卷八《重修城隆庙碑记》中是这样描述城煌庙的“古之善治民者,不以刑而以法。刑禁于已然,法禁于未然。刑之所禁易见,法之所禁难知此庙既成,凡远近游观者,莫不惊然畏,惕然惊,曰福善祸淫之不爽也如此'善者以劝,恶者以惩,举严刑峻罚之不能禁者,而为善去恶之念油然而生,此先王之神道设教意也。”由此不难看出官方对于报应观的推广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⑪[清]宋楚望《公门果报录》
⑫[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⑬可以参见吕丽:《中国传统的慎杀理念与死刑控制》,当代法学2016年第四期,37-47页;徐忠明《:案件、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⑭转引自[清]翁传照《:书生初见》,载《官箴书集成》。
⑮[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三《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⑯[清]汪辉祖:《续佐治药言》。
⑰《太平广记》卷一二四《报应二三》引《报应记》
⑱《尚书·大禹谟》。
⑲《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二《官吏门昭雪》。
⑳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㉑《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六
㉒《明宣宗实录》卷九十四
㉓前引②《法录计》。
㉔[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当官功过格。
㉕[清]汪辉祖《佐治药言》。
㉖[南宋]洪迈:《夷坚乙志》卷二十《祖寺承》。
㉗见《汉书·路温舒传》。
㉘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㉙[元]叶留:《为政善报事类》卷一引《汉书·于定国传》。
㉚[元]叶留:《为政善报事类》卷一引《后汉书》本传。
㉛《汉书·酷吏传》。
㉜《旧唐书·酷吏传》。
㉝冯卓慧:中国古代关于慎刑的两篇稀有法律文献——《劝慎刑文》(并序)及《慎刑箴》碑铭注译.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3):第116页。
㉞《图民录》卷二《治狱主仁恕》。
㉟[清]宋楚望《公门果报录》。
㊱[清]汪辉祖《佐治药言》。
㊲《论语颜渊》。
㊳《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
㊴[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考代书。
㊵[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当官功过格。
㊶[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当官功过格。
㊷参见胡东兴:《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五期,187-193页。
㊸参见《墨子》天志中第二十七
㊹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㊺《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
㊻《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㊿《宋史》卷一百九十九,《刑法志》。
㊽《大清律例》四,《名例》上“,常赦所不原”条乾隆八年例。
㊾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十二·赦宥
㊿同上
[51]《龙图公案》卷七《善恶罔报》。
[52][清]袁枚:《子不语》卷二四《盗鬼供状》。
[53]从“彭宇案”到“大学生掏鸟案”再到现如今的“雷洋案”等等一系列热点法律案例,突出体现了社会群众观点的复杂多样性,更深层次的体现了我国法律规范与法律文化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