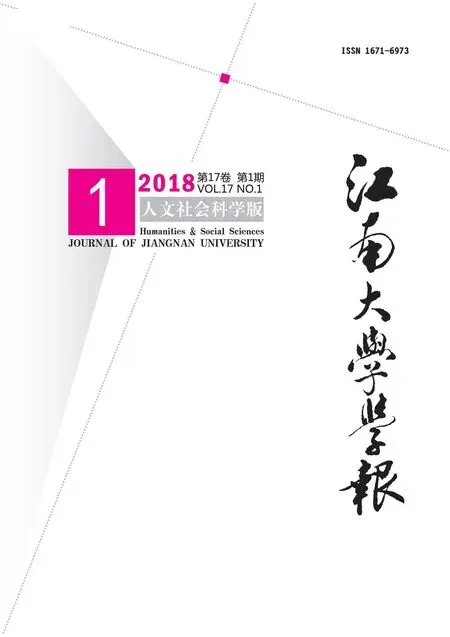空间美学的主体性特质及话语表征呈现
裴 萱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475001)
美学作为研究主体感性认识能力和审美活动的学科,以主体的感性经验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到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文学与艺术活动中美的规律问题、以及主体的审美直觉和经验问题。而空间美学的建构则是以“空间”作为美学研究的中介,并发掘空间元素、空间话语、空间理论等如何生成主体的审美经验,推动了美学话语的进一步延展。从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空间天然地构成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对空间的视知觉感知往往凸显出审美经验,而这构成空间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美学的研究内容而言,空间也构成当代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美学则以理论的高度来论证艺术活动中的空间特质,从而拓展美学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理论张力;从美学的表征呈现而言,空间话语和空间元素成为主体审美经验萌生的契机。在空间中,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距离”完成情感的往复回流,进而凸显了一条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再到主体心理空间的审美经验谱系。空间美学的生成具有三个层面的理论支撑。首先,是源自美学学科的本体属性。美学作为“感性之学”,其理论生成和知识场域的确立正是源自对主体感性认识能力的确证,直觉、形象、想象、身体、存在等都构成美学知识话语中的关键词汇。而与此同时,主体对空间的感知、空间的视知觉经验等等也构成感性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格森、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理论家纷纷从不同维度论证了空间如何参与进主体的感性活动之中。由此,便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论脉络:美学是系统研究主体的感性认知能力,主体的感性认知能力中包含了大量的空间元素,甚至空间直接构筑成为主体的感性经验。美学便天然地包含了空间理论、空间经验和空间话语。而空间美学则是将空间感性经验进行“剥离”与“独立”,通过“空间”确证自身的场域伦理,可以说是从空间维度生发出的美学,或者是以空间塑造全新的美学形态。其二,空间美学的生成还得益于美学史层面的自我延展。在现代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论美学发展的进程中,空间性逐步得以明晰。比如存在主义美学中对主体生存的空间“栖居”描绘、詹姆逊等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空间审美批判理论、精神分析美学中的“空间符号”以及新媒体语境下的视觉空间等等,这些都通过美学史谱系流变的纵向维度确证空间性的自我凸显。其三,空间美学的生成还得益于现代文学、艺术等文本实践的推动。空间与场景的变迁、主体精神空间的描绘、“第三空间”与“超空间”的存在感知等等,都成为介入文本艺术文本的有效策略。作家和形象主体面对空间的游移、放逐与回归,萌发出精神层面的审美感知,并将空间视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承载着主体情感的悲欢离合。以此为核心,文本中的空间审美经验进而辐射出差异性反思与美学批判的社会学意义。文本实践的空间形式、空间叙事、空间符号等不仅实现艺术自身形态的多元开放,更是也推动空间美学自身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伦理的实现。
一、空间美学的生成及主体性特质
审视空间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表征呈现等,其核心话语依然存在于主体对空间的感性认知能力之上,是主体以诗性智慧和审美直观来体验空间,并由此形成的、具有独特审美效应的美感。由此,空间美学的话语内涵便以空间的审美体验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延展和生发。在现代性视域中,空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理属性,而是经过主体的物质实践称为被“生产”出来的本体性空间。空间已经成为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印证着主体的生活和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表述的:人在空间中栖居,这也正是空间自身的“敞开”,主体与空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体验、共生共存的关系。“终有一死者在栖居之际根据他们在物和位置那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而且,只是因为终有一死者依其本质经受着诸空间,他们才能穿行于诸空间中。”[1]空间不仅具有建立在主体生产论和实践论基础上的崭新形态,更是成为与主体“共存”的关系结构,进一步凸显出具有审美意义层面的精神体验。现象学哲学认为,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构成“意向性”的指向关系,主体把自己的意识活动“投向”外物,在“悬置”理性、道德等干扰因素之后,以本质直观的形式完成了对外物的统摄。客观外物成为主体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和对象便构成了统一的意向性结构形式。在此其中,直觉、想象等构成“意向性”投射的关键词,而空间作为客体外物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创设出的实存样态,同样是作为主体意向投射的外在形式而出现的。空间就成为主体直觉和意向性投射的重要客体,并成为意义投射的关键。“意识在事物界里所面临的一切具体和真实的境地都充满着想象的成份,因为这些境地的呈现总是超溢出真实的。”[2]由此,空间美学话语得到诞生和延展,其核心正是建立在主体与空间“意向性”共存基础上的审美体验。这不仅导致空间维度“美感”的产生,也实现了空间美学话语内涵的拓展。英国美学家奥斯本在《鉴赏的艺术》中曾经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主体对空间和自然外物的审美体验,充满着浓厚的空间美学话语:“叶落时直接穿过树枝,然后在空间犹豫片刻,在最低层的树枝下飘了一会儿。在阳光的照射下,上面的露珠光彩熠熠,雾气蒙蒙。……你见证了叶落的全部过程。其中有某种东西使你惊奇得透不过气来。你周围的城镇、乡村和花园都已被忘却。时间陷入停顿状态。你的思路也被打断。树叶上的金红色泽,飘落时弧形的优美形式,充满了你的整个意识,充满了你的心灵。”[3]主体美感的产生也正是美学知识话语自身凸显的过程;而建立在空间感知基础上的审美体验,也正是推动了空间美学的成立。所谓审美体验,主要是立足于主体感性与心理层面的自由感、愉悦感。主体在面对自然外物、艺术作品和文学文本之时,产生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独特的、超越的以及无功利的情感状态,并且处于心醉神迷的高峰感官体验。在此状况中,主体彻底摆脱外在功利性和道德性活动的规训,完全进入审美的空间场景并且流连忘返、不可自拔。同时,对人类主体的生存价值、生命活动等也有了更加自由的感知。主体的美感和美学话语也就油然而生,从外在的感官认知到内在的情感共鸣、从心灵的审美沉浸到主体释放的自由超越,这些都可以纳入到审美体验的语境之中。“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他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了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4]在充满审美直观和审美想象的体验中,主体彻底摆脱了外在对象束缚,进而进入到属于自我的自由之境,获得精神愉悦和满足。“审美的快感可说简直没有对象。审美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价值的感觉。”[5]而在空间美学的视域中,主体对空间的审美体验构成其主导脉络和核心话语。宇宙时空的幽深奥妙、山川河流的悠远不息、日升月落的情感追忆、故人远游的空间思念、自我放逐的故土留恋等等,都成为主体对空间独特的审美体验,生发出全新的空间美学话语。同样,空间审美体验也大量表现在文学、艺术等经典文本中,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传达出浓郁的空间感悟和个体悲凉的孤独情怀,把作者登幽州台时的空间感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念天地之悠悠,独创然而泣下”也具有了“扶四海于一瞬”的人生超越之感。主体对于空间的审美体验也成为美感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空间美学便走出了一条“审美体验——空间视知觉——空间审美话语——空间美学”的理论谱系,成为美学知识话语的新形态。后现代地理学家戴维·哈维便认为美学和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能够相互影响和渗透,最终建立起关于特定空间的主体审美体验和美学意识形态思索。“在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里,对于地方、民族和传统,以及美学感受的神话的诉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蕴含了将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在一起的重要意义。”[6]与此同时,主体对空间的审美体验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审美自律的“精英式”与“波西米亚”窠臼中,而是延展到社会文化语境中所有涉及到空间元素的场域,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意识形态的浪潮。现代空间意识与与艺术的探索、后现代空间批判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拓展等等,都建构了全新的空间美学面貌。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和文化实践的视角出发,认为空间审美体验不仅构筑了主体的美感,更是也成为后现代表征意义的美学符号,从而参与进知识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之中。“各种表达空间的方式都包含着一切符号和含义、代码和知识,他们使得这些物质实践能被谈论和理解,无论是按照日常的常识,还是通过处理空间实践的学术上的学科。”[7]
美学作为研究主体感性认知能力的学科,其主要理论与话语内涵却源自对主体审美体验的确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感经验。从此视角而言,美的本质、美的形态、美的任务、美的对象等等,都无法脱离主体的审美体验。只有当主体沉浸在“共鸣”的审美体验之中,获得美感经验后,才能进一步从理论的角度对优美、壮美、自由、形式、荒诞等关键词范畴进行论证。康德曾经论证审美的自由,认为这是超越了道德判断和实践判断之上的情感自由,“它纯是静观的。……是主体把它摆在自己心面前而在它里面觉得有直接的满意的某种东西。”[8]黑格尔也认为审美具有推动主体自我超越、获得精神自由的功用,而这些依然源自于主体的个体化审美体验,“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加以利用。”[9]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感经验其实正是美的现象的源泉,也是所有美学相关现象衍伸的根据。审美对象也并非是立足于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而是主体与对象之间形成的审美关系。“没有超出美感经验之外的‘美’这样的东西存在,一切所谓‘美’都是在美感经验之中。”[10]空间美学的话语内涵则是将“空间”与“审美体验”融合,一方面,是对自然空间的审美意义、艺术文本的空间元素以及主体精神层面的意识空间进行考量,试图发掘曾经被美学史所忽略的审美空间话语;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破除美学超验的“形而上”质,试图在后现代多元空间语境中探究主体的空间存在话题。建立在主体感性视知觉和身体基础上的空间体验被进一步延展,被赋予情感体验的超越性含义。阿诺德·柏林特在《美学与环境》中曾经把主体的身体感官经验同空间进行结合,认为审美体验经过主体空间的塑造,成为一种“敞开”、“在场”的美感,是对美学话语的极大释放。“构想活生生的身体的空间性就是要认识到:场所和运动都是在与身体的关系中被感知的,被看做生活在这里或在那里。只有与身体的中心位置相关,才能洞察场所的价值和意义……上述现象学的诸多观念在研究空间时,都考虑到空间与身体和环境关系;它们不是把空间当作独立的数量,而是当作与感知着的身体有关连的意向性对象。”[11]空间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多元性特质不仅延展了主体进行感性直观和审美体验的广度,同时也给主体之间的审美经验交流带来更大的可能性,促使后现代公共空间美学形态的到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也通过对儿童心理学的考察得出,主体的身体和视知觉构成空间体验的初步特质,而随后则通过心理层面的“完形”作用与审美符号话语的延展,最终推动主体对空间的感受力[12]。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则通过对家庭中个别空间的考察。认为每一处细微的空间都具有特定的审美含义,比如所“柜子”就充满了家族历史神秘的想象和甜蜜的怀旧;“角落”则是代表了主体某种层面孤独的象征和交流的渴望,等等。不同的物质空间经过主体的审美体验,重新焕发出诗性的面貌,并进而具有了诸如美学层面孤独、荒诞、优美等形而上质。由此,巴什拉对空间进行了诗意的感叹:“巨大的空间,是存在的朋友。”[13]在空间美学的视域中,空间本体更加呈现出“微观论”和“经验论”的形态,并在与主体进行密切联系的同时不断拆解宏大叙事和本体论给美学的规训,进而成为以体验和交往为核心的动态话语。
二、空间美学的话语基点:身体空间体验
如果说主体的空间审美体验以及精神超越构成空间美学的研究对象,那么空间美学表征凸显方式则是身体空间感的确立和审美距离的呈现。主体对空间的审美体验源自于身体的视知觉,而美感的生成又是依托空间距离,由此,便梳理出一条从“身体”到“距离”的理论谱系。从“身体”的维度而言,美学全部的话语延展其实都是从“身体”这一“原点”产生的,身体对外在世界的感官体验、对自然空间的视知觉感触、对艺术文本的审美体验等等,都是源自于身体感官的摄取。空间与身体一直都构成了相互交融、密切结合的关系,空间也成为身体视知觉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不仅参与构建了主体感性认知能力和空间经验,更是成为美学话语延展的立足点。白先勇曾经表达了主体对遥远空间的诗性留恋,而这些首先是通过身体的感觉与知觉完成的,“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但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14]同样,作家尼·斯米尔诺夫也在《夏日的芬芳》中完成个体身体经验和外在自然空间的情感交流,审美的意义得以凸显,“对着阳台的窗户彻夜敞着,我觉得,我朦胧中不仅听到了夜莺的婉啭啼鸣,还有蔷薇和茉莉开放时的沙沙声响。一天夜里,掠过一阵雷雨。雨后花园里吹来如此丰厚的暖意和浓烈的芳香,几乎令人眩晕了。”[15]在这段描绘中,主体的听觉、触觉、味觉、视觉等身体知觉同时与外在空间发生作用,产生出令人迷醉的审美愉悦。身体作为美学关键元素的确立,实现了现代性工程以来主体性美学的延展,因为身体是作为主体的重要表征而出现的。将身体纳入美感和美学范畴中,也正是对感性、直觉和形象的确证,是对主体能够自由体验美的艺术并生发审美经验的肯定。
马克思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就曾经批判过历史上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美学与主体的感性活动息息相关,而主体感性活动的来源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从主体实践论出发,最终将审美同主体的感性经验进行结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6]马克思认为实践主体的确立需要身体主体的推动,而身体主体又是结合了感性和理性双重维度的辩证存在。艺术和审美正是存在于主体的感性审美活动中,“说人是肉体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7]。如果说马克思从实践论出发,认识到主体身体的历史性功能,那么唯意志论美学家尼采则进一步高扬了身体作为激进美学的对抗价值。尼采认为现代理性构成对主体的“总体化”压抑,而破除此种压抑的最佳手段便是审美的“身体”。审美不仅仅是纯粹直观的审美愉悦,更是身体感性的释放与狂欢,由此,身体、审美、感性就具有了同一性含义。现代主体的身体承载着审美现代性的渴求,成为对抗话语霸权的强大力量。“人们称之为陶醉的快乐状态,恰恰就是高度的权力感……时空感便了,可以鸟瞰无限的远方,就像可以感知一样;视野开阔,越过更大数量的时间和空间;器官敏感化了,以致可以感知极微笑的和瞬间即逝的现象,预卜、领会哪怕最微小的帮助和一切暗示。”[18]身体和感性就如同“酒神”的沉醉一样,彰显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和美感的社会力量。从此意义上讲,身体既成为审美的主体,同时也构成审美的客体与承载。
相比较于马克思的实践主体观、尼采的感性身体观,梅洛-庞蒂将视角更加集中于身体如何产生审美的内在机制层面,并且从心理学的视角详细论述视知觉和艺术之间的联系。梅洛-庞蒂认为,世界的外在存在是混沌的、混乱的,其中有自然界的实存空间、有艺术文本的审美蕴含、还有各种各样的审美符号和文化传统,而这是如何与主体发生关联的呢?身体、视知觉和空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主体通过身体的感官作用,对外在空间进行摄取和重塑,最终将其纳入到自身的心理空间中。“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纳在空间里。”[19]67与此同时,梅洛-庞蒂的身体空间理论并未就是止步,而是继续深入,并且具有美学层面的意义。在身体视知觉的空间体验中,除去感性直观的呈现,还有一种通过语言、符号和表达等建构出的独特空间样态。此种空间虽然也依靠视知觉,但是却传达出某种更为深层的空间内涵。比如通过语言所建构出来的诗性空间、通过色彩等建构出来的艺术绘画空间、通过造型设计所传达出的历史意蕴空间,等等。这些就需要在身体视知觉空间之内,进一步发掘出深层的空间意义序列,这被梅洛-庞蒂概括为“深度空间”。其实,“深度空间”也正是审美空间,是经过身体感知渗透之后形成的、具有美感体验的空间。“我称之为深度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或者是我参与到一个没有限制的存在中去,首先是一个超越了全部视点的空间存在中去。事物彼此侵越,因为它们一个外在于另一个。其证明是,通过注视一个画面,我能够看见其深度。”[19]57通过主体视知觉的摄入,空间具有了审美符号学层面的含义。形象、语言、文字、造型等等,都可以延展出一条从身体空间到审美空间的理论谱系。在主体视知觉空间的建构过程中,主体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空间的认知,同时也把自己身体的视知觉广泛“渗透”进外部空间,并采用模仿、表现等形式呈现出诗意的表达。比如画家在绘画中,往往也是把自己的“视域”和画面中的“视域”进行融合,将外在的现实空间转换成为绘画的形象空间,然后接受主体再对艺术品进行体验和摄取。在此进程中,空间是流动的、融合的,并与视知觉空间广泛交织在一起。在“深度空间”的不断融合、交融流动中,空间审美体验和艺术美感得以逐步清晰,美学话语也逐步得以凸显。这些恰恰是空间美学形态的重要基石。我们认为,梅洛-庞蒂的“深度空间”不仅延展了主体性美学的脉络,凸显出后现代非理性美学的强大话语包容力;更是成为空间美学形态产生的理论原点,是空间美学得以生成的合法性论据。空间美学紧紧依托于“身体”、“感性”的美学本体,并以视知觉空间为基础由此向外辐射延展。经过感性身体的经验和视知觉的体察,空间美学的深层意义找到了表征呈现的路径。“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绘画,一支乐曲,都是个体,也就是人们不能区分其中的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其意义只有通过一种直接联系才能被理解、在向四周传播其意义时不能离开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存在。”[20]比如塞尚在绘画中,就在“自然”和“自我”之间找到了和谐共存的路径。一方面塞尚承接了古典绘画空间透视的技巧,实现了视知觉空间的释放;另一方面,也在绘画是融汇了自身独特的印象式感知与理解,从而构筑了新的“深度空间”。画面结构的轻微差异、自然空间与知觉空间的巧妙融合、多层面空间体验的生成等等,这些都促使塞尚在绘画中达到新的和谐。可见,从身体对空间的视知觉感受,再到“深度空间”的审美体验,“身体”构成了空间美学的基本立足点,也成为阐释众多审美空间文本和文化现象的良好切入点。
三、空间美学的话语延展:“距离”与审美经验生成
从空间“距离”的角度而言,审美经验的生成也依托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主体视知觉空间和艺术文本空间之间的“距离”。正是因为有了空间距离,主体才能够“跳出”意识形态规训和功利化视角,以纯粹直观的方式来审视审美对象,进而获得美感和审美自由。如果说空间美学是以“身体”为美学话语 “原点”的话,那么“距离”则直接推动了审美经验的生成。主体的身体正是在对外在空间与艺术进行有距离的观审,才得以超越世俗价值伦理的规训,进而沉浸到“深度空间”的审美体验中。而此种空间距离正是蕴含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互动,本身就已经成为空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王国维曾经在论述“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时,就彰显出此种情感往复回流的空间距离:“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空间距离一方面推动了主体审美经验的生成,促使主体以“陌生化”的视角来进行审美直观;另一方面自身也形成了一个贯穿时空的情感场域和诗性空间,在此空间中,山川可以含媚、花鸟可以含笑。从郭熙在画论中的空间表达:“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漂漂渺渺”[21];再到王夫之在诗论中的空间体悟:“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蜜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22],这些都营造了充满美感和自由感的空间距离。在主体身体以视知觉空间向客观外物进行观审之时,其本身正是一个审美创造和审美构思的过程;与此同时,主体和艺术文本之间、创造者和欣赏者之间都会产生相应的审美关系。而在此“互为主体”的审美活动进程中,创造主体和欣赏主体总是试图想找到最能够唤起自身情感共鸣的艺术经验,这种艺术经验既能够契合主体已有的生活习惯、知识积累以及文化心理等“期待视野”;同时又能够给主体带来某种新奇感,带来超越于日常生活习惯之上的另类审美体验。由此我们来审视艺术作品中的空间元素,一方面其原型往往是来自主体熟悉的自然场景和生活空间,能够引发主体的共鸣;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某种距离、变形、夸张、延宕等方式来重新“唤起”主体的审美快感。比如梵高在《向日葵》《星空》等画作中就展现了一系列别样的审美空间,它们不仅是主体熟悉空间符号,能够通过视知觉进行把握;同时再次通过线条、色彩、结构、形状等元素的夸张与变形,凸显出独特的深度艺术空间。而主体和艺术文本之间以及主体内在的心理世界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场域,该场域正是一个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审美空间。朱光潜曾经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主体审美经验是如何生成并拓展的。直觉的观审构成审美经验生成的第一个维度,而有距离的观审则实现了审美心理层面的自足,成为审美经验拓展的第二个维度。“创造和欣赏是否成功,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空间距离不仅体现在艺术创造和欣赏之间,同样,心理距离也能促使审美经验的生成。“艺术家的剪裁以外,空间和时间也是‘距离’的两个要素。愈古愈远的东西愈易引起美感。”[23]与朱光潜的理论阐释相比,宗白华则把空间距离与主体移情进行诗性的联系,理论中更加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风貌,从而建构出一个从主体到客体、从“实在”到“虚空”的美学话语表达。“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上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干,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24]可见,空间距离便如同在艺术世界、现实世界、主体世界和超验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主体形成新的审美心态,也提供给主体一个发现美、体验美的契机。
与此同时,空间距离也不仅能够以审美直观的方式推动审美经验的生成,更是以“陌生化”和“间离”的视角完成美学更高层面的意识形态反思。陌生化和间离效果作为美学理论中的关键内涵,分别属于形式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畴,但是其最终理论指向都是美学理论的反思性价值,其表征形式依然是空间感的体察。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论证了文本中人物形象、故事设置、形象描绘、文学语言等方面的陌生化效果,认为整个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就在于“拉长”审美感知的空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觉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对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25]而间离理论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布莱希特,他试图通过戏剧中演员表演和观众欣赏进行交流,来拆解到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审美沉浸”与“审美幻觉”,从而实现理性的、思考的和批判的美学话语。间离效果的本质依然是要在审美高峰体验和主体反思能力之间找到空间,实现美学的社会学意义和历史批判意识。欣赏主体只有与艺术文本保持适当空间距离,破除沉浸与共鸣的“神话”,才能够最大限度激发主体的审美意识形态反思力量。既然主体和艺术之间要保持空间距离,那么艺术形式的自我变革就逐步凸显出来,这也正是形式主义美学的理论旨归。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等正是立足于形式自身的陌生化力量和深度空间的体验,完成了艺术从“形式”到“意蕴”的深层美学观念。“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和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它就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共性。”[26]罗杰·弗莱则通过对后期印象派绘画的分析,并且对贝尔理论的吸收,提出了全新的“双重生活”美学论。他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类,能够通过审美想象产生出超越于现实生活的“另类空间”,在艺审美想象中能够产生更加清晰的审美知觉与更加自由的情感体验。而这些都需要与日常现实生活保持距离。所以,通过有空间距离的观审,主体能够对艺术文本进行有选择的体验,并且能够保持适度的理性思维对其进行反思,进而实现“陶冶”与“净化”的“卡塔西斯”效应。正如在对悲剧和电影进行鉴赏的过程中,主体暂时生活在一个密闭的审美空间内部并且沉浸于影像的快感。而与此同时,也必须促使主体时刻注意到自我和舞台上的距离空间,破除舞台上的神秘幻象,以反思和理性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审美活动。最终实现从情感共鸣到社会人生反思的升华。“我们离开剧场,内心充满哀痛,但是一切琐事俗念都已丢在脑后,感情得到净化,进而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27]通过空间距离,主体能够剥离悲剧中痛苦、怜悯、恐惧等情绪,实现具有崇高特质的悲悯感和超越感,使自身的审美体验不断得以净化。此种距离空间不仅能够实现美学意识形态的反思,更能够在后现代社会中延续“艺术自律”的理论脉络,保持相对独立的“审美伦理空间”与资本主义异化空间进行对抗。齐美尔希望现代生存的主体能够与外在“物化”的世界保持距离,以艺术和美学的力量对主体进行“救赎”。由此,空间美学又被赋予了“价值论”层面的含义,它不仅实现主体感性对空间的诗意体验,更是成为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推动艺术和美学自律的关键性存在,空间距离成为美学反思社会历史、对抗异化霸权的重要元素。“只有在距离基础上他才可能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审美观照,此外通过距离还可以产生那种宁静的哀伤,那种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浪漫的自然感觉的特征。”[28]可见,空间美学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延续,也将深刻而持久地在美学领域中凸显自身的力量。
从“身体”的空间审美经验,到“距离”的空间审美反思,凸显出空间美学的表征呈现形态。空间美学作为众多美学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以空间的视角、空间的体验、空间的视知觉以及空间的文化批判为基本立足点,审视主体的感性审美能力和艺术文本的美学话语呈现。可以说,空间美学诞生于主体身体对空间的视知觉体验,以及希望通过空间来实现生命自由的希冀;延展于主体与客观世界、艺术文本、自我心灵以及他者空间的“距离”体察之中,最大限度改变了传统历时性、本体性的美学话语模式,凸显出并置化和价值论的美学新样态。与此同时,空间美学的生成也契合了后现代语境中意义播撒、知识互涉以及主体间性的文化景观,并以“游牧”、“图绘”、“栖居”、“流动”等特质实现美学话语的进一步释放。而这些都是以主体身体的空间审美经验为基础的,正如约瑟夫·弗兰克对艺术绘画空间的诗性描绘:“叙述的时间流被中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实践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联系游离叙述过程之外而被并置。”[29]
[1] 海德格尔.筑·居·思[M]//孙周兴编选.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200.
[2] 萨特.想象的事物[M]//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02.
[3] 奥斯本.鉴赏的艺术[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5.
[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8.
[5] 里普斯.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M]//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401.
[6] 戴维·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00.
[7]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5-276.
[8] 约翰·华特生.康德哲学讲解[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55.
[9]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7.
[10] 牛宏宝.美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0.
[11] 阿诺德·柏林特.美学与环境[M].程相占,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1.
[12] 罗伯特·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的视角[M].黄春芳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7-169.
[13]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27.
[14] 温奉桥.最后的贵族——白先勇先生印象:下 [EB/OL].[2017-05-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0c883010008by.html
[15] 陈湘.自然美景随笔[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35-36.
[1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8.
[18] 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4.
[19] 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7.
[20]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0.
[21]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M]//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71.
[22]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M]//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十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736.
[23]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4.
[24]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4.
[25]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M]//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6.
[26] 克莱夫·贝尔.艺术[M].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
[27] 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63.
[28] 西美尔.货币哲学[M]. 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89.
[29] 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