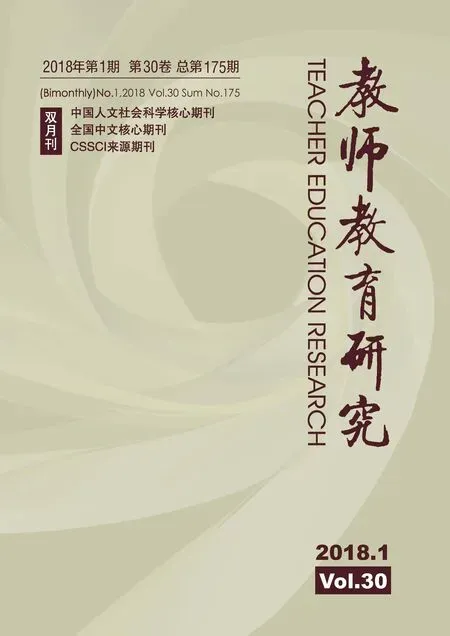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习得及运用路径
沈晓燕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国家课程与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的疏离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表现落后。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课堂教学中强调现代教学的共性较多,关注文化差异性较少,这是导致民族地区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然而,少数民族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落后的原因缺乏准确的归因。[2]事实上,少数民族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疏于运用地方性知识,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经验世界与国家课程之间的断裂,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与自我认同。例如,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存在偏差、母语系统向汉语系统转换复杂等问题导致他们在回答教师课堂提问时遭遇困境。[3]
笔者在参与乡村教师研究等课题调研过程中,访谈或接触了广西、西藏、云南等地的乡村少数民族教师。本文将结合笔者的调研数据和现有文献资料,以文化阐释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以下问题:乡村少数民族教师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实践主体,他们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何在?他们如何在学术场域和本土场域中习得地方性知识?他们运用地方性知识的路径有哪些?
一、概念内涵
1983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首次由美国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一书中提出,[4]对人类学、社会学、科技哲学、生态学等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本土知识抑或乡土知识的内涵作了不同角度的界定,对于“地方性知识”概念本身的内涵亦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抽象的知识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套带有地方性特征的知识系统。[5]本研究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内涵理解采用后一种观点,将其看作是一套以地方性特征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或意义系统,这种知识体系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知识,而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和发展中形成,并共同认可的,与地方环境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包括传统民俗、历史文化、生产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知识。[6]“地方性知识”作为阐释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对其的解读离不开格尔茨的文化阐释理论。[7]
二、乡村少数民族教师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符号(symbol)”是文化阐释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承载意义的系统。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符码(code)”,后者指“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特殊的符号体系,包括关于世界的信息,及如何解释、处理这些信息”。[8]巴希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符码理论(code theory)认为,出生在不同阶级背景家庭的孩子的学业成就存在着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家庭中使用语言方式上的差别:工人阶级家庭的语言是适用于实际经验沟通的有限符码(restricted code),中产阶级家庭的语言是更容易表达抽象观念的精密符码(elaborated code)。[9]将此推及至乡村少数民族家庭之中,不仅存在着语言符码限制带来的文化再生产,亦可见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阐释差异所致的儿童学习处境不利。因而,乡村少数民族教师拥有地方性知识,理解地方化的意义系统,是帮助当地学生跨越有限符码与精密符码、本土意义系统与主流意义系统的关键所在,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改善、少数民族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少数民族学生回归本社区皆有重要价值。
(一)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效果
学生学业表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方法、师生关系等等的差异都会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分化上。教育社会学家发现,文化因素也是决定学生课业成绩的重要变量:[10]既然学生们的认知和理解方式皆受文化背景的形塑,那么当学校教育脱离了学生的文化背景时,[11]学生的学习则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当前,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文化并未很好地体现在国家课程中,如果乡村少数民族教师不认同和掌握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和文化,那么势必在课堂上将很少提及和运用,少数民族学生觉得掌握自身民族的知识和文化并不能在学校教育中得到认可,甚至无助于学业成功,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将慢慢减弱,抑或对学校中的主流文化有所排斥。例如,云南少数民族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上下、左右”等方位词,并且以生活环境中的山或河为参照物,但不经常使用“东南西北”这种绝对方向,只是根据教师“告诉的”死记硬背而已。[12]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够使乡村少数民族教师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重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对其自我形成、道德养成、认知发展的影响,而非因为他们的知识习得困难而产生某种偏见。
(二)促进少数民族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个体专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教师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历程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13]乡村少数民族教师的专业性需要立足于本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才能得以更好地发挥,掌握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其了解本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了解民族地区乡村孩子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认知风格,从而形成课程与教学地方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将地方性知识与教师的学科知识相结合,提高了教师对教材的解读能力和深加工能力,从而将知识更好地教给学生。[14]乡村少数民族教师需要在不断地探索、反思中摸索出适切于自身的专业发展之路,其专业发展核心则在于成为“文化敏感型教师”。[15]
(三)为少数民族学生回归本土社区服务
调查表明,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多数人会选择在户口所在地就业。[16]当前的教育仍是精英取向的教育,对于大多数乡村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而言,他们一旦升学无望,终将回归本土社区发展。乡土文化中凝聚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寄托,镶嵌于本土的时空脉络之中。少数族群学生因着对本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情况不同,而变成“调适者”、“同化者”、“边缘人”和“分离者”。[17]当少数民族学生未完全接受学校教育中的官方知识,却已疏离地方性知识之时,他们也逐渐成为了徘徊于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无根的边缘人”。少数民族教师掌握地方性知识并融入于学校教育教学之中是解决少数民族学生扎根本土、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现代化背景下,“地方人”不是偏居一隅之人,而是具备跨文化视野、体察本土文化价值并将个人发展与社区发展融合之人。
三、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地方性知识的习得
在乡村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教师,不论其民族、其原本所在的文化环境,皆需增强多元文化意识和文化阐释的能力,积累地方性知识,成为“浸润民族文化,兼具国家情怀”的人。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应 “从文化持有者的视角看”,在田野工作中通过理解、分析当地人所表达的象征形式(词汇、意象、制度等)获得地方性知识。[18]这一能力是逐步发展的。
(一)在职前培养阶段学习人类学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渗透于民族地区的习俗文化、民族歌舞、地理风貌、神话传说等各个方面。因此,少数民族教师习得、运用地方性知识的前提是学会理解文化、阐释文化的方法路径。在少数民族教师教育中,可在通识课程中增开文化人类学或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等专题课程,旨在奠定教师对于不同文化与人、教育发展关系的基本认识,增强多元文化意识。[19]师范生可通过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等课程学习规范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为自主习得地方性知识打下基础。在文化阐释理论看来,习得地方性知识在于同“文化持有者”互动、对话之中的理解、阐释,其关键在于具备在田野工作——对少数民族教师而言,这里的“田野”包含了本土文化场域和乡村学校场域——基础之上撰写民族志的能力,尤其是撰写课堂民族志的能力。民族志是阐释性的,是微观的描述,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对话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20]进而言之,不仅仅是人类学家关注教师研究(teacher-anthropologists),教师也应成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teachers),关注边缘(弱势)群体及其文化,实现教学民主,注重教育公平,营造和谐共生的教育新生态。[21]
(二)在职后培训阶段学习地方性知识
在入职培训阶段,少数民族教师可以系统深入地学习教学所在地区的地方史、民族信仰、风俗习惯等等。在培训过程中,注重将地方性知识的内容与国家课程的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在理解当地民族文化、呵护民族认同的同时,乡村少数民族教师也应理解、融入主流文化,从而成为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村落村民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认识和融入主流文化的桥梁。在入职培训的基础上,在职后培训中定期进行积累、运用地方性知识。访谈中发现*笔者访谈的一位广西壮族乡村教师表示:“我觉得书上的有些理论知识可能不是很适用于农村孩子吧。(我)希望学习更多的教学经验,但不要仅限于城市老师向农村老师传授经验,做得好的农村老师也可以给我们传授,可能农村老师的经验更适合。……我觉得应该创造条件开阔农村学生的视野,比如提升学校的图书量和种类,推荐一些视频资源。”,乡村教师的地方化经验有其重要价值,一些乡村学校的教育资源也确实存在着匮乏之处,但是乡村教师对地方化教学资源的价值认识、开发能力尚待提高,这是通过职后培训学习地方性知识的意义所在。乡村教师需要适合于、满足于他们的培训项目,需要特殊性、个性化、在地化的培训模式。[22]在培训的方式上,应重视案例教学法。
(三)基于文化自觉主动学习地方性知识
除了通过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在学术场域中习得地方性知识以外,更需要少数民族教师自觉地在本土文化场域中深入学习、思考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因为意义不是拥有它的物体、行为、过程等等所固有的,而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赋予的,所以需要到赋予者那里去寻找。[23]佐藤学教授认为,“学习”就是跟客观世界的交往与对话,跟他人的交往与对话,跟自身的交往与对话,即“构筑世界”、“构筑伙伴”、“构筑自身”的实践。[24]其实,这正是教师和学生在一定文化场域内生活、学习、延伸、成长的轨迹。教师在与世界、他人、自我的交往与对话中成为“整全的人”,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心灵世界。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25]因此,扎根乡村的少数民族教师需要带着文化自觉之心,在生活世界中积累地方性知识,并与其他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抑或是主流知识比较、理解、阐释。就如格尔兹所言,“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来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以来自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隐翳掉的部分”。[26]
四、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地方性知识的运用路径
“阐释”即想象、建构、书写,作为一种内生的范式包含在特定的外在公共文化背景之中,表现为对意义的探寻。[27]乡村少数民族教师运用地方性知识的根本在于通过对其意义(meaning)的阐释、连结实现其价值,具体包括两种运用路径。
(一)基于地方性知识特征的课程资源开发
地方性知识具有经验性、丰富性和情境性,[28]可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此类课程资源开发的前提是乡村少数民族教师比较熟练地了解和掌握地方性知识,并且能够对其中蕴藏的符号意义进行显性化表达。因为“民族地方性知识的许多表现形式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核的民族地方性知识几乎都是隐性的”。[29]例如,苗族居住的飞檐翘角的吊脚楼,不仅是独特的民族建筑景观,其建筑设计、材质选择、空间布局背后隐藏着苗族的生活方式、民族信仰和审美意识,可开发为语文、社会、美术乃至物理课的课程资源。此外,与地方性知识密不可分的是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这需要教师通过田野工作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观照、审视和整合地方性知识,通过“深描”的方式丰富课程的内容和深度。[30]
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具有开放性,我们可以打破“地方”的封闭性,将地方化的意义或行动“放置在更广阔的符号指涉框架(frames of signification)之中”,[31]即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之中。以“认识家乡的河流”*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云南项目的结题会上,腾冲地区一所项目校展示其开展的地方课程,“认识家乡的河流”是其中之一。的地方课程为例,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可以引导少数民族儿童从他们身边的生活世界出发,请他们介绍一下他们最熟悉的一条小河,然后再引申至中国的河流,乃至世界上的著名河流。对于像“认识家乡的河”这样的教学主题,乡村少数民族教师自身需要对本地区河流的状貌、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说故事等有所了解,能够基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加以诠释,并将相关知识拓展延伸,开阔少数民族学生的视野。在此基础上,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可以基于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发展需求与学生、家长共同开发课程教学资源。
(二)在教学中运用叙事教育渗透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
如果说“文化是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32]那么叙事就是彰显此意义之网的关键所在。叙事教育即通过叙事达到教育自己也教育他人、感动自己也感动他人、警示自己也警示他人的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33]通过叙事教育在教学中渗透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可使教师体察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灵世界,因为“心灵是文化的心灵,其成长来源于文化的演化和塑造,并通过文化的演化实现世界在心灵内部的存在”。[34]例如,小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作《望庐山瀑布》,诗仙李白是汉族人,七言律诗属汉族诗歌体裁之一。类似“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的自然景观,对于一些山区的少数民族的师生应该并不陌生,或许学校周边就有这样的自然风景。这时乡村少数民族教师若能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以合适的载体(如,民族诗歌、自然音乐及其背后的故事)呈现,或是邀请学生分享相关的经验故事,如此可使学生更容易跨越民族文化、语言方式的差异,既能理解主流诗歌的内涵与情感,又能唤起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与认同。
再者,乡村少数民族教师能否在叙事教育中深化互动决定着教学的有效性。笔者曾在云南腾冲的一所民族小学*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云南项目的项目校之一。参访听课,其中一节是介绍民族节日的地方课程。授课老师和学生们都穿着傈僳族的民族服装,授课老师是一位当地的傈僳族青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教书。那节课主要介绍傈僳族传统节日“刀杆节”。授课老师课前请学生们分组准备“刀杆节”的节日介绍、现场主持和模拟表演。模拟表演环节包括:上“刀山”、下“火海”、“村民们”一起跳民族舞。授课老师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抛出问题——如,“刀山”上一共有几把刀?勇士们踩在刀刃还是刀背上?“下火海”时需要注意什么细节?这些环节有什么含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积极思考。在课程的尾声,教师由傈僳族节日引申至中国其他民族的节日、其他国家的节日等等,实现课程知识的延伸与拓展。这位老师在此处的角色虽然更主要的是一位引导者,但是富有成效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内容阐释本身就体现了教师地方性知识的积淀与民族文化素养,课堂互动的过程亦是意义阐释的过程。
五、结论
乡村少数民族教师习得、运用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亦是他们对学科知识、教育事件、儿童成长的“文化语境化(cultural contextualization)”[35]理解、阐释的过程。这并非易事,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与教师的个人努力,需要在认同中学习积累并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却对提升民族教育质量、滋养少数民族儿童成长具有长远的意义。当乡村少数民族教师在本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穿梭、适应,抑或在共存的多种文化中冲突、协商、选择、融合,并将自己的文化适应、文化自觉的思考与体悟融入到民族教育的课程与教学之中,他们便是当之无愧的教育人类学家。
[1]王鉴,张海,李子建,尹弘飚,张忠华. 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师生课堂互动的比较研究——以西北地区部分汉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课堂教学状况为例 [J]. 教育研究,2011(9):68-75.
[2] 郑新蓉,杜媛. 少数民族学生需要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J]. 中国教师,2016(3):22-29.
[3] 欧群慧,滕星. “静寂的课堂”——一项民族志研究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7-21.
[4] (美)克利福特·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6][28] 李长吉,张晓烨. 教育学视域下的地方性知识研究述评 [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6):20-24.
[7][20][23][3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38,23,456,5.
[8][27](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二版)[M].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3,199.
[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83-584.
[10] Irvine,J. J.Educatingteachersfordiversity:Seeingwithaculturaleye[M].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2003:67.
[11] Shizha,E. Indigenous? What indigenous knowledge? Beliefs and attitudes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towards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 curriculum in Zimbabwe [J].TheAustralianJournalofIndigenousEducation,2008,37:80.
[12] 王学男,郑新蓉. 不同民族及文化背景下儿童科学素养的实证研究——以地球运动内容为例 [J]. 民族教育研究,2015(3):79-86.
[13]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0.
[14] 李长吉. 论农村教师的地方性知识 [J]. 教育研究,2012(6):80-85.
[15] 王艳玲. 培养文化敏感型教师:多元文化教师教育的议题与挑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A. Lin. Goodwin教授访谈 [J]. 全球教育展望,2012(2):12-19.
[16] 陈小昆,毛小刚. 新疆少数民族就业状况调查 [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2(1):76-80.
[17] 郑新蓉.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课程与教材建设 [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2):26-29.
[18][26][31][3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95,366,283,283-284.
[19] 孟凡丽. 论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教师的培养 [J]. 教师教育研究,2007(3):12-16.
[21] 桑国元,王文娟.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教师研究:以一项师生互动研究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2016(6):30-39.
[22] 刘录护,扈中平. 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理念、案例与研究批判 [J]. 教师教育研究,2015(3):79-85.
[24] 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20.
[25] 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 [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
[29] 欧阳佩瑾. 民族地方性知识的隐性表象及其显性化 [J]. 铜仁学院学报,2010(4):124-126.
[30] 成尚荣. 地方性知识视域中的地方课程开发 [J]. 课程·教材·教法,2007(9):3-8.
[33] 任丹凤. 对教育叙事和叙事教育的功能及意义的解读 [J]. 教育探索,2009(12):137-138.
[34] 曹文明,O.А.玛什基娜. 论布鲁纳的民间教育学 [J]. 外国教育研究,2015(3):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