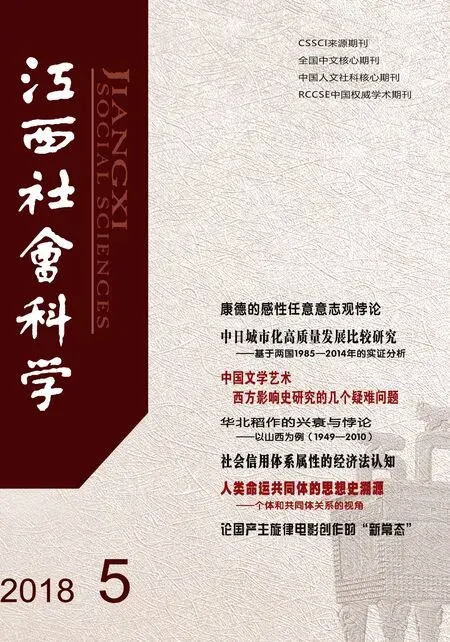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史溯源
——个体和共同体关系的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世界共同体关系构建的新尝试,是探索共同体关系建构的“中国道路”,思考共同体关系建构的“中国智慧”,是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圆融状态的理想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构建的思想史基础是什么?其蕴含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后世经典哲学家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洛克之前的传统共同体主义倡导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统一,洛克的政治哲学是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分裂的源头。黑格尔试图在理性国家中和解二者之间的分裂,但这种和解是在观念中进行的。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致力于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二者的现实和解,并且这种现实和解在当代的新发展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本文试图通过思想脉络的阐释,探寻现代政治意义上个体与共同体之争产生的源头,反思经典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思想史的角度为当代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
一、个体与共同体之争产生的源头
近代以降,伴随着个人主体性原则的觉醒,个体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便产生了,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使个人主体性原则在近代一路凯歌前行。笛卡尔认为:“自由运用理性只有在追求科学知识的时候才予以认可,而在政治和宗教上运用理性须精心加以监督。”[1](P370)然而就本文的着眼点,即从政治哲学视角而言,笔者不得不承认,笛卡尔的“主体”是一个纯反思哲学的概念,它很少涉及政治。而洛克主张理性可以“自由地在政治和宗教领域起作用,这如同在科学上一样”[1](P370),所以将主体理性引入政治领域,使个体与政治共同体间发生冲突的是洛克,而不是笛卡尔,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意义上个体与政治共同体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始于洛克。
(一)洛克之前的传统共同体主义
在洛克之前,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的霍布斯基本奉行一种比较传统的国家主义或者共同体主义,不存在现代政治意义上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分裂。在古希腊,“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2](P41),由于当时的城邦面积较小,人口不多,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个人和城邦基本上可以融为一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人由于本性或者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个超人。”[3](P17)因此,在城邦生活中,人类在本性上就是政治动物。然而,城邦并不是永世长存的,伴随着城邦衰败是罗马帝国的兴起。罗马帝国时期,疆域的扩张、人口的膨胀使公民不能像城邦时期一样完全地投入政治生活之中,因而他们有了精力去关注个人生活,独立于共同体的个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开始萌芽。塔恩曾说:“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4](P48)然而罗马帝国时期的个人概念仅是萌芽,个人还不能想象脱离强大的帝国而生存。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起使个人概念进一步得到解放,但是由于世俗权力总是渗透于教会权力之中,因此,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独立个体在这一时期仍不能实现。在中世纪后期,王权战胜了教权,统一的专制国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统一国家的形成似乎表现出共同体向希腊城邦复归,然而,事实是霍布斯等人的思想构成了传统政治哲学向近代政治哲学的过渡。
之所以说霍布斯的理论具有过渡性质是因为,一方面,霍布斯把自我保存、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这与近代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用绝对国家权力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这又有传统共同体主义的影子。霍布斯认为,“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5](P131-132)同时也是社会契约的形成,通过这种社会契约产生的国家对个人具有绝对的权力。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中,绝对国家还是能够通过外在强制控制个体的。因此,总体而言,在洛克之前,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还是统一的。
(二)洛克政治哲学中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矛盾与分裂
洛克是政治个人主义者,在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上,他更偏向于个体而主张有限政府理论。他认为,个人是目的,政府或国家是手段,并认为政治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尽管洛克也从个人与群体(特别是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给自己定位,但是历史证明,在他那里,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开始出现内在的紧张关系。因此,对于“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洛克没有完全解决”[1](P317)。在洛克的理论中“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充分解释这二者是如何都能成为绝对原则的”[2](P211),所以,在洛克那里,个体与政治共同体首次出现了分离。如果为了个体自由必须限制国家权力,那么国家就应当是一种“最小国家”,国家整体利益有可能会受到个体利益的蚕食,我们将之称为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Ⅰ。如果政治国家对于人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就必须赋予政治国家一定的权力,也就是说,政治国家不能是“最小国家”,这将有损害个体自由的可能,我们将之称为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Ⅱ。
1.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Ⅰ。按照洛克的观点:个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如果确实如此,那应该如何使社会利益或者整体利益不受到损害呢?霍布斯认为,个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自我保存,在这一方面,洛克受到了霍布斯的影响。萨拜因就此评价道,洛克的思想“就其含义而言,乃是与霍布斯的理论一样都是利己主义的”[2](P211)。对于萨拜因的这种看法,笔者表示赞同。洛克的政治个人主义甚至比霍布斯走得更远,在近代早期政治思想中是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他将政治权力的建立置于个体的人民手中,将反抗暴政看成每个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无疑,个体在洛克的理论中占有绝对的地位。
但同时,洛克接受了胡克的观点。胡克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经常被引用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人物之一。萨拜因认为,胡克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权力是不可取消的”[2](P210)。如果政治国家仅具有工具性,个人才是目的,而国家对人的存在来说又是必要的,那应该如何保护国家整体利益呢?洛克曾经提到士兵必须在危急时刻服从上级军官的指挥,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洛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解释士兵有什么义务必须为了他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将个体保存放在第一位势必导致这样一种矛盾,即在个体保存与国家整体保存之间无法协调一致。
2.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Ⅱ。从人的本性上说,个人不能自足,政治社会是人所必需的,国家的权力是不可取消的,这是洛克从胡克那里继承来的;同时个人权利又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洛克从霍布斯那里接收来的。由此产生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间的第二种矛盾:个人权利可能会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尤其是洛克认为,政治社会建立以后个人就要服从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以,如何保证这个大多数人作为整体意志不会损害个人利益也是成问题的。对于霍布斯和胡克的观点,“如果洛克采纳其中的一种观点而反驳另一种观点,那么他的思想就会比他现有的思想更前后一贯”[2](P211)。这个事实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时常看到,在有些方面,洛克坚持认为个人是终极性的原则,个人权利、个体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另一些方面,他又认为国家才是终极性的原则,国家的权力也是不可取消的。
这就是洛克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在自由主义体系内部,斯密、边沁、密尔等人曾经觉察到了这个矛盾,他们都意识到了共同体价值的缺失。斯密由此从经济角度指出“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自然和谐。边沁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来弥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分裂。密尔则提出利用道德教育实现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然而斯密、边沁、密尔等人虽然看到了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并未真正解决这个矛盾。
二、黑格尔的观念和解
哈贝马斯曾经说过:“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6](P51)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就是黑格尔所意识到的现代性问题之一。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在伦理国家中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并且黑格尔从卢梭那里继承了伦理共同体思想。
(一)黑格尔和解思想的卢梭基础
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一脉相承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黑格尔无疑是康德和费希特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卢梭思想的传承者。洛维特曾指出:“柏拉图的国家和卢梭的社会契约(黑格尔在里面只重视人权的观念,而不重视公民义务的观念)是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的现实提升为一种哲学的实存的两个前提条件。”[7](P326)卢梭首次把人道与爱国主义的问题表述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是强调个体意义的洛克和强调整体性意义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桥梁。
卢梭从洛克式个人主义中看到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分裂,他使自己努力摆脱这种个人主义,用人道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来表达这种分裂,用道德共同体来弥合这种分裂。洛维特指出:“卢梭的著作包含着对市民社会属人的问题的第一次、也是最清晰的刻画。这种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人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他一方面是私人,另一方面又是公民,因为市民社会存在于同国家的一种成问题的关系中。二者之间的不相配自卢梭以来就是所有现代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基本问题。”[7](P319)卢梭认为,人道与爱国主义是不相容的,在现代社会中就表现为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冲突。
那么,如何弥合这种冲突与分裂呢?虽然卢梭向往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但是他认识到,那种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中实现自由这是更切合实际的,卢梭写道:“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P19-20)笔者认为,在公意基础上建立的这种道德共同体就是卢梭所构想的弥合市民与公民、人道与爱国主义之间分裂的最佳方案。在这种道德共同体的描述中,卢梭主要借鉴了古希腊哲学的城邦思想,把政治共同体看作是伦理性的,并且把社会本身看作是一种道德化的力量,他的这种整体主义观点延及到黑格尔及整个黑格尔主义。
(二)黑格尔和解思想的观念性
然而在黑格尔所处的年代,自由主义已经表现出很多弊端。黑格尔逐渐认识到卢梭的理论尤其是普遍意志(笔者认为这是指公意)学说的缺陷。他认为,卢梭的普遍意志暗含着一种绝对自由和狂暴,黑格尔称之为“绝对自由和恐怖”。并且黑格尔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也不像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那样理想化,事实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已经发生了分裂。为了弥合这种分裂,黑格尔重新定义了自由。他认为,自由不是现成的,自由是生成的,自由是在意志的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意志发展到自在自为的阶段就产生了“法”。黑格尔所说的“法”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而是“抽象法”“道德”和“伦理”。在抽象法和道德阶段自由都是片面的,只有作为抽象法和道德相统一的伦理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黑格尔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中三种不同的伦理关系和秩序,这三种关系和秩序是渐次演进的。其中家庭代表了以自然血亲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和秩序,在这种伦理关系中,个体与共同体是直接统一的,家庭成员不允许退出这一统一体,这种统一感来自家庭所特有的伦理精神——爱。从家庭到市民社会的过渡意味着特殊与普遍、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裂。“市民社会就是个人私利的战场,特殊性充斥着市民社会”[9],然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市民社会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环节。从市民社会上升到理性国家则是个体与共同体达成的更高程度的统一,国家作为扬弃了家庭(共同体)和市民社会(个体)的真理性环节,实现了普遍与特殊、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和解。然而,由于黑格尔的和解方案是在逻辑学的框架中完成的,因此,被马克思斥为“逻辑神秘主义”。
笔者认为,黑格尔的和解方案是一种观念和解,这里的“观念”只是就黑格尔的和解方法而言。事实上,就哲学内容来说,黑格尔甚至促进了马克思的现实哲学转向,意大利学者洛苏尔多就持这种观点。按照洛苏尔多的观点,黑格尔比洛克等自由主义者要现实得多,由于洛克等把所有权绝对化,因此,他为所有权所做的辩护都是抽象的,没有考虑社会现实,而黑格尔对抽象所有权的否定体现了他立足于现实。比如,黑格尔认为:“当一个人在饥饿的驱使下,在必须保存生命的驱使下,对所有权的侵犯不算是任意和暴行,而是对一个更高的权利的肯定。”[10](P203)在洛克等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体的财产比生命要重要得多。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命需求,偷了一块面包,他确实是侵犯了某人的“私人所有权”,但就此认为这种行为是盗窃的违法行为是不公正的。另外,黑格尔也“把大众的贫困看作一个社会问题”[10](P206)。总之,黑格尔对贫困与饥饿等的描述说明了黑格尔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只关注抽象权利,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马克思更为接近。
三、马克思的现实和解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也试图解决在黑格尔那里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分裂。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和以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政治解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第三条道路。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也曾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追随者,到《莱茵报》时期,比如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他看到了现实的国家与理性的国家之间的巨大矛盾,思考问题的视角越来越向客观现实偏移,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赋予市民社会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地位。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展开论战,他批判了自由主义理论家所倡导的政治解放的限度。他认为,真正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导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分离,只有人类解放才能消解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
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和自由主义政治解放的批判,马克思为自己廓清了道路,确立了以市民社会批判为基石,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现实道路,这为和解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奠定了基础,彰显了其和解方案的现实维度。
(二)马克思和解方案的现实维度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现实和解的主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受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直接影响,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他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11](P71)以此为前提,他区分了虚幻的共同体和真实的共同体,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导致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对个体自由造成了压迫。只有在真实的共同体,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自由。
其次,“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现实和解的目标。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机体”的概念,指出了未来社会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趋势。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市民社会批判、资本逻辑批判、交换、雇佣劳动与“世界历史”出发阐述了国家向社会复归的未来社会形式——自由人联合体。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基本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资本的发展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传统的国家共同体,它是一种社会共同体,这种社会共同体以无产阶级为主体,以劳动实践为基础最终实现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和解。
最后,劳动实践是马克思现实和解的路径。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与浪漫派的黄金时代充满了相似性,这是因为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他受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韦伯和阿伦特就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过于浪漫化和理想化,而刘森林教授则认为:“浪漫主义是马克思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缺少这一维度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思想是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维度的结合。”[12]笔者认为,马克思实现了对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双重继承与超越,他不像浪漫派一样将自由理想的实现转向主体自身,而是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他认为,理想信念的实现是建立在现实和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现实的发展会支撑起一个伟大的理想王国。而且马克思破解了黑格尔观念辩证法和逻辑学的神秘性,通过实践辩证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立媒介,以辩证和解的方法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因此,不论是从和解路径还是从和解方法来看,马克思的和解方案都是一种“现实和解”。
马克思的“现实和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现实原则。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和自由主义政治解放的批判,马克思立足社会现实,指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和抽象性。第二,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认为,抽象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转变为“虚幻的共同体”和抽象资本共同体的根源。第三,全球维度。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思想表达全球化发展,他认为,世界市场的扩大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将会突破地域限制,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创造条件。第四,理想维度。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是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和解的理想形态。
总之,马克思通过颠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去除雇佣劳动的私人规定,找到了实现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和解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了高度的和谐一致。
四、马克思现实和解的当代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关系构建
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自我调节,并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出现了新的发展。但是抽象资本的统治仍然存在,资本逻辑仍然起作用,资本与劳动的主要矛盾没有本质改变。如何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构建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解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矛盾的有效样态,是建构马克思理想社会共同体的有效形态。因此,马克思的和解方案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曾经百余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世界共商共建共享。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重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这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它不只是中国的外交战略,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总体前途命运的关心和关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共同体关系构建的新尝试。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遵循了“自由人联合体”和谐共生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没有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作详细的论述,因此,探索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之路依旧敞开。但“自由人联合体”在价值导向上是明确的,它是一个这样的共同体:人们在其中充分发展着自由与个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自我与他我和谐一致,共生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理想社会共同体所蕴含的各种关系和谐共生的基本价值导向和价值追求,预示着全球价值观的生成,这种价值观是一种唇齿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价值诉求。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新的政治共同体关系建构。“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五位一体的共同体建构,重构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全球命运与共的大共同体。在经济上,消除资本的放任自流,建立互利的经济共同体;政治上,消除霸权,建立平等的政治共同体;文化上,建立兼容并包的文明共同体;安全上,建立相互沟通、尊重的安全共同体;生态上,敦促发达国家共同致力于世界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生态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构国家共同体间国际关系的新尝试。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建构的根基仍然是个体与共同体的圆融。“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3]这里的“人类”必然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表面上看是解决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它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以共同体的形式,解决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问题。个体不可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生活,真正的共同体能够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人形成的联合体,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15]“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过构建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共同体思想,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圆融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共同体关系多维度、多层面的建构,“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对人类自由解放理想目标的追求和决心”[16]。从价值诉求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达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从国际关系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实现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从个人发展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从根本上消除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现实尝试,是马克思现实和解方案的当代发展。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转化,是探索共同体关系建构的“中国道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思考共同体关系建构的“中国智慧”。从思想史的角度理清个体与共同体之争产生的源头,阐释黑格尔、马克思等经典哲学家对个体与共同体之争进行和解的方案,澄明马克思和解方案的现实性和优越性,有利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建构提供思想基础与学理依据,也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感和时代关照。
五、结 语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自古希腊至近代一直存在,发展到当代则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从古希腊到洛克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经历了统一—分裂—和解的过程。马克思与黑格尔都主张和解,相比于黑格尔的观念和解,马克思的和解方案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和解方案的当代发展,是当代世界共同体关系构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
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视角出发,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史基础,勾勒历史上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自古希腊以来就存在的两难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马克思理想社会共同体的有效尝试,是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关系圆融状态的理想形态,是解决共同体关系难题的新创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有力回应了‘自由人联合体’即为‘乌托邦’的错误观点,而且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找到了现实路径。”[17]
[1](英)R.I.阿龙.约翰·洛克[M].陈恢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
[5](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7](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出版馆,2003.
[9]李丽丽.马克思“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矛盾关系和解之现实基础”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10](意)洛苏尔多.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M].丁三东,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刘森林.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与唯物史观[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28/c1001-29613514.html.
[1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15]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
[16]黄婷,王永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世界秩序的话语表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5).
[17]杨宏伟.“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路径[J].理论学刊,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