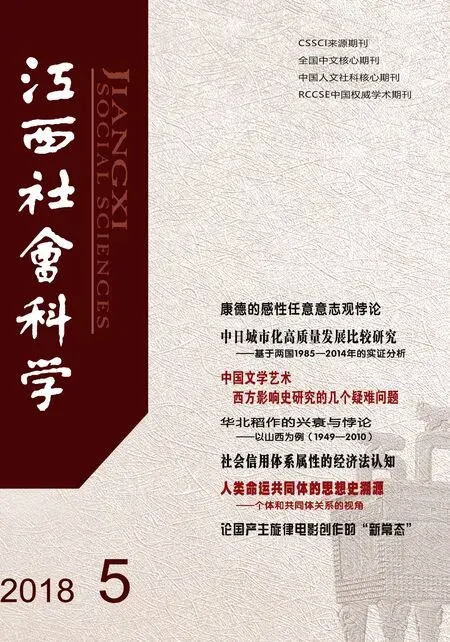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罚没分成”的证券监管有奖举报制度构建
随着金融市场的纵深发展,证券违法行为的数量也日趋渐长,行为的隐秘度以及复杂程度逐步提高。从内幕交易到基金经理“老鼠仓”,从欺诈发行上市到虚假信息披露,证券市场层出不穷的违法违规事件不停“鞭打”着本就脆弱的“三公原则”,严重伤害了投资者的信心。[1]受制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手段,监管者要凭一己之力实现完全有效的监管,并不现实,违法违规行为的频发与证券监管执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发显著。[2]作为扩充证券稽查线索来源的方式之一,对于举报人的物质激励可以提高公众参与证券执法的积极性。但自2001年《关于有奖举报证券期货诈骗和非法证券期货交易行为通告》颁布实施以来,实践反响平平。虽然证监会于2014年发布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对内幕交易或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或期货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欺诈发行证券等行为,知情人都可以通过实名举报的方式获得一定数额的物质奖励。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由于缺乏足够的物质激励和配套措施,举报人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通过知情人举报来获取相关线索和证据的比例依然偏低,这也是导致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3][4]为此,以“罚没分成”为核心构建证券监管有奖举报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举报人参与提供证券期货违法违规线索的积极性,并助力于实现监管效能的最大化。
一、法理论:证券监管中有奖举报的法理基础与监管逻辑
监管对象的激增,监管要求的提升,都在考验着本就有限的证券监管资源的承受力。如何改变过去“保姆式”的监管方式,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效能,是在监管转型下证券监管机关所面临的重要考验。在这其中,有奖举报制度的推出便是法律实施中私人监督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
(一)私人举报涉入行政监管的立法依据
立法依据的确定,事关制度设计的思路、架构、内容。从法学视角而言,证券监管中私人举报的立法依据大致有“权利说”和“权利义务综合说”两种学说。[5][6]在“权利说”的学者看来,私人举报源于宪法上的监督权,但这多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举报。[7]在“权利义务综合说”学者看来,举报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多指向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对任何违法行为的举报。[8]在我国,向行政机关举报对法律实施的私人监督是一种重要的宪法权利,同时也是一种法定义务。但同时,私人举报的立法根源又较为复杂,需根据举报主体和对象来探查。[5]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举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公民监督权的表现,但如果是公务员就内部不当行为的举报,因为涉及对内部举报是否属于其法定义务的判断,所以这类举报行为的性质尚未有明确定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6年“塞巴洛斯案”(Garcetti v Ceballos)中就认为:“如果政府公务员基于其职务身份举报,因为所举报的内容与其职责有关,因此被其所服务的机构解雇的,不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5]事后虽然国会迅速通过法案以消除上述案件的影响,但小布什总统却对此法案发动否决权。直至2012年奥巴马总统签署 《揭发者保护加强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Enhancement Act of 2012)后,才将保护的范围扩大到联邦职员。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在对各国公法实施问题的研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私人监督与公权力监督的关系以及公法框架下私人的诉权。[9]如何将证券监管中私人举报与公权力监督联系起来,寻求公私合力执法体系搭建的法理依据与制度的正当性,就成为有奖举报制度入法,以及制度顺利推行的保障。
(二)有奖举报的监管逻辑:法律实施中的私人监督
法律实施是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在出现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法律事实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所建立起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活动。[10]在这其中,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是法律实施的主要途径。同样,在英美法系语境下,虽然与我国关于法律实施的定义不同,但从其所包含的监督被法律约束主体的行为、对违法行为起诉、对是否违法作出裁判、对违法者进行惩处在内的四块具体可供细化研究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法律监督在法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编纂的《法学辞典》对于法律监督的阐述,其一方面可以被解释为实施监督法律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法律实施的监督。[11](P272)从狭义上说,法律监督多出现在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所为的对立法、司法、执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监督活动。但从广义上而言,也是从法律实施的制度规范角度来看,在法律监督中,以社会组织和公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监督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英美法系也认为,法律监督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交融、混合交错的综合体。只有将国家机关监督和社会力量监督有机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实施监督体系。[12](P452)国家并非法律监督的专断者,我国法律也同样认可私人监督的概念。包括私人、社会团体等在内的私法主体是法律所允许的对国家、对其他私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违法信息的发现者和法律监督的发动者。对此,我们可认为,私人监督是作为违法行为案外人的私权主体对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监督,包括但不限于发现违法行为、收集违法信息、采集违法证据,并提供给公权力机关供后者进行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6]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在道义上鼓励私人监督,但依靠道德驱使的监督行为却因无法提供足够的补偿和激励机制而在现实生活中“举步维艰”。虽然应该对私人参与共建公私合力的监督和执法体系大加褒奖,但若制度的设计仅仅是建立在对个人道理主义的非理性期待上,那么就完全丧失了制度规范本身所应具有的意义。[13](P10)
(三)私人参与分享执法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域外实践中,违法行为举报者具有监督并调查违法行为、代表政府起诉、分享罚款和赔偿等兼具公权和私权双重属性的权能。这种公私共同参与分享执法权的做法可以被理解为执法权在公共机关和私人之间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分配和共享。[6]尽管很难解释清私人在罚没分成中的行为和权力性质,但这样一种理论上的阐述困难并未对实践中制度的顺畅执行带来阻碍,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私人在法律实施和监督中角色的异化,而给法律实施带来了活力。[6]在传统法学理论无法为私人参与公权力执法提供太多的论证支撑的背景下,若从法经济学视角来揣摩该制度的内涵,大致能得到较为恰当的解释路径。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执法权的法律归属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并不存在任何公诉机关。肩负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组织还不够健全,法律也常会赋予公民以政府名义执行某些公权力职能,以弥补政府执法能力和执法力量的不足。[14]可以说,法律实施的最初形态就是依靠私人执行,警察实质上只是被允许的私人法律实施者,其所有的公共性也仅是名义上而已[15](P780),如何寻求执法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才是制度探查的着眼点[16]。经济学家们认为,执行法律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并不会影响到公共机构的自身利益。既然执法者不能够从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中受益,也不会因为不积极作为而受到利益上的减损,那么其在执行法律上漠不关心或是缺乏效率就有因可循了。[17](P167)所以要想在现有社会背景下寻求执法效率的提高,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就是扩大执法的主体范围并给以激励,将执法权恰当地在公共机关与私人间分配。若私人执法主体能够从执法效率提高中持续获得利益,其在利益的享有上便能更好地与全社会利益相协调并保持一致,有助于最佳执法效果的实现。[18]
二、比较论:域外有奖举报制度的经验借鉴
在证券监管中采用举报奖励并非新鲜事,这在域外实践中早已有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该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相关配套制度相伴成长。我国在构建以“罚没分成”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有奖举报制度的过程中,既不能盲目照搬域外经验,也不能搞“单兵突进”,而是应该将相关配套制度同步推进,避免证券市场沦为令人咂舌的“柠檬市场”。
(一)国际组织在内部人举报制度上的努力
作为私人监督法律实施的一条重要路径,对有奖举报制度的研究要与内部人举报制度联系起来。从域外实践来看,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对内部举报人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构建对其利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以促使公共和私营机构更加透明而负责的机制的实现。[5]就国际组织规范制定而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第8条规定:“各个缔约国应当基于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通过相关制度的制定,来便于公职人员在履行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对所发现的腐败行为进行举报。”[5]OECD在2000年修订的 《跨国公司行为准则》(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总方针中提到:“企业应克服对善意的向管理者、合适的公共机构举报企业违反法律、行动准则、企业方针的企业从业者进行歧视或惩戒。”[5]OECD紧接着在2004年《公司治理准则》中又指出:“利害关系人可不受拘束地向董事会告知其对违法或不合理的行为的疑虑,前者权利并不得因此而受减损。”
(二)美国对于内部人举报立法的两大路径
美国是较早对内部人举报进行立法的国家,其大致包括了两大路径。[2]一是旨在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不当减损的《反欺诈政府法》,该法案允许不隶属于政府的公众,代表政府向在政府项目中有意对政府钱财不当占有而为欺诈行为的人提起诉讼并追讨,举报人可根据诉讼所裁定的赔偿额获得15%~30%的奖金。[5]另一路径是旨在维护雇员权利的有关举报人保护的系列法案,这其中又分为针对政府机构的内部举报和针对民间机构的内部举报两种方式。从1978年《文职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of 1978)正式提出对政府内部揭发者的保护措施,并设立了专职机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来担负日常职责开始,美国正式拉开了对内部举报人保护的立法序幕。1988年《军队内部揭发者保护法》(Military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1988)和1989年 《揭发者保护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1989)的制定进一步强化了对内部举报人的法律保护,后者还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专门保护揭发者的法案。[18]199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意在减轻举报人举证压力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再授权法》,从而形成了对政府机构内部举报的举报人保护制度体系。相比而言,虽然对于民间机构的内部举报人保护没有形成一部较为完备的法案,但在涉及环保、证券、核能等领域的多部联邦法中,依然可见对于内部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制度安排。[19]特别是在“安然事件”后,美国国会快速通过了《公司舞弊责任法案》(Corporate and Criminal Fraud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2),对涉事公司施加了较为严苛的规定,用以防止因举报而遭解雇员工的利益受到不当减损。
(三)英美法系其他国家关于内部人举报的立法历程
英国对于内部举报人的保护较早见于1975年颁布的 《雇佣保护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EPA),该法规定,雇主对披露工作环境中健康安全问题的劳工的解雇是不公正的,雇主不得对上述劳工报复。[5]但该法所关注的内部人披露和举报仅限于有关工作环境的健康安全问题,对于其他内部举报暂不涉及。之后,英国又于1998年通过了《公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of 1998)。该部法律扩大了《雇佣权利法》(Employment Right Act)对于“劳动者”范围的界定,将派遣员工、研修生、公务员等均纳入其中。在适用范围上也十分广泛,突破了以往就具体类型和事项的特别立法,而是不分行业和公私性质的对进行举报的内部人适用同一标准的规范保护,且披露对象不仅包括发生在英国本土境内的违法行为也同样适用于境外的违法行为。当然,《公益披露法》出台的目的并非鼓励或抑制举报,而是减少企业对举报的限制,保护善意举报人不会因为举报或披露而遭受不利的对待。[20]同为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在最近几十年来也相继出台了有关内部人举报的法律[21],但遗憾的是,制度规范的重点主要针对基于政府机构违法行为、腐败和不当行政的举报,仅有个别法律将保护范围延展到私人企业。不过在2004年澳大利亚《公司法》修改中,也为公司员工内部举报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5]该法与2013年通过的《公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of 2013)一起构成了澳大利亚对内部人举报保护的法律框架。
(四)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内部人举报上的立法概览
再将视野转到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最初是通过判例来保护内部举报人的。日本最高裁判所于1983年9月16日在一则裁判中曾指出:“在雇主行使惩戒权或解雇权时,如果欠缺合理理由且也无法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同,那么雇主的行为就可能因为滥用权利而无效。”②在2003年著名的大阪和泉市民生活协会内部告发案中,法院认为:“内部告发在内容失当时,具有对被告发者造成名誉、信用减损之风险;但在告发内容真实时,又可为被告发者组织运营方法改善提供契机,并且后者不得因为内部告发而对举报人进行惩戒或解雇。”③之后,日本又于2004年在借鉴英国《公益披露法》的基础上,针对日本社会实际情况,制定了《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其对以往法律所提及的“内部告发”概念进行了小幅修正,排除了内部告发字面所可能具有的公报私仇、自首告发的概念外延,将法律所保护的告发严格限制为基于公益的告发,但在规范内容上,该部法律又与英国《公益披露法》相似,对内部举报人实施的是不分公私、不分事项的综合性特别保护。包括企业和事务单位中的劳动者、公务员在内的内部举报人均可以得到法律的“庇护”。[22](P1-2)在《公益通报者保护法》中,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犯罪行为也属于公益通报的事实之一。
三、监管论:建立有奖举报制度的必要性与或然性风险
目前在我国,对证券违法行为查出的有效性和执法效率还不能完全适应监管和市场需要,突出表现为在调查和取证上的困难,而有奖举报制度的建立毫无疑问对扩大违法线索的搜集来源大有裨益。但与此同时,一些缺乏基本线索的“冗余”举报以及恶意失实举报也会给本就有限的监管资源造成浪费,带来资源分配上的难题。
(一)证券监管转型下推行有奖举报制度的必要性
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实施难度的日渐增高,使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公权力机关的一己之力来推动,所以通过扩大法律实施的参与主体,以有奖举报机制来分散证券监管的成本,并分担因法律实施错误导致的实施失败的风险,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需要来说,都是必要且可行的。
第一,证券监管机关在证券稽查和执法中具有天然缺陷。证券违法行为具有复杂、多样且隐蔽的特点,证券监管部门作为外部公权力监管者,很难获得违法信息。政府对于证券商事活动,往往存在信息偏在的情况。即使依靠专业调查和审计等手段,依然难以和掌握实质信息的内部人相比拟。对于后者而言,他们有信息获取的独特优势,通过物质激励来扩大法律监督队伍,对削弱公权力主体与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有很大帮助。且在利益俘获理论者看来,公权力机关的官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人”,极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收买,从而在查处违法行为上多有懈怠。故而通过扩大执法主体的范围,将私人监督有效运用到证券违法行为的查处中去,可以起到对公权力机关及官员的社会监督的效果,同时也可以减少政府官员在法律执行中不作为或不合理作为发生的概率。
第二,知情人在证券违法行为的情况掌握上具有天然优势。虽然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企业应当遵纪守法,但法律的维护与执行依然离不开知情人的参与和配合。内部知情人因知晓内部信息而具有天然的维护法律的优势。若能本着社会良知的观念去关注企业发展,恪尽职守的维护社会安全,便可以及早披露相关企业的违法信息,成为行政监管的有效支持者。按照一般道德观念,在股票发行注册制下,当信息披露存在欺诈、虚假等违法行为时,知情人应当对此积极举报并加以遏制,而非放任自流的任凭其发生。但事实上,知情人对于证券违法行为的举报并非是一种揭露和遏制不法行为的有效方法,这在欠缺对举报人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激励的我国更是如此。
第三,扩大执法参与主体是监管资源匮乏下监管效率提高的需要。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组织体规模扩大且复杂程度提高,被监管者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监管者对上述违法行为的查处难度也在日益增大。包括内幕交易和虚假披露等在内的对证券违法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已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有研究指出,对于实践中证券违法行为的禁止和打击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并成为衡量一国金融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3]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监管水平、提升监管效率就成为监管层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加强监管固然重要,外部监管也可以对证券违法行为起到威慑效果。但在机构精简的大环境下,有限的执法主体却常常因为难以获得被监管者隐秘的违法信息而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使得监管缺乏成效,并且还可能因为过分加大监管或是惩处力度而与行政比例原则相悖。[24](P26)所以作为对证券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的积极促进因素,建立在举报奖励制度上的公私合力执法模式的推行,是对监管资源匮乏的一个有力补充。
第四,私人监督在证券监管领域往往比公权力监督更有效。在证券法实施中,依靠公权力监管者凭借自身调查去发现证券违法行为,并掌握其中证据,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成本,甚至还会一无所获。受制于编制、人力、经济等软约束,稽查局每年派出人手参与具体线索搜集的案件也较为有限,这直接导致了执法人员的水平和执法质量与监管需求不匹配。所以,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使得监管效果得到最大程度体现就成为监管部门的困扰所在。有学者指出,正是因为案件执行效率的低下,部分受公共预算约束的国家机关会刻意对某些案件淡然处之,将有限的预算投入能获得较好监管效果的工作中去。[17]然而,在证券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当下,证券监管部门无法对现存问题视而不见,他们也在努力调动各方力量来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频率。从法律的私人监督视角出发,证券违法行为的知情人毫无疑问可以用比外部监管者低得多的成本发现违法信息,违法者也将因为担心被内部人举报而内心受到强大震慑,故而调动知情人参与证券执法的积极性就成为有效遏制证券违法行为发生的一条可行路径。
(二)有奖举报制度实施的或然性风险
一方面,有奖举报制度实施可能导致举报量激增,对监管资源带来挑战。来信、来电、来访是证券稽查最主要的举报渠道,但在这其中,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甚至是虚假的举报。一旦举报激励机制建立后,可能会出现相当一部分抱着“中奖”心态的举报。在监管者看来,如果对所有举报一一核实,监管者自身和被调查对象都将“被负担“较高的监管成本,但由此是否会带来高监管收益存有很大质疑。举报核查任务量的增大,会耗费监管机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会对本就有限的监管资源造成很大压力。如何合理分配既有的监管资源,成为有奖举报制度推进的一大难点。
另一方面,有奖举报制度实施可能招来恶意失实的举报,浪费监管资源。在中立的观察者看来,对证券违法行为的举报并非一定出于道德因素,而是富有争议的,甚至可能导致破坏性的出现,所以举报本身所蕴含的正义性也就大打折扣。[25]在有奖举报制度较早实行的美国,举报者不需要承担足够使监管者信服的证明责任,法律在匿名举报制度下,又对举报者施以额外的制度保护措施。即使存在举报不实的情况,公司也不敢随意惩戒作为举报者的员工,受损失的只能是涉事公司和监管资源,这其实大大降低了举报的可信度。[26](P186)就我国实践来看,在对上市或拟上市公司的舆论监督中,也不乏滥用举报政策的情况。一些不良用心的人可能捏造事实、制造麻烦,将举报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恶意侵害竞争对手或他人的商业信誉,甚至发生欺诈、敲诈的行为。这无疑浪费了监管资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虽然最后无辜的公司会得到“清白”的裁决,但其中的调查和核实会占用大量时间和资源。
四、构建论:完善以“罚没分成”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有奖举报制度
以“罚没分成”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有奖举报制度,对于监管资源的节约、违法线索的获取、监管效率的提高等确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不过要想让这一工具真正成为“治市利器”,仍有待制度设计的进一步细化和合理化。
(一)厘清举报内容的正当性判断标准
在以“罚没分成”为核心的证券监管举报制度下,举报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是举报人当否获得法律保护,乃至享受“罚没分成”的重要前提。所以对于举报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是在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和举报目的的正当性两方面来做探查。鉴于不同举报人在证据搜集上的能力存在天然差异。公权力机关在判断举报人所提供线索真实性的时候,应当将举报人信息收集能力的差别考虑进行。只要善意举报人提出了支持其举报内容真实性的一定理由,其举报就当然的具有正当性。故而对于影响举报行为正当性的举报内容真实性的判断,指的是善意举报人基于一定理由对于所举报内容真实性的内心信服。在对举报目的正当性的把握上,只要举报事项确定真实,涉案主体所为行为被法律明确禁止,举报人的举报就应当被认为带有公益性,并符合举报目的的正当性。
(二)明确举报奖金来源的两条路径
根据国际惯例,用以奖励举报者的资金一般来源于罚款收入的分成。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证券监管部门的罚没款收入要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具体需要开支费用时再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由财政部门拨付,所以包括对举报人奖励在内的证监会各项行政支出都必须事先得到财政部门的核定和批准。从实践来看,有奖举报的资金来源需要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存在一定的难度,罚没款全额上缴财政的现行做法无疑是有奖举报制度推进中的一大阻碍。借鉴美国投资者公平基金制度的实践,建议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投资者公平基金。一方面可以对因证券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进行补偿,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对举报人奖励的一个资金池,将来源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中的罚没收入归入该基金。此外,对于证券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建议在满足一定程序后,于收支两条线之外,由证监会直接按照一定比例奖励给举报人,以“罚没分成”机制解决目前奖金来源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困扰。[27]
(三)增加举报奖励金额
在证券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中,私人监督的成本固然比公共机关低,但隐藏在之后的潜在成本不可小觑。这其中,作为私人监督的潜在成本之一,举报人面临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且对其来说,这一潜在成本比直接成本大得多。若完全依靠举报人的道德自发和无偿自愿行为,会导致私人监督成本与收益显著失衡,长此以往,是对监督动机养成的破坏。[1]以内幕交易为例,内幕交易知情人往往也是参与人或潜在参与人,与内幕交易可以或可期待获得的非法所得相比较,目前我国实行的1%的奖励标准、10万和30万的封顶额度对于承担了很大风险的知情人来说,确实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奖金数额对于举报人来说虽然只是一种激励,但若奖励太低,势必无法弥补举报人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精神负担。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可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都相当有限,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实现完全有效的监管,因而全民监督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物质奖励作为促使举报人进行举报的关键,不仅要对举报人所承担的私人监督成本以补偿,还要将这个补偿程度提高到足以抵消困扰举报人的潜在的监督成本承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通过有奖举报的利益导向机制,将捆绑在违法行为人和举报者身上的利益链条割裂,以减少证券违法行为的发生。
(四)罚没分成数额的确定
为了防止举报人为了获取更多奖励而知情不举、放任违法行为的道德风险的发生,在计算应得奖励时,要注意将举报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考虑在内,对于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违法行为发生日之后产生的、因损失扩大所应当处以的罚金,在计算奖励金额时,不应纳入罚没分成的计算基数内。[6]此外,还要将奖励金额的多少与以下因素结合起来确定:(1)被举报信息的重要性,包括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关联性;(2)被举报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危害性;(3)依靠公权力机关调查取证的困难性;(4)举报人的举报行为对于阻止违法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利益;(5)举报人的举报行为对于具体案件稽查的帮助程度。还应赋予监管机构进一步结合市场情况、监管能力对分成比例做出适当调节的权力,给举报人稳定的可得利益期待。
五、结 语
证券监管中有奖举报制度在美国运行已有三十余年,司法实践的良好效果充分显现了执法权公私共分体制的积极作用。从我国现有规定来看,已出台的规范立法层级较低,奖励条件和梯度规定模糊且奖励金额偏低,在配套规则上也无法给举报人以充分保护。因此,有奖举报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落地生根”后能否“枝叶繁茂”,还有赖于相关规则的完善。参考域外市场的制度经验,以既存问题和风险为导向,厘清对举报内容的正当性判断标准,扩充奖励金来源并提高奖励数额是在已有制度改进上需多加关注的。同时,围绕制度的或有风险,明确影响罚没分成数额确定的若干要素,更有利于提升监管效率,防止举报人道德风险的发生。
注释:
①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与所任职单位无关。
②参见《判例时报》第1093号。
③参见日本大阪地方裁判所大阪府堺市支部判决2003年6月18日,《判例タイムズ》第1136号。
[1]潘清.构建“全民监督”新防线 A股“有奖举报”效果待观察[EB/OL].http://finance.chinanews.com/stock/2014/07-01/6339394.shtml.
[2]刘沛佩.论我国证券监管中有奖举报制度的完善[J].证券市场导报,2017,(5).
[3]武俊桥,刘沛佩,邢梅.2014年证券市场法治述评[A].黄红元,徐明.证券法苑(第1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4]李虹.美国证券违法举报者“罚没款分成”机制及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2012,(12).
[5]王贵松.论公益性内部举报的制度设计[J].法商研究,2014,(4).
[6]李俊峰.法律实施中的私人监督[J].社会科学,2008,(6).
[7]赖彩明,赖德亮.加强公民举报权的制度保障[J].法学,2006,(7).
[8]汤啸天.举报人的权利与我国《举报法》的制定[J].人民检察,2004,(1).
[9]William E.Kovacic.Whistleblower Bounty Lawsuits as Monitoring Devices in Government Contracting.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1996,(9).
[10]吴淑贤.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研究[D].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201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法律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3](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M].李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4]蔡巍.美国“公私共分罚款之诉”及其评析[J].法商研究,2007,(4).
[1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6]徐昕.法律的私人执行[J].法学研究,2004,(1).
[17]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8]Mark A.Cohen, Paul H.Rubin,Private Enforcement of Public Policy.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1985,(3).
[19](日)境新一.内部告発者保护制度に关する诸问题[Z].东京家政学院大学纪要,2003,(43).
[20]David Lewis.Ten Years of 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1998 Claims: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tatistics and Recent Research?.Industrial Law Journal, 2010,(39).
[21]Parliament of Australia.Whistleblowing in Australia[EB/OL].http://www.aph.gov.au/binaries/library/pubs/rn/2004-05/05rn31.pdf.
[22](日)小西啓文,角田邦重.内部告発と公益通报者保护法[M].东京:法律文化社,2008.
[23]UtpalBhattacharya, HazemDaouk.TheWorldPriceofInsiderTrading.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
[24](日)阿部泰隆.内部告発(ホイッスルブロウワァ﹢)の法的设銒[M].东京:信山社,2003.
[25]缪因知.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之合法化[J].中外法学,2011,(5).
[26]Jonathan Macey.Corporate Governance, Promise Kept, Promise Brok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7]李季先.当下重塑资本市场法律信任的有效选择[N].上海证券报,2014-07-30(A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