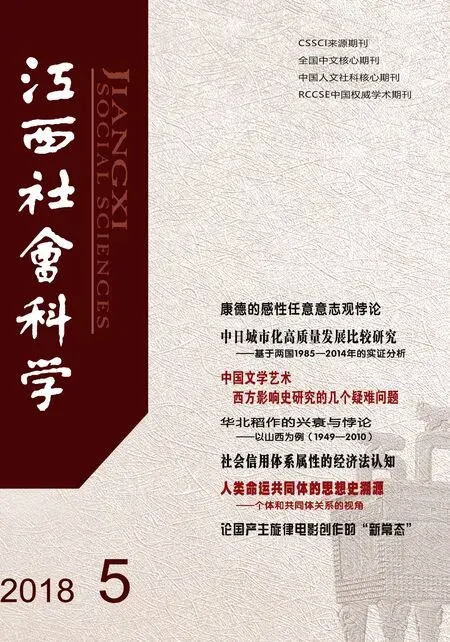政治、空间与城区变迁:清末民初天津的河北新区
晚清以降,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之路在政治激荡的氛围中缓慢起步。受西潮影响,中国城市也开始着力于城市空间的重构①。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一方面在于改造老城,拆毁城墙,打破了城市内的传统空间布局;另一方面在于扩建新区,城区的扩展既促成了新的城市格局,同时也利用新区的内部空间塑造了新的城市形态。清末天津的河北新区②即是中国城市近代化历程中扩建新区的鲜明例证。
近代天津的河北新区是1903年由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主导兴建的一片新市区。新区所在的河北一带在开建新区前还是“人迹罕到之处”[1](卷五《舆地(坊巷)》,P10),但在袁世凯主政期间得以快速营建。新区内街道规划整齐,房屋林立,近代化的市政设施一应俱全,一时间被誉为“天津新世界”[2](P87)。清末的河北新区生机勃勃,大有抗衡租界之势,但却在进入民国之后意外消沉。其从无到有、从兴盛到落寞的历史变迁值得关注。目前学界关于河北新区的研究,尚以地方志为主③,侧重于记述城区史话。其他关于天津的城市研究中对河北新区也有涉及④,但多为概述。此外建筑学领域对于河北新区也有相应关注⑤,其研究视角则集中于城区规划和城市形态的演变。本文则旨在从政治与空间的双重因素入手,对天津河北新区兴建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一梳理。
一、城市变革与空间诉求:开发河北新区的最初决定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始于1860年天津开埠,租界将城市近代化的因子带入天津。而在此后几十年间,华夷两立。尽管在当时国人的眼中,租界区“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3](P121-122),但天津华界却依然固守成规,变化缓慢。不仅如此,开埠后城市人口激增,规模扩大,华界的城市管理却在“走向失控”[4],以致20世纪前的天津华界,道路“狭窄且肮脏”[5](P41),加之失修严重,一遇雨天“行人断绝,全市就像死一样的沉寂”[6](P20),同时卫生情况堪忧,“所有污秽之物无不倾弃沟内,以致各处沟渠尽行堵塞”[7]。连彼时旅华的外国人也将天津称为“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最肮脏、看上去最贫穷的地方”[8](P32)。如此恶劣的城市状态急需整治,但在天津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下,却难以有效解决。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为天津的城市改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年7月,八国联军侵华后进占天津,联军在天津设立都统衙门,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八国联军设立的都统衙门,作为一个西式的市政管理机构,其在统治天津以后,迅速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法规、管理机构用于城市治理。都统衙门的管理颠覆了天津传统时期的城市管理模式,将近代化的市政体系引入华界。对天津华界的城市改造也在此时开始起步,其首先改组了成立于1882年的公共工程局,由“都统衙门书记官雷那德任工程局主任,专门着手于道路的改良”[6](P20)。改组后的工程局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填平了壕沟,扩建了城内的道路,设置了多条碎石马路。还极具效率地拆毁了天津城的四面城墙,并在城墙的旧址上建设了四条环城马路。城墙的拆毁成为打破天津传统城市空间布局的第一步,而为了满足城市近代化的需要,此后天津华界的城市改造,也在不断地进行城市空间上的重塑。
1902年8月,袁世凯奉命代表清政府接管天津。接管后,按照协定,都统衙门的许多管理措施和行政机构得以保留。在此基础上,袁世凯继续致力改革,其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就表达了这样的决心:“拟趁此变乱之后,将从前各项积习,痛于刷除,务期弊去利兴,庶以仰副圣朝整顿地方至意。”[9](P621)袁世凯的天津改革同样涵盖从政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改革的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天津因此成了“新政权兴之地”,“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咸集于津”[10](P3)。袁世凯依然延续了都统衙门时期对于城市建设的重视。天津于1902年9月设立了新的工程局,主要参与整修道路、疏浚河道、新建桥梁,并管辖田亩的注册、道路路灯安装、街道绿化等。新工程局装备精良,职责明确,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天津自庚子年后在城建机构上的系列改制和人员、设备的引入,为其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提供了政治与技术上的可靠保障。
此外,在袁世凯的改革中,作为其新政的主要内容,大量的新式机构、工厂、学校纷纷设立。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新设的机构多置于老城厢内,但随着空间需求的提升,如工艺总局“限于地势,无可开拓”[11](P684)之类的情形十分常见,天津城发展空间不足的形势严峻起来。
清末天津城的空间困局源于历史形成的城市形态。天津城始筑于明永乐二年(1404),筑城时仅按卫城的规格修建,清雍正朝城墙大修后,“东西长五百零四丈,计二里八分;南北长三百二十四丈,计一里八分五厘”[1](卷一《舆地·城垣一》,P9),即天津老城厢面积仅约1.76平方公里。至道光年间,城内共有“一大街、四小街、四衖巷、一百有六铺……共九千九百一十四户”[12](《县城内图说第一》,P435),已然十分拥挤。天津依水运而兴,因而更靠近河流的东门外和北门外最先得以开发,并迅速形成了商业聚集区,尤其是北门外,“商旅辐辏,屋瓦鳞次,津门外第一繁华区也”[12](《北门外图说第五》,P439)。而与市面鼎沸相对应的是空间利用上的饱和,当时《直报》就曾形容天津城“街道已极狭窄,更兼东洋车、地排车、小推车每日在各街走者络绎不绝,尚遇拥挤,无立足之地”[4]。此外,天津城地势北高南低,城南多是水洼之地,西门外也同样“地稍荒僻,围城多积水”[12](《西门外图说第三》,P437),加上距作为转运中心的三岔河口颇为偏远,这两片区域虽一直闲置,但却难以利用。这样一来,环顾20世纪初的天津城,老城的四周已无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空间可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改革中的空间诉求,天津城就必须穿过河流去开拓新的城市空间。位于金钟河以北、新开河以南的河北地区被首先选中。这片区域西连北运河,东接京奉铁路,直到开建新城之前还“向系贫民居住,地临旷野,荒冢累累,纵有田园,值价无多”[13]。决定在这片“人迹罕到之处”开拓新区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直隶总督行署的迁移和河北新车站的设立。
在庚子事变中,原本位于老城外的总督衙门被战火焚毁,袁世凯接管后,“查新浮桥北旧有海防公所一区……即于十二日驻扎该处,作为办公之所”[14]。如此,直隶总督行署最先迁至河北。天津政治中心的迁移,立即提升了河北的空间地位。与此同时,庚子年后各国租界分别设立,已有的老龙头车站毗邻俄租界,这样无论是官员往来,还是经营发展,都必须经过租界,十分不便。“天津铁路旧设车站货厂,地方逼近租界,开拓经营,诸多窒碍。”[15](P839)于是袁世凯饬令在河北添设新车站,新车站通车后,“北来官员多在该站下车”[16],“车行数月,商民称便”[15](P839)。河北新车站的修建是为了打破租界对老车站的封锁,同时也让官方对这个车站给予厚望,希望其能成为新的转运中心,以替代老车站。而新车站与老城区之间的河北地区也因此变得重要起来。
督署行辕的迁移提高了河北地区的政治地位,新车站则为其带来了充满希望的经济价值,河北地区整体空间价值的迅速提升,使其很自然地成了新城区的不二之选。由此,1903年初,袁世凯正式批准了由天津工程局拟定的《河北新开市场章程十三条》(以下简称《十三条》)[17],建设河北新区的序幕正式拉开。
二、行政效力与空间形塑:清末河北新区的快速营建
围绕着河北新区的开发在《十三条》颁布后迅速展开。对于在新政氛围中营建的河北新区而言,其建造既需要有效的行政推动,同时还需考虑如何形塑好新的城市空间。行政效力着眼于解决建设中的具体事务,而如何形塑空间则关乎河北新区的基本内在。这两者在清末河北新区的开发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对。
在行政效力上,受袁世凯新政的影响,此时天津的市政机构已被革新,并在新区的建设中展现出积极务实的行政作风。从直隶总督衙门到天津府县,再到工程总局,相关机构通力配合,形成了一套运作良好的管理体系,保证了新区建设中各项活动的平稳进行。
在开发之初,市政部门首先制定了管理城区开发活动的若干条例。1903年2月由袁世凯批准的《十三条》,是最早颁布的一份管理条例。《十三条》的内容涉及新区界内的土地征用、坟茔迁葬和税收问题,同时还专门针对私人的建设活动作出了若干规范。此后随着城区开发的进行,不同的情况开始出现,“随时考察,证以原定章程其中有办法未宜,情形稍异之处,以及原章之外,续经禀定,盖房取土各章程自应因时制宜,分别增改,量为变达,以期尽利便民”[18],所以在《十三条》颁布两年之后,新的《变通现行新章十三条》[18](以下简称《新十三条》)颁布。《新十三条》涵盖了《十三条》的绝大部分内容,并对之前的内容做了一些细化和变通。《新十三条》颁布的宗旨是“尽利便民”,其在许多方面宽限了一些原定的期限,同时强调“其有未尽事宜,随时察看情形,分别禀办”[18],也体现了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
官方的行政效力还体现在处理新市区的征地、拆迁和迁坟等棘手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市政部门同样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性。新区内有大量土地归私人所有。对于私有土地的征用,通常由工程局先行勘验,依据规划决定征地的范围,然后工程局会将详细的征地情况,“其所分之地段、号数,详注绘图一面……悬挂工程局门首,以备商民人等,照图细看分明”[19]。同时被征用土地会依照土地优劣,分段标注对应的征地价格。在不同的工程项目中,土地价格则因地制宜,被标注不同的价码,如修建种植园的征地中,土地的价格被分为了六种[20],而在筹建海防公所时,土地则被分为了三等[21]。此后,工程局会要求界内的业主携带土地的契据到工程局注册。虽然早在建设之初的《十三条》中就要求新市区界内的所有业主都需要到工程局对所属土地进行注册,但实际上土地的注册工作一直进展缓慢,以至于在实际的征用过程中,工程局仍然需要频繁地公示告知被占用土地的业主到局注册。在河北窑洼的土地征用中,呈契注册的时间就被迫改期[22]。业主完成了土地的注册后,工程局会派员随同其一起前往勘验确认。业主对注册工作并不十分配合的一个原因是作为旷野的河北地区,很多地户原本就没有契据,因此便无从注册,而针对这种情况,工程局也给出相应的对策,其在征用建设种植园的土地时就曾给出公示,允许“无契地户赴局声明,准其取具甘结照数领价,以示体恤”[23]。
在房屋拆迁时,官方除了为拆迁的民户补偿房屋款项外,还会为其提供必要的安置。河北贾家大桥一带的民居拆迁共涉及90余家[24]。在发款补地之后,该处居民仍“联名禀求缓期迁移”,天津县因此决定“其房地银价及移费均行加增”,同时将该处居民暂时安置在西南角广仁堂。[25]界内坟茔的迁葬也十分棘手,尽管府县反复饬令界内坟茔迁葬,但和征地注册时的情况类似,实际的迁坟往往是在冢墓的确影响到建设时才会进行。工程局只能一再示令要求有主坟自己迁葬,对于无主之坟则一般由义阡局完成。如河北窑洼一带的迁坟工作即是如此。[26]市政部门耐心程度如此,连《大公报》也感叹:“今地方官不避嫌怨,不惮烦劳,苦心经营,无非为民兴利。”[23]
官方务实且灵活的行政效力促成了新区开发中诸多事务的平稳推动,而对于新政氛围中开拓的新城区,官方显然也更希望利用他们的行政力将新的城市空间完全革新。因而在他们看来,新的空间就需要制造新的城市形态,而中国传统的筑城理念已经过时,租界成为他们所营建新区的模板。
早在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开始之前,天津工程局就很快完成了对河北新区的建设规划。《大公报》曾对此次规划做了较详细的披露:“河北一带开修马路建造市场等情已志本报,兹闻现经工程局绘画详细总图,东至铁路,西至北运河,其东西两头距离四里余,南至金钟河,北至新开河,其南北两头距离亦约四里,新开河开建南北大街十三道,直达金钟河及河北窑洼一带,以便商民居住云。”[27]河北新区最初的四至被限定在东至京奉铁路、西至北运河、南至金钟河、北至新开河的范围内。在工程局的规划中,新车站与总督衙门连接起来的马路成为新区的中轴线,其将新区切割为南北两个部分。以中轴道路为基准,十三条南北向、六条东西向的马路,将中轴线以北的城区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方块。中轴线以南的地区则同样被三条南北向、八条东西向的马路分割开来。道路网和被马路分割开的方格状土地,构成了新市区的基本空间形态。这种学习自租界的城市规划理念,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建造的制式,它摆脱了传统城市空间中的城墙和壕沟,也不再以官署府衙为中心,一切以道路为基础。
界内道路的命名,也颇有特色。新区由总督衙门至新车站的中轴线被命名为“大经路”。以“大经路”为基准,所有与其平行的东西向道路被称之为经路,与其相交的南北向马路则被称为纬路。大经路以北的七条经路,被以数字为首命名,如“二经路”、“三经路”等,以此类推。大经路以南,平行的经路依然以数字命名,但都以“东”字为首以示区分,分别是“东二经路”、“东三经路”等。纬路的命名则取自“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共十三条。大经路以南,与之垂直的三条纬路则命名为“阳纬路”⑥、“昆纬路”、“冈纬路”。新区道路的命名方式,虽字面多取自中国传统文化,但其形式上的统一性,也与传统城市的道路命名中强调以城中为核心、四方分开的命名方式不同,同样体现了西式城市规划的特性。
新空间的产生一方面促成了新的城市形态,同时也成了新设施的载体。新政中由官方主导的各类新式机构,如新式衙署、新式工厂、新式学堂等,在新区开发后迅速或迁入,或新建于河北新区。正是这些新机构组成了河北新区内的空间主体。
随着总督行署向新区的迁移,大量附属的行政机构首先迁入新区,其后在清末各项改革的推动下,产生了许多新置的行政机关,也多数设于河北新区。如:天津巡警总局,1902年设立,是新式的警察机关,位于总督衙门旁;学务公所,1905年设立,是直隶提学使的办公场所,位于河北公园内;直隶禁烟局,1907年设立,主管直隶省的禁烟工作,位于地纬路,等等。根据1911年《天津指南》的记载[28],河北地区的全部行政机构共分11类,总数达到42所之多。这其中除了单独管理河北新区治安的部分警察局所,以及京张、津浦铁路的管理机构外,多数是直隶省属机关,以及官办实业机关。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新区内的集聚,迅速强化了河北新区在空间上的政治属性,也使之成为天津城市空间布局中的政治中心。
新区内同时新置了各类实业。在袁世凯推动新建的实业中,影响力最大的要属直隶工艺总局。其在成立之后,“凡学堂工厂、劝工陈列所及劝业会场,与夫本郡、本省之各厂所、各堂场为总局倡导而创办者,远近向风,咸次第林立”[1](卷九《工艺》,P39)。在工艺总局的主导下,由其设立的工艺学堂、实习工厂、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北洋劝业铁工厂、劝业会场纷纷成立,皆驻于河北新区。这些官办实业有些侧重于制造实物,有些在于教授技能、展示模范。它们设立的近代化意义非凡,也促成了河北新区作为一个新经济空间在清末的快速崛起。
大量官办的公立学校也在新区内纷纷设立。在我们的统计中,清末新建于河北新区的学堂共有18所⑦,其中以专门性的学堂影响力最大,共有5所。如: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6月迁往河北黄纬路;北洋巡警学堂,1902年设立,位于河北堤头村;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7年设立,位于新开河新桥以北。此外的新式学校还包括各类师范学校和女子学校,共有5所。如:北洋师范学堂,1906年设立,位于新开河新桥北;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设立,位于天纬路。除了这些专门性的新式学堂外,还有大大小小的中小学堂在河北地区新设,这些学堂是新政中教育改革的重要一部分。
除此之外,官方还力求在新区内塑造更具近代性的公共空间,于是诸如公园、种植园、图书馆、电影院、展览馆等公共的文化设施也在新区内纷纷设立。界内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设施是筹备于1905年的“劝业会场”,其作为一个近代公园,早在筹备之时,袁世凯就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它“非漫为俗尘之游可比”[29]。劝业会场于1907年正式完工,开放后的劝业会场不仅是一个风景独特的游览地,而且包括市场、展览馆、照相馆、会议厅、电影院、西餐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官方对于劝业会场的精心构建使得劝业会场成为天津华界中首屈一指的公园,其“二门以内所有山亭花木、曲沼游廊、洞口流泉、笼中禽鹤,均任游人随意观览,不取分文”[28](卷五《园林》),这种保持对民众开放的姿态进一步促进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近代意义。此外界内还新建有种植园和李公祠等,种植园于1906年设立,位于新车站以东,占地十余顷,种植园设立之初在于培育植物,辅助工业,后对外开放,可供民众游览。李公祠,原本是为了纪念前直隶总督李鸿章而修建的祠堂,位于河北金钢桥北岸以西,后亦逐渐成为商界以及自治团体集会的重要场所。教育和公共设施在新区内的涌现,成为活跃河北新区文化活动的助力,显然也帮助提升了新空间的文化属性。
不仅如此,市政部门在主导了新区的大格局和主要建筑的同时,还力图塑造新空间的细节。比如,为了加强河北新区与老城区的联系,市政部门对界内的桥梁进行了大的改造,主要的桥梁如新浮桥和贾家大桥都被改造为新式铁桥,分别被命名为“金钢桥”和“金钟桥”。自来水和电灯照明也被应用于新区。城区绿化很受重视,树木的栽植一直在进行,如北洋银元局在建设新厂时就“种植树木二百余株,罗列内外,以待成荫”[30]。为了繁荣城区经济,官方也大力提倡工商,劝业会场建成后就曾专门盖房70余间,用于铺户租用。[31]
从衙署、实业到学堂、公园以及各类公共设备,这些官方主导下的新式设施,在河北新区崭新的空间形态中,成为新城市空间中的实体。它们的快速营建,填充了新市区的内在,帮助河北新区完成了早期的空间形塑。而这些设施本身所具有的近代性,也使得河北新区以一种更活跃、更文明、更近代的形态展现出来。河北新区因此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标杆。
总之,清末的河北新区在官方的推动下,日渐兴盛,房屋林立。《大公报》曾载文评论:“河北贾家桥及窑洼一带向系贫民居住,地临旷野,荒冢累累,纵有田园,值价无多,自添修马路后,日日兴隆起盖楼房无数,添设生意日多。该处之地,自三百两一亩涨至五六百两一亩。现时红楼处处,种柳栽花。大有各国租界之风致。”[13]此时旅华的日本人也感叹:“中国街亦不愧为直隶总督所居之地,中国洋式之华丽建筑亦不少。……其华丽,其殷赈,天津为北清之门户绝无可羞之处。”[32](P4-5)
三、政治动荡与空间劣势:民初河北新区的最终落寞
河北新区的发展在民国肇建之后再次因为政局的变动发生巨变。1912年后,帝国威权的丧失引起了各种派系之间的政权之争,政局动荡的局面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天津城的整体形势表现萎靡。因政治助力而兴的河北新区,受制于此,很快暴露出其在城市经济空间上的劣势,新区发展陷入低迷。
对于河北新区而言,首先由政治动荡引发的军事冲突,为其带来了直接且暴力的冲击。在军阀混战的数年间,界内修建的大量官私房屋,常被进驻天津的士兵侵占,“区中多阔老公馆今则□数迁入租界,且稍大住房亦多数为军队本部所占,客栈旅馆欲罢不能,更较其他为棘手,衙署局所多在区内,大小学堂亦多属之,大半因军队占用不能开学”[33](《区域(西区)》,P2)。新区内如华北博物馆“惜为军队占用,几等于废”,天津公园“楼房多为官兵所占,从前景象变更殆尽”。[33](《名胜》,P17)此外,在战争威胁的环境下,出于自保,华界的商民不断向租界转移资产,1922年直奉战争期间,“河北一带及中国界之富户,无不日夜搬箱运篋迁往租界,以冀趋吉避凶”[34]。商民向租界的转移进一步拉大了租界与华界的差距,而原本还希望能与租界抗衡的河北新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形势一落千丈,一时间难有起色。
战争的威胁可能仅延续数年,但受北洋时期政局不稳的影响,清末强有力的行政效力已经消失,政府的管理几近停滞。政治上的内耗首先体现在不断的人事更迭上,在1912年至1930年的十八年间,天津共出现了十四位军政长官,另外还有十五位兼任或单独担任的民政长官,即便是天津县的长官也有八位。政府行政长官的频繁更迭显然意味着城市发展很难有持续性的行政推动,河北新区在行政助力消失之后,城区的发展也很自然地跌入谷底。
在整个北洋时期,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河北新区市政建设都处于停滞状态,以至于界内道路、卫生等状况都差强人意。据1930年《天津市政调查汇志》统计,河北新区内只有大经路一带因为道旁左右官署较多,商店房屋集中,“尚比较齐整”,但即便这样大经路也“小坑亦不为少”。[35]相对之下,界内其他路段就很糟糕了。三马路⑧与天纬路的交叉口为往来要道,因而“界内马路之损坏,亦以此二路为最,界内卫生,尚差强人意,于午后八钟起首,各脏水车分取各户脏水,倾于市府西旁河内”[35]。海河历经几次裁弯取直工程后,金钟河成为废河,成了倾倒垃圾的地方,“皆任意倾倒废水,臭不可近”[36]。界内的中山公园在北洋时期内“毁坏程度太钜,殊非易于整顿”[37]。
整体来看,北洋时期的河北新区,因为市政上的不作为,整个新区除了东南大经路一带因为在清末就已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以外,其他地区,尤其是西北一带一如民国前的情形,发展几乎可以忽略。市政调查中也这样反映:“自宇纬路直至车站,东界大经路,西界新开河……因近年时局不靖之影响,始终未见繁荣,界内马路,除大经路尚敷衍可观外,余如三马路之下游,及各纬路,均损坏不堪,坎坷不平,西北角空地尚多,未曾建筑,亦自民十以来,市政未有进步之明征也。”[36]
行政助力的消失促使了河北新区开发活动的停滞,随之而来的是市政的衰落。而对于城区自身的发展而言,缺乏了有效干预,河北新区则被迫进入自然生长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河北新区既表现出固守已有空间格局的特点,它依然作为天津的政治中心存在,同时新区在经济空间上的劣势也随之暴露,其已经距离成为天津城经济中心的最初定位相去甚远。
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行政结构多因袭前制,天津多数的衙门机构仅作名称上变动,职权和驻所多未有变化,河北新区依然是天津大部分政府机构所在。1928年之后,天津一度成为河北省省会,在此期间“河北省之机关,自由平迁津后,增加甚多”[38](第三编《政治》,P127)。新增的政府机构仍然大量设置于河北新区。根据《天津志略》[38](第三编《政治》,P126-142)的统计,当时天津市共有省属机关23所,其中12所位于河北新区,市属机关有11所,其中5所位于河北。民国时期河北新区政治中心地位的强化,首先是由于旧衙门驻所仍然需要利用,其次也是人们对河北作为行政中心一种心理上的默认,时人亦认为:“该项地带,前清即为总督衙门,民国以来,地方长官,均以此为衙署,有此悠长之历史,市民心目中已认此为全市精神上之行政中心区域。”[39](P33)
尽管民初的河北新区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中,依然作为华界的政治中心存在,但此时空间上的政治属性并没有引发如同清末时期的示范效应,河北新区在设立之初就隐藏着的经济空间上的短板,使得它的城区经济失去活力。在河北新区的最初规划中,“自光绪庚子而后,津埠商业渐趋于租界一带,河北地面空旷,当道筹划振兴市面之策”[40](P30),官方原本计划提振河北新区从而使之能抗衡租界。为此,市政机关力促筹建河北新车站,望其能替代老车站,成为新的转运中心,但这种设想显然忽略了经济距离的巨大影响。虽然铁路的接通为天津的货运带来了新的交通方式,但天津庞大的货运往来依然有相当部分依赖于水路,所以即便是有新的马路和铁桥将新车站与老城区联系在了一起,但新车站与水路的遥远距离还是成了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个方面,距离河岸更近的老车站依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一情形实际上在清末已有所隐现,其时的常关报告中就曾评论:“该站(北站)因货运量小,倘不计客运,则较为次要;再者,水路之远隔,即此或令该站无以成为货物的集散要地。”[41]正因如此,新车站显然没能为河北新区带来预设中的助力,而华界传统的商业布局又依然集中在老城区的城东与城北,与河北新区始终保持隔河相望的态势。总览民国时期天津工业发展的概况,此时的工业分布仍以河道布局为主,老城的北门外和西门外都成为工业的重要聚集区,甚至南门外区域也成为地毯业的聚集区,相比之下河北新区在工业布局中就仅仅以几家纱厂、面粉厂散布,并没有大面积的工厂聚集[42](P116)。而根据1929年的调查,天津共有工厂2186家[42](P117),河北新区在我们的统计中却仅有33家⑨,占比极低。此外,我们还利用1921年的《天津指南》和1930年《天津志略》中的统计⑩,对驻区的若干项小工商业进行了简单对比,这一时期界内的小工商业也十分匮乏,除了客栈业有一定占比之外,其余各业都十分低迷。这些也都恰恰印证了河北新区经济发展中的空间困局。
回顾民初河北新区的发展际遇,动荡的政治环境成为城区失势的最主要原因,它在直接破坏城市的同时,也加速了华界与租界的差距,直接导致了河北新区的一蹶不振。但从河北新区发展的内力来看,空间距离上原生的劣势,使得河北新区在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后,随之也丧失了与租界抗衡的空间资本。河北新区在经济空间上的巨大不足,成为民初河北新区颓败的内因。
四、结 语
总的来看,清末民初天津的河北新区,其从无到有、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一直伴随着政治的干预和空间因素的影响。清末天津城在政治上的变革,提供了城市近代化的需求和条件,先进制度和优秀技术的引入使得城市改造成为可能。而面对历史遗留的城市空间困局,开拓新空间成了破解困局的最优方案。政治力在这中间也表现得极具魄力,很快促成了河北新区的诞生。不仅如此,高效的行政能力还成为河北新区在晚清时期快速营建的重要保障。官方在保证新区内各项建设活动平稳进行的同时,也行之有效地塑造了新的城市空间。他们在新空间内既制造了新的城市形态,也建设了新的城市内容,河北新区也因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城区。在清末数年间,显然是政治一直在塑造空间,进而改变了城市的近代化历程,而这种影响显著且积极。
但是进入民国以后,政治与空间两重因素的交合,其作用力却在数十年间发生了由正向到逆向的转变。北洋时期的政局动荡,不仅让河北新区失去了必要的政治支持,还迫使新区暴露出了其在经济空间上的劣势,从而导致了河北新区的最终落寞。事实上,河北新区的空间劣势早在其设立时便已经存在,只不过彼时强大的政治力帮助掩盖了它的不足,但当政治助力消失时,空间上的缺憾却成为城区颓败的重要原因。
由此,从河北新区的兴衰变迁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能否提供持续的行政支持关系着城区发展的成败。但是当政治力过于强大时,又很容易忽略城区发展中的空间合理性。虽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能够弥补城区发展中的空间劣势,但一旦行政力消失,空间上的不合理就会成为制约城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此情形在形势激荡的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事实上,倘若我们正视当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之路,在层出不穷的城市新区中,如河北新区这样重政治干预、轻空间合理性的情况还在不断上演。如何从历史中得以警醒,值得我们思考。
注释:
①围绕着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重塑这一命题,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周锡瑞强调城市的空间重塑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参见: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2002年Z1期)、《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陈蕴茜则强调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重塑的巨大影响,参见:陈蕴茜《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在河北新区设立之初并无“河北新区”这一概念,官方文件中以“河北新开市场”具体指代,其他场合,如晚清民国的报刊等指代也常简略为“河北”。“河北新区”概念作为一种特定指代,最常出现于近年学者们的研究论述中。本文则沿用这一提法,指代1903年《河北新开市场章程十三条》中确定的“河北新开市场”这一区域。
③比如:天津市河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天津河北简史》(内刊,1995年)、天津市河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④比如: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森《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城市史研究》1996年Z1期)、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⑤比如:傅东雁《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缩影——20世纪初的天津河北新区》(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靳润成、刘露《明代以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主要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秀芹、洪再生、宫媛《1903年天津河北新区规划研究》(《多元与包容——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5.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2年)。
⑥“阳纬路”一名又因谐音不雅被改为“新大路”。
⑦统计数据来自(清)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4页)。
⑧河北新区界内“经路”在此时已改称为“马路”,如“三经路”改称“三马路”。
⑨统计数据来自天津市河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天津河北简史》(内刊,1995年)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河北地区工厂一览表》,第143-146页。此数据虽不精确,但也能反映河北新区工业情况。
⑩统计数据来自《天津指南》(新华书局1921年版),以及1930年宋蕴璞编《天津志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清)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A].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2]津门精华实录[A].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一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3](清)张焘.津门杂记[M].丁绵孙,王黎雅,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4]陈克.十九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J].中国社会科学,1989,(6).
[5](日)坪谷善四郎.北清战地地志[A].津沽漫记[M].万鲁建,编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6]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Z].天津:天津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
[7]通沟除秽[N].直报,1895-05-15.
[8](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M].许逸凡,赵地,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9]袁世凯.恭报抵津日期接收地方情形折[A].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清)李映庚.北洋公牍类纂序[A].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11]工艺总局禀酌拟创设考工厂办法四条[A].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12]津门保甲图说[A].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13]新开马路[N].(天津)大公报,1906-06-27.
[14]袁世凯.驻扎天津海防公所办事片[A].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5]袁世凯.天津车站接修西沽岔道拨关内外铁路借款折[A].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6]马路告成[N].(天津)大公报,1903-02-03.
[17]再纪河北一带开筑马路市场章程十三条[N].(天津)大公报,1903-02-28.
[18]道府工程总局回街告示[N].(天津)大公报,1905-04-05.
[19]地段绘图[N].(天津)大公报,1903-05-03.
[20]具领地价详纪[N].(天津)大公报,1907-06-10.
[21]验领地价[N].(天津)大公报,1908-02-08.
[22]呈契改期[N].(天津)大公报,1903-03-30.
[23]展期领价[N].(天津)大公报,1907-01-31.
[24]续纪开修马路[N].(天津)大公报,1903-01-18.
[25]移民善政[N].(天津)大公报,1903-01-11.
[26]工程局示[N].(天津)大公报,1904-05-06.
[27]纪开修市场事[N].(天津)大公报,1903-03-14.
[28]石小川.天津指南[M].天津:文明书局,1911.
[29]银圆局总办周详遵饬会勘公园地址及工程局绘图呈督宪文[A].直隶工艺志初编:上[M].天津:北洋官报总局,1907.
[30]补种树木[N].(天津)大公报,1904-04-02.
[31]提倡工业[N].(天津)大公报,1907-05-17.
[32](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张学锋,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33]甘眠羊.新天津指南[M].天津:绛雪斋书局,1927.
[34]战事结束中近闻[N].(天津)大公报,1922-04-15.
[35]天津市政调查汇志(六)[N].益世报,1930-07-12.
[36]天津市政调查汇志(九)[N].益世报,1930-07-15.
[37]炎威逼人中之清凉世界[N].益世报,1930-07-14.
[38]宋蕴璞.天津志略[A].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9]梁思成,张锐.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A].梁思成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0]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京奉铁路旅行指南[Z].天津:京奉铁路管理局,1917.
[41]吴弘明.试论京奉铁路与天津城市的发展[J].城市史研究,1998,(Z1).
[42]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A].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上[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