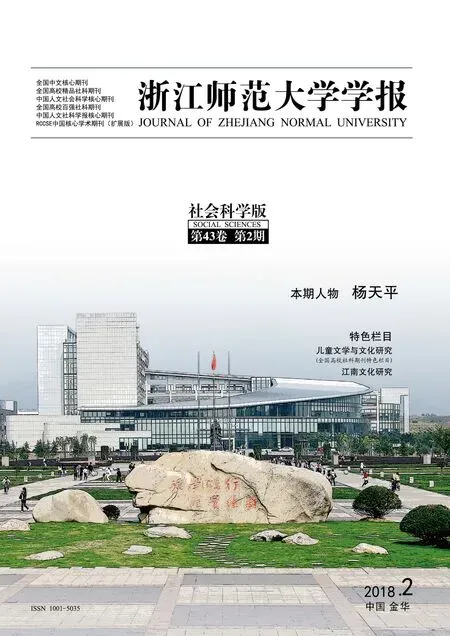幸福是美德指引下求善的实践
——亚当·弗格森的幸福观探究
林子赛, 赖晓彪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幸福是每个人都关心和渴求的东西,但由于幸福与生活的主观感受紧密相关,所以对幸福的理解亦是多种多样。幸福有时被直接等同于快乐,有时被理解为外在的财富、权力、名誉、幸运,有时被理解为德性,等等。幸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正如弗格森所言,幸福“这个意蕴丰富的词最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交谈中,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但是,仔细思量一下,或许它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一个词”。[1]45纵然幸福是人人都趋之若鹜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少会静下心来去思考它。下面笔者通过阐述幸福与快乐、美德、追求等之间的关系来看看弗格森是如何看待幸福的。①
一
有些人认为,快乐就是一种幸福,有时甚至把幸福直接等同于快乐,这是典型的快乐主义幸福观。一般认为,西方快乐主义幸福观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底波创始的昔兰尼学派。该学派认为,每个人都有感觉,唯有人的感觉才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因此,感觉是快乐的唯一源泉。同时指出,快乐是最高的善,追求快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由于昔兰尼学派所说的快乐主要是指肉体感官的满足,因而遭致了许多批判。实际上,对西方产生更深远影响的快乐幸福观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的。他同样从感觉主义出发,认为人的一切认识皆源于感觉,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人的感觉。由此他推出感觉上的快乐与否是人们进行行为选择的根本标准,也是幸福生活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但与昔兰尼学派不同的是,伊壁鸠鲁所指的幸福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即他认为幸福是指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在他看来,身体上的康健和基本的物质资料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一个疾病缠身或衣食堪忧的人是不会有快乐的,也很难想象能获得幸福,换言之,幸福的生活必须要有物质基础的保障。同时,伊壁鸠鲁也非常强调幸福的精神方面要素,在他看来,就快乐的程度来说,精神上的快乐远远高于物质上的快乐。
弗格森并不赞同快乐主义幸福观,他指出这种幸福观以人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为判断标准,即欲望得到了满足为幸福,得不到满足为不幸。他认为这是对幸福的错误认识。他说:“若幸福只是人的自然最易感染的那种最大的享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则应该说人不因其欲望实现而被认为是幸福的,而因其有所欲望而不幸。”[2]75他举例说,通常情况下邪恶之人并不因为他们实现了邪恶的目的而被人们视为幸福,反而会因为他心怀邪恶而被视为不幸福;愚蠢之人并不因为他们占有所羡之物而被视为幸福,而因其所羡之物无甚价值而被视为不幸福;放纵之人不因其享有平庸之乐而被视为幸福,反因其没有舍弃低劣而求自然中更高的享乐而被视为幼稚和不幸福。[2]75因此,弗格森认为,以欲望的满足作为幸福的标准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必然会产生新的欲望,如此一来,人永远处于焦虑状态之中,毫无幸福可言。
在弗格森看来,幸福生活必定是快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幸福的,因为快乐过多,或由快乐带来的痛苦过多,那快乐就是恶,它带来的只能是不幸,而不是幸福。显然,快乐是与幸福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当我们饥饿、口渴、睡眠等得到满足时,我们维持了自身的生存需求。换言之,人类自我持存的本能得到了满足,这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如此,如果把幸福简单地等同于快乐,尤其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强调感官的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对幸福很可能是有害的。与伊壁鸠鲁一样,弗格森同样把快乐区分为物质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快乐。他说:“对于动物性持存有益的、必要的东西的使用,是快乐的。那些有害的东西,则是痛苦的;关于任何完美的感觉是快乐的,而关于那些缺陷的感觉则是痛苦的。”[3]31-32这些快乐和痛苦弗格森把它们归为两类,即“一种是动物性的,一种是有心智的”。[2]72动物性的享乐,如吃、喝、睡、性等,它们来自于对人作为动物生命有益的事物的恰当使用,从根本上说,它们服从生命的欲望或自我持存的法则。这种快乐或享乐取决于欲望的恢复,或自然的紧迫要求。弗格森进一步指出,这种快乐无法保持连续性,它所带来的心灵感受往往是一时的、稍纵即逝的,人们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愉悦感远远不如真正幸福所带来的持续的情感体验。在他那里,有心智的快乐和痛苦按其层次从低到高可分为三类:意见、②感情、实践。其中,与意见相关的快乐和痛苦,主要是一些喜悦或忧愁、希望或恐惧,它们总是与相关事物的在场或缺席相伴,这种快乐离物质性快乐最近,很容易滑向物质性的享乐;出于感情的享乐或痛苦是由爱或恨这两种相对立的情绪构成的,即爱总是快乐的,尽管有时也会夹杂着折磨或悔恨;恨总是痛苦的,尽管有时也会夹杂着兴奋;快乐的实践则源于行动过程中身心的贯注,是最高级的快乐。[2]72-73
在弗格森那里,人的这两种快乐和痛苦的地位是不同的,换言之,“动物性的享乐与痛苦一般而言服从于有心智的享乐与痛苦”。[2]73动物式的快乐是人的一种感官体验,通常只是在人体某个感官受到具体的刺激时才产生,这种快乐仅仅是人类的生物属性的体现。而且,人们在获得这种快乐的满足之后,往往会产生新的、更多的需求,即时快乐的短暂满足总是赶不上人所意欲追求的快乐,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人们永远处在患得患失的焦虑状态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且过分地沉迷于这种快乐会扼杀人应对危急情境时的敏感和决断能力,最终导致痛苦和不幸的发生。因此,弗格森认为快乐通常具有短暂性,幸福具有持久性,并由此指出,通常感官上的享乐在很多程度上依赖于意见,人们一旦觉察到沉溺于其中的恶,这些享乐很快就会破灭。他说:“比起情感(affection)和行动(conduct),感官上的快乐是低俗的、转瞬即逝的”,[3]35而且,很多时候动物式的感官享乐是有害的,若强要使之延续下去,“将会导致人类心灵机能的中断,并且使其堕落为禽兽或以不幸而告终”。[4]5弗格森认为,所谓感官的生命,要么是极度麻木不仁,要么是迷乱的消遣放纵,它源于幻觉所带来的愉悦。最多不过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逗趣。同样,身体的痛楚也受意见的影响,极端惧怕痛楚的懦夫痛苦最多,而无惧痛苦的勇者或强人反而痛苦最少。痛苦也止于炽热的感情和积极的投入。[2]72-75弗格森由此指出,“越是严肃和紧迫的事务越可取,越是微不足道、越是只能带来表面快乐的事务,越不可取”。[2]74
显然,生活中如果没有快乐,一切将平淡无奇,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幸福生活。但快乐有别于幸福,尤其是动物式的快乐是由某些具体的生理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而幸福是人生中根本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某种满足所产生的愉悦感。弗格森认为,动物式的快乐往往会使得我们过于关注财物,而对财物的过分关注对于幸福是非常有害的,比如导致人的冷漠麻木、焦虑不安等。可以说,幸福是我们最大最长久的快乐。在自我选择的行动获得成功之际,快乐便自然而然地到来了,但不能把快乐凌驾于一切之上。弗格森指出,“快乐一词因太过模糊而不能替代幸福”,[2]76在他那里,唯有有心智的快乐,特别是基于德性的情感和实践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才能促进人类幸福。而且,从总体上讲,快乐相对于幸福来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正如他所言:“除了感官享乐之外,我们所有的享乐都来源于我们心有所图或心怀所感,而快乐对它们来说不是目标,而是途径。因此,狩猎之乐来自于对捕获猎物的渴望;操持之乐来自于我们追逐目标的兴奋;而友爱之乐来自于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善的快乐则在于德性带来的尊重。”[2]76由此可见,快乐仅仅是实现幸福的一种途径、一个工具,快乐自身作为工具不能说明快乐的价值,而是要以是否有助于幸福的实现为标准来衡量自身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快乐侧重的是感官欲望的暂时满足,幸福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持久满足;快乐体现的是表层情绪状态,幸福体现的是深层的心理状态。幸福以快乐为基础而又高于快乐,快乐是获得幸福的工具,而不是幸福本身。
二
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历来也是伦理学上争论的热点,可是,过去的伦理学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有的强调德性,不仅把德性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而且把德性作为个人和社会的终极追求目标;有的则强调幸福,视幸福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孰重孰轻,莫衷一是。自柏拉图以来,在西方道德哲学领域中,关于幸福与德性关系的理论强调两者统一的并不太多,大都视幸福与德性是相互对立的,甚至是处于矛盾、紧张的冲突之中的。初看上去,幸福与德性似乎确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幸福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而德性则通常是限制个体以服从社会或国家的。
综观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关于德性和幸福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两种典型的观点,即“德性即幸福”和“幸福即德性”。“德性即幸福”的观点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出现。柏拉图认为“至善即幸福”,人为了得到幸福,就必须抑制自身的激情和欲望,使之合乎理性和德性的要求。因此,“德性即幸福”的观念在很多时候要求人们超越肉体感官享乐,而追求心灵的至善。这一思想经由斯多亚学派的发展,在中世纪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禁欲倾向,当时的神学家大多否定人的自然需求,并将其作为邪恶加以批判。持这种幸福观的思想家大多认为幸福只是德性的附属品,拥有了德性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幸福,因此只有德性才是最根本的。这种幸福观的最大特点是将德性等同于幸福,强调精神幸福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幸福的物质条件。所谓“幸福即德性”的幸福观主要表现为快乐主义。快乐主义幸福观的主要代表有伊壁鸠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及之后的英国功利主义者等。他们大多把快乐,甚至是感官上的快乐看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德性则是实现幸福的途径和工具。他们大多强烈地批判彼岸的精神幸福,认为只有现世的幸福才是合理的、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获得了幸福也就得到了德性。
对于德性与幸福问题,弗格森指出,人类的幸福主要不是通过外在东西获得的,而是从人类自身内在的品质中获得的,“外在的物质如果不同人的心灵联系在一起,将毫无价值可言”。[4]77他强烈地批判了快乐主义幸福观,指出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试图在外界寻找那种只有在心灵的品质上才能寻找得到的幸福”,[1]59他们在实践中往往适得其反,不是获得幸福、反而遭受苦难。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幸福寄希望于外在偶然的机遇,故而常常患得患失、焦虑不安;或是认为幸福的获得取决于他人的意愿,故而常常卑躬屈膝、怯懦无能;或是认为幸福在于和他人竞争的事物中,故而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陷入了那些导致更大痛苦的妒忌、仇恨、憎恶和报复的情绪之中。[5]54在弗格森看来,为了将来考虑,我们必须抛弃当前的享乐,而且我们更应该坚持基于正义、正直情感的行动而不是为了利益和安全的考虑。一个正直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为了坚守职责而放弃自身的享乐,正是这种坚守才是终极的快乐。[4]50
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弗格森是如此论证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即德性、完美、善与幸福之间是一致的。仁慈、坦诚的情感构成了有智生灵的完美和幸福,反之,恶意、嫉妒带来的是苦难。弗格森进而指出,“如果说追求的目标是善的,那么每前进一步必然都通向幸福”,[2]78换言之,“善的拥有为幸福,恶的累积为不幸”。[4]77而他的“善”就是一种卓越的人类性情、品质,即德性,反过来也可以说“通常被视为人性上卓越的东西是善”。[3]32因此,在弗格森那里,美德、完美和幸福对人类来说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对同一情形的不同表述而已,幸福就意味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完美状态和一些最值得赞赏的品质上的美德。[4]5,73-74弗格森尤其强调,德性对人的幸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获取幸福的能力,美好的生活无外乎德性的运用和实践,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行”。用弗格森的话说就是“人们性情的流露和满足,同样可能证明对于我们的幸福或不幸是至关重要的”,[1]58“善的性情(德性——笔者注)对人类的幸福是必要的,而负责任的行为(德行——笔者注)则自然地源于善的性情。”[2]127拥有德性的人远离恐惧和厌恶、羡慕和嫉妒,怀着最好的情感,如人道、友谊和爱,他们致力于追求至善的目标、人类的公益,他们是幸福的。[3]35换言之,弗格森认为,拥有善良、睿智、勇敢等美德的人享有最高的快乐,承受最少的痛苦,他们是幸福的;而且这些美德本身是有价值的、可欲求的,这些品性会给其拥有者带来幸福。[2]76因此,可以说幸福是一种需要完善的美德,而不是一种需要减轻的罪行(宗教的禁欲主义幸福观所认为的那样)。
同时,他指出对于幸福的理解非常重要,理解的不同有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比如说把幸福简单地等同于快乐(pleasure),将会导致人们钟情于动物式的享乐,变得懒散。反过来,如果在美德的意义上理解幸福,将会使人们致力于行动、勇气和心灵的高级快乐。[3]35显然,弗格森本人是赞成后者的,即美德与幸福是一致的。在他那里,幸福不是暂时的享乐,而是德性的积极实践。由此,他指出,要想获得幸福,人们必须要永怀德性、做符合德性的事情。他说:“看来要使人感到幸福,就要使他的社会习性成为他行动中占主宰地位的源泉;声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对社会的整体利益他怀有满腔激情,抵制那些成为痛苦的焦虑、恐惧、妒忌和羡慕的基础的个人利益。”[1]61
弗格森总结说:“德性与幸福的定义是一致的,并由此可推说,幸福在于个人的品行,而非外部条件所赐”,“单纯的生命无法构成幸福或苦难,却是获得幸福或苦难的前提”。[2]76因此,总体上讲,弗格森持德性即幸福的观点,但是他并不完全反对现实的物质幸福,认为这是构成幸福的物质基础、前提、工具。
三
关于幸福与追求或人的行动的关系亦是伦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是灵魂(心智)合乎德性的活动。而且“德性”一词在亚氏那里的范围比较广,包括优良性、优良品质,它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而且他还把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并且认为理智德性优于伦理德性,因此他讲的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也主要是指合乎理智德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他那里主要指的是思辨。弗格森同样强调行动和追求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但弗格森的德性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品性而不是指理智德性。因此在弗格森那里,我们可以说幸福是合乎人之品性的生活实践,也就是说,幸福是在表现人的品性的活动中实现的,或者说幸福就在于善的行动过程之中,实践才是幸福。在实践事务中,目的并不在于理论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它们的实践,对德性只知道是不够的,还要力求运用或者以某种办法使我们变得善良。
弗格森强调,人类的幸福依赖于行动,最能使人愉悦的莫过于那些最使人专注的行动,那些能够唤醒其感情、运用其才能的行动。[2]74相反,认为幸福就是无忧无虑或无所事事,是卑劣的意见。[2]79真正的幸福是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的,这也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而且幸福本身的获得是通过把某种行为看做我们的娱乐,不仅在每一特定场合,而且在对人生价值做一般估量时,把人生看做只是发挥心智,吸引人心的一个舞台”。[1]57仅仅所谓的“成功”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很多暂时实现了自身“目标”而变得“怠惰”(inactive)的人往往很不幸福,伴随他们的是单调和无精打采。[5]51在弗格森看来,不管那是出于对幸福的渴望,还是对痛苦的排斥。人的行动比起他要追求的快乐重要得多,无聊比起他想逃避的痛苦更为可怕。[1]48“然而,我们很少考虑与人生福祉有关的、我们注定要完成的任务。我们总是向往着一个纯粹只有快乐的时光,或是要结束一切烦恼,同时忽视了我们眼下对大部分事情之所以感到满意的根源。问一问忙碌的人们,他们追求的幸福在哪儿?他们可能会回答,它就存在于当前追求的东西里。”[1]47同时,在弗格森看来,德性的养成不能仅仅通过理论的灌输或理性的说教,应始终坚持以行动为本的原则。实际上,弗格森强调的是道德践履即道德实践活动是提高道德认知能力、养成良好德性的重要方法,因为人的德性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不断完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一个普遍特征,人类就是在对幸福的不断追求中进步的。
人的幸福在于行动、在于永恒的追求之中。那么,幸福的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以什么为追求目标的人生历程才是幸福的呢?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永恒追求过程之中的必然牵涉的一些问题呢?
其一,人类追逐幸福的行动中必然面临诸多挫折、困境。弗格森尤其强调,在困难和危险中,一个人的能力与行为的坚毅性将得到大大的提升,人作为有生命的、积极的自然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自身的能力会得到加强,而不像机器那样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磨损、削弱,直至毁灭。这种能力上的锻炼、提升,既体现在动物性的机能上,如体型、肌肉的机能的加强;又体现在心灵上,如知识、睿智、判断力、创造力等能力的提升。[4]79,87但是,人的心智和力量的运用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极限,机体将会过劳而衰。因此,谁在一定的范围内尽力运用自己的心智和力量,谁就会获得远远超出预期的进步,获得更大的幸福。[6]
其二,感官的需求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构成幸福的主体部分。如前所述,在弗格森那里,感官的需求是人类生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是动物性和有智性的统一,动物性是人性的物质基础,动物性的感官需求在保存个人以及全人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即使如此,感官需求也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是一种有智的生灵,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因此,“如果把感官享乐看成是构成幸福的主体部分,这在思想上将是个错误,在行动上将是个更大的错误”,因为感官享乐往往是非常表面的、短暂的,很多时候是无意义的,而“追求的习性是很容易战胜对感官享受的爱好的”。[1]49
其三,我们要正确认识竞争、冲突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的重要性。弗格森指出,现实生活中似乎存在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看似合理的信条:一方面人们大多认为和平、团结是公众幸福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不同社会的竞争和民众的激情是政治生活和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如何协调这两种信条呢?弗格森认为或许没必要调和,这是促成幸福的两个重要方面,是可以兼容的。这是因为,热爱和平的人将尽一切努力去消除敌对情绪,调和不同意见,而且,这也非常有利于阻止犯罪等恶性事件,促成和谐共同体的形成,这当然是有利于人们实现幸福的。在弗格森看来,“拥有善的事物而对善无动于衷,或者拥有恶的意见,却对事物的恶逆来顺受,皆是可怜之举”。[2]80显然,弗格森本人则更加强调人类“分歧”的本性,认为作为一个好的市民应该有所争执,竞争是点燃美德的火炬,而人们没有深思熟虑就提交自己的意见,这种谦恭顺从是腐化堕落的主要原因。[1]69他举例说:“战争对于多少人而言是一种消遣,有多少人选择了危险而又常年疲惫的戎马生涯?有多少人选择了毫无舒适可言,要不断与困难作斗争的水手生涯?……并不是说这种人甘于放弃快乐,而选择痛苦,而是说他们受到一种永远不想静止不动的天性的驱使,要不断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决心,他们在斗争中感到欣喜。当他们停止工作时,他们就会垂头丧气,萎靡不振。”[1]50弗格森进而指出,平静、非对抗不是国家幸福的重要因素,对抗、动乱、分歧、争论对国家幸福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国家自身就是起源于对立团体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虽然相对于野蛮民族之间及内部纷争、暴乱,“一个更为安宁的国家会产生许多幸福。但是,各国若是实行扩张和绥靖计划,直到国民再也无法感受到社会的共同纽带,也不再热衷于国家事业,那么,它们一定会在相反的一面犯错误。由于它们几乎没剩下什么可以唤起人类精神的东西,随之而来的即便不是一个衰亡的年代,也是一个消沉的年代”。[1]245-246
因此,在弗格森那里,人性是好动的,渴望一种需要付诸激情的挑战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断地运用理智克服、防范可能出现的谬误,同时在这个实践中我们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改善,我们或许会犯错,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追求,理智进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些谬误指引着我们完善自我、发现真理。[4]60,72,84而且,人类正是在从事严肃“事务”过程中实现自我、获得幸福的,反之,“将一切义务、一切积极的投入拒之门外,只会使生活成为不堪之重”。[2]79但是弗格森把商业活动排除在他的“事务”之外,另外,他的“事务”必须是选择的“自由”实践,而不是对生理需要的反应。换言之,自由的公民是这种严肃“事务”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人类的幸福和美德才能真正得以保障。公民积极参与严肃的“事务”是一个社会繁荣兴旺的标志。弗格森反对休谟、斯密的“现代性”,主张一种思想的传统性,即探索人的美德领域的严肃的“事务”,与动物的感官领域的需求和物质享乐是不同的。这里,他继承了斯多亚主义关于幸福和美德的思想,即真正的幸福只有在美德的积极实践中才能获得,换言之,美德是积极努力的结果。因此,幸福与美德是统一的,他们都是人的好动本性的正确实践的结果。[7]由于我们拥有理智的积极能力,我们能够选择在严肃的“事务”中追求真正的美德以实现自我。外在行为是他们判断我们内在动机(美德的标志)的必要条件,弗格森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通过其外在的效果为人所知的,尽管外在结果是从属于精神上的情感的。他指出,一个有德之人拥有从善的倾向,并以饱满的热情和活力追求积极的美德。
四、结 语
前面我们探讨了弗格森关于幸福与快乐、幸福与德性、幸福与行动(实践)之间关系的思想。那么,到底什么是幸福呢?对此,弗格森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
“幸福不等于连续不断地一味享受肉体快乐。除了人们在职业和朋友方面所花的时间外,这些肉体的快乐只占据了人生很少时光。如果重复得过于频繁,这些肉体的快乐就会让人发腻,令人作呕。过分纵欲很伤身体。肉体的快乐就像夜空里的闪电,只能使闪电偶尔划破的夜空变得更加黑暗。幸福并不是舒舒服服的休息,也不是幻想中的无忧无虑。当它们遥不可及时,它往往是人们向往的目标,但是,一旦接近,它就会给人带来一种比痛苦还要难以忍受的单调和无聊。如果上述的有关幸福的评述是公允的话,那么幸福应该是来自追求,而不在于任何一种目标的实现。并且,在我们达到的每一种新的境界,甚至于在一个一帆风顺的生命历程中,与其说幸福依赖于我们注定要有所作为的环境,依赖于我们手中所拥有的物质,或依赖于他人为我们提供的工具,不如说幸福依赖于我们心智适当地发挥作用的程度。”[1]55
由此可见,在弗格森那里,幸福是合乎人的卓越、仁慈等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以快乐为基础,但高于快乐,幸福是精神上的持续的快乐而不仅仅是肉体上欲望的短暂满足;幸福与德性密不可分,德性是通往幸福之途的必要条件和追求幸福之人的目标;幸福存在于不懈追求善的过程之中,幸福在于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换言之,幸福不是暂时的满足与享乐,而是人类自身进步、完善所指引的高峰,是人之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趋向“善”和“智慧”的能力。
注释:
①本文所讲的“快乐”通常是指英文中的“pleasure”,“幸福”主要是指“happiness”。
②本文所提到的“意见”(opinion),在弗格森那里主要是指基于外在事物、表象所获得的个人成见、偏见。
参考文献:
[1]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M].林本椿,王绍祥,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M].孙飞宇,田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ADAM FERGUSON.Analysis of Pneumatics and Moral Philosoph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1766.
[4]ADAM FERGUSON.The Manuscripts of Adam Ferguson[M].by Vincenzo Merolle.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6.
[5]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M].by Fania Oz-Salzberg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6]ADAM FERGUSON.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M].New York:AMS Press,1792:228.
[7]CRAIG SMITH.Ferguson and the Active Genius of Mankind Eugene Heath and Vincenzo Merolle[M]//ADAM FERGUSON.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Publishers) Ltd,2008: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