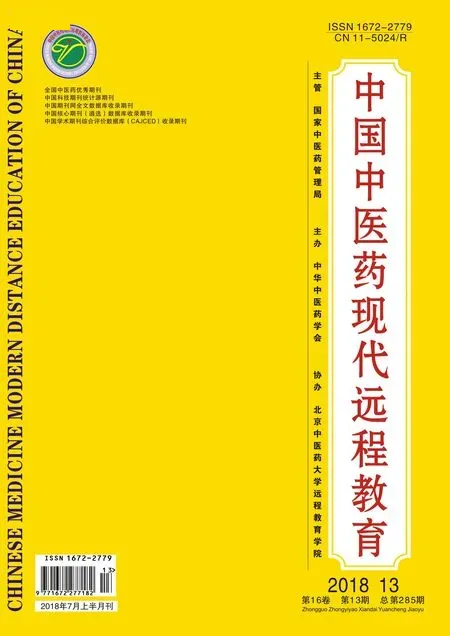中医药治疗肾性骨病临证体会
王晓蒙
(河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2017级,河南 郑州 450000)
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脏损害进行性恶化将导致肾衰竭,肾性骨病是慢性肾衰竭特别是透析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主要表现为骨骼的严重损害以及钙磷代谢异常所导致的皮肤瘙痒、贫血、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损害[1]。近年来慢性肾衰竭患者数量逐渐增加,肾性骨病的发病率也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几乎累及所有肾衰竭终末期的患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西医的治疗方案主要是控制高磷血症、调整血钙浓度、控制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2],虽能部分改善患者症状,但临床长期疗效不甚理想。虽然传统中医古籍并无“肾性骨病”的明确记载,但从中医学肢节内合脏腑的理论角度讲,骨为肾之合,自《内经》起就有关于“肾”与“骨”关系的论述。《素问·宣明五气篇》曰:“五脏所主,……肾主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肾生骨髓”,《素问·六节藏象论》又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充在骨”。肾主骨髓的生长发育,与骨的功能有关。肾藏精,精生骨髓,肾的精气盛衰,直接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代谢等,肾精充实则骨骼强健,肾精亏虚则髓减骨枯,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女子以“七”、男子以“八”为周期的生理变化一样,随着肾气的逐渐充盛,骨髓逐渐充满,齿更发长;然后肾气平均,骨髓藏而不泻,骨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再而肾气渐衰,骨髓生化之源匮乏,骨的功能逐渐衰退[3]。《内经》中所记载肾与骨的联系是中医学对肾性骨病理论认识的基础,后世医家在临证学习过程中也给予验证与补充,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骨极》中说:“骨极者,主肾也,肾应骨,骨与肾合。若肾病则骨极,牙齿苦痛,手足疼,不能久立,屈伸不利,身痹脑髓酸”,又有《医经精义》指出:“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也;髓者,肾精所生,精足则髓足,髓在骨内,髓足则骨强”。中医学对此独特的理论认识使得肾性骨病的临床辨证治疗有据可依,颇有收效,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整理论述。
1 病因病机
1.1脾肾亏虚 李中梓在《医宗金鉴》中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一方面肾主骨生髓,肾气衰弱,精不生髓,骨失所养而出现本病,恰如《素问·肾气通天论》中所讲:“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另一方面,脾主四肢肌肉,肌肉的营养靠脾运化水谷精微而得,脾气健运,则肌肉丰盈而有活力,反之脾气亏虚,则四肢萎弱不用,正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脾病……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肾与脾、先天与后天,须相互资生、相互促进,《景岳全书·脾胃》中讲“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脾的健运与生化,有赖于肾气及肾阴肾阳的资助与调节,肾的藏精与生髓,亦赖于脾运化水谷精微的不断充养。生理上,先天温养激发后天,后天补充培育先天;病理上,肾精不足与脾精不充,脾气亏虚与肾气亏虚,脾阳虚损与命门火衰,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肾性骨病所出现的骨痛、关节不适等症状属中医“骨痿”“骨痹”范畴[4],主要病因往往责之于脾肾两亏,先天匮乏,后天不足,髓无以充,筋骨失养。
1.2浊瘀互阻 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肾脏实质受损,无法进行正常的代谢,血液中毒素堆积,中医学认为肾衰患者体内的毒素主要是浊和瘀,浊即湿浊、痰浊,瘀即瘀血[5]。《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说:“清邪居上,浊邪居下”,首次提出了“浊邪”这一概念,仲景在《伤寒论·辨脉法》中说:“浊邪中于下焦”“浊邪中下名曰浑也”,提示了浊邪的重、浑之性,这就决定了湿浊之邪为病,往往出现沉重感及附着难移为特征的临床表现,例如水肿以及骨节酸楚疼痛。《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证治准绳·杂病》又云:湿气入肾,肾主水,水流湿,从其类也”,湿浊邪气的蕴结阻滞是慢性肾脏病各种标实之邪的基本与关键,在慢性肾脏病过程中广泛存在,并随着疾病的发展而渐次加重,故湿浊的结聚阻滞及其对脏腑气化功能的干扰在慢性肾脏病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诸病源候论》说:“血之在身,随气而行,常无停积”,若血液运行不畅则留积体内形成瘀血,不仅失去正常血液的濡养作用,而且容易阻滞气机导致病变发生,瘀阻肢体肌肤,则见关节疼痛不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到:“久痛必入络,气血不行,发黄,非疸也,血络瘀痹”。肾性骨病湿浊逆留,积滞血脉之中,化为浊瘀,浊瘀闭阻经脉,不通则痛,出现关节疼痛、肿胀、屈伸不利,浊瘀蓄积,化腐成毒,甚至出现骨节畸形。
2 治则治法
2.1补肾健脾 养血填精《理虚元鉴》中讲:“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类证治裁》云:“凡虚损多起于脾肾”,脾肾两脏的功能协调对于化生精血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脾肾双补则是通过补益脾肾的虚损或调整其生理功能,从而调和人体气血阴阳,在临床治疗中应用广泛。肾性骨病根本在于骨骼精髓虚损,因此,健脾补肾、养血填精是其根本治疗大法[6]。临床上在治疗此病时,强调先天与后天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将健脾补肾作为基本治则贯穿整个治疗过程,但又不可拘泥一方,可脾肾同治,或可有所偏重,并结合湿、瘀、毒等常见标证随症加减。补肾之药,温肾阳的常用药为补骨脂、肉苁蓉、淫羊藿,滋肾阴的常用药为地黄、酒萸肉、鳖甲等,常加牛膝、续断、桑寄生等药物以达到强筋骨之效;健脾药用黄芪、白术、党参、山药、陈皮等以求益气健胃,本病病程中常见阴损及阳、阳损及阴甚至阴阳俱损的情况,因此,在温肾为主时佐以滋阴之品,滋阴为主时佐以温养之药,以阴中求阳,阳中求阴而达阴阳互生。
2.2利湿泄浊 活血通络《血证论》说:“血与水本不相离”,湿浊与血瘀相互影响,而在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观察中,湿瘀互结是造成大多数病情恶化的根本病理因素,故而利湿泄浊、活血通络,湿浊与瘀血同治成为慢性肾功能衰竭以及肾性骨病的又一治疗大法。在行湿化浊同时应用活血化瘀治法,有助于提升肾性骨病疗效,延缓其进行性恶化。其中,湿浊轻者,可燥湿化浊,药选苍术、厚朴、砂仁;湿浊重者,可利湿泄浊,药选泽泻、通草、车前子;血瘀轻者,可和营通络,药选当归、川芎、茜草、桂枝等;血瘀重者,则活血化瘀,药选红花、桃仁、地龙、水蛭等。考虑肾性骨病多本虚,宜选用作用较和缓药物,如丹参、牛膝、鸡血藤、益母草等,化瘀泄浊兼具之药如泽兰、王不留行、大黄、皂角刺等可更多选用。
另外亦不可忽视痰浊,《赤水玄珠》指出:“若血浊气滞,则凝聚而为痰。痰乃津液之变,遍身上下,无处不到”,痰浊较湿浊更加黏稠而易于阻塞经络,使气血涩滞不畅,临床可加用三仁汤、温胆汤、导痰汤治疗,或酌加昆布、海藻、地龙等。痰浊与湿浊、瘀血亦易相兼,临床治疗应辨明标证,分清主次。
3 临证心得
3.1顾护脾胃 肾性骨病是尿毒症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中医临证时应当首先考虑患者的基本病情,病患往往体虚,万不可急用峻猛之剂攻下以求泄浊排毒。药物应用时应当注重顾护脾胃,以免脾虚不能受药,针对素体脾胃虚弱,或肾衰竭伴有胃肠道反应的患者,临床上常配合选用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平胃散、胃苓汤、益胃汤等加减化裁。张仲景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胃是肾性骨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论骨痹、骨痿,只有保护好脾胃,使其健运受药,才能把握治疗的先机,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7]。
3.2药选血肉有情之品《黄帝内经》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血肉有情之品对虚劳、血枯等虚损至极之症有着极佳的疗效。虚损之疾多因积虚成损,积损成劳,加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又因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应使用温阳补气、益精填髓的血肉有情之品,以填充肾脏所亏之真阴真阳。地龙、水蛭、僵蚕、蝉蜕、蛤蚧、鹿茸类药物乃血肉有情之品,性攻逐走窜,可通经达络,与草木及矿石药物相比更容易吸收利用,故效用可靠。肾性骨病多缠绵不愈,非虫类药搜剃以攻逐邪结不可,故而血肉有情之品对久病入络的肾性骨病有其独特的治疗效果[8]。
3.3不拘一脏 攻补兼施 在脏腑辨证上,不可拘泥于肾,需兼顾肝脾。肝藏血主筋,筋束骨。脾主肌肉四肢,生气血,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营养骨骼,所以调补肝脾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和肾性骨病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慢性肾功能衰竭所导致的肾性骨病不等同于虚性骨病,属本虚标实,病机复杂,在临床治疗中不能纯补、峻补,否则适得其反,关门留寇。《素问·三部九候论》中讲:“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应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肾性骨病时多采用脾肾双补、活血通络、泄浊解毒、攻补兼施之法,只有把各种病理因素祛除,肾精才能充养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