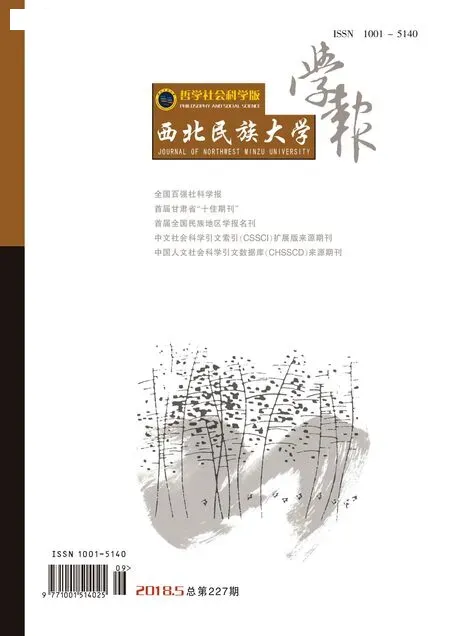“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
刘希瑞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社会迈向全球化4.0时代我国构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它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和日趋完善的过程。2013年9至10月,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理念;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参会各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构建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关键在于“五通”,其中“民心相通”是根基。语言是开启“民心相通”之门的钥匙。“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用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等区域通用语可以达意通事,但不易表情通心。“一带一路,语言铺路”,沿线国家有200余种民族语言,其中与我国邻接的跨境语言约为40种[1],跨境语言的使用不仅事关“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还关乎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对这些语言的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本文首先梳理跨境语言及其研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的现状,最后探讨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的规划问题。
一、跨境语言研究概述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状况
(一)跨境语言及其研究概述
“跨境语言”又称“跨国语言”(cross-border/cross-nation language),马学良、戴庆厦在“语言和民族”一文中最早提出“跨境语言”这一术语[2]。随后,诸多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新的修订和补充。其中,戴庆厦认为“跨境语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之一,是同一语言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语言变体,既不同于语言的历史演变,也不同于方言的共时差异”[3],较为全面地指出了跨境语言的内涵。关于跨境语言的外延,戴庆厦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跨境语言,前者仅指“跨境两侧语言分布上相接壤,而后者既包括接壤的也包括不接壤的”[4]4;周庆生强调“族体”“接壤或邻近”,旨在把跨境语言和“移民语言”“国际语言”“跨境方言”等概念区别开来[5],属于狭义的跨境语言。
跨境语言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为我国语言学界所独创,其重要性已为学界所共识,它对语言本体和功能研究、语言演变规律、跨境民族和谐、国家安全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均有重要意义[4]5-6,[6]。跨境语言研究肇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渐渐起步,2006年起受到广泛重视并被提到语言学分支学科的高度,当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在这个学科发展过程中,我国著名民族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先生厥功至伟。下文从本体结构与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概述。
一是跨境语言本体结构研究,多为跨境两侧语言的比较研究。我国第一部多语种的跨境语言研究论文集《跨境语言研究》,初步比较了傣、壮、布依、苗、瑶、傈僳、景颇、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跨境语言在语音、同源词、借词、词法、语序、复句、语体等方面的特点[7]。后续的此类研究还有中越拉祜语与仡央语、红仡佬语、白傣语等其他壮侗语族语言及中泰苗语的语音演变特点及对应规律、核心词亲疏关系及基本词对应的比较、系属地位、变异及成因等[8]-[12]。在比较研究之外,2009年后,戴庆厦主编的《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境外一侧国家的语言本体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描写和分析,包括泰国阿卡语和勉语、琅南塔克木语、跨境俄罗斯语、中亚东干语等。
二是跨境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主要成果多汇集在戴庆厦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和《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中。前者主要是关于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新时期的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涉及哈尼族、景颇族、拉祜族、布依族、傣族、克木人等一些跨境族群;后者则对国外一侧跨境族群的社会文化概况、语言使用情况及成因进行了调查和探索,包括泰国阿卡族、拉祜族和优勉族、老挝克木族、蒙古国蒙古族等,为认识跨境语言的使用现状和演变趋势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一手资料。另外,朱艳华通过对缅甸克钦族语言生活现状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多民族国家语言文字问题的一些建议[13]。
此外,2006年至今跨境语言研究百家争鸣的局面还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跨境语言研究专题学术会议及“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第二,《当代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多家语言学权威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跨境语言研究专栏的设置;第三,中泰跨境苗语、中缅跨境孟高棉语、中老跨境哈尼语、中缅印跨境景颇语、中哈跨境哈萨克语等多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等。所有这些对推动跨境语言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语言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在戴庆厦先生等国内学者的极力推动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研究内容、调查方法、语言关系和学术价值等方面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正逐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跨境语言的记录、描写和粗浅比较等本体结构与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少有涉及跨境语言的规划问题。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状况
语言状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分布、语言活力、语言关系、语言功能及政府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等情况。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规划的线路,沿线国家使用的跨境语言约40种,主要分布在与我国邻接的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系属分类上包括汉藏语系、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等四种语系。这些跨境语言广泛应用在民间交往、人文交流、边境贸易、边境维稳等方面,为实现沿线跨境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合作共赢,促进其他“四通”的实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身份多有差异、文字系统各不相同、语言活力逐渐衰退且我国境内的跨境语言基本不具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加快对沿线国家跨境语言规划的研究时不我待。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语言规划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有近60年的历史,一般认为始于Haugen论及挪威标准语规划时首次使用了“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一术语[14]8。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语言规划的界定逐渐达成了共识,即语言规划的对象是社会语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和语言本身[15]3。关于语言规划的类型,根据其内容的特点来划分,通常认为包括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和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两类,郭龙生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语言传播规划这一类型[16]67-73,李宇明则批判性地提出了语言功能规划(language function planning),规划语言生活在功能层面上的价值和作用[15]2。综合以上学者语言规划的分类方法,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的基本情况,这里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规划分为跨境语言本体规划、跨境语言功能规划和跨境语言传播规划三类。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本体规划
跨境语言的本体规划一般指对其结构系统本身的规划[14]9,如跨境语言的保护、分布在多个国家的同一跨境语言和方言的规范和推广、跨境语言文字的创制或文字规范的制定与推广、术语的整理和规范化、词典等工具书的编纂及语言的信息化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多为人口较少民族的人们使用,有不同程度的濒危化,对其规划的首要任务便是做好这些语言的保护工作,如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日常生活中使用本民族母语、要求适龄儿童学习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本民族母语、对这些跨境语言进行记录并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录音、录像、建设多模态语料库等方法进行科学保护。分布在多个国家的同一跨境语言的规范和推广亦是本体规划的一项核心内容。以南亚语系的跨境克木语为例,它分布在中国及老挝、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使用人口约70万,有东部和西部两大方言,前者处于克木语发展的保守阶段,无声调对立,但辅音库藏丰富,且有清浊对立的区分,元音有长短对立;后者浊声母清化发展出了高、低两个声调,方言之间差别较小,彼此间均可相互通话。对其进行本体规划时,究竟是采用哪种方言作为标准语需要综合考虑使用人数、易接受度、政治文化因素等。由于国情改变等原因而引起的跨境语言文字体系的差异往往大于语言本身的差异,沿线国家跨境语言常见的文字体系有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希腊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汉字为基础的文字等,同一跨境语言采用不同文字体系会造成书面语交流的障碍,对其规范化可大大提高该语言的活力和效率。术语的整理和规范化主要指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娱乐等)术语使用的规范问题。词典等工具书的编纂中也有诸多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外来语词条究竟如何选取,以跨境克木语为例,表达相同意义的词条究竟是选用汉语借词、老挝语借词、泰(傣)语借词等,鉴于傣族与这些国家跨境克木人常年交往,同等条件下泰(傣)语借词应该优于其他的。语言的信息化问题是当今时代语言本体规划中日趋重要的一个方面,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的信息化程度一般较低,更应该重视诸如建立语言数据库、开发电子词典、开展智能语音技术研究、研发语言自助翻译服务系统等工作。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功能规划
语言功能规划是指对各语言现象(如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国语文等)在各功能层次(包括国语、官方工作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化、日常交际等八个层次)价值和作用的规划,是从语言生活的角度进行的更为缜密、操作性更强的语言规划[15]7。
据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功能规划主要指对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文字、沿线国家官方语言文字和区域通用语言文字等语言现象在工作语言、教育、大众传媒、文化交流、日常交际等五个功能层次价值和作用的规划。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倡导者和引领者,应在尊重沿线国家官方语言文字和跨境语言文字的前提下,着力把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规划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语言,逐步弱化沿线国家区域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功能,确保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及沿线国家政府中的影响力,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教育领域,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另一方面要重视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的保护、普及和推广,充分发挥它的表情通心功能,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民意基础。在大众传媒领域,尤其是要重视数字电视、网络媒体、移动终端媒体(如WeChat等)等新媒体传播过程中跨境语言文字的便利性、有效性和亲和力,采用沿线国家跨境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交流和日常交际领域,更要强化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的功用,使之功能最大化。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传播规划
语言传播规划这一类型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郭龙生首创,他指出“语言的传播规划是指为扩大某种语言在国内或国际上的影响力而开展的一系列规划活动。主要包括:确定传播范围、手段、方式与途径,建立传播机构和组织,组建传播队伍,传播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和价值观等”[16]67-7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传播规划,不仅涉及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本身的传播,还包括我国的官方语言汉语在沿线国家的传播,两者各司其职、互为补充,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就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本身的传播而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那些跨境范围广、使用人口多、区域影响力大的语言进行重点传播,例如东南亚地区沿线跨境语言可选择克木语、景颇语、傣语、苗语等;然后因地制宜确定传播范围、手段、方式和途径,传播范围一般是跨境语言所在地区及周边地区,传播手段、方式和途径主要是在日常交往、贸易往来和工作场景中口耳相传以及通过教育、大众传媒等手段进行传播,通过跨境语言的传播助力“一带一路”各项工程的开展,并促进地区间文化的融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沿线国家“汉语热”的浪潮不断高涨,为汉语国际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何做好沿线国家的汉语传播也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传播规划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首先要做好开展汉语在沿线国家需求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对策。其次,汉语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是汉语作为外语在沿线国家的教学问题。外语教育由教师教育、大纲设计、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测评等六大要素组成[17]。具体到沿线国家的汉语教育,需要从语言规划角度统筹上述六大要素及社会需求等规划内容,尤其是教师教育和教材建设,应结合外语教育、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及当地特定的国情与文化审慎规划。就教师教育来说,不论是当地的本土教师还是汉语为母语的我国教师都需要具备扎实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熟谙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华武术、中国戏剧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沿线国家及沿线国家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化,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公共外交能力。我国派出的汉语教师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使者,还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外交力量,对宣传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至关重要。就教材建设而言,教材编写一方面要更新编写理念和内容形式,注重现代技术和新媒体手段的应用;另一方面还要平衡中国和沿线国家及沿线国家跨境民族的元素,体现多元文化特征。
此外,沿线国家跨境语言传播规划还关涉“一带一路”各方平等话语体系的构建,各种概念和术语汉译外的措词和表达都应尊重沿线国家的语言使用习惯和文化心理,例如从早期“‘一带一路’战略”的说法到现今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改进,对促进民心相通大有裨益。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现阶段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也需要语言学、文化学、民族学、教育学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多方协同和群策群力。在“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开展沿线国家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有助于相关部门做好沿线国家跨境语言的本体规划、功能规划和传播规划,更好地服务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