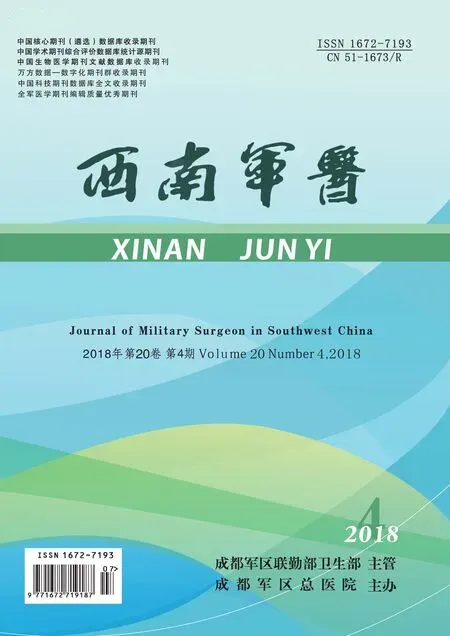肝巨噬细胞与慢性肝脏疾病的研究进展
林云霞,何晓彬
肝脏是多功能器官,在机体的代谢、生物合成、分泌及解毒等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在不同的微环境中,如炎症、肿瘤、感染,巨噬细胞表现出多样性表型它可以跨越从抗炎到促炎症表型的光谱。在不同细胞因子作用下极化成M1 型巨噬细胞和M2 型巨噬细胞。M1 型巨噬细胞又称经典活化巨噬细胞(CAMs),M2 型巨噬细胞又称替代活化巨噬细胞 (AAMs)。通常CAMs在清除病原体、促进炎症反应并引起肝脏损伤、杀肿瘤方面起作用。而AAMs在吞噬寄生虫、抑制炎症和肝脏损伤修复、促进肿瘤生成中起作用。本文主要了解肝巨噬细胞在慢性肝脏疾病中的发生发展,为认识及治疗肝病开辟新的视野。
1肝巨噬细胞极化通路
巨噬细胞极化是调节炎症反应的重要机制。相关研究表明,参与巨噬细胞极化存在以下三种信号通路:
1.1JAK/STAT信号通路JAK/STAT信号通路与各种细胞因子诱导的各种生物应答有关,并受各种内外环境的刺激因素调节,从而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1]。研究者[2]提出干扰素-γ(IFN-γ)能通过诱导JAK-STAT1途径诱导巨噬细胞向M1极化,而IFN-α/β与IFN-γ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它能抑制STAT1 磷酸化,抑制M1极化。Fang等[3]提出转录因子EB(TFEB)能调节巨噬细胞肿瘤微环境中的极化,减少了MHC-II和共刺激分子CD80的表达,TFEB下调通过增强STAT3激活导致巨噬细胞M2极化。同样IL-4、EPO、鞘氨醇1-磷酸等物质可通过JAK/STAT6通路向M2细胞极化[4-5]。
1.2PI3K/Akt信号通路 研究表明Akt1和Akt2分别作用于M2和M1极化。Ren等[6]提出睾酮在Akt磷酸化中起双重作用,它抑制Akt2并增强Akt1磷酸化,它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和Akt信号传导途径诱导巨噬细胞向M2极化。此外,细菌、LPS、DSS分别诱导的感染、内毒素性休克、结肠炎均可激活PI3K,分别调节Akt1与Akt2的活化[7]。
1.3JNK信号通路JNK信号通路属于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s)超家族。MAPKs是细胞活动的关键调节剂,它有利于炎症的发生[8]。有研究[9]表明在胰岛素抵抗的发病机制中,miR-27a是通过JNK/NF-κB通路调节巨噬细胞极化,促进M1巨噬细胞极化。另外有研究证实犬尾杆菌可以通过上调JNK的活性来促进M2极化表型[10]。
2肝巨噬细胞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是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系统性炎症,它是最常见的慢性肝脏疾病。从简单脂肪变性开始,可进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硬化和肝癌[11]。炎症巨噬细胞可以通过几种机制促进NAFLD的疾病进展,包括影响肝细胞脂肪变性,吸引炎症淋巴细胞,刺激血管生成或促进肝纤维化[12-13]。
尽管肝巨噬细胞在肝细胞损伤后被激活,但它们也作用于肝细胞并直接影响疾病进展。在NAFLD的发病中,已经证明在CAMs的信号传导中,微小RNAmiR-155与小鼠脂肪性肝炎有关,它能诱导参与脂质代谢的基因表达,M1巨噬细胞也可直接促成肝脂肪变性[14]。He等[15]提出异丙内酯能通过抑制LPS诱导的CAMs激活的NF-κB通路。类似地,由炎性介质激活JNK-AP-1信号传导导致JNK的磷酸化和活化,最终刺激炎症靶基因的转录,促进NAFLD。而甲基苯丙胺(一种强力上瘾的精神兴奋药)通过促进CAMs的极化和炎症反应导致脂肪变性[16]。最近Johnson等人[17]提出炎症小体(NLRP3)在NAFLD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中的角色,脂肪酸代谢能通过NLRP3炎症小体在肝巨噬细胞的极化发挥重要作用。总之,炎症相关信号可以促进CAMs释放炎性因子,从而增加脂质代谢及胰岛素抵抗。
此外,2型免疫在炎症和脂肪代谢的发病机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细胞因子如IL-33和IL-25通过Th2细胞间接诱导AAMs。IL-33参与多种肝脏疾病的发生过程,包括病毒性肝炎、肝脏纤维化、脂肪肝、肝癌,与ST2L(IL-33受体的亚基)结合,诱导下游IL-4/IL-13启动2型免疫[19]。同时有文章指出IL-33抑制小鼠结肠炎和通过增强AAMs极化来促进糖尿病小鼠的伤口愈合[20]。Song等[21]也发现IL-25与肥胖和脂质代谢相关,可将巨噬细胞分化为M2表型,释放游离脂肪酸,从而促进脂肪动员,减轻肝脏脂质积累及NAFLD患者的体重。
3肝巨噬细胞与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的特征在于活化的肌成纤维细胞的损伤和细胞外基质(ECM)的沉积,最终导致瘢痕形成和器官衰竭。纤维化的病理生理主要是慢性肝损伤,包括慢性酒精消耗,化学诱导的肝细胞损伤和病毒感染。在慢性肝损伤中,肝纤维化被认为是一个动态及可逆的过程,包括以下两个:⑴ECM降解及纤维化瘢痕的恢复;⑵肝祖细胞活化的肝细胞群的再生。
肝巨噬细胞在慢性肝损伤中起重要作用,它是肝纤维化发病的中心环节[22]。然而,巨噬细胞具有基因和功能异质性。M0和M1骨髓源性巨噬细胞(BMDM)均显着改善肝纤维化,调节微环境。M2巨噬细胞对肝纤维化无效[23]。M1表型的特征是表达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致使抗纤维化活性。相比之下,M2巨噬细胞表达高水平的抗炎细胞因子,促进组织重塑。
目前,有几种可能的方法可将巨噬细胞的关键功能运用于抗纤维化治疗中。例如,通过使用目标纳米粒子来调节巨噬细胞的极化或功能。有文章显示[24],在肝纤维化模型小鼠中,脂质体递送的纳米粒子能显示出一些抗纤维化功效,但是该方法运用于临床之前仍需优化靶向特异性。另一种方法是抗炎巨噬细胞的过继转移抑制纤维化小鼠模型。此外,Ewelina等[25]研究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能重塑窦状脉管系统,消除了小鼠肝纤维化。骨髓细胞中失活的缺氧诱导因子(HIF)可使VEGF表达增加,加速基质降解并降低了CCl4攻击后的肌成纤维细胞数。因此,在巨噬细胞中促进HIF-VEGF信号轴代表了治疗肝纤维化的有希望的治疗途径。
4肝巨噬细胞与肝细胞癌
肝细胞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癌症(包括HCC)是从慢性炎症部位的出现。炎症能促进肿瘤生长和发展[26]。肿瘤微环境主要由炎症细胞形成,有利于肿瘤的生长和发展,它包含多种浸润性免疫细胞,包括成纤维细胞,脂肪细胞,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影响肿瘤进展的炎性细胞[27]。其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激活与肿瘤的进展密切相关。它在肿瘤进展中发挥双重作用:M1样巨噬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M2样巨噬细胞促进肿瘤的进展。
已经提出TAMs通过几种机制促进肿瘤的进展,包括抑制免疫激活,促进细胞外基质重塑,促进血管和肿瘤生长以及增强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28]。关于HCC,有学者指出TAMs通过“骨髓”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形成来源抑制细胞(MDSC),从而抑制T细胞应答并提供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同时,我们发现TAMs分泌IL-8,增加细胞存活和转移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IL-8增加miR-17簇的表达,包括miR-18a和miR-19a。它可以促进HCC转移和细胞生长,并与HCC患者的转移和长期存活能力相关[29]。此外,血管紧张素II亚型受体1a(AT1a)也参与HCC转移,它的形成与转移区胶原沉积相关,依赖于AT1a信号传导。
TAMs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IL-1β,IL-6,集落刺激因子-1(CSF-1)以及作为趋化因子配体18(CCL18),VE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促血管生成生长因子,其促进肿瘤生长[30]。已经证明在HCC中TGF-β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EMT)对于癌细胞传播至关重要[31]。而来自AAMs的CCL18促进HCC进展,因此,靶向CCL18可能为临床治疗HCC提供有益的效果。研究证明CSF-1及其受体CSF-1R也调节巨噬细胞的分化和功能,促进肿瘤的生长[32]。令人惊讶的是,巨噬细胞也参与肿瘤监测。在没有慢性肝损伤的情况下,致癌基因诱导的衰老肝细胞分泌CCL2,其吸引单核细胞衍生的巨噬细胞。CCR2巨噬细胞与T细胞共同清除衰老肝细胞,从而防止HCC发展[33]。
研究证明,TAMs是癌症免疫治疗的靶点。目前,将治疗药物递送到促肿瘤的M2样TAMs中是有挑战性的。而将TAMs作为抗癌药物的载体运用于癌症治疗是最有前途的策略之一。据报道,巨噬细胞可以内化金纳米壳,并将其递送到肿瘤的低氧区,诱导巨噬细胞周围的癌细胞死亡[34]。Yuan等[35]开发了M2型TAMs双靶向纳米颗粒(M2NPs),其结构和功能受到与M2pep(M2巨噬细胞结合肽)连接的α-肽的控制,通过在M2NPs上加载抗刺激因子-1受体(抗CSF-1R)小干扰RNA(siRNA)来特异性阻断M2样TAMs的生存信号。同时,研究证明小分子治疗剂可以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有力工具。化合物9#,一种新的JAK2抑制剂,可以抑制巨噬细胞中的JAK2-STAT3信号传导,并将巨噬细胞引导至促炎症(M1样)表型,还能有效增加CD4 +和CD8 +T淋巴细胞和抗肿瘤活性,从而有效抑制肿瘤生长。
5小 结
过去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肝巨噬细胞的看法,它是肝脏结构的“关键”。肝巨噬细胞在诸多方面与肝脏疾病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肝巨噬细胞具有维持人体体内平衡和识别损伤的核心作用。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肝巨噬细胞的理解与认识将会更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寻找更有效的疾病治疗靶点及治疗药物,采取更好的治疗方法阻止肝脏病变,改善患者的症状及增加生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