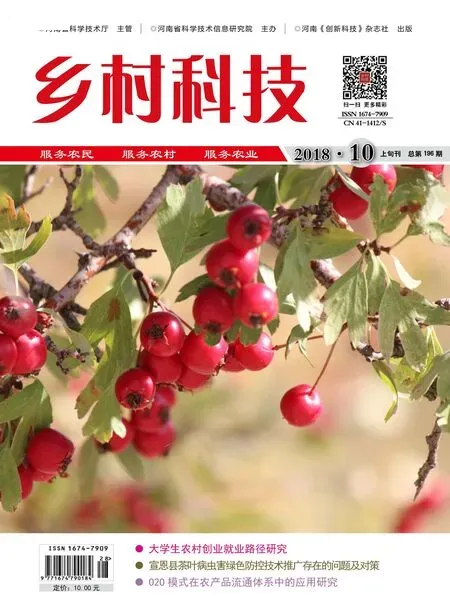基于树种结构调控的松材线虫病防控技术
吴建华 蔡文经
(抚州市临川区生态公益林场腾桥分场,江西 抚州 344000)
松材线虫是一种多点入侵型松林虫害,其中松褐天牛是主要传播媒介。而在疫木的运输过程中,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松材线虫病会出现扩散,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影响。我国自1982年发现首例松材线虫病开始,截至目前,该病虫害已经蔓延至我国16个省300余个县级疫区,致死率和松林毁灭率极高,成为松林培育中破坏力巨大的病虫害类型。
1 传统松材线虫病防控难点
1.1 疫情发现及处理困难
在理论分析当中,一般生物学家认为,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具有高度随机性。在以往的发病机理中,人为诱发的松材线虫病传播确实具有随机性,松材在发病初期无法被及时发现。此外,大部分松材线虫病具有发病初期的潜伏浸染特征,松林发病时会表现出与周边气候环境及松树自身抗性相关的特点,因此监测难度会大幅度提升。
在松材线虫病大规模发病阶段,由于其发病特征具有多样性,同时受制于林间监测技术手段单一、落后,难以精确判断和处理绝大多数病情。例如,在以往的疫区中,由于松材线虫病表现与马尾松毛虫、松枯梢病甚至雷击十分类似,监测人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并采取处理措施。
1.2 松林树种结构存在问题
作为我国主要的造林树种,松树在我国林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广东省等南部地区为例,这些南方省份受到气候的影响,以马尾松作为荒山造林的优选树种,该树种通常以人工栽植与飞机播种2种方式相结合实现植树造林。但是,随着马尾松种植范围的逐渐扩大,造成目前我国南方大部分省份的树种结构过于单一,这种单一、不协调的树种结构对于松林虫害防控而言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十分容易遭受诸如松褐天牛、马尾松毛虫等害虫的侵入,造成叠加伤害。
2 基于树种结构调控的松材线虫病防控策略
2.1 搭建精准疫情监测体系
松材线虫病的防控效果与疫情监测的精准性和及时性密切相关,但是我国缺乏精准度高的疫情监测体系,难以实现对于疫情的第一时间防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部分林业部门已经形成了专项自动化监测系统,利用自动系统平台优势,提高松材线虫监测能力。在实际应用中,专项自动化系统需要包含有松材线虫数据信息、无人侦察机及诱虫灯等硬件设备,利用硬件设备进行林场内部的信息采集,并开展针对疑似患病松材的疫情盘点,从而借助系统完成分布范围的规划。在系统内部,借助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可以将已经采集到的样本信息以数据形式进行整合,从而帮助监测管理人员对当前某一阶段的林场内松材线虫病的发病可能、已发病状态、发生程度、流行动态等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完成疫区与非疫区之间的划分,为提高疫情防控能力做好基础准备[1]。
2.2 非疫区树种结构调控防治技术
针对非疫区,应将防范和统筹兼顾作为基本原则,利用生态系统建设,实现全过程管理,最终达到合理调控有害生物、从根源避免松材线虫病的目的。实际上,松林管理需要将树地适宜性作为前提条件,通过调控树种结构的方式,合理回避传统林业中存在的树种单一性,利用多元化的树种结构,提高松材线虫病抵御能力。以南方地区松林为例,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主要种植树种为马尾松,部分南部地区还种植了湿地松。因此,我国南方地区树种结构调控应基于马尾松或湿地松的生长特性和自然松林的演化交替规律,以森林景观格局作为出发点,结合树种之间的生克关系,利用多层次、多树种的改造方式,因地制宜配置树种,避免传统单树种松林对于病虫害缺乏抵抗力[2]。例如,在林场景观建设中,可以利用松林碎片化的方式,加强其他类型植物隔离带的作用,并借助隔离带优势,打造物理隔离和化学驱逐带,增强森林对于松林线虫病的抵抗力。
2.3 疫区松材线虫病防控措施
与非疫区的积极防控、合理调配策略不同,在已经出现松材线虫病的松林疫区应采用积极主动的治理策略,致力于将疫区虫害所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相关防控经验显示,面对实际疫情,应建立起封闭治理的长效机制,通过隔离疫区控制发病范围。与此同时,还应针对疫点采取加强的根除措施,利用科学的防控策略,清除疫情范围内的病害,避免疫木出现流失。其基本原则为“就地解决,及时清理”。在疫情出现初期,松林内部患病松树植株较少,自动化监测系统第一时间发现后应第一时间皆伐松林,以避免疫木疫情的扩散。对于疫情扩散较为严重的疫区,应根据松林的具体情况制订处理方案。例如,疫区内部松树植株较少、相对分散,可以采用皆伐策略,进行全面处理;对于植株密度较高的疫区,需要及时采用封闭治理与隔离治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套种方式种植其他类林木,以此来逐渐取代原有的松林,实现针阔混交林种植。此外,还应在套种过程中喷洒嗜麦芽糖寡养单胞菌,以提升松林生物防治力度[3]。
3 结语
松林线虫病在我国对于松林的危害极大,在以往的林业管理过程中,缺乏专项的疫情监测手段及疫情处理措施,导致疫情出现至今30年来始终呈现出扩大势态。对于林业管理来说,需要结合具体的环境气候特点,采用林区混合结构策略加强松林内部树种结构调控,从而实现对于松林线虫病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