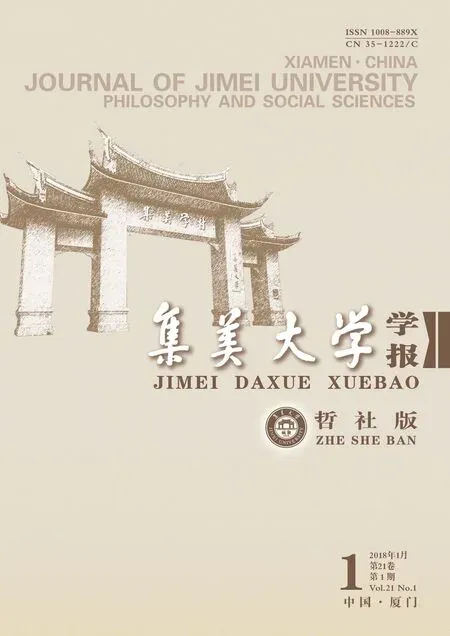印第安口头叙事传统与创伤书写
——厄德里克《拉罗斯》解析
陈金星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一、引 言
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drich,1954— ),当代美国著名的印第安裔女作家。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16部小说、6部儿童小说、3部诗集、2部纪实性作品及一系列短篇小说,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协会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拉罗斯》(LaRose)是厄德里克2016年出版的最新力作。《拉罗斯》是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第3部。其故事主要地点为位于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虚构的镇子——普鲁托镇。小说采用多线叙事,其主线讲述了兰德洛·艾伦打猎时射中了邻居彼得5岁大的儿子达斯蒂,为了补过,他把自己的小儿子拉罗斯交给彼得一家抚养,彼得一家的家庭创伤逐渐愈合。小说的副线之一讲述第一代拉罗斯的传奇经历,另一条副线讲述兰德洛与罗密欧的恩怨。
“创伤”(trauma)是理解《拉罗斯》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创伤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书写创伤及幸存者的故事,这既是厄德里克创作中一贯的主题,也是当代印第安作家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一个主题。厄德里克指出:“当代本土裔作家有一个与其他作家不同的任务……鉴于巨大的损失,在保护与庆祝文化内核留存在灾后复苏的同时,他们必须讲述幸存者的故事。”[1]23-24在现实生活中,厄德里克曾经历过巨大的心理冲击。1991年,她的养子因车祸丧生。她曾经的丈夫多利斯在1997年自杀身亡。书写创伤及幸存者受伤之后的生活,成为厄德里克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小说《羚羊妻》就书写了遭受白人袭击的印第安村庄的历史创伤、丧女之痛与丧夫之痛的创伤及幸存者走出创伤的故事。“正义三部曲”之一《鸽灾》书写了普鲁托镇四个印第安人遭受白人私刑的历史创伤,“正义三部曲”之二《圆屋》则书写了普鲁托镇部落人口书记员杰拉尔丁遭受白人男子强奸后的家庭创伤。书写创伤,某种意义上成为厄德里克渡过心理危机的一种自救方式。
目前,国内尚无研究《拉罗斯》的相关论文,国外与《拉罗斯》相关的研究资料也只限于访谈与介绍性书评。结合文学创伤理论视角与印第安文学传统,可以发现《拉罗斯》这部小说分别展现了家族创伤、家庭创伤、个人创伤的形成与终结,还可以发现其小说叙事融合了印第安口头叙事传统。与当前一些英美创伤小说相比,《拉罗斯》具有传奇性与哀而不伤的特点。
二、拉罗斯家族的历史创伤
所谓“创伤”通常指对某种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心理体验,遭受创伤者会出现延时的不由自主的重复性幻象或其他困扰性现象[2]11,比如战争创伤者梦中见到死去战友的脸庞。从心理学来看,第一代拉罗斯临终前见到“滚动的头颅”即是一种由心理创伤引发的梦靥性幻象。文学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指出,创伤事件的意义并非直接明了的,再次回顾创伤史不是消除它而是为了理解而重置场景。[2]11《拉罗斯》糅合神话叙事而讲述拉罗斯家族创伤史正是为了彰显家族创伤的文化意义。厄德里克曾在访谈中透露,祖上确有一位家庭成员叫拉罗斯,在1897年龟山户口统计中有名可查。[3]在小说《拉罗斯》中,共有五代拉罗斯,前四代为女性,第五代为男性。其中叙述较详细的要数第一代与第二代拉罗斯的故事。
小说第一章《两家:1999—2000》设置了两条情节线*文中引用《拉罗斯》为笔者翻译,原文出处见参考文献[4]。:一条是千禧年前后兰德洛与彼得两个家庭的故事,另一条是第一代拉罗斯的逃亡与求医经历。第一代拉罗斯的母亲明克(“水貂”)将女儿卖给了贸易点商人麦金农,麦金农试图侵犯拉罗斯,拉罗斯与贸易点的年轻伙计沃尔夫雷德一起逃跑。这条情节线具有神话色彩。女祖拉罗斯因害怕污辱而裸身卧雪求死,但得到另一世界的神灵照顾。神灵给她穿上衣服,披上一条新毯子,并说:“当这种事发生可以呼求我,这样你可以活下去。”[4]63其后,拉罗斯与沃尔夫雷德一起逃离贸易点。他们的逃离对应了“滚动的头颅”神话故事,具有神秘恐怖色彩。“滚动的头颅”是北美印第安神话中常见的一种母题,版本众多,其共同点是叙述一个无身人头追逐或陪伴他人。《拉罗斯》第四章就讲述了一个“滚动的头颅”故事版本。小说第一章描述,麦金农的头在雪上不知疲倦地滚动着,它的头发着火,火焰欢快地闪烁。有时它撞到一棵树上并呜咽,有时它用舌头、脖子或耳朵拍打着推进,有时它飕飕前进几英尺接着后退,在失望中呜咽着尴尬地前进。在逃亡的途中,沃尔夫雷德生了病。神奇的是,靠着一只飞来的鼓,拉罗斯治好了沃尔夫雷德的病。病好之后,沃尔夫雷德还伴随着拉罗斯的歌声灵魂出游。他们飞到密林上空,脚下是一座离他们的茅屋大约两天路程的村庄。《拉罗斯》中,“滚动的头颅”可以视为白人文化的象征物,头颅的追逐可以视为对印第安文化的追逐。小说还通过描写第一代拉罗斯上寄宿学校批评了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拉罗斯在寄宿学校一呆就是6年,在学校不能讲印第安语,穿着紧身胸衣却一点也不暖和,吃咸肉与白菜,并且老是放屁。她还习惯于同学因染上流感、猩红热、结核病等疾病而死亡。
第一代拉罗斯也染上结核病,但是她顽强地活着。她与沃尔夫雷德结合,生下四个儿女,最终因结核病发作而死。死前,麦金农的头颅反复出现。死后,她的遗体无法入土为安,不时被展览。第二代拉罗斯继续遭受同化政策的压迫。她学会了给白人干家务活,她知晓了种族等级:白人、黄种人、黑人、野蛮人,印第安人最低等,她学会了白人的穿着、饮食、言行举止。拉罗斯家族的创伤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民族创伤。多年以后,遗体被归还且亲子隔离的寄宿学校停办,这才表明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略有改善。迟来的公道得以体现,家族创伤不再延续。
三、诺拉的家庭创伤及其愈合
达斯蒂的去世,给诺拉一家留下了严重的家庭创伤。达斯蒂去世的那天,其母诺拉向他叫吼,达斯蒂不敢回家。达斯蒂死后,诺拉负疚在心,怀有自杀倾向。诺拉与女儿麦琪的关系恶化:在做弥撒的时候,诺拉打了麦琪一巴掌;吃豆子的时候,诺拉也嫌麦琪吃相难看,却被女儿反唇相讥。麦琪觉得自己是一只受伤的动物。弟弟死后,麦琪的笑不再是像铃儿清脆的笑,她的笑变成一种嘲笑,为伤心事笑而不是为有趣的事物发笑。小拉罗斯被送到诺拉家之后,诺拉家的成员状况慢慢好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关于诺拉的叙事是碎片化的,散见于各个章节,不留心的话不易发现,这一点也是创伤小说的常见特点。拉卡普拉指出,应对创伤存在着三种方式:逃避、复现或展演及克服与应对[5]193。诺拉的心理也经历了从创伤展演到创伤克服的过程。
小拉罗斯来自一个治疗师家族。他自身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不伤害小动物,他不说别人的坏话。他被送到诺拉家之初,也遭受了一些心理挫折。之后,诺拉的丈夫彼得与兰德洛决定两家共同抚养小拉罗斯。小拉罗斯的经历具有“梦幻故事”的神奇色彩。所谓“梦幻故事”指一些萨满经历超自然幻象的故事,这些故事以J.哈利法克斯的《萨满之声:梦幻故事概览》与苏族印第安人“黑麋鹿”口述的《黑麋鹿如是说》最为著名。《拉罗斯》中,小拉罗斯看见他界灵魂的梦幻故事共两处。小说第4章《1000记扣杀:2002—2003》先叙述小拉罗斯在树林与他界灵魂的首次交谈。一名女性祖灵告诉他:“到时候我们就会教你。”[4]211在树林,小拉罗斯还与达斯蒂的魂灵一起玩动漫玩具。另外一处梦幻故事位于第五章《聚会》结尾,在霍利斯的毕业聚会上,山姆用奥吉布瓦语吟诵了一段祈祷文,小拉罗斯凝神倾听。他注意到他界灵魂们在聚集,并开始讲话:“我们爱你们,不要哭”“悲伤吞噬时间”“耐心”“时间吞噬悲伤”[4]371
小说还叙述了小拉罗斯的拯救行动。麦琪见到母亲穿戴整齐试图上吊自杀,她答应母亲不透露此事,诺拉才走下自杀用的椅子。麦琪告诉小拉罗斯:诺拉打算自杀。经过一番思考,小拉罗斯展开了他的拯救行动。他把家里的双面剃须刀以及锋利的肉片刀与厨刀都收起来,并把彼得枪里的子弹也收起来。他还扔掉了农药、老鼠药、绳索。正是这种预防措施救了他的生父兰德洛一命。因为其后罗密欧告诉彼得,达斯蒂的死因是由于流血过多而非中弹,而兰德洛阻止了诺拉及时救治。彼得听信了罗密欧,怒气冲冲地携枪邀请兰德洛打猎,正当他试图射杀兰德洛时,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当小拉罗斯的母亲艾默琳决定留下小拉罗斯并不再住在诺拉家后,小拉罗斯说服了艾默琳让他继续住在诺拉家。正是小拉罗斯的支持以及麦琪对母亲态度的改变,诺拉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诺拉与麦琪原本恶化的母女关系也最终得到了改善。诺拉与彼得去观看麦琪的排球比赛,为麦琪呐喊助威,麦琪深受感动。麦琪曾被一帮自称“恐怖四人帮”的男孩性骚扰,小拉罗斯试图为麦琪复仇,年幼的他却被心狠手辣的巴基打得灵魂出窍。但他的勇敢行为也赢得了“恐怖四人帮”其他成员的尊敬。
在叙述诺拉家庭创伤与愈合的同时,厄德里克也较为详细叙述了麦琪的成长。这延续了她小说创作中常见的成长母题。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创伤主题与成长主题常常交织互补。《羚羊妻》书写了卡丽的孪生姐妹狄安娜的夭折及卡丽之后的成长。卡丽确信印第安文化内核将永远留存,并最终明白自己的任务是理解与讲述[6]220。《鸽灾》中,埃维莉娜的外公穆夏姆告诉她印第安人遭受白人私刑的往事。穆夏姆讲述的这桩创伤史对埃维莉娜多少产生了影响,她开始痴迷家族关系[7]87。之后,《鸽灾》还以埃维莉娜的视角叙述了她的大学生活与成长迷惘。《圆屋》以少年乔的视角叙述了母亲杰拉尔丁遭受白人强奸的创伤,并叙述了乔的成长与族裔身份建构历程。[8]101-106《拉罗斯》中,麦琪是个叛逆的女孩。起初,她与母亲诺拉相处得并不融洽。由于小拉罗斯的到来,她的成长得到了斯诺与约瑟特两姐妹的帮助。不过,她的成长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她过早地偷尝了禁果,且未采取避孕措施。以至于祖灵预言:“那个麦琪,要当心她。”[4]371
四、罗密欧的创伤及其报复
罗密欧是一个颇具喜剧感的反面角色。他趁别人上教堂偷汽油,他偷药房的药,参加葬礼为的是饱餐一顿。有趣的是,有一次他服用了偷来的药,整夜拉肚子,皮肤滚烫刺痛、恶心,却又处于性兴奋状态。罗密欧心中暗恨兰德洛,源于他的童年创伤。他恨兰德洛夺走了他的所爱艾默琳,他恨兰德洛造成自己的脚伤。原来罗密欧幼时曾与兰德洛读过寄宿学校,他们一起逃过学。在明尼阿波利斯,他们落入一个贼窝。在逃脱贼窝时,罗密欧摔断了腿。之后,兰德洛向警察寻求帮助,但贼伙已带着罗密欧逃离。最终,罗密欧落下腿脚不便之疾。其后,罗密欧与兰德洛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至于罗密欧对兰德洛拔刀相向。罗密欧为了给儿子攒一笔钱,电视音响坏了也不愿换。他自负可通过嘴唇的蠕动与字幕明白新闻的真相。毋庸置疑,他很聪明。为了报复兰德洛,他偷了一份法医报告。他根据偶然听来的只言片语并依据己意解读法医报告,且自认为找到了达斯蒂死亡的真相。他告诉彼得:兰德洛并没有打中达斯蒂却击中了他坐的树枝,达斯蒂死于流血过多,且如果不是兰德洛拦住了诺拉或者他没有逃跑而是为达斯蒂止血的话,达斯蒂本可以获救。彼得相信了罗密欧的解释,愤怒的他携带着猎枪试图结果兰德洛的性命。若非小拉罗斯事先卸掉了彼得枪中的子弹,兰德洛的性命不堪设想。
自觉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的罗密欧与神父特拉维尼斯展开了一番一对一的谈话。他情不自禁地向神父吐露他过往的委屈,接着再次推销他对达斯蒂死因的解释。不过,特拉维尼斯神父并未相信他的解释。厄德里克是带着幽默、同情、微讽的语调叙述罗密欧的思想行为的。由于罗密欧的行为并未导致兰德洛的死亡,故全书以聚会结束。祖灵也预言,罗密欧的儿子霍利斯与兰德洛的女儿将会成为幸福的一对,这正如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结尾,米兰达与斐迪南的相爱化解了上一辈的仇恨。因此,罗密欧的形象更多地带有喜剧色彩。
罗密欧善于偷窃与欺骗的特点与印第安民间故事中的恶作剧精灵颇有类似之处。恶作剧者形象在世界文化中广泛存在,如西非的恶作剧者阿南瑟(Ananse)、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东非的恶作剧者兔子、鬣狗、鸟、蛇、老女人等。印第安民间故事中的恶作剧者通常是一只兔子、一只乌鸦、一只郊狼或一个老人,它们介于神人之间,有时为世界的创造者,有时为世界的毁灭者,善于欺骗,但不时吃苦头。恶作剧者的行为伴随着欢笑、幽默与讽刺[9] Ⅸ-Ⅹ。罗密欧的报复是假借正义之名的私人报复,他的报复实际上是一种对正常秩序的破坏。像恶作剧者的失败那样,罗密欧的失败报复引人欢笑,同时也强化了读者对世界秩序的信念。
研究者已注意到,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四部曲”小说中,纳纳普什与露露是具有恶作剧者(trickster,或译“千面人物”“变形者”)特点的文学形象。厄德里克继承了恶作剧者传说的幽默感。在小说《羚羊妻》中,弗兰克丧失了幽默感,叙事者之一卡丽以为:“现在他是唯一没有幽默感的活着的印第安人了。”[6]115卡丽的观点其实也是隐含作者的观点:印第安人是具有幽默感的民族。厄德里克是一位有意识运用幽默的作家。据她解释:“本土印第安人普遍存在的一件事物是幸存者幽默——幽默让你能够与不得不共存的事物共存。你不得不调侃主导你生活与家庭的人。”[10]144在小说《痕迹》中,纳纳普什带着幽默的口吻叙说自己如何死里逃生:“在疾病之年,我是最后一个幸存的,我通过讲故事拯救了自己……我通过讲话好转。死神无法插一句话,变得沮丧,走开了。”[11]46纳纳普什的原型是契帕瓦部族神话中的恶作剧者纳纳博卓。如同纳纳博卓一样,纳纳普什也是一位滑稽幽默的人物。在饥荒之年,他以地鼠肉为食,并称之为“印第安牛肉”,声称自己给他们打上了牌子。除了《痕迹》,厄德里克还在《博戏宮》《蓝松鸦之舞》《甜菜女王》等作品中运用了幽默笔法。她透露,除非作品包含了某些有趣的东西,否则就无法感觉到创作了一本书。她曾在创作《拉罗斯》的笔记本中写道:“问题。大问题。在这一手稿里没有幽默。”[12]可以看出,《拉罗斯》中的幽默叙事是厄德里克有意追求的最终结果。
五、结 语
创伤书写是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她的小说杂糅了现代小说叙事艺术与印第安口头叙事艺术。她的“正义三部曲”故事地点皆为普鲁托镇,这显示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影响,《爱药》《羚羊妻》《鸽灾》等小说的多角度叙事也显示了福克纳的影响。不过,厄德里克的小说也继承了印第安口头叙事传统。《鸽灾》与《圆屋》中穆夏姆的口述就显示了这一点。
厄德里克的新作《拉罗斯》延续了之前杂糅性叙事策略,这部小说细致展现了幼子意外过世引发的家庭创伤、遭受白人文化侵食与同化的家族创伤、肉体创伤引发的精神创伤与私人报复。小说还通过对印第安传统治疗方式、灵视幻象、聚会的具体描述,展现了印第安文化的魅力。与以往多角度叙事的小说不同,厄德里克在《拉罗斯》中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并设置了多条情节线。第一代拉罗斯的逃离与小拉罗斯的灵视幻象的叙述继承了印第安民间故事的传奇性,罗密欧的形象刻画则继承了印第安恶作剧者故事的幽默感,因此,小说《拉罗斯》显得摇曳生姿,引人入胜。2017年3月,凭借小说《拉罗斯》,厄德里克再次揽获美国书评家协会奖,[7]1这也是学术界对其创作的再次肯定。
[1]LOUISE ERDRICH.Where I ought to be: a writer’s sense of place[J].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85(1):23-24.
[2]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EMILY G TEDROWE. The Sunday Rumpus interview: Louise Erdrich[EB/OL].(2016-05-29)[2017-09-08].http://therumpus.net/2016/05/the-sunday-rumpus-interview-louise-erdrich/.
[4]LOUISE ERDRICH. LaRose[M].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6.
[5]DOMINICK L. History, theory, traum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6]LOUISE ERDRICH. The antelope wife[M].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7.
[7]路易丝·厄德里克.鸽灾[M].张廷佺,邹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8]朱荣华.《圆屋》中的文化创伤与印第安文化身份的建构[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2):101-106.
[9]PAUL RADIN. The trickster: a study in American indian mythology[M].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6.
[10]CHAVKIN ALLAN, NANCY F CHAVKIN. Conversations with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C]//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11]LOUISE ERDRICH. Tracks [M]. New York: Haper Collins, 1988.
[12]LAURIE HERTZEL. Minneapolis author Louise Erdrich finds writing humor is the “hardest thing”[EB/OL].(2016-05-05)[2017-11-21].http://www.startribune.com/minneapolis-author-louise-erdrich-on-family-justice-resilience-and-humor/378195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