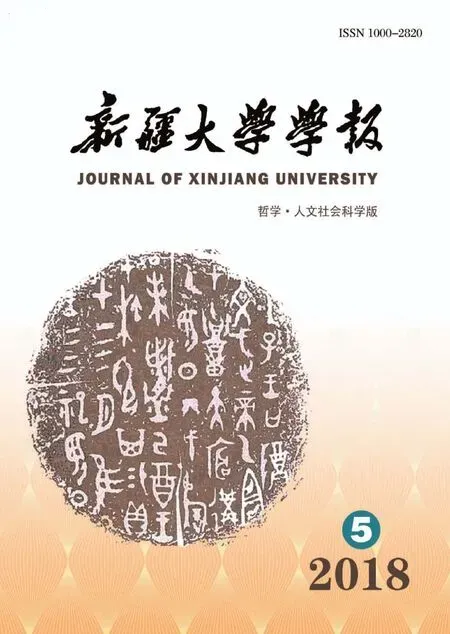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诗画分界问题*
杨 桦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2)
一
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2)个性中具有一种天然的天平气质,在她的意识天平上,各式各样的两极构成均取得了一种巨大张力下的内在平衡,这其中包括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平衡、生活与艺术的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创作与批评的平衡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致力于考察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天平上的这样一组两极关系:文学与视觉艺术。在20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文艺思潮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归属于现代主义阵营,在这一阵营内部,18世纪启蒙时代由德国思想家莱辛正式提出的诗画分界问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启动,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这两大领域,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都面临着如何跨界合作、如何划界合作和如何划界自立的双重难题,弗吉尼亚·伍尔夫深度介入到这一新时代的升级版诗画分界问题当中,以她特有的方式做出了极富启发性的思想回应。
在18 世纪启蒙时代,作为德国第一伟大艺术史家的温克尔曼以对希腊雕塑的观照作为基点,推出了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经典命题。温克尔曼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视觉艺术,对于这一领域之外的希腊文化向度极少涉猎,不过,他仍旧自信地宣称:“希腊雕塑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也是繁盛时期希腊文学和苏格拉底学派的著作真正特征。”[1]对于温克尔曼的这一论断,德国思想家莱辛明确表示反对,在《拉奥孔》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诗画分界问题。
按照莱辛的说法,“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一命题揭示了希腊视觉艺术的美的原则,却并不适用于希腊诗歌,希腊诗人热衷于表现人类痛苦和哀伤的情态,哪怕这样的描写与美的原则相冲突也在所不惜,美对于诗歌而言不像对于视觉艺术那样基本和迫切,而情感表现对诗歌的意义则要比对视觉艺术的意义大得多。对于莱辛的思想主旨,韦勒克做出了这样的概括:“莱辛反对温克尔曼关于希腊视觉艺术与文学的同一化处理……在文学方面坚决主张突出情感效果,在美术方面则禀持一种非常抽象的形体之美的理念,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情感表现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2]凭借着对温克尔曼理论的批判,莱辛划定了诗歌与视觉艺术的界限,事实上确立了诗歌相对于视觉艺术的等级优越性,其理由在于诗歌侧重的情感表现与现实人生密不可分,而视觉艺术则易于偏向一种纯粹形式之美,这是出于启蒙人生主义立场的一种价值评判。站在视觉艺术研究的角度上看,“莱辛使美学脱离了对于主题的严格关注,转而聚焦于空间存在的基本形式要素”[3],而形式问题恰好成为一百多年以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的核心问题。
二
在欧洲文艺史上,从17世纪起,法国开始引领视觉艺术的潮流,19 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心无疑是在巴黎。以巴黎为中心,塞尚、高更、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推出了层出不穷的视觉艺术新理念,这其中尤其以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的塞尚贡献最大。按照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说法,“塞尚已经不再把任何传统画法看成理所当然的画法,他已经决心从涂抹开始,仿佛在他以前根本没有绘画”[4]。相比于以塞尚为首的欧陆现代主义艺术变革,英国美术界的整体表现偏于保守,以写实为主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仍然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最早做出积极反应以文化团队形式大力引进和效法欧陆现代主义艺术新理念的是20世纪之初成立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
1904年,英国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莱斯利·斯蒂芬逝世,他的两个女儿瓦妮莎·斯蒂芬和弗吉尼亚·斯蒂芬搬至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 号的一处大宅开始了新生活。从幼年时代开始,瓦妮莎和弗吉尼亚就锁定了各自的文化领域,前者钟情绘画,后者醉心文学。在布鲁姆斯伯里斯蒂芬姐妹周围,逐渐聚集起十几位各大文化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形式松散但又有思想文化同盟性质的小圈子,这便是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斯蒂芬姐妹分别嫁给了小圈子中的两位成员,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和政论家伦纳德·伍尔夫,因此改称为瓦妮莎·贝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现代主义的主要阶段,新的视觉语汇正在改变文学与文化文本”[5]。现代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视觉艺术的活跃程度和新观念影响力远在文学之上,或者说,领先于文学界一大步,而这一态势也清晰地体现在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建构之中。1905年,瓦妮莎·贝尔在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首创了星期五俱乐部,定期讨论前沿视觉艺术问题,奠定了视觉艺术在这一精英知识分子团体中的中心地位。瓦妮莎·贝尔属于英国自觉效法以巴黎为中心的欧陆现代主义美术的第一代画家,其画风偏向于高更风格和马蒂斯风格的一种合体。瓦妮莎·贝尔的绘画作品一般采用大色块平涂的手法,明显出自高更的谱系,不过,高更绘画中与象征派诗歌关联密切的文学叙述性因素在她这里极大地减弱,高更绘画中的宗教主题在她这里几近消失,色彩和构图的形式构成成为关注的绝对焦点,倾向于一种消解意义的装饰性作风,在这个方面,瓦妮莎·贝尔更为认同的是更具现代意味的马蒂斯。马蒂斯强调,绘画的目标不再是叙述性的描绘,他梦寐以求的是“一种平衡,单纯而又宁静的艺术,它避开了令人烦恼和沮丧的题材”[6],也就是说,在马蒂斯式的绘画理念中,欧洲文学传统中有关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切重大主题都被悬置起来,正如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说的那样,“对于新艺术家而言,美学享受来自于对人性化因素的征服”[7]。瓦妮莎·贝尔就是这种类型的新艺术家,整个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向英国公众推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去人性化”的视觉艺术新理念。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创作实践中,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处于瓦妮莎·贝尔的“影响的焦虑”之中,终其一生对姐姐保持着一种混合了依赖、爱恋、崇拜、嫉妒、竞争意识的特殊心理反应。对于瓦妮莎·贝尔的绘画实践,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表现出的接受立场相当复杂。
弗吉尼亚·伍尔夫相当认同姐姐在绘画方向上的现代主义选择,试图在小说领域以其为导引借鉴和引进现代主义绘画的构成原则。吉利斯皮准确地指出:“视觉艺术,特别是瓦妮莎所归属的那类,向弗吉尼亚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王国,那里没有人的自我存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8]瓦妮莎·贝尔现代主义绘画“去人性化”的直接结果便是造型、空间、色彩等所谓形式要素成为真正的绘画主题。弗吉尼亚·伍尔夫探索现代主义小说的革新手法,对于在欧洲传统小说中处于遮蔽状态的形式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移植现代主义绘画形式问题的已有成果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弗吉尼亚·伍尔夫称姐姐为色彩方面的诗人,并在给姐姐的信中写到,“作为一名作家,我感觉到美差不多全部都是色彩”,[9]可以说,单就“美”的范畴而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小说与瓦妮莎·贝尔的现代主义绘画有着诸多内在构成的一致之处。
1917年,伍尔夫夫妇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大部分出版物的封面设计交由瓦妮莎·贝尔设计,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几乎所有作品的视觉艺术装饰也都由她完成。瓦妮莎·贝尔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提供的插画与设计,并不注重对文本意义的图像阐释,而是偏重于视觉效果,以简笔花卉与几何图形的抽象图案为主,明显是“去人性化”的,对于姐姐的工作,弗吉尼亚·伍尔夫多次表达了满意和赞赏的态度,可见她对于自己文学文本的这种视觉艺术对位予以了肯定。不过,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对瓦妮莎·贝尔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绘画形式观的认同并不是无保留的,她以文字的形式与姐姐的画笔竞争,并没有忽略文学与造型艺术的性质差异,对于莱辛以来的诗画分界问题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在1918年7月1日写给瓦妮莎·贝尔的一封信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表明了一个原则性的立场:“我对于造型艺术的思考,始终受到有关文学本质其他因素考量的制约。”[10]这里所谓的“有关文学本质其他因素”,指的是现代主义形式问题之外并与之构成重大张力的诸问题。正是由于有这种思考张力的存在,弗吉尼亚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才与瓦妮莎·贝尔的现代主义绘画实践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内在对话状态。
三
为瓦妮莎·贝尔现代主义绘画实践提供最强有力理论支撑的是她的丈夫克莱夫·贝尔。在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这个以视觉艺术为关注中心的小圈子里,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于1914年出版纲领性的现代批评名著《艺术》一书,正式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经典命题。克莱夫·贝尔的理论中所说的艺术,主要就视觉艺术而言,他的观点更精确的表达为“有意味的形式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共通的一大特质”[11]。克莱夫·贝尔认为,在视觉艺术作品中,线条与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可以激起审美情感的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对此可以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的理论把视觉艺术中的线条色彩等形式要素设定在本体或核心的位置上,形式主义色彩相当强烈,轰动一时,影响深远,在相当程度上被公众认为是代表了整个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批评立场。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在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内部,视觉艺术与文学两大最主要势力有分有合,而作为文学势力一方最主要的代表,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诗画分界问题上也与克莱夫·贝尔展开了充满思想张力的理论对话。
站在小说家的立场,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情感是我们的材料,形式是安置情感、排列情感、整合情感的东西。”[12]这种关于小说艺术形式与情感关系的论断是明显借鉴克莱夫·贝尔的艺术理论的,甚至可以说“实现了‘有意味的形式'在文学领域内的有效平移”[13]。在克莱夫·贝尔艺术理论的启发下,弗吉尼亚·伍尔夫致力于发现传统现实主义视域内被极大忽略的小说形式要素,赋予结构和情节组织一定的本体意义,对传统小说理论中过分偏重模仿和再现的倾向做出了大幅度的修正。不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论与克莱夫·贝尔艺术论的契合之处基本上到此为止,接下来,二者之间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理论观念上的分歧与冲突。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小说与其它诸种艺术形式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无法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这也就是其最大文化价值所在;而克莱夫·贝尔则强调说,把我们从人类活动的天地引入审美狂喜的境界,艺术的终极存在意义实在于此,“现实感”问题显然是两人理论观念分歧与冲突的焦点所在。
关于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做出过一个著名的界定:“所有小说中有一个元素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是人的元素,小说是描写人的,它是完整而真实地记录现实人类生活的唯一艺术形式。”[14]这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主义命题,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小说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身份认同,坚信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比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更能体现人类生命的“现实感”存在,而体现人类生命的“现实感”存在正是文学最古老也最本质的功能和意义所在,在现代世界中,相对于诗歌或其它文学体裁,小说最能承载这种文学最古老也最本质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它实际上也最能代表文学的最高价值指向。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体裁等级评判立场相反,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出了扬诗歌而抑小说的鲜明态度。克莱夫·贝尔基本上把他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限定于视觉艺术的界域之内来应用,不过,他也进一步申明,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它艺术门类。耐人寻味的是,当克莱夫·贝尔讲到文学问题的时候,认为相对于视觉艺术以及音乐,文学从来没有成为纯粹的艺术,也从来不是人类生活的纯粹艺术情感的表达。克莱夫·贝尔所谓的“纯粹艺术情感”,是一个极具典型的“艺术的去人性化”的概念范畴建构,强调纯粹的艺术必须与现实生活实现精神上的分离,进入纯粹艺术情感状态,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鉴赏领域,都无须熟悉和体验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只有超乎其上,方能通于至高艺境。带着这样的视角来审视文学体裁,克莱夫·贝尔认为,小说这种文体相较于诗歌,因其再现生活的主导功能,在形式感上尤其无法达到纯粹而严格的标准,所以是较为低级的艺术门类。当提到小说家身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时候,克莱夫·贝尔称赞她拥有其他小说家所不具备的纯粹的画家式视觉审美感受力,他的确准确地捕捉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形式观照特质,但是另一方面,却由于“艺术的去人性化”偏见而悬置了其更为根本的人性关注的目光。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根本不存在克莱夫·贝尔所设想的超乎现实生活情感之上的纯粹艺术情感,相较于视觉艺术、文学、尤其是小说,形式的要素往往离纯粹状态要远一些,这种诗画分界恰恰显示了文学的优势所在,那就是在形式与生活的永恒张力中,生活永远是主导的一方,小说诗学是形式诗学,但更是生活诗学,生活诗学统摄形式诗学是小说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基本前提。
四
在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文学势力的首席代表,她在视觉艺术势力一方真正唯一的竞争对手和同等级对话对象是罗杰·弗莱。1910年11月,罗杰·弗莱策划并主持了英国首次展示塞尚、高更、梵·高、马蒂斯等现代主义画家作品的大型展览,对于这些画家,他统称为“后印象派”,从此,这个名称成为概括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期欧陆现代主义视觉艺术的权威说法。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10年12月参观了此次画展,深受触动,宣称“大约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15],事实上,是她本人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而这一改变主要是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下产生的。
罗杰·弗莱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视觉艺术思想的真正灵魂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克莱夫·贝尔充当的仅仅是一个向公众阐释罗杰·弗莱理论的传声筒角色,而且这位门徒对罗杰·弗莱理论的阐释并没有令他的导师感到满意。罗杰·弗莱公开表达了他对于《艺术》一书的意见和与克莱夫·贝尔之间的思想分歧,认为克莱夫·贝尔理论最致命的问题便是将所谓纯粹艺术情感从整个人类情感综合体中分离出来,在这一点上,他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批评立场是一致的。
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罗杰·弗莱是一个较之克莱夫·贝尔远为强大的思想对手,在某种程度上,她甚至能够接受罗杰·弗莱在她精神生命中扮演过导师角色这一事实。罗杰·弗莱评论他所推崇的塞尚、高更、马蒂斯等法国现代主义画家时,把他们称为“试图发现合适于现代世界观感受的图画语言的现代人”[16]。弗吉尼亚·伍尔夫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命题,并实现了其在文学领域的有效转换,致力于发现适合现代世界观感受的文学语言,她在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上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罗杰·弗莱的理论启示。不过,在诗画分界问题的大方向上,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罗杰·弗莱的思想分歧仍然是主导性的。
在视觉艺术批评的形式主义立场方面,罗杰·弗莱与克莱夫·贝尔基本上属于同盟军。罗杰·弗莱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其最根本的性质,他的艺术理论的第一关键词是“造型性”(plasticity),对于这一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认识相当清晰,她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品《罗杰·弗莱传记》中描述说,“只要罗杰·弗莱口中吐出‘造型性'这个词,他的魔法就施展起来了”[17]。可以说,抓住了“造型性”这个关键词,也就深入到了罗杰·弗莱理论的核心地带。
我们看罗杰·弗莱对他最崇拜的现代画家塞尚后期作品的评论:“造型性压倒一切,一切均被简化成为最纯粹的结构设计语言。”[18]在这里,“造型性”的含义大体等同于纯粹形式,包括构图(compostion)、结构(structure)、色调(tone)、设计(design)等构成要素,按照罗杰·弗莱的思路,视觉艺术的题材和内容应该仅仅作为形式的导引,否则会引起现实再现与纯粹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符合罗杰·弗莱“造型性”概念的艺术门类是建筑,建筑相对于绘画和雕塑,显然更符合形式即本体的原则。在1929年所做的一次题为《艺术的再现》的演讲中,罗杰·弗莱用“艺术的建筑理论”这一说法来概括自己的艺术思想,而将传说的绘画理论称作“艺术的文学理论”,前者倾向于悬置现实再现的题材和内容维度,聚焦于绘画作品的纯粹形式本位,而后者与西方文学理论中最古老也最流行的摹仿论趋同,主要关注绘画作品中的叙述性方面。罗杰·弗莱认为,绘画史上表现人类生活场景的大师经典之作,往往建筑因素和文学因素相对依存,既存在着与建筑相类似的空间与体积构成,也存在着与文学相似的心理瞬间的刻划,而在二者之间,占据主导权的一方是建筑因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杰·弗莱的这一说法其实相当忠实地复述了莱辛《拉奥孔》中的诗画分界观点,即绘画领域中的情感表现处于造型美之下的从属地位。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可了罗杰·弗莱“造型性”概念在视觉艺术批评中的有效性,而且还进一步将其移植到自己的小说批评领域,尝试着从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和看待小说。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无论如何,小说是一种结构,在有识者的目光中留下一个形,有时是方形的,有时是塔状的,有时是发散开张,有时团聚紧结,就像穹顶状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19]罗杰·弗莱偶尔谈论到小说的时候,倾向于把小说纳入到他的形式理论,将其视为一个建筑式的有机审美整体,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这里所说的“有识者的目光”,其实就是一种罗杰·弗莱式的审美目光。然而,接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话锋一转,切入到她所认为的小说诗学更核心的问题:“小说的‘形'并非由石头对石头的关系制作而成的,而是由人与人的关系制作成的,因此,一部小说打动我们的是各种矛盾对立的情感。”[20]相对于罗杰·弗莱的视觉理论第一关键词“造型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诗学的第一关键词是“人性”,在她看来,作为现代世界的第一文学体裁,小说首先承载的是揭示人性和人类情感活动真实状态的功能与意义,对于视觉艺术而言最重要的“美”或“造型性”问题,换位于这一领域依然具有有效性乃至本体意味,但是无论如何,小说的“造型性”问题必须从属于“人性”问题,只能占到次重要的位置。
罗杰·弗莱有这样一个关于“造型性”原则的最直观的说法,在一副绘画作品中,“一个人的头并不比一个南瓜更重要或更不重要”[21]。从这一观念出发,当他展开艺术的批评的时候,对于西方绘画传统中后起的静物画常常予以特别关注。罗杰·弗莱认为:“在任何其他绘画类型里,人性的因素都不免会掺杂进来,而在静物画中,与被再现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和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平常,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艺术家和观众根本无需考虑它们。”[22]在罗杰·弗莱眼中,静物画因人性因素的悬置而最易于凸显纯粹造型意义,最适用于他的“艺术的建筑理论”。我们不妨看一看罗杰·弗莱有关塞尚一副静物画《高脚果盘》的相关解读:“椭圆形以两种十分不同的大小在高脚盘与玻璃杯中重复,这些形状是根据几乎与古希腊建筑经典一样严格和谐的原理被安排在一起的。”[23]“艺术的去人性化”倾向在这个批评案例中表现得非常清晰。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时时出现优美传神的静物描写,例如《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凝视水果一节:“她的目光一直出没于那些水果弯曲的线条和阴影之间,在葡萄浓艳的紫色和贝壳的角质脊梗上逗留,让黄色和紫色相互衬托,曲线和圆形相互对比。”[24]文本中拉姆齐夫人的目光无疑是典型的罗杰·弗莱式审美目光,我们甚至可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在通过这样的描写向罗杰·弗莱致敬。然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向罗杰·弗莱致敬的同时,其实也在与他进行着关于诗画分界问题的思想论争,在这段文本中,“艺术的建筑理论”仍然从属于“艺术的文学理论”,水果的“造型性”出自于拉姆齐夫人的一个心理瞬间,弗吉尼亚·伍尔夫用自己的第一关键词“人性”统摄了罗杰·弗莱的第一关键词“造型性”,与莱辛《拉奥孔》的批评立场相仿,同样旨在确认文学相对于视觉艺术的等级优越性。
五
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小说是在阅读过程本身之中构成的,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所看到的形式,而是你所感受到的情感,正如韦勒克所说,在她如此使用“形式”概念的时候,“形式一词对她来说等同于视觉性和静态”[25],这种“去人性化”和非生命化的形式观与她的“生命写作”(Life-Writing)原则形成了巨大的冲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篇关于哈代小说的评论中,借用了哈代一部1917年诗集的标题“视觉的瞬间”这一提法强调“视觉的瞬间”(Moments of Vision)其实也就意味着“生命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指向人性和人类情感活动的维度。
弗吉尼亚·伍尔夫最为欣赏和钦佩的同时代画家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之外的希科特。希科特一直坚持绘画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观点,将自己明确划归到反文学绘画理论的对立方阵营,他所师法的现代法国画家是与“艺术的去人性化”主流拉开最大距离的德加。德加的绘画致力于表现人类生活中的动态瞬间,保持着绘画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再现生活的传统,希科特秉承了这样的原则,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即便是物体或建筑物也反映人性的轨迹,连风景画也能涌出一种人性”[26],因此取得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共鸣和青睐。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实践中主张汲取视觉艺术的手法加强创新,她曾与法国画家雅各·拉弗拉深入讨论过文学写作的“线性”构成与画家创作的“共时性”构成之间的差异,表示要突破传统文学叙事的线性构成,达到绘画的“共时性”构成效果,“宣称自己有那个能力(或至少有那个意图)不合时宜地看待事物,去领会思考和感受的过程,就好像它们是图形那样”[27]。
在她的小说《到灯塔去》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设置了一个看似极不起眼的配角形象,女画家莉丽。在这部小说的故事中,莉丽是主人公拉姆齐一家的朋友,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为拉姆齐母子画像,一度决心以一个抽象的紫色三角形构图代表拉姆齐母子,在作品的结尾处,已是十年之后,她才在画布中央添上最后一笔,最终完成了画像。对莉丽而言,一支画笔,就是这个充满斗争和混乱的世界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可以通过它来揭示出世界纷扰表象下存在着的形状、秩序和美。莉丽这个形象中包含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瓦妮莎·贝尔的影子,也折射出了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艺术理论的意蕴。不过,更为关键的是,她实际上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的一个签名式的文本潜入,正如哈里斯所言,“最终成为了位于中心的灵魂人物”[28]。莉丽的画像实际上是《到灯塔去》这部小说本身的一个隐喻,无论是抽象的紫色三角形构图,还是其它的“有意味的形式”或“造型性”,其意义都指向更核心的人性挖掘之维。通过莉丽这个女画家形象的塑造,弗吉尼亚·伍尔夫形象地传达出了她对于诗画分界问题思考的部分结论。“美”“有意味的形式”“造型性”,这些要素对于文学和视觉艺术来说都是共通项,只不过在后者哪里更具有本体论意义,而“人性”这个要素,或许在视觉艺术中可以被悬置甚至解构,但是在文学中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是其最核心的指向。秉承着这样一种认识,弗吉尼亚·伍尔夫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上,确认了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相对于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在现代世界中的文化等级优越性,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小说家身份认同的“傲慢与偏见”,然而,在“艺术的去人性化”浪潮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呈席卷之势的状况下,这样的“傲慢与偏见”无疑具有一种存在的伦理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