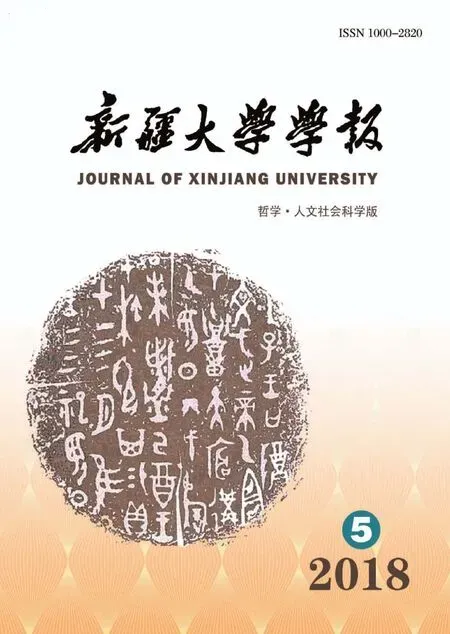元词走向及其异质特征*
任红敏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元代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激荡融合的结果,“元代文化是多源融会、多元一体的。多元,基本上是三源:以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主导,以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为主干,西域商业文化为重要一源。元代文化的共有精神,既不单是中原传统的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固有文化精神的延续,也不是北方游牧文化精神的入主,更不是西域商业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的移植,而是这多元文化冲突、融合后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精神。”[1]50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凭借政权的威力强制推行其文化,西域色目民族也是元代多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草原游牧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所固有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生活信念、文化特质等必然会冲击高度发展的中原传统农业文化,汉族人民也会主动从草原游牧文化中吸取新的思想观念,给多元交织的中原文化注入新鲜、活泼的生机。在元代多元文化背景之下,元词有元词之特色,通观元词的发展和元代词人的创作情况,较之于宋、金词有着独有的时代风貌,元词上承宋金词,下启明清词,是整个中国词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衔接两宋和明清之间一个重要的环节。元代少数民族词人群体的涌现,元词兼容南北,风格多样以及元代词与曲之间的递变均是元词的特征。
一、少数民族词人群体的涌现
元王朝不仅疆域辽阔,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民族大迁移与大混居的时代,多民族共居,民族之间相互涵化与融合,各类人才都非常多,在文学领域出现很多卓越的少数民族大家,如耶律楚材、廉希宪、贯云石、赵世延、马祖常、孛术、鲁翀、廼贤、萨都剌、郝天挺、余阙、颜宗道、瞻思、辛文房。”[2]卷七可谓人才济济,名士辈出。
当然,元代词坛因为少数民族词人群体的出现,也使元词成为整个中国词史上最复杂、最丰富的一个时期,特色独具,这既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元代少数民族词人众多,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斐然①王叔磐先生《元代北方民族词选》一书中共收录有元代40位北方民族词人的280首词作。这40位词人的所属是契丹、蒙古、突厥、女真、拓跋、维吾尔、鲜虞、安息、氐、高丽、鲜卑、党项、回,还有一些属于色目人或西域他族。王叔磐《元代北方民族词选》自序中论述:“总计元代词人共有200多位,其作品仍流传至今者,有耶律楚材、李治、许谦、李庭、刘秉忠、杜仁杰、耶律铸、白朴、王恽、胡祗遹、廉希宪、卢挚、张弘范、姚燧、刘敏中、刘因、程文海、吴澄、赵孟頫、管道升、鲜于枢、吴存、王沂、蒲道源、袁易、安熙、杨载、朱晞颜、虞集、欧阳玄、张玉娘、王结、王旭、张埜、元卿、张雨、冯子振、乔吉、张可久、刘燕哥、吴镇、李孝光、贯云石、薛昂夫、许有壬、张翥、李齐贤、宋褧、偰玉立、谢应芳、倪瓒、萨都剌、华幼武、邵亨贞、顾阿英、柯九思、陶宗仪、高明、韩奕、梵琦、尹志平、宋德芳等等。”(王叔磐《元代北方民族词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l版)。元初有辽宗室后裔契丹人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诗文词兼善,以及集金文学之大成、开元词学之先河的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元好问,还有鲜卑族王沂,女真词人兀颜思忠和奥敦周卿,西域色目文人中廉希宪、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偰玉立、薛昂夫、丁鹤年等均有词传世,萨都剌被元代林人中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高昌色目人小云石海涯(贯云石)是廉希宪之弟廉希闵的外孙,曾出任翰林学士,是散曲大家,词也别有特色。回鹘文人薛昂夫是元代著名曲家,精通儒学,兼善书法,只可惜他创作的诗词多已散佚,《全金元词》收其词三阙。高丽士人李齐贤,字仲思,号益斋、栋翁,韩国高丽时期优秀卓绝的文人,作为高丽忠宣王侍从留居中国,所存词53首。少数民族词人群体的出现改变和丰富了元代词坛面貌,他们的创作风格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别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和审美意趣,在中国词学史上光彩独具,为元代词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
(一)以山水、田园、隐逸展示士大夫文人情怀,在物质与精神都达到富足的元士大夫文人中相当普遍,以展示内心自适情怀和看破看淡世俗功名地位的洒脱,是一种悠然闲适生活情态。元代文人追求隐逸之风非常兴盛,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真正隐居田园山林,或者隐逸于书画,或隐于市井勾栏,在诗文词曲中大谈特谈隐逸之趣,对世俗生活的不屑,对安静无为生活的享受。元代少数民族词人濡染汉文化多具有深厚儒学学术背景,自然词作中山水、田园、隐逸也占有较大比重,如耶律楚材、耶律铸、元好问、王沂、兀颜思忠、廉希宪、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偰玉立、薛昂夫、丁鹤年等,与汉族士大夫文人别无二致。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博学多才,据史载:“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2]燕京破,成吉思汗召至帐下,后随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振兴儒学,保护儒士文人,为当时士人所景仰,今仅存词《鹧鸪天·题七真洞》一首:“花骨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3]耶律楚材虽备受成吉思汗赏识,但并非以治国之才受到重用,而是以精通阴阳术数与符瑞卜筮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他曾感慨到:“学术忠义两无用,道之将丧予忧惶。”[4]初行汉法步履维艰,难免其词作流露出故国家园之思,以翠嶂、寒烟、啼鹃以及闲花野草等景物衬托此情,境界开阔,在悲慨、苍凉底色下有着旷达豪迈,大有辛词之风。况周颐赞曰:“高浑之至,淡而近于穆矣。庶几合苏之清、辛之健而一之。”[5]79
鲜卑后裔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北魏拓跋氏后裔。曾从郝经祖父郝天挺学,淹贯经传百家。作为元代词坛开创者的元好问更是凡词体所能写均纳入笔下,因其醇厚的儒学学术背景,北方地域文化的豪迈基础,以及本人对雅正风格的推崇,遗山词的风格更是兼容各家而自成一体。元好问词数量多,质量高,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谓:“乐府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况周颐《蕙风词话》认为他遭遇国变,“神州沉陆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自金亡后,元好问词多以隐逸为主。如其《满江红·内乡作》一词:
老树荒台,秋兴动,悠然独酌。秋也老,江山憔悴,鬓华先觉。人到中年原易感,眼看华屋归零落。算世间,惟有醉乡民,平生乐。
凌浩荡,观寥廓。月为烛,云为幄。尽百川都酿,不供杯杓。身外虚名将底用,古来已错今尤错。唤野猿、山鸟一时歌,休休莫[6]80。
与山水云月为伴,以诗酒自娱,确实是任性而逍遥,哪里还在乎那身外虚名,把国家覆亡之伤痛化作了诗和酒。词风也是旷达洒脱之极。少数民族词人写隐逸,写山水,写田园,与南方词人的悲秋伤春、感念故国明显不同,这显然与北方民族的个性以及生存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对这种旷达,引用刘扬中先生的话:“‘旷达'是一种超脱世俗、达观自适的从容风度,也是一种参透物理、冲淡玄远的思想境界和疏放闲逸、与物俱化的审美情味。”[7]201又如《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一词:
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
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唯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6]117。
这种超逸和洒脱让人难以想象词人经历了金元易代的社会动荡与战乱,只感觉到真正的田园之乐,生活闲适之趣,何其洒脱的境界和胸怀。
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的廉希宪,畏兀儿人,名将布鲁海牙之子。儒学素养深厚,自幼“延明师,教之以经”,又曾师从名儒王鹗,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色目文人。廉希宪常与当时文士名流交往,常常在自家的万柳堂置酒招客,和名士文人浅斟低歌①据沈雄《古今词话》《词辨》卷下载:“都城外万柳堂,廉野云(廉希宪)置酒招卢疏斋(卢挚)、赵松雪(赵孟俯)同饮。时歌妓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行酒,歌《小圣乐》。”又《日下旧闻考》:“元廉希宪万柳堂在今右安门外草桥相近。。他虽存留下来的诗词不多,《全金元词》仅存其一首《水调歌头·读书岩》词,从词中仍可看到元代文人非常典型的士人心态,且颇能显示其名士风流,词如下:
杜陵佳丽地,千古尽英游。云烟去天尺五,绣阁倚朱楼。碧草荒岩五亩,翠霭丹崖百尺,宇宙为吾留。读书名始起,万古入冥搜。
凤池崇,金谷树,一浮鸥。彭殇尔能何许,也欲接余眸。唤起终南灵与,商略昔时名物,谁劣复谁优。白鹿庐山梦,颉颃天地秋[6]721。
完全是沉浸于诗书,词人的淡泊恬退、自在逍遥和周围的碧草、翠霭、朱楼、丹崖等融为一体,即使置之于宋代士大夫文人词中也难以择出,是传统的士大夫文人词。
在朝为官者如李齐贤、王沂、兀颜思忠等亦时以隐逸词表达向往丘壑山林之愿。鲜卑士人王沂,字思鲁,仁宗延祐二年进士,官国子学博士、翰林待制、礼部尚书。身居高位,他的词仍时流露对隐逸生活之向往。《菩萨蛮·题李溉之词卷》:“大明湖上秋容暮。风烟杖履时来去。说与病维摩,可人秋水呵!自书盘谷序,和了停云句。把酒为君歌,济南名士多。”[6]833也是洒脱,借勉励朋友归隐,而抒发词人之淡然心境。女真人兀颜思忠,字子中,居东平(今属山东),历官淮西廉访副使、浙西廉访使。是顾瑛玉山草堂座上客,与杨维桢、李孝光、柯九思、黄溍、张雨、倪瓒、高明等名流交往颇多,现存词《水调歌头·偕宪椽分司尉邑,偶得友人招隐之章,率尔次韵》一首:
白云渺何许,目断楚江天。悲风大河南北,跋涉几山川。手线征衫尘暗,雁足帛书天阔,恨入短长篇。青镜晓慵看,华发早盈颠。
叹流光,真逝水,自堪怜。明年屈指半百,勋业愧前贤。霄汉骖鸾无梦,桑梓归耕有计,醉且付高眠。寄谢鹿门老,待我共谈元[6]848。
是典型的士大夫文人词,有苏、辛词风之豪迈超逸,感慨时光易逝,功业愧对前贤,不如归耕桑梓,借归隐之意表达自己清虚自守的境界和旷达胸襟。“儒业起家”的文人偰玉立,出身于畏兀儿世家,他的词作和兀颜思忠词有很多相近之处,仅存的词作《菩萨蛮·蒙岩石刻》:“蒙岩几日桃花雨,依稀流水章桥去。只恐到天台,误通刘阮来。玉堂开绮户,不隔尘寰路。休认避秦人,壶中别有春。”[8]554都是以山水写闲情逸致,然后以“隔尘寰路”表达了归隐之情。
李齐贤(1288 一1367),字仲思,号益斋、栋翁,朝鲜高丽人。李齐贤出生书香世家,作为高丽忠宣王侍从留居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广交名士,与姚燧、阎复、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交游颇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所存的53首词中,寄情山水景物词作颇多,如《沁园春·将之成都》:
堪笑书生,谬算狂谋,所就几何!谓一朝遭遇,云龙风虎,五湖归去,月艇烟蓑。人事多乖,君恩难报,争奈光阴随逝波。缘何事,背乡关万里,又向岷峨。
幸今天下如家,顾去日无多来日多。好轻裘快马,穷探壮观,驰山走海,总入清哦。安用平生,突黔席暖,空使毛群欺卧驼。休肠断,听阳关第四,倒卷金荷[6]1024。
词作虽有乡关之思,但透露出疏散从容的气度,语言清新爽朗,别有意趣。清代词学家谢章铤认为:“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9]528少数民族词人未必具备辛弃疾那样的才华,但北方民族豪健洒脱的性格具备了辛弃疾的超迈、真气和奇气,所以词作超迈而旷达,雄远壮阔,而清灵隽秀。
少数民族士人的词作和汉族词人在题材方面几乎没有区别,如唐圭璋、钟振振《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前言》所说:“元人笔下的好词,大都集中在隐逸、山水、怀古这三大部类。元代的著名词家,鲜有不同时或分别在这三大部类中搴旗拔垒、登坛拜将的。”元代少数民族词人的作品几乎都涉及了山水、田园、隐逸的内容,这和他们融入汉文化圈有很大关系,也是当时词坛风貌的反映。受北方地域和文化的熏陶以及北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类作品都质朴从容、旷达超逸,无矫揉造作之感,任感情流露。
(二)耿然于心的英雄心态与英雄情结。这些少数民族文人虽然久居中土,从学术修养以及汉文化水平上已经与汉族士人别无二致,但“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文化认同感却难以改变。”[10]68他们的相貌自然也改变不了,如贯云石的西域民族体貌特征“芙蓉仙人冰玉质,貌粹骨刚长八尺。阅遍尘寰扰扰人,玄鬓朱唇双眼碧”(叶顒《第一人间快活丸歌》,自《樵云独唱》卷二),而且游牧民族自古“逐水草而居”的民族性格和气质依然存留在他们骨血里,诸如豪放洒脱、阳刚英武、剽悍勇猛、游牧民族最典型的崇尚勇力征战的英雄情结等。突厥人有“贵壮健,贱老弱”的价值观,崇尚英武,女真人在推选酋长和家族继承人时把勇毅善战作为选拔标准,蒙古人更是崇尚勇武。这一点从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诗也能看出,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均是描写金戈铁马的征战,自然是强者为王,推崇的是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英雄,史诗中江格尔被称为大力士,食量惊人,力大无穷,臂力超群,作战勇猛。马祖常是“西北贵种”,西北古族雍古人,出身于一个剽悍勇猛的西北尚武的也里可温家族,家族中有几代铮铮铁血硬汉以自己的武功垂名金、元史书,曾祖月合乃曾从元世祖南征。萨都剌出身将门,祖、父“以世勋镇云、代,居于雁门”[12]1445,戎马倥偬一生,萨都剌虽然偃武修文,但也自有一股天生的英雄气概。贯云石,“公生神采迥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善骑射,工马槊,尝使壮士驱三恶马疾驰,公持稍前立而逆之,马至腾上,越而跨之,运稍风生,观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欧阳玄《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13]卷9骑射与马上功夫了得,臂力超人,乃是典型的西域勇士。薛昂夫乃“西戎贵种。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其风俗固然也”(《薛昂夫诗集叙》)[14]卷6血脉中流淌的民族性格与西域地域气质和文化的影响,使得他勇决而豪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因素有关,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信仰方式影响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气质和文化性格自然影响他们词的创作,体现在词作中的民族性特征是英雄意识和英雄情结,词风劲健爽朗而且个性张扬。
如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字成仲,号双溪,溢号文忠,契丹人,长于塞北,又曾出征伐蜀,驰骋沙场,任中书省左丞相,后赴山东任职,仕途坎坷,屡罢屡起。他的词以清爽清丽为主,但时常流露出建功立业的英雄之气,即使以婉约笔墨写文士风流,也总有军事意象的词汇出现,如《满庭芳·西园席间用人韵》:
酒阵诗坛,征兵命将,得无倾动华筵。拟勤春事,还自要相先。天地元如逆旅,应自愧不驻流年。凭谁问,姮娥心事,何惜月长圆。
西园张乐地,献歌呈舞,燕扰莺喧。尽未妨颓玉,锦瑟旁边。脱落尘凡健笔,终不负,与染芳烟。欢缘在,判家视草,仍是玉堂仙。[7]623
他非常渴望如英雄一样横刀立马,能够建立不世之功而扬名后世,正因为常常带兵打仗,对戎马倥偬的生活有深刻的体会,一腔英雄气常在,才会有“酒阵诗坛,征兵命将”之语脱口而出,词人虽然看透了世事无常,仕途蹭蹬,但驰骋沙场多年,早已把怨气悲戚化成了豁达洒脱。即使是送别词如《南乡子·送人北行入燕作》:“匹马赴严宸,将谓青云上致身。不是男儿容易事,风尘,水远山长愁杀人。 离别若为情,雪暗西山泪满巾。还忆夜来分手处,天津,桃李无言各自春。”[6]623也无半点哀怨悲伤,而是看到友人将青云直上,忠告他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有豁达也有洒脱。
萨都剌继承了苏、辛清旷雄奇的风格,《天锡词》雄奇豪迈、刚健质朴。元张翥题其画像云:“词林推为雄伯,而宪府叹为宗工。至其纂组锦绣,吐纳珠玑,才华鹄峙,文采鸾飞。富五车而登屈宋之奥,高八斗而窥班马之微,俾功开手,学美绍前,微论昭代之风雅,非先生其谁与归。”[12]对萨都剌推崇非常。萨都剌一生以儒者自居,“有子在官名在儒”(《溪行中秋玩月》),关心时政,充满忧患意识,词作中最突出的就是怀古词,因看到了元朝的种种弊端和衰亡的景象,万古苍凉,千秋兴废,奔来眼底。如其最负盛名的怀古词《木兰花慢·彭城怀古》: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起伏如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木兰花慢·彭城怀古》)[6]1092
这首词是萨都剌怀古词中的代表作。豪迈、博大、俊逸、旷达、深沉、清新、苍凉,还有潇洒旷达,人事代谢,古往今来,令人感慨万端,对历史兴亡、世事沧桑、人事短暂的感慨,对英雄的功业无成和美人的忠贞执着的嗟叹,是词人对元王朝的一片忠心以及无力扭转王朝颓势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其中在“消磨尽、几英雄?”怀念英雄,向往英雄,多种滋味涌上心头,是萨都剌游牧民族英雄情结的体现,如今英雄何在?他呼唤英雄,诗词中也常有描写金戈铁马的征战,“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念奴娇》)的争战厮杀,他把自己对人生、对历史的认识和感慨写进词里,豪壮中有一种雄壮的动态美、力度美、阳刚美,代表了元代少数民族词人洒脱旷达的风格,语言省净,意境清新。
再如贯云石、薛昂夫等西域子弟,均以曲名世,存词不多。畏兀儿人贯云石(1286-1324),名小云石海涯,元初重臣阿里海涯之孙,祖籍高昌,其曲清新俊逸,疏放流丽,名重文坛,今仅存词两首,《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和《蝶恋花·钱塘灯夕》。薛昂夫(1267-1359),本名薛超吾,回鹘人。汉姓马,字昂夫,号九皋。薛昂夫历官江西省令史,金典瑞院事、太平路总管、衢州路总管等职,后归隐杭州西湖一带,在山水田园中终老,今存词三首。贯云石和薛昂夫词作均与曲相通,有明显的曲化倾向:散曲的句法,散曲的意绪化,词作存留较少,叹世乐闲居多,而英雄气多在曲中体现,词雅丽清新,如贯云石《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晚来碧海风沉,满楼明月留人住……关河如此,不须骑鹤,尽堪来去。月落潮平,小食梦转,已非吾土。且从容对酒,龙香涴茧,写平山赋。”[7]950薛昂夫《最高楼·九日》:“登高懒,且平地过重阳。……也休说、竹篱茅舍恶。花与酒,一般香。西风莫放秋容老,时时留待客徜徉。便百年,混是醉,几千场。”[6]951两首词的共同点都是洒脱放达,即使是有愁绪,也没有进退失据的苦闷,而是超脱之感,没有英雄气概,怎么会有如此的俊爽,如此不羁与洒脱!
二、南北词风之交融
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打破元代词坛南北分流的格局,北方与南方词风交汇融合,使得元词体现了更大的包容度,也是元词区别于宋金词的一个突出特征。对南北词风的融合,赵维江先生有过专文论述,他认为:元词的发展经历了北方词独盛的前期之后是南、北词派并行共荣的中期,最后是南宗词复兴与北宗词衰微的后期,“在元朝有国130余年间,元代词坛经历了一个由北方独支到南北合一的过程。地域文化环境意义上的南北分合的格局变化,规定了元词发展的大致走向和总体的风貌特征。体现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精神的南北词派,从相互间的隔漠、自是到关注、认可,最后以南兴北衰为结局走向融合归一。”[13]72
北宗词主要继承了北宋词人苏轼和辛弃疾豪爽刚健、洒脱旷逸的词风以及“以诗为词”的观念,元好问奠定了元初北宗词沉郁苍凉、雄奇豪迈、爽朗清刚的基调,元初北方文人学苏、辛的路子,元代南方词人承南宋余绪,感沧桑巨变,以尚周邦彦和姜夔的风流蕴藉为主,婉约清丽、声韵流美,使得整个元代初期词坛呈现南北不同风格的词学风貌。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对北宗词和南宗词有过非常详细的论述:
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顾细审其词,南与北确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轩、李庄靖、段氏遯庵、菊轩,其词不入元选,而其格调气息,以视元选诸词,亦复如骖之靳,则又何说。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善读者抉择其精华,能知其并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难于合勘,而难于分观。往往能知之而难于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5]57。
况氏之论主要是阐述北宗词和南宗词之不同,而北宗不仅仅是豪放刚健之气,也有清雅婉约之风,元好问则是吸收苏、辛词之雄奇豪放以及兼容秦、周、姜、史之婉约而自成一格。到了元前期,北方在蒙古族统治之前,早已经历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他们很容易认同和参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权,有志之士为推行汉法,保存中原文化而积极努力,虽然金遗民不愿出仕新朝者隐居避世,但多数能直面社会现实,北国自然环境孕育的豪健方刚性格,所以元前期北方词人即使表达颠沛流离、人生多艰之感伤,风格也疏朗,他们的词风受元好问影响,呈现豪迈明快,清疏澹净,且有缠绵婉曲、清雅秀丽之特色,比金代词风格更为多样,所以况氏用一个“清”字概括北宗词的特色,清标、清雅、清美、清醇、清刚、清隽、清爽、清新、清朗、清润、清劲,与北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一致,北方草原游牧在辽阔无垠的草原,天寒地冻,一年之中常见洁净的冰雪,因之,“北人以冰霜为清”的地域文化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南宋偏安南国,词仍沿着“本色”方向发展,虽有稼轩大倡北宗,但主流未改。南宋遗民词人们以山林田园为归,以自然云水为乐,追求闲适、淡泊的情怀,身处江南钟灵毓秀、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南宗词婉约流美、清空骚雅的境界,南宗词占得一个“秀”字,秀雅、秀美、秀拔、秀润、灵秀、秀洁、秀澈,自然也是和南方的山清水秀,风光秀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一致的。
元初南方词坛以周密、张炎、刘辰翁、蒋捷、仇远、王沂孙、陈恕可、唐珏等词人为主,一大批南宋遗民词人创作开创了当时的词坛盛况。他们目睹了国家社稷的覆亡,身遭乱离,最触动他们情感的是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为了不居乱邦而选择遁迹隐居在湖山泉石之间,于山林云水之中寻求解脱,或者深入寺院道观,游于方外,求禅问道。经历了精神上的困惑与迷惘之后,相互唱和以相互激励,“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馀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15]。虽然诸如王沂孙、张炎、周密、蒋捷等以山水为寄,但宋元易代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遭到沉重打击,少有真正的惬意和快乐,南宋虽然政治腐败,但家国完整,南宋灭亡,他们只能以隐逸自保气节,从山水田园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看一下南宋灭亡给这些文人带来的伤害,周密是南宋遗民词人的领袖人物,宋亡前曾为义乌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借亲友资助寓居杭州。邓剡“一门十二口都死于战乱”,王沂孙亡国之后也是过着“形容憔悴,料应也、孤吟山鬼”的生活。张炎更是如此,在宋亡之前,张炎出于词学世家,多才艺,能度曲,乃是南宋初期功臣循王张俊的后裔,祖父张濡和父亲张枢地位显赫,他身为富家公子过着悠游的读书交友游乐生活,但在元兵进入临安之时,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因祖父张濡镇守独松关时,部下误杀元朝使者、礼部尚书廉希贤,临安陷落时惨遭元兵报复,祖父被凌迟处死,家产被掠,家人或被杀或被掳,父亲张枢也下落不明,张炎侥幸逃脱,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不得不以文寄食于人。他那首非常有名的《解连环·孤雁》词系是他这种身世和情景的再现: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卷半[15]。
张炎词中孤雁失群惊散的凄惨,实为词人家国两失之痛,虚实结合,既写物又写人,展现当时亡国文人士大夫的悲苦遭遇和漂泊不定的悲苦凄凉,暗含亡国之痛的哀思。
王沂孙宋亡后隐居遁世一段时日,因生活衣食无着,入元后为谋生计,曾出仕为庆元路学正,但其词作也是沉郁幽深、哀思凄婉、悲苦无依之状,如其《扫花游·秋声》:
商飙乍发,渐淅淅初闻,萧萧还住。顿惊倦旅,背青灯吊影,起吟愁赋。断续无凭,试立荒庭听取。在何许。但落叶满阶,惟有高树。迢递归梦阻。正老耳难禁,病怀凄楚。故山院宇。想边鸿孤唳,砌蛩私欲。数点相和,更著芭蕉细雨。避无处。这闲愁、夜深尤苦[16]75-76。
落叶、孤雁、芭蕉、细雨多种意象组成了凄清秋景图来烘染词人那颗悲苦不堪的心和潦倒穷愁的生活状态,读罢黯然失色。张炎经历了无奈之后词风变得疏旷了,他心志上获得了自由,才能超脱心灵苦闷,才能求得安闲,登临山水,能赏得自适的清幽世界,陶醉隐居优美环境中,深得道家隐居终老、旷达任性的自然之道,词风变得朗畅清疏,清空、雅正,这才是张炎的特色,张炎论词提倡“雅正”“自然”:“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陈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20]38,也是这样心态才能有的。
当他们结束飘泊流离生活后,内心平复了,才能在白云、青山、流水的自然景色中心态保持平和,真正看到青山是山,流水是水,不再看山也悲苦,观水也伤情,多以词抒写山林云水间甘于恬淡,以参禅悟道保持心态平和,以隐逸追求安乐。如蒋捷在《沁园春·次强云卿韵》中说:
结算平生,风流债负,请一笔句。盖攻性之兵,花围锦阵,毒身之鸩,笑齿歌喉。岂识吾儒,道中乐地,绝胜珠帘十里楼。迷因底,叹晴干不去,待雨淋头。
休休,著甚来由。硬铁汉从来气食牛。但只有千篇,好诗好曲,都无半点,闲闷闲愁。自古娇波,溺人多矣,试问还能溺我不。高抬眼,看牵丝傀儡,谁弄谁收[18]。
不再以秦楼楚馆、歌席酒筵寻欢作乐,而是在大自然清景中细细品位山林云水的隐逸乐趣,词人胸怀大畅,体验那种闲适、淡泊的快乐。南宋遗民词人忘却或减轻了感情上的沉重负担,开始在隐逸田园山水中享受平淡之趣,心境宁静适意了,心态自然也平和了,无论一丘一壑,一花一草,是渔樵共话,还是茅斋索居,都变得清新可喜了。他们的词作即使写隐逸也有不同的个性,有旷达潇洒的,有闲适疏狂的,有宁静悠闲的,有诉诸佛道排遣忧郁的,不同的隐居方式,不同的个性,形成了元初南方词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元初南方遗民词人更重视词体功能,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9]认为词可以委婉含蓄地抒发诗所不能言的情,他们绝少涉及男女艳情一类,多抒写隐逸生活的状态与情致。
由此可知元混一之后,词坛上依然是北宗与南宗并峙的现象。南宋遗民词人张炎、周密、仇远入元后,依然是按照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创作词,或述幽怨悲怀,或浅吟隐逸闲适,由于他们极力倡导“雅词”,张炎作《词源》张扬其“清空骚雅”的词学观,给元代词坛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复雅风气。元初北方词坛包括由金入元的遗民词人元好问、杜仁杰、杨弘道、段克己、段成己、李俊民,还有仕元的文人郝经、刘秉忠、许衡、杨果、张弘范、卢挚、王恽、张养浩、刘敏中、白华等,其他金源词人李治、姜彧、王旭、曹伯启、曹居一、白朴、刘因等,他们仍多属苏、辛一脉,元初北方词坛创作成就和艺术成就也十分可喜。如上文所言,北宗词以“清”为审美好尚,北宗词人很少专写词的,多是词曲兼善,如张养浩和刘敏中,或者是诗文名家,如卢挚、姚燧、王恽以诗文为主兼写散曲,并不是全副精力都投入词创作,因而和元初南方词坛无法相比,南方词人无论是词作水平还是词人群体均高于北方词人,尤其是仇远(1247—1326)入元后近50年才去世,词多作于入元后,与张炎交善,元后期重要词人张翥、张雨等皆出其门,受其沾溉,仇远可谓元词南宗之祖。
随着赵孟頫、仇远、吴澄、赵文、刘埙、詹玉、冯子振、蒲道源、虞集等南方词人先后入仕,他们挟南宋雅词传统以入北方词坛,与北方词坛的王恽、胡祗遹、魏初、卢挚、姚燧、梁曾、张之翰、刘敏中等,在元大都形成北、南词风交汇合流趋势。所谓“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21],南北分合是元代词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在元代结束了长期的地域阻隔和政治态度的差异而造成的隔膜,及其文化观念上的相互排斥,经过不断的磨合交流,逐渐融合为一。赵孟頫和虞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他们在当时文坛地位和影响力,再者他们大批优秀词作产生较大的影响,赵孟頫所作词不事雕琢而保其自然真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南宗词人,吴梅《词学通论》称:“其词超逸,不拘于法度,而意之所至,时有神韵。”[21]虞集被认为在元代词坛上“最为雅正”,“兼擅苏、秦之胜”,由于虞集在政坛和文坛上的地位,其创作对于南北词风的融合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同一般,虞集被认为从延祐年间到元末期间最突出的词人。“南风之熏兮”南宗词在元代再度复兴,曾兴盛于南宋词坛的“雅词”占据了上风,词坛形成了以雅正为宗的风气,以北宗词豪放俊逸之气渗透到了清空、雅正的南宗词的创作之中,而放弃北宗词诗化和曲化的现象,更重视词体观念,因词的诗化和曲化会导致词体本身某些艺术特性的丧失,创作主体也以阵容壮观的南方词人为主,无论作品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元后期,以张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活跃在江南一带的文学创作群体,张翥是北方人,长于南方,受南方地域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又跟从倡导风雅的仇远学习,其词被誉为“元词之冠”,在张翥周围有着一个经常宴集唱和并以雅正相尚的词人群体,如谢应芳、倪瓒、邵亨贞、危素、顾瑛等承袭“仇白”词风,其词风大多也为近姜张者,以风雅为尚,即使托迹为黄冠的张雨,其词也是以浓郁的文士气息居多。
三、词曲的融合
元词沿金词方向发展,作法呈诗化兼曲化倾向,大凡个人怀抱、人际交往、游赏品物、社会百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可见诸词人笔下,受元曲影响,许多词纪俗事、写常情,未尝不是词体开放的积极尝试。尤其是元代北方词人群体的词作曲化倾向较明显,元词的曲化并非元词之衰亡,这种文体的互相渗透,是词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换个角度来看,词体能以诗为词,扩大词体的抒情功能,苏轼“词诗”观念能被词坛普遍接受,那么元词的曲化在词体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且直接影响了明词的曲化。
元代文人对元曲的评价很高,徐世隆说:“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22](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虞集也说:“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23](《中原音韵序》)把散曲与汉代的文章,唐代的律诗,宋代的道学相提并论,可见元曲在虞集心目中地位之高。如果说虞集属于在学术和文学观念上通达的贤者观点,我们从元末杨维祯评价曲的价值也能看到元人对元曲的喜爱:“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彦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25]元代文人对元曲非常看重,评价也高,而且自金代开始,文坛即是诗、词、曲三体并行,元代继承并延续了金代三体并行的格局,曲虽然是新兴的文体,但文人对曲的热爱使得元曲创作出现生机勃勃的兴盛局面,因而,词体受到曲体文学的繁盛的冲击和影响是必然的。元代很多词人是以曲创作为主,刘毓盘《词史》早已经指出:“关、马、郑、白为元曲四大家,鲜于枢、姚燧、冯子振、白无咎、乔吉、张可久、陶宗仪等皆工于曲,故其词亦近于曲。”[25]诸如马致远、白朴、刘敏中、张养浩、卢挚、乔吉、贯云石、薛昂夫等写词,但同是曲坛大家,元好问、杜仁杰、刘秉忠、张弘范、杨果、王恽、胡祗遹、姚燧、魏初、滕宾、虞集、鲜于枢、刘因、薛昂夫、杨立斋、赵孟頫、赵雍、张可久、张雨、徐再思、李齐贤、吴镇、沈禧、萨都剌、倪瓒、蒲道源、邵亨贞等也都是词曲兼擅,所以在他们写作时必然词和曲相互影响。
元词的这种类曲倾向主要体现在部分作品风格的通俗化或俚俗化上。“金元词的曲化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二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在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这方面主要指文人词在当时的俗文学——曲的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突出地体现在许多作品流利、明快、直率、浅白,甚或谐谑的语言特色上。词体曲化,从根本上说削弱了词体的自身特征,但对于处于不景气的词坛,也并非全然无益。”[26]散曲最大的特点在于“俗”和豪辣,词的曲化就是吸收元曲内容的通俗简易,语言的直白畅达,“词的曲化最直接的表征是仿曲为词,也就是指词人模仿市井俗曲的语言、手法、情调和意境进行词的创作,但并不改变原有词牌和音乐。”[27]26词体的类曲即是如此,因此,金元时代文人创造的一些小令作品往往使人词曲难辨,正如唐圭璋先生在《全金元词》凡例中所说:“金元人词集中,往往羼入曲调。如王恽《秋涧乐府》中,竟有三十九首曲调。其他作家亦多类此。是编于词集中之曲调如《天净沙》《凭栏人》《小桃红》《干荷叶》《水仙子》《折桂令》等皆不辑录。至如《太常引》《人月圆》等调,词曲全同,无法区分,则仍于词集中保留。”[6]3比如,元人冯子振写有《鹦鹉曲》42首,这些曲子似词又类曲,因而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一书全部收录,但现在学界仍然有很多学者分析认为冯子振的42首《鹦鹉曲》不是词而应当是曲。张可久也是词曲兼善的作家,他的15首《人月圆》被作为曲收入《全元曲》,而《全金元词》也全部收录,真是词曲莫辩。元好问的词也有类曲化倾向,如:
阿仪丑笔学雷家。绕口墨糊涂。今年解道,疏篱冻雀,远树昏鸦。乃公行坐文书里,面皱鬓生华。儿郎又待,吟诗写字,甚是生涯。(《眼儿媚》)[31]455
风格是词曲兼而有之,有词的流丽,也有曲的流畅和活泼。金元之际,曲文学骎骎以盛,作为通俗性、娱乐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这种时代文学风气下,词家填词不能不受其影响,于是此时期的词文学遂出现了“类曲化”倾向。如白朴,元曲名家,他填词时不知不觉有了曲的某些色彩和特征,情调真率自然,语言俚俗活泼,如《玉漏迟·题阙》一首:
碧梧深院悄。清明过也,秋千闲了。杨柳阴中,又是一番啼鸟。人去瑶台路远,孤负却、花前欢笑。音信杳。西楼尽日,凭栏凝眺。缥缈。雾阁云窗,恨梦断青鸾,夜深寒悄。檐玉敲残,捱得五更风小。麝注金猊烬冷,画烛短、银屏空照。芳径晓。惆怅落红多少[29]190-191。
“清明过也,秋千闲了”非常通俗明了,读起来朗朗上口,明白如话。“杨柳阴中,又是一番啼鸟”一句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句转化而来,后半部分则又是词体味道,写一个女子相思与闲愁,援引曲入词,倒也与其它清雅明丽的句子相融合,并不显得突兀。又如《西江月》:“世故重重厄网,生涯小小渔船。白鸥波底五湖天。别是秋光一片。竹叶醅浮绿酽,桃花浪溃红鲜。醉乡日月武陵边。管甚陵迁谷变。”[32]169风格更加曲化,直抒胸臆,置于元曲别无二致,曲的意象,曲的构思,曲的语言,俗白、清浅。
总之,元代多民族多元文化决定了元词的异质特征。在元曲兴盛的同时,元词退出主流地位,但元词有其独有的特色,本文仅以多民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词的繁荣,南北词风相互影响和融合以及元词的“类曲”化倾向等三方面来论述远不充分,要真正认识元词发展与元代词坛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元词已“衰”之论,元词与音乐关系等等,很多问题尚待展开,本文从以上三方面探讨元词走向以及其异质特征,粗陈管见,以待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