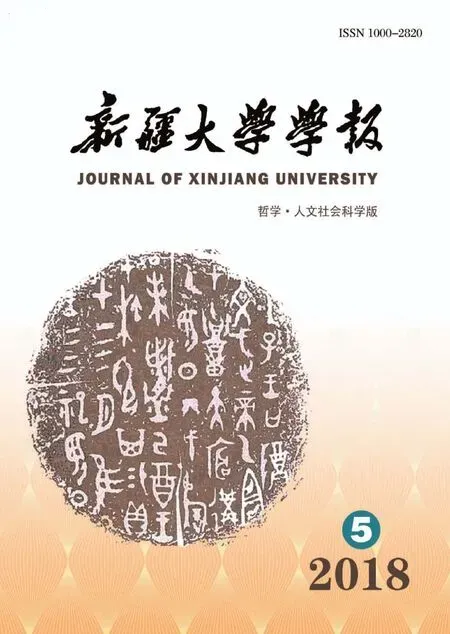通与变:论杜预之“左传”学*
刘运好
(亳州学院中文系,安徽亳州236800)
杜预“左传”学成就集中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下称《集解》)和《春秋左传释例》(下称《释例》)。《集解》问世不久即被列入学官,南北朝时与服虔注并行于世,清阮元又收录于《十三经注疏》中,影响十分深远。关于杜预《集解》研究,赵伯雄、戴维分撰之《春秋学史》,沈玉成、刘宁合撰之《春秋左传学史稿》及诸种经学史著作皆有评介。此外,海内外关于杜预《集解》研究论文也积案盈箱。然而,综合考察现有成果,关于《集解》学理特点、诠释原则、解经方法、义理特点之研究或付之阙如,或间有涉及,又语焉不详,故本文综考《集解》,证之《释例》,具体论述如下。
一、原始要终的学理特点
《集解序》不仅详细阐释了《集解》的体例特点及其产生缘由,也是一篇富有理论思辨的《春秋》学论文。浦卫忠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对此前之《春秋》与《左传》研究的一次理论总结和爬梳整理。”[1]《序》所论《左传》“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的特点,也正是杜预“左传”学的学理特点。其要者有三点:
第一,论述了《春秋》由史而经的历史形成。因鲁史而作《春秋》是一般史学家的基本观点。然而,自《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之论出,追寻《春秋》“诛讨乱贼以及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2]1的经学意义,则成为《春秋》研究的核心。《序》则从史与经的双重维度论述《春秋》的特质:“《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考其源头,《春秋》本是鲁国史书之名,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孔子乃因袭鲁国史策,辨其真伪,撰修《春秋》。其采摘旧史的部分,或文或质,或详或略,不加删改。且旧史所记,先标其时间,以明其事件原委。其记事亦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方法,以记载年月之远近,分别事件之同异。然而,孔子刊正旧史,修撰《春秋》又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即以“志其典礼”为核心,上承周公之遗制,下明后世之法度,以存教化,以示劝戒。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又是一部体现儒家思想的经学著作。可见,杜预论《春秋》乃推究源头,考察本质,从历史发展的原委上揭示《春秋》亦史亦经、由史而经的学理特点。
第二,论述了《左传》本原《春秋》的经学特点。自刘歆校书发现《左传》之后,是否立《左传》于学官,一直成为经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左传》是否立于学官的关键在于“经”之地位的确立,所以刘歆之后,学者为了立《左传》于学官,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就特别凸显《左传》重“礼”的特点,以争得“经”的地位。杜预以论《春秋》经为基点,从师承与释经两个方面阐释《左传》“经”的特质。《序》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在师承关系上,“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左传》是直接师承仲尼的结果;在经典认知上,丘明认为《春秋》经乃是不可刊削之书,具有“为经作传”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网罗圣人修撰《春秋》略不尽举的“旧史遗文”,且“广记而备言之”,著成《左传》,目的在于使学者能够推究渊流,因末求本。所以《左传》的四种释经方式:“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辩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于释尽经意而已。”[3]12行文与经虽有不同,却又尽在诠释经意。因此,在行文立意上,《左传》也本原于《春秋》,是直达《春秋》经意的津梁。
第三,揭示了经传义例同体的传承关系。《序》在论述《春秋》“志其典礼”的内容特点后,又论述其“发凡言例”,抽象出《左传》“三体”“五例”,论述其传经同体的义例特点。“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书'‘不书'……之类,皆所以起新例,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因为《春秋》志在昌明典礼,彰显法度,寄托圣贤大义,并形成相对固定的行文规则,即凡例。所谓“三体”,即孔颖达所言“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3]18三类。发凡正例乃周公所制,旧史之体,传以“凡”字引起,《左传》共有五十节,称之为“五十凡”;新意变例是旧史错失,仲尼正之,传不言“凡”,而以“书”“不书”等七类称之,以“发明经之大义”;归趣非例即经无义例,直书其事,传亦直接释之,明其旨归而已。传之三体,源自本经,故孔颖达谓“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3]17,表现出鲜明的传经同体的义例特点。上文所论《左传》四种释经方式,其中“依经”是正例,其余三种为变例,皆凸显了传经义例的一致性。所谓“五例”,孔颖达曰:“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3]18《序》概括曰:“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三体”的划分主要着眼于经传的形式作法,“五例”则主要着眼于《左传》“变例”或“新例”的叙事特点及其社会功能。杜预认为,《左传》“新例”的叙事特点有四:在语言与意义关系上,用辞幽微而意义显明,委婉以达意;在语言与叙事关系上,用辞隐晦而叙事有序,简约以明志;在语言与伦理关系上,用辞委婉而合乎伦理,避讳以示义;在语言与讽喻关系上,用辞剀切而不作迂曲,直言以见讽。《左传》这几种叙事特点,都旨在发挥一种社会功能:“惩恶而劝善”。虽然杜预之说取自《左传·成公十四年》而略加改动,但论述更为全面,且更为自觉地揭示了文本的审美属性及其功能特征,带有显明的“文学自觉”的时代特点。杜预所论“五例”(五体)是传与经的共同特点。通过这种义例,叙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左传》与《春秋》都具有“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的经典特点。
客观上说,杜预论述也有未尽合理之处,如将义例分为新旧两种,认为旧例乃周公所制之《礼经》,也引起后人不少非议。但是,杜预正是希望通过学理上原始要终、沿波讨源的方法,论证《左传》出于《春秋》,而《春秋》记事保留了周公礼制,既彰显了《左传》“经”的地位,也表现出古文学家尊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经学理路。所以沈玉成、刘宁将其“看成是对东汉以来古文学派意见的一次集中概括。”[4]139
二、比类相从的诠释原则
惟因杜预追求一种原始要终的学术理路,所以《集解》采用比类相从的诠释原则。在整体结构上,以传系经,兼取《公羊》《谷梁》,突出传与经的整体性;在具体阐释上,荟萃名家经解,见其同异,突出经学发展的连贯性。
关于《集解》注经的诠释原则,《序》有比较明确的阐释:“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淑),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杜预所论,要点有三:追溯汉魏《左传》学研究名家,论四家之优劣,并说明《集解》乃取诸名家之义而解之;说明《集解》名称之由来:按照年号,以传系经,排列经传,取其义类集而解之,故曰《集解》;解释《释例》的内容、体例、特点及其功用。补充说明的是:第一,《集解》荟萃名家止取四人,且未备列姓名,很难“以见同异”,故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序》提出了尖锐批评。然《释例》引四家之说以辨正之,则可见其同异。推论杜预原意,《释例》列举四家之异,《集解》则择善而从,融会贯通而别为之解。第二,杜预《集解》与何晏《论语集解》虽都是“集解”式著作,且成为后代经学阐释的经典范式,然二者体例并不相同。孔颖达曰:杜预之前,“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3]24杜之“集解”是汇集经传而为之解,何之“集解”是汇集众说而为之解,两家体例迥不相同。第三,《释例》重在解释《春秋》义例,与《集解》互相补充发明,共同建立了杜预“左传”学体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释例》又以是书为羽翼。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5]144因此,研究《集解》则不可不读《释例》。
所谓“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简言之即比类相从,这是杜预建构的基本诠释原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以传系经的“集解”范式;兼取《公羊》《谷梁》二传,融合三传的学术理路。
先言以传系经的“集解”范式。经传分立,是自汉之前的一个基本学术传统。孔颖达曰:“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3]24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汉代经师、门生,白首穷于一经一传是一种普遍现象,“经”为诸家通习的对象,“传”则为某一师门所授,因此后世传《春秋》者出现了《左传》《公羊》《谷梁》三个传承系统。而且由于刻写条件限制,对于诸家通习之经,就不再附于传前,这也自然造成经传分离的状态。直至杜预之前,经传分立仍是经学研究的一个常态。陆澄《与王俭书》曰:“《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6]684服虔《左传注》有传无经,只是一个典型例证而已。至杜预始打破藩篱,采用以传系经的“集解”模式,不仅凸显了传从经出的源流关系,为传争得“经”的地位,也论述了《左传》与《春秋》义例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互补性。《序》明确指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又曰:“《春秋》虽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固当依传以为断。”也就是说,“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3]21。这种开创性的“集解”模式,在经学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言融合“三传”的学术理路。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公羊》《谷梁》立于官学;刘歆之后,古文《左传》才开始为经学家所重视,并逐渐争得“经”的地位。然而,由于两汉经学传授的门户之见,造成了《春秋》三个传承系统各守壁垒,町畦畔然。直至魏晋,学风为之一变。一些学者开始抉破町畦,整合诸家学说。刘兆考察三家之异,整合而通释之,作《春秋调人》,又作《春秋左氏解》,《公羊》《谷梁》解诂皆周纳于经传的阐释中;氾毓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王长文据经摭传,著《春秋三传》十二篇。马宗霍云:“此皆兼治三传之学者:乃或调之,或正之,或通释之,亦自我为法,不同前人矣。……是故魏晋经学,王、何既以名理易训诂,杜、范复以博采破颛门,持较两汉,得失诚未易评,然其自为魏晋之学,则可断言。盖亦经学之一大变也。”[7]68荟萃旧说,融合贯通,是魏晋经学基本特点。杜预《集解》既是这种学风变化的产物,也体现了这一学风变化的特点。
“简二传而去其异端”,是杜预取舍的基本原则。所谓“简二传”,即选择《公羊》《谷梁》之说,或正误,或补充。第一,若《春秋》经误,援引二传以正之。如庄公六年:“冬,齐人来归卫俘。”杜注:“《公羊》《谷梁》经传皆言‘卫宝',此传亦言‘宝',唯此经言‘俘',疑经误。”孔颖达又引《释例》曰:“‘齐人来归卫宝',《公羊》《谷梁》经传及《左氏传》皆同。唯左氏经独言‘卫俘',考三家经传有六,而其五皆言‘宝',此必左氏经之独误也。”[3]228此类情况在《集解》中惟此一例。第二,若《左传》失载,援引二传以释经。如庄公十九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无传。公子结,鲁大夫。《公羊》《谷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其称陈人之妇,未入国,略言也。”此类情况在《集解》中最为普遍。所谓“去其异端”,孔颖达解释曰:“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3]23《春秋》亦有今古文之别。《汉书·艺文志》载有《春秋古经》十二篇,是《左传》所依据的古文经;又载《春秋经》十一卷,是《公羊》《谷梁》所依据的今文经。按照周予同先生《群经概论》的说法,“在内容方面,《左传》以‘史'为主,而《公羊传》则以‘义'为主。”[8]261“《谷梁传》的体裁,与《公羊传》相近,而与《左传》不同。”[8]263杜预《释例》固然受二传对《春秋》义例阐释的影响,然其《集解》则惟取“二传”的史料,或正《春秋》之失,或补《左传》阙文,却不取“二传”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故曰“去其异端”。可见杜预注经,虽融合三传,却又仍然站在古文家立场上,取舍相当严格。然而,融合三传以解经,所表现出的学术胸襟,援引二传以正《春秋》经之误,所表现出的学术态度,都需要有极大的学术勇气,尤其是后者。
综上,杜预《集解》所采用的比类相从的诠释原则,既表现出原始要终的一贯的学术理路,凸显了学术思想的历史性、逻辑性原则;也表现了开放的学术胸襟,不盲从经典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三、以传释经的解经方法
由于《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寓一字以褒贬,往往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后人不遗余力地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三传”就是传述《春秋》的经典之作。因为“《公羊》《谷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传乱之”[3]33,杜预乃错综微言而著《集解》。以传释经以彰显其微言大义,是杜预解经的基本方法。
所谓以传释经,即以《左传》阐释《春秋》之义。其《序》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杜预藉此说明:第一,以传释经的必要。《春秋》与《易经》不同:《易》一爻之变,则成一卦;《春秋》则必须藉语句的聚合,方可以传达意义;而《春秋》经语言简约,必待传之阐释而彰显其意义,故当依传为断。第二,以传释经的理由。《左传》为经作传,故经之义例,必依赖传而阐明之。故《集解》之不同者,则专以《左传》以释经。第三,以传释经的体例。《左传》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推原变例,即可正经的褒贬之义;若《左传》未解,则简选二传,撷取符合经义的内容而删汰异端,这才符合左丘明的本意。如果说,以传系经的释经原则偏重于“原始”,那么以传释经的解经方法则偏重于“要终”。
从《序》的分析还可以看出,所谓以传释经,实际也包含释传以明经义。因此论述《集解》以传释经的方法,必须从解经和解传的两个层面考察。
从解经的角度看,以传释经是基本的诠释方法。因为《春秋》叙事“微而显,婉而辨”,欲昭明其义,必赖其传,故杜预以传释经。下文以“隐公”为例论述之。
其义例阐释有两类:第一,阐明正例。正例是周公依据礼仪制度所定之义例,举凡此类,杜注则以“凡”概言之。如“元年,春,王正月”,杜注:“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也就是说,人君即位,因为希望这是泽被万物的开始,故不说一年一月,而谓之“元年”,这是《春秋》的通例(正例)。传曰:“不书即位,摄也。”故杜预曰:隐公虽未即位,而摄政君主之事,亦行朝庙告朔之礼。这就将《春秋》所以谓“元年”,又未书“即位”的义例阐释得非常清楚。下文所言“郑人伐卫”,杜注“凡师有钟鼓曰伐”,亦此例也。第二,辨析变例。所谓变例乃是孔子匡正旧史所定之义例,凡此类义例,杜注则以“例”概言之。如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从字面上解释,经句是说元年三月,隐公与邾君在蔑地结盟。然而,传在此句后又有“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通过综合考察《左传》与杜注,则可知,邾子名克,字仪父。因为邾子只是诸侯国的附属小国,周王并未封其为侯,故没有记载其爵号。按照《春秋》正例应该直接称邾克之名,称“字”即是一种尊称,乃因为“其后仪父服事齐桓以奖王室”的缘故。杜预取《左传》内容将《春秋》之变例阐释的非常清楚。
其内容阐释亦有两类:第一,彰显褒贬。《春秋》以特定的义例,寓褒贬于简约的记事之中,若无传述,则难明其义。如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杜注:“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郑伯虽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隽杰,据大都以耦国,所谓‘得隽曰克'也。”郑伯与公叔段血缘上是兄弟,政治上是君臣。郑伯讨伐公叔段,不称国而直接言郑伯,不言弟而直接称段,不言以君讨臣而用“二君”,是讽刺郑伯为兄失教之过,共叔段为弟凶逆之情,既失君臣之礼,又失兄弟之情。这实质上也就是“推变例以正褒贬”。杜预的解释也是取自传“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而加以发挥。通过杜预分析,《春秋》的微言大义更加历历可辨。第二,辨正讹误。上文已论,《春秋》记事亦偶有讹误,杜预引经传以正之。如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注:“八月无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误。”孔颖达疏:“杜勘检经传上下月日,制为《长历》。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无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则九日有庚辰。杜观上下,若月不容误,则指言日误;若日不容误,则指言月误。此则上有秋,下有九月,则日月俱得有误,故云‘日月必有误'也。”[3]65通过孔氏所考,可证杜预引传而辨正讹误的准确性。此外,若有经无传,意义明确则直接注明“无传”;若有微言大义则藉《公羊》《谷梁》二传以释之,这在上文已有论述。一般说来,杜预注经,有传则略,无传则详。
总之,取传之内容,通过“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的方法,辨析《春秋》义例所蕴涵的深刻内容,是杜预注经的基本特点;“以传为断”,正经之讹误,则是杜预注经的创造性。
从解传的角度看,释传明经也是基本的诠释方法。杜预注经,重在阐释所取之义例,或义例所包含的微言大义;注传,则以训诂为基础,以解释传义为津梁,进一步补充、明晰经义。重点则是阐释义例的具体内涵,或义例的确定原则。下文以“庄公”为例论述之。
就其训诂而言,或训释词义,如二十二年,“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弛于负担”,杜注:“羁,寄也。旅,客也。宥,赦也。弛,去离也。”整个意群,皆为训释词义。通过训释词义,以扫清理解传义的障碍。或训释名物,如四年,“于樠木之下”,杜注:“樠木,木名。”又训释地理名号,如十年,“荆败蔡师于莘”,杜注:“荆,楚本号,后改为楚……莘,蔡地。”或训释礼制,如十一年,“列国有凶,称孤,礼也”,杜注:“列国,诸侯。无凶则常称寡人。”所训释内容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礼乐、典制等诸多方面,征引广博,解析允当。
就解释传义而言,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第一,解经揭示义例,通过释传明晰义例的具体内涵。如十一年,经曰:“公败宋师于鄑。”杜注:“传例曰:敌未陈曰败某师。”传曰:“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杜注:“通谓设权谲变诈以胜敌,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陈独败为文。”注经惟在说明其所采用的义例,注传则重在说清其内涵:对方部队尚未排成阵列,即攻击之,是乃以权谋机诈而胜敌,谓“败某师”;若以双方列阵而正面胜敌,则不可谓“败某师”。“败某师”乃有虽然取得胜利却不符合道义的含义。这就将《春秋》义例的内涵揭示得非常清晰。第二,经传无义例,通过经传互释而阐释其义。如十二年,经曰:“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杜注:“捷,闵公,不书葬,乱也。”传曰:“宋万弑闵公于蒙泽。”孔颖达引《释例》曰:“先儒旁采二传,横生异例。宋之蒙泽,楚之乾溪,俱在国内。闵公之弑,则以不书蒙泽国内为义,楚弑灵王,复以地乾溪为失所,明仲尼本不以为义例,则丘明亦无异文也。”[3]247国君被弑而经不书葬,是因为发生内乱的缘故;诸侯之君被弑于国内,传或书地名,或不书地名,是史书叙事有详有略,并无一定义例,也没有特定含义。此乃经传皆无此义例,杜预补充说明之。举凡这类情况,杜预皆以经传互释的方式,阐明事件原委,揭示其意义。第三,经传书例不同,通过释传而补充辨正之。如十四年,经曰:“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杜注:“背北杏会故。”传曰:“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杜注:“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经书人,传言诸侯者,总众国之辞。”传补充了“齐请师于周”的史料,因此经、传叙述义例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因此杜注的重点也各不相同:其注经说明齐、陈、曹伐宋的原因;注传则阐释经、传义例不同的原因。然而,“经书人,传言诸侯”是否有特别含义?杜预认为,都属于“总众国之辞”,并无褒贬之义。孔颖达引《释例》云:有经称“人”,传称“诸侯”,亦有经称“诸侯”,传却称“人”,“此盖当时告命记注之异,非仲尼所以为例故也”[3]251。但是诸儒注释,皆“据案生意”,深文周纳,认为寓有褒贬之义,实际上都没有经、传的依据。通过杜预辨正可以看出,经、传书例有时虽有不同,也并非有特定含义,不可穿凿附会。总之,杜预注传,释义清晰,考辨翔实,成为准确理解经义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上所引例证可以看出,杜预《集解》所采用的以传释经、注传明经的诠释方法,使其注经与解传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通过阐释义例、补充史实、训诂语词,既阐明其微言大义,又辨别同异,匡正讹误,并在注释中表现自己的明于兴废之道的思想倾向。
四、经权思想的现实倾向
杜预是典型的古文经学家,其《集解》与《释例》遵循“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的阐释原则,因此很少脱离经传而自由发挥。因此,杜预注经,以阐释经传思想为旨归。然而“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晋书·杜预传》),又是杜预治学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杜预学术,并非仅仅是独坐于书斋中的把玩经典,而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对经典“权义”的双向阐释上。
《集解》《释例》发明了《春秋》之正例、变例,孔颖达曰:“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3]16其实,这既是杜预对《春秋》体例的发明,也隐含着一种“权”与“义”的辩证逻辑。唐刘蕡《春秋释例序》曰:“圣人文乎鲁史,志乎周道,笔削隐显,有权有义,一正于周制而已。权焉,故有讳国恶、避世祸、矫事以变文也。义焉,故有例典礼、贬僭乱、尊王以行法也。彰明五始,上禀班朔布象之本,则公旦礼经,列国群史,悉得书之矣。详略一字,下救衰俗;强臣之渐,则仲尼志蕴,异代鲜克究其极焉。有晋大儒杜预,皓首《春秋》,深明权义,乃谓学者未可与权,必先讲义。义之通明,概有宗本,举一则推万,可知计源,则众流毕会。”[9]597有权有义是《春秋》的义例特点。所谓“义”即正,是经的不刊之论,典章礼制、贬斥僭乱、尊王执法皆属于“义”,是国之大体;“权”即变,是经的权宜之变,讳言君恶、避祸全身、曲笔隐文皆属于“权”,是政治或行为之策略。刘蕡认为,杜预深明权义之别,并且以义为宗。其《集解》《释例》,一方面强调德、仁、义、信、礼、孝、亲等儒家的经典伦理;另一方面又突出孟子所发凡的儒家权变的逻辑,带有因时而变的思想倾向。以“义”为正,以“权”为变,是杜预思想的基本特点。这种思想在《集解》《释例》中表现比较复杂,有政治的,也有伦理的;有治国方略的,也有政治权术的。下文从君权与政权的两个主要方面加以论述。
在君权上,杜预强调君主之神圣,臣民之忠诚,然而又曲辩弑君之罪。宣公四年,子家弑郑灵公,“君子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注:“称君,谓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终为不义。”孔颖达引《释例》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故戴之如天,亲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严,雷电之威,则奉身归命,有死无贰。故传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执之常也。然本无父子自然之恩,本无家人习玩之爱,高下之隔悬殊,壅塞之否万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诚以感之,然后能相亲也。若亢高自肆,群下绝望,情义圮隔,是谓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则位号虽存,无以自固,故传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称君者,惟书君名,而称国、称人以弑,言众之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主名,以垂来世,终为不义而不可赦也。'”[3]607从臣民的角度说,君主御民是上天的意志,君就是天,所以臣民必须爱戴之、亲近之、仰视之、事奉之,即使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也必献身而受君命,至死也无贰心。然而,从君主的角度说,因为君与臣无父子之恩、血缘亲情,上下阻隔,堵塞不通,所以在上之君必须心系于下以体察臣民,以诚心感动下人,然后才能君臣相亲。如若君主高高在上,纵恣放肆,则阻隔毁坏了君臣情义,于是臣民绝望,视君主如若路人。一旦人心涣散,君主之号虽存,则君位不稳。杜预又将春秋弑君之例,分为君罪、臣罪两种。若是君罪,臣民共绝之,虽弑之亦非臣下之过。这种对弑君之例的曲辩甚至回护,在昭公三十年孔颖达所引的《释例》中说得更为明白:“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季氏未有篡夺之恶,公虽失志,亦无抽筋倒悬之急。听用隶竖,侥倖之私,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身死于外,见贬于春秋也。”季氏是鲁国之臣,舞八佾于庭、祭泰山、敛财富、伐颛臾,操弄鲁国政权,是一个典型的逆臣,故孔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然而,杜预却对季氏虽“贰鲁侯”的行为极力回护,并认为,君主听信小人,存侥幸之私心,才造成“身死于外,见贬于《春秋》”的后果。
杜预的这种思想倾向,不仅与圣人迥异,而且与秦汉以来的主流意识也相差甚远。自秦汉建立中央专制集权后,君主具有绝对权威,一切善归于君,一切恶归于臣,董仲舒《春秋繁露》曾有详细论述。杜预之所以曲辩弑君、回护逆臣之行为,实际上是以阐释《春秋》为手段,为司马氏的篡逆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司马氏弑曹髦、杀名士,最终篡魏建晋,这种血腥而大逆不道的篡权行为,经过杜预的阐释,在理论上就合法化了。
在政权上,杜预强调国之礼制、王度,君主之权威,然而又突出君主设官分职、厚以待下,注重民力、民心。社会的伦理秩序是集权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方面秩序是国家礼制的表现,另一方面君主也正是在秩序中显现其绝对权威。故《释例》曰:“朝以正班爵之义,率长幼之序,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古之制也。”[9]603颁布爵位,长幼有序,是朝聘训诫上下的主要目的。诸侯朝聘,既是礼制,又可构建显示君主权威的政治秩序、政治昭明。杜预进一步论述道:
第一,就政治秩序而言,首先必须设官分职。文公六年,杜注:“诸侯每月必告朔听政,因朝宗庙。”孔颖达引《释例》曰:“人君者,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远细事以全委任之责,纵诸下以尽知力之用,总成败以效能否,执八柄以明诛赏……故受位居职者,思效忠善,日夜自进,而无所顾忌也。天下之细事无数,一日二日万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有时而用之。如此则六乡六遂之长,虽躬履此事,躬造此官,当皆移听于内官,回心于左右,政之秕乱,恒必由此。圣人知其不可,故简其节,敬其事,因月朔朝庙,迁坐正位,会群吏而听大政,考其所行而决其烦疑,非徒议将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恶其密听之乱公也,故显众以断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万民以察,天下以治也。”[3]509因为治理天下,琐细之事万端,若人君皆亲历躬行,力所不堪,必然听信于宫廷内官,如此,则下层官僚又听命于内官,这就可能造成政令不通,皇权下移,故人君必须通过设官分职,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使自己始终居于权力的顶端,而后因智力而使用之,以成败而考察之,执权柄以赏罚之。并藉朝聘制度,形成垂直畅通的政令体制,惟此才能“上下交泰,官人以理,万民以察,天下以治”。可见,皇权的绝对权威是建立在有效的政治体制和国家职能上。
第二,就政治昭明而言,就必须厚以待下,注重民力、民心。从君臣关系上说,“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股肱元首,同体合用,相须而成也。然假异气以合德,执名义以相服,非忠诚之感,和理之应,则四体交兢,元首失德,燕款以多宠见逐,郑突以专臣失位,蔡朱以外谗出奔,莒展以弃人不立。由此观之,君臣之间,有衅多矣。唯秉德而志公者,必博听而远览,无常亲也,无常疏也。有亲必有疏,有常必致非常也。此人君之安危,今古之成败也。”[9]656君与臣如元首与股肱,是相辅相成的一体关系,所以必须同心同德,各守名位,服从于义。如果为臣不忠,为君不德,则君臣产生嫌衅,或失位,或见逐。故为人君必须无亲无疏,惟在秉德志公,博听远览。然而,这种君臣关系又必须建立在人君厚以待下的前提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杜注:“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所以示薄厚也。”孔颖达引《释例》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疾则亲问焉,丧则亲其小敛、大敛,慎终归厚之义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不书日,示厚薄,戒将来也。”[3]47杜以《春秋》为例,说明君主对待股肱大臣,有疾则亲自慰问,病死则亲自参与殓葬,以显示其慎终归厚之义。他还推而广之曰:“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诚以感之,然后能相亲也。”从道义与情感上表达君主的诚心和亲和力,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政治生态链。从治国御民上说,杜预强调王度,又注重民力、民心。中国封建社会,制由天子,天下莫不统一于天子之制,故《春秋》反复强调“王度”。以王度使民是封建时代治国御民的基本政治伦理。然而,王度是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上。《集解》发挥了《左传》民本思想,明确指出:“民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昭公元年)又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桓公六年)神之主是民,道之心是忠于民,若“信于神”,就要恤民、利民。这种对春秋时期神灵信仰的世俗化解释,恰恰反映了杜预民本思想的时代光辉。他又从两个方面论述之:一是“国之用民,随其力任”。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引《逸诗》:“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注:“言国之用民,当随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随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饱过盈之心焉。”浦卫忠解释说:“杜预用形象的‘如金冶之器,随器而制形'的比喻,来解释‘式如玉,式如金',十分巧妙地将‘形民之力'与‘王度'结合起来,以民力作为‘王度'之根本。所谓‘随其力任',除了‘王度'应顺应民心、因民所利而利之含义外,还强调了王之‘惜民',即治理国家,应当珍惜民力的思想。”[10]治国御民,除必须遵循王度外,还必须“随其力任”,切忌聚敛无度,满足其“醉饱过盈之心”。二是“酌取民心以为政”。治国理政的核心是“酌取民心”。只有做到抚民以信,以德治政,才能够真正“酌取民心”。
综上,杜预从君、臣、民的三维关系上,论述了和谐政治秩序的建立;从王度、政体、御民的三个层面上,论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谋略。其政权理论则是为司马氏治国御民提供政治方略与权谋。可见,“明于兴废之道”,是杜预学术的基本特点。
虽然,《集解》对《春秋》义例的阐释、微言大义的发挥,或曲经以从传,也间有穿凿附会之处,《直斋书录解题》首先发难,清中期以后,诟病之议论蜂起。赵伯雄《春秋学史》总揽前人批评,概括为“曲从《左传》,违背经旨”“隐没前贤,迹近攘善”“疏于训诂,好逞臆说”[11]299三个方面。然而,以传系经、原始要终的学术理路,比类相从、以传解经的阐释模式,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春秋》学的发展与深化。特别是大胆地匡正经传的谬误,在那个时代是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的。杜预《集解》及《释例》所阐释的理论本身以及治国之方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