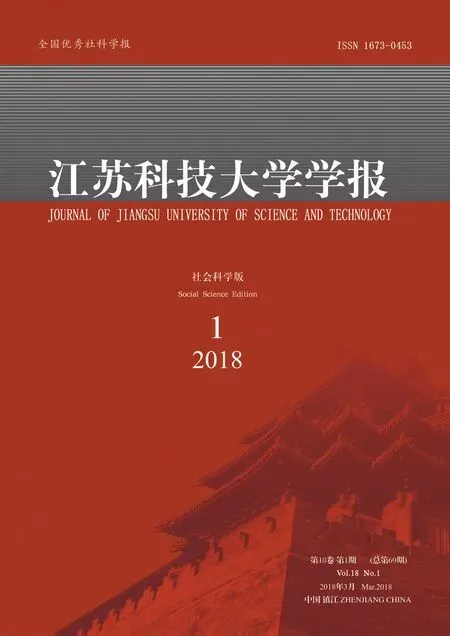葱郁在“南高原”的故乡
——谭宁君诗歌论
董迎春, 覃 才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在故乡主题的书写中,乡村与城市并不处于同一个意识维度。乡村与城市的区分,不能算完整的故乡主题书写。因为现代的乡村区别于古代的乡村,现代的乡村是正在城市化的乡村。乡村的城市化,或城市化蔓延至乡村,理应成为重要的故乡主题书写,不应区分开来。诗人谭宁君的故乡书写,涵盖个人记忆中原有的故乡重庆开州的书写,也包括乡村城市化、四川“南高原”地域普遍的故乡书写。他关于故乡和乡愁的诗性言说及心灵价值的体认与探求,既形成了他个人追求的诗歌书写意义,也完成了故乡书写的地域观照及生命意识道说。
一、 两种“乡愁”
故乡是个复杂的诗歌书写对象,诗人对故乡书写的偏爱,要么在开始写作的时候,要么在写作很成熟的时候。前者是以故乡作为叙事媒介寻找诗歌写作的门径,偏重方法和抒情,属于一种诗歌入门的直浅书写;后者随着诗人年龄的增长和人生经历的丰富,故乡作为诗人反思人与世界本体意义的对象再次出现于诗中,成为一种深度而复杂的书写。从诗歌写作意义角度看,后一种故乡书写因写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往往更有价值。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谭宁君,近年来偏重故乡的写作,因个人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的故乡书写就属于第二种书写。
诗人的故乡是一种过去,是很多往事的集合。这些时间和事件的过去性、丰富性不仅让诗人产生了书写的压力和渴望,更让诗人产生以此复杂而厚重情感进行某种深度的“诗歌制造实践”的可能。“诗人是诗歌的制造者,而诗的内容则是诗人全部的生命感知。”[1]85诗人书写故乡,感知故乡的全部内容,靠抓住过去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不在场性,靠抓住过去时间、人物、事件在岁月里发酵出的乡愁之感与生命之思。综合地看,诗人谭宁君的故乡书写有两种乡愁。一是关于亲情和乡土风物的“温暖性乡愁”,二是故乡变迁与城市化的“寒冷性乡愁”。在诗作《不可丢失的两种往事》中,对个人诗歌写作中的两种乡愁,诗人谭宁君说道:“温暖的往事不可丢失”,“寒冷的往事不可丢失”[2]65。在故乡的维度上,这两种不可丢失的往事是诗人谭宁君乡愁表达的意义核心和价值所在。
因为亲切的地域、亲情和乡土风物,过去的故乡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面对自己的故乡,诗人谭宁君捕捉到这种人所共有的温暖感觉,并通过诗歌艺术把这种温暖感觉上升到个人化的“温暖性乡愁”书写。对这种“温暖性乡愁”,谭宁君写道:
挽朝阳,踏清风的轮滑,/走,伙伴们,到田野去!/去寻找那些走丢的麦穗,/它们是乡亲滚落的汗珠,/它们也是迷路盼归的小伙伴,/你,听到它们的哭泣了吗?//我们,拾回了父母的微笑,/我们,拾回了满心的阳光。(《走,拾麦穗去》)[2]94
小麦是高原地区的故乡最本质的象征物,是体现故乡人情味和生命意义的想象符号。“走,伙伴们,到田野去!”诗人谭宁君与童年的伙伴奔跑在田野里“拾麦穗”的记忆场景是快乐与温暖的,这种温暖经由时间的沉淀成为乡愁最丰实的组成成份,这种记忆很容易在诗句间被回忆与呈现。“诗是体验,这些体验同某种具有活力的接近方法相关联,同某种在生活的劳作中,在严肃中完成的行为相关联。”[3]75诗人谭宁君的乡愁体验,有关于童年伙伴的温暖记忆,更有关于父母辛苦劳作的温暖瞬间。这种父母劳作的体验,是一种有活力、有诗性关联性的体验。“去寻找那些走丢的麦穗”,“我们,拾回了父母的微笑”,“拾麦穗”行为除了是童年的一种娱乐,更是让父母开心的最美瞬间。诗人谭宁君“温暖性乡愁”书写坚实地捕捉到乡愁之中关于童年时光与父母之情的本质内容。
每当生活的车遇到浓雾重霾/母亲自己,便化作一枚顶针/母爱凝成针尖,勇敢无畏顶上去/压顶黑云,就被顶开针眼大的一个洞/一丝丝阳光,从这里透过来,透过来/无边的暗,就被一点点撕裂/岁月,依旧花环体一样美丽圆满。(《顶针,是母亲用得最好的修辞》)[2]8
乡愁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谭宁君家庭并不富裕,在艰难的年代对人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品质和精神。回忆那个艰难年代时,诗人谭宁君说:“母亲的乐观、坚韧、能屈能伸,对我和姐姐妹妹的影响都很大,让我们一生受用。”[3]后记由于母亲的特殊意义,谭宁君对母亲的回忆与想念是积极的。在诗歌这种艺术载体中,母亲是“深植中国土壤并有着中国文化内涵与人格力量的原型人物”[4],而“顶针”是与母亲关系非常密切的物件,在诗人的记忆中,母亲用这枚“顶针”支撑那个艰难年代的家,也用这枚“顶针”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变好。细小的“顶针”在诗人谭宁君的乡愁里是母亲的象征,更是他多年后怀念母亲与故乡的情感涌现对象,在诗中被温暖地观照与想象。
古代的乡愁多是咏物思乡感人,现代的乡愁远不止古代乡愁那么简单与直接。现代人的乡愁不仅包括对过往的回想和过往变迁的感叹,更陷于对今时今日的异变,及对在此种异变之下个人、故乡、城市三者关系的思考。对现代人来说,城市化是乡愁的重要内涵。现代的乡愁,很大的一部分是在现代社会压力下产生的,这种乡愁交织着人、事、物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现代性的乡愁,即故乡城市化的乡愁,是诗人谭宁君诗歌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
粮仓里装艺术/看起来很雷人 也很酷/只是奇怪 艺术住进粮仓/粮食们逃亡到哪里去了呢//从高高的透气窗我发现一方瓦灰的天/不是画的 是真正的瓦灰瓦灰的天/像孤独的独眼 独自疑惑茫然/一束浑浊的泪光 潸然而下。(《谁走丢了粮食》)[2]34
这是诗人谭宁君参观艺术粮仓时即时的发现与感受。朝向城市化变化的故乡,属于故乡标识性元素的“粮仓”被城市化和艺术化,用于参观与游览。故乡在城市化变化的时代氛围里,正在慢慢失去原来的朴实属性。故乡与乡愁之感的淡化,成为诗人谭宁君的一种生命担忧与反思,成为他对故乡变迁与城市化的“寒冷性乡愁”书写。
寻寻觅觅,开始于一条临水的半边街/很民族的建筑里,拥挤着喘息与混合体味/城市有的这里有,城市没有的这里也有。(《泸沽湖之夜素描》)[2]177
故乡城市化的结果是故乡农耕习俗与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消失,让故乡变成“大城市有的,这里几乎全有/大城市没有的,这里也有许多”的“非故乡”。对“非故乡”化的乡愁,诗人谭宁君是否定与批判的。
我想定制一条小径,迤逦起伏/恰好容纳我的脚印/每次,脚掌触底的瞬间/可以清晰听到心跳/展臂,鸟一样驾驭炊烟/穿过云层,扶摇而上/消失在大雪覆盖的森林边沿/雪野里,小径与对称的脚印/是森林中最高最大的树。(《我想定制一条小径》)[2]88
“我想定制一条小径”是诗人谭宁君对城市化的“非故乡”否定态度的直白陈述,也是对他记忆中故乡的真切想象与守望。居于城市化的“非故乡”之中,诗成为谭宁君感知原有故乡与回归原有故乡的方式,是他个人生命的吟唱与诗性状态。可见,谭宁君对过往故乡的美好想象和对现时“非故乡”的否定,成为他个人化“寒冷性乡愁”书写的主要情感与态度。
诗是想象的艺术,能够把已经过往的一切想象为在场。这种过往的在场,是诗人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创建与保留,能够组成不同的意义与生命言说。“诗人的本性在于,诗人必须创建持存东西,从而使之持留和存在。”[5]161故乡是过去与正在过去的,决定了人只能以守望姿态面对故乡,使它持久留存于人心中。诗的想象与书写功能很好地进行着这种守望。诗人谭宁君通过对过往故乡的“温暖性乡愁”想象和对城市化“非故乡”的“寒冷性乡愁”陈述,表达了对故乡的守望和保留。谭宁君对故乡两种乡愁的守望,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两种态度对应着不同的乡愁言说与价值探索。
二、 诗性言说
故乡是个很旧很新很复杂的书写对象,一个诗人写好故乡是门技术活。对故乡进行诗性言说,是写好故乡主题的重要方法与策略。在文本中创造故乡诗性,需要抓住能够表现故乡诗性的关联物和因素加以“重复”,以部分的故乡诗性的重复,创造整体意义上的故乡诗性言说。这是一种有效的故乡书写方式,因为重复能够创造诗性。“诗性的一个重要标记是重复某些要素,让这些重复之间出现有趣的形式对比。”[6]159对故乡和与故乡乡愁相关的一切书写,诗人谭宁君以“重复”修辞的方式进行,其创造故乡诗性言说的方式表现为三种,即重复同类意象、重复句式结构及重复主题。
意象是携带有意义的形象,在诗歌文本的内部,意象是重要的诗性言说。意象的诗性是故乡意象背后一种感性的诗性感知,它出现于文本内有强弱之分。想获得明显与强烈的意象诗性,就要加强这些意象诗性的出现频次,即重复使用同类的意象。相近与相似意象的重复运用,组合于一处可以很好地显现意象的意象诗性。以重复同类的故乡意象创造诗性,增加文本内整体的意象诗性,进而呈现诗性故乡与诗意乡愁,是诗人谭宁君诗歌写作的重要特征。
故乡的睫毛上,晾晒了太多期盼/黄玉米,红辣椒,紫色的干豇豆/流苏似的招展,秀发般的飘扬/桔树林也早已经把千万盏小桔灯点亮/故乡太远,高楼绵亘山高水长/故乡很近,子夜梦回总在心上。(《秋天,故乡在更远的远方》)[2]54
远去的故乡,既是时间之远,也是感知之远。重新创造远去之实与感知之远的故乡的诗性,需要多个同类意象的诗性加强来完成。“黄玉米、红辣椒、干豇豆、桔树林”这些同类同性的故乡之物、故乡之意象的重复出现,它们本身具有的意象诗性密集组合于一处创造了远去故乡较强的诗性。“组合重复产生的诗性,是在文本中有规律又有变化的重复某些特征,形成节奏或图案。”[6]153通过这些同类的故乡意象诗性汇聚与组合,已经远去的故乡的诗性近在身旁,对它的诗性言说成为可能。
意象的诗性言说依赖于诗句。诗句语言的诗性张力,远比意象携带的诗性言说具体而强烈。“诗句最开始是在叙说、描写、感觉,也即将注意力引向一个有限的内容,而后来却将注意力引向其自身,引向语言的自为存在。”[7]96进入语言的诗句,所承载诗歌的具体内容及诗句结构都表现出语言本身的诗性。在诗歌文本内,重复使用相同的句式,能够增强某个句式结构具有的张力和言说能力,并以句式间新形成的张力与诗性完成某种情感的强烈道说与叙述。
一年过去,百年过去/千万年过去/豆蔻枝头的羞涩/守候中缤纷凋零/层层落红浇铸,铸成/灿若丹霞的爱情城堡。(《天仙洞鼓耳石》)[2]196
时间是一个诗性概念,也是一个诗性言说的空间。“一年过去,百年过去/千万年过去”,三个重复的句式,三种逆时的时间言说,把感知与想象推向时间诗性的远方。在这种悠远的感知与想象里,“天仙洞鼓耳石”的自然生成状态和历史情感成为一种时间的诗性言说,呈现故乡的时间之美。
那就牵手一起幸福的沉陷吧/把我们沉到生活的底部,再向天空上升/一边沉陷,一边与水和泥土交换心情/一边上升,一边将日月意念为两枚戒指/我带一枚,你带一枚/此后的日月,我们联袂书写平凡的浪漫。(《在美丽的沼泽中幸福沉陷》)[2]080
故乡是一个深度的感情空间,这个情感空间联系着人对日常生活的全部感知。书写故乡就是要呈现这个情感空间的诗性部分,用这种美好的诗性装饰平凡生活,赋予生活诗性的意义。“一边沉陷,一边与水和泥土交换心情/一边上升,一边将日月意念为两枚戒指”,在这两个重复的句式里,诗人对故乡的水、泥土、日月的情感想象与言说,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命态度与感觉用于平凡生活的浪漫言说。
从形式上看,故乡或乡愁是一个书写的主题。面对明确主题,最好的书写策略是系列的主题写作。对宽泛的故乡主题写作,需要集中选择具体的主题内容加以合理驾驭。“当一部作品、或一个人的全部作品,并非通过其所有品质而只是通过其中某一点或某一些对某人起作用时,这就是影响获得最有意义的价值的时候。”[8]198在个人密集的故乡书写中,重复“秋天”这一丰富而诗性的指称内容是诗人谭宁君对故乡主题的书写策略。我们看到,“秋天”主题书写成为诗人谭宁君故乡书写中最有显性价值的部分。
想给老屋前慵懒的芭茅捋捋乱发/想给小桥下淘气的溪流擦擦汗珠/想给半山腰贪睡的云雾抻抻裙裾/回家的渴望在菊花的手影上怒放/新稻米蒸的饭,老南瓜煮的汤/稔熟的乡音敲打碗沿脆生生的响。(《秋天,故乡在更远的远方》)[2]54
秋天是一条空灵的返乡之路,它再现诗人曾经的回家场景,再现诗人家乡熟悉的老屋、芭茅、小桥、溪流、云雾、新稻米饭、老南瓜汤,再现诗人在家乡里的诗性时光。“也许只有诗人这样的人,他可以很坦诚地说,自己宁可生活在更早的时代而不是现在,而且他知道这么说意味着什么。”[9]239过去的故乡意味着生命最原始的美好,是人非常珍视的生命内容。故乡的诗性言说,必定是故乡过去熟悉风物的诗性言说,“秋天”这个书写场、心灵场能够很好地统摄过去的、已经逝去的故乡的情感风物与诗性感知,从而完成了诗人自身的返乡之旅。可见,秋天是诗人重返故乡式的想象与诗性言说。
远山,依偎着饱满的谷粒沉思/父老乡亲蘸着晚霞打磨弯镰/装谷子的木桶,是奶奶笑得合不拢的嘴/乡亲们的目光也渐次饱满起来/远方的梦,枕着那熟悉的芬芳//秋天,在城里思念稻香/这思念, 是一队勤奋奔忙的大雁/一次次,在我流浪的河流上/为奔忙断句,为生活分行/老屋上的炊烟给我捎来口信/新米饭的味道,升高了异乡寒夜的温度。(《秋天,在城里思念稻香》)[2]57
诗是情感的诗性叙述,“父老乡亲打磨弯镰”“远方的梦枕着熟悉的芬芳”“勤奋奔忙的大雁” “老屋上的炊烟”轻扬,故乡秋天的景象充满着自然与乡村本身的诗性魅力。故乡永远是自然状态的故乡,诗人能够“从和自然共生关系中获得一种深刻的能力:对各种形象的精神回响的熟悉和反省。要去描绘花的感情,动物的感情,溪流和采石场的感情,甚至是星星的感情,它们的源头只可能来自他本人”[9]228。诗人对故乡秋天景象的自然性叙述就是一种诗性的言说,在这种诗性言说里,诗人实现对故乡的诗性回归与认知。
在诗人的感知世界里,有事件,有活动,有收获和期待的秋天代表了故乡,秋天的季节意义也就是故乡诗性的重要内容。重复与故乡感知关联性密切的“秋天”主题书写,就是诗人感应故乡、言说故乡诗性的最好方式。
至此可见,重复故乡同类意象,重复故乡诗性句式结构及重复特定故乡主题是诗人谭宁君进行故乡诗性言说的主要方式。在关于故乡的意象、句式及主题里,谭宁君完成了对故乡的诗写和诗性言说,完成了他对故乡与故乡乡愁的诗性守望。
三、 心灵价值
诗是一种有意义的书写,每个诗人的书写都会创造个人化的意义世界。意义是诗歌书写的直接结果与价值显现。“我把用声音歌唱逐渐集中到以文字歌唱,或许我的这些文字组合的音符、节奏、旋律并不优美,但是它们起到了我用声音歌唱同样的作用,让我在生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3]后记诗人谭宁君以诗歌文本的歌唱与诗性言说作为个人诗写的意义追求,作为他对故乡和乡愁的思考形式。我们看到,对乡愁的守望,对重庆、四川“南高原”地域的记录,对个人生命意识的道说是谭宁君诗歌写作创造的三个主要意义领域。这三个意义领域表现着诗人谭宁君故乡和乡愁书写的心灵价值。
诗歌创造出的意义,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可靠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接近真物、真事和再现过去现实的特性。出于强烈、急切的意愿,书写故乡,守望乡愁,两者创造出的承载着故乡与乡愁的诗歌话语与意义,直接由写作者的心灵转化而来。诗歌书写是一种即时形而上学,反映人即时的体验与内心世界,“包含了对过去的重新思考,这些思考是出于现今的急切需要,或者是对现今所有的一些术语的重新斟酌,因为这些术语往往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10]255。在诗人的意识世界里,这种话语是稳定的、不可丢失的心灵意识。诗人谭宁君眷恋自己的故乡,诗歌中的故乡与乡愁是他生命意识中不可丢失的心灵意识而被时时守望。
必须屏住呼吸,并竭尽全力/让一段回忆分娩,并保证顺产//一行雁,或者一只雁/都可以画龙点睛,灵动秋水长天//枫叶内心的火苗,点燃血脉,骨骼/痛快的的焚烧中,我们匍匐在地//聆听猎猎西风血性的诉说/岁月的鱼尾纹里,回忆沉积为种子。(《秋天素描》)[2]56
守望乡愁就是要在内心里找出关于故乡的记忆,并呈现这些记忆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找出与呈现对诗人来说是“分娩”的行为,在“屏住呼吸”的冥想、幻想及“竭尽全力”的身体感知与诗歌技艺创造下,故乡的“一行雁,或者一只雁”、土地、风声变成内心之中故乡记忆的“种子”,被诗性地道说出来,形成故乡与乡愁可靠的心灵价值。
纵使神山 面对科技含量丰富的现代巫术/也只有惊慌失措 挣扎撕裂的身骨/亘古冰瀑 是神山圣女的万丈泪水/在喧嚣的寂静中默哀 喑哑哭诉。(《游人脚下的神山》)[2]131
“神山”“圣女”是人的精神寄托对象,而在被科技的“现代巫术”改造过后,它们已经淡去了作为人精神象征的意义,沦为城市化进程的“副产品”。在不局限于个人固定村落的故乡写作的诗人谭宁君看来,城市化是故乡最快的消逝方式,它滋生了让人更加担忧的现代乡愁。对故乡、故乡乡愁及城市化的现代乡愁进行守望,是诗人谭宁君个人化的内心坚守,也是现代社会普遍的共同心愿。谭宁君的诗歌写作在创造与坚守着自我和社会的故乡与乡愁应该具有的心灵价值。
诗人的故乡是一个具体的村落,也可以是一个省份的地域范围。这个故乡的大小,取决于诗人本身感知世界与诗人诗歌书写的能力。诗人对故乡的情感和经验感知可以由小及大,对故乡诗性言说的对象也可以由小及大。在小故乡到大故乡的转换之间,诗人才能真正地完成对心中故乡、记忆故乡的想象与记录。近年,对自己生活与行走的重庆、四川“南高原”地域,诗人谭宁君先后完成了《川南行吟》《川北行吟》《羌山纪行》《青铜高原的侠骨柔情》《蜀山四季写意》等系列组诗创作,以“长居”与行走见证的生命与心灵姿态进行着对四川“南高原”地域诗性记录。
在组诗《川南行吟》中,诗人谭宁君以诗的形式呈现了他在川南之行的所见所感。在书写对象为古蔺、黄荆老林、八节洞、凤凰湖、天仙洞、尧坝古镇、笔架山等的诗作中,谭宁君对故乡的心灵守望已变成对川南地域古蔺、黄荆老林、八节洞、凤凰湖、天仙洞、尧坝古镇、笔架山的心灵记录与心灵守望。
一潭如梦,枕长江之高崖静谧/是我凝思的伊人,在精心存盘/阳光融化的清脆,以及/在黑土中顽强渗透的淅沥/还有洗涤灵魂拍浪而歌的痛快/还有一篙惊碎飞珠溅玉的鸟啼。(《寻梦凤凰湖》)[2]195
海德格尔说:“诗宛若一个梦,而不是任何现实,是一种词语游戏,而不是神秘严肃行为。”[11]37梦的意识与梦的诗感给诗歌书写创造了一种深度的现实,似真非真的梦是人心灵的深度述说与再现场域。在梦境般的身心感知里,凤凰湖的湖水、竹篙、鸟鸣成为心灵之中故乡湖水、竹篙、鸟鸣的再现之象。眼前凤凰湖的怀想与记录,不仅连接着原来故乡记忆,更是对更大一种“故乡”的建构与记录。我们看到,通过梦的书写意识,诗人谭宁君超越原有故乡记忆的“大故乡”形象得以完成与呈现。
诗不仅承担着人的某种主题叙述,更重要的意义是呈现一个“完整的人”。诗是人进行的语言艺术,“一旦人在心灵中真正感觉到,语言不仅仅是实现相互理解的交流渠道,而且也是一个实在的世界,即一个精神必须通过内部创作活动在自身和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世界,他便走上了一条恰当的道路,能够不断地从语言中汲取到新的东西,不断地把新的东西赋予语言”[12]209。这决定了诗是在语言中展现人心灵世界的艺术,是在语言中道说人的个别时刻和个别状态的艺术。它的功能与展现主体最终要着落于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应和”之处,以揭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谭宁君写道:
风来了!香气开始弥漫,唤醒忘却的我/游弋娑婆世界,邂逅属于我的拈花使者/香气竟还是那年一样浓稠/终于黏合了你给我的伤口。(《木槿花的香气黏合了我的伤口》)[2]58
吹风、喝茶本是人日常的一个生活细节,但就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细节里,因为风,或是茶,诗人进入了一个个人的个别时刻、个别状态之中。这个个别时刻、个别状态的人往往是一种心灵意识的“创伤时刻”“创伤状态”,这是一个“完整人的”最深度、最本质的创伤与状态。诗人进行诗歌书写,表面上看是进行日常情感的宣泄与释放,本质上是以诗歌进行心灵的诗性“治疗”,及更高层面上的生命意识建构与道说。凭借诗歌,诗人谭宁君无形中呈现了最本质的生命意识与内心世界。
“寻根归家可以说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取向和情感体验。家园意识,更是农耕民族传承久远、底蕴深厚的原型基因。”[13]故乡是一个地点,更是心中之“乡”。因为故乡的过去性、变化性,消逝的真实故乡会慢慢变成人的乡愁意识与情感。对心中的故乡之“象”,诗是最好的表达与言说方式。要适宜地言说心中故乡之“象”,就是引出超越原有故乡的内容,引出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故乡书写,包括乡村和城市化的乡村两个范畴。诗人谭宁君以诗性言说的方式,不仅完成了他对原有故乡重庆开州、城市化乡村及四川“南高原”地域的完整故乡书写,实现了他对故乡与乡愁的心灵守望,更由此进行了个人的更高层面上的生命意识建构与道说,为当代的故乡书写增添了一些新意。
[ 1 ]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 2 ] 谭宁君.守望乡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
[ 3 ]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 ] 张媛.共名状态下“母亲”的伦理困境——社会学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34-141.
[ 5 ]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6 ]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7 ] 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8 ] 瓦莱里.文艺杂谈[M].段映红,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9 ] 哈罗德·布鲁姆.读诗的艺术[M].王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 苏珊·斯图加特.诗与感觉的命运[M].史惠风,蔡隽,译.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13.
[11]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 张媛.何处是吾乡——《同胞》中两代旅美知识分子家园意识对比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24-130.